鼠疫、远征与全球化
2020-03-24威廉·麦克尼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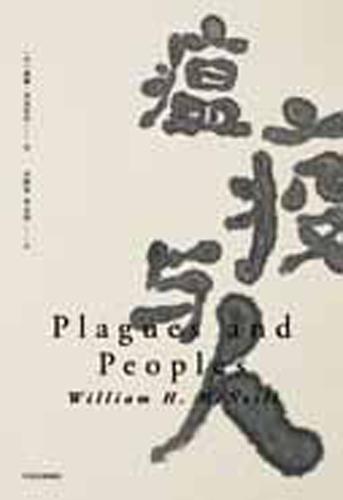
故事开始于中国腹地。
早在公元纪年之后几个世纪(抑或更早时代),鼠疫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喜马拉雅山地区就已作为地方病扎下根来。
欧洲和中国的鼠疫大流行以及军事政治动荡,直接导致远东和西欧的人口急剧减少,既出现在公元初期,又出现在 14 世纪。两地之间的广大地区,不管是疫病史还是人口史,若要想全部搞清楚,的确困难重重甚至是没有可能。
没有人确切知道亚欧大草原上穴居的啮齿动物何时变成了鼠疫的携带者。它们在传播鼠疫上的作用,直到1921—1924 年,才被一个派往中国东北地区调查人类鼠疫的国际传染病专家小组发现。
隐匿的推手
大草原啮齿动物的感染,始于13 世纪中期,那是蒙古征服者第一次靠机动的骑兵在云南—缅甸和蒙古草原之间构筑起通道之后不久。
对蒙古草原的感染,肯定不等于对整个亚欧大草原的感染,这需要时间。可以想象,在将近100年的岁月里,鼠疫杆菌在亚欧大草原上到处蔓延,从一个啮齿群落传到另一个啮齿群落。
一种假设是,在 1253 年蒙古军队从远征云南—缅甸的行动中撤回不久,鼠疫桿菌就侵入到蒙古的野生啮齿动物群落,并逐渐转化成地方病。随后几年,随着受感染的老鼠、跳蚤和人无意识地把杆菌传播到新的啮齿群落,它就向西沿着大草原扩张,其间,有时也因人类活动而加速。在1346 年前不久,啮齿动物的地方病传染圈开始达到其自然极限。
不过,重构以上事件总体上似乎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的文献记录中,并未显示 1331 年之前有何异常,而在那一年,河北的一场瘟疫据说杀死了 9/10 的人口。直到 1353—1354 年,才有资料表明出现了更大范围的灾难,流行病肆虐于中国 8 个相距很远的地区,编年史家说,有多达“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
即便考虑到蒙古人对中国的长期征伐(1213—1279 年),使得地方混乱和行政崩溃而中断历史记录,我们也很难相信会有任何真正大规模的病亡能够逃脱史籍编纂者的注意,而他们对于灾难的记录,则是为今人提供有关中国瘟疫史的唯一依据。
我们只能假定,在1346年致命袭击了欧洲的鼠疫,在中国的出现不会早于 1331 年 。
在1331年,尤其是1353 年之后,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的灾难期。鼠疫与汉人反抗蒙古统治的内战结伴而行,汉人终于在 1368 年推翻了外来统治,建立了明王朝。战争与瘟疫的结合无情地蹂躏了中国人口,最合理的人口估计是从1200 年(蒙古入侵之前)的1.23 亿减少到1393年(最终驱逐蒙古人之后的一代)的 6 500 万。
即使是蒙古人的残暴也无法解释如此急剧的衰减,在中国的人口减半事件中,疾病肯定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而腺鼠疫就像在欧洲那样,初次暴发之后便颇为频繁地反复流行,无疑最有可能扮演了这一角色。
亲历鼠疫最初泛滥的阿勒颇 (Aleppo)的穆斯林作家伊本.阿尔.瓦尔迪(Ibn al-Wardi)曾指出,该病起源于“ 黑暗之乡 ”,先在亚洲北部传播,然后侵入文明世界,首先是中国,而后是印度和伊斯兰世界。阿勒颇本身就是一个商队城市,又是 14 世纪横跨亚洲草原贸易网中的一个枢纽,因此是一个获取信息的理想地点。
一种可能是,鼠疫杆菌于1331年现身于中国,或者源自云南—缅甸一带原始的疫源地,或者源自在中国东北地区—蒙古大草原的穴居啮齿动物中新出现的疫源地。之后,鼠疫沿亚洲的商路游历了15 年,才于1346 年传到克里米亚。在这里,鼠疫杆菌登船沿着从海港向内地辐射的路径,继续渗透到近东乃至整个欧洲。
欧洲最初遭受的疫病打击出现在 1346—1350 年,但各地的情况差别极大。有些小社区被彻底毁灭,也有像米兰等一些地区似乎完全未受影响,关于死亡率,最合理的估计是约为总人口的 1/3。鼠疫致命的后果还被下述事实放大:它不仅通过跳蚤的叮咬传播,而且还通过人—人传播,即感染者由咳嗽或打喷嚏将携带病菌的飞沫散播到空中再被别人吸入的方式传播。
至于中国,在 14 世纪以后,这个大国拥有两处易受鼠疫侵扰的边界:一处在西北,与大草原的疫源地接壤;另一处在西南,与喜马拉雅山的疫源地毗邻。然而直到 19 世纪,现有史料并不能区分鼠疫与其他烈性传染病,而那时与喜马拉雅山疫源地相联系的云南疫情最终于1894 年扩散至沿海,其世界性影响已如前述。
在1855 年之前,烈性传染病的流行在中国相当普遍;其中很多应当是鼠疫,但现有史料不足以支持我们做出更确切的判断。尽管如此,1200—1393 年中国人口的减半,用鼠疫解释比用蒙古人的残暴解释更为合理,即使中国的传统史书宁愿强调后者。
中国不可能是唯一遭受鼠疫重创的亚洲地区。有理由认为,在整个喜马拉雅山北部,重大的人口损失出现于14 世纪,那时大草原才刚刚接触鼠疫,当地人还来不及适应这种致命的疫病流行。
如果我们联想到东部大草原,以 1368 年撤出中国为标志的蒙古人势力的衰落,显然与猜想中的鼠疫蔓延大草原不无关系。有人甚至质疑:与瘟疫尤其是鼠疫的接触日益密切,会不会就是颠覆蒙古人军事力量的真正因素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不难相信,这些游牧在黑龙江河口到多瑙河河口之间的大草原上的人们,正是因为遭遇了烈性传染病才遭受了人口上的重大损失。
我们便不难明了,蒙古人失去了故乡充足的后备人口,他们无论在中国、波斯还是在俄罗斯的军事霸权都难以维系;我们也可以清楚,对于纵横于整个亚欧大陆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正是大草原的疫病经历,加速了他们被自己的农业臣属人口推翻和(或)同化的进程。
1346年后大草原上的政治失序,或许正是源于统治阶层面对鼠疫流行的短视反应。遭受鼠疫骚扰之前,商人和手工业者曾以交纳重税的形式支持了中亚和东欧国家的建立;遭受鼠疫重创之后,人口急剧减少的草原臣民已无力满足统治者的要求了。
可以确定的是,那些从事商品收购、转运和买卖的人对鼠疫尤其敏感。特别是在瘟疫刚刚出现、尚未制定有效应对规范的几十年里,蒙古征服者造就的整个亚欧草原的商队网络,极有可能毁于严重的疫病死亡。
来自大草原东部推论性的证据表明,到17世纪或更早些的时候,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已经学会如何有效地防范鼠疫。不然,满族在 17 世纪 40 年代对汉民族的征服(正相当于以前对大草原的入侵)就不可能发生,而征服的成功又要求兵员众多且军纪严明的满族“旗兵”来支撑新的王朝。
最后,清王朝终于依靠中原地区的雄厚资源征服了西藏和蒙古,并把它们纳入帝国统治之下。这一进程付出的努力极大,直到 1757 年,天花瓦解了大草原上由卡尔梅克(Kalmuks)组织和领导的最后一个战斗联盟,清朝军队才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一征服记录意味着,到 17 世纪中期,东部大草原仍保持或重新获得了自己的人口强势,以维系他们面对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时的传统角色。何以如此,确切原因自然无从知晓。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医学观察者在中国东北地区和蒙古认识了鼠疫杆菌的生存环境,研究了它与人类、土拨鼠和其他穴居啮齿动物的关系之后,当地社会逐渐形成了有针对性的卫生习俗,有效防范了人类被疫病感染。
盲目的漫游者
19 世纪早期,萨尔温江上游构成了感染区与未感染区的分界线。后来,1855 年云南爆发了起义,中国军队跨过萨尔温江前往镇压,由于未意识到鼠疫传染的危险,染病后的军人就把它带往各地。此后,鼠疫接连暴发于中国内地各处,但未引起外界的注意,直到1894年该病传至广州和香港,给当地的欧洲居民带来了恐慌。
1894 年,细菌学说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鼠疫在中国的出现,激活了欧洲梦魇般的民间记忆,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年,法国细菌学家)和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年,德国细菌学家)的弟子们,急切地要去揭示其传播的秘密,国际研究小组于是被派往现场。
仅在他们到达香港的几周内,一名日本和一名法國的细菌学家,分别发现了鼠疫的病原体,即鼠疫杆菌(1894年)。在随后10 年间,从事这项研究的国际医疗特遣队在香港、孟买、悉尼、旧金山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众多地区展开研究,鼠疫杆菌从啮齿动物经过跳蚤传到人类这一过程的诸多细节,随之逐渐浮出水面。
在鼠疫出现在香港的10年里,世界所有的重要海港都经历了这一可怕疫病的袭击。这一事实,也不断强化了国际社会对鼠疫的关注。在大多数地方,传染很快被遏制了;但在印度,鼠疫却深入内地,在它到达孟买(1898年)的10年中造成大约600万人的死亡。
鼠疫接连不断地小规模暴发,以及有可能给欧洲、美洲和非洲带来重大灾难的风险,激发了每个受威胁地区研究鼠疫的渴望。
最具意义的发现之一便是,在美国、南非和阿根廷,穴居的野生啮齿类动物群落甚至比人更容易感染鼠疫杆菌。1900 年加利福尼亚的地鼠最先被发现感染了鼠疫,同年,该病局部地流行于旧金山的华人当中。鼠疫在人群当中很快消失了,但杆菌仍兴盛地存活于地鼠之中,并一直持续至今。
在不到10 年的时间里,类似的传染病在感染了南非的德班(Durban)和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后,又很快在德班以外的南非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外的阿根廷的穴居啮齿类动物群落中被发现。
上述啮齿动物在种类上存在区域性差异,与亚洲穴居的啮齿动物群落也不尽相同,但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啮齿动物的洞穴里,不管混居着哪些种群,对杆菌的态度都被证明是“友好”的。
事实上,自从这种传染病在旧金山外围地区首次出现后,北美受感染的地区逐年增加,到1975 年,美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了疫源地,并且扩展到加拿大和墨西哥。如此广阔的感染区域,事实上不比旧大陆任何长期的疫源地逊色。
考虑到穴居啮齿类动物生活方式的改变,产生了疫病从一个地下“城市”传播到另一个地下“城市”的条件,鼠疫在北美的地理扩张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事。当啮齿类动物的幼崽稍稍长大时,它们就被父母逐出老洞穴,到处乱窜,甚至干脆远离群落,漫游几英里寻找新家。
这些盲目的漫游者,一旦发现新的啮齿动物群落就会企图加入。这种生活方式给它们提供了交换基因的绝佳途径,也使它们从中获得了众所周知的进化优势;但也为群落间的疫病传播创造了条件,这种传播速度高达每年 10~20 英里。
此外,人类活动亦加快了鼠疫在北美啮齿动物中的传播。牧场工人把生病的啮齿动物装进卡车,以运到数百英里以外,目的是让它们把致命的鼠疫传染给那里的草原松鼠,尽可能地消灭它们,为牲畜留出更多的牧草。然而,北美鼠疫的传播在受这类行为影响的同时,却并不限于人类的干预。结果,到 1940 年,美国全部穴居啮齿动物至少有 3/4 的种类都携带鼠疫杆菌,各类跳蚤中也有 3/5 被感染。
1900 年后,在北美、阿根廷和南非,人类鼠疫继续零星出现,患者的死亡率大约稳定在 60%。
直到20世纪40 年代出现了抗生素,只要及时确诊,治疗就变得既容易又保险。而生活在美国和南非半干燥平原的牧场工人和其他居民,不同的生活习性使他们远离杆菌流行的啮齿—跳蚤群落,所以在新感染的地区,人类鼠疫的发作次数不多,且尚未引起社会注意,特别是地方当局面对辖区内流行如此可怕的疫病,第一反应往往是遮掩事实。
土拨鼠与新规则
1911 年,一场大规模的人类鼠疫暴发于中国东北,又复发于 1921 年。新的国际行动被迅速组织起来以遏制疫情。
随后的调查表明,人类鼠疫源自土拨鼠。土拨鼠体形硕大,其皮毛可在国际市场上获得高价,与新近感染的地鼠和北美其他啮齿动物一样,它们的洞穴也往往是鼠疫杆菌的幸福家园。
在土拨鼠出没的大草原上,游牧部落自有一套习俗以应对感染鼠疫的危险。这套习俗从流行病学上看相当合理,只是在解释上带有神秘色彩。
根据这套习俗,土拨鼠只能射杀,设陷阱则是禁忌;活动懒散的要避免接触。如果看出哪个土拨鼠群落显出生病的迹象,人们就要拆掉帐篷远走他乡以躲避厄运。很可能就是靠了这些习俗,草原上的人们才降低了感染鼠疫的概率。
1911年,随着清王朝的土崩瓦解,长期禁止关内人移民中国东北地区的官方规定不再被遵守,毫无经验的大批关内移民追随土拨鼠的皮毛而去。由于对当地习俗一无所知,移民对土拨鼠一律设陷阱捕杀,结果鼠疫最先在他们中间暴发,并使哈尔滨市迅速成为鼠疫中心区,然后从这里出发,沿新建的铁路向外扩散。
1894—1921年的一连串事件,都发生在具有职业敏感的医学小组的眼皮底下,他们的工作是研究如何有效控制鼠疫,也的确成功地弄清了鼠疫的传染途径和传播路线。
没有这些研究和随后的预防性措施,20 世纪的地球就可能任由鼠疫蹂躏,由此造成的死亡将令那些查士丁尼时代留下的记录相形见绌,甚至 14 世纪肆虐欧洲和旧大陆的黑死病,也无法与之相比。
审视已知的 19—20 世纪人类与鼠疫的对抗过程,有必要指出以下三点:
其一,19 世纪70 年代出现的汽船航线网,是将鼠疫扩散到全球的便利渠道。
事实上,一旦鼠疫出现于广州和香港,其传播的速度就只受限于轮船把受感染的老鼠和跳蚤带到新港口的速度。传染链如果能从一个港口延伸到另一港口而不被切断,速度显然是关键。既然鼠疫杆菌会使幸存者产生免疫力,它在船上的老鼠、跳蚤和人类宿主中的存活就很難坚持数周以上。
在航海时间太长、大洋太宽的过去,鼠疫杆菌无法在船上长期存活,更谈不上登陆美洲和南非的港口,在那里找到安身之处了。但是,当汽船更大、更快,或许还携带了更多的老鼠,便将传染链拉得更长,跨越大洋顿时就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了。
其二,船上感染的老鼠及其跳蚤,不仅把鼠疫传染给港口上的人,还传染给它们在半干旱地区的野生远亲。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阿根廷和南非,野生状态的鼠疫潜在宿主种群已经存在了无数代。要产生新的疫源地,所需的只是杆菌赖以跨越地理障碍(此处指海洋),蔓延至已有适量穴居啮齿动物的新地区的途径。穴居的啮齿动物,尽管在种类和习性上存在很大地域性差别,但它们既易于感染又能维持传染链永不中断。
自从医务工作者开始观察到这类现象,重要疫病就未再发生地理上的意外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类似的突变没有发生过。相反,19—20 世纪的鼠疫史提供了这种变化的范例和模式,一旦阻碍鼠疫杆菌扩散的既有障碍被突破,它就会极其迅速地占据新的领地。
实际上,无论变化看起来多么突然,鼠疫的最新胜利也依然是一种正的生态现象。因为某个生态龛一旦空出,通常很快就会被某种人类或非人类的有机体占领,并据以繁衍生息。
其三,在中国云南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当地人当中同样存在的古老习俗,似乎相当有效地阻止了鼠疫对人类的感染。
尽管这些地区的啮齿动物洞穴中始终存在着鼠疫杆菌,但只有当新来者不再遵守当地的“迷信”做法时,鼠疫才成为人类的问题;而且对传染病一无所知的外来者对当地的侵扰,还经常伴随着军事—政治动荡,这类动荡在过去也经常引发疫病灾难。
从云南和东北的民间习俗在鼠疫防范的有效性上,我们可以看出,1894—1924年成功发展起来的医学预防措施,不过是人类应对疫病危机的正常反应,只是更为迅速和科学有效而已。
在过去,人们总是习惯于容许神话和习俗通过试错法,来确定一套可接受的人类行为方式,把疫病限制在可容忍的范围内,但科学的医学不再如此,而是就新的行为规则达成共识,并动用“国际检疫规则 ”这一全球性的政治框架,来强制推行新规则。
就这一角度而言,20 世纪的医学和公共卫生管理的辉煌成就,看起来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富有创意;尽管这个世纪应对鼠疫的医学措施的有效性,远远超过了以前限制疫病肆虐的那些方式。事实上,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可以事先制止这些流行病,而这些流行病本来可能抑制甚至扭转人口大量增长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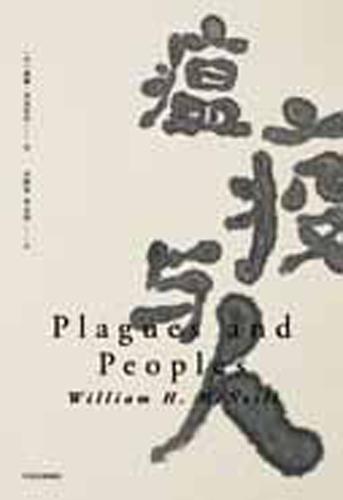
本文选编自《瘟疫与人》,威廉·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中信出版社授权刊载,2018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