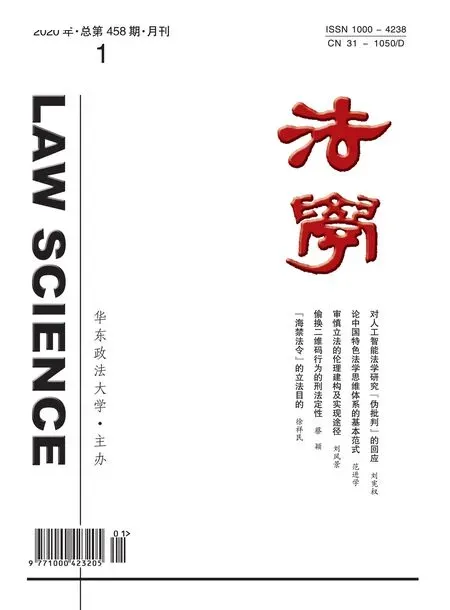市场操纵犯罪司法解释的反思与解构
2020-03-23谢杰
●谢 杰
一、问题意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6月28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操纵市场司法解释》)。市场操纵是金融市场犯罪中行为结构最为复杂、理论解释与实践认定最为疑难的犯罪类型之一。《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的出台,有利于推进司法实务部门更为公正、准确且有效地认定《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兜底条款”中的“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实际控制账户、市场操纵“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量化标准、违法所得等证券期货犯罪刑法理论与实践中长期存在争议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的实施对于依法惩治证券期货犯罪,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保障科创板改革有序开展,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1〕参见姜佩杉:《“两高”公布关于证券期货犯罪司法解释 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载《人民法院报》2019年6月29日,第1版。
然而,由于法律与金融跨学科知识的交叉性与纵深性、金融市场机制的创新性与技术的前沿性、市场操纵犯罪司法实践问题固有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科创板试点注册制的探索性与改革性,〔2〕参见侯捷宁、苏诗钰:《易会满:在新的起点上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载《证券日报》2019年6月14日,第A2版。实际上已经明显超越了单一学科框架下证券期货犯罪刑法理论的预期以及传统司法解释的逻辑准备与技术能力。因此,有必要针对实际控制账户的认定、特定市场操纵模式的判断规则、市场操纵定罪量刑的数量标准、违法所得的计算方法等重大且疑难问题,就《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相关条款进行批判性审视与建构性优化。
对市场操纵犯罪司法解释进行深刻反思与细致解构,不仅有助于推动证券期货犯罪刑法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升级,而且有利于为正在推进的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提供坚实且具体的司法保障措施。〔3〕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0日出台的《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审理证券期货犯罪刑事案件的政策导向:依法从严惩治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内幕交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金融犯罪分子,严格控制缓刑适用,依法加大罚金刑等经济制裁力度。更具价值的是,以法律与金融的双面向视角解析市场操纵犯罪司法解释,进而形成的完善意见与补充规则,能够在《证券法》大修和加快推进《期货法》制定的关键时刻、《刑法》证券期货犯罪条款协调修正的重要节点,提供立法参考。基于此,本文尝试反思与解构最新市场操纵犯罪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规则优化建议,以期对金融立法与司法及时应对证券期货犯罪的挑战有所裨益,同时希望通过精细化的制度安排更好地实现资本市场效率与投资者权益的协调和统一。
二、市场操纵刑事案件中实际控制账户的认定问题
实际控制账户的认定是市场操纵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只有明确可以归属于特定行为主体的账户范围,才能将之作为潜在的操纵主体及其操纵行为进行刑法评价。《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5条所设置的核心标准是:(1)区分本人账户与他人账户。(2)实际控制他人账户表现为:控制资金流动并承担损益;行使管理权、支配权或者使用权;基于投资或者协议方式行使交易决策权;基于其他方式行使交易决策权。(3)以没有交易决策权作为免责事由。〔4〕《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5条规定:下列账户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82条中规定的“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一)行为人以自己名义开户并使用的实名账户;(二)行为人向账户转入或者从账户转出资金,并承担实际损益的他人账户;(三)行为人通过第一项、第二项以外的方式管理、支配或者使用的他人账户;(四)行为人通过投资关系、协议等方式对账户内资产行使交易决策权的他人账户;(五)其他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具有交易决策权的账户。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账户内资产没有交易决策权的除外。可见,司法解释在吸收证券监管文件相关条款〔5〕参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指引(试行)》(证监稽查字〔2007〕1号)(以下简称“《操纵认定指引》”)第8条规定:利用他人账户操纵证券市场的,利用人为操纵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前款所称利用他人账户:(一)直接或间接提供证券或资金给他人购买证券,且该他人所持有证券之利益或损失,全部或部分归属于本人;(二)对他人持有的证券具有管理、使用和处分的权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实际控制账户的核心判断依据是对他人账户的交易行为具有决策权。这确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刑法实质判断规则,将普遍认为具有隐蔽性的操纵交易关联账户予以有效且全面的规制,并通过例外规则允许辩方提供排除交易决策权法律属性的证据进行反驳。实践中比较典型的控股关系、投资关系、代持关系、融资关系、委托代理关系、近亲属或者关系密切人的身份关系等,在司法解释做出了上述规定之后,基本不会出现较大争议。但上述司法解释仍不乏重大疑问。
(一)司法解释“交易决策权”标准的困境
《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5条不仅没有对“其他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具有交易决策权的账户” “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账户内资产没有交易决策权”中的“有证据证明”提供方向性的证据规格指引,而且并未就证券、期货市场中交易结构相对复杂的账户类型提供明确的判断指引。
一是信托计划项下的证券账户。在典型的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交易结构中,投资者委托信托公司担任管理人并从事相关证券交易,信托公司进一步委托各类专注于二级市场交易的私募机构担任投资顾问。在具体交易时,投资顾问通过软件向管理人下达投资建议指令,信托公司基于风控指标、管理人职责等选择接受或者拒绝投资顾问的建议;接受建议的,信托公司根据建议指令,在信托计划对应的证券账户下达交易指令。如果相关证券账户中特定交易行为构成市场操纵——投资者虽然是信托计划受益人,对于账户资产享有投资权益,但显然不是账户实际控制人。信托计划管理人(信托公司)尽管是证券账户的客观交易主体,但交易策略并非由其制定,很难将证券账户中的操纵性交易归责为信托公司的实际控制行为。根据《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5条的“交易决策权”标准,真正形成并提出操纵性交易策略与建议的投资顾问,能否构成对案涉账户的实际控制,实际上存在极大争议。投资顾问的行为性质是投资建议,权利属性是交易建议权,所以,将信托计划投资顾问认定为对信托公司管理的、投资者享有财产权的账户具有“交易决策权”,不无疑问。
二是各类场外衍生工具挂钩的自营账户。在场外个股期权、〔6〕关于证券公司场外期权业务的内容及其监管标准,参见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公司场外期权业务监管的通知》(证监办发〔2018〕40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通知》(证监办发〔2016〕81号)等监管文件。股票收益权互换〔7〕股票收益互换通常是指客户与证券公司互为对手方,双方通过合同约定,在未来特定期限内,就特定股票的收益表现与名义本金的固定利息进行现金流交换。See John C. Hull, Options, Futures, and Other Derivatives (6th Edition), Prentice Hall, 2006, p.1.等各类场外衍生工具交易中,证券公司通过场外交易专用的自营账户进行个股风险对冲交易。以实践中常见的股票收益权互换交易为例,客户向证券公司就其收益权互换账户的交易发出指令(买入或者卖出挂钩股票标的),证券公司根据风控指标、合规要求或者其他全权自主认定的因素,决定接受还是拒绝互换交易指令;证券公司选择接受并执行指令的,互换交易双方采用现金净额进行结算;证券公司有权根据互换交易指令决定是否在自营账户中进行对冲交易,如进行对冲交易的,互换交易成交价格以甲方对冲交易实际成交结果为准。可见,在客户与证券公司互为对手方的场外衍生工具交易中,客户在系统中下达的是互换要约、买入或者卖出期权要约等衍生交易指令,证券公司针对挂钩股票在其自营账户中进行对冲交易。从法律关系上分析,似乎是归属于券商独立决策下的自营交易行为。但实践中确实存在且已经查处了部分客户利用场外衍生工具交易作为“通道”实施市场操纵等违法行为的情况。〔8〕参见蔡奕:《证券创新交易模式对市场监管的挑战及法律应对》,载《证券法苑》第11卷,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页。如果客户下达的收益互换、期权交易等衍生交易策略具有操纵性,而证券公司又根据衍生交易指令在其自营账户中对挂钩股票标的进行实时完全对冲交易,〔9〕实时完全对冲策略在场外衍生工具交易实践中通常是指,客户通过互换交易操作终端发出互换交易申请,并通过证券公司风控审核,证券公司在其专用的自营对冲账户中买入或者卖出相同数量的标的股票,将标的股票的交易收益按照合同约定的现金交割模式与客户进行结算。根据“交易决策权”标准,由于自营账户的交易决策、盈亏风险等均归属证券公司,能否认定客户对于终端买入或卖出股票的证券公司自营账户形成实际控制,值得商榷。
《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5条将实际控制账户的核心依据定位于“交易决策权”,其内部逻辑进路是稳定且自洽的,即尝试在“隐蔽”的操纵性交易中,基于主观意图与实行行为相统一的“决策”概念来锁定异常账户之间的实质关联。但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一旦遭遇结构复杂且合约设计精细的金融交易,司法解释便容易陷入困境——对下达投资建议或者衍生交易指令的客户不予认定其实际控制证券账户,存在市场操纵刑法规制不力的风险;基于“其他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具有交易决策权的账户”的“兜底条款”认定其实际控制相关账户,又与显而易见的部分证据〔10〕在此类案件中,合同等书证通常显示,行为人只是投资顾问或者衍生交易对手方,这样的合同主体身份不可能得出实际控制证券账户的证明结论。与法律解释〔11〕投资顾问建议权通常不能直接解释为信托计划项下对证券账户的决策权,客户的互换交易指令权通常也不能直接解释为对证券公司进行对冲的自营账户的决策权。相矛盾。
(二)解锁困境与排解矛盾的具体路径
刑事司法实践有必要还原真实的证券、期货市场交易逻辑与场景,在厘清复杂金融交易民事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完善认定实际控制账户的证据规格,回归实控关系的“行为”本质而非“权利”依据,针对金融行为做出刑法实质判断。
第一,通过交易所大数据分析系统监控异常证券账户组,据此调取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留存的客户交易数据,以客观的金融交易及其账户信息将“隐蔽”还原为“透明”。
信托计划、场外衍生工具等复杂金融交易确实具有隐蔽交易主体与持仓规模的金融功能。〔12〕See Henry T.C. Hu & Bernard Black, The New Vote Buying: Empty Voting and Hidden (Morphable) Ownership, South California Law Review, 79 (4), 2006, p.825.例如,股票收益互换交易只对收益进行现金流交换,不需要进行股票实物交割,股票实物交易的实施、股票的投资者权益均归属于证券公司,作为交易对手方的客户表面上是“隐蔽”的。尤其是我国证券、期货市场充斥着类型繁多的通道业务,券商、保险、信托等都可成为各种资金进出股市、债市、期市的管道。尽管“资管新规”执行一年多以来通道业务明显收紧、收缩,〔13〕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号)明确规定:金融机构不得为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提供规避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但毕竟层层嵌套的金融交易结构并未全面禁绝,通道业务的客观存在进一步加深了操纵性交易形式上的隐蔽性。
然而,当前我国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模式与技术能力,已经足以将看似“隐蔽”的账户及其操纵性交易还原为透明的客观数据。一方面,看穿式监管切实提高了市场监察效率、加强了市场风险监测,能够有效识别特定投资者对应的不同账户的交易、持股等信息。〔14〕参见皮六一、薛中文、刘苏:《看穿式监管的国际实践及主要模式研究》,载《证券市场导报》2019年第1期。另一方面,随着交易所大数据分析已经提升至每秒百万笔以上的信息处理水平,数据监测在对象、手段、模式、管理、资源等方面均实现了重大转变,违规监测模型更加智能化,能够支持不同金融产品的差异化监察、跨市场监察。〔15〕参见深交所综合研究所:《丰富监管手段,加强交易监控和风险管理》,载《证券时报》2018年9月18日,第A12版。交易所自律监察、证券行政监管、刑事司法有必要在线索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实现案件移送与证据移交,以交易所移送异常交易数据与调取金融机构客户交易信息为核心,还原交易者、各类通道、证券账户客观且透明的金融数据,尤其是将以投资顾问、场外衍生交易等间接形式参与证券、期货交易的IP地址、Mac地址、投资建议指令、场外衍生交易指令等数据与对应的金融机构账户信息进行比对,供司法机关进行法律判断。如果投资顾问建议指令、场外衍生交易指令的网络协议、时间、价格等数据均与金融机构实际交易证券、期货的账户数据高度一致,或者金融机构接受客户指令、账户执行交易比率极高,则可以作为投资顾问、场外衍生交易对手方等行为主体实际控制他人账户的初步证据。
第二,复杂金融交易结构所内含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市场操纵刑事案件法律适用的基础,可以将民事法律关系背后所隐藏的异常要素作为补强证据方向,但不宜以“权利”依据为导向设定实际控制账户的核心判断规则。
无论是普通市场参与者还是涉嫌市场操纵的主体,其实施相关金融行为都必须借助于一系列合约安排。刑事司法分析相关账户是否受到特定行为主体控制,还是需要依托于民事法律对基础法律关系、权利义务要素等进行判断。刑法评价不宜直接超越或者打破民事法律框架,否则会造成刑法过度介入证券、期货市场,妨碍金融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继而导致证券期货犯罪刑事立法、司法解释反倒成了制约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的制度成本。就前述信托计划、股票收益互换等复杂金融交易所内含的民事法律关系而言,信托账户、证券公司自营账户中的权益都不可能在民事法律层面归属于信托计划投资顾问、券商场外衍生交易业务对手方。
以股票收益互换为例——在金融交易的法律属性上,收益权互换交易与股票交易完全不同,场外衍生工具交易主体根本不可能对证券账户行使任何形式的“交易决策权”;在账户的区分层面,客户的收益权互换账户独立于证券公司用于风险对冲的自营账户,客户的控制权仅限于针对收益互换账户发出交易指令,该账户并不交易实物股票;从交易策略角度分析,客户制定的是收益权互换策略,自营账户的风险对冲策略由证券公司全权制定并执行;在投资权益上,自营账户如果买入实物股票,其股权均由证券公司行使。
上述完整的“权利”解释决定了刑事司法不能跨过民事法律判断,直接将客户在收益权互换账户下达指令、证券公司在自营账户中实时且完全按照客户指令进行对冲交易的情形,认定为客户实际控制自营账户。相反,刑法评价应当尊重民事法律关系下的金融交易逻辑,从中发现针对偏离标准民事权利义务模型的“异常”交易的查证方向:(1)客户与证券公司在订立收益权互换合同时,是否明知所有收益互换指令均会基于完全风险对冲转化为自营账户交易实物股票;(2)自营账户买卖股票所产生的交易成本是否均由客户承担;(3)客户提交的收益互换指令经由证券公司风控审核(主要是排除超额交易、ST股票等禁止交易标的等指标)后,是否以极低的时间损耗快速传递至自营账户下达股票交易指令。如果上述查证方向下与金融交易权利义务有关的问题,均能得出肯定性的回答,则可以作为客户实际控制证券公司收益权互换专用自营账户的补强证据。
同时,民事法律关系的“权利”解释逻辑不能成为限定刑法实质解释边界的桎梏。《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5条将实际控制他人账户的核心判断标准确立为“交易决策权”,显然是受到了民事法律解释的过度影响。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的法律,其看待问题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自始至终都会回归至对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恢复和补偿上;刑法与民法有着截然不同的宗旨与视角,刑法在于惩罚行为人破坏法益的行为。〔16〕参见刘宪权:《网络侵财犯罪刑法规制与定性问题》,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4期。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是权利(义务),管理权、使用权、决策权等以“权利”为导向的判断标准完全契合民法判断的逻辑基础。但是,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是行为,刑法判断必须针对行为的实质做出评价。《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5条所规定的“交易决策权”实际上是在刑法判断问题上混用了民法判断标准,容易出现刑法规制不力的风险、刑法判断与法律属性矛盾的困惑。
第三,从实际控制账户的行为本质出发进行刑法评价,《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5条规定的“交易决策权”标准有必要调整为特定行为人对涉案账户交易实施“决定或者重大影响行为”。
信托计划中投资顾问交易建议权与管理人交易决策权的分离,场外衍生工具中客户衍生交易决策权与金融机构自营账户交易决策权的分离,深刻揭示了没有账户“交易决策权”的行为主体,仍然可能存在实际控制从事操纵性交易账户的重大风险。这就要求司法机关需要考察复杂金融交易结构中的投资建议,间接作用于证券、期货合约买卖的衍生工具交易等,是否构成针对案涉账户的“决定或者重大影响行为”,即行为人是否实质上决定了账户的交易或者对之施加了重大影响。所谓决定行为,是指账户中的具体交易可能由金融机构或者其他市场参与者实施,但交易时间、方式、价格、策略、损益等均按照特定行为主体的指令予以确定并执行。例如,在信托计划中,终端投资者的资金来源、信托参与股票二级市场买卖的交易结构、证券交易策略与指令、超额收益的分配等均由投资顾问操作,信托公司仅作为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管道收取“通道费”,投资顾问虽然在合同层面没有限定于管理人的交易决策权,但其投资顾问建议指令均由名义上的管理人全盘采纳并在信托账户中执行相关交易。行为主体对于案涉账户的交易实施了决定行为,可以认定为实际控制账户。所谓重大影响行为,是指虽然没有达到全部决定的程度,但涉案账户的交易时间、方式、价格、策略、损益等指标与行为主体的指令高度一致。例如,在股票收益互换中,客户与证券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场外衍生交易的实质,是为客户提供交易杠杆,双方原则上并非互为交易对手方进行“对赌”,证券公司有权根据客户的收益互换指令在自营账户中进行实时且完全对冲交易,尽管部分收益互换指令因为风控审核被拒绝,或者证券公司发现成为交易对手方的套利机会而没有在自营账户中进行完全对冲,但绝大部分收益互换指令被直接转化为自营账户中的股票实物交易。虽然证券公司自营账户不可能由客户行使交易决策权,但确实构成了对自营账户的交易施加了重大影响,也可以认定为实际控制账户。
三、市场操纵行为模式的判断规则
由于市场操纵犯罪“兜底条款”的刑法解释长期以来一直是证券期货犯罪理论与实践中争议最大的难题,〔17〕参见刘宪权:《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兜底条款”解释规则的建构与应用——抢帽子交易刑法属性辨正》,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6期;谢杰:《资本市场刑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31-238页。《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1条〔18〕《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1条规定: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182条第1款第4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一)利用虚假或者不确定的重大信息,诱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并进行相关交易或者谋取相关利益的;(二)通过对证券及其发行人、上市公司、期货交易标的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并进行与其评价、预测、投资建议方向相反的证券交易或者相关期货交易的;(三)通过策划、实施资产收购或者重组、投资新业务、股权转让、上市公司收购等虚假重大事项,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并进行相关交易或者谋取相关利益的;(四)通过控制发行人、上市公司信息的生成或者控制信息披露的内容、时点、节奏,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并进行相关交易或者谋取相关利益的;(五)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申报、撤单或者大额申报、撤单,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并进行与申报相反的交易或者谋取相关利益的;(六)通过囤积现货,影响特定期货品种市场行情,并进行相关期货交易的;(七)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明确了六种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其他方法”,可谓本司法解释最为重要的条款及亮点之一。〔19〕参见戴佳、徐日丹:《“两高”出台两部关于证券期货犯罪司法解释7月1日起施行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立案追诉标准有六方面修改》,载《检察日报》2019年6月29日,第1版。《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1条具体规定的六种行为模式是:(1)蛊惑交易操纵;(2)抢帽子交易操纵,也就是利用“黑嘴”荐股操纵;(3)重大事件操纵,主要是指“编故事、画大饼”的操纵行为;(4)利用信息优势操纵;(5)恍骗交易操纵,也称虚假申报操纵;(6)跨期、现货市场操纵。〔20〕参见姜佩杉:《依法惩治证券期货犯罪 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两高”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司法解释答记者问》,载《人民法院报》2019年6月29日,第4版。
相对于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追诉标准二》)第39条规定的虚假申报操纵、信息操纵、抢帽子交易操纵等“其他方法”,《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1条不仅新增了蛊惑交易操纵、跨市场操纵的判断规则,而且对抢帽子交易操纵、信息操纵、虚假申报操纵的构成要素进行了重大调整。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其构成市场操纵犯罪的“其他方法”,显然有利于实务部门准确适用《刑法》第182条“兜底条款”,但司法解释中有关市场操纵模式的具体判断规则,仍然存在诸多值得商榷、反思、补充与完善的空间。
(一)蛊惑交易操纵的刑法规制边界
理论上一般认为,蛊惑交易操纵表现为向证券、期货市场及投资者编造、传播、提供、发布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不确定的重大信息,诱导投资者在不了解真实、全面信息的情况下从事相关证券、期货交易,操纵者通过预期的证券、期货市场价格波动谋取交易利润。〔21〕参见钱列阳、谢杰:《证券期货犯罪十六讲》,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334页。需要注意的是,蛊惑交易操纵是一个包含违法与犯罪两种危害层级的概念。利用虚假信息从事操纵性交易显然属于蛊惑交易操纵犯罪的规制范围。但基于不确定信息等非虚假类信息实施的市场操纵行为能否纳入刑法规制,实际上是存在较大争议的。《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1条设定的蛊惑交易操纵犯罪的判断规则,将该种市场操纵行为模式的刑法规制边界拓展至“不确定的重大信息”,是一种相当重要的突破。
虚假的重大信息势必会误导投资者决策,但除了虚假信息以外,不确定的重大信息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其他市场参与者金融交易决策的误导性影响,继而通过受到影响的投资者的金融交易行为,制造证券、期货市场价格的波动。美国反期货市场操纵立法中的蛊惑交易操纵刑事处罚,其信息范围就不局限于虚假性,而是覆盖误导性、不确定性等诸多特征——根据美国《商品交易法》第6条(c)款1项的规定,禁止明知信息具有虚假、误导性或者不准确性,或者鲁莽地无视信息具有虚假性、误导性、不准确性,传播该信息,影响州际期货、互换等交易的市场价格,从事相关期货交易行为。〔22〕See 7 U.S. Code Chapter 1 - Commodity Exchanges § 6c (1).美国《商品交易法》第13条(a)款2项进一步规定,操纵或者意图操纵期货、互换等市场交易构成联邦重罪,单处或者并处100万美元以下罚金或者10年以下监禁。〔23〕同上注。从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践中的立法例来看,《操纵市场司法解释》将利用不确定的重大信息实施操纵性交易认定为蛊惑交易操纵犯罪,具有一定合理性。
但是,蛊惑交易操纵的刑法规制范围推进到“不确定的重大信息”存在以下问题且有必要进行相应优化:一是与我国《刑法》证券期货犯罪条款之间的体系性关系不相协调,二是模糊了蛊惑交易操纵违法与犯罪的实质边界;所以,蛊惑交易操纵犯罪中的信息属性仍然有必要限定为虚假信息。
《刑法》第181条规定了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24〕《刑法》第181条第1款规定: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蛊惑交易操纵犯罪是《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行为模式之一,两种犯罪类型的实质区别是: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所侵害的法益是证券、期货市场的信息秩序。所以,“扰乱秩序”是本罪的构成要件,而行为人是否实施交易行为、是否获取交易利润并非入罪条件。蛊惑交易操纵犯罪则必须具有交易相关证券、期货合约的客观行为,同时操纵者应当以谋取交易利益作为主观故意的内容。然而,无论是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还是蛊惑交易操纵犯罪,其构成我国《刑法》规定的证券期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实质基础是完全一致的,即对证券、期货市场中的信息效率的严重妨害。可见,刑法对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行为与蛊惑交易操纵行为均进行谴责,根源在于伴随着这两种犯罪行为的“信息”,在属性上具有相同的危害实质。因为《刑法》第181条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与作为《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行为模式之一的蛊惑交易操纵犯罪在法条关系上具有极强的关联度,并且两种犯罪类型具有相同的罪质,所以,尽管蛊惑交易操纵犯罪所依赖的刑法条文“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没有明示性地规定这种特定的市场操纵类型及其重要构成要素——信息的属性与特征,完全可以从文义明确程度更充分的《刑法》第181条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中求得具体的证明与解释。既然《刑法》第181条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将侵害证券、期货市场信息效率的信息属性限定为“虚假性”,那么蛊惑交易操纵犯罪不宜拓展至“不确定”的信息。
此外,在证券、期货市场行政监管层面,对蛊惑交易操纵的行政处罚可以将信息的属性拓展为“不确定性”,甚至可以推进至不准确、不完整等更广范围。〔25〕《操纵认定指引》第31条规定:本指引所称蛊惑交易操纵,是指行为人进行证券交易时,利用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不确定的重大信息,诱导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做出投资决定,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交易量,以便通过期待的市场波动,取得经济上的利益的行为。上述美国《商品交易法》蛊惑交易操纵条款中的信息属性不局限于虚假性,并且对市场操纵行为配置了相对严厉的法定刑。但实践中被认定为期货市场操纵犯罪的刑事判例非常罕见,绝大部分都是在操纵者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或者司法部(DOJ)进行和解或者行政处罚。这说明在发达资本市场的法律框架中,蛊惑交易操纵的信息范围尽管比较宽泛,但主要适用于证券期货行政法律而非刑事法律领域。因此,将蛊惑交易操纵刑事责任的实质边界限定为信息虚假性,更有利于从行为实质层面,合理廓清行政处罚与刑事责任的边界。
(二)抢帽子交易操纵的违法性实质与免责事由
《追诉标准二》第39条第7项〔26〕根据《追诉标准二》第39条第7项的规定,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专业中介机构或者从业人员,违背有关从业禁止的规定,买卖或者持有相关证券,通过对证券或者其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做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在该证券的交易中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构成抢帽子交易操纵。和《操纵认定指引》第35条〔27〕《操纵认定指引》第35条规定:本指引所称抢帽子交易操纵,是指证券公司、证券咨询机构、专业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买卖或者持有相关证券,并对该证券或其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开做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以便通过期待的市场波动取得经济利益的行为。都对抢帽子交易操纵这种行为模式进行了特殊主体限定,即行为人构成抢帽子交易操纵的前提是证券公司、证券咨询机构、专业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1条第2项则取消了抢帽子交易操纵的特殊主体要件,并从误导投资者决策、反向交易的角度进一步对客观行为的操纵性特征予以细化阐释。
《操纵市场司法解释》对抢帽子交易操纵司法判断规则做出的上述重大调整,有助于将非特殊主体实施的情节恶劣的“黑嘴”荐股行为纳入证券期货犯罪规制范围。例如,知名证券节目主持人廖英强通过提前买入、公开荐股、反向卖出手法操纵39只股票,获利超过4310万元,证监会认定其构成抢帽子交易操纵,对其做出1.29亿元的行政处罚。〔28〕2015年3月至11月,廖英强利用其知名证券节目主持人的影响力,发布了含有荐股内容的博客60篇,平均点击次数为110399次,在其微博、博客“午间解盘”栏目视频中公开评价、推荐“佳士科技”等39只股票共46次,在推荐前使用其控制的账户组买入相关股票,并在公开荐股下午开盘后或次日集中卖出相关股票,违法所得共计43104773.84元。证监会认定,廖英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77条第1款“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操纵证券市场”中第(四)项“以其他手段操纵证券市场”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203条所述情形,对廖英强没收违法所得43104773.84元,并处86209547.68元罚款。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廖英强)〔2018〕22号。涉案金额如此之高的“黑嘴”却没有进入刑事程序追责,主要法律原因在于当时的立案追诉标准等都要求抢帽子交易操纵构成犯罪必须是证券、期货从业人员等特殊主体。廖英强“戏谑”回应1.29亿罚款更是引发各界反思抢帽子交易操纵行为的入罪条件是否过高从而难以震慑证券市场违法犯罪行为。〔29〕参见皮海洲:《建议对股市“黑嘴”采取市场禁入措施》,载《证券时报》2018年5月15日,第A版。基于《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1条第2项的规定,刑法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有效震慑此类非特殊主体实施的抢帽子交易行为。但随之又产生了全新的疑问:非证券、期货从业人员先期或者同期减仓,对相关证券、期货合约进行公开评价,投资者受到相关信息影响之后做出金融交易决策,行为人实施反向交易获利的行为,是否完全符合抢帽子交易操纵的犯罪实质?
市场操纵的法律与金融分析理论认为,抢帽子交易操纵的违法性本质在于行为人与证券、期货市场中其他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即向投资者或者证券、期货市场传递与金融商品有关的评价、建议、咨询、意见等信息,应当杜绝利益冲突。〔30〕同前注〔17〕,谢杰书,第 286 页。这意味着信息传递者只能进行“二选一”:(1)戒绝与该信息关联的金融交易;(2)只能从事与接受该信息投资者时间、方向等核心要素均保持高度一致的金融交易。否则,行为人在发布信息之前或者同期建仓并在信息发布之后平仓,作为信息接受者的投资者利益与从事相关金融交易的信息发布者利益就会出现显著的冲突风险,即行为人为确保建仓之后能够在盈利的价格位置平仓而发布倾向于本人利益的信息,引导投资者按照有利于本人平仓方向、价格、时间等要素从事金融交易决策,从而产生损害投资者利益的重大风险。这种杜绝利益冲突的义务,绝对且直接的来源是信息发布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又来源于信息发布者的金融从业人员主体身份。〔31〕See Jill I. Gross, Securities Analysts’ Undisclosed Conflicts of Interest: Unfair Dealing or Securities Fraud?, Columbia Business Law Review, 2002 (1), 2002, p.632.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等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主体身份与业务属性,决定了应当以客户、投资者利益为导向发布具体的研究报告、投资建议、评价意见,其与接受相关信息的客户(付费获取信息的投资者)之间是代理关系,与接受相关信息的市场参与者(免费获取信息的投资者)之间是信赖关系。行为人实现市场操纵的关键在于发布信息行为对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影响力,行为人品牌效应越强,信息内容认可度越高,信息发散范围越广,对投资者决策的控制水平就越高,信息介入前后的金融商品价差水平相应越高,操纵性交易获利金额就越大。此类特殊主体不能基于本人利益实施具有利益倾向的信息发布与关联金融交易行为,否则即构成抢帽子交易操纵。所以,在不具有特殊主体身份的情况下,信息发布者与接受者之间并没有绝对且直接的杜绝利益冲突义务来源,司法解释将这种不完全符合抢帽子交易操纵违法性实质的行为认定为市场操纵犯罪,有必要予以进一步的解释论证并配置补充规则。
抢帽子交易操纵经由司法解释正式被确立为《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中的“其他方法”,其目的在于规范证券、期货市场中的信息效率与秩序,防范利益冲突,禁止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利用对本人金融交易有利但会阻碍其他市场参与者经济效率实现,甚至损害其利益的信息,谋取本人金融商品交易利润。实施此类行为的证券、期货等市场从业人员与信息接受者之间,构成绝对且直接的利益冲突。因为金融行政法律与刑事法律制度均严格保护从业人员与客户之间的代理关系、与投资者之间的信赖关系,禁止行为人传播的证券、期货信息与本人的金融交易利益挂钩。〔32〕See Arthur B. Laby, SEC v. Capital Gains Research Bureau and the Investment Advisers Act of 1940,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91 (3), 2011, p.1056.所以,从业人员实施抢帽子交易行为,没有任何阻却市场操纵属性的免责事由。
向证券、期货市场传递信息的非特殊主体,与接受其信息的其他市场参与者,既非受托人与客户关系,亦不存在任何法定的信赖义务来源。对证券及其发行人、上市公司、期货交易标的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的行为主体,与该等信息的接受者之间,形成了客观的利益冲突。行为主体发布的信息所指向的证券、期货交易品种,与其先前建仓、信息发布之后平仓的证券、期货交易品种相同的,使得信息本身具有利益冲突性。在投资者按照行为主体发布的信息做出金融决策与交易行为时,行为主体却实施与信息内容及投资者交易方向相反的金融交易,使得交易行为具有利益冲突性。行为人与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客观利益冲突并非源于法律关系、主体身份,而是源于信息内容与交易内容,属相对与间接的利益冲突。
理论上有条件通过两种路径化解相对于间接利益冲突:一是利益冲突关系的事先披露,即行为人在对证券、期货合约等交易标的进行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之前或者之时,充分公示其自身实施的相关金融交易,可能正在或者已经利用上述建议、分析、报告等信息对投资者的影响力及其引发的金融市场价格波动等获取交易利润。二是信息接受者的事后同意,即市场参与者在知悉行为人建仓、发布消息、影响市场、平仓等情况后,以明示的方式同意上述行为,从而对利益冲突予以豁免。由于实践中很少会出现第二种情形,故披露利益冲突构成了非特殊主体实施抢帽子交易的免责事由。欧盟《内幕交易与市场操纵(市场滥用)指令》(以下简称《市场滥用指令》)就采用了这种立法例——《市场滥用指令》第1条第2款以禁止利益冲突为核心设置抢帽子交易操纵的认定依据,不设主体要件限制,禁止包括金融分析、传统新闻媒介或者网络信息传播渠道等在内的任何主体从事抢帽子交易,但承担市场操纵法律责任的前提是行为人在违规不披露相关金融交易信息的情况下向市场发布投资信息。〔33〕See Commission Directive 2003/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8 January 2003 on insider dealing and market manipulation (market abuse), Article 1 (2).
《操纵市场司法解释》将抢帽子交易操纵拓展为一般主体且并未针对性地设置免责事由,在今后的疑难案件法律适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争议。证券、期货市场中一种典型的交易模式是,针对特定金融商品发布利空研究报告并做出相应的建议卖出评级,基于研究报告对市场的影响引发投资者卖出或者做空相关金融商品,在金融商品市场价格短期内形成快速下跌趋势时,通过事先融券卖出、事后买入回补的方式谋取做空利润。浑水公司(Muddy Waters Research)等境外机构就时常针对中国概念股进行做空,但其利用发布利空研究报告对市场的影响力而实施的卖空交易实际上很少受到刑事指控。〔34〕See Carrie Sperling & Kimberly Holst, Do Muddy Waters Shift Burdens?, Maryland Law Review, 76 (3), 2017, p.629.因为发布研究报告等信息的市场参与者,通过全面且充分披露其交易情况,免除了利益冲突的法律责任,不再具备抢帽子交易操纵的违法性实质。随着我国证券、期货市场不断完善融券交易、股指期货与期权、ETF期权等各类做空工具,利用公开研究报告做空相关证券、期货交易品种的投机行为也会逐渐增多。由于《操纵市场司法解释》并未规定一般主体实施抢帽子交易的免责事由,完全可能出现符合行为要件但通过信息披露而不具备利益冲突违法实质的争议性案件。所以,实务部门在具体适用《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1条第2款认定非特殊主体实施的抢帽子交易案件时,有必要考虑是否补充免责事由。行为人制作或者发布信息之前或者同时,向市场披露其从事的与该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合约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且有证据表明其获取的交易利润并不以投资者损失为代价的,可以认定其不构成市场操纵犯罪。
对此建议的一种可能的质疑是,《操纵市场司法解释》已经细致规定了“进行与其评价、预测、投资建议方向相反的证券交易或者相关期货交易”,实施反向交易的事实能够证明,行为人获取的利益必须通过受到诱导的投资者交易行为实现,利益冲突在结果层面并没有基于披露交易信息而化解,故一般主体也不得基于信息披露而免除市场操纵犯罪的法律责任。但是,以反向交易否定利益冲突豁免的适用空间,其经济逻辑与法理依据是不充分的。因为所有的建仓行为想要兑现利润都需要平仓行为进行了结,即基于利好信息买入必有卖出(与信息方向相反)才能获利,基于利空信息卖空必有回补(与信息方向相反)。所以,反向交易充其量只能是计算获利的基准,不能作为锁定利益冲突犯罪实质的充分条件。
(三)信息操纵的司法认定
《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1条第3项、第4项分别规定了重大事件操纵、利用信息优势操纵两种行为模式的具体判断规则。根据《证券法》第67条和第75条的规定,《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1条第3项中的资产收购或者重组、投资新业务、股权转让、上市公司收购等“重大事项”在未公开之前,实际上就是对证券市场交易价格具有显著影响的重要信息,即内幕信息。故重大事件操纵、利用信息优势操纵都是基于信息对于金融商品市场价格的重大影响而实施的市场操纵行为模式,可以统称为信息操纵。广受关注的徐翔操纵证券市场案就是典型的信息操纵模式,即行为人与上市公司董事长或实际控制人合谋后形成信息优势及其炒作股价优势,控制上市公司发布“高送转”信息生成及信息披露的节奏、内容等,引发投资者大量跟风交易并推动股价、交易量异常波动。〔35〕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2刑初字第148号判决书。
《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1条第3项、第4项对于解决之前信息操纵司法实践争议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判断规则,但随之也产生了如何认定策划、实施虚假重大事项、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等全新疑难问题,有必要进一步予以概念澄清、具体分析、细化阐释。
第一,司法解释规定的“策划、实施资产收购或者重组、投资新业务、股权转让、上市公司收购等虚假重大事项”,并不意味着其要求与此类重大事项有关的信息与内容全面造假或者纯属无中生有。这里的虚假性内涵应当是策划、实施相关事项并无执行的客观基础,行为人不以并购、重组、交易、业务等内容的达成为目的,而是以配合影响价格、交易量为目的。
有的操纵者在控制上市公司经营活动与重大资产交易时,股权收购、业务拓展、技术研发、资产置换等基础交易关系及其磋商过程本身是真实存在的。例如,交易双方就并购重组问题进行了初步磋商、实质谈判等多轮会谈;相关重大交易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重大项目订单等。但该重大交易客观上并不具备兑现条件,行为人也没有完成重大事项的主观心态,行为人筹划、实施此类重大事项的意图在于制造并发布重大信息,从信息所引发的股价变动中谋取交易利润(如高位减持)或者其他相关利益(如维持股价高位运行使得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股票质押处于平仓线之上)。实践中将此类操控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的行为称之为“忽悠式”重组。〔36〕参见孙华:《执法升级 “忽悠式”重组难逃监管法眼》,载《证券日报》2017年5月3日,第A2版。在此类情况下,行为人不能以其策划、实施的重大交易是真实推进的为由,抗辩其不属于《操纵市场司法解释》规定的策划、实施资产收购或者重组、投资新业务、股权转让、上市公司收购等“虚假”重大事项。
《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1条第3项尽管使用了“虚假重大事项”的概念,但虚假性标准并不要求证明与重大事项推进有关的一系列事项是否真实发生,而是需要重点考察以下内容:(1)与重大事项有关的财务文件是否存在虚假记载。以证监会查处的浙江九好办公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九好网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好集团”)等“忽悠式”重组案为例,九好集团以虚增收入、虚构银行资产为手段,将自己包装成价值数十亿的“优质”资产。〔37〕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浙江九好办公服务集团有限公司、郭丛军、宋荣生等4名责任人员)》(2017)32号。行为人执行的重大事项行为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但其在信息披露文件中进行虚假记载,可以认定为策划、实施虚假的重大事项。(2)重大事项进程及其结果是否依法披露信息。与重大事项有关的公告信息不符合《证券法》及信息披露监管规则,公告的信息内容与实际事件的起因、筹备、策划、合约签署、执行、具体实施、结果等存在明显不一致的,可以认定为策划、实施虚假的重大事项。(3)策划、实施相关事项是否具有不正当目的。在上市公司收购资产、投资新业务中,经过完整的筹备、磋商、尽职调查、合同签订等环节,但资产估值水平明显不符合行业、市场规律,最后项目无法执行或者投资失败,而股价已经因为前期的信息披露波动,可以认定为不以重大事项执行为目的,构成策划、实施虚假重大事项。在重大资产重组中,虽然签署了协议,但实际执行具有先决条件(如主管部门审批)或者需要很高的履行能力(如交易金额巨大而必须通过融资获取充足资金),行为人在不可能满足此类条件、具备相关能力的情况下,签署合同并进行信息披露,引发股价波动的,可以认定为不宜实际执行合同为目的,构成策划、实施虚假重大事项。
第二,《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1条规定的“诱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本质上是对重大事件操纵、利用信息优势操纵等条款〔38〕《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1条第1项至第5项都规定了“诱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中所描述的异常行为与投资者受到误导性影响之间关联性的推定,控方并不需要证明操纵行为与投资者受引诱从事的金融交易具有直接对应的因果关系。
市场欺诈理论对此进行了比较充分的阐释:基于证券、期货市场当时的交易价格以及市场信息从事相关金融交易,同期存在涉嫌证券欺诈的行为,且投资者出现损失的,无须证明投资决策与证券欺诈行为之间的特定因果关系。〔39〕See Basic v. Levinson, 485 US 224, 244 (1988).误导性陈述、操纵性交易等欺诈行为向证券、期货市场传递了扭曲的价格信息,可以据此推定误导性、操纵性行为期间的投资者的决策与证券欺诈行为之间存在“交易关联”,〔40〕W. Scott Laseter & Phillip E. Friduss, 10b-5 Reliance Requirement in the Eleventh Circuit After Kirkpatrick v. J. C. Bradford &Co., Mercer Law Review, 40 (3), 1989, p.752.不需要提供直接证据证明投资者基于误导性陈述、操纵性交易而做出资本配置决策。〔41〕See Louis Loss, Joel Seligman & Troy Paredes, Fundamentals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 (5th Edition), Aspen Publishers, 2003,p.845.因为由竞争性交易与各类信息汇集所形成的市场价格,不仅是对基础资产内在价值、外在供求关系的准确体现,也是对介入市场的操纵性行为做出的失灵反应,投资者的金融交易以当时的市场价格成交,其做出资本配置决策可以认为受到了失灵、虚假或者错误的价格信号影响。〔42〕See William W. Bratton & Michael L. Wacht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raud on the Marke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60 (1),2011, p.83.
《操纵市场司法解释》对重大事件操纵、利用信息优势操纵等“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模式配置了“诱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这一要素,但“诱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并不要求查证,在操纵性行为实施期间从事交易的投资者,进行决策时主观心态是否受到误导。行为人实施了“策划、实施资产收购或者重组、投资新业务、股权转让、上市公司收购等虚假重大事项” ,“控制发行人、上市公司信息的生成或者控制信息披露的内容、时点、节奏”等可能对证券、期货市场价格信号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通过行为特征上明显的操纵性与异常性,嫁接起了与投资者决策受到影响之间的关联性。
四、市场操纵定罪量刑的数量标准
针对近年来证券、期货市场环境发生的明显变化,及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活动出现的新问题,《操纵市场司法解释》运用了成熟的司法解释技术,对《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完善。〔43〕同前注〔20〕,姜佩杉文。《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二条〔44〕《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2条规定: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82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持有或者实际控制证券的流通股份数量达到该证券的实际流通股份总量10%以上,实施刑法第182条第1款第1项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连续10个交易日的累计成交量达到同期该证券总成交量20%以上的;(二)实施刑法第182条第1款第2项、第3项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连续10个交易日的累计成交量达到同期该证券总成交量20%以上的;(三)实施本解释第1条第1项至第4项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证券交易成交额在一千万元以上的;(四)实施刑法第182条第1款第1项及本解释第1条第6项操纵期货市场行为,实际控制的账户合并持仓连续10个交易日的最高值超过期货交易所限仓标准的二倍,累计成交量达到同期该期货合约总成交量20%以上,且期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五)实施刑法第182条第1款第2项、第3项及本解释第1条第1项、第2项操纵期货市场行为,实际控制的账户连续10个交易日的累计成交量达到同期该期货合约总成交量20%以上,且期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六)实施本解释第1条第5项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当日累计撤回申报量达到同期该证券、期货合约总申报量50%以上,且证券撤回申报额在一千万元以上、撤回申报的期货合约占用保证金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七)实施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违法所得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针对刑法第182条第1款规定的三种及本解释规定的六种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情形,明确了七种“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为更加有力、有效地惩治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犯罪,《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3条〔45〕《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违法所得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82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发行人、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实施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的;(二)收购人、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实施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的;(三)行为人明知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被有关部门调查,仍继续实施的;(四)因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受过刑事追究的;(五)二年内因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六)在市场出现重大异常波动等特定时段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又规定了七种“数额+情节”的“情节严重”的情形。《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4条〔46〕《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4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82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一)持有或者实际控制证券的流通股份数量达到该证券的实际流通股份总量10%以上,实施刑法第182条第1款第1项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连续10个交易日的累计成交量达到同期该证券总成交量50%以上的;(二)实施刑法第182条第1款第2项、第3项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连续10个交易日的累计成交量达到同期该证券总成交量50%以上的;(三)实施本解释第1条第1项至第4项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证券交易成交额在五千万元以上的;(四)实施刑法第182条第1款第1项及本解释第1条第6项操纵期货市场行为,实际控制的账户合并持仓连续10个交易日的最高值超过期货交易所限仓标准的五倍,累计成交量达到同期该期货合约总成交量50%以上,且期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在二千五百万元以上的;(五)实施刑法第182条第1款第2项、第3项及本解释第1条第1项、第2项操纵期货市场行为,实际控制的账户连续10个交易日的累计成交量达到同期该期货合约总成交量50%以上,且期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在二千五百万元以上的;(六)实施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违法所得数额在一千万元以上的。实施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违法所得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并具有本解释第3条规定的七种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明确了六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按照证券交易成交额的五倍、违法所得数额的十倍确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数额标准,规定了七种“数额+情节”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47〕同前注〔20〕,姜佩杉文。《操纵市场司法解释》设定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无论是在条文结构还是在条款内容层面,都属于刑法司法解释中比较复杂的,有必要就其中的重大适用问题进行深度阐释。
(一)交易量标准的辨正
市场操纵犯罪性质的确定是“定性”与“定量”的结合。“定性”是基于《刑法》第182条及《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案涉行为模式的市场操纵法律性质予以确认;“定量”是根据《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2条、第3条的规定,确定市场操纵是否构成“情节严重”。不管是之前的《追诉标准二》还是现在的《操纵市场司法解释》,都将交易量指标设定为定罪量化标准之一。尤其是连续交易、相对委托、洗售、虚假申报等四种行为模式,行为人的交易量是对其进行定罪的核心数量标准。实践中出现了一种倾向性认识,即涉案行为符合市场操纵行为模式的特征(定性),同时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交易量标准(定量),就构成相应的市场操纵犯罪。上述意见似乎在定罪逻辑上严丝合缝,实际上代表了市场操纵刑事司法实践的典型误区。司法解释规定的交易量标准的连续交易、相对委托、洗售、虚假申报行为直接认定为市场操纵犯罪,并不符合《刑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解释规则。
其一,连续交易、相对委托、洗售、虚假申报等行为达到《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2条所规定的交易量标准,只是满足了《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犯罪构成体系中的部分内容,不一定符合市场操纵犯罪的实质,更没有齐备市场操纵的犯罪构成。
《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文本内容和罪状结构〔48〕《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期货合约,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四)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清晰地呈现了犯罪构成前后递进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行为模式,即对操纵性行为的样态、特征、情形的具体规范描述。市场操纵行为模式具体包括:(1)连续交易,即独立、联合其他行为主体,实施连续性的证券交易行为,操纵证券的市场价格、交易量。(2)相对委托,即复数行为主体在交易价格等核心要素约定的情况下,相互买卖证券,影响证券、期货合约的市场价格或者交易量。(3)洗售,即独立行为主体在实际控制证券、期货合约交易账户中买卖证券,影响证券、期货合约的市场价格或者交易量。(4)“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49〕《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1条对每项“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行为模式都将价量影响要素,即“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作为构成要件之一。的其他方法。第二层次,刑事违法性实质,即对符合刑法及其司法解释既定行为模式所具体描述的各类操纵性行为,在刑事违法性层面的实质内涵。符合第一层次的行为模式之后,必须能够被评价为“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才能在刑法上具备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法律属性。第三层次,刑事处罚标准。“情节严重”是刑法介入的具体数量标准;“情节特别严重”是提升至第二档法定刑的具体数量标准。对于连续交易、相对委托、洗售、虚假申报等行为模式而言,《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2条所规定的交易量指标,实际上只解决了刑事处罚标准中的定量问题,并没有解决行为模式中亦需要解决的定量问题,即如何认定“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
其二,连续交易、相对委托、洗售、虚假申报等涉嫌操纵的行为是否“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应当在行为模式判断环节就价量形成机制是否受到扭曲进行独立评估,并且不能重复使用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中的交易量标准。
《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2条规定,连续交易、相对委托、洗售、虚假申报等行为模式的交易量,属于判断其是否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的量化标准。《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1条规定了“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独立构成要素。作为“情节严重”判断尺度的交易量标准不能重复用以直接证明是否存在影响证券、期货交易量。从经济机理与法律属性的双重角度分析,任何交易行为介入市场后都会对交易量产生影响,因为在一定交易日期间内实际控制一定数量的证券或者超出持仓限额的期货合约,行为人的交易量占据到市场总量中一定比例,这就是一种经济上的影响,不能直接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影响交易量。作为法律标准的影响交易量更侧重强调的是对交易量的扭曲。
市场操纵犯罪是包括行为、结果及因果关系等构成要素的法律概念。《刑法》第182条及《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1条规定的“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是对结果性内容的罪状描述。达到司法解释规定交易标准的连续交易、洗售、相对委托、虚假申报等,都只是市场操纵犯罪构成体系中的行为概念。这种疑似具有操纵属性的交易行为,须在证券、期货市场中形成具有可责性的结果——价量形成机制受到扭曲——才能将交易行为与危害结果联系起来认定为市场操纵犯罪。价量形成机制受到扭曲的核心内涵是证券、期货合约的价格或交易量处于明显异常水平,可比数据的选择标准应当根据不同的市场操纵犯罪行为类型的特征进行调整。例如,对于连续交易、相对委托、洗售等操作期间相对更长的操纵行为类型,可以选取同期行业指数、盘块指数、大盘指数、同类个股价格或交易量数据、境外相同期货交易品种的价格或交易量数据等;对于虚假申报操纵等具有短线或者超短线特征的操纵行为类型,可以选取该证券、期货交易品种日内、开盘或收盘集合竞价时段、行为介入前的极短区间(以分、秒为单位,对于通过程序化交易下单的操纵行为不排除使用微秒、毫秒等时间单位)的价格或者交易量数据。如果连续交易、洗售、相对委托、虚假申报等所指向的特定证券、期货交易品种的市场价格或者交易量,并没有偏离能够合理推论或计算的、资本市场正常或自然竞争所形成的价格或者交易量,即使行为人本身的交易量超标,只能根据《证券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及交易所规则等,认定为信息披露违规、违反超仓限额等证券期货违法行为,并不能构成市场操纵犯罪。
(二)违法所得的计算方法
《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2条至第4条规定,违法所得构成市场操纵定罪量刑重要的量化指标:(1)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具有《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的七种情形之一的,构成“情节严重”;(2)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违法所得数额在一千万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并具有《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的七种情形之一的,构成“情节特别严重”。有的行为人“风控水平”与“操纵技术”较强,可以在交易量不超标的情况下实现相当惊人的非正常收益率。此时,通过违法所得的量化标准将具有严重市场危害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尤为关键。公正、有效且科学地对违法所得予以认定,对市场操纵定罪量刑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然而,《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9条〔50〕《操纵市场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本解释所称“违法所得”,是指通过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所获利益或者避免的损失。仅就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违法所得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没有提供计算方法与认定规则,而该问题在市场操纵犯罪刑事司法实践中争议极大,亟须以契合刑事法律规则与数量金融逻辑的双重视角,就市场操纵违法所得的计算方法与认定问题进行细化阐释。
市场操纵违法所得的认定规则是:(1)计算违法所得的时间区间为市场操纵行为发生时至实施终了之时;(2)证券、期货合约全部平仓的,以累计平仓收入减去累计建仓金额,同时扣除证券、期货合约的交易成本(税费、交易佣金、手续费等合理费用);(3)尚未全部平仓的,核定收入部分还应当加入市场操纵实施终了时所持有证券、期货合约的市值。〔51〕《操纵认定指引》第50条规定:违法所得的计算,应以操纵行为的发生为起点,以操纵行为终止、操纵影响消除、行政调查终结或其他适当时点为终点。第51条规定:在计算违法所得的数额时,可参考下列公式或专家委员会认定的其他公式:违法所得=终点日持有证券的市值+累计卖出金额+累计派现金额-累计买入金额-配股金额-交易费用。市场操纵行为发生时与终了时是违法所得计算重要的时间基准,但这两项时间节点的确立规则应根据不同市场操纵类型的特征而进行针对性调整。
对连续交易、相对委托、洗售等交易型操纵而言,交易过程需要一定周期,市场操纵行为发生时、终了时应分别以交易量超标的最初交易日与最末交易日为准。对于蛊惑交易、抢帽子交易、重大事件操纵、利用信息优势操纵等信息型操纵而言,可能存在操纵性信息传播行为与交易行为并存的情况,应当将先出现的操纵性信息行为或交易行为认定为操纵行为发生时,将后出现的信息对市场的影响消除或交易行为结束认定为操纵行为终了时。对于虚假申报操纵,其核心客观行为表现为短期内频繁或者大额申报并撤回,应当首先确立其操纵行为终了时间。由于虚假申报操纵具有非常显著的短线或者超短线特征,故(1)对于发生在开盘集中竞价或者盘中阶段的,应当将操纵行为影响的程度界定为日内影响。实践中需要首先确立操纵行为终了时间并对操纵行为发生时进行倒推,即实施虚假申报当日最后一笔平仓行为发生的时间为终了时,然后计算日内平仓总交易量,以此交易量数额等值确认前期建仓总数额,并以该等持仓量中最先成交的时间为操纵行为发生时。(2)对于发生在收盘集中竞价阶段的,其操纵意图显然是控制收盘价,应当将操纵行为影响的程度界定为翌日影响。应当将收盘价形成后一个交易日最后一笔平仓行为发生的时间为终了时,然后计算日内平仓总交易量,以此交易量数额等值确认前期建仓总数额,并以该等持仓量中最先成交的时间为操纵行为发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