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装还是平装:由“新书旧装”引发的讨论
2020-03-17
20世纪20年代,在新文学著作的出版中,出现了一种“新书旧装”的现象,亦即内容趋新的书籍在装帧设计过程中反而采用或借鉴了传统线装的形式。唐弢《线装诗集》一文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对此类线装本新诗集进行了全面介绍。此后由薛冰、王稼句策划的“新文学线装珍本丛书”更是选取部分此类代表作品影印出版,其中包括徐志摩《志摩的诗》(中华书局代印1925年)、俞平伯《忆》(朴社1925年)以及刘复《扬鞭集》(北新书局1926年)等十部著作。姜德明在为“新文学线装珍本丛书”撰写的序言中提到:“‘五四以后出版的新文学书刊,几乎都采取平装铅印本的形式,只有整理古籍或写作旧体诗词时,仍有人沿用旧式线装本。”职此之故,这批此时出现的新文学线装书籍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新书旧装”反映的是书籍内容的趋新与装帧形式的守旧,这也是前人重点关注的一对矛盾冲突,但这其中却忽视了著者本身。作为新文学运动的推动者,他们思想前卫,但在所出版的书籍中——不仅仅包括新文学类,为何会采用传统的线装形式,及其产生的后果与影响,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不爱“平装”爱“线装”
“线装书”是我国传统的装订方式,用此法制作的书籍代表并影响着国人的审美观念与阅读习惯。这一观念与习惯并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西方印刷装帧技术的传入而立刻改变甚至消逝。“新书旧装”下的新文学运动者,即有着对于“线装书”的偏爱。
1925年12月,俞平伯所著诗集《忆》由朴社出版,当时朴社刊发的广告中曾写道:“全书由作者自书,连史纸影印,丝线装订,封面图案孙福熙先生手笔。这样无美不备,洵可谓艺术的出版物。先不说内容,光是这样的装帧,在新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可见,装帧成为《忆》的一大特色。它表现出一种中西融合的设计理念,此书是由作者手写石印,使用的是西方传来的印刷技术。纸则用中国的连史纸,装帧也借鉴了传统的线装形式,并稍作改良——以丝线打结装订。
周作人对这种设计并不满意,觉得它还不够“中式”。故特意撰写《〈忆〉的装订》一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还希望能用木刻才好,倘若现在还有人会刻。石印总是有点浮光掠影,墨色也总是浮薄,好像是一个个地摆在纸上,用手去一摸就要掉下来似的。我对于《忆》也不免觉得这里有点美中不足,虽然比铅印自然要有趣得多了。”“(《忆》)那钉法我觉得还不如用中国式的线装为佳,因为原来的绢线结我不知怎的觉得有点像女学生的日记本,——自然这只是我一个人的偏见罢了。”由此亦可看出周作人对于木刻本线装书的喜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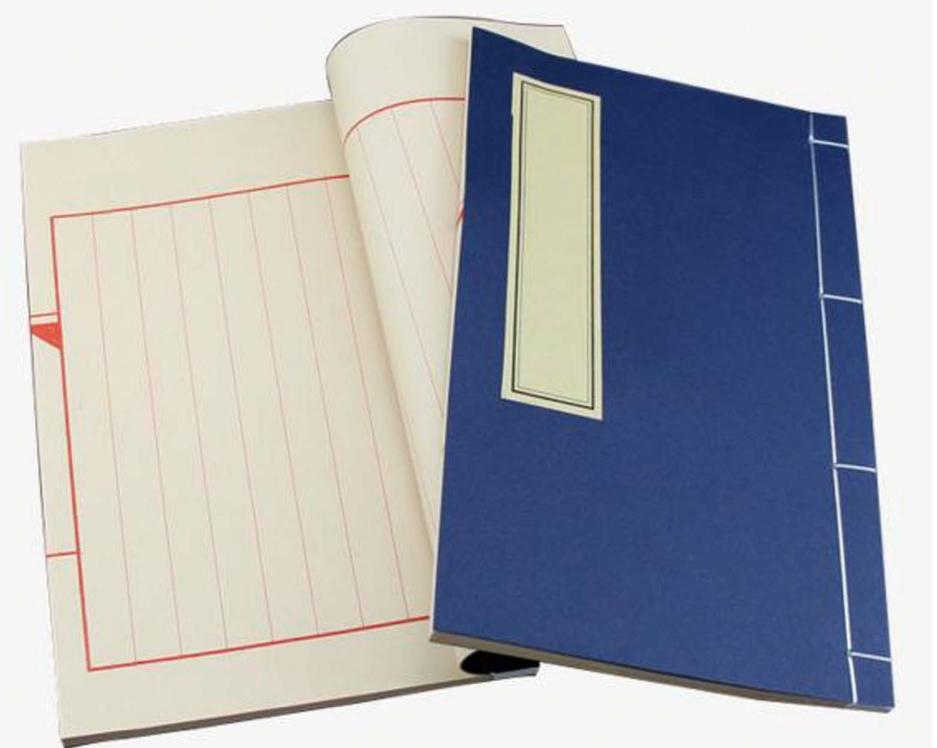
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刘复也持有同样的喜好。在其所出版的著作中,大量使用或借鉴传统线装的形式。1926年4月,刘复所著《瓦釜集》在北新书局出版,该书后附有广告一页,介绍了他的四部作品,即《扬鞭集》《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何典》《敦煌掇琐》,总名曰“如是丛书”。这套丛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使用传统的装订方式,如《扬鞭集》《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皆采用线装形式,《敦煌掇琐》更是除线装外,还欲使用精雕木板印行。
“线装书”尤其是木刻本线装书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与阅读习惯。就连新文化运动中主张不读“线装书”的钱玄同,在其青年时代的日記中也表达了对木刻本线装书的喜爱。“若欲认真刻书,木板既不可必得,则求其次,石印可也”,“装订必以华装为最合,洋纸洋装实不相宜也”。周作人、刘复等人亦是如此。故受此审美观念之影响,在这些对“线装书”有着偏爱的趋新人士带动下,“新书旧装”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潮流。
“艺术”还是“复古”
如何评价“线装书”这种装订方式呢?20世纪20年代,国内曾经有过关于出版艺术的讨论。其发轫者即为孙福熙,他是俞平伯《忆》一书的封面设计者。1926年9月15日,孙福熙发表了《出版事业的艺术》一文,其中提到线装的问题:“用铁丝钉者易生锈,书面与底黏贴。穿钉处者翻不开,而且面上折成一条痕迹。……《扬鞭集》与《痴华鬘》纸的捻钉是中国旧法而有新鲜意义的。”纸捻钉是线装的一种改良形式。从美观与实用的角度来看,孙福熙对于刘复《扬鞭集》所使用的纸捻钉大为赞赏。
但“线装书”这一书籍装帧方式在另外一些人眼中却代表着“复古”,应当加以彻底否定。批评者们以《幻洲》半月刊为阵地,对刘复展开了暴风骤雨式的攻击。如1926年8月13日,裴华女士在《洋翰林刘复“复古”》一文中写道:“我骂他复古,不是骂他的根本思想复古,我是买了他编著的《扬鞭集》而有感于中。你看一本深紫色的书面,贴上一条大红绯金珊瑚纸书名签儿,订上一寸余长的两个白纸捻,里面是加边划格的双页连史纸用蓝墨油印的。嘻,假使你没有瞧见著者刘博士半侬的大名,也没有翻阅里面是的吗了呢的新诗,你一定要奇怪这本‘纸捻装的书,起码是明末清初,那一个江南才子,或者词人墨客的遗著罢!”“装订虽是小事,但照‘因小可见其大的定律推算起来刘博士复古的嫌疑是证实了。”
又如1926年10月1日,潘汉年在《钉梢“洋翰林刘复复古”》一文中提及:“《太平天国文件》和《扬鞭集》等,是Dr.刘主张‘古装印刷是无疑了。……讲到这里,裴华女士骂Dr.刘‘复古,好算不过火吧?”并进而指出刘复引发了一场装帧方式上的“复古”风潮。“然而中国的事情总是奇怪的:惟其因为古色古香颇有遗古风,仿而效之的就像‘雨后春笋,大有其人,什么《痴华鬘》、《浑如篇》……甚而至于美术家兼文学家又兼美专校长的秘书(现在不知道还兼不兼?)滕固先生的《迷宫》也是古色古香颇有遗古风的了!”
再如集中发表于《幻洲》第1卷第9期上的四篇文章,即迪可《刘半侬之流可以休矣!》、潘汉年《我也来说几句》、泼皮男士《博士的胜利——纪念我家博士而作》以及山风大郎《骂半侬劝北新》等,对刘复展开了轮番的攻击。饱受攻击的刘复,其《扬鞭集》下卷迟迟未能刊出,应当即是受此影响。《敦煌掇琐》亦是如此,钱玄同致胡适信中曾调侃道“半农博士的《敦煌什么》(即指《敦煌掇琐》),用于古法去刻木板,久无消息了,该木板大有‘披发入山,不知所终之象”。
新旧冲突下的“线装书”
在书籍的生产过程中,装订是其重要一环。著者采用何种方式装订书籍,既要考虑到技术、成本以及个人喜好等因素,又受制于当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
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平装”方式逐渐超越并全面取代传统“线装”的背景下,因线装书符合中国人传统的审美习惯,即使是新文化运动干将、留学欧洲的刘复在其著作出版之时仍采取了“线装”形式,并在当时引发一股“新书旧装”的风潮。出现了一大批采用传统“线装”形式而内容趋新的书籍。
这一装帧方式却引起了一场大的争论。孙福熙从出版艺术的角度对于刘复《扬鞭集》等书所采用的“线装”形式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一些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又极为激进的人士以“线装”代表“复古”为由,对此类出版行为进行了猛烈抨击。书籍的正常发行也因此受到影响。这也是刘复始料未及的,亦即书籍的装帧方式也会牵扯到趋新与守旧的问题。可见,受当时舆论环境的影响,“平装”或“线装”的选择已远远超出审美或技术考量,成为新与旧的另一种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