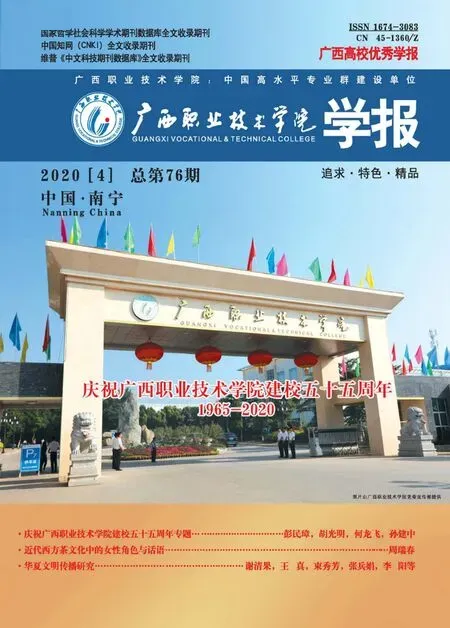清代邸报的受众、“报案”及其舆论控制
2020-03-17孔泽弘种晓明
孔泽弘,种晓明
(安徽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清代是我国古代新闻传播事业的最后阶段,也是古代新闻传播活动最为成熟的时期。其成熟性在受众的广泛性和政府的舆论控制等方面表现得尤为典型。清代邸报有着不同的受众群体。邸报的发行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专门从事报业经营的“京报人”,看到报业有利可图,为了扩大发行量,增加可读性,实现经济利益,不惜违规操作,甚至伪造“邸报”,以此博人眼球,因而导致多起“报案”的发生,由此带来了清廷对于邸报发行的种种控制。
1 清代邸报的受众群体
清代报业发展相对活跃,邸报的读者相对较多,邸报受众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受众群体。具体来说,邸报受众包括京内外各级政府官吏、文人士大夫、市民阶层和少数平民百姓。
1.1 官吏阅读群体
清代邸报的接受主体是各级政府官员,尤其以驻京衙门的高级官员和各省督抚提镇等封疆大吏为主,再加上府州县一级的部分官员,他们人数虽少,但却是邸报的主要受众。提塘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每日将邸报传递给本省的督抚提镇藩臬两司等官员。邸报是清廷中央政府沟通地方大员的主要信息桥梁。
邸报为各省封疆大吏服务,同时也培养出这些官员阅读邸报的接受心理。的确,各省督抚提镇在长期阅读邸报过程中,养成了阅读邸报的习惯,形成一种稳定的阅读期待,如果超过一定时间,看不到邸报的送达,他们反而会觉得不太正常。如道光元年七月,琦善接任山东巡抚一职。上任后很长时间没有接到京城提塘寄来的邸抄,他觉得很不正常,于是立即向兵部咨询,兵部回复说,山东抚标右营千总左某负责此事。左某回话说,已经于六月二十五日将《京报》(即邸报)交给值日提塘官石殿卿了。该提塘官也已经将第七十八号《京报》封好,于二十九日寄出。琦善得知此事后立即责成驻省提塘张守训彻查。张守训查得结果后回禀说,七月二日接到驻京提塘发来的第七十八号《京报》,立即于七月二日投递。琦善细审,向来京塘传递来的《京报》都要经巡抚两司各衙门抄送。他随后调查两司收文号薄的记录,发现并没有第七十八号《京报》的收文记录,便知肯定是提塘没有投递。
除此之外,各府州县一级的地方官员也多半是邸报或《京报》的读者。“(府城)城中看报的不过几十份,稍远之府城,尚无此数,若县城则每县不过几份”[1]。可见,府州县级的官员也能成为邸报的少部分受众。但清代府州县及以下的低级别官吏不具备由驻京提塘直接派送邸报的资格,他们的阅读渠道主要有两条:
其一,阅读由驻省提塘再次翻抄的邸报。省内各地在省城设有驻省提塘,负责翻抄邸报,以满足府州县及以下各级官吏的阅读需求。
其二,通过私人关系获得。如从京城、省城的朋友处购买获得。道光年间一份外文报刊记录了下级官吏获得《京报》的基本途径:
“《京报》由政府刊行,在北京叫‘京报’(King-paou)……在地方叫‘京抄’(King-chaou)该报由北京发向各省,但极少按时到广州,一般需40到50天,有时要60天。……大号是专为高级官员如总督、巡抚而发的;小号则是省里那些下级官员看的,他们得花高价从文吏那里购买,也有人花少钱租来看。有钱的人通过朝里的朋友,可以私下搞到最好的版本”[2]。
这段文字记录了《京报》的两类读者群。其一是封疆大吏如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吏读者群,他们的邸报由固定的发送渠道——驻京提塘负责递送。其二是下级官员,他们的阅读渠道主要是通过花高价钱向转抄的文吏们购买,或者花少量钱去租赁。可见,在京报的阅读环境中,还有租赁这一市场。花钱购买京报阅读到了清代中后期就更加普遍了。晚清时期发行的“良乡报”“涿州报”,其读者群主要就是依靠购买邸报的读者建立起来的。
1.2 士人阅读群体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阅读邸报的传统和习惯。究其原因,主要与传统中国士绅一体、士绅不分的文化背景有关。科举取士制度实施以来,高中进士、举人的士人多能步入仕途。古代士人往往有着双重的社会角色——在朝为官,在野为士。古代知识分子是一种身份,两种角色。士人阅读邸报有多重目的。
首先,可以了解国家大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往往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由于很多重大的朝政信息都来自邸报,读邸报就成为了士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康乾时期,一代名臣陈宏谋先后任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职。乾隆三十六年(公元l771年),他因病回乡,乾隆准允,加其太子太傅衔,谕令所经处官员二十里内料理护行。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在为诸生时,即留心时事,闻有邸报至,必借观之[3]。
其次,可以从邸报中获得科举信息,特别是人事升黜的变动信息。每一届科举的信息往往都刊登于邸报上,邸报是士人了解科举状况的主要信息来源。另外,人事变动也是邸报的主要内容之一,可以说邸报是朝廷人事变动的晴雨表。邸报上常有专门刊登朝廷人事任命的“选单”,“选单”是各级官吏最为关心的内容之一。
再次,作为资料珍藏。在古人看来,邸报不仅具有新闻价值,还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他们一边阅读,一边抄记,日积月累,就保存了大量的朝政信息资料。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说,其祖父不仅喜欢阅读邸报,还亲手抄写,留下了大量的邸报文献。清初修明史时,顾炎武虽然没有入明史馆直接参与修撰,但他经常提醒其学生和外甥,要充分利用明代邸报作为史料文献。据《顾亭林诗文集》记载:“窃意此番纂述,止以邸报为本……访问士大夫家,有当时旧抄,以俸薪别部购买一部,择其大关目处略一对勘,便可知矣”[4]。他还说在他写《日知录》时,就“参阅完实录,并崇祯邸报”[5]。明代邸报在民间士人中有大量抄录和收藏,明清士大夫人家很多都有家藏邸报的习惯。其中著名的如咸同年间士人穆缉香阿。据《清史稿》载称:
“穆缉香阿,字居南,满洲镶红旗人。……穆缉香阿,通知国故,家藏邸报,自国初以来几备”[6]。
穆缉香阿作为咸同时期的名臣,深通国故,他在阅读邸报的同时,还大量收藏清代立朝以来的邸报,达到了“国初以来几备”的程度。
其四,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清初诗人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中保留了数篇“邸报诗”,其卷三《邸报二首》其一云:
“曾趋绝域拜毘卢,降将还朝籍未除。博得封侯须好语,太平天子是文殊。暴露扬灰罪未伸,肻容武库贮亡新。专车长狄侨如骨,四出犹烦驿骑尘”[7]。
又如,卷二十三《保定旅次阅邸抄得从弟东亭及儿建南宫捷音口占志喜兼寄嘲老友姜西溟》云:
“邸报传来乐事重,一尊相属慰浮踪。青春三月客怀好,白发半头归兴浓。子弟联翩同榜羡,家门成就老夫慵。探花却入少年队,试问髯姜可胜侬(时姜亦为进士,笔者注)”[8]。
再如,卷四十五《阅邸报北直学使交替有人知德尹归期不远矣作诗志喜四首》其一云:
“冬来日日望回轮,邸报遥传信渐真。客病也应资药饵,长途未可恃精神。官随年限才经腊,农告归期正及春。劳动里中羊酒贺,一家遂有两闲人”[9]。
查慎行从阅读邸报中获得诸多的信息,然后借题发挥,有感而发,写出十多首邸报诗。清代文人留下邸报诗歌的岂止査慎行一人,落迫文人蒲松龄也有《邸报》诗,晚清文人龚自珍《乙亥杂诗》第八十八首亦涉及邸报:“河干劳问又江干,恩怨他时邸报看。怪道乌台牙放早,几人怒马出长安。”这些“邸报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士人阅读邸报时的忧谗畏讥、伤时忧国和怀才不遇之情。
1.3 市井胥吏阅报群
一般来说,邸报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各级官吏和士人群体,普通市井百姓是不允许、也难有机会读到邸报的。由于清代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伪邸抄案”(后文详述),使得清政府严格控制邸报的阅读范围。雍正年间,还曾明令禁止普通胥役贩卖、阅读邸报,如有违反,要严加惩处。清廷认为,这些平头百姓阅读邸报会“讹传惑众”,不利于国家稳定。但是,随着新闻意识的觉醒,普通百姓也日益关心所谓的朝政大事,也渐渐成为了阅读邸报的“小众”。
关于市井胥吏阅读邸报的情况,史料上少有记载,追述其阅读线索十分困难。但是,在明清时期的各种通俗白话小说中却有大量关于市井胥吏阅读邸报的生动描绘。最著名的如《红楼梦》,其书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有这样的描述:
“却说雨村忙回头看时,不是别人,乃是当日同僚一案参革的号张如圭者。……雨村领其意,作别回至馆中,忙寻邸报看真确了”[10]。
又如,第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云:
“话说尤氏从惜春处赌气回来,正欲往王夫人处去。……尤氏听了道:昨日听见你爷说,看邸报甄家犯了罪,现今抄没家私,调取进京治罪”[11]。
再如,第一○一回《大观园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写到:
“至次日五更,贾琏就起来要往总理内廷都检点太监裘世安家来打听事务。因太早了,见桌上有昨日送来的抄报,便拿起来闲看。第一件是云南节度使王忠一本,……第二件苏州刺史李孝一本”[12]。
文中“抄报”即邸报。清代小说《歧路灯》也有关于市井胥吏阅读邸报的描述:
“孝移在读画轩上,每日翻阅塘务日送邸钞。……忽一日阅至浙江奏疏,有倭寇猖獗、蹂躏海疆一本。……孝移便道:昨前阅邸钞,见潜老高发,喜不自胜。已从提塘那里,寄回一封遥贺的信未知达否?”[13]
可见,清代的邸报阅读已经较为普及,不仅官宦等钟鸣鼎食之家订阅邸报,就连普通的平民百姓也能看到邸报。贾雨村是个被革职的小吏,他可以回旅馆阅读邸报,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官复原职的机会。尤氏不过一妇人,她居然也关心邸报上的内容。上文中的普通书生孝移也可以在寓所中读到邸报,看来清代旅馆等羁旅之所也已经常备有邸报之类的读物。足见清代邸报阅读群体开始下移,普通百姓也有机会阅读邸报之类的新闻传播媒体。
2 清代前期的“报案”
清入关后,虽然取得了政权,但是其政权的合法性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特别是江南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普遍存在“华夷之辩”的思想。为了政权的稳固,清初开启了“三禁”(言禁、书禁、报禁)运动。“报案”即因报纸而起的案件,是“报禁”的必然结果。清代前期,随着邸报传播、阅读面日益扩大,邸报的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部分报业经营者为满足读者的新闻需求,或为了扩大发行数量,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不惜违规制作、发行和传播邸报,由此发生了多起伪造及传播邸报的“伪邸抄案”。
2.1 顺治朝伪邸抄案
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清廷吏部官员冯应京收受随州知州程文光的贿赂,采取欺上瞒下、偷梁换柱之法,伪造皇帝的朱批“依议”,意在推荐程文光去重要州府任职。该朱批邸报在民间报房发抄时,被人发现举报。此事泄露后,冯应京和其助手书吏李德美被绞杀,京报经营者茅万懋则被刑部追查审讯。
据现有文献记载,这桩顺治朝伪造皇帝朱批案是清代最早的伪邸抄案。作伪者的目的很有意味。作为吏部官员的冯应京是因为接受了他人的贿赂,因财作伪。作伪的报房人茅万懋,显然是为了扩大邸抄的阅读和销路才接受这笔业务的。从后来的审讯口供中得知,报人茅万懋有点被蒙蔽的感觉。但作为报人,他十分清楚清廷对邸抄严格的管控,没有六科的发抄,不得随意抄印。他事发后解释说:作为专门做刻发报生意的人,原来是知道不能尽行刻发的,但是,冯应京谎骗说是陈年的旧本,所以没有追问他,就尽行刻发传抄了[14]。冯应京没有告诉茅实情,试图瞒天过海,结果落得个身死名裂。
2.2 康熙朝伪邸抄案
在清代《圣祖仁皇帝圣训》《平定准噶尔方略》《东华录》等文献中,皆有关于康熙朝伪邸抄案的记载。据《圣祖仁皇帝圣训》记载:
“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丙申三月戊午,九卿议覆贵州巡抚刘荫枢题请缓图北征一疏。上曰:策妄阿喇布坦无知蠢动,侵扰我哈密,应发大兵即行殄灭。但朕好生为念,不忍骤加剿除,因备兵边地,遣使宣谕,俟其悔罪自新,为中外生灵计其万全措置之际,必筹其前后,虑及久远,防微杜渐,始合机宜。……刘荫枢尚未衰迈,着乘驿前赴军前,尽心周阅矢公详议具奏”[15]。
这段训示是康熙对刘荫枢的奏折所做的御批。刘荫枢的奏折已经看不见了,但从皇帝的谕旨中基本能看出事件的原委。刘谏阻皇帝不要“逞一己之怒”“形诸声色”“统兵亲剿”,而要“缓图北征”“分清边界”。这份谕旨非常明确地说刘荫枢是“听信讹传邸抄”才“妄行具奏”的。到底刘荫枢如何听信讹传邸抄?“讹传邸抄”从何而来?怎样传到刘荫枢之手?这些都已不得而知。但是,刘荫枢“听信讹传邸抄”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最终他被发配到傅尔丹等地种地。据《平定准噶尔方略》记载:
“遣刘荫枢军前种地。刑部议奏原任贵州巡抚刘荫枢供称:臣年老昏愚,茫无知识,伏见皇上用兵西陲,妄行奏折,及命臣赴军前,周阅营垒诳言,适逢大雪,坠马伤足,病甚难行,又不请旨,径回甘州。蒙恩宽恕,令臣仍往看雪,又不遵行,妄求宽免。蒙恩令臣赴任,彼时病势渐减,遂尔直行前往。种种乖谬,罪应万死。刘荫枢应革职,拟绞立决。但议政大臣等,前于不肯进兵之提督师懿德议以立绞。奉旨暂停治罪。刘荫枢亦应暂行停决,发往侍郎海寿处种地,俟大兵回日治罪,奏入得旨:刘荫枢岂可复行发往陜西,着发往傅尔丹等地方种地”[16]。
刘荫枢因听信伪传邸抄,险些被判以绞刑,最终被发配充军。此为因讹传邸报而引发的封疆大吏被处罚案。
2.3 雍正朝伪小抄案
雍正时期,报禁更严。朝廷一律禁止小报的发行。雍正元年规定:“书吏、提塘、京报人等,除红本上谕外,如有讹造无影之辞者,该司坊官严行察拿。……吏、兵部科衙役及各省报房,探听事件,捏造言语者,该司坊官严行察拿”[17]。
即便如此,“伪小抄”事件仍时有发生。最著名的就是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五月发生的“雍正游园伪钞案”。事件的过程可以从皇帝的御批中得以窥见:
“初五日,王大臣等赴圆明园叩节毕,皇上出宫登龙舟,命王大臣等登舟共数十只俱作乐,上赐蒲酒,由东海至西海,驾于申时回宫等语。夫人君玉食万方,偶于令节宴集群臣,即御龙舟奏乐赐饮,亦蓼萧湛露之意,在古之圣帝明王亦所不废,何不可者。但朕于初四日即降旨,令在城诸臣不必赴圆明园叩节,初五日仅召在圆明园居住之王大臣等十余人,至勤政殿侧之四宜堂赐馔食角黍,逾时而散,并未登舟作乐游宴也。……而报房竟捏造小抄,刊刻散播,以无为有,甚有关系。着兵、刑二部详悉审讯,务究根源,以戒将来,以惩邪党”[18]。
雍正皇帝御批中说,皇帝和群臣偶尔筵宴,赏赐臣僚酒食,本无可厚非。但是“报房竟捏造小抄”,捏造了君臣“登舟作乐游宴”之事。雍正非常生气,命兵、刑二部捉拿审讯,严肃惩处。
这道谕旨中所提的专门刻印小抄的报房,显然不可能是提塘报房,因为提塘报房深知关于皇帝活动报道的慎重性,不会如此轻率发抄传播的。从报道的内容上看,“登舟作乐游宴”之事显然不符合提塘报房发抄内容须经“六科所抄”的规定。因此,可以推定这是一起由民间报房抄传引起的“报案”。
这份“捏造”报道的始作俑者何遇恩、邵两山①关于“邵两山”其人,目前的资料多称之为“邵南山”,不知何故。笔者猜测,可能是因为方汉奇先生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上首先使用这个名字,后来的研究者遂相习沿用。但《四库全书》称其为“邵两山”,本文从“四库”说。两人后来被处决: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五月十九日,刑部等衙门议奏:捏造小抄之何遇恩等依律斩决。奉上谕,何遇恩、邵两山俱改为应斩,着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报房小抄捏写端午龙舟游燕之事,以无为有,甚属可恶”[19]。
有学者称:何遇恩、邵两山“是中国新闻史上因办报获罪被杀的有姓名可考的最早的两个人”[20]。
2.4 乾隆朝伪邸抄案
有清一代,影响最大、最富政治意味的伪邸抄案,当属乾隆年间的“伪孙嘉淦奏稿案”。此案应该叫什么名称,有不同说法[21]。按照乾隆时期的谕旨所言,有“伪稿案”“伪造孙嘉淦奏本案”“捏造孙嘉淦本稿”等多种称呼,用得最多的是“伪稿案”,但其实质就是伪邸抄案。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七月,江西抚州卫千总卢鲁生闻听乾隆皇帝要南巡,认为此举一定会劳民伤财,百姓遭殃,“虑及办差陪累,妄希停止巡幸”。于是,卢鲁生“起意捏造伪稿”。他在南昌卫守备刘时达家,与刘时达共谋,“编造奏稿”,凑成“五不解、十大过各目”。考虑到当时的名臣孙嘉淦“肯上条陈”,以敢言著称,就假托孙嘉淦之名,伪造了一份奏疏,交给书办彭楚白钞传[22]①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说的是:“交各提塘传抄,印入《京报》”。但从乾隆谕旨中并没有发现交给提塘报房的记载,不过从发行如此之广的角度看,通过驻京提塘发抄的可能性是有的,惟没有史料证明。。其目的,是想借此来阻止皇帝的南巡。
此封“伪孙嘉淦奏稿”在社会上流传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八月,才被云贵总督硕色发现,然后上奏禀报皇帝。硕色是在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七月初一日接到古州镇总兵宋爱的秘密奏报才知道的。当年六月二十二日驻安顺府提塘吴士周发现邸报中另附了这份“伪稿”。
乾隆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怒,立即传谕步军统领舒赫德、直隶总督方观承、河南巡抚鄂容、山东巡抚准泰、山西巡抚阿思哈、湖北巡抚恒文、湖南巡抚杨锡绂、贵州巡抚开泰,令他们“选派贤员,密加缉访,一有踪迹,即行严拿”[23]。
经过两年多的追查,朝廷终于抓获肇事者。此案影响之大、迁延之广,在整个大清报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仅《东华录》中关于“伪孙嘉淦奏稿案”的谕批就达二十多道。其中,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三月的一道谕旨,带有总结性,道出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庚申,军机大臣刑部奏捏造伪稿一案,先经云贵总督参奏,辗转追至江西传钞之江锦章,递究至彭楚白,经江抚审拟,彭楚白得稿于段树武,发落完结。臣等因案情可疑,将传钞援受未明之段树武、彭楚白等,请旨行提到京,详细推究。据段树武供称,实未给稿,曾经彭楚白告知伊另有得稿来历。及研讯彭楚白,始供系伊本官抚州卫千总卢鲁生给稿传钞,所供得稿于段树武,实因卢鲁生之次子卢锡荣属令隐瞒等情。随提卢鲁生审讯,诘其得稿来历,初供系伊次子卢锡荣不知从何处钞来,迨再三究诘,忽供系伊在赣州卫千总李世璠处得稿于永新所千总石宪曾,忽供得稿于南昌卫守备刘时达,并称系刘时达之子刘守朴任所寄来。因其言语支离,反复开导,始据该犯供认自行起意,与刘时达商谋捏造。缘该犯系四川南部县人……该部另行请旨”[24]。
追查的结果是:卢鲁生是整个报案的始作俑者,为主犯,被判决凌迟;刘时达属合谋的从犯,此外,牵涉此案的卢鲁生之子卢锡龄、卢锡荣等被判斩监侯。
“伪孙嘉淦奏稿案”从调查到审讯,前后长达两年九个月,从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七月一直延续到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三月。此案涉及范围广,波及全国十六个省份。据《东华录》统计,案件牵涉人员多达四十多人。此“报案”的内在意蕴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政治角度来看,此案属于典型的政治事件。乾隆皇帝自视甚高,号称十全老人。此事的发生让乾隆帝感到了政权的危机——各级地方官员不仅玩忽职守、敷衍塞责,有意放任伪奏稿流传,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的味道。这是乾隆绝对不能容忍的,他要通过彻查此案,肃清官员的思想,实现政权的巩固。
其次,从传播学层面看,“孙嘉淦伪稿”的传播无论在范围、效果或是影响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一,“伪稿”突破了“提塘”这一把关人。根据清代的邸报发行体系,邸报的发行有几个关键节点——通政使司、内阁、皇帝、六科、提塘。这份“伪邸稿”很有可能是在提塘抄传环节出了问题。如果是提塘官有意为之,则表明提塘是将“伪邸稿”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发泄对皇帝的不满情绪。如果说没有经过提塘环节,令人困惑的是:纯粹的民间报房印刷的报纸又如何进入政府官员的阅读视野呢?前后推论,这份“伪稿”应该是经过了提塘的抄传。第二,从传播范围上看。“伪邸稿”传播达十六省之广,除了官员的懈怠或放任之外,“伪邸稿”激起了广大受众强烈的新闻欲,这可能是它能够传播如此之广、时间如此之长的重要原因。
3 清廷对邸报的控制
从朝政信息的流通和传达角度来说,清廷需要通过邸报或其他报纸来实现政令的上传下达,朝政信息畅通有稳定社会民心的作用。从此种意义上说,邸报是清政府所需要的和不可或缺的,有清一代基本上没有禁止过邸报。但另一方面,为了政权的巩固,清廷采取多项措施,严密管控邸报的运行,严厉打击各种违规的编辑、传抄行为。清廷对于邸报的控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制度控制
清代不同时期颁布了一系列管理邸报的规定,并根据社会舆论形势的变化,不断更新和完善。这些规定并非专门法规,现多见于《清会典》《清会典事例》《钦定大清会典》《清实录》以及“历朝朱批奏折”之中。比如清廷对邸报抄传有明确规定,在正式公文“到部”之前,禁止邸报传抄或发布相关内容,否则将予以惩罚。清廷对这项制度非常重视,一直予以强调和完善。如康熙十七年议准:
“凡奉旨事件未到部之先,即行钞传报知者,将传报之人交部治罪。该科给事中,罚俸六月”[25]。
《大清会典则例》规定:
“凡提塘与衙役人等,漏泄密封事件,仍照定例分别议处外,其虽非密封,但未经御览批发之本章,即钞写刋刻图利者,该管官失于觉察,该管科道不行察参,皆照漏泄密封事件例,分别议处”[26]。“红本已奉旨到科,未经到部,有豫钞泄漏者,将本科给事中议处,泄漏之人,交刑部治罪”[27]。
雍正时期,邸报较政府公文先期到达四川,致使“钦犯”程如丝在“部文”到达之前即获知消息,未及正法即“自缢身死”。雍正针对这起“塘报”泄密事件,再次强调邸报抄传的时限规定。
“雍正六年二月。又奉上谕。据四川巡抚宪德奏称,程如丝于未正法之先,自缢身死,固属地方该管各官疏忽之咎。但程如丝正法之旨,于部文未到之先此信已早到五六日,显系提塘于塘报中先期漏泄。向来提塘之弊,似此预通信息者甚多,大有关系。请将各省提塘通行革退等语。朕思:提塘管理京报,设立已久。若禁革不用,似属难行”[28]。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又奏准:“各省督抚提镇投递各衙门掲帖,凡关渉紧要事件,均用密封投递。其寻常事件,亦不许先行刊刻传播。……如提塘私行探报,先期传播者,察出送刑部治罪”[29]。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议准:“各省提塘,钞发本章必须谨慎,有应密之事,必竢科钞到部十日之后,方许钞发。如有邸报先于部文者,该督抚将提塘参处”[30]。
对于无中生有或未经御批的奏章,清廷更是严禁传播:“一应题奏本章,非经奉旨下部,不准擅以揭帖先行发抄。其有原无本章,径以私揭妄付邮递抄传者,尤宜严禁”[31]。
3.2 内容控制
清廷对于邸报内容有非常明确的规定。邸报的内容完全来源于皇帝的谕旨和臣僚的奏章,此外别无其他信息源。即使是臣僚的题本章奏也分“发抄”与“不发抄”两部分。据统计,可以“发抄”的内容只占全部章奏的“十之三四”[32],其余“十之六七”被归入宫中档案库,秘而不宣。
清廷控制邸报内容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严禁提塘、报房人将自行采访的内容刊登在邸报上。清廷对此有明确规定:
“康熙五十三年议准:各省提塘除传递公文本章,并奉旨科钞事件外,其余一应小钞,既行严禁,违者照刷造小说淫辞例,革职治罪”[33]。
提塘的职责只是传递政府公文、臣僚章奏和科抄的邸报,其他内容“概行严禁”,违反者将按照“刷造小说淫辞”论处。“小说淫辞”是清廷言禁、文禁、报禁等“三禁”内容之一。自行采访、编辑、刷写“小说淫辞”者,将会受到惩罚。
其二,严禁抄传与科抄不同的内容。邸报的内容都来自“科抄”,除此之外的内容一概不许抄传。如“近闻各省提塘及刷写报文者,除科抄外,将大小事件探讨写录,……请严行禁止,从之”[34]。
这种管控方式即使到了晚清时期,仍在施行,如1908年清廷颁布的我国第一部新闻法规《大清报律》就规定:“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35]。
清廷规定,禁止邸报刊登如下内容。
其一,真实但不宜发抄的内容。即使信息内容是真实的,但未经六科发抄,邸报也不得抄写和刊行。如臣僚章奏,皇帝御览之后认为不宜发抄,最后也只能存入宫中档案。《大清律例》规定:
“凡平常事件,虽非密封,但未经御览批发之本章,刊刻传播,既行严禁,如提塘与各衙门书办彼此勾通,本章一到,即抄写刊刻图利者,将买抄之报房,卖抄之书办,亦俱照漏泄密封事件例治罪。”[36]
清廷密件传播的主要形式是“廷寄”。雍正以后,出于皇权斗争的需要,皇帝的谕旨分两类:第一类是明发谕旨(或称内阁奉上谕)。明发谕旨由军机大臣书写,皇帝批览,经内阁六科抄传后,由邸报传递给京师衙门和各省的督抚提镇。另一类即“廷寄”。对于一些重要的信息、文书,为防止泄密,就不交内阁六科,而是由军机大臣直接密封,军机处钤印后,交兵部捷报处寄送给各省有关官员,这就是“廷寄”。廷寄属密件,提塘、报房人是不能抄报的,否则就会构成泄密罪。
其二,虚张内容的信息。所谓虚张内容,是指所报道的内容有一部分是事实,但绝大部分细节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如上文提到的“雍正皇帝端午节与大臣游览圆明园”报道。该报道整体来看是真实的,雍正皇帝五月初五确实在圆明园,也接见过十几位大臣并进行过简短的叙谈,但绝没有“乘游船”和赠臣僚“葡酒”之事,报道的很多细节显然是报房人自己想象虚构出来的。结果两位新闻报道者何遇恩和邵两山以“捏造小抄,刊刻传播”罪被处决。
其三,虚假伪造,子虚乌有,或者是提塘或报房人出于某种政治或经济目的而恶意编造出来的信息。伪造邸报内容性质严重,处罚也最为严厉。雍正元年就明确规定:
“凡书吏、提塘、京报人等,除红本上谕外,如有讹造无影之辞者,本科给事中,察拏治罪。”[37]
“讹造无影之辞”即伪造邸报内容的行为,如伪造御批、伪造奏稿等情形,这些都要被治罪的。
概言之,清代对于新闻传播的管控是十分严密的,尤其是对代表政府观点的邸报或《京报》的控制,更是到了严酷的程度。由于管控严厉,导致清代的邸报基本上停留在政治工具的层面,只能发挥为朝野上下传达信息舆情,服务封建政权的功能,而未能发挥新闻舆论的社会监督功能。这也是清代末年随着西方近代报业的进入,中国古代报业迅速衰落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