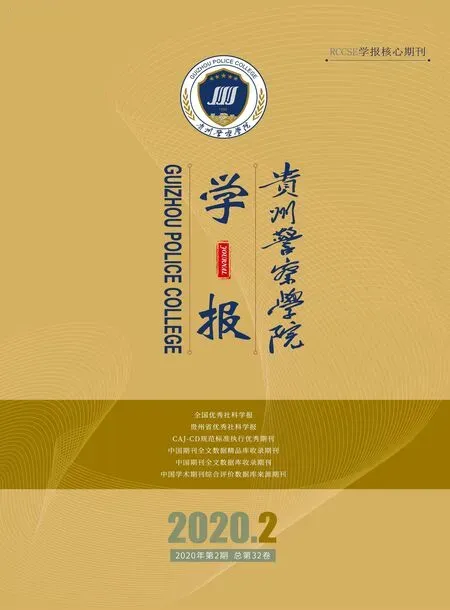论价值权衡论证的道德根据
2020-03-15陈灼灼陈伟功
陈灼灼,陈伟功
(1.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2.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哲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24)
在启动法律推理程序之前,有一种预设的“结论”其实已经或明或暗地出现在人的意识中了。可以说,直觉往往跑在理性思维之前,而逻辑推理、修辞论证只是对已直觉到的某种“结论”进行证实或证伪。理性思维为了保持客观性和确定性,力图要摆脱情绪、臆测、幻想等非理性的纠缠,这也就是“价值中立”观念在理性思维领域被置于崇高地位的重要原因。但在理性思维之前,其实价值及其判定已经乘着直觉的翅膀在人的意识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追求确定性的理性思维则坚守怀疑的精神要冷峻地对价值秩序进行一番分析、衡量,以判定最终哪种价值起决定性作用。本文拟对此观点进行论证,并主张在理性思维的传统中,在一些有代表性的法律案件审判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比较稳定的“价值秩序”,而这种“价值秩序”表现为生活世界的一种道德根据。“虽然在上个世纪,我们费尽心机地想使司法自由裁量无立锥之地,但事实业已证明,规则和机械适用在某些场合仍然是无能为力的。当今的趋势,是扩大自由裁量的范围,而不是去限制它。使自由裁量变得可以容忍的正确方法,或许就是承认此时我们已进入了伦理学的领域,而伦理学同样是一门科学,并且也包含了一些原则。”[1]庞德的这段话恰好说明,本文的努力也许是值得的,应该不会一无所获。
一、“先在”的价值
人不仅有会思维、有理性的本质特征,更体现为有意识、能感受的原初本性。在其通过语言、运用各种工具进行理性地思维之前,实际上人已经通过自己的整个身体及其各种感官对包括自身在内的世界进行了感受,而这些感受有的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有的则难以表达甚至表达不出来。在感受中,必然要遇到一些“抗阻”,或者说,正是由于有了“抗阻”的存在,人的感受才得以产生;如果没有“抗阻”,也就没有感受。这些“抗阻”就是其感受到的对象,如果某对象引起有意识的注意,人就会主动地去了解、辨认这些对象究竟是什么、它们怎么样。马克斯·舍勒指出:“抗阻是一个现象,它以直接的方式只是在一种追求中被给予,亦即只是在一个意欲中被给予。在它之中并且只有在它之中,对它的实践实在的意识才被给予,这种实践实在同时也始终是价值实在(实事和价值事物)。”[2]而价值就是这样一种“抗阻”,人在直觉感受中与其遭遇,而意识则可能对此产生好奇,进而努力去弄清价值是什么、价值怎么样。因此,这种“遭遇”是首要的、先在的,好奇、认识、分析等则紧跟其后。
那么,价值作为一种特殊的“抗阻”,其特殊性表现在哪里?首先,价值必须依附于某种“价值物”而存在,否则,价值就不能表现出自己来。当然,这里所说的“价值物”并不一定特指某种物体,而是指称那些现实的存在。比如,人们一旦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一定会先了解那里有什么规矩、有什么法律制度,并告诫自己千万不要违法。这些规矩和法律条文就是“价值物”,法律价值则依附于其上。这里的法律价值主要指社会秩序稳定,人的权利得到保护,义务能够被强制实施等。其次,价值能够被人的“直观”或“直觉”感受到。例如,价值最通常的特征是“有用性”,即其能够满足人们的某些需要,这就是价值物在被人们感受到时,依附于其上的“有用性”价值就表现出来了。当然,价值物是被人的身体感官感受到的,而价值被人感受到则不是通过身体的感官,它的“通道”是意识的“直观”或者说“直觉”。再次,价值世界非常丰富,不仅有“有用”的价值,还有真、善、美的价值,有生命健康的价值,更有精神方面崇高、神圣的价值,更不用说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了,价值不可能被穷尽地列举完,甚至可以说,有多少修饰性的词,比如形容词、副词等,就至少有多少价值。对于如此纷繁复杂的价值世界,绝不能仅仅以“有用”与否来对其进行价值判定。那么,对于如此众多的价值,它们不可能具有相同的“价值”,即,它们不可能在测量的意义上是同一个重量级的,应该有高有低、有深有浅、有大有小、有长有短等等,能不能从某一个维度对价值进行一种排列?下文对此进行分析。
二、“客观”的价值秩序
如果同时对众多价值从不同维度进行比较和评估,试图得出一种价值秩序,那样的难度一定很大,但仅从一个维度得出一种价值秩序还是可能的。问题是,仅从这个维度得出的价值秩序能够运用于别的维度吗?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答案,但循着这条思路去考察却可以获得不少有价值的信息资料,并使我们的思维得到很有效的训练。本文仅能够限于从“直观”的维度进行考察,以便于得到在未经理性思维加工前、尚未运用语言进行表达前的那种原初的价值秩序。当然,直观虽然走在理性思维和语言表达之前,但我们要把直观到的内涵重新用语言表达出来,这就需要现象学的“加括号”或者说“搁置”的方法,以便尽可能“还原”原初的那种直观内涵,从而呈现出那些价值间应有的秩序来。
我们先来做一个思维实验,反思人生活在世界中,必然会感受到哪些“抗阻”。
首先,食物是最根本的对象,人这种有机体要活下去,必须先满足饮食之需要,那么,所有这些食物本身当然有价值,但人并不仅仅以享受这些食物的价值为满足。即人们常说的“人吃饭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不是为了吃饭”,饭本身具有自身的价值,而依附于这种价值之上的就是为了能够活着的生命价值。因此,包括食物在内的任何财产本身一定具有自己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位于这些价值之上的却是“生命价值”。排除任何前提性条件,比如,设定这些所说的财产与当下言说者无关,那么,他们可能都会认可“生命价值”高于财产本身的价值;对于财产所有者而言,他可能就不这么认为,他当然认为他的生命价值要高于这些财产的价值,但别人的生命价值就不一定如此了。但从本质上来看,他认为自己的生命价值更高于财产价值,这是直观;而不认为别人的生命价值更高于财产价值,这实际上是一种“价值的颠覆”,即把更低的价值置于更高的价值之上,属于自欺欺人即“价值的欺罔”。从而反证了生命价值高于财产价值这一事实。
其次,必然有比生命价值更高的价值,如人们为什么有时候宁愿舍弃生命而维护某种价值?这一现象表明,被维护的价值更高于生命价值。除了“价值欺罔”之外,我们来思考高于生命价值的那一阶邻近的价值。君子不食“嗟来之食”,志士不饮“盗泉之水”,西方传统中有“决斗”的习惯,这是为什么呢?显然,比生命更珍贵的是人人能够感受到的“尊严”,这是一种人格价值,这种唯一性的个体价值相互不可替代。生命价值是由人的身体所感受到的,而这种人格价值却是由人的心灵所感受到的。如果从反面来讲,当人格价值遭遇毁灭时,人们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当然也有大量的事实表明,人们在一些特定环境中会忍辱苟活。如果说苟活是为了维护或争取比人格价值更高的价值,那么,这样的行为本身也就又具有更高的价值了;如果苟活仅仅是为了生命本身,那么,这可能就更清楚地反映了“价值的颠覆”,因而会被人们所唾弃,比如叛变、不忠、投降等行为,这些行为所毁灭的则是比人格价值更高的价值了。
再次,如果说人格价值是属于个体的价值,那么,属于共同体的价值则又高于这些人格价值了。为什么共同体价值高于人格价值呢?可以说,这是我们能够直观到的本质现象,难以通过分析、推理或论证等方法来证明,这些证明的工作当然是值得去做的,而实际上这种原初的本质直观却是后继的分析、推理、论证等工作的基础。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而直观到某种本质,这是一条形而上学的原理,是我们的意识从事进一步思考的基础。人们在一些特定环境中会舍弃自己的生命价值、人格价值而去维护共同体的价值,比如,警察打入贩毒集团内部,忍受与毒贩沆潔一气的耻辱,冒着生命危险搜集证据的英勇行为,这就是为了维护人类共同体价值的安全而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价值与人格价值。而毒贩却为了金钱而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和人格价值,吸毒者为了身体能够享受那种变态的过瘾感觉而宁愿放弃包括生命、人格在内的一切,诸如此类,这些都是“价值的颠覆”。
上述文字简略地对价值及其秩序进行了概要式的描述,也许基本能够提供一种进行理性思维的框架。这个直观到的框架是原初的被给予的基本事实,我们可以进一步丰富这个框架,尽可能比较详尽地完善这个价值体系,那样一定可以建立一套扎实的价值理论体系,从而可以更深入地体会、理解并践行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过,这个工作需要一个长期而艰辛的积累过程,在此不再赘述。本文的目的是在这个框架基础上为法律推理探寻其价值基础和道德根据。考夫曼引用拉德而鲁赫的文字,其中提出三个价值主体:“个人主义的社会、超个人主义的生活整体、超人格的共同体”[3]189,其相关讨论与本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说明对价值及其秩序的直观、描述既有其理论意义,也有必要在开放的视域中不断完善这种框架。
三、“反思”的理性思维
法律人在第一时间面对案件时,往往是先产生一些直觉,他意识到相关的价值,对事实与应当怎么做有了初步的判断和假设,然后就寻找各种证据来对它们进行证实或证伪。一般情况下,事实清楚,法律依据确凿,那就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按照法律条文进行处理,这是没有任何悬念的。问题是有些案件比较复杂,往往是事实很清楚,但法律依据之间产生冲突,或者法律虽有规定,但在具体情况下依法处理却与情理相悖,或者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行为本身的确违背人性或公序良俗,等等,在不能一目了然而进行判定的情况下,必须进行权衡、斟酌时,一定是对相关的价值及其秩序的认识不明确,对相应的价值无法做出识别和比较,这时,就需要在理性上对价值进行反思。
也就是说,法律人此时通过直观而感受到了价值,但价值及其秩序并没有被清楚地呈现出来,因此必须对这些模糊的价值直观进行反思,清理掉无关紧要的表象,而去把握住案件事实的本质。现象学上称这种方法为“搁置”或“加括号”,也就是要拭去那些遮蔽事实的面纱,而还原、呈现价值本身。比如,有些案件事实很清楚,但它损毁的是什么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举例来说,如“四川南江县‘婚内强奸’案”,法院判决的结论是:“四川省南江县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吴某与被害人王某‘夫妻关系还处于存续状态’为由,认定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强奸罪”[4]131,而“上海青浦区‘婚内强奸’案”,法院判决的结论是:以“被告人王某与被害人已不具备正常的夫妻关系”为由,“认定其行为构成强奸罪”。在这两个案件中,事实很清楚,但行为是否触犯了《刑法》存在争议,法官以“夫妻关系”是否存续为依据来断定“强奸”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从而忽略了妇女的身体自主即及其人格价值。这样的判决理由,就是用“夫妻关系”这张面纱遮蔽了身体及人格价值。如果说这样的案件尚属简单明显,尚且出现论证和推理不充分的裁决,那么,遇到那些复杂的疑难案件时,则更容易导致不充分的裁决了。
比如发生在美国的“海因斯诉纽约中央铁路公司案”中,事实很清楚,小男孩爬上河堤的一个跳板准备跳水时被铁路公司所有的电线杆上掉下的高压电线电死,该案的问题是,铁路方是否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下级法院认为不应该,理由是小男孩“非法入侵”铁路方的土地;而上诉法院则判决被告即铁路方应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比起“土地所有权”来说,个人生命健康更应该得到优先保护。这个案件说明,价值及其秩序就在那里,人们通过自己的直观应该能够感受到,但这种感受也许是模糊的,应当通过理性的反思,还原价值秩序,使具有更高阶位的价值得到保护。然而,正如王洪教授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律并没有规定这些利益或价值的选择次序或排列等级。一旦面临法律冲突,就可能面对不同利益或价值之间的一场激烈角逐,就需要法官在具体案件中且在正义的天秤上对冲突的利益或价值进行比较与权衡并最终做出选择。”[4]150法律虽然没有规定价值秩序,但价值及其秩序却是一种现实存在,因此,法官们此时要做的工作就是要通过理性思维去发现它们,并依此为根据而进行法律推理。博登海默说:“一个时代的某种特定历史偶然性或社会偶然性,可能会在社会利益中规定或强制制定某些特殊的顺序安排,即使试图为法律制度确立一种长期有效的或固定的价值等级并无什么价值。”[5]显然,这种观点一方面试图从社会历史中寻找法律推理的依据,一方面却又否认这些依据的稳定性、持续性,而采取一种权宜之计,信手拈来,随手即弃,只求当下有用即可。事实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表明,一直有一种比较稳定而长久的价值秩序在那里存在着,人们一直在为拥有它们而进行着努力奋斗。比如,法律的正义价值高于生命价值,这难道不是苏格拉底之死所揭示的永恒真理吗?
四、“权衡”的法律论证
法律人如果对原初被给予的价值进行冷静、理性地反思,也就相当于对案件的认识经过了假设、分析、推理阶段,在这里,他自己基本已经有了答案,而且自己相信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剩下的工作就是进一步用语言论证,在最后这个阶段,不仅要更充分地说服自己,而且最重要的任务是说服听众。在事实论证方面,使听众相信自己对事实的推理是有效的,而且使案件事实本身得到了“还原”,正如发生在美国的辛普森案中,辩护律师所做的“精彩”的事实推理[4]253-254,这当然是法律论证的一个方面;不过,本文要讨论的是,面对清楚的法律事实,如果法律规定也很明确,但其中充斥着左右为难的价值冲突时,法官如何进行判决,如何进行论证才能以理服人?这里的价值权衡论证就不得不诉诸于价值秩序,以此作为道德根据来说服人心了。卢曼认为:“以道德为依据有(令人难以承受)的弊端,这就是不得不否认在判决强制压力下被否定的法律观点具有道德依据。”[6]本文赞成卢曼在此之前对“疑难案件”的分析,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被否定的法律观点具有道德依据”与追求更高阶价值的判决并不矛盾,也就是说,实现较低阶的价值固然也是道德的,但实现更高阶的价值也是道德的,道德价值之间也是可以比较的,两善相权取其重的价值选择本身就是其道德依据。
价值秩序就是人心能够感受到的道德规律,顺应这种规律就可能说服人心,否则,任何判决都有可能留下难以挽回的遗憾。比如,发生在美国的“罗伊诉韦德案”中,胎儿的生命权与孕妇的健康和自由权发生了价值冲突[4]154-156,无论选择保护前者还是保护后者,那样都难以说服人心,但如果像美国最高法院所做的裁决,将孕期分为三段(头3个月、3~6月、7月之后),分别保护孕妇的选择权、健康权以及胎儿的生命权,则比较合情合理地化解了价值冲突,从而提供了解决类似疑难案件的法律智慧。可以说,这种将一个完整的过程分解为几个不同的阶段,运用相应的法律规定加以保护不同的权利,确实是一种智慧。不过,对这个案件的分析依然存在不同的观点,如美国联邦政府司法部首席律师、哈佛法学院教授弗里德代表布什政府提出了推翻罗伊判例的法律意见,主张“国家应当根据多数意见,而不是根据最高法院的判决去制定规制堕胎的法令,为此必须全面推翻罗伊案确立的规则。”[4]156-157本文基本赞成不论是立法还是判决,都“应当根据多数意见”,不仅如此,更要考察这多数意见背后的价值选择。虽然有时候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大多时候,大多数人的价值选择还是正确的。人数的多少不是一个绝对标准,人数背后的价值选择才是最终应当反思、分析、论证的内容。具体在罗伊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很有智慧,是因为他们把握住了个人自由选择的这种人格价值要高于胎儿的生命价值,这并不是说某人的人格价值比他人的生命价值更高,而是抽象地说,“人”的人格价值高于生命价值,具体到一个个体的人,他的人格价值也要高于他的生命价值,而胎儿的生命与孕妇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虽不能混同,但毕竟是完整的一体,因此可以说,孕妇的人格价值依然更高。但是,如果考虑到胎儿的生命不只属于他自己和母亲,而且还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时,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因为,共同体的价值是更高一阶的,所以,禁止堕胎就是基于这种价值选择而做出的法律规定。
由上述讨论可知,当生命价值、人格价值、共同体的价值发生冲突时,多数人一般会依次选择更高阶位的价值,这是一般原则,具体到某个案件中,这种选择有时却变得更加纠结和复杂。其中的原因在于,不同的行为指向不同的价值选择,而这些价值并没有构成一个维度的、扁平的、可量化的世界,而是需要人们不断地去研究,进行更为细致的本质化的还原,进一步探讨深层的价值规律。考夫曼说:“原则上不能抽象叙述一般法律原则在论证上有何种效力方式,而只能依个别事例来解说。”[3]203例如上文所提及的一个问题:某人的人格价值与他人的生命价值相比,哪个更高?我们的回答应该是:他人的生命价值当然要高于某人的人格价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生命价值高于人格价值呢?因为,这是从另一个维度进行考察的:从不同的价值载体来看,他人的价值一般要高于自我的价值,这不是自贬、自谦等等,而是说,从自我的维度来看,他人的生命不是单独地呈现在我面前,而是连同他的人格、他所属的共同体一起作为一个整体而出场的,这么多的价值加在一起,当然要比自我的这个个体的人格价值要更高了。列维那斯说:“承认他人,因此就是穿过被占有之物(组成)的世界而到达他人那里,但同时,又通过礼物而建立起共同体与普遍性”。[7]这就是说,他人与世界联系在一起,之所以一般性地承认他人的价值高于自我的价值,正是基于这个理由。
一个个体、共同体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的价值相比,一般会认为共同体越大,价值越高,这是一般性的原则,在具体的案件中,则需要更为细致的分析。比如在“纽约时报公司诉美国案”中[4]157-162,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的价值相比,到底哪个更高?凭借直觉,可能会得出后者价值更高的结论,但将此案置于当时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具体环境中,言论自由所代表的厌战舆论则似乎代表了比美国政府更大的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因此,美国最高法院竟然以政府“举证不足”为由而判《纽约时报》胜诉,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价值权衡论证复杂性的深入思考。虽然“举证不足”常常是法官在裁决疑难案件时避实就虚的一种技巧和智慧,但这种智慧也许是法官在洞察到更高价值又不能以语言轻易地将其表达出来时所采用的技巧。而法律逻辑作为一门学科则必须研究这些智慧背后所隐藏的本质和规律。我们之所以感到这种裁决很有智慧,是因为它所体现的价值选择符合我们心中的价值排列顺序,至于价值究竟是如何排列的,虽然很不容易搞清楚,更不容易道出来,但这正是理论工作者应该用力的领域。
五、结语
法律裁决必须实现法律正义,而法律正义实际上是对各种价值的权衡,最终使价值的颠覆现象尽量得到纠正,从而恢复各价值在比较中体现出来的平衡,这种平衡也就是指正常的、善的价值秩序得到维护,避免较低价值僭越于较高价值之上的混乱现象。价值秩序并非临时的规定或偶然的发现,而是深深地扎根于人们心中的良知公序,法律人在遇到疑难案件的价值冲突时,只有依据这种价值秩序才有可能得出合理合情的裁决,才能说服人心,实现法律的目的。然而,对价值及其秩序的理论研究并没有穷尽所有可能性,因为这是一个开放且不断发展的观念体系,它与人的实践如影随形,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价值体系也在发展,必须将这个体系深入地揭示出来,才有可能解释并完善现在的法律实践。富勒说:“如果有人要求我指出可以被称为实质性自然法的那种东西——大写的自然法——无可争议的核心原则,我会说它存在于这样一项命令当中:开放、维持并保护交流渠道的完整性,借此人们可以彼此表达人们的所见、所感、所想。”[8]本文认为,价值秩序正是这样一种自然法的核心原则,它不能仅仅是一些理论工作者思辨和研究的领域,也应该是所有法律人在交流当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