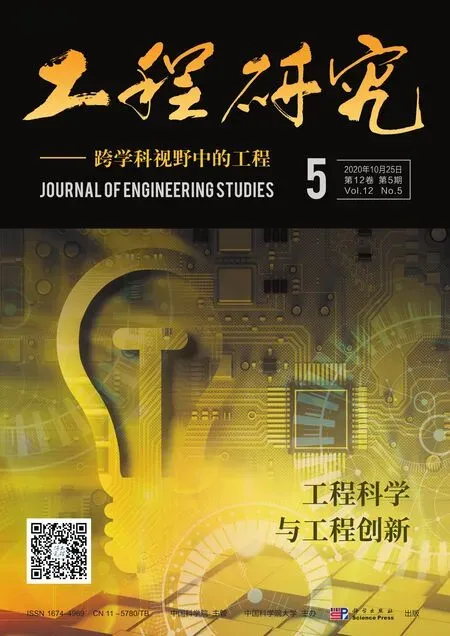工程科学的对象、内容和意义——工程哲学视野的分析和思考
2020-03-14李伯聪
李伯聪
“工程科学与工程创新”专刊
工程科学的对象、内容和意义——工程哲学视野的分析和思考
李伯聪
(中国科学院大学 跨学科工程研究中心,北京 100049)
工程科学不同于基础自然科学:从“研究对象”看,前者以人工物为研究对象,后者以天然自然界和所有自然物为研究对象;从“研究目的”和“发展动力”看,前者是“价值导向”和以满足社会需求与人类福祉为目的,后者是“真理导向”和“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从心理特征看,前者的核心是社会责任心,后者的核心是探索自然界奥妙的“好奇心”;从内部分类原则看,二者也有根本性不同;此外,工程活动中常常出现“错误”,其机制和规律性问题也成为了工程科学需要研究的“特殊问题”,而“自然界和自然现象本身”是没有“错误”的。简要分析了“基础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双向转化问题,对“工程科学”曲折发展的“命运”进行了若干理论反思和政策反思。
工程科学;工程哲学;钱学森;巴斯德象限
1 引言:从“卡脖子技术之痛”和“钱学森之问”谈起
所谓“卡脖子技术之痛”,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以美国对中兴的制裁为导火线,当前国内各界都在对由此引发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和新的反思。现在我们研讨工程科学,其背景也是有关“卡脖子技术之痛”的一种新反思。此外,还有引发社会各界广泛讨论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去看望钱学森,钱老感慨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句话被许多人称为“钱学森之问”。由于影响之大,它甚至还成为了一个“百度百科”的条目[1]。钱老心目中的“杰出人才”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呢?人们也已对其有许多分析和认识。“卡脖子技术之痛”和“钱学森之问”是两个有密切联系的问题,需要联系起来分析和考虑。
从直接对象和直接意义上看,“卡脖子之痛”直接涉及的是技术问题,“钱学森之问”直接涉及的是人才问题。然而,其中深层次的问题应该是如何认识和应对我国“科学-技术-工程体系”的动态关系和升级演进规律这样一个问题。《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杂志刚创刊时曾想组织一个专刊,对大家谈得比较多的“中国如何从工程大国转变为工程强国”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彼时大家都认为这一选题很重要,但因组稿困难未能实现。现在,我们可以把“卡脖子之痛”同工程大国向工程强国的转变问题联系在一起,由此应该能够有新的思考和新的认识。“卡脖子之痛”的“表面痛点”在技术,而病理本质却深藏于我国“科学-技术-工程体系”的“某种程度的动态关系失调状况”之中,以及“适应升级演进规律”的“某种程度的茫然失策现象”之中。人们应该从这里面进行分析,获得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面对“卡脖子技术之痛”和“钱学森之问”,我们应该研究和反思的问题很多,其中的关键点之一是应当从“工程科学”角度进行理论反思、战略反思和政策反思。需要研究工程科学-工程技术-行业演化以及这三者的立体网络结构和关键网络节点问题。在人才战略方面,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到,新时代正在呼唤着中国涌现一批新型“战略工程师”和“工程科学家”。
2 工程科学概念的缘起和命运
2.1 钱学森与工程科学概念
钱学森最早在1947年明确阐述了“工程科学”这一重要概念的本性、内涵和意义。大连理工大学的王续琨教授是研究学科分类问题的专家。按照他的说法,英文工程科学术语“engineering sciences”最早于1665年就出现在英国皇家学会创办的《自然科学会报:数学科学、物理科学、工程科学》(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Mathematical, Physical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不过并没有对“工程科学”进行明确定义和概念阐述。有学者认为,“engineering sciences”真正被赋予特定含义,应当始于冯·卡门1943年在美国《应用数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的“TOOLING UP MATHEM ATICS FOR ENGINEERING(《把数学用作工程的工具》)”一文中[2]。但更多学者说到工程科学概念时都认为这个概念最早是钱学森提出来的。
究竟是谁最早提出了工程科学这个概念呢?是冯·卡门还是钱学森?如果核查冯·卡门的那篇文章,可以看到其并没有直接使用工程科学这一概念。但必须承认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生动、深刻的文章。冯·卡门对工程、数学家、工程师、工程与数学的关系以及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关系等,都有独特、深刻的认识,甚至可以认为他“实质上”已经认识到工程科学是一类具有特殊性质的科学,并且深刻地分析和阐述了工程科学的一些特性和特征,但他没有直接使用“工程科学”这个术语。许多人都承认数学是科学的皇后,其他都是数学的应用,但冯·卡门却将数学视为“服务于工程的工具”。由此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认识角度和评价:有人立足于数学,认为数学就是皇后;也有人立足于工程,认为数学是工程的工具,是为工程服务的。这两种观点表面上矛盾,而实质上并不矛盾。在数学领域,数学是皇后;可是,在工程领域,应该有明确的认识,数学在这里就是工具。工程师和工程科学家都会赞同冯·卡门的这一观点。
工程界还流传着冯·卡门的一句话:“科学家发现已经存在的世界;工程师创造尚未存在的世界(Scientists discover the world that exists; engineers create world that never was)”[3]。不过也有人说,在冯·卡门的文集中没有找到这句话。但既然这句话广泛流传,并且都承认是冯·卡门说的话,这就使我们推论这是冯·卡门经常口头讲述的话。从这句话和前面提到的文章看,可以确定冯·卡门对于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两种职业、这两种社会角色的本性和差异已经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和社会职业的科学家,其任务和职责是“发现已经存在的世界”,而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和社会职业的工程师,其任务和职责是“创造尚未存在的世界”。冯·卡门这句话在我国也传播得颇为广泛,经常被人提起。
钱学森是冯·卡门的学生,钱学森发展和深化了冯·卡门的有关思想。1947年,钱学森回国探亲,先后在浙大、交大、清华做了学术报告。其中在交大的演讲整理后以《怎样研究工程科学和研究些什么》为题在《工程界》1947年第2卷第12期上发表。这篇文章首次以书面的形式明确提出了工程科学这个新概念。1948年,钱学森又发表英文文章“ENGINEERING AND ENGINEE RING SCIENCES(工程和工程科学)”[4]。2009年,谈庆明把这篇文章译为中文,发表在《力学进展》第6期上。2010年,《工程研究》第4期又转载了这篇文章。这确实是一篇首次为“工程科学”进行理论奠基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钱学森首次明确提出了“工程科学”这一基本概念,并且指出了工程科学和基础科学(以物理学为例)存在着两个重大区别(后面讲到基础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或纯科学也都是这个意思)。一个区别是,物理学家要把问题简化从而得到精确解答,这是科学;而工程科学要的是实际问题的近似解,这是不一样的。物理学家的工作常常是不实用的,而工程科学家的工作则必须是实用的。另一个区别是,物理学家对工程问题没有兴趣;工程科学不得不把物理学放弃的问题接过来,发展它的物理原理,形成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工具。所以说,对于搞工程的人来说,工程科学是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工具。对于理论家来说,理论就是个人的成果。但对于工程而言,理论是工程的工具。回到冯·卡门那句话的含义,对理论家来说是以理论为主;可是对于工程来说,理论则是为工程服务的。钱学森先生还曾指出,农业和医药都是广义的工程。这个思想也很重要,这里就不多展开了。钱学森指出工程科学有三项重要任务:其一,关于工程方案的可行性问题;其二,工程实施的最佳途径等,即节省人力、财力问题;其三,在项目失败时能够正确分析失败的原因,并及时提出补救的措施等。应当注意的是,这三项任务都不是“基础科学”的“任务”,但对于工程科学非常重要。在这篇文章中钱学森强调,工程科学是纯科学和工程之间的桥梁,这一桥梁很重要。钱学森还提出了关于“基础科学-工程科学-工程技术”三个层次的思想。关于如何培养“工程科学家”,钱学森也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建议。从以上对这篇文章内容的简述中可以看出,钱学森的这篇文章确实是为工程科学这个新概念奠基的文章。
钱学森提出的“工程科学”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然而,发表这篇文章的杂志《J.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其中文名称是《中国工程学刊》)是中国工程学学会的会刊,1949年后,这个学会在大陆不存在了,但在台湾还有,2015年这个刊物的影响因子为0.241,影响力不大。由于种种原因,钱学森先生1955年回国后没有再使用“工程科学”这一概念,而改为使用“技术科学”这个术语。
回顾历史,虽然钱学森早在1947年就在理论上明确提出了“工程科学”这个概念,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个概念未能在工程界和学术界广泛传播。
2.2 “技术科学”概念的提出和传播
钱学森在20世纪50年代回国后使用了“技术科学”这个概念。实际上,对于工程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关系,包括钱学森和郑哲敏等人都认为,技术科学跟工程科学是一样的[5]。但也有另外一些人认为,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是不一样的。对于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今后还需要有更进一步的研究。
对于技术科学这个术语的来源,王续琨曾有比较详细的追溯和研究。他认为“技术科学”这一概念可能存在多种不同来源。1935年,前苏联科学院根据新的章程调整科研机构,设立了物理数学、化学、地质地理、生物、技术科学、经济和法学、历史和哲学、文学和语言8个学部。1952年,新成立的波兰科学院设立了社会科学、生物科学、数理科学、技术科学4个学部。20世纪50年代初《科学通报》发表了多篇介绍前苏联、波兰等技术科学发展状况的文章。从当时的背景看,或许是这样一些事件,让中国科学界接受了“技术科学”这一术语。1954年,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物理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社会科学部。钱学森是1955年回国的。
面对这样一种现实,一方面我们要学习苏联,另一方面我们这里也有了技术科学部。在“技术科学”概念已被国内科技界广泛使用的情况下,1957年,钱学森在《科学通报》发表《论技术科学》一文[6],使用了技术科学这个新术语,对技术科学的性质和特征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这篇文章进一步深化了他在40年代关于工程科学的思想,虽然在汉语术语上使用了“技术科学”一词,然而对于与其相对应的英文,钱学森仍然明确指出是“engineering sciences”。钱学森还反复强调了关于“基础科学-技术科学(或曰工程科学)-工程技术”三个层次的观点。由此来看,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钱学森分别使用了“工程科学”和“技术科学”这两个不同的“汉语词汇”,但其基本思想是一以贯之的,特别是钱学森指出二者的英文翻译都是“engineering sciences”,这就更加“表明”我们最好还是把钱学森在这个问题上“一以贯之”的思想称为关于“工程科学”的思想。
2.3 “巴斯德象限”的特征和意义
1997年,司托克斯出版了《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7]提出“巴斯德象限”这一概念。提出“巴斯德象限”的背景是布什在《科学——无止境的前沿》[8]一书中阐述的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基础研究不考虑应用;另一个是基础科学有根本意义,是技术创新的源泉。由此形成了基础科学-技术发明-经济发展的“线性科技政策观”。
该书出版以后,有人认为:“D.E. Stokes 的立场只适合于科学比较自主和发达的美国社会,而不适合于缺乏科学自主性的其他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9]。然而,中国大多数学者普遍能够接受斯托克斯的观点。2018年8月,刘鹤副总理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巴斯德象限”[10],立即引起了国内舆论热议。虽然司托克斯在象限上明确命名和区分了玻尔象限和巴斯德象限,并且作出许多深刻的分析,但他并未在概念内涵和定义上明确阐述巴斯德象限的本质特征。从今天所讨论的工程科学这样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理解,从概念内涵和定义上看,我们应该明确地肯定“巴斯德象限”的“本质特征”就是“工程科学”,而与此区别的“玻尔象限”的本质特征是“基础科学”。这样便把基础科学与工程科学概念同司托克斯的象限概念联系起来了。
2.4 世界范围内多国工程院的成立与发展:启示、意义和使命
对于如何认识工程、如何认识工程科学,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工程院的成立和发展,因为科学院和工程院是从制度上承认基础科学和工程科学这一事实或概念的重要标志。这里不妨简单地对比一下科学院和工程院建立的时间: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是世界历史上建立最早而又从未中断过的科学学会,在英国起着全国科学院的作用,就是英国的科学院,是1660年成立的;而英国工程院(Roy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则是1976年成立的,中间隔了17、18、19三个世纪。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于1863年,而美国工程院成立于1964年,相隔百年;俄国科学院成立于1724年,而俄罗斯工程院成立于1990年;中国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于1949年新中国建立伊始,可见新中国是很重视科学的,可是中国工程院成立于1994年。从世界范围看,工程院成立的时间都晚于科学院。为什么工程院“千呼万唤始出来”,其成立晚于本国的科学院?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这说明工程院的成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背后有复杂的原因。这种深层的原因就是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工程技术、对工程科学的认识水平和认知程度不够,工程界和工程科学界的价值自觉和自立精神还有欠缺。而工程院的成立往往标志着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工程技术、对工程科学的认知水平和认知程度达到了一种新高度,并且工程界和工程科学界自身的自觉、自立和自强精神也同样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当然工程院成立后绝不意味着这方面的问题会“一劳永逸”地解决。例如,我国的载人航天、载人深潜、探月工程、三峡工程、青藏铁路、高速铁路、西气东输、特高压输电、超超临界发电、高性能计算机、下一代互联网、超级杂交稻、重大疾病防治等,本来都是“工程领域的成就”,而不是“纯科学”领域的成就,但在进行宣传时,却都被说成是科学成就。这种情况不仅中国存在,美国同样存在,并且美国工程院同样因此而不认同。
工程是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它不是纯科学的单纯应用,不是纯科学的附庸、派生物或衍生品。工程界必须确立工程自觉、自立、自强的基本观点和认识。中国工程院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中成立的。工程院不是中国科学院的一部分。那么工程院成立了是不是意味着就得分家了?这一点不得不佩服钱学森,他下面这个观点既很深刻,也很实用。中国工程院成立的时候,怎样选出第一批院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此,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学部委员成为了基础。但科学院和工程院究竟什么关系?工程院同科学院的技术科学部又是什么关系?钱学森给朱光亚写了一封信,信中他是这样说的:“我现在想到一个中国工程院与中国科学院分工合作的说法,即:全部学问分三个层次——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中国科学院是基础科学兼技术科学,而中国工程院是工程技术兼技术科学”[11]。钱学森再次阐述了他关于“基础科学-工程科学-工程技术”三层次的观点。
2.5 “工程科学”曲折发展的“命运”及其理论和政策反思
上面已经谈到了关于“工程科学”这个概念曲折发展的“轨迹”和“命运”。
钱学森在1947年提出工程科学这个新概念以后,他在工程科学领域不断有新的重大的成就和贡献:一个重大成就是工程控制论,属于工程科学理论研究的成就;另一个重大成就是钱学森对两弹一星的贡献,这是工程技术实践领域的成就;还有一个重大成就是系统工程,主要是工程管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成就。除此之外,他在工程管理的制度创新上,总结和概括了两弹一星研制中总体设计部的成功经验,把它上升为一般性思想,也是一个重大创新。还有就是反复强调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是三个不同的层次。只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钱学森没有继续使用他曾经提出的工程科学这个概念,而改用技术科学这一术语。
关于“工程科学”概念的曲折命运,我们应该有新的理论和政策反思。
从“科学技术工程跨学科研究”和“科技工程经济政策”的角度看,钱学森提出的关于“工程科学”的思想和理论,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郑哲敏院士曾十分敏锐、深刻地指出:工程科学是一类科学,也是一种观点,一种文化。遗憾的是,“钱学森工程科学思想没有很好的实现”,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继承和发展[5]。
同“钱学森工程科学思想没有很好的实现”密切联系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工程师的地位、性质和作用?工程师和科学家是两种不同社会角色和社会职业,具有不同的社会本性和社会职能,社会对他们也有不同的社会要求和社会期望。科学家不能取代工程师的社会职能,而工程师也不能取代科学家的社会职能。不是说他们没有联系,但不能够把工程师和科学家混为一谈,不能用工程师的标准评价科学家,也不能用科学家的评价标准评价工程师。
钱学森曾谈到工程师和科学家之间的隔膜:“在欧洲的一些学者和科学家,对工程师是看不起的,认为他们是一些有技术但没有学问的人。而工程师们又认为科学家是一些不结合实际的幻想者。一般讲来,两方面的人缺乏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合作。”[6]田长霖1984年在西北工业大学有一个演讲,说得就更加尖锐,他表示:“很坦白地说一句,我们做工程师的人,不要说在中国,在美国也没有提到应该的地位,在中国更谈不上,技术科学的地位远远不及它们所应该有的地位。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一定要提高技术科学家的地位”[12]。
3 工程和工程科学的对象与内容
工程和工程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工程的本质进行分析和确定。
工程活动的本质特征是造物和用物。相应地,工程活动的目的和结果就是创造自然界不曾存在的“人工物”,例如火车、汽车、飞机、计算机、手机、电视机、微波炉、机床、住房、体育场等。自然界、自然物是天然存在而不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于是自然物和人工物形成了两类物质,形成了两类物质世界。两类物质世界构成了两类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科学”以天然自然界和所有自然物为研究对象,而“工程科学”以人工物为研究对象。
工程和工程科学的研究内容是什么?一般说来,工程科学研究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研究人工物的原理、设计、制造、功用、结果等领域的规律性问题,也包括与人工物相关的产品和工艺的规律、原理、程序、方法和规则等。另一方面,研究工程活动的规律性问题。工程活动是技术要素和非技术要素的统一,所以,工程科学不仅应当研究工程活动的技术要素和规律,而且还应当研究工程活动中的经济要素、社会要素的规律性问题,包括经济成本,工程管理等问题。它既包括人工物的自然属性,也包括它的社会属性。
4 工程科学和基础科学的比较分析以及二者的双向转化
4.1 “物”、“器”、“事”的联系和区别
“物”、“器”、“事”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中国古代常常不区分“物”、“器”、事”、“器物”、“事物”等概念。在中国古人的眼里,器物、事物、物和器都是一样的。然而从现代的观点看,“物”(一切自然物)、“器”(人工物)、“事”(人的行动)是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含义。“物”中包括了所有的“自然物”和人工物,范围很广。器是人工物。人工物是器,只是“物”中很小的一部分。但这很小的一部分人工物,也是跟我们的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联系最密切,从而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需要承认“人工物”也“属于”“物”,因而人工物也要“服从”“物的一般规律”。“事”是指人的行动。
与此相关,还有一个概念是“理”。这是一个表示规律性、普遍性、共性的概念。所谓科学,可以解释为对“理”的探索和把握。从这种意义上讲,古代的“理”翻译成现代的术语,就是科学,“物”的科学就是“物理”。要注意,这个“物理”不是物理和化学中的物理,这个“物理”是指所有的自然科学。“物理”、“器理”、“事理”具有不同的内涵。自然科学研究“物理(关于自然物的一般规律、普遍规律)”;工程科学则研究“器理”和“事理”(关于人工物和工程活动的一般规律、普遍规律)。“器理”是工程科学,主要研究人工物的规律,比如发动机、飞机、汽车、计算机里面普遍的规律性问题。“事理”是工程活动的规律,它们有不同的内涵和不同的规律。由此看来,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既具有密切联系,又存在根本性区别,需要分别对待。
4.2 “基础(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比较分析
第一,“研究对象”不同。基础科学对象是“所有的自然物”,“所有”二字就意味着“包笼一切没有例外”和“一视同仁没有偏爱”,不管它们与人类的利害关系如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研究应该是“为科学、为真理而研究”,应该以“好奇心”驱动而不能以“利益考量”为导向。例如物理学中万有引力定律适用对象就是“包笼一切没有例外”和“一视同仁没有偏爱”;化学元素周期表对元素的表述也是“包笼一切没有例外”和“一视同仁没有偏爱”;植物分类系统的研究也是如此。工程科学研究对象不是“所有的自然物”而是“数量有限的与人类有利害关系的人工物”,例如车辆、房屋、计算机、飞机、芯片、交通网等。虽然与自然物相比,人工物数量有限,但就其与人类的关系而言,人工物与人类生存关系更加重要,更加密切。人工物与人类的福祉、国家的繁荣富强密不可分。人工物的发展演化,无疑是人类福祉增进和国家更加繁荣富强的基本内容、方法、途径和标志。
第二,“研究目的”和发展动力不同。基础科学的目的是探索真理,就此而言,可以说,科学研究是“真理导向”和“真理标准”的研究,是“为科学、为真理而研究”,从而推动“基础科学”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心理要素也是人类探索自然界奥妙和真理的这种“好奇心”。工程科学研究是以“价值导向”和以“功利效益”作为标准的,工程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利用人工物谋求人类的福祉,从而推动“工程科学”发展的基本动力是满足经济需求和社会需求,是工程师和工程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心。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又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这里所讲的“天行之常”就是自然科学的内容和特征,是真理导向的。而工程科学是价值导向的。荀子又说:“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这里“善假于物”,就具有工程科学的内容和特征,高度赞扬了“善于利用人工物”的作用和意义。
第三,“工程科学”的分类原则和类型划分不同于“基础科学”的分类原则与类型划分。一般说来,基础自然科学是以客体为核心、以事实为基础,根据事物的内在本质进行分类的。例如自然界一切物理变化都属于物理运动,是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自然界的一切化学变化,涉及物质分子结构,属于化学运动,是化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与此不同,工程科学是以主体为核心、以价值为基础,按照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进程进行分类的,具有浓厚实用色彩。例如上天入地下海,便相应产生航空科学、航天科学、海洋工程科学等。
第四,工程科学还要研究工程活动中出现的“工程活动中的特殊问题”。对于自然界来说,没有“错误”。地震、海啸、星球相撞,都不是自然界出现了“错误”。然而工程活动中则常常出现重大事故,这里出现了“错误”。工程科学必须分析和研究工程事故问题,从中汲取各种教训。自然界也没有“安全”问题,而工程活动中的安全始终都是首要问题,“安全科学”成为工程科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还有工程设计的原理和规律性问题,也是工程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莱顿说:“从现代科学观点看,设计无可称道;可是,从工程观点看,设计最重要。”这也是工程科学同基础科学的重要区别。
还有一个“基础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双向转化关系问题。一方面,基础科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工程科学不可或缺的思想前提和基础,原则上只要它需要,其中所有理论和方法都可以移植到工程科学中。因为人工物也是物。另一方面,工程科学基本理论和方法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人类关于物质世界的理性认识,把科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工程科学主要以任务带学科。这方面栾恩杰院士的文章《论工程在科技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创新驱动作用》[13]讲得非常全面、系统。他还讲到“扳机作用”等,在这里笔者不再复述。
5 “工程活动的规律”和“工程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双向转化问题”
关于工程活动规律和工程科学与工程技术双向转化问题,这里简要叙述以下三点。第一,工程活动具有社会性,从而我们就不仅必须研究工程活动中的工程技术规律、工程科学规律问题,而且必须同时研究与此相关的经济规律、社会规律问题。也就是说,工程科学还要研究工程实践中的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等问题。这也是钱学森曾讲到的问题。
第二,从工程技术向工程科学转化,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攀登工程科学高峰”的问题。“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14]同基础自然科学一样,攀登工程科学高峰的任务不但艰巨而且急迫。目前要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核心技术、关键环节,在多数情况下,对我们而言,这样的问题都有属于工程科学领域的新问题,有属于需要克服的攀登工程科学高峰中的险阻问题。
第三,从工程科学向工程技术转化,同样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严重困难,这就是所谓“达尔文之海”的风浪。人们常常把市场比喻为海洋。下海遇到的风浪险阻和困难不亚于登山。在新技术、新产品的“工程化”、“市场化”过程中要解决许多新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工程发展的难点是“应对”下海的风浪问题。无论高校、科研院所,还是工业企业,“面对”“达尔文之海”的风浪时,都不可能有百分百成功的把握,而是必须面对可能“沉船”的风险。人们看到,许多新技术都经受不了“下海的考验”而“壮志未酬”。对于工程技术来说,“下海的考验”是一种“生死考验”。
6 对“工程科学”的理论和政策意义的反思
第一,在认识“科学-技术-工程”关系时,要把“以基础科学为基本动力的线性模式”转变为“更加重视工程科学作用”的“工程科学-工程技术-工程实践”的“立体网络模式”。
第二,必须对工程科学的性质、特点和意义有更清醒、更明确、更自觉的认识。要更明确地意识到工程科学的独特地位、意义与作用。工程科学是工程技术发展的直接基础,是工程技术联系基础科学的桥梁。没有这个桥梁,就不能实现双向转化,基础科学也难以发挥指导工程技术发展的作用。在这里,我还想再引用郑哲敏在《从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谈起》一文中说的一句话:“在科技界,一个极端是按照基础科学的标准来规划和指导技术科学,按组织基础研究的传统方式组织技术科学研究;另一个极端则是把技术科学研究看作是为解决具体工程和生产问题的工作。如此导致一个个产品的开发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也无法与知识的积累互动,长久以往便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在政策制定和科研管理方面,对于科学技术研究如何支持,如何组织,如何评价,认识也都不够,而且缺少统筹规划。”[5]
第三,我国面临着把工程大国转变为工程强国的历史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发展工程科学常常是关键之关键。它是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的孵化器。如果没有工程科学的大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和完成从工程大国向工程强国转变的历史任务。
第四,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时,必须把工程科学创新、工程技术创新、工程制度创新等密切结合起来,实现工程科学创新、工程技术创新、工程制度创新三者的相互促进。
第五,许多“卡脖子技术”的“命门”是工程科学问题。于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关键环节和核心内容常常就是要解决与其相关的一系列工程科学问题。在这种情况和形势下,攀登工程科学高峰往往就成为解决卡脖子技术的关键环节和核心内容。
第六,我国科学-技术-工程体系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任务。为此,必须把大力发展工程科学作为实现我国科学-技术-工程体系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之一,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中的一项战略任务。否则,就难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和历史任务。
最后,时代呼唤涌现一大批工程科学家和战略工程师。冯·卡门、钱学森和田长霖都曾提到过工程科学家这个概念。工程科学家是从事工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不同于纯粹自然科学家,也不同于一般技术专家。对于工程科学的发展、工程技术的发展,对于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等,工程科学家都将发挥关键作用。战略工程师是工程师中的领军人物,不仅可以丰富工程师的知识谱系,而且无疑是中国从工程大国走向工程强国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的建设力量。
[1] 钱学森之问. 百度百科条目. [2019-10-10]. https://baike. baidu.com/item/钱学森之问/3287915?fr=aladdin.
[2] 王续琨. 科学学科学引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287-288.
[3] Bucciarelli L L. Engineering Philosophy[M]. Delft: Delft University Press, 2003: 1.
[4] 吕成东. 他日归来:钱学森的求知岁月[M]. 杭州: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277.
[5] 郑哲敏. 从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谈起[N]. 学习时报, 2017-12-27.
[6] 钱学森. 论技术科学[J]. 科学通报, 1957(3): 97-104.
[7] 司托克斯. 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M]. 周春燕, 谷春立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9.
[8] 布什. 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M]. 范岱年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9] 王鸿飞. 黑暗中的烛光——1000年来的科学发展及20世纪社会中的科学[N]. 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 2000-1-25. [2019-10-1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 php?mod=space&uid=460156&do=blog&id=827397.
[10] 刘鹤.推动全球机器人领域开放合作发展,更好造福人类社会[EB/OL].网易科技, 2018-08-16. [2019-10-10]. http://tech.163.com/18/0816/10/DPAUNN73000998SL.html.
[11] 葛能全, 陈丹. 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历程[J]. 科学文化评论, 2016(1).
[12] 田长霖. 田长霖教授在西工大做报告[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1984(2).
[13] 栾恩杰.论工程在科技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创新驱动作用[J]. 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 2014(4).
[14] 马克思. 资本论[M].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6.
Object, Contents and Significance of Engineering Sciences: Analysis and Thinking from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Li Bocong
(Center for Interdisciplinary Engineering Studi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Engineering sciences and basic natural sciences are two areas of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object”, artificial objects are adopted as research objects in engineering sciences, whereas nature and natural objects are adopted as research objects in basic natural sci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purpose and development motivation, the former is value-oriented and aims to meet social needs and human well-being, whereas the latter is truth-oriented and pursues truth for that purpose. Based on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core of engineering sciences is the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ore of basic natural sciences is the “curiosity” to explore the mysteries of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s, both areas are also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In addition, errors often occur in engineering activities, and their mechanism and regularity have become uniqu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investigated in engineering sciences, while nature and natural phenomena involve no errors. This paper also briefly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the two-way transformations of bas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discusses theoretical and policy reflections on the fate of engineering sciences.
engineering sciences;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Tsien Hsue-shen; Pasteur’s quadrant
2020–01–05;
2020–09–10
李伯聪(1941–),男,教授。研究方向为工程哲学、工程社会学、工程史。E-mail:libocong@ucas.ac.cn
N03;B01
A
1674-4969(2020)05-0463-09
10.3724/SP.J.1224.2020.00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