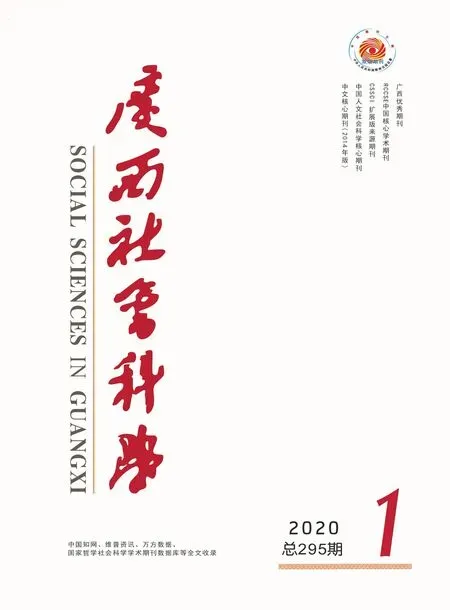北魏法制的文化基础
2020-03-11
(河南科技大学 法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北魏是一个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政权,其发展是落后民族走向先进的典范,北魏的法制就经历了一个由粗陋到完备的发展过程。导致北魏法制发展的原因包括社会生活结构、社会观念、伦理道德、教育以及统治者有意识地推动等因素。北魏的社会生活结构由游牧方式转变为农耕方式,儒学教育的广泛开展和普及,伦理道德由质朴的原始状态转变为高度儒家化的社会伦理,统治者对法制由推动建立法家式法制转变为推动建立高度儒家化的法制,所有这些最终造就了北魏法制的根本转变和巨大变迁。
一、北魏法制的发展历程
北魏是北朝的开创者,由鲜卑族的一支——拓跋部所建。由于政治比较稳定,北魏的法制也相应经历了一个全面发展的过程,实现了从粗陋到完备的历史性进步。
(一)拓跋鲜卑的早期法
东晋咸康四年(338年),拓跋鲜卑的部落首领拓跋什翼犍(即昭成帝)建立了北魏的前身——代国。《魏书·刑罚志》对拓跋什翼犍及其之前的拓跋鲜卑法制有如下记载:“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穆帝时,刘聪、石勒倾复晋室。帝将平其乱,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民乘宽政,多以违命得罪,死者以万计。于是国落骚骇。平文承业,绥集离散。昭成建国二年: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
《魏书》的这部分记载简要勾勒了北魏建国前拓跋部的法制传统,可知其当时的法律体系由部落习惯法、军令以及自昭成帝以来的若干法令构成。由于这一时期的拓跋鲜卑还处于相当落后的发展阶段,由此也相应地导致了鲜卑法的以下特点:首先,鲜卑习惯法粗疏简陋;其次,鲜卑法反映游牧文明的观念意识,受战争推动发展;再次,鲜卑法粗暴野蛮[1]。
(二)道武帝时期的《天兴律》
386年,拓跋鲜卑的首领拓跋珪乘前秦在淝水之战大败之机复建代国,不久后改国号为“魏”,即北魏。拓跋珪即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398年,道武帝改年号为天兴。此时,北魏已经将后燕打垮,进一步入据中原。同年,道武帝命王德等人制定《天兴律》。这是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后制定的第一部律典。对这次修律,《魏书·刑罚志》记载:“太祖幼遭艰难,备尝险阻,具知民之情伪。及在位,躬行仁厚,协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纲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是时,天下民久苦兵乱,畏法乐安。帝知其若此,乃镇之以玄默,罚必从轻,兆庶欣戴焉。然于大臣持法不舍。季年灾异屡见,太祖不豫,纲纪褫顿,刑罚颇为滥酷。”
此时的北魏尚处于立国初期,正在与其他北方政权争夺天下,四面环敌,其军事游牧政权的文化性质还相当明显,在法制方面相应表现为刑罚繁多且残酷的特点。
(三)太武帝时期的《神麚律》和《正平律》
北魏的第三位皇帝太武帝拓跋焘武功赫赫,他在位期间最终实现了对北方整个黄河流域的统一。与政治上的统一相对应,北魏王朝的第一个立法高潮也发生在太武帝在位期间。
1.《神麚律》。神麚四年(431年)十月,太武帝“诏司徒崔浩改定律令”(《魏书·世祖纪上》),修成《神麚律》。对这次修律,《魏书·刑罚志》记载:“世祖即位,以刑禁重,神麚中,诏司徒浩定律令。除五岁四岁刑,增一年刑。分大辟为二科死,斩死,入绞。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为蛊毒者,男女皆斩,而焚其家。巫蛊者,负羖羊抱犬沉诸渊。当刑者赎,贫则加鞭二百。畿内民富者烧炭于山,贫者役于圊溷,女子入舂槁;其固疾不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阶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年十四已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岁,非杀人不坐。拷讯不逾四十九。谕刑者,部主具状,公车鞫辞,而三都决之。当死者,部案奏闻。以死不可复生,惧监官不能平,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绝之”。
这次法律修订在立法及司法两个方面都有触及,在刑名、刑罚、赎刑、服刑及司法程序等方面都有改革。从崔浩这次法律改革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是加重对大逆不道、蛊毒等罪的惩处力度;二是对一般罪行尽量减轻处罚,同时考虑贫富、男女之别,对老幼、孕妇、残疾人予以适当照顾,惩处危害家庭成员的行为;三是慎重司法程序,特别重视对死刑的判决以免误杀,也注重冤情的申诉。
总之,这次由崔浩主持的法制改革是北魏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体现了统治者加强君主权威的意愿,也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儒家人性化的法律思想,反映了北魏法律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尽管如此,总体上来看崔浩主持改定的律令对于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极其残酷,因而在本质上仍然属于法家性质的法律,同时也仍然保留着部分拓跋鲜卑的旧制[2]。
2.《正平律》。神麚修律二十年后,正平元年(451年)六月,太武帝命太子少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等人进行新的修律活动。修成的新律即《正平律》。《魏书·刑罚志》记载:“初盗律,赃四十匹致大辟,民多慢政,峻其法,赃三匹皆死。正平元年,诏曰:‘刑网大密,犯者更众,朕甚愍之。其详案律令,务求厥中,有不便于民者增损之。于是游雅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盗律复旧,加故纵、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条。’”这表明,正平元年六月的改定律制是一次涉及内容广泛的法律改革,其背景是《神麚律》确立的严刑峻法不但未能消除犯罪,反而使犯法者更多,具体而言,主要是“盗律”有关赃罪的惩处过于严厉。因此将“盗律复旧”,也就是恢复“赃四十匹致大辟”的旧制。这次改革还对其他法律条文进行了修订,从“门诛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占全部律条的三分之一以上,可以推断此次所修订的仍是一部十分严苛的法律,体现出北魏的统治仍然具有极强的暴力特征。这表明经修订后的北魏律仍然非常粗糙,远未成熟完备[3]。
(四)文成帝时期的《太安律》
文成帝拓跋浚初年,仍遵《正平律》。太安四年(458年)设酒禁,改定律令。《魏书·刑罚志》记载,“又增律七十九章,门房之诛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太安律》在条文方面的增加幅度相当大,族刑数量大增,刑罚再次加重。可见,文成帝时期的修律使北魏律再次趋于严苛。
(五)孝文帝时期的《太和律》
1.第一部《太和律》。这部《太和律》的立法自太和元年(477年)五月开始,至太和五年(481年)冬完成。《魏书·刑罚志》中记载,“五年冬讫,凡八百三十二章,门房之诛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群行剽劫首谋门诛,律重者止枭首”。这次定律显示了北魏法律文明程度的提高,也体现了冯太后欲改变北魏严刑峻法暴力政治的主张[4]。此外,太和第一次定律,其议律之人如高允、高闾等皆中原儒士,保持汉代学术之遗风者[5],这样的因素使第一部《太和律》与文成帝时期的《太安律》相比,残酷性有了较大幅度的减轻。
2.第二部《太和律》。孝文帝时期的第二部《太和律》的制定始于太和十五年(491年),次年四月,第二部《太和律》完成,于是孝文帝正式“班新律令,大赦天下”(《魏书·高祖纪下》)。与此前相比,这部《太和律》不是简单的修改,而是重新制定[6]。由于均田制①均田制,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实行。和三长制②三长制,北魏太和十年(486年)实行。已经确立,农耕经济在北魏的经济结构中已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相当程度的儒家化社会伦理也已确立,制度的创新和文化的进步使孝文帝具备了不再只对之前的律典进行局部性修补,而是重新制定的可能。另外,由于太和年间北魏的汉化不断加速,第二部《太和律》在参照汉魏律的基础上又受到两晋、南朝法制的明显影响,总体表现为向西晋、江左一脉的进一步靠拢,并为北魏律的最终定型打下了基础。
(六)北魏律的最终定型:《正始律》
正始元年(504年)十二月,孝文帝的继承人宣武帝诏令制新律令。参与正始修律的是一个由三十余人的庞大班子,在这批人中,尤其应当注意刘芳、常景、元勰三人:刘芳是一代鸿儒,长于经学,号为“刘石经”;常景熟悉太和律令,善决狱;元勰是宣武帝之叔,博综经史。在这三人之中,元勰对正始议律有决策影响力,正始律必定以太和十六年律为基础,再权衡选择宣武帝时的部分诏令条制,纳入某些司法判例而成[7]。
这是北魏王朝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修律活动。经过这次修律,北魏律确立了由“刑名”“法例”为首的二十篇篇章结构,在对《太和律》加以补充、修改的基础上,编纂完成了《正始律》,即最终定型的北魏律。《正始律》通过全面、深入地将儒家礼教与法律相结合,基本上实现了北魏法律的儒家化进程。《正始律》的完成,标志着北魏王朝引礼入律历史进程的最终完成。
这部完成于正始元年的《正始律》,是北魏王朝在法制建设方面百余年间孜孜不倦努力的结果,北魏律至此大功告成。北魏历次修订刑律,其主持者皆为精通汉律或晋律的汉族士人,他们来自具有不同文化色彩的中原、河西、江南三大地区,使《后魏律》③此处的《后魏律》即《北魏律》。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能综合比较,吸取诸律精华,因此修成后价值很大[8]。《北魏律》的成就超过了同时期的南朝诸律,成为北齐律的基础,而且对隋唐法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前辈学者陈寅恪先生对此曾经作过这样的评价,“于是元魏之律遂汇集中原、河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于一炉而冶之,取精用宏,宜其经由北齐,至于隋唐,成为二千年来东亚刑律之准则也”[9]。
三、前北魏时期(386年以前)拓跋鲜卑法制的文化基础
前北魏时期,拓跋鲜卑法制的文化基础主要是其生产生活方式和宗教。
首先,在生产生活方式方面。拓跋鲜卑亦称别部鲜卑,原居于大兴安岭地区。1世纪末,匈奴被东汉彻底击溃,向西溃逃。拓跋鲜卑逐渐占据匈奴故地,成为蒙古高原新的主人,其生产生活方式也由狩猎式转变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式。总体而言,在进入中原前,拓跋鲜卑的文明程度比较低,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这一阶段拓跋鲜卑的法制必然是粗陋的。
其次,在宗教信仰方面。拓跋鲜卑作为鲜卑族的一支,其宗教信仰与匈奴等游牧民族一样,同为萨满教。他们“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毕皆烧之”。匈奴春秋祭祀,奉献牺牲,祈祷人畜兴旺。鲜卑“饮食必先祭”,祭仪频繁[10]。萨满教的宗教信仰,表明在北魏建立之前,拓跋鲜卑的文明程度还比较低。同时也表明,前北魏时代的文化性格是质朴的。在这种原始质朴的文化土壤上,前北魏时期的法制一方面表现为简单粗疏,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刑罚的残酷。
四、北魏前期(386—471年)法制的文化基础
自386年至471年孝文帝即位前这一阶段,北魏法制的文化基础可归纳为:儒家思想对社会的逐步浸润和统治者对儒学的提倡与儒学教育的建立。
(一)儒家思想对社会的影响
儒家思想很早就对北魏统治者产生了影响。北魏统治者开始接触并重视儒家经学,与汉族士人的建议有关。《魏书·李先传》载:“太祖问先曰:‘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对曰:‘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又问曰:‘天下书籍,凡有几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备?’对曰:‘伏羲创制,帝王相承,以至于今,世传国记、天文秘纬不可计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道武帝于是班制天下,经籍稍集。由此记载可见,北魏初建,最高统治者已经相当重视儒学。
由于儒家思想对北魏社会的逐步浸润,北魏统治集团及鲜卑民众草原游牧式的传统观念开始发生转变,这为法制的逐步发展和转变奠定了观念上的基础。
(二)统治者对儒学的提倡与儒学教育的建立
就儒学而言,北魏统治者很早就开始提倡儒学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儒学教育。《魏书·儒林传》记载:“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岂不以天下可马上取之,不可以马上治之,为国之道,文武兼用,毓才成务,意在兹乎?圣达经猷,盖为远矣。四年春,命乐师入学习舞,释菜于先圣、先师。太宗世,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太学于城东,后征卢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举才学。于是人多砥尚,儒林转兴。显祖天安初,诏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后诏: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五经博士由精通经传的汉族士人充当,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向统治者传授经学。梁越“少而好学,博通经传,无所不通”,“国初为《礼经》博士。太祖以其谨厚,举动可则,拜上大夫命授诸皇子经书”(《魏书·儒林传》)。
太学和五经博士的设立,表明汉族士人的政治主张为北魏拓跋统治者所采纳,并且体现到文化传播中去,为拓跋鲜卑及汉族官僚子弟提供了受教育的场所。此后传授经学成为王朝制度,汉族士人以正常而有效的渠道影响着北魏统治者。太学(后改为中书学)后来继续发展,并为北魏王朝培养了不少人才[11]。
由于统治者对儒学的提倡及儒学教育的逐步建立,北魏国家的文化气质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这为法制的整体转变奠定了教育文化基础。
五、孝文帝以后(471—534年)北魏法制的文化基础
皇兴五年(471年),北魏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孝文帝即位。自此,北魏政权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之前的残酷法制,北魏法制由此不断向汉化方向发展。就孝文帝即位至北魏最终分裂这一历史阶段而言,其法制的文化基础具体表现为:具有相当程度的儒家化社会伦理的出现、儒学教育的广泛推行与新型学校的建立以及鲜卑贵族的高度汉化和门阀士族化。
(一)相当程度的儒家化社会伦理出现
孝文帝即位后,北魏统治集团的汉化程度明显加深,社会伦理也呈现出加速儒家化的趋势。在深具汉文化修养的孝文帝的大力倡导和亲自推动下,北魏进行了一系列礼制改革,整个社会的儒家化日益加深,相当程度的儒家化社会伦理出现了。
1.婚姻制度的变革。太和七年(483年),在太皇太后冯氏的支持下,孝文帝下诏禁止同姓婚姻。《魏书·高祖纪上》中记载:“十有二月癸丑,诏曰:‘淳风行于上古,礼化用乎近叶。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斯皆教随时设,治因事改者也。皇运初基,中原未混,拨乱经纶,日不暇给,古风遗朴,未遑厘改,后遂因循,迄兹莫变。朕属百年之期,当后仁之政,思易质旧,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绝之,有犯以不道论。’”客观来看,婚姻制度的变革是北魏王朝全方位接受汉族传统文化、进行自身系统性文化变革的起点。以婚姻制度的变革为标志,北魏在太和年间改革动作不断。在冯氏和孝文帝的大力推动下,以皇室为核心的统治集团的观念被逐步纳入儒家文化的轨道之中。存留养亲制度的创设就是一个突出的标志。
2.存留养亲制度的创设。根据儒家孝的伦理观念,子孙必须尽养老送终的义务。而由孝观念引出的一项制度——存留养亲则源于北魏。该制度是指,犯人直系尊亲属年老应侍而家无成丁,犯人所犯死罪非十恶之罪,经过上请,流刑可免发遣,徒刑可缓期,将犯人留下赡养老人,老人去世后再实际执行。
太和十二年(488年)正月乙未,孝文帝下诏:“镇戍流徙之人,年满七十,孤单穷独,虽有妻妾而无子孙,诸如此等,听解名还本。诸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以闻”(《魏书·高祖纪下》)。这一诏令所针对的对象是流徙边镇的罪犯和死刑犯家属,但体现的是北魏政府对年老体弱者的关注,专门以老年犯人和罪犯的年老长辈为对象的尊老法令,这还是第一次[12]。这一政策的背景是儒家思想成为北魏统治者治国的主导思想,而尊老养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魏书·刑罚志》记载:“太和十二年,孝文帝下诏:‘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著之令格’”。
以上《高祖纪》及《刑罚志》所记载的内容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存留养亲”制度的雏形。这一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律家族化、伦理化的突出体现,它强调养老、尊老,注重维护家庭关系的稳定,它的创设是北魏社会的儒家化伦理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标志。如此以“孝道”为核心内容的制度能够产生于北魏这样一个由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不能不说是拓跋鲜卑统治者进入中原地区后深受汉族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存留养亲制度被后世历代所沿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3.“门房之诛”的废除。相当程度的儒家化社会伦理出现在北魏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门房之诛制度的废除。北魏所实行的“门房之诛”是一种极其残酷的株连之法,即族诛,与秦朝的连坐苛法几乎完全相同,极其残酷。这项制度与儒家所提倡的孝道相悖,适时废止非常必要[13]。《魏书·刑罚志》记载:“太和十一年春,孝文帝诏曰:‘前命公卿论定刑典,而门房之诛犹在律策,违失《周书》父子异罪。推古求情,意甚无取。可更议之,删除繁酷。’”至此,门房之诛这一北魏历史上长期实行的酷刑被废除。
(二)儒学教育的广泛推行与新型学校的建立
《魏书·儒林传》对这一时期儒学教育的发展和新型学校的建立记载:“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高祖钦明稽古,笃好坟典,坐舆据鞍,不忘讲道。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达,其余涉猎典章,关历词翰,莫不糜以好爵,动贻赏眷。于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
由此可见,儒学教育在太和年间得到了广泛推行和进一步发展。此时的北魏,在教育方面俨然已与之前的中原汉族王朝几无差异。不仅如此,新型学校的创立对于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发展也是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补充。此外,以儒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礼仪、乐律、道德风范正成为影响北魏社会的主旋律[14]。至此,北魏的文化气质已经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这就为其法制的整体儒家化转型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三)鲜卑贵族的高度汉化
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这是北魏政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至此,地处塞北的平城在作为北魏国都近百年后,让位于位居中原的洛阳。洛阳是东汉、曹魏及西晋的故都,迁都于此的重大意义在于:自东汉以来,定都于洛阳的均为统一王朝或正统王朝,且洛阳是华夏文化的精华所在,建都洛阳将使北魏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
在中原地区站稳脚跟后,北魏统治者如历代一样尊崇孔子、提倡儒学,发展儒学教育。孝文帝本人就是具有高度汉文化素养的北魏皇帝。在他的身体力行和大力提倡、推动下,北魏统治集团的汉文化素养在整体上不断提高。拓跋皇族及上层子弟读儒经、诵诗书,接受儒学教育成为普遍现象。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越来越多的鲜卑贵族偃武修文,他们身上的文化气息日渐浓厚,在言行举止和道德伦理方面都越来越像中原的传统士大夫而不像其鲜卑先祖。鲜卑贵族因此实现了高度汉化。迁洛鲜卑贵族的整体汉文化素养可以说已经达到不逊于汉士族的水准。鲜卑贵族的高度汉化使北魏文化的汉化程度进一步提升,这进一步夯实了北魏法制发展的文化基础并最终奠定了其高度。
(四)北魏法制儒家化的标志性案例:宣武帝时期的“费羊皮卖女案”
宣武帝时期,发生了北魏法制史上著名的“费羊皮卖女案”。该案在当时的北魏朝廷引起了大规模讨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宣武帝本人也参与其中并最终亲自拍板定案,这一案件堪称北魏法制儒家化的标志性案例。
该案案情如下:永平三年(510年),在冀州阜城之民费羊皮的母亲去世,因家贫无钱葬母,费羊皮于是将自己七岁的女儿卖与同城人张回为奴婢,张回又将该幼女转卖给鄃县之民梁定之,而没有向梁定之说明该幼女为良民。
对于该案的处理,当时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尚书李平认为,依律规定“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魏书·刑罚志》),张回故意买费羊皮之女,谋以转卖,依律应当处以绞刑。延尉少卿杨钧认为,费羊皮卖女属于尊长出卖卑幼,按律“卖子孙者,一岁刑”(《魏书·刑罚志》),应处一年徒刑,费羊皮未说要追赎,所以张回才把该幼女转卖给梁定之,张回的过错轻于费羊皮,如果判处费羊皮一年徒刑,却判处张回绞刑,显然处刑过重。三公郎中崔鸿认为,根据被卖者尊卑地位的不同,对出卖者的处罚也应有所不同。费羊皮卖女属于尊长出卖卑幼,按律应当判处一年徒刑;如果费羊皮出卖的是尊长,按律将会被判处死刑。张回与费羊皮之女没有亲属关系,他收买费羊皮之女后又隐瞒真实情况再次将其出卖,这一行为导致良人被辗转买卖而永远沦为奴婢,其社会危害性很大,应当对张回处以绞刑。高阳王元雍认为,不论是否转卖,费羊皮之女已经沦为奴婢,对张回应当处鞭刑一百;而费羊皮之所以卖女儿,是为了安葬母亲,这不仅是孝心的体现,更是敦化教民的榜样。因此,对费羊皮不仅不应处罚,反而应作为模范人物来进行表彰。最终,宣武帝综合考虑多方意见,根据儒家“礼”的精神而不是法条作出了最终裁决:“羊皮卖女葬母,孝诚可嘉,便可特原。张回虽买之于父,不应转卖,可刑五岁”(《魏书·刑罚志》)。也就是说,宣武帝基本上采纳了高阳王元雍的意见,认为费羊皮卖女儿葬母是孝心的体现,这样的孝诚是值得嘉奖的,因此对费羊皮免于处罚;而张回买费羊皮之女虽然是为自己的父亲(作奴婢),但是不应当再转卖他人,因此对张回处五年徒刑。可见,本案的最终判决没有拘泥于法条或者说突破了法条,这显然是自孝文帝以来不断引礼入法、以礼统律的结果。如果没有整个北魏社会礼治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没有统治集团观念的日益儒家化,这样的处理结果是不可能的。
经过孝文帝的改革和宣武、孝明帝等后继者的传承,北魏法制向礼法结合、轻刑化、封建化的方向发展,并且取得不小的成就。在法律理论、法律形式等方面,北魏法制都对中华法制文明作出了贡献[15]。
北魏的法制何以能从当初落后的阶段,达到后来的先进水平,文化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在传统社会,文化为法律制度提供合法性的基础,决定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并将作为规则载体的法律制度锻造成价值和意义体系[16]。孝文帝倾心仰慕汉文化,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全身心投入汉文化的怀抱,终于实现了“以夏变夷”,在迁都洛阳后铸就了北魏文化的繁荣。
综上所述,决定北魏法制的社会历史生活结构以及反映这一结构的价值体系自拓跋鲜卑统治者进入中原起就不断发生变革:其社会历史生活结构由原先的游牧生活结构转变为后来的农耕定居生活结构,其反映这一结构的价值体系也由最初质朴的原始状态转变为得到广泛认可的儒家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价值体系完全汉化、儒家化,加之统治集团整体汉文化素养的提高以及北魏后期高度繁荣的文化,所有这些为法制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也最终造就了北魏法制由粗陋到先进的巨大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