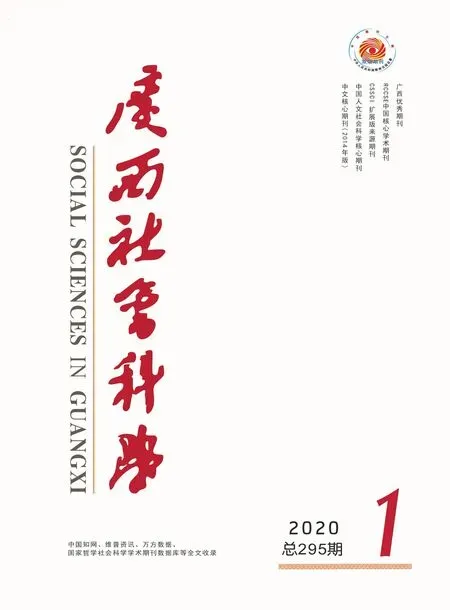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到中国济难会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视阈下中国济难会创建之历史解读
2020-03-11
(山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中国济难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号召下于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以后领导成立的一个革命性、群众性救助组织。中国济难会成立之后“积极从事被捕或牺牲革命者及其家属的营救与救助工作”,“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而重大的历史贡献”[1]。对中国济难会进行系统性研究,不仅可以再现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艰苦卓绝的岁月里领导革命济难工作的历史,还可以为考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统战工作、群团工作、理论宣传工作、社会救助工作等重大问题提供一个独特而鲜活的视角。然而或许由于史料及认识方面的局限,截至目前,学术界研究中国济难会所取得的成果不但数量鲜少且缺乏系统性,尤其对于该组织的创建问题仍语焉不详。故此,本文主要在前人研究成果①截至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济难会创建问题有所涉及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雍玲玲的论文《1925—1933:中国济难会的产生、发展及其活动》(《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2期)、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中国济难会革命互济会在上海》(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谢忠强的专著《中国慈善救助事业发展史论纲》(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等,而研究中国济难会创建问题之专论暂付阙如。启发的基础上,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角度对中国济难会的创建问题进行专门的梳理和分析,权充引玉之砖。
一、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救助组织的源头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从根本上动摇了资本主义世界旧有的政治格局,同时也引领了全世界范围内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进行阶级革命、民族解放斗争的时代潮流。而面对具有颠覆旧有世界格局倾向的革命浪潮之形成,资本主义国家及落后地区的统治阶级对革命者均进行了残酷的暴力镇压。
自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第二年至中国“五卅运动”爆发之前,世界各地工人及农民因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而被难的数目与日俱增且分布较广。根据约略统计,1918年至1925年间,“全世界因解放运动而死伤的革命者总数超过二十多万”,其中“德国有二万人,芬兰有三万五千人,罗马尼亚有八千人,意大利有五千人,匈牙利有三万人,保加利亚有二万多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及立陶宛三国内有二万五千余人,东方及南非诸国如印度、埃及、苏丹、米苏帕托米亚、叙利亚、朝鲜、中国及日本共有二万五千余人”[2]。
除上述为数众多的被难者外,还有大量因参加或支持革命活动的工农群众被捕入狱。在各国统治阶级的监狱中,革命者或进步群众均遭受到了残酷的折磨。统治阶级为了镇压革命浪潮而掀起的白色恐怖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因此,如何对因参加革命事业而牺牲的革命者及其家属进行必要的救助,并对因参加或支持革命事业而被捕入狱的革命者或进步群众进行及时的营救便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难题。毕竟“这种救济是革命事业必须做的事,因为当顶好的革命战士陷于敌人之手而不去救护他们,革命便不能进行了”,故而“全世界的革命党应当在各地组织这种‘红十字会’式的工作”,但考虑到“革命党是战争的团体,他们全副精神应当注意于战争,他们不能费许多心思于救济工作”,所以“济难工作必须组织一个无党派的大团体来担任”[3]。
为了解决被捕或牺牲革命者及其家属营救、救助这一现实问题,苏俄共产党人首先进行了有益尝试。1922年11月,由俄共(布)党内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党人及部分沙皇俄国时代的政治犯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俗称为“国际赤色救济会”)的组织[4]。
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成立以后,因其对世界各地被捕或遇难革命者及其家属之救助工作成效明显,对革命阵营的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故而引起了1922年11月至12月间召开之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之重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听取了俄共(布)代表关于成立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报告之后,就曾指出“在反革命势力疯狂肆虐的严峻形势下该组织的成立是促进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一件好事”,认为该组织的创办“是适时的,且有必要通过国际间的联合而使之进一步发展和壮大”[5]。
继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对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成立的历史意义进行充分肯定的基础上,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又通过专门决议对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组织发展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指导。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议事日程之第十四项即专门讨论了“国际红色援助问题”[6]。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认为: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是一种党外的组织,其主要任务是从法律上、精神上和物质上支援被监禁的革命战士及其家属子女和烈士家属”;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所开展的工作具有“巨大政治意义,因为这是无产阶级战斗大军的一个后方组织,工人阶级无论在退却或进攻时期进行经常的斗争中都需要有这种组织”,它“会使被监禁的革命战士感到同志式的关怀,从而可以鼓舞他们继续进行斗争的勇气和决心”;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在其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已逐渐成为实现统一战线策略的最重要工具之一,而且国际团结的具体实例说明,它正在组织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力量,直接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应把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小职员群众及一切遭受资本剥削和民族压迫的人、一切渴望劳动战胜资本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不问他们属于何种党派”[7]。
在充分肯定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重要意义的基础上,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还明确将每年的3月18日(巴黎公社纪念日)确定为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日。而在如何进一步扩大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国际影响的问题上,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认为必须通过世界无产者联合的方式使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有鉴于此,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向各国共产党和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发出呼吁:“各国共产党应尽一切力量协助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帮助它在本国设立分会和支会,并组织本党成员积极参加”;“党的报刊对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必须给以应有的重视,宣传鼓动救济革命战士”;“在进行党的一切运动时,也必须考虑到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这个组织”[8]。
作为共产国际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亦派李大钊、王荷波、罗章龙等人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9]。中共参会代表回国之后亦将包括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决议在内的全部会议精神带回到了国内并向全党同志作了传达。毫无疑问,尽管因为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组建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中国分支组织的工作直到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以后才正式启动,但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关于各国共产党应建立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分会的要求为中国济难会的创建提供了政策依据和组织蓝本。
二、“五卅运动”及共产国际的声援和救助:中国济难会诞生的历史契机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各国共产党要创建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分会的决议传到国内后,因历史条件不够成熟及当时自身对开展革命救助事业必要性认识上的不足,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立即着手组建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中国支会。而真正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组建革命救助组织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则是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为数众多的革命者遇难、被捕的残酷现实给中国共产党人及广大革命群众内心所产生之情感触动。
“五卅运动”的爆发在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推向高潮的同时也遭到了国际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军阀势力的残酷镇压,“参加运动的革命者及进步学生、群众死伤及被捕入狱者不计其数”[10]。除震惊国内外的“五卅惨案”中为数众多的死难者与被捕者外,全国各地在声援“五卅运动”的过程中也有许多革命者及进步群众被难或入狱。据统计,仅广东一省,“五卅”以后,“农民被地主残杀的已经四百多人”,“工人各地死伤者已有二百多人”,“零整被捕在狱者总数在千人以上”[11]。而广东以外,“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均发起了声援运动,其间死难或被捕的革命者、爱国者总数不下数万人。
正是“五卅运动”中出现了大量需要救助的被捕或遇难的革命者及其家属使得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从维护统一战线的高度去重视革命救助工作。这一点在《中国济难会发起宣言》中也得到明确的印证:“此次五卅事变前后,青、沪、汉、粤、渝、宁、津等处死伤入狱者之多,近代所未有”,“并且内外强敌方盛,吾民欲争的自由今后还不知有若干牺牲”,“这些为国家、社会而牺牲的人们固然不期他人之救济”,“但社会人士却不应坐视他们和他们的家属之危难而不予以同情的救济”,“这就是我们所以要发起济难会之最近动机”[12]。
除“五卅运动”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救助被捕、死难革命者及其家属的现实需要外,共产国际对“五卅运动”的声援和救助也给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创革命救助组织方面提供了认识上的重要启发①见《中国济难会发起经过》,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D2-0-1315-39。。
如上所述,在共产国际的号召与推动下,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发展迅速,截至1925年7月份,该组织已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32个支部,会员数量达到500多万,救助成效日益显著,国际影响亦不断扩大。据统计,该组织仅用于“救济政治犯及其家属之款项”支出方面,“1923年共用十三万九千元”,“1924年共用六十一万元”,“1925年上半年六个月中共用四十万元”[13]。除对被捕及遇难革命者及其家属予以救助外,该组织还曾领导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抗议美国、保加利亚等国资产阶级镇压革命运动之白色恐怖,以及反对第二国际所建议之交换政治犯之提议、参与各国政治犯审判之辩护工作等。鉴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4],故而“五卅运动”爆发后亦得到共产国际领导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声援和救助。
中国“五卅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国际以后,共产国际对其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应该获得“世界无产阶级的大力支援”[15]。共产国际对“五卅运动”的“大力支援”主要表现在“声援”和“救助”两个方面。
“五卅运动”爆发后,苏联各大报刊、共产国际各大组织纷纷发表宣言和文章,声援中国工人的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6月5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专门致信鼓励中国工人:“苏联工人密切关注你们展开的英勇斗争,在你们遭受挫折时,我们和你们一起感到痛苦,而在你们取得胜利时,则感到万分高兴”[16]。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与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共产国际联合会发表《关于青岛和上海惨案告工人、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书》,号召人们要全力支持中国工人的斗争,抗议资产阶级国家的资本家精心策划的新战争危机,抗议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滥施暴行,要求从中国撤出外国军队。6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致电法、意、美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中央,建议他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吸引工人阶级广泛的社会舆论支持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并努力与社会主义国际的和无党派的工人一道组织抗议大会和募捐活动。
共产国际在对“五卅运动”进行大力声援的同时还给予了经济上的援助。1925年6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拨出10万卢布,6月13日又决定从苏联人民委员会储备基金中拨出5万卢布,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苏联工人将这两笔现金汇往中国,支援中国反帝罢工的工人。1925年6月以后,《真理报》《消息报》又连续报道了“五卅运动”的重要影响以及苏联和其他国家捐款支援中国罢工的消息,进一步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支援“五卅运动”的捐助运动。据不完全统计,仅俄国贸易联合会就向上海罢工工人提供了14.8万卢布的援助。1925年8月5日至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通过电话形式表决,决定建议由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紧急汇款10万卢布交由上海、香港和中国其他城市的罢工者[17]。
共产国际对于“五卅运动”的声援和救助极大地鼓舞了国内革命热情的高涨。1925年8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为答谢共产国际对“五卅运动”的声援和救助而专门致信说:“我们在反对残酷的、强大的敌人的斗争中,得到了你们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深为感谢。”[18]而中国的革命者在有感于国际革命救助事业所带来的无限温暖与感动的同时,也对革命救助事业开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了切身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因此,如何响应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关于建立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中国支会的这一号召,即在中国也建立起革命性的救济组织便成为“五卅运动”过后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这一点在《中国济难会发起宣言》亦有明显的印证:“济难会这种相类的组织各国都有,例如德国有济难会,英国有国际革命入狱者救济会,俄国、法国、意大利及巴尔干诸国都有国际赤色救济会”,“他们这些组织之目的,不但在救济被难者及其家属,还要因此促进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及被压迫阶级之友谊与联合”,“本会之发起,不待言也合上述种种之意义”[19]。
三、应运而生:中国济难会的创建
中国济难会是“在共产国际的号召下,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性救助组织,济难会的创建既是“五卅运动”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高涨的产物,也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发展的结果①见《互济会革命活动(初稿)》,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办公室1984年编印,第2页。。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此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即在上海开始酝酿建立中国的革命济难组织”[20]。1925年9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着手中国济难会的筹备工作。经过将近一周左右的准备时间,到1925年9月20日,中国济难会“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在上海西城小学召开,会议通过发起宣言、组织章程并选举了筹备委员会,确定上海闸北天通庵路三丰里31号设立会所机关”;“9月30日,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确定委员分工,讨论发展会员,开成立大会及修改简章等”;“10月3日,中国济难会发起成立的消息公开见报”;“10月4日,筹备委员会分别发出致工、商、学界及华侨同胞书,并致函各社会团体,请代为调查在各种解放运动中牺牲烈士的经历及家庭状况”[21]。
1925年10月,正当中国济难会的发起工作在上海区委具体领导下积极进行的同时,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执行会上也出现了一份名为《救济问题议决案》的提案,对于在中国建立革命救济组织的必要性及该组织的性质和任务等内容作了明确的阐述②见《中国济难会发起经过》,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D2-0-1315-39。。提案认为,对于革命斗争中大量的被捕、牺牲的革命者及其家属的救济问题,必须建立类似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组织才可以解决,而由共产国际发起组织的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已在包括中国“五卅运动”在内的革命救助事业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作用和成效,共产国际的多次会议也规定每个支部要在各自国内设立一个这种组织,“所以组织这个会的需要非常迫切,决不能再延”,“这种会的目的在救济为人民奋斗的死者、伤者、被囚者,给予他们以物质与精神的援助,帮助为参加工农群众活动之故而被逮捕的人,帮助政治犯早日获得释放,并将国际间同志、劳动群众对被捕者的同情散布于他们”[22]。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高潮中,中国济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成立工作进展顺利。1925年“双十节”和“十月十八日上海各界反对沪案重查的市民大会”上,“中国济难会筹备委员会派员到处演讲,宣传济难会宗旨,争取了上海许多团体和个人入会”[23]。1925年10月25日,中国济难会召开了代表大会,讨论发展会员、国际联络、募集经费以及济难会对“五卅运动”后各地发生的反动派镇压革命群众事件的态度问题等,“大会决定将筹备委员会改为全国总会临时委员会,并增加委员数人,以深入推动全国济难工作之开展”[24]。到1925年底,中国济难会“由上海发展到全国”,除江西省已成立全省济难总会外,“广州、长沙、天津、北京等地也都展开了当地济难组织的筹备工作”[25]。
1926年1月1日,中国济难会总会主办的《济难》月刊创刊,并向社会各界公告:“本会以救济一切解放运动之被难者并发扬世界被压迫民众之团结精神为宗旨,定名为中国济难会”;“凡赞成本会宗旨,遵守本会章程,赞助本会事业,按章缴纳本会会费之个人或团体,皆得为本会会员”;“本会总会会址暂设于上海”,“本会事业”主要包括“救济一切为解放运动而死伤或入狱者及其家属并予以法律上之辩护及教养其子女等”,“宣传救济事业之状况并量力救济各国解放运动之被难者”,“印行因一切解放运动而被难者之照片、传记、书信、遗言及其他记载”,“与各国类似之团体联络”①见《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D2-0-1315。。
1926年1月17日,中国济难会筹备委员会与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文治大学、上海艺术大学、中华艺术大学、东华大学、东亚同文书院、上海大学附中、复旦中学等学校的中国济难会分会及启贤公学的中国济难会儿童团暨“上海各界各团体济难会同仁”在上海北四川路中央大会堂共同发起举行“募捐游艺大会”[26]。“一百八十余团体的三百多名代表与会,连同其他来宾约两千人。会上,宣布了济难会上海市总会正式成立,同时选举产生了市总会的领导成员:韩觉民、李石岑、杨杏佛、吴山、恽代英、孙云鹤、刘俊山、李硕薰、胡宗南、倪无斋等十人为审查委员;阮仲一、余泽鸿、姜长麟为组织股委员;萧朴生、郭沫若、陈望道为文书股委员;熊季光、丁晓先、王弼为会计股委员;朱乐天、周逸心、游世璋为交际股委员;陈伯华、王心恒、黄娃英为庶民股委员;曹声潮、徐汉臣、谢旦如为调查股委员;徐恒耀、周全平、杨贤江为宣传股委员;唐豪、黄振盘、王开疆为法律委员;郭景仁、蒋仁东、吴开先为赈济股委员;林钧、柳亚子、钟复光为筹款股委员。”[27]
以1926年1月17日中国济难会全国临时总会的成立以及上海和全国其他省市总会与基层济难会组织的相继建立为标志,中国济难会的创建工作正式完成。中国济难会成立之后,在我国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②见《中国济难会与社会各阶级》,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D2-0-1315-23。,“其间尽管一度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28],但无论是在援救革命战士及其家属还是在动员、组织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以及加强国际革命力量的联系等方面均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③见《济难会的目的与意义》,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D2-0-1315-16。。
四、结语
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演变动力模式的学术讨论中,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提出的“刺激—反应”说和柯文提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国中心观”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解释路径。然而从近代中国社会自身新陈代谢的历史纹路分析,这两种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虽各有道理,但又各失偏颇。就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型过程而言,既有西方外来影响的客观因素,也有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按照传统封建道路向近代艰难踟蹰的意味,故而笔者认为将两种观点相互结合或许更利于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的特定现象或事件。
近代以来,在“千年变局”逼迫下中国社会意识出现了几次大的转型[29],中华民族在求强之路上曾经因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而以英、法为师,因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以日本为师,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先进中国人则又有感于马克思主义之伟大而转向以苏俄为师。而当中国人因追求民族自强、独立的主观意识与“共产国际力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外在刺激相结合则又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30]。毫无疑问,在近代积贫积弱的状态下中国儒家文明所与生俱来的包容性和强大的吸纳、融合能力,为中华民族向一切先进文明或理论学习提供了固有的知识话语体系之内在转换机制。因此,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都离不开“外在刺激”和“中国本土特色”这两种解释方向的交叉、对照。
中国济难会的创建其实就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本国反帝反封建大革命高潮相结合的历史产物。如前所述,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救济组织的源头为中国济难会的创建提供了蓝本性的示范及组织上的领导作用,1925年“五卅运动”为数众多的革命者遇难、被捕及共产国际对“五卅运动”的声援和捐助给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展革命救助事业必要性认识上所带来的深化,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催生了中国济难会这一全国性革命救助组织的出现。
揆诸史实,中国济难会的创建既是20世纪20年代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救助事业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同时也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本国革命救助事业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