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的“别称”*
2020-03-08崔际银
崔际银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 人文学院,天津 301811)
“别称”指正式名称之外的名称,是自古至今常有之现象。人的别称所指应是“名”与“字”之外的称呼(1)每个人的“名”通常是按照家族谱牒严格排序;“字”是对“名”的意义的解释、说明或呼应。“名”和“字”的确定是非常严肃、严格的;而“号”(别号)的命名与含义则灵活多样,应当属于“别称”范围。。由于时代及人物阶层、身份的不同,“别称”的风格也大不相同。大致说来,文化素养深厚、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物,其“别称”较为雅致,反之则较为俚俗。在中国传统文化视域内,文人群体的“别称”值得特别关注。李白既是唐代最著名的诗人,也是古代“别称”非常多的文人之一,因而具有专门探讨之必要。
一、李白“别称”的基本状况
李白的“别称”颇夥,主要表现为出处不一(李白自我命名及他人命名),形式多样(一字至多字、单称与多称),内容广泛(涉及性格、爱好、文学成就、现实社会、神仙世界),时域绵长(从李白生前直至清代)。因此,须将这些方面的情况进行适当的归纳梳理。
(一)出处
某个人的“别称”通常是由与之相熟(或对其感兴趣)的人提出,相当于“绰号”,李白的不少“别称”便是由此而来。李白也喜欢自我命名,而且自命的“别称”不在少数。
1.自我命名
李白“别称”的自我称呼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出自李白之口的称呼,第二种是由他人讲出的李白自称。
出自李白之口的“别称”,其标识为“我”“余”“李白”。他有时将自己定位于尘世中有知识、有抱负的“布衣”“野人”“草间人”。如“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1]1775(《与韩荆州书》);“白,野人也,颇工于文,惟君侯顾之”[1]1761(《上安州裴长史书》);“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2]1735(《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他认为自己就是“南阳子”诸葛亮,希望受邀出山,辅佐君王、建功立业:“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甫吟。……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2]1781(《留别王司马嵩》)。李白一生的定位目标是“功成身退”,“山人不照镜,稚子道相宜”[2]1813(《答友人赠乌纱帽》)与“一昨于山人李白处奉见吾子移文”[1]1744(《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的以“山人”自称,正是这种追求的体现。不过,由于到处碰壁,他只能以“妄人”“可笑人”“楚狂人”自嘲自解,如“白,嵚崎历落可笑人也。……昔徐邈缘醉而赏,魏王却以为贤;无盐因丑而获,齐君待之逾厚。白,妄人也,安能比之”[1]1752(《上安州李长史书》);“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2]1773(《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以曾任翰林供奉为荣,借助推荐自己的官员宋中丞之口,说明自己任职时的状况:“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1]1899(《为宋中丞自荐表》)李白深信自己不同凡俗,是“谪仙”“酒仙”“岁星”:“四明逸老贺老章呼余为谪仙人……,群子赋诗以出饯,酒仙翁李白辞”[1]1877(《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自是客星辞帝座,元非太白醉扬州”[2]1817(《酬崔侍御》);“闲倾鲁壶酒,笑对刘公荣。谓我是方朔,人间落岁星”[2]1781(《留别西河刘少府》)。他甚至在同一首诗中多次称自己属于仙佛之身,与如来佛祖关系直接:“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2]1813(《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对酒忆贺监二首》其一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2]1859由此可见李白非常认同贺知章对自己的称呼。
由他人之口提到的李白自我称呼,最有名的是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2]2259宋人乐史说李白“效谢安石风流,自号‘东山’,时人遂以‘东山李白’称之”[3],认为李白自称“东山”源自对谢安的仰慕,因此被别人称作“东山李白”。这种说法大致可信。晚唐李山甫的《代张孜幻梦李白歌》,叙述自己在梦中与李白相见,李白“自言天上作先生,许向人间为弟子”[4]438。明代张以宁《题李白问月图》所谓“举杯一问月,我本月中仙。醉狂谪人世,于今几何年”中的“月中仙”“醉狂”[5],是直接从李白诗句中摘抄而来,并非出自李白之口。
2.他人称呼
李白的“别称”多数是由他人命名的,这些“别称”始于李白生活的盛唐,延及中唐、晚唐五代,唐是李白“别称”的创制生成时期。如盛唐贺知章(李白《对酒忆贺监二首》其一)、杜甫(《饮中八仙歌》),中唐的韩愈(《石鼓歌》《荐士》《调张籍》)、白居易(《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晚唐的李商隐(《漫成五章》其二)、张祜(《偶题》)、温庭筠(《秘书省有贺监知章草题诗笔力遒健风尚高远拂尘寻玩因有此作》),五代的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王定保(《唐摭言》卷七),等等,都曾命名或描述过李白的“别称”。唐代为李白送上“别称”的人士,除了文坛同仁,还包括官员、僧侣(贯休、齐己)等各界人士。有的“别称”,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百姓皆知。如唐文宗说:“朕曾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常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6]可见在唐文宗当政时期,包括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在内的“四绝”之称在社会上传颂极盛。
唐以后的李白“别称”可以分成两个时段。第一时段是宋代,宋距唐世未远,“李杜”“谪仙”之类的称呼仍然流行。如“篇章取李杜,讲贯本姬孔”[7],“深美谪仙遗世务,酒船椎鼓浪如山”[8](李觏《太平州十咏亭》)。有的称名稍有调整,如将杜甫的“饮中八仙”改为“酒中八仙人”:“白……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人’。”[9]同时,宋代出现了一些新的“别称”。如张齐贤《书杜工部祠堂》有“三贤出蜀,俱有高名:房相为中兴名臣,陶甄品汇;翰林旅窆采石,屹立丰碑;工部寓葬耒阳,显存遗迹”[10]88等句,将房琯与李杜合称“三贤”,当属“跨界”组合(房琯属政界、李与杜为文人)。钱易称李白为“天才绝”:“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为人才绝,李贺为鬼才绝。”[11]308田锡称李白为“俊人”:“又有长庚字太白,下笔一万字,是为唐朝之俊人。”[12]郭祥正称李白为“酒家仙”“金銮客”“诗中元帅”:“君不见,李太白。朝为酒家仙,暮作金銮客”[13](《西山谣寄潘延之先生》);“太白之精生李白,诗中元帅酒家豪”(《李白祠堂》(2)一说该诗出自郭祥正《青山续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有录;或传为孔平仲所作,详见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清江三孔集》,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423页。)。人们熟知的“诗仙”之称,见于宋人徐积《李太白杂言》:“至于开元间,忽生李诗仙。是时五星中,一星不在天。”[14]1844叶廷珪的《海录碎事》记载多个李白“别称”,有的是前人所言(海上钓鳌客、竹溪六逸、天才绝、青莲居士、翰林伯),而“仙宗十友”之称(“唐司马承祯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为仙宗十友”[15]),则首见于此。
第二时段是金元至清末,此时李白的“别称”仍大量出现,但较多为重复唐宋时期的称呼或稍有变动。本期较有特点的“别称”是“诗中豪杰”(金·李俊民《李太白图》“谪在人间凡几年,诗中豪杰酒中仙”[14]1932),“真仙人”(元·黄玠《月下独酌似谢季初叔久兄弟》“太白真仙人,俗客匪其偶”[16]17),“饮中豪”(王恽《太白扪月图》“诗中无敌饮中豪,四海飘萧一锦袍”[14]1945),“千秋才”(王世贞《题钱舜举太白观瀑图》“匡庐万古瀑,太白千秋才”[14]1940),“旷世逸才”(“太白旷世逸才,自成一家”[17]),“开元供奉”(陈维崧《西江月·题六合孙公树捧书图》“李白开元供奉,当年恩礼偏隆”[18])。明人陆深《李白对月图》对李白的称呼最为通俗:“老白爱月不爱身,酒阑捉月秋江滨。平生见月即举盏,自道对影成三人。采石深不测,青天高无垠。骑鲸一去忽千载,月与老白俱精神。”[16]276-277“老白”之称极为平易亲切。清代何栻所作《李白斗酒诗百篇赋》,将李白自称及流行的有关“别称”予以列举,包括“金粟如来”“青莲居士”“酒国醉侯”“诗城仙史”“酒狂”“诗癖”“酒仙”“诗伯”等[16]1242,具有总结性的意义。
(二)形式
李白“别称”的形式,是指这些“别称”的命名,是单一“别称”独自出现(单称),抑或与李白另外的“别称”、与其他人的“别称”同时出现(合称)。
1.单称
以单一名称出现在某作品的李白“别称”,占据李白“别称”的大多数。如“谪仙”“酒仙”“仙翁”“星精”“诗仙”“诗杰”“诗豪”“诗客”“高士”“狂士”等等。
2.合称
合称(多称)的情况较为复杂。有的是针对李白一人的合称,如晚唐诗人郑谷《读李白集》:“何事文星与酒星,一时钟在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间伴月明。”[2]7736此作中“文星”“酒星”及“李先生”,所指均为李白。李白与他人合称,最早当出自杜甫《饮中八仙歌》,该诗将李白与贺知章、张旭等七人并称为“饮中八仙”。二人合称中最著名者为“李杜”,此称最早见于中唐韩愈,在其《感春四首》其二、《荐士》《调张籍》等作品中多次出现。三人合称中,较早出现的是“三星”(裴说《怀素台歌》“杜甫李白与怀素,文星酒星草书星”[2]8260)和“三绝”(“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9])这两个“别称”,包含着李白爱好艺术、借鉴艺术、文学创作与各类艺术融合的信息。多人合称者,人们熟知的是“竹溪六逸”和“饮中八仙”。“方外十友”是从崇道尚隐视角命名的:“司马承祯……居天台山,事体元正潘先生,传辟谷导引术,无不通。后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维、孟浩然、王适、毕构、李白、贺知章为‘方外十友’。”[19]“盛唐十大家”则是从诗歌创作视角命名:“诗至开元、天宝间为最盛,若杜工部、孟襄阳、高渤海、岑嘉州、王右丞、储御史、王江宁、李颀、常建者,皆声振艺林,言中金石,彬彬乎一代之英也,故世称盛唐十大家云。”[16]303(李濂《唐李白诗序》)
(三)内容
考察李白“别称”的词义内蕴可知,这些“别称”有的是符合实际的实称,有的是出自夸饰的虚称,还有的是将实与虚融为一体的称名。
1.实称
在李白的“别称”之中,有些名称是属实或合乎实际的,可以称之为“实称”。如“君不见饮酒吟诗狂太白,曾是匡山读书客”[20](柳贯《商学士画云壑招提歌》),因李白早年在江油大匡山(戴天山)读书而称其为“匡山读书客”,是与事实相符的;“翠羽雕虫日日新,翰林工部欲何神”[2]3038(窦牟《奉酬杨侍郎十兄见赠之作》),“学士风流不可名,暮云犹著古贤声”[21]198(赵公豫《暮云亭谒青莲先生祠》),因他曾任“翰林学士”而称为“翰林”“学士”;李白时常饮酒大醉,故称“醉客”(温庭筠《秘书省有贺监知章草题诗笔力遒健风尚高远拂尘寻玩因有此作》“李白死来无醉客,可怜神彩吊残阳”[2]6726);他葬于采石矶近旁(青山脚下),“采石李”是对其死所、葬地的真实记录(丘濬《丁卯舟中望鞋山因忆解学士吊李白诗戏作》“惊醒采石李,触起耒阳杜”[22])。李白的声名隆盛,主要源自其优秀诗作,称其为“诗客”(欧阳澈《送吴教授古诗》“公不见,先朝谪仙李太白,晦迹嵩山号诗客”[23]),“诗杰”(“子美诗闳深典丽,集诸家之大成;……太白诗豪迈清逸,飘然有凌云之志,皆诗杰也”[14]1871),“诗翁”(杨万里《又跋东坡太白瀑布诗示开先序禅师》“东坡太白两诗翁,诗到庐山笔更锋”[24]),“诗豪”(“近读古乐府,始知后作者皆有所本。至李谪仙绝出众作,真诗豪也”[14]1897)等,都是可以接受的,也是与实际情况大体相合的。
2.虚称
李白“别称”之中,相当一部分具有过度夸饰或异化的特征。李阳冰是李白生命最后阶段的见证人,不仅安排了李白的葬事,还负责整理其诗文著述,并专门撰写了《草堂集序》。文中记述了李白家世:“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祖上)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1]1949其中说明李白的“名”与“字”的确定,是因其母临产前梦见天上的“长庚”(金星、太白):“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这些文字虽然自古迄今仍有争论,但大体上是合乎情理的(包括其母夜梦金星)。李阳冰又以“太白之精”(“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1]1949)称呼李白,强调了李白生而神异的特征,带有明显的虚构夸饰成分。
李白“别称”中的“虚称”,大多受到道教的影响。除了论者最常用的“谪仙”,还有“仙才”(“庆历间,宋景文诸公在馆。尝评唐人之诗,云太白仙才,长吉鬼才”[11]1347),“星精”(贯休《观李翰林真二首》其一“虽称李太白,知是那星精”[2]9338),“水仙”(萨天赐《采石怀李白》“只应风骨蛾眉妒,不作天仙作水仙”[14]1847),“神人”(黎廷瑞《过太白墓》“神人岂久谪,旋复御炁回”[25]),“金星”(傅察《和鲍守次韵林德祖十四首》“梦得惠连春草句,虚传李白是金星”[26]),“仙翁”(罗与之《题采石李太白祠》“仙翁谪堕岷山下,逸气如虹耿林罅”[27]498),“长庚之星”(梅灏《祭李白文》“公之之亡余三百祀,意其长庚之精,与天地而终始”[10]278),“天上飞仙”(王沂《登李太白捉月之亭访温峤燃犀之所览草庐吴先生蛾眉亭记宋漕使韩南涧及学士欧阳圭斋乐府李溉之长歌慨然有赋》“风流往事凭谁问,天上飞仙醉不醒”[28]),“五通仙人”(“太白是五通仙人”[29]),等等。这些称呼,以“神”“仙”“星”为标志,与道教有着直接关系。
佛教化的“别称”,在李白身上比较少见。具有佛教色彩的“别称”,典型的例子来自明代屠隆的《论诗文》:
以禅喻诗:三百篇是如来祖师,《十九首》是大乘菩萨,曹、刘、三谢是大阿罗汉,颜、鲍、沈、宋、高、岑是有道高僧,陶、韦、王、孟是深山野衲,杜少陵是如来总持弟子,李太白是散圣,李长吉是幻师,郊、岛是苦行头陀,《玉台》《香奁》是绮语破戒僧,温、李二罗是野狐禅。[16]432
这段文字中,将李白称之为佛界“散圣”,约略相当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与李白的个性仿佛近之。此外,称李白为“诗魂”(薛师石《李白墓》“野人烧残竹数枝,诗魂飘荡定何之”[27]569),也可归入佛教化的“别称”,因为佛教讲究“六道轮回”,“魂魄”是要进入“阴曹地府”的。就此视角而言,“诗魂”之称的档次,不及“散圣”“谪仙”之类的称名。
3.虚实共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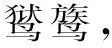
简而言之,李白的“别称”源于其自身且涉及“三教”(儒:翰林学士;释:青莲居士;道:谪仙人),与其思想观念之复杂、人生经验之丰富、创作成就之巨大、传播影响之深远密切相关。因此,其“别称”在数量、内容、形式等方面都独具特色。
二、李白“别称”的作用价值
在前文中,我们列举了若干例证,对李白“别称”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大致的梳理。下面拟就李白“别称”所发挥的作用、具有的价值,进行一些说明阐析。
(一)概括特征
李白的“别称”,多数是对李白的性格、个人爱好、文学成就等方面特征的概括说明。
1.人物性格
在描述李白其人形象及性格的“别称”之中,“士”的特征得到了彰显。好友崔宗之视李白为“雄俊士”:“思见雄俊士,共话今古情。李侯忽来仪,把袂苦不早。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2]2905(崔宗之《赠李十二白》)“雄俊士”是对李白才思敏捷、辩口超群的赞赏。唐人李华称其为“高士”:“姑熟东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同时解释“高士”的含义:“夫仁以安物,公其懋焉;义以济难,公其志焉;识以辩理,公其博焉;文以宣志,公其懿焉。宜其上为王师,下为伯友。”[1]1952(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在他看来,李白是一位具备“仁爱、正义、识见、文采”素养,胜任“帝王之师”的非凡“高士”。明代王守仁称其为“狂士”:“李太白狂士也,其谪夜郎,放情诗酒,不戚戚于困穷。盖其性本自豪放,非若有道之士,真能无入而不自得也。”[16]219这是出于对李白不因挫抑而折、不为困穷所屈的豪放性格的肯定。明代方孝孺称李白为“特达士”:“君不见唐朝李白特达士,其人虽亡神不死。声名流落天地间,千载髙风有谁似?”[14]1848(方孝孺《吊李白》)这些诗句主要是对李白千古流传之声名风范发出的由衷感叹。除了以“士”为称名,表现李白性格的“别称”还有不少。有的从为人处世角度入手,称其为“天地臣、平地仙”,以表现其不畏权贵、平交王侯的性格,如宋人李吕形容李白:“奴视髙力士,风期鲁仲连。……自谓天地臣,浪称平地仙。”[31](李吕《读太白集》)明代江盈科称李白是情绪化极强的“快活人”:“李青莲是快活人,当其得意斗酒百篇,无一语一字不是高华气象;及流窜夜郎后,作诗甚少,当由兴趣消索。”[16]461这种被得失、喜忧影响的表现,展示李白凡夫俗子的人格界面。反映李白性格的“别称”还有“真放”(“负逸气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为真放焉”[2]7016)、“放旷士”(“先生放旷士,浩气吞洪濛”[32])、“高旷人”(“太白高旷人,其诗如大圭不琢,而自有夺虹之色”[33])、“澹荡人”(“濯锦沧浪客,青莲澹荡人”[34]975)等。
此外,有些“别称”是从李白衣着形貌入手的。陆游泛舟经过采石李白墓附近时写道:“尚想锦袍客,醉眼隘八荒。坡陁青山冢,断碣卧道旁。”[34]168宋人赵公豫《采石矶怀古》有言:“姑孰江头暂置邮,凉风萧飒胜三秋。燃犀韵事归何处,披锦诗人迹尚留。”[21]197他们二人所称“锦袍客”“披锦诗人”,都是由李白身披锦袍、饮酒邀月的故事生发而成。
2.自我好尚
论及李白的个人生活习惯爱好,排在首位的当是饮酒。“酒星”“酒仙”“酒仙翁”“酒中仙”“酒家仙”等,已在前文有述。对于李白嗜酒,晚唐诗人皮日休以《七爱诗·李翰林》为题,称李白为“酒星魄”来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吾爱李太白,身是酒星魄。……醉中草乐府,十幅笔一息。召见承明庐,天子亲赐食。醉曾吐御床,傲几触天泽。”[2]7018在他看来,李白的口才、文思、傲然之气,全部与饮酒醉酒密切关联。皮日休的观点代表了不少关注“李白与酒”的论者的意见。对于酒之于李白的作用,唐人沈光在其《李白酒楼记》中有专论:
(酒)视其强者弱之,险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于人也如是。噫!翰林李公太白,聪明才韵,至今为天下唱者,业术匡救,天必付之矣。……太白触文之强,乘文之险,溃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觞,沉溺曲糵,是真筑其聪,医其明,醒则移于赋咏,宜乎醉而生,醉而死。[35]3734
由此可见,酒之于李白的作用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李白是为醉酒而生、因醉酒而死,堪称“醉酒人生”。
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观览大好河山、登临古迹名胜,也是其一大爱好。魏颢《李翰林集序》称他为“李东山”:“间携昭阳、金陵之妓,迹类谢康乐,世号为李东山。”[1]1877张祜《梦李白》诗称其为“李峨嵋”:“我爱李峨嵋,梦寻寻不见。忽闻海上骑鹤人,云白正陪王母宴。”[4]221这两个“别称”与李白的游历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前文言及的“匡山读书客”“竹溪六逸”“锦袍客”“披锦诗人”“方外十友”诸称,均与李白的游踪有所关联。
3.文学成就
李白的身份是天才文士、著名诗人,其文学成就,特别是诗歌创作成就,历来成为关注的重点。这一情形在其“别称”中得到了反映。“诗仙”“诗杰”“诗豪”“诗客”等,都是对他诗歌创作成就与特色的概括。值得注意的是论者时常将李白与其他诗坛名家进行对比。如明代杨慎称“陈子昂海内文宗,李太白为古今诗圣”[14]1860(杨慎《周受庵诗选序》);南宋刘克庄称李白与苏轼为“翰林两仙人”[36](刘克庄《十一月二日至紫极宫诵李白诗及坡翁和篇因念苏李听竹时各年四十九余今五十九矣遂次其韵》)。
在李白与名家的对比中,关涉最多、最重要的诗人是杜甫。有人将李杜并称“诗圣”:“李杜得诗圣,迥出诸家前。寂寞千载后,身死名流传。”[37](杭淮《挽李献吉四首用曹太守韵》其二)有人将两人称为“大宗”(大,一作“太”;大宗,即大宗师):“唐以来诗人,唯李杜为大宗。”[38](陈谟《鲍参军集序》)不过,在众多李白与杜甫比较之“别称”中,影响最大的是“李杜”。“李杜”之称最初主要是针对二人创作成就而言。韩愈多次论及“李杜”,盛赞二人的文学特色及贡献,所持观点为“李杜并尊”:“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2]3780(韩愈《荐士》),“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2]3792(韩愈《感春四首》其二)。与韩愈同时的皇甫湜也认为李杜二人难分高下:“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2]4150(皇甫湜《题浯溪石》)而元稹则认为李白不及杜甫,坚持“尊杜抑李”观点:“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35]2946(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元稹此言一出,引发了“李杜优劣”的论争,迄今仍未完全平息。当然,这种争论大多是从二人的文学成就,以及人物性格特征等方面进行的,能够增进对其深入体察与领悟。
(二)评价方式
李白的“别称”也是对李白进行评价的重要方式。在此,我们重点列举他人对李白评价的“别称”。这些“别称”包括正面评价(赞赏、同情),也包括负面评价。
1.赞颂
有关李白此类评价的“别称”数量不少,其中“诗仙”“诗杰”之类,是直接赞誉李白诗作文才的。有的“别称”字面并非关涉诗文,但观其前后文字,则知意在称颂李白文才。皮日休《郢州孟亭记》所谓“明皇世,章句之风,大得建安体。论者推李翰林、杜工部为尤”[35]3703,意在表彰李白与杜甫继承发扬建安风骨的贡献。至于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虽然列出李白“狂客”“谪仙人”两个“别称”,但重点则在“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2]2430二句。杜甫此言一出,即成概括李白诗风特色之定评。宋人徐铉称李白为“圣代词臣”[39],包含着对李白职司翰林学士的看重,可视之为对李白文才兼功业的肯定。有些“别称”使用戏谑之语,表面贬抑而实为赞赏,如贯休《书陈处士屋壁二首》其二云:“新诗不将出,往往僧乞得。唯云李太白,亦是偷桃贼。吟狂鬼神走,酒酽天地黑。”[2]9318自己新写的诗歌被别人拿走,作者反而自我解嘲说李白也是个“偷桃贼”(喻指借鉴前人他人),表现出对李白诗歌神奇卓异特色的欣赏。宋人孔平仲说李白是“诗家徒”(指其作诗极为投入与痴迷,近似常人所谓的贪杯的“酒徒”),也是为了赞誉其才:“卓哉太白诗家徒,天然俊逸不可拘。豪文脱去刻削巧,远意得自浑沌初。酒醒落笔洒风雨,当时所就皆须臾。”[40]
有些论者在利用“别称”赞誉李白时也兼顾到自己。他们或将自己与李白比作同类人物:“君抱碧海珠,我怀蓝田玉。各称希代宝,万里遥相烛。……雪上天台山,春逢翰林伯。宣父敬项橐,林宗重黄生。一长复一少,相看如弟兄。”[2]2905(魏万《金陵酬李翰林谪仙子》)或以李白为学习榜样,表达仰慕之情:“我身若在开元日,争遣名为李翰林。”[2]6521(薛能《寄符郎中》断句)另有一些论者,在赞誉李白时兼赞他人。晚唐诗僧齐己认为,李贺的“狂”与李白的“颠”都非常有特色,极具威慑力、感染力:“长吉才狂太白颠,二公文阵势横前。谁言后代无高手,夺得秦皇鞭鬼鞭。”[2]9593(齐己《谢荆幕孙郎中见示〈乐府歌集〉二十八字》)宋代大诗人黄庭坚则极为钦佩李白和苏轼:“不见两谪仙,长怀倚修竹。行绕紫极宫,明珠得盈掬。……我病二十年,大斗久不覆。因之酌苏李,蟹肥社醅熟。”[41](黄庭坚《次苏子瞻和李太白浔阳紫极宫感秋诗韵追怀太白子瞻》)清代的俞廷举在《全蜀艺文志序》中将李白、苏轼和杨慎三人称为天下“真大才子”:“余尝与天下士论古今真大才子,得三人:一曰唐太白,一曰宋东坡,一曰明升庵(杨慎);才皆天纵,殆文苑中之生知安行者,是以天骨开张,横纵自如,冠绝当代。”[16]1031杨慎与李、苏二人并列,可能仍有异议,但将李白与苏轼称作真正的“大才子”,是公认的。
2.同情
李白文才超群、立志高远、心怀天下、热衷建功立业,但其命运不偶。功成身退的人生目标不仅无法实现,反而招致各种无端的非议与责难。对于李白一生的遭遇,不少人表达了深切的同情。白居易《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云:“每叹陈夫子,常嗟李谪仙。名高折人爵,思苦减天年。不得当时遇,空令后代怜。”[2]4896他还在《序洛诗序》中具体说明李白、杜甫等著名文人遭遇不幸的原因:
予历览古今歌诗,自风骚之后,苏李以还,次及鲍谢徒,迄于李杜辈,其间词人闻知者累百,诗章流传者钜万。观其报自,多因谗冤谴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今古,什八九焉。世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于斯见矣。[35]3056
白居易的解说,融入自己真切的人生感受,是中肯的肺腑之言。李白在安史之乱时入永王李璘幕以及被流放夜郎的经历,人们十分关注。有些论者对李白的“从璘”给予否定性的评价。不过,也有人对此较为宽容:“士负其才,词彩足以惊众者,岂尽济世之人也哉?李太白天人也,而失节于永王璘,况余子乎?”[42](王庭珪《跋颜持约诗》)这一评价虽然仍将李白“从璘”视为“失节”行为,但是表现出相当的理解与同情。李白生前文声隆盛、名满天下,身后之事却极为萧索。五代殷文圭《经李翰林墓》描述了这种状况:“诗中日月酒中仙,平地雄飞上九天。身谪蓬莱金籍外,宝装方丈玉堂前。虎靴醉索将军脱,鸿笔悲无令子传。十字遗碑三尺墓,只应吟客吊秋烟。”[3]8134“鸿笔悲无令子传”与李白生前的耀眼光芒形成鲜明对比,其中传达出的不仅仅是同情,还有巨大的悲哀。
3.贬责
李白是才华志向远远超越凡俗的人物,必然令人“侧目”。李白的人生遭遇,正应验了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43](李萧远《运命论》)的名言。李白自己曾说:“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2]1818(《醉后答丁十八以诗讥余捶碎黄鹤楼》)可知当时对他持否定态度、加以贬责的人不在少数。文坛上对其不满者,也是时时皆有。从韩愈《调张籍》中“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2]3814等句可见,中唐时期对李杜不满者(不满李白者居多),形成不小的声势。与韩愈同时且身居高位的元稹坚持“扬杜抑李”的立场,对文人士子评价李白产生负面的影响。如有宋人以“卫道士”的口吻对李白诗歌内容提出批评:“李杜,号诗人之雄,而白之诗,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正何补于教化哉!”[44](赵次公《杜工部草堂记》)也有人对李白任职翰林时受命写过的几首应制适景之作予以讥讽:“花底杯盘藉翠茵,折花围坐当歌人。谪仙自是开元客,玉帐熏香揖太真。”[45](王安中《清明后一日出寻梨花……作诗凡得三首绝句》其三)与贬责相关的李白“别称”并非全无合理之处,但其中也不乏感情用事、不切实际之点,需要认真加以甄别。
当然,无论赞誉、同情与贬责性的“别称”,都属于评价李白的方式。这些方式,对提高李白的声誉、引发对李白的关注与深入研究,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三)传播载体
传播指对信息的发布与传送,是利用具有意义的符号(文字、声音)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别称”源自对相关信息的概括提炼,构成形象简洁的文字符号,以利于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别称”又可以稀释化解、添枝加叶,形成新型的信息(故事)。李白的“别称”完全具备这些传播的特征与功能。
1.文人着意推出
李白“别称”的形成,主要来自包括李白在内的文人之手,特别是历代著名的诗人文士,在李白“别称”的命名及推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唐代贺知章、杜甫、韩愈、白居易、元稹、杜牧、李商隐,宋代王禹偁、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郭祥正、陆游、杨万里、刘克庄,元代萨都剌、张养浩、王恽,明代方孝孺、王世贞、杨慎、屠隆、王守仁,清代陈维崧、方东树、沈德潜、贺裳等。他们或者提出(命名)李白的“别称”,如贺知章的“谪仙”,郭祥正的“金銮客”“诗中元帅”“酒中豪”,王世贞的“千秋才”,陈维崧的“开元供奉”;或者表达对李白的仰慕之情,如韩愈《石鼓歌》中的“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2]3811;或者将李白置于文学发展史之中,以之为范,如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有“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2]5941等句,作者将“李杜”与“韩柳”并列,向晚辈介绍当代“诗”与“文”创作的榜样;更有将其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步,说李白是“诗中天子酒中圣”,要“千秋万世诗人酒客群奉先生为至尊”[16]961(孙珮琳《谒太白墓》)。但从整体上讲,文人们推出李白“别称”(特别是唐宋时期)的过程,是对李白相关信息的选择、精炼及形象化,目的在于以醒目的词语快速地加以传播。
2.文学(文艺)创作素材
李白的“别称”,自其出现的盛唐时代起,就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特别是大多进入了诗歌创作。到了晚唐五代时期,距离李白在世的时间渐远,李白的“别称”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愈益紧密,其标志是对“别称”加工并收录于笔记小说之中。有的增加了情节,如贺知章与李白相遇,多数人认为只是赠其著名的“别称”——“谪仙”(或“谪仙人”),之后孟棨《本事诗》沿袭了“谪仙”的说法,同时增加了《乌栖曲》的内容: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尝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赠诗及焉。[46]2385
而稍晚于孟棨的王定保,其《唐摭言》所载情节与称呼均有所不同:“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46]2859将贺知章对李白的“别称”,由“谪仙”变为“太白星精”,显然是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加工的结果。王仁裕对李白的关注度更高,经他之手,李白的“别称”出现在不同的文学体式中,名称也不同。如诗歌中是“李杜”,如其《和蜀后主题剑门》云:“孟阳曾有语,刊在白云棱。李杜常挨托,孙刘亦恃凭。庸才安可守,上德始堪矜。暗指长天路,浓峦蔽几层”[2]8401;小说中则是“醉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李白嗜酒,不拘小节,然沈酣中所撰文章,未尝错误,而与不醉之人相对议事,皆不出太白所料,时人号为‘醉圣’。”[46]3174王谠《唐语林》所录“李白谒宰相”事,彰显出李白的超凡气势:
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曰:“海上钓鳌客李白。”宰相问曰:“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白曰:“风波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线,明月为钩。”又曰:“何物为饵?”白曰:“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饵。”宰相竦然。[47]
王简的《负琴生》则将李白提高至与神仙直接交往的地步:
负琴生者,游长安数年,日在酒肆乞酒饮之,常负一琴。人不问即不语,人亦以为狂。或临水,或月下,即援琴抚弄,必凄切感人。李太白闻焉,就酒肆携手同出埛野。临水竹籍草,命之对饮,因请抚琴。生乃作一调弄,太白不觉怆然。……与太白同醉而回。明日,太白复欲引之于酒肆共饮,不复见。后数日,太白于长安南大树下见之,方欣喜欲就问之,忽然而灭。[48]
至此,李白实现了由文人(与贺知章交往)、高人(与宰相对话)到仙人(与神仙饮酒)的故事化过程。李白的“别称”,参与到李白事迹故事化之中,属于传播的二次具象化、丰盈化的范畴。
3.文化建设平台
李白是著名诗人,其思想品格、政治追求、人生经历又极为独特卓异,因此他已不仅仅属于文学范围,而是属于文化领域。李白的文化价值、作用与影响力,随着时代的推移愈益明显。他的“别称”,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这些“别称”,有的直接成为李白纪念建筑的名称,如宣州的“二仙亭”(3)此处“二仙亭”,或为“二仙堂”之误。见下文《五贤堂记》所云。,宋代杜范《二仙亭祝文》有言:“维昔谢公尝为郡牧,‘净练’‘晴绮’之句,迨今为此城绝唱。后数百年间,谪仙来游,凡所赋诗于公亦多称道。……二仙并祠,才自近岁。某切睹遗迹,企仰清风,莅职之初,一酹致敬。”[49]此处的“二仙”指谢朓和李白,谢朓在其《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中有“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之句。李白对谢朓十分仰慕,多有咏谢朓之诗作,“二仙亭”因其二人而建。与“二仙亭(堂)”相关的是同样坐落于宣州的“五贤堂”。宋人王遂《五贤堂记》曰:
二仙堂者,祠齐尚书谢公朓、唐供奉翰林李公白也;五贤者,增唐宣州观察使颜公真卿、太子宾客白公居易、吏部侍郎韩公愈也。祠事二仙而增三贤为五者,所以追仰高风,景行行哲,非徒设也。[10]733
这里“二仙”“五贤”之称,均包括李白。李白一生游历大江南北,在其经行之处多有遗迹存在。比如当涂是其离世所葬之地,就有名为“骑鲸处”“捉月台”之类的所在。这些遗迹的命名,与李白“骑鲸仙子”(《当涂县志稿》“骑鲸仙子千年恨,万石佳人万古情。牛渚矶前浪好屋,区区名利与生轻”[10]133)、“捉月仙”(韩淲《李白泛舟图》“采石矶头捉月仙,脱靴意气尚飘然。沈香亭北惊尘世,且惜闲身棹酒船”[50])等“别称”有所关联。与此同时,李白遗迹又会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进而形成新的李白“别称”。“捉月仙人”(戴昺《五松山太白祠堂》“舣舟来访宝云寺,快上山头寻五松。捉月仙人呼不醒,一间老屋战西风”[51])、“天上仙人”(郑獬《五松山》“天上仙人谪世间,醉中偏爱五松山。锦袍已跨鲸鱼去,惟有山僧自往还”[52])之称,就是宋代两位学者游览五松山时所形成的。至于“太白酒楼”“谪仙居”“读书处”之类的称呼,在与李白相关的地区,可谓比比皆是。凡此,都为李白其人其作其事的传播、李白文化的弘扬提供了助力。
晚唐诗人杜荀鹤在其《经青山吊李翰林》诗中有言:“青山明月夜,千古一诗人。天地空销骨,声名不傍身。”[2]7942曹松《吊李翰林》也说:“李白虽然成异物,逸名犹与万方传。”[2]8245能够使李白千古不朽、万方流传的原因,包括他创作的优秀诗歌作品、正史稗说的实录记闻;同时,历代累积的“别称”,也因其文词简洁、形象鲜明、概括力强、易于记诵、便于联想、有助发挥等优势,在李白其人其诗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