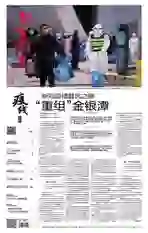社会组织不扎根,谁做社区工作?
2020-03-05刘怡仙
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

社区志愿者在武汉汉口一社区门口分菜装袋,准备给居民配送。 南方周末记者 ❘ 翁洹 ❘ 摄

社区工作人员在社区门口设岗,限制人员进出。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 ❘ 摄
上游的社区出现堰塞湖,下游医疗资源不足,这种情况下,根本没办法疏通河道。而且在武汉当地,社会组织较少扎根社区。一旦问题出来了,找谁来做社区的工作呢?
武汉封城当日,71岁的杨团得知几个公益人联合发起京鄂iWill志愿者联合行动,主动要求加入,“以个人名义参与,担任专家组顾问,定位是三线志愿者。”
数日来,她在北京远程在线参与武汉抗疫行动,工作至今,不断为公益组织和武汉、北京的社区防控提供行动建议。
从抗疫行动开始,杨团就认为居家隔离的社区是此次防疫的前沿,应当和医院一样成为重点。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政策中心顾问,她不断上书相关部门,提出以线上支持线下社区排查的“三群联动,三师联动”的工作方式,即尽早将社区全体居民纳入大群,再将有症状者拉到中群,症状特别突出的进入小群管理,大中小群联动,由医师、社工师、心理师进行专业服务,发现病案,通过绿色通道送往医院。
但这一模式,通过武汉社区服务有所表达,但总体目标并没有实现。
2020年2月25日,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杨团,从志愿经历和社会学学者角度,分析疫情防控的重心和方法,深入反思为何社区防疫早期在武汉不太理想。社会组织为何在社区防疫中参与程度不高。以下内容为杨团自述。
调研群变成了咨询群
我认为,首先要好好理解这次疫情是怎么回事。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当天下午1点半,iWill志愿联合行动开始,通过他们的微信群,我开始正式参与志愿活动。
在群里我了解到,当时无论是社会还是医院,秩序比较混乱,看病的人很多,但床位不够,医生也不够,而政策倡导居家隔离。我一听到居家隔离政策,意识到社区的作用非常重要,就跟陈兰兰(武汉市逸飞社工服务中心负责人,iwill志愿者联合行动的本地社工)建议,你赶紧拉一个群,把社区里的人找来,专门了解下居家隔离的情况。
当天下午,群就建起来了,哗啦啦地进来一大拨进不了医院的病人,调研群变成了咨询群,很多人问病情。社工们只好赶紧找专业医生,当线上志愿者解答问题。
我一边看,一边做调查,通过陈兰兰,我找过社区干部,社区卫生中心主任。自己也在大群里找武汉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的人,统统是了解情况,还找了好几家大学的教授。通过差不多一天半的密集调查,基本上厘清了情况,除夕下午就开始针对社区防控写“三群联动”方案。
24号开始,我认准社区防控的目标,一边写政策建议,一边努力推动支援武汉社区的线上实践。
“三群联动”是把疫区的社区居民先聚到大群里,通过社工工作,发现有困难、有疑似症状的居民,再拉入中群,中群的高危人群再分别进入不同的小群,进行一对一的个案辅导和医疗转介。同时线上无接触的支持能弥补社区工作人员不足,有利于线上排查。
这套方案提出后,由iWill志愿者联合行动的专家组不断提炼和完善。后来,我们和陈兰兰一起努力地做,但在当时无法真正实行。
首先大群建不起来。当时社区基层做排查很难,缺人手,连挨个打电话的工作都完成不了。工作人员也缺乏防护用品,甚至存在部分社区工作人员被感染的现象。基本上,社区居委会瘫痪,没人给你从大群里“捞人”。患者或疑似患者自己给社区打电话,社区无法解决(求诊、入院治疗的)问题,患者只能绕过社区,直接到医院去。
但医疗资源也严重紧缺,患者很难入院。这样一来,患者在发热门诊、隔离点、医院三个地方来回穿梭,增加交叉感染机会,导致感染基数大幅增加。直到方舱建成,“应收尽收”落实。
社区防疫实践为什么不理想?
我后来一直反省,“三群联动”做不出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十七年前,我参与了非典救援,那时街上也没有人,我们甚至没强调每个人出门要戴口罩。
那时,社会组织很少,我们做的事情主要是张贴疫情科普广告、给病人送药。当时我不担心自己会被感染,因为SARS感染症状明显,很快发高烧,病情很重,感染者能马上被识别出来。
但这回大不一样,新冠病毒肺炎有隐蔽性,轻症、重症、无症状感染者什么样的都有。
上游的社区出现堰塞湖,下游医疗资源不足,这种情况下,根本没办法疏通河道。而且在武汉当地,社会组织较少扎根社区。一旦问题出来了,能找谁来做社区的工作呢?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都是线上远程支持,线下无法实操。
这个事让我挠头很久。总的来说,社会组织这次的响应也不够快,协同作战不足。虽然在防护物资筹集上,不少志愿者和社会组织也快速行动,但这些行动大多以松散组织存在,看到前线有需求,七手八脚地做,推进很迅速,很难做到真正协调与合作。
线上支持,最终也没形成与社区线下密切合作的社区排查格局。最后,真正起作用的都是拉“散客”的大群。起初想做调研的大群,吸引了许多求助的居民,他们咨询、求诊,陈兰兰从散客大群中识别出高危居民,再拉到小群,进行个体辅导。但对有高危迹象的居民,没有办法链接社区资源走绿色通道,而是依靠武汉社工的个人关系找医院床位。这说明什么? 巨灾来临,所有秩序被打乱,还按照平时的思维方式制定的政策和方案,无法契合混乱的秩序。
我认为真正应该表彰的是春节期间站出来的武汉普通志愿者。他们最了不起。有个志愿者叫汪洋,在一家社工机构任职,大年三十跑出来,和一群志愿者结成战队。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自愿站出来,各个年龄层的都有,明确知道有感染的风险,在外租房子住,不回家,奋战了一个多月。上班复工以后,很多地方开始招党员志愿者、青年志愿者、退役军人志愿队等等。汪洋他们的志愿队也转为由防控指挥部指挥,每天都派任务。
最紧急的关头,这样的志愿者冲在一线,是大灾救援的规律。在大灾面前,个体是最敏感的,也是反应最迅速的,迅速组织战队,许多不认识的人在危难中结成战友情谊。
这次iWill志愿者联合行动,我只认识郝南、翟雁几个组织者,但工作中,却认识了一大拨专业的志愿者,他们很多人给我打过很多电话,一起开过无数次线上会议,但是我们从来没见过。
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为什么不高?
为什么社会组织这次参与程度不高,要从系统说起。
目前的大灾救援中,简单地说,可以分成正式系统和非正式系统。正式系统即行政系统,包括政府的事业单位、各类群团组织。非正式系统指的是非行政系统,可以简单理解为“政府不会发工资”的系统。非正式系统里又分为正规军、杂牌军和游击队。正规军指的是慈善会、红会系统以及国字头基金会,杂牌军则指在民政系统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游击队是冲在最前面的志愿者团队。
目前政府提及的社会力量,首先指的正式系统,然后是非正式系统。
所以,当我们提到社区成为行动主体,需要注意,社区里有各种各样的组织,不要只想到只有社会组织。在社区里,社区领导、网格员属于政府发工资的正式系统。而社区里社会组织,有些是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有些是在街道备案但没有注册的社区社会组织。
实际上,我们常说的社会组织都不是扎根在社区的社会组织。社区里大量存在的是社区社会组织,备案但没有注册,大多是文艺兴趣、体育类的协会。
这次疫情中,在武汉真正起作用的是业主委员会。许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合作,自己招募志愿者,给小区筹款,买消毒液、口罩、防护服,甚至帮助老年人、儿童,救急救困的活儿他们也做。这是真正在非正式系统里,在社区起作用的组织。
武汉早期如果采用社区防控方式,是比较能够消化矛盾的。但大批病人集中出现,医疗资源被挤兑,谁也不知道怎么办,毫无经验可循的时候,甚至有些社区基本瘫痪,再做居家隔离,也没有办法改变状况,最后还是方舱医院应收尽收,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要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政策偏向社区后,我发现又有新的问题。社区缺人、任务太重,人手不够。一个社区工作人员需要服务五百人甚至上千人。任务层层下压,社区玩不转。
2月6日,我提出十条建议,其中一条关乎社区人力。社区没人怎么办? 干部春节后返岗,可以去社区上班,后来省直市直干部都下社区了,武汉一个社区能够下沉三十多名干部。
方舱建成后,医院压力缓解,社区也逐渐建立秩序。我建议,民政部门把过去政府购买服务的社工组织动员起来,帮助支持社区保障生活物资供应,还有各种非新冠病人的用药以及生活支持。
武汉陷于紧急状态下,难以抽出身来认真考虑政策。但是湖北以外的其他省市,在社区工作有一定基础的社会组织,还是能发挥作用。尤其是四川,经过两次地震的洗礼,成长出一批优秀的社会组织,像成都的“爱有戏”,过去就一直做社区工作,这次配合街道和社区防疫,做得挺好。
我发现,凡是扎根社区的社会组织,疫情面前就特别主动,立刻能跟社区连接,做老百姓的心理安抚、科普宣传等。这些机构原来就活跃在社区,做社工服务。但要发挥作用,首先要和社区跟街道协商,要提出有效的思路,且能够对接社区需求。
所以,我现在指导这些社会组织设计社区防控机制,将衡量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无风险的指标标准化,再用色块标出来,再将指标具体化。这些指标不仅包括四类人群,确诊的、疑似的、密切接触的、返岗隔离的,还有其他重要指标,比如说外来人口比例、人口密度、地理位置、社区工作能力、社区社会组织等。最后形成一个信息化系统,动态更新。
要让社区的工作系统下沉到楼栋,信息要与楼栋长连接,所有居民都进入群组,这样不仅限制防控工作好做,帮助、支持困难人群,以及今后做社区基层治理都会容易的多。发一个信息,老百姓就都知道了。这就是以人为本、真正照护到人的基层体系。
我原来设想的“三群联动”,在武汉,最终是在一个叫金地太阳城的小区基本实现了,他们是线下为主。
北京有个公益组织叫“夕阳再晨”,负责人叫张佳鑫,以前是专门研究计算机的博士。近期,我在指导他做一个以街道社区为范围的防控体系,起名叫“街道大脑”。我希望能将这次防疫经验,嵌入日后常规工作的职能模块,结合社区未来一定要做的大健康和基层治理,长期走下去。
未来,常规社区管理模块中,如果能有一个与CDC的公共卫生预警体系链接,延伸到社区的功能模块。而且,这些内容都通过计算机搭建的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去实现,把各个方面的网络信息连起来。那对于防控未来的不可知风险,就真的有力量了。
从这次武汉防疫来看,我觉得我们往后还要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哪怕是文艺团体、老人团体都可以,因为自组织有力量。社区外的社会组织,可以对这些自组织加以引导。
我认为,在病毒灾难面前,我们对共同体伦理倡导不够。应该强调“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他人”,每个人之间互相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无论在一个小区、武汉、中国,乃至世界都是由小及大的共同体。如果不倡导共同体伦理,彼此就无法互信、无法协作。
现在抗疫已经进入新阶段,未来社会心理、社会信任重建的任务会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