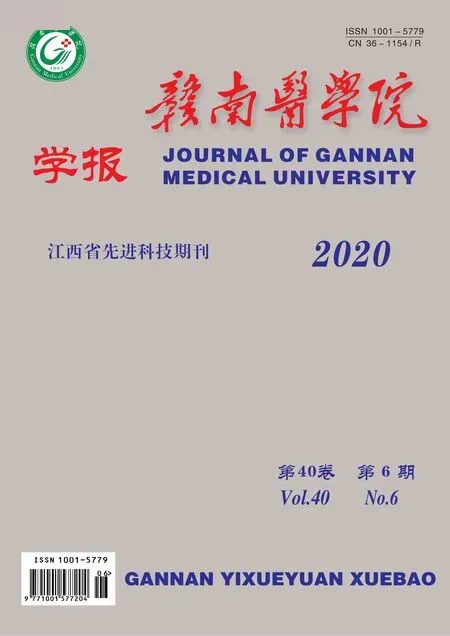肠道菌群失衡对同种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影响
2020-03-04谢景春谢保平余丽梅
谢景春,谢保平,余丽梅
(1.于都县人民医院,江西 于都 342300;2.赣南医学院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西 赣州 341000;3.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细胞工程重点实验室,贵州省生物治疗人才基地,贵州 遵义 563003)
人体内定植了1013~1014不同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也是影响我们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1]。近十几年来,随着对肠道菌群(Intestinal microbiome,IM)研究的不断深入,越发突出了IM在维持人类健康,肠道正常生理功能,如营养吸收、能量代谢及抵御肠道感染和促进免疫系统成熟等方面的关键作用[2],而IM失衡与一些重大疾病密切相关,如结直肠癌、肠易激综合征、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肥胖和过敏等疾病。美国“国家微生物组计划”和中国联合全球12个国家发起全球微生物基因组测序计划的提出,又使得微生物与疾病或药物不良反应相关性的研究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3]。
干细胞移植是治愈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和其它多种疾病的重要手段,接受同种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llo-HSCT)的患者由于其自身疾病以及广泛接触抗生素和放化学治疗抑制异种排斥的关系[4],而使得她们的IM结构被严重破坏,丧失了正常IM组成的屏障功能,削弱了对致病菌的抵抗作用,从而加重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versus-host disease,GVHD)和感染等并发症,制约了allo-HSCT在临床上的应用。因此,动态观测、深入地研究人体IM变化以及它们如何影响allo-HSCT并发症发生、发展,对于提高allo-HSCT的疗效与成功率,制定有效措施,防治不良反应发生具有重要价值。
1 肠道菌群和allo-HSCT并发症的关系
1.1 IM失调与GVHD的关系GVHD是移植相关并发症最严重的一种,它与肠道功能紊乱密切相联系。早期研究IM的作用发现,在无菌环境中进行allo-HSCT后,小鼠死亡率和急性GVHD的发生率显著降低[5]。在allo-HSCT治疗过程中,发现使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全身治疗会减少梭状芽孢杆菌的丰度,并增加了丹毒丝菌 (Erysipelotrichia)和肠球菌的数量,加重GVHD的程度[4],提示IM的改变对GVHD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在骨髓移植后的小鼠和GVHD患者中,也发现梭菌及乳酸杆菌的减少;骨髓移植前清除小鼠肠道乳酸杆菌也可促发GVHD,当重新引入主要的乳酸杆菌时,GVHD症状得到缓解[6],进一步研究发现allo-HSCT治疗后细菌移位会触发急性GVHD发生[7],且发现活动性胃肠道(Gastrointestinal, GI) GVHD的患者IM中肠球菌的移位最为明显[8]。
健康人的IM呈现高度多样性,而allo-HSCT受者通常表现为细菌多样性的下降[9]。allo-HSCT患者早期的放化疗,使得IM多样性在早期阶段便显示出大幅减少,其中包括梭菌和双歧杆菌的减少及肠球菌的增加[10]。小鼠实验还证明放疗后细菌移位是导致嗜中性粒细胞向肠道组织募集的关键,嗜中性粒细胞的浸润可介导活性氧进一步损伤局部组织,导致GVHD恶化[11]。此外,研究发现从移植当天开始,患者表现低IM多样性,其中肠球菌比例增加,其他厚壁菌门显著减少。尤其在活跃性GVHD中,这些表现更为明显,表明保护性和致病性细菌之间的不平衡可能是导致GVHD的因素[8]。另一项GVHD的研究也指出,当体内梭状芽孢杆菌类的布劳特氏菌属(Blautia)占主导时,对GVHD的好转有益[12],而肠球菌增高则通过毒素介导的肠道炎症和损伤对结肠上皮组织产生直接有害影响,并通过诱导巨噬细胞释放TNF-α发挥效应,最终发展为GVHD[13]。因此用特异性细菌来作为GVHD发生、发展的预测或采用补充益生菌群,减轻或延缓GVHD具有十分可行的理论或实验基础。共生厌氧菌的减少,特别是抗炎梭菌的减少,肠球菌的大量扩增,以及用抗生素治疗的GVHD小鼠效应CD4+T细胞浸润增加和IL-23水平升高都与经典的急性GVHD相关[4]。
其次,与肠上皮细胞(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IECs)损伤相关的宿主组织相容性复合体的抗原暴露增加也会促进急性GVHD的发展,具体而言,环磷酰胺能改变小肠中的IM组成,并诱导特定的革兰氏阳性细菌转移至肠道次级淋巴器官中,加强 “致病性”Th17细胞和Th1介导的特异性免疫应答发挥功能[14]。
最后,基因层面也发现IM中的FUT2基因的改变会增加allo-HSCT后急性GVHD和菌血症的风险[15]。也有研究表明细胞内NOD2的宿主突变与急性GVHD相关,NOD2功能的丧失可能导致微生物感染控制失败,从而引发全身反应和异常炎症[16]。也就是说,IM的改变与allo-HSCT后GVHD并发症出现息息相关。
1.2 IM失调与炎症感染的相互作用炎症感染是IM失调和免疫应答引起的移植相关并发症常见的结局。allo-HSCT前的高剂量放化疗也会使肠道稳态受到干扰,导致肠道微绒毛的损失,紧密连接受损和IgA分泌减少,进而GI上皮完整性被破坏,方便病原菌定植进入血液循环,导致严重的炎症感染并发症。而在allo-HSCT后IM,炎症感染和免疫反应之间却具有复杂和多方向性相互作用的关系[17]。
高剂量放化疗会引起黏膜损伤,导致炎症细胞因子的释放,包括TNF-α、I型干扰素、IL-1和IL-6,这些炎症细胞因子可直接改变IM的组成,上调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和免疫共刺激分子的表达,从而促进GVHD和炎症感染的发生[18]。组织损伤又增加了肠道的通透性,可使内毒素在肠黏膜中无障碍性转运,进一步激活了宿主的先天免疫系统及细胞因子释放。
现已证明,清髓或非清髓处理的allo-HSCT及使用免疫抑制剂后,IM多样性减少,丁酸盐的缺乏以及梭菌属IV和XIVa的相对丰度减少与肠道炎症强度呈负相关[19],而肠球菌丰度的增加与炎症程度呈正相关[20]。艰难梭菌感染(Clostridiumdifcileinfection, CDI)作为allo-HSCT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患者发病率在10%~15%之间[21],CDI通常是使用广谱抗生素和化疗导致的后遗症,有研究表明allo-HSCT受者的CDI比率高于自体移植患者[22]。小鼠模型证明梭状芽孢杆菌可通过产生继发性胆汁酸,抑制艰难梭菌的生长和毒素产生,有效防止CDI的发生[23]。同时CDI也是allo-HSCT受者感染性腹泻的常见因素,据报道发病率约为15%~20%[24]。另外allo-HSCT后IM失调常常也出现菌血症[10]和GVHD症状[25],这些都说明了IM的改变也是移植后炎症感染并发的重要潜在诱因。
2 肠道菌群调节allo-HSCT并发症的免疫机制
以往的研究资料证明,革兰氏阴性细菌外壁层中的脂多糖会通过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 4, TLR4)信号启动GVHD过程,刺激嗜中性粒细胞浸润产生活性氧来介导局部组织损伤,导致GVHD恶化[11]。提示IM通过免疫应答调节allo-HSCT并发症。肠道免疫系统依赖于完整微生物群强直信号的传导来发挥最佳功能。受微生物组影响的免疫细胞包括固有淋巴细胞、嗜中性粒细胞、DC细胞、T细胞和B细胞以及NK细胞。所以从免疫调节角度探讨移植并发症与IM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关键的。
动物实验显示,在无菌条件下生长的小鼠不具有正常的免疫系统,易遭受病原菌感染,而抗生素摄入会增加条件致病菌的定植和致病性[26]。其机制可能是共生菌与代谢相关的病原体肠内竞争营养物质有关。另一种可能的机制是共生菌对粘蛋白产生有促进作用。正常情况下,杯状细胞产生的粘蛋白所形成粘液层作为物理屏障可以抑制病原体侵入,而无菌小鼠的粘液层比正常小鼠薄得多[27],导致病原菌侵入更为顺畅,机体的防御越发脆弱,说明了共生菌在体内是相辅相成的,某一方失衡都会引起免疫系统紊乱,进而不利于移植效果的稳定及促进多种不良反应的发生。
固有的淋巴细胞(Innate Lymphoid Cells,ILC)作为免疫效应物,是对抗病原体的第一道防线。ILC具有显著的免疫调节和组织再生作用,特别是在粘膜表面能加强IECs的紧密连接性。ILC也能产生集落刺激因子2来应答巨噬细胞衍生的IL-1β,刺激DC产生视黄酸以促进Treg的募集发挥免疫作用[28]。研究发现ILC1在IL-12的刺激下能分泌IFN-γ和TNF-α来响应肠道感染[29];ILC2则能在慢性炎症区域分泌组织再生所必须的双调蛋白;而NKp44阳性ILC3则在IL-23信号刺激下产生组织保护性细胞因子IL-22,抑制局部和全身炎症来调节共生菌[30]。由此可知,它们在维持肠内稳态平衡和肠上皮再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此外,IL-22也可触发AMP的释放来促进IECs再生,保持上皮的老化更新来促进屏障的完整,IL-22治疗后小鼠肠GVHD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也说明作用机制与IL-22促进肠干细胞介导的IECs再生有关[31]。
其次,特定的IM还可以促进T细胞分化,如梭菌物种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已被证明可促进叉头蛋白3(forkhead box protein,Foxp3)诱导Tregs的扩增或分化,也可通过上调TGF-β以支持FoxP3的诱导来识别微生物抗原[32]。肠球菌的增加,梭菌的减少使得病原相关分子通过IL-1和IL-6诱导炎症反应加强后,产生的级联信号进而会激活Th1和Th17的适应性免疫应答[8];这种反作用致使 Tregs也通过抗炎细胞因子IL-10在GI稳态中发挥重要作用,或者直接影响巨噬细胞快速应答以保护机体[32]。
此外,共生菌还能调节粘膜免疫系统中的自然杀伤性T细胞的发育和成熟,诱导的Treg细胞以及效应T细胞向肠固有层中的抗原位点募集[33]。这种将IM与T细胞功能连接的潜在分子机制还可能与DC和巨噬细胞表达的催化色氨酸降解的初始限速酶吲哚胺2,3-双加氧酶(indoleamine 2,3-dioxygenase,IDO)有关,因为IFN-γ等炎症性细胞因子也可诱导IDO,并通过消耗色氨酸抑制T细胞活化,并上调Tregs诱导免疫耐受,而共生细菌产生的丁酸盐可通过IECs中的双重机制下调IDO的表达[34],提示微生物群在调节IDO中发挥一定作用。
B细胞也参与了肠道免疫系统的调节。有数据证明共生菌能够影响肠道固有层早期B细胞谱系的发育,并且由IECs分泌的细胞因子以T细胞依赖性方式介导B细胞产生IgA,穿过上皮屏障进入肠腔,亦为另一条防治微生物紊乱的重要防线[35]。
3 调节IM改善Allo-HSCT并发症的临床治疗
外在条件和宿主本身可以影响微生物的组成,导致IM多样性的波动,影响移植后并发症的发生。这些因素包括年龄、饮食方式的改变、抗生素使用、炎症、代谢产物和压力[2]。因此针对性采取措施可能是改变移植后效果的可靠方式。
3.1饮食饮食方式的改变在影响IM组成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allo-HSCT后饮食方式的不同可能导致GVHD的发展,数据显示接受全肠外营养的小鼠和人受试者会表现出INF-γ的增加,以及IL-4、IL-10、肠道CD4+细胞减少的现象,这很可能就是促炎症反应的免疫应答方式,而在allo-HSCT的患者中,转而慢慢采用肠内喂养的饮食方式,可降低Ⅲ~Ⅳ级GVHD和感染事件[36]。此外,肠内补充低聚糖,纤维和谷氨酰胺,对接受allo-HSCT的患者具有降低死亡率和肠球菌移位的趋势[37]。在环境因素方面数据也显示,allo-HSCT后在家接受护理与在医院调养相比,Ⅱ~Ⅳ级急性GVHD的发生率较低[38],说明暴露于医院环境也可能对IM产生不利影响。
3.2抗生素抗生素治疗可能是影响allo-HSCT过程中IM多样性破坏的主要因素[10]。研究显示口服环丙沙星和广谱抗生素的患者易出现肠球菌增加及共生菌主导力的下降[39]。共生菌作为AMP的重要诱导物,长期抗生素治疗,会使得Paneth细胞产生的抗微生物活性的C型凝集素-再生胰岛蛋白3a(regenerating isletderived 3-alpha)等特异性AMP的诱导下降,抑制肠球菌过度生长的作用就会减弱,IM多样性的维持反而不佳。在回顾性研究中,发现allo-HSCT患者使用利福昔明可以保护肠道多样性,并与环丙沙星和甲硝唑联合治疗的患者相比,其移植相关死亡率更低[40],可能是利福昔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留某些有益的厌氧肠道微生物,不影响微生物群的总体组成有关。广谱抗生素虽可减少细菌毒力因子的表达,病原体的粘附和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来调节肠道炎症,但是它也会加重IM多样性的丧失。据推测,共生厌氧生物如梭状芽孢杆菌可能有助于维持和恢复IM多样性,并且使用耐厌氧菌的抗生素可能有益于患者[41]。但会引发多药耐药菌的定植[42],因此研发单一稳定的靶向抗生素依然是当务之急。
3.3益生元和益生菌益生元在调节IM的方面,主要表现为抑制肠道致病菌与上皮的粘附,增强肠上皮的抗感染和抗炎作用。益生元作为一种难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在共生菌的发酵下产生短链脂肪酸,如丁酸盐、醋酸盐和丙酸盐,然后被用作能量来源促进IECs的健康。其中一些短链脂肪酸能通过诱导Treg细胞来产生一些抗炎性的细胞因子,在抗炎性通路上调节GVHD的发生和严重程度[32]。又一研究证实allo-HSCT后的小鼠黏膜组织中丁酸盐水平含量降低,可能与组蛋白乙酰化减少和IECs凋亡增加有关,而给予丁酸盐治疗可减少肠道损伤和GVHD,其机制可能与增加跨上皮的电阻和降低菊糖渗透性促进肠壁屏障功能有关[25]。共生菌产生的3-吲哚酚硫酸盐(3-indoxyl sulfate,3-IS)是由结肠细菌中的毛螺菌科(Lachnospiraceae)和瘤胃菌科(Ruminococcaceae)产生的一种L-色氨酸代谢产物,在IM中起细胞间信号作用,调节肠道黏膜屏障功能或IECs中表达促炎和抗炎特性。与晚期抗生素治疗相比,早期使用抗生素会降低3-IS水平和共生梭菌的丰度[43],说明allo-HSCT后早期低3-IS水平是微生物群被破坏的标志,并可导致移植相关的高死亡率[7]。
益生菌则在增加Treg细胞数量的同时上调TGF-β水平来降低CD4+/CD8+T细胞的作用赋予宿主获益[44]。
乳酸杆菌作为良好的益生菌来源,可以改善移植后的急性GVHD和肠道炎症发生。前期有人观察到,在移植前后接受鼠李糖乳杆菌GG的小鼠,可减少病原菌移位进入肠系膜淋巴结,局部组织学炎症和GVHD减轻,然而这也存在争议,有报道指出,用鼠李糖乳杆菌GG补充治疗的allo-HSCT患者并未显着改变IM多样性,也未改变GVHD的发生率或严重程度[45],这可能与Elan等研究的样本量较小有关。
3.4粪菌移植粪菌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 是一种通过重建IM来治疗疾病的方法。在恢复IM物种多样性丧失或减少方面,FMT被认为是很好的益生菌来源,而且在难治性或复发性CDI中的疗效已经明确。研究提示,FMT可以根除受者GI中抗生素抗性细菌的定植,而且对于恢复allo-HSCT前后导致的梭菌降低十分有益。此外,减少抗生素的使用有利于提高FMT的效果[46]。另一方面FMT对于激素抵抗型GVHD的改善也有帮助[47],然而,FMT的临床研究还需要更为多样的益生菌移植加以验证,并需要更大样本量的临床试验加以深入阐释、实证。间充质干细胞联合allo-HSCT移植,不但可明显提高HSCT的疗效,还可大大降低或延缓GVHD的发生或减轻其临床症状,间充质干细胞的移植是否也明显影响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的IM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
4 展 望
人体IM的变化对allo-HSCT后并发症的影响使人们更加关注肠道功能紊乱的潜在标志。除了对IM失调的监测外,还应对关注饮食、生活方式、种族和环境因素对IM的影响。虽然我们对IM在人类健康中的角色做了很多探索,但具体机制和非细菌性病毒体的研究尚十分有限。病毒体与菌群基因的改变可能也是诱发潜在感染的重要线索,潜在感染一旦发生,势必引发更严重的肠道感染和免疫应答失调,对干细胞移植治疗效果及其并发不良反应的影响可能会十分突出,因此加强针对IM失调全面而深入的探索对于提高疗效、降低不良反应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干细胞移植技术的改进和IM精准医学检测的发展,及IM与allo-HSCT后不良反应发生关系认识的深入,未来将会有更多的策略来改变IM失调,改善allo-HSCT效果,为临床治疗移植后严重并发症提供更好的防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