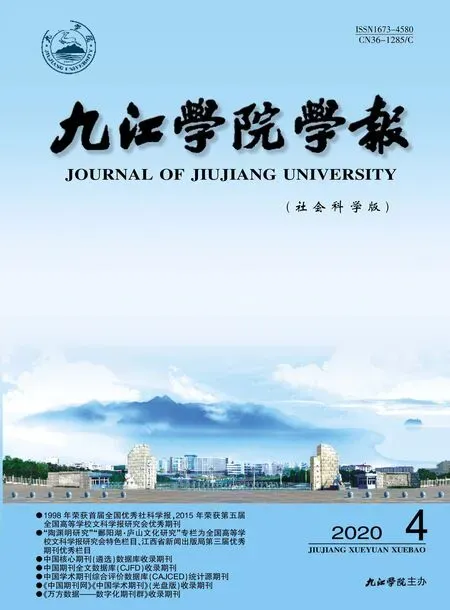东晋士僧交往与山水诗的生成
2020-03-04胡亚琦
胡亚琦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河南信阳 464000)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1]此句指出山水诗脱胎于玄言诗,目前学术界也普遍认同此观点,但东晋“庄老”如何“告退”,宋初的“山水”如何“方滋”,刘勰并没有详言。现当代学者则多从玄理、佛理发展的角度来阐释山水诗的产生,这种观点得到了学界认可,但忽略了重要的一点,无论是支遁的佛教思想,还是慧远的佛教思想,在对诗歌发展进程产生作用及影响时,都是通过“人”即“诗歌创作者”这一媒介来完成的。东晋时期,佛教为谋求自身发展依附于玄学,主动向士族阶层靠拢,士僧交往迅速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开启了后世士僧交往的先河。东晋士人所特有的文学文化因素,以及大部分僧人所具备的文学才能,决定了士僧交往的过程中必然会或直接或间接地进行大量文学创作。据笔者粗略统计,现存士僧交往直接产生的诗歌作品共计59篇(士人作品48篇,僧人作品11篇),其中涉及山水描写,或直接于自然山水环境中创作而成的诗歌作品共计49篇(其中士人作品41篇,僧人作品8篇),另有其它体裁文学作品6篇(序记4篇,誓文1篇,书信1篇)。山水诗歌作品所占比重之大并非偶然,士人和僧人作为诗歌创作群体的主力军,这两个文化群体的交往活动显然与山水诗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即试从东晋士僧交往这一角度切入来阐释由玄言诗到山水诗这一文学现象的转变。
王国璎先生在其《中国山水诗研究》一书中,这样定义山水诗:“所谓‘山水诗’,是指描写山水风景的诗。虽然诗中不一定纯写山水,亦可有其它的辅助母题,但是呈现耳目所及的山水状貌声色之美,则必须为诗人创作的主要目的。在一首山水诗中,并非山和水都得同时出现,有的只写山景,有的却以水景为主。但不论水光或山色,必定都是未经过诗人和知性介入或情绪干扰的山水,也就是山水必须保持耳目所及之本来面目。”[2]仔细分析这一定义,可得出两个要点:第一,山水诗必然以呈现山水之美为主要创作目的,或可有其它辅助创作目的;第二,所呈现之山水必然是耳目所及之本来面目。“耳目所及”和“本来面目”二词甚值得玩味,自然山水的“本来面目”经过创作主体的耳目,再由其笔端呈现出来,此时的山水已非真正意义上客观存在的“物象”,而是经过了主观过滤和提炼的“心象”,只有当“物象”与“心象”高度融合之时,才能自然而然地呈现山水之“本来面目”,“山水诗”才真正诞生。笔者在对山水诗产生以前文学作品中的山水描写进行源流梳理时发现,这些山水描写或因“知性介入”,或因“情绪干扰”,均呈现出或重“物象”或重“心象”的特点。而这两条脉络恰在晋宋玄佛合流之际,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完美地合而为一,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由此诞生,而士僧交往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一层面来探究,诚然不能视为山水诗生成的全部因素,但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去评价,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东晋初期及其以前文学作品中山水描写脉络梳理
“山水”进入诗歌的时间极早,《诗经》创作时期,自然山水是先民们生活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先民对其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但《诗经》中却没有以歌咏自然山水为创作目的的诗篇,山水入诗仅有只言片语,作为起兴“言志”的手段,且都是质朴的“物象”描写。继《诗经》之后,《楚辞》中山水描写的篇幅有所增加。首先,《楚辞》中描写的多为楚地风物,受楚地“巫”文化的影响,多以奇幻的想象描写神灵居住的环境和氛围,因而呈现出的山水描写多为夸张变异化的“心象”。其次,“香草美人喻”是《楚辞》的一大特色,故而《楚辞》中的山水花草树木并不为展现其“本来面目”而被描写,只是作为寄予作者情感倾向的工具。
秦汉时期,作为汉代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文体——汉赋中有大量的山水描写。汉初的骚体赋直接继承了《楚辞》的抒情传统,其中对山水的描写也多为“心象”描写。如淮南小山《招隐士》中对山林环境的描写,“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山气巄嵷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曾波。猿狖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通过对山中桂树、云气、山谷等夸张变形处理,营造出一种森然可怖的氛围,从而引出主题“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王褒的《九怀》、蔡邕的《述行赋》也都有类似这种虚幻性“心象”山水描写。稍晚,以“体物”著称的汉大赋体式形成,因其创作内容多涉及园林、游猎等,故有不少山水描写,但因其艺术手法强调铺排夸饰,故其中模山范水的片段亦多为艺术夸张之后的“心象”。至东汉,赋体文学发展至抒情小赋,则出现了纪实性的山水描写(如张衡《归田赋》),预示出山水摹写由虚幻的“心象”逐渐向纪实的“物象”转变的趋势。
汉魏之际,社会的动荡不安迫使文人将目光重新投向现实生活,创作目的及描写对象也随之改变。建安时期,产生了“第一首纯然描写自然景物的山水诗”[3],即曹操《步出夏门行》组诗第一章《观沧海》。但由于文学创作外部条件的限制,以及文学自身内部发展的不足,山水诗并没有因此兴起,故而王国璎先生称之为“一首早期的孤立的山水诗”。
建安时期,邺下文学集团多有游园宴饮赋诗活动,因而创作了大量的公宴诗。“风月”“池苑”自然成为公宴诗的描写对象,但池苑之美仅是无意识中被呈现,建安文学主缘情、重个性的特质决定了,抒情依然是主要创作目的。故刘勰将“怜风月,狎池苑”的创作目归结为“述恩荣,叙酣宴”。因而邺下公宴诗中山水实为“情绪干扰”下的“物象”描写。但这种对山川之美的捕捉能力,为后世山水诗的艺术技巧打下了基础。
至正始,政治黑暗,玄风大畅,形成了与建安完全不同的文学风格。玄学的基础是老庄哲学,崇尚自然,文学创作中即表现为追求人与自然冥合的境界。“只有在这种人生境界之上,完全摆脱功利的目的,才有可能在文学创作中把对于自然的态度引向了审美的层次。”[4]而自然山水成为抒写这种境界的必然媒介,审美趋向的出现,使山水描写中“物象”与“心象”出现了融合的趋势。
两晋之际,社会再次进入分裂状态,残酷的现实致使游仙诗创作风尚兴起。诗中着意刻画仙人居住的仙境,而仙人多隐于远离世俗的天宫、山岳、河海之中,故而诗中涉及大量虚幻性山水描写,尤以郭璞的游仙诗作为代表。与正始时期相比,正始诗歌多追求与自然同化的感受,即“物象”与“心象”的趋同,游仙诗重在表现畅游仙境的快意,即更偏重于“心象”描写。
至东晋,玄风复炽于江左,玄言诗大作,山水描写进入玄言诗,山水诗已初具雏形(下文将具体论述,此处暂且不论)。东晋几乎与玄言诗同时期,而略早于山水诗,产生了山水赋,代表作有孙绰《游天台山赋》《望海赋》、郭璞《江赋》、庾阐《涉江赋》。山水赋中大规模的山水描写,和汉大赋一样,多为虚幻的“心象”,但又有本质的区别。汉大赋中的山水描写都是片段性的,并非创作内容的主体,而其写作目的也是通过对山水中众多物产的描写间接赞颂政治;东晋山水赋则是将对自然山水描写作为创作的主体和创作的直接目的。尽管铺陈夸饰的艺术手法难以描摹出自然山水真实的面貌,但这一点对稍晚产生的山水诗,在题材选择上具有启发性意义。
二、东晋中期由玄言向山水的转变
东晋中期,玄言诗逐渐成熟,在山水悟玄的指导思想下,不少玄言诗中借助对山水的描写抒写玄理,兰亭诗即为最典型的事例。穆帝永和九年,“时高士许询、孙绰、李充、支遁并居东土,羲之尝与同志宴会,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序,以申其志。”[5]由王羲之所作《兰亭集序》可知,兰亭雅的目的是“游目骋怀,畅叙幽情”,故传世的兰亭诗多为直述玄理的玄言诗,但由于其创作环境的特殊,多有自然山水入诗句。王玄之《兰亭诗》有诗句:“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清流。”[6]王彬之《兰亭诗》有诗句:“鲜葩映林薄,游鳞戏清渠。”其中最具山水诗特质的是孙绰的《兰亭诗》:“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此诗笔墨轻盈自然,将自然景物和人物活动以及所悟之玄理巧妙地融为一体。
玄佛合流的背景下,不少僧人创作的玄理诗或佛理诗中亦有山水描写。如支遁的《八关斋诗三首(其三)》,对山水的描写占据了较大的篇幅,全诗如下:
靖一潜蓬庐,愔愔咏初九。广漠排林筱,流飙洒隙牖。从容暇想逸,采药登崇阜。崎岖升千寻,萧条临万亩。望山乐荣松,瞻泽哀素柳。解带长陵陂,婆娑清川右。冷风解烦怀,寒泉濯温手。寥寥神气畅,钦若盘春薮。达度冥三才,恍惚丧神偶。游观同隐丘,愧无连化肘。[9]
这首诗首句“潜蓬庐”点明这次八关斋活动,之后“广漠排林筱……钦若盘春薮”数句着重描写了山中的自然景色,青山,松柏,秋水,柳树,高坡,溪水皆入诗中。全诗20句,其中14句皆落笔于自然山水景物,虽然支遁的本意在于末尾4句玄理的表达,之前均为悟道过程的描写,但不可否认这首诗中自然山水所占篇幅之大,“山水”可称为诗歌描写的主体。
如果说支遁的诗作还是明显的玄言诗,其目的明显还是表述玄理的话,那么庾阐和僧人帛道猷的诗作直观看来,则与山水诗无异。庾阐《三月三日临曲水诗》:
暮春濯清汜,游鳞泳一壑。高泉吐东岑,洄澜自净荥。临川叠曲流,丰林映绿薄。轻舟沈飞觞,鼓枻观鱼跃。[10]
帛道猷《陵峰采药触兴为诗》: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间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这两首诗完全以描写山水为创作内容,但将其分别与兰亭诗、支遁《八关斋诗三首(其三)》和后世成熟的山水诗作相比较,则不难发现它与兰亭诗及支遁诗的相似度明显更高。这两者对山水的描写呈现出单一化的特征,比如描写的景物多为“林”(“竹”“松”)“流”(“川”“渠”)“风”“云”“鱼”(“鳞”)等,且“林”(“竹”“松”)的特征都是“修”,“流”(“川”“渠”)的特征都是“清”,对水中事物的描写仅有“鱼”(“鳞”)。虽然看似对自然山水“物象”的描写,但实则是经过玄理过滤的“心象”的呈现,被选取景物的共同特点是清淡、秀美、玄远。而自然山水的美却是具体的,多种多样的,这种单一特点显然没有呈现出自然山水的本来面貌,“心象”与“物象”仍然没有完全融合。庾阐和帛道猷的诗作,与其称之为山水诗,不如称其为隐藏了玄言尾巴的玄言诗。
三、晋宋之际慧远及庐山僧俗的山水游记
慧远及庐山僧俗所作的山水游记,均为实地游览庐山山水而作,其所描写的对象是真实的自然山水,这一点与兰亭诗相同。但与兰亭诗不同的是,兰亭诗人游赏山水的动机是感悟“独化于玄冥之境”的玄理,故而笔端所呈现出的是玄理化的“心象”。而庐山僧俗游庐山的动机则是探寻“即有以悟无”的佛理,故而其山水描写能够从玄理的时代风气中解放出来,走向独立的山水审美观。
“即有以悟无”是慧远的主要佛学主张之一。就本体论而言,慧远肯定“实有”存在,他曾这样论述“法性”(即事物或现象的本质):“性空是法性乎?答曰:非。性空者,即所空而为名。法性是真法性,非空名也。”同时他认为这种“实有”并非是静态存在且一成不变的,而是由于因缘条件的不同,不时发生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物象,即“一切众缘力,诸法乃得生。”但物种的自性(即事物的本质)是始终不变的,想要把握本质(真理),就必须从这些不断变化的表象中来探索,即“寻相因之数,即有以悟无,推至当之极,动而入微矣。”[7]因此,庐山僧俗游山并极力描写山水的目的,实则是希望通过自然山水瞬息万变、姿态万千的物象,把握佛教所言终极真理。在这一探索佛理的过程中,山水却以其独特的审美特质唤醒了庐山僧俗的审美体验,众人将这种独特的审美感受通过笔端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
以庐山诸道人所作《游石门诗序》为例:
石门在精舍南十余里,一名障山。基连大岭,体绝众阜。辟三泉之会,并立而开流,倾岩玄映其上,蒙形表于自然,故因以为名。此虽庐山之一隅,实斯地之奇观。皆传之于旧俗,而未睹者众。将由悬濑险峻,人兽迹绝,径回曲阜,路阻行难,故罕径焉。
释法师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咏山水,遂杖锡而游。于时,交徒同趣三十余人,咸拂衣晨征,怅然增兴。虽林壑幽邃,而开途竞进;虽乘危履石,并以所悦为安。既至,则援木寻葛,历险穷崖,猿臂相引,仅乃造极。于是拥胜倚岩,详观其下,始知七岭之美,蕴奇于此:双阙对峙其前,重岩映带其后,峦阜周回以为障,崇岩四营而开宇。其中则有石台、石池、宫馆之象,触类之形,致可乐也。清泉分流而合注,渌渊镜净于天池。文石发彩,焕若披面;柽松芒草,蔚然光目。其为神丽亦已备矣。
斯日也,众情奔悦,瞩览无厌。游观未久,而天气屡变:霄雾尘集,则万象隐形;流光回照,则众山倒影。开阖之际,状有灵焉,而不可测也。乃其将登,则翔禽拂翮,鸣猿厉响。归云回驾,想羽人之来仪;哀声相和,若玄音之有寄。虽仿佛犹闻,而神之以畅;虽乐不期欢,而欣以永日。当其冲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也。
退而寻之,夫崖谷之间,会物无主,应不以情而开兴。引人致深若此,岂不以虚明朗其照,闲邃笃其情耶?并三复斯谈,犹昧然未尽。俄而太阳告夕,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玄览,达恒物之大情,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哉!
虽不能否认这次活动的宗教内涵,但“因咏山水”已明确可知慧远此次游山的目的确为吟咏山水。序中对庐山石门景物的描写细致入微,有山水之奇丽石台之光彩,“双阙对峙其前,重岩映带其后,峦阜周回以为障,崇岩四营而开宇。其中则有石台、石池、宫馆之象,触类之形,致可乐也。清泉分流而合注,渌渊镜净于天池,文石发彩,焕若披面,柽松芒草,蔚然光目。”有光影之变化云雾之聚散,“游观未久,而天气屡变:霄雾尘集,则万象隐形;流光回照,则众山倒影。开阖之际,状有灵焉,而不可测也。”有禽猿之声响,“乃其将登,则翔禽拂翮,鸣猿历响。归云回驾。想羽人之来仪;哀声相和,若玄音之有寄。”这种真实的、具体的山水景象的呈现,完全不同于玄言诗中千篇一律的山水,是耳目所到之处所捕捉到细微的、独特的自然之美。且其中多有独特的审美体验,如“触类之形,致可乐也”“焕若披面”“蔚然光目”“状有灵焉,而不可测也”“想羽人之来仪”“若玄音之有寄”。这种既将具体的自然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和描写对象,同时又能够表达出真实的、个性化的审美体验的山水描写,已然既不是单纯的“物象”,也不是单纯的 “心象”,而是二者的高度融合。从“拂衣晨征”到“太阳告夕”,众人在山水之间流连整日,“斯日也,众情奔悦”,“众情”既包含有对玄理佛理的感悟,亦包含游赏山水而产生的审美体验,“奔悦”则是这种审美体验不由自主的喷涌而出。序末“情发于中,遂共咏之云尔”再次强调了这种“物象”与“心象”高度融合所产生的强烈审美体验。黑格尔在其《美学》中的一段话恰能准确表明这一艺术过程的发生,“这些自然形式并不因为它们本身而有意义,而只是它们所表现的那种内在心灵因素的一种外现。就是这种心灵因素使这些自然形式还在现实状态而尚未进入艺术领域之前就已具有观念性,不同于不表现心灵的单纯的自然。在艺术的较高阶段里,心灵的内在的内容(意蕴)就应该得到它的外在的形象。”[8]
慧远《庐山记》一文中“自托此山二十三载,再践石门,四游南岭”[9]明确指出庐山僧俗的游山活动至少有六次之多,传世的作品中虽未明确指出“交徒同趣三十余人”的究竟为何人,但据《高僧传》记载“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10]刘遗民、张野等皆有《庐山记》佚文存世,推测应为同游者。庐山僧俗皆有文学才能,具有超于常人的审美能力,在多次的游山及文学创作活动中,山水的宗教内涵逐渐削弱,而文学及审美内涵日益深化,山水描写逐渐完成由“物象”和“心象”的合一。
四、士僧交往与山水诗的生成
由上文论述可知,山水描写“物象”和“心象”的合流,必然要满足两个前提:一是将自然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和描写对象;二是能够表达出真实、个性化的审美体验。将庐山僧俗这种山水游记的创作经验成功移植入诗歌创作中的第一人,即是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
文学史多评价谢灵运的山水诗往往带有玄言尾巴,不可否认其诗必然受到了东晋时代风气的影响,但仔细对比,则不难发现谢诗中的山水描写与玄言诗中的山水描写截然不同。每一处山水描写都细致入微,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化特征,这显然与庐山僧俗游记中的山水描写相一致。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谢灵运游赏山水的经历十分丰富,“爰初经略,杖策孤征。入涧水涉,登岭山行。陵顶不息,穷泉不停。栉风沐雨, 犯露乘星。”[11]每到一处,总能目睹其独特之处,故而呈现于笔下也是千姿百态。另一方面,谢诗能够呈现出与玄言诗截然不同的山水描写,不得不归功于他在与庐山僧俗的交往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庐山佛教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与庐山僧俗相同的山水审美观。回过头来,追溯山水“物象”与“心象”逐渐融合的过程,东晋中期诗歌描写内容由玄言向山水的转变的过程,亦与士僧交往有密切的关系。
东晋初,世族南渡,江南蕴藏着中国最秀丽的山川景致,地域风貌与中原截然不同。士人作为一个文学素养极高的群体,对于自然之美的感悟力远超常人,会稽为名士聚集之地,会稽山水是最早进入士人视野的。“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12]“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山岳、河流、草木、四时之景的变换,会稽山水以其特有的情韵打动了士人的情怀,而此时东晋初期诗歌创作内容仍以玄言为主,极少出现对自然山水的描写。究其原因如下,东晋初社会思潮中玄学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士人主要的社会活动依旧是清谈玄言;与此同时,这一阶段僧人刚刚渡江,为传播佛教提高个人社会声誉,多游于京师,依附于名士,士僧间的交往多发生于城中的寺庙或者士人的官邸之中,其交往活动也多为清谈玄言,比如竺法潜,“晋元、明二帝,游心玄虚,托情道味,以宾友礼待法师;王公、庾公倾心侧席,好同臭味也。”,再如,成帝咸康四年,支遁在余杭白马寺中与冯怀论及《逍遥游》新义。文学是对社会生活及人的思想情感的反映,与之相对应,远离山水的创作环境和交往内容,决定了东晋初期的诗歌仍以玄言诗为主。
大概东晋成帝末年开始,不少僧人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声誉,佛教进一步得到了士人的认可,名僧重拾佛教最初的教义,即修道必居于山泽之中,纷纷离开都市,隐居山泽。东晋中期已形成了“天下名山僧多占”的局面,如《高僧传》篇目所载“晋豫章山康僧渊”“晋剡东仰山竺法潜”“晋庐山释慧远”等,更有支遁向竺法潜买山的典故。名僧的隐居并没有阻断士僧之间的交往,相比于东晋偏安一隅的政治局面,士人无心施展政治才能,而是更加乐于同名僧一起游目骋怀、谈玄论佛。与东晋初期不同的是,士僧交往的场所由都城、皇宫、士人官邸转移至自然山川中,此时交往的内容也不再是单一的手执麈尾针锋相对的清谈论辩,而是加入了诗文赠答、交游唱和或者建斋立誓。由于士僧交往地点的转变,山水自然而然地进入士僧的视野中,同时玄理与佛理的进一步交融,玄学已进入“山水悟玄”的阶段,且交游唱和与建斋立誓的文学意味比之清谈玄言明显增强,士僧交往的种种转变促使自然山水成为诗歌描写对象。如支遁的《八关斋诗》,诗序中称“间与何骠骑期,当为合八关斋。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同意者在吴县土山墓下,三日清晨为斋始。”可见这首诗的写作契机正是支遁与名士共集于吴县土山墓下进行斋戒悟道活动。
谢灵运与庐山僧俗的交往,促使其将庐山僧俗山水游记的创作经验成功移植入诗歌创作中。据《高僧传》记载,谢灵运不仅面见过慧远,且对慧远崇敬不已,“陈郡谢灵运负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见,肃然心服。”这种“肃然心服”应该是建立在深入的思想交流之上的。慧远在庐山所建“万佛台”竣工后,曾派遣弟子道秉请谢灵运为其作铭,“道秉道人远宣意旨,命余制铭,以充刊刻。”作佛影铭,不仅需要较高的佛学造诣,且需要较高的文学素养,选中谢灵运,则表明慧远对谢灵运佛学及文学造诣的双重认可。谢灵运《佛影铭并序》:“我无自我,实承其一。尔无自尔,必祛其伪。伪既殊途,义故多端。因声成韵,即色开颜。望影知易,寻响非难。形声之外,复有可观。”[13]其中体现的佛学思想与慧远所主张地“即有以悟无”如出一辙,可见,史料中对二人交往之记载虽不多,但二人佛学思想之交流程度匪浅。《高僧传》记载慧远去世后,“浔阳太守阮保,于山西岭凿圹开隧,谢灵运为造碑文,铭其遗德,南阳宗炳又立碑寺门。”谢灵运《庐山慧远法师诔并序》不仅表达了对慧远的崇敬与仰慕,其序中还表达了自己未能拜于慧远门下的遗憾之情,“予志学之年,希门人之末,惜哉诚愿弗遂。”谢灵运诗集中又有《送雷次宗》一诗,可见其与慧远弟子雷次宗亦有交往。从思想层面来看,谢灵运与庐山僧俗的交往使其与慧远佛学思想保持一致,这是其山水诗创作与慧远的山水审美观具有一致性的根本原因。从行为层面来看,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是其游山玩水活动的文学化表现,而谢灵运的游山玩水并非平心静气的“游目骋怀”,而是“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这种“探险式”的玩赏,更像是对庐山僧俗共游石门“人兽迹绝,径回曲阜,路阻行难”的模仿,亦可看作是谢灵运与庐山僧俗精神层面的间接交往。
综上,山水诗的形成有三个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东晋中期,玄佛合流,僧人隐居山泽,士僧间交往地点及交往内容的改变,为“山水”进入诗歌提供了契机;产生了玄言山水诗;第二阶段是晋宋之际慧远的佛学思想及庐山僧俗的游山活动及山水游记创作,促使“物象”与“心象”的合一,形成了山水审美观;第三个阶段是谢灵运与庐山僧俗的交往,佛学思想的一致性,促使其将庐山僧俗山水游记的创作经验成功移植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中,终成为山水诗一派的开山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