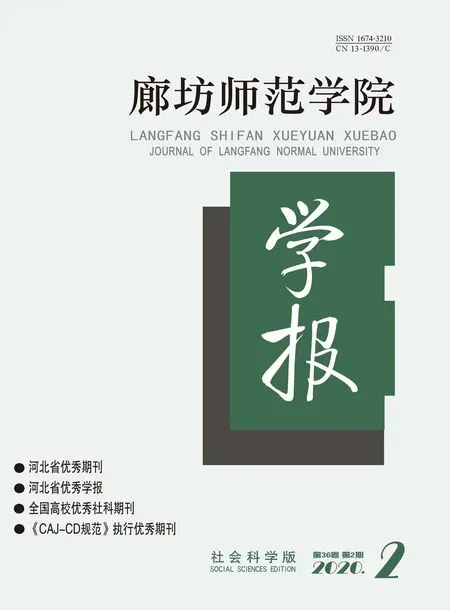从媒介行为看“先锋”小说思潮
——以文学月刊《作家》1980年代的办刊实践为例
2020-03-04孙明
孙 明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在1990 年代之前的中国“当代文学”中,文学期刊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不可忽视。一方面,由于文学期刊拥有优先的发表权限,大多数作品、评论和理论首先发表在期刊上,而后才收入专集、选集或扩充为单行本由出版社出版,因此,文学期刊留下了文学发展的最初轨迹。另一方面,文学期刊作为传播媒介之一,具有过滤并放大信息的传媒功能。具体而言,“传媒对信息的‘把关’,包括什么该发、什么该改、什么不予放行”①[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151页。。正是文学期刊的遴选、编修、发表及后续传播等多样的期刊行为,使“文学”得以被广泛地传播和接受。同时,文学期刊的“生产力”功能,对文学创作、作家群体、文学潮流的形成也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1980 年代的文坛,“先锋”小说是一个有较大影响的文学潮流。在“先锋”小说分散出现、渐成气候、直至引起创作界、批评界和文学史研究者关注的过程中,文学期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不同的时间段,《收获》《上海文学》《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中国》《北京文学》等期刊以不同的方式推举过“先锋”小说的部分作品,对“先锋”文学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支持作用,吉林省的文学月刊《作家》(其前身为《长春》,从1983年第7期更名为《作家》)就是其中之一。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言,“《作家》是较早给中国先锋文学提供机会的登陆场所,几茬先锋作家马原、苏童、格非、余华、潘军、孙甘露等都与它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作家》不是跟随者,而是实验者和开拓者之一”②汪政、晓华:《对〈作家〉的凝望与沉思》,《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从1980年代初大胆地推出发轫之作到1980 年代中期大力地培植新作,再到1980 年代后期有意地推动文学潮流的编辑活动,《作家》见证、参与、促进了“先锋”小说潮流的发展。从不知名的边缘省份小刊物到1980 年代末期就被称为“先锋的文学重镇”,再到逐步跻身“四小名旦”的办刊历程,《作家》与“先锋”小说共同成长。本文试从文学环境、传播媒介入手,探究“先锋”小说思潮的发展轨迹和发展特点。
一、发端:《长春》的胆识与“先锋”的零星探索
“先锋”小说在成为一个潮流之前,经历了一个大胆探索、艰难起步的准备期。《长春》自1978 年复刊以来,第一次有影响的期刊行为就是对“现代派”小说发端的参与。《长春》编者在一定的胆识和对“新锐”艺术倾向敏锐的“把关”意识下,发表了“先锋”小说起步阶段的名家力作——宗璞的《我是谁》和吉林省青年作者傅百令的“现代派”小说《梦》。在发表“新锐”作品要冒极大风险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长春》对“先锋”小说的发生有开路之功。
在社会思想文化氛围刚刚“解冻”的时期,在批驳“左”的话语、倡导人道主义的政策任务和公众共识下,出现了一批在题材上有探索倾向的作品,被时人命名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同时期,“复出”的女作家宗璞创作了一篇与“伤痕”“反思”文学似乎相似又有所差异的短篇小说《我是谁》。在《我是谁》中,叙事者讲述了女科学家韦弥的故事。她学成归国,全身心投入科研,却被批斗为“牛鬼蛇神”。遍体鳞伤的她意识产生错乱,看见自己及周围人变成虫,在“我是谁”的追问中投水而亡。“人变虫”的荒诞情节及冷淡的外聚焦叙述语调使该作品明显区别于同期的“伤痕”“反思”文学。虽然宗璞是“新时期”“复出”的名作家,但《我是谁》的发表却不尽顺利,“遭到多家刊物退稿,辗转周折近半年,后来被《长春》接收,《长春》将之放在1979 年第12 期的头题位置发表出来”①宗璞:《写给〈作家〉——祝贺〈作家〉创刊三十周年》,《作家》1986年第10期。。而后,《长春》在1980 年第11 期发表了本省作者傅百令创作的“意识流”短篇小说《梦》。该作品以老何在梦中的意识流动,串起了20 世纪50 年代至70 年代他与亲友的交际、在历次历史运动中的遭遇以及笼罩其中的恐惧心理等片段。《长春》还在该作品后面附上了评论文章——许震的《可喜的尝试:略谈〈梦〉的意识流手法》,该文章认为,作品“自由联想把琐碎的往昔经历融合成一个整体,扩大了作品容量、使结构新颖别致,带来自然真实的阅读感受”。
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这两篇“现代派”小说能够发表,足见作者和《长春》编者为艺术而冒险的胆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们与建国前30 年的作品以及当时发表的极大多数作品相比,其现代主义的艺术探索倾向都显得有些“异类”,而且,已出现的艺术探索尚未获得文坛主流的认可。在这两篇小说发表之前,尽管李子云的《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等文章讨论和驳斥了六七十年代文学规范的合法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第四次文代会也确立了思想解放、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任务,但社会思想解放的程度尚不足以使这些“现代派”小说的出现畅通无阻。当时,响应政策号召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在接受过程中尚时常碰壁,“现代派”艺术探索的难度可想而知。此前,对于被命名为“伤痕”与“反思”的文学作品,尽管曾引起社会的关注,轰动一时,但“暴露文学”②批评的观点认为作品揭露了阴暗面,是“暴露文学”。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页。“缺德文艺”③李剑:《“歌德”与“缺德”》,《河北文艺》1979年第6期。“题材禁区”这样的批评声音并不在少数。
特定环境下的种种现实条件,决定了艺术探索的艰难,而这也是“现代派”小说在发生期必然要面对的。《长春》在发表这两篇具有风险性的作品时,不得不采取一些策略以应对可能的“麻烦”。比如,以极低调的姿态推出《我是谁》:未用任何“版面语言”④指书籍报刊等出版物中用以体现编辑意图而在版面处理上采取的种种方式和手段。见李频:《期刊策划导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对之进行介绍,也未附任何评论文章对之进行解析,仅是将之置于头题位置。一般来说,头题在一期刊物的版面中具有重要地位,因处于版面之首,头题文章一般是编辑部推出的主打文章。编辑部低调如此,是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发表《我是谁》并不是轻松的事。人们对未接触过的文学样式、手法、内容等,不像后来能抱以宽广的襟怀去接受”①宗璞:《写给〈作家〉——祝贺〈作家〉创刊三十周年》,《作家》1986年第10期。。相较于《我是谁》,《梦》的发表显然面临的是一个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1980 年4 月至5 月,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召开,周扬在讲话中表示,“期刊三年来在解放思想和广开文路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文艺刊物是百花齐放的园地,新生的花比较脆弱特别需要保护”②周扬:《周扬同志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录)》,《中国出版》1980年第8期。,这就预示了在稍微和缓的思想文化氛围中,一些艺术探索能够成为可能。基于这样的社会形势,《长春》在发表《梦》时,才敢于运用多种“版面语言”。
从1980 年开始,《长春》编辑部关于阐明编辑工作意图的文章和“版面语言”陆续发表。在这些阐释文字中,《长春》编者努力从“思想解放”“双百方针”“艺术多样化”“现代化”角度,阐明编发“现代派”艺术探索作品的用意。时为《长春》主编的胡昭认为:“我们应该努力供应人民多种多样的艺术精品,纠正、培养和提高读者的欣赏趣味。作为编辑必须公正无私、兼收并蓄,给各种风格的作品以存在的权利。”③胡昭:《寄希望于编辑》,《文艺报》1980年第3期。《长春》1980 年第7 期发表了《花前漫议》,从编者的用意、作家的创作偏好和读者的接受个性三个角度,阐述了关于贯彻“双百”方针的看法。文章认为:“不要简单粗暴的文艺批评!读者、作者和编者应该是同志,向着一个目标前进,文艺才会欣欣向荣。”④赵宝康:《花前漫议》,《长春》1980年第7期。1980 年第11 期编发《梦》时,在目录下方的卷首语“这一期”中,《长春》编者对这两篇“现代派”小说的发表进行了细致的解释:“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我国文坛出现了十分可喜的现象,有不少作家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创新的艺术探索。对于这种探索和试验,我们不只赞同,而且乐于提供篇幅。鲁迅也曾呼唤中国新文艺的闯将。本着这种精神,去年十二月号,我们发表了女作家宗璞同志的《我是谁》,这一期我们又发表了省内业余作者傅百令的《梦》。我们认为,他们在艺术上所作的尝试是具有启发性的。”⑤《长春》编者:《卷首语“这一期”》,《长春》1980年第11期。如上所述,在当时复杂艰难的出版环境下,《长春》以“落实文艺政策”为名,支持、鼓励文学的艺术探索倾向,为“先锋”小说的发生起到了开路作用。
二、萌芽:《作家》的培植与“先锋”的边缘实验
在以潮流化现象冲击文坛之前,“先锋”的艺术探索更多的是在地处边缘的省份进行的,“先锋”小说的实验之作多发表在边缘地区的文学刊物上。因京沪等地的文学期刊位于文化中心,较易受政策或时势变动的影响,进行艺术实验受到的阻力比较大,对有意发表具有艺术探索倾向的“新锐”文章的刊物来说,“想要打破成规常要承受种种压力,这就为那些远离权力与文化中心的边缘期刊带来了发展契机”⑥黄发有、王云芳:《文学期刊与先锋文学》,《山花》2004年第11期;黄发有:《活力在于发现——〈人民文学〉(1949—2009)侧影》,《文艺争鸣》2009年第10期。。《作家》在对文艺政策、创作动向和文化环境的多重把握中,参与了边缘省份“先锋”小说的发展进程,为“先锋”小说在下一阶段的潮流化发展储备了力量。
《作家》在1983 年改刊后,于1980 年代中期推出了吉林省作者的多篇“先锋”小说实验之作,有的是在每年第9 期的“吉林青年作者小说专辑”中发表,有的是在各期的短篇小说板块中零散地刊载。这些具有“先锋”倾向的作品风格各有不同:洪峰的小说与西方哲学思想有更紧密的联系,在艺术探索的程度上比其他作者走得更远,更为“大胆”。他的《奔丧》(1986 年第9 期)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其“新锐”的创作特征以及内容上对传统伦理道德的颠覆、思想上与存在主义的关联,使得这篇小说甫一问世就引起了文坛的极大关注;而此前被《作家》编辑部同仁称为洪峰转向“先锋”的转型之作《公园里,有一棵树》(1985年第9 期),已透露出冷漠、虚无的小说氛围;《蜘蛛》(1986 年第4 期)也借梦幻和玩世不恭的主人公传达了一种现代的情绪;其后的《小说》(1987 年第9 期)和《天气与照片》(1988 年第5 期),则以游戏式的叙述虚构生活琐事。吴若增的小说以荒诞的情节为特色,整体上又是在批判现代主义的框架内。他的《走失了的模特儿》(1985 年第4 期)整体运用讽喻,失意女孩与橱窗模特互换社会角色,离奇的情节讽刺了悲观失望的现代情绪;《长尾巴的人》(1987年第10期)运用象征手法,臆想的尾巴给懦弱的男主人公的生活平添了哭笑不得的色彩。周松林的《回忆我临终之日》(1986年第8期)用“垮掉的一代”的语调自述冷酷的校园人际关系,“我”被同学嘲笑、被学院领导批评,最终借体育训练之机坠崖而亡。
《作家》对本省的“实验”文学的促进,除了为有潜力的作家作品提供发表的园地外,还深入地参与到培植本省的创作力量的实践中以评论指导创作。例如洪峰的《奔丧》发表后,《作家》及时发表了编辑朱晶的评论《地域、人性与现代意识》,对洪峰作品的出色及有待磨练之处及其创作道路的流变进行了评析。《作家》还举办创作研讨会,在本省文艺部门领导、《作家》编辑部、评论家和作者等不同视野内,及时对本省的实验文学作品进行研讨,扶植本省“先锋”文学创作的后备力量。1985—1987 年间对本省实验作品的讨论较为频繁,在此期间的《作家》上时时可以看到讨论本省青年作家作品的文章或综述文章。《有潜力,有希望——对“吉林青年作者小说专辑”的评论》《哲学意识的觉醒——谈我省青年小说创作及对他们的批评》《创作的自由试验与艺术的自觉选择——“吉林青年作者小说专号”讨论后综述》《沟通·理解·探索——吉林青年小说创作谈论会侧记》等文章,就本省青年作者“远离”为政策而写作的创作观、作品中的现代意识和哲理内容、冲破文艺禁区的勇气、顺应全国文艺发展流向等方面,表示了肯定,当然,也有少数的保留意见。另外,《作家》也为作者的成长做更长远的打算,“鼓励本省有潜力的作家‘走出去’,向中心地区的《收获》《花城》等投稿”①《瀚海》结稿后,主编王成刚鼓励洪峰“拿出去试试”。见洪峰:《和成刚相遇》,《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3期。。
此阶段吉林省的实验小说能够逐步发展起来,与省内外文学的动向不无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吉林省文联、作协就召开会议,“规定培养文艺新人,发展我省的文艺队伍,作为‘新时期’省内的文学任务”②吉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80 年1 月10 日至16 日在长春举行。“培养新人、繁荣本省创作”是这次大会确定的任务之一。见《长春》编者:《卷首语“这一期”》,《长春》1980年第3期。。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的机关刊物,《作家》在办刊实践中自然也要体现并参与其中。主管部门的要求,使《作家》在1980 年代以来的办刊历程中,形成了“鼓励创新、扶植新作”的编辑取向。另外,吉林省青年作家的文学实验也很难说未受省外风气的影响。在1970年代末宗璞的《我是谁》开实验探索风气之后,带有“现代派”艺术探索倾向的小说越来越多地见于文坛,冲击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文学观,为创作界带来一派不一样的风景。而同时期的翻译活动引入了大量西方20世纪以来的人文学科思想理论和欧美文学作品。先行者的文学实践及思想理论的创作资源储备为文学实验准备了可行的条件。在省外的文学实验渐成风气之时,《作家》逐步调整办刊方向,“跟踪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加强文学的现代意识,鼓励和支持新老作家进行各种探索和尝试”③公木:《回顾与前瞻——为〈作家〉创刊三十周年而作》,《作家》1986年第10期。,积极扶持本省的实验小说。艺术创新和探索逐步能获得更大的空间,也是因为顺应政策要求的“反思”和“改革”文学,因题材和写作方式的相近,难免陷入数量众多却雷同、僵化的困境中。自然,“文以载道”的写作难以维持原来的权威地位,而此时期《作家》的用稿标准是“艺术品位第一、探索创新第一”①这是曾任《作家》编辑的洪峰对主编选稿的回忆。见洪峰:《和成刚相遇》,《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3期。。《作家》的“艺术品位、探索创新”的用稿标准和“培养新生力量”的编辑方针,为本省青年作家初出茅庐的文学实验提供了必要的机遇和条件。
三、潮流化:《作家》的改刊与“先锋”的蔚为大观
在1980 年代中后期,凭借期刊中推出的专题专号和明确的理论方法的命名,“先锋”小说才以潮流化的面貌登陆文坛。继1985年第6 期《西藏文学》推出“魔幻小说特辑”②克珠群佩:《在坎坷中前进,在变化中发展——记〈西藏文学〉的三个阶段》,中国民族文学网,2011-09-21,http://iel.cass.cn/ztpd/ddlt/wtxx/201109/t20110921_2763323.shtml.之后,“1987年第5期的《收获》杂志,推出了一期‘实验文学专号’,‘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被冠以‘实验文学’的名号集体亮相,在文坛尚属首次,标志着作为一种流派或思潮性的‘先锋小说’正式登场”③易晖:《20世纪80年代文艺思潮中的先锋小说》,《文艺评论》2017年第12期。。在此之前,“先锋”小说未获得统一的命名,其中的代表作只是零散地发表在一些看好艺术实验的期刊中。《收获》《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中国作家》《中国》这些地处京沪、由文坛名流或权威部门主持的大型文学期刊,曾在特定时期内,以其便利地辐射文化中心区的名刊效应,为各地的“先锋”作家提供了更大的平台,使他们走出边缘,逐渐为主流文坛所熟知。而这一时期的《作家》,也通过吸引名家来稿,对“先锋”小说的潮流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以20 世纪80 年代为时间限定,在1986—1989 的几年间,众多名家来稿使《作家》在期刊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作家》“鼓励创新、面向全国”的全新的办刊宗旨提高了稿源的质量、扩充了稿源的范围。在如此优势下,“先锋”小说的名家作品、评论和理论频繁地出现在各期《作家》中。
《作家》发表的“先锋”小说主要代表作有:马原的《康巴人营地》(1986年第8期)、《大师》(1987 年第3 期)、《说梦的书》《凉爽的错觉》(1988 年第3 期),苏童的《岔河》(1986 年第8 期)、《丧失的桂花树之歌》(1987 年第7期)、《怪客》(1988 年第5 期),余华的《爱情故事》(1989 年第6 期),黑孩的《醉寨》(1987 年4—5 期合刊号),莫言的《爱情故事》(1989 年第6期),残雪的《两个身世不明的人》(1989年第2 期),孙甘露的《附近的行星》(1989 年第9期),吕新的《楼道》(1986年第9期)、《市场街》(1987 年第9 期)、《山谷对面的房子》《那儿有一群鸟》(1989年第5期),潘军的《省略》(1989年第10 期),陈村的《爹》(1987 年第11 期)、《起子和他的五幕梦》(1989年第4期),蒋子丹的《蓝颜色》(1987 年第3 期),王蒙的《夏天的肖像》(1988年第3期),皮皮的《把她分给你一半》(1987 年第10 期),何立伟的《诗人》(1986年第7期)等。
其中,《岔河》用流畅的语言叙述了完整的船家故事,也不乏对悲剧结局的形而上的思考。《丧失的桂花树之歌》以唯美的风物景观、古老图腾的失落,传达了一种迷幻的感伤情绪。《爹》以大篇幅的“感冒”和“意外遭际”,戏说、消解爱情的浪漫。《醉寨》在安静阴森可怖的氛围中,大量运用隐匿标点的长句,寄寓了与死亡有关的现代意绪。《楼道》整体上突出生活的无聊、无奈、感伤,无所谓的叙述语调中拼贴了几段极富诗意的手稿。《市场街》由“女作家”“摆书摊的男青年”“大哥”各自的“我”视角自述,总是穿插变换叙事聚焦点,制造叙事迷宫的效果。《山谷对面的房子》写儿童的感觉、印象,深蕴关于“命运”“死亡”“偶然”与“必然”的哲理。《那儿有一群鸟》,在联想和回忆中穿插了神秘人的反常生活。《大师》各节小标题和个别段落不时制造间隔效果,有意打破关于青年画家的故事的完整性。《说梦的书》涉及关于梦魇的历史隐喻。《凉爽的错觉》颇似游记的“实录”,直接提示写作的虚构性。《蓝颜色》写溺水而亡的“我”自述自己于死后目睹尘世间的所见所想。《夏天的肖像》中,琐碎的回忆、纷乱的情绪及大段的口语化的自由间接引语,散漫地冷静旁观年轻母亲曼然在海边休养期间的日常所见、所思。在1989 年第6 期《作家》刊载的“同题短篇小说专号”中,17 位作家提供了名为《爱情故事》的不同版本的作品。 其中,余华外聚焦的回忆和内聚焦于“我”对婚姻现状的自述,揭穿了爱情的虚伪;莫言以感觉叙事对视觉、知觉的精到表现,写出20 世纪70 年代末少年对女知青朦胧的爱。《诗人》《把她分给你一半》《附近的行星》都采用元叙事,对文学创作中本来严肃的作家身份、创作过程及作品进行了解构。《两个身世不明的人》写身世诡异、行为离奇的朋友之间的关系,给人“他人即地狱”般的阅读观感。《省略》构筑了马原一样的连环套故事结构,在小说中叙述如何制造小说,又嵌入作家本人部分真实的信息,大量拼贴日记与梦呓,又置入类似寓言的“狂人”被治愈的故事,营造了亦真亦幻的阅读印象。
“先锋”小说能够崛起为一种文学潮流,力作和理论堪称“一体之两面”,是不可或缺的两个基础。因为在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成规主导下,以新异的创作观、创作手法及解读方式为特点的“先锋”小说,在进入文学接受领域时难免遭遇阻力,于是,对解读和创作起指导作用的新潮理论和方法就应运而生。由此,在“先锋”小说的潮流中,“新潮”理论和“新潮”批评家具有不亚于作家作品的重要地位。《作家》在推动先锋小说潮流的具体策略上,也重视理论和批评。
《作家》刊载的对“先锋”小说的评论文章有:曾镇南的《读〈醉寨〉》(1987年第4—5期合刊号)、《读王蒙的〈铃的闪〉〈致“爱丽丝”〉〈来劲〉》(1987 年第10 期),费振钟、王干的《走向哲学的深邃意境——小说的时空意识》(1987年第4—5期合刊号),陈思和的《声色犬马,皆有境界——莫言小说艺术三题》(1987 年第8期),程德培的《逃亡者苏童的岁月——评苏童的小说》(1988年第3期),雷达的《〈危楼记事〉的批判精神和文体价值》(1988年第3期)等。
《作家》发表的“新潮”理论文章有:纪众的《非性格小说与非性格人物》(1985 年第10期),程德培的《完整性的破裂——当代小说形态的新变》(1986年第7期)、《叙述语言的功能及局限》(1987年第3期)、《读的现实——关于阅读的能动作用》(1987年第10期),吴亮的《期待与回音——“先锋”小说的一个注解》(1989 年第9 期),南帆的《文学:规范与反规范》(1990 年第5 期),章明的《小说的成功:超越单一的审美层次》(1986年第8期)等。这些评论文章,从正面的价值意义角度对各“先锋”小说的审美特征进行了评述。而“新潮”理论,或结合“新时期”以来文学风格流变,或以新的方法论如符号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等,对“先锋”小说出现的原因、意义及如何应对“先锋”小说带来的审美变革,作了不同侧重的界说。
文学界、时代环境和文学期刊的媒介行为的合力,助力“先锋”小说从起步艰难到发展成一种较有声势的文学潮流。精英圈子内的理论吁求为其生长开辟了空间,在1982 年高行健、王蒙、李陀、刘心武关于现代派的讨论中,以“中国需要现代派”的结论首次开启了“先锋”小说合法化的道路,而1985年、1986年的“理论方法热”提供了大量可行的阐释依据和充足的理论资源,奠定了言说“先锋”、言说“现代”的底气,激起精英圈子内对“先锋”小说的热情。随着文学实验呈规模化的发展趋势,理论界对“先锋”小说批评的声音也逐渐增多,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以“伪现代派”为名的责难,“认为先锋小说的现代情绪在中国没有现实的对应物,基本是亦步亦趋对先锋文学形式的模仿,但后来在《北京文学》组织的更集中的讨论中,黄子平、李陀等评论家对‘伪现代派’概念进行了否定,以‘创作为体、中西并用的改革精神’为由为‘现代派’声援,本次讨论以几乎全面支持‘现代派’而结束”①刘小新:《伪现代派》,见南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133页。。可见,“先锋”小说在精英圈子内的认可程度是颇高的。同时,“刘再复《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开启的‘文学/政治’的二元对立观念方法,及后来鲁枢元呼吁‘向内转’以摆脱机械化的创作规范,都为“先锋”小说反叛现实主义叙事成规提供了理论支援”①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51页。。
“先锋”小说得以蔚然成风,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期刊策略和文学传播中的名家效应。《作家》能够征得名家稿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刊。《作家》早在1983年下半年就进行了改刊,1983 年第7 期将原来的《长春》更名为《作家》。改刊后的《作家》“看重受众基础中的青年群体,办刊宗旨明确为‘时代感’,稿源的特点表现为庞大的作者阵容”②《长春》编者:《本刊更名致读者》,《长春》1983年第6期。。在20 世纪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伴随着“文学热”的出现,文学刊物大量涌现,《作家》有感于开放的思想文化环境,目睹文学探索创新成为大势所趋的现象,“越来越感到我们唯恐有所闪失惹出麻烦的心态和心理与整个时代精神的不协调,多了点文学杂志编辑的职业自觉,主动克服趋同心理,增强竞争意识,做出走自己的路的选择”③《作家》记者:《编刊物也要树立主体意识》,《作家》1986年第12期。。而且,“改刊更名,不再迁就那种‘近水楼台先得月’式发表的功利的地方性”④张健、宋静思:《好期刊要成为作家的真朋友——对谈〈作家〉主编宗仁发》,《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日。。改刊之前的《作家》延续的是“十七年”时期的期刊风貌,以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四个大板块(偶尔有社论、评论员文章或对文联、作协工作及会议的报道置于头题,成为一个独立板块)分割整本刊物的版面。在“十七年”时期,“为便于政府的统一监督和管理,办刊有着‘国家级——省级——地市级’这样的严格的等级结构,各省的省级文学期刊都以《人民文学》为办刊的样板,各省刊物之间是‘兄弟’的关系,不存在竞争”⑤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4页。,这就难免千刊一面。同时,省级文学期刊负有发展本省文学的主要使命,“面向省外”并不是办刊工作的重点。改刊后的《作家》不以“地方性”为由偏袒本省作品,而以“艺术性”“创新性”为标准,看重的是稿件质量。一向重视艺术探索的《作家》,对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的“先锋”小说自然更为赏识。与此同时,《作家》在1980 年代初期对宗璞等“现代派”的推重、1980 年代中期将本省青年作家的实验之作推向省外等对“先锋”小说潮流的铺路行为,使其获得了一定的象征资本,成为其能够吸引名家来稿的有利因素。改刊建立了《作家》与作家的良性互动关系。“推举先锋”的特色化办刊风格,使《作家》乐于以版面支持“先锋”小说的潮流化发展,而名家来稿则提升了《作家》在期刊格局中的位置,使《作家》突破了地缘的劣势,逐步成为有一定名气的刊物。总之,改刊为《作家》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推动了“先锋”小说的潮流化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