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刘
2020-03-04向思源
向思源
当7点的闹钟响起的时候,老刘睁开了眼睛。老刘7点前就醒了,醒得很早,但闭着眼睛。老刘睁开眼睛前是闭着眼睛的,老刘在等7点的闹钟响。老刘睁开眼睛后,伸手拿起床头的卡通闹钟,按了上面那个关闭闹钟的大按钮。闹钟是迪士尼人物米妮,孙女小学时用的闹钟。现在孙女读大学了,孙女已经用不到这个旧闹钟了。过去每回回家看见这个旧闹钟,孙女都嚷嚷着要再买一个,现在每回回家看见这个旧闹钟,孙女都劝老刘用老年智能机上的闹钟。老刘不愿听从孙女,孙女让他换成智能机上的闹钟。叫醒老刘的闹钟被老刘拿在手里,除了旧的掉漆,老刘拿在手里的米妮闹钟和过去一样好用。老刘刚刚睁开的眼睛看着手里的闹钟。7点的闹钟响之前,老刘的眼睛是闭着的。
像通常一样,老刘7起床后去洗漱,刷牙先刷门牙,然后左上大牙,左下大牙,右上大牙,右下大牙,吐泡沫,漱口。一般来说,那个漱口杯可以吐出五口水,今天老刘漱了四次,杯里就没水了。老刘的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下意识地又接了一点水,漱满五次。这个漱口杯是粉红色的,老伴活着的时候,老刘和老伴共用这个杯子。老伴去世后,老刘一个人用这个杯子,每天接满一杯水,刚好够漱口五次。老刘漱口五次,嘴里就漱干净了。
老刘爱干净,所以他的衣服也像老刘一样干净。老刘蹒跚着从洗漱间走向卧室,从枕头下面拿出一团纸,厚厚一卷纸,像上个世纪老农民家过年时,自己家蒸的馒头一样,厚实,大个。那卷纸比他一个拳头都大,老刘把它从枕头底下拿了出来,再把枕头抚平。剥卷心菜似的,一层又一层,老刘不紧不慢地剥开厚厚的一卷纸。厚厚的一卷纸被老刘剥开,里面是一把生锈的钥匙。老刘把纸垂直平放到床沿,去开了床边的柜子。开锁时需要手向下发力,使劲一按,才能开锁。老刘力不比当年,锁也锈迹斑斑,但是几十年都这样过来了,现在他也懒得吭声让别人来帮忙。从柜子里拿出点钱,老刘把柜子推上,挂上锁,把锁按进去,钥匙拔下来。老刘拔下了钥匙后自然是找那卷纸。那卷纸乖乖地躺在那里,在等老刘。厚厚的纸等着老刘,从白色等成黑色。老刘黝黑的手掌,包好柜子的钥匙。老刘披上了大衣,迎着晨曦凉风出门买菜。
老刘买菜,只要王婶家的一斤豆腐,老张家的两斤里脊,还有一把新鲜的小菠菜。老刘和儿子儿媳住,服侍走了大孙女,又将迎来老二。“孙女爱吃小菠菜。”他就记着这个。不论春天还是冬天,他只知道要买小菠菜。什么萝卜冬瓜紫薯下来了,他都置若罔闻。那个春天他上集市买菜,挨家挨户瞪着看,怎么没有小菠菜?要不是媳妇抱怨总是这几个菜,他就不知道晚饭还可以吃玉米。“明明是你们要吃的这三个菜。”他会在心里嘟囔一句。老刘在心里嘟囔一句,每月一次。
王婶家的豆腐孙女最不喜欢,这个老刘知道。老刘明明知道孙女不爱吃王婶家的豆腐,又干又硬,但老刘还是一步一崴地走到王婶卖豆腐的摊位前,从干瘪起皮的老嘴里硬巴巴地吐出一句话,要了一斤豆腐。老刘的话干巴巴地掉出嘴里,王婶报之以一个理解的微笑。老刘心满意足地走了。
回家之后是一条讨人厌的老狗上来迎接了他,一条跟了他10年的老狗。老狗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调皮过,挨了打,老了后很稳重成熟,任劳任怨,但老刘讨厌老狗,正如讨厌当年那个调皮的小狗一样。皮东西!他说。
老狗恹恹地甩甩尾巴,知趣地跑到一边去了。老狗其实知道自己走上来会被老刘斥责,但是惯例如此,老狗必须迎上来接老刘。老狗不会因为老刘的斥责而伤心,老刘骂老狗,不过是一个惯例。老狗和往日一样,甩甩尾巴继续回去睡。
老刘脑子里还要再想一会王婶,不是因为有什么别的意思,而是没别的可想了,老刘每天生活如此,上一秒就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按照惯例,这个时候是该想好心的王婶的时候了。清早的总要找一点事情干,老刘没什么好想的,不如想想王婶。王婶爱笑,递给老刘豆腐的时候,左边的肉脸上印着淡淡的酒窝,她像快要吹扎的气球,硬生生拉直了满脸的皱纹。
老刘想着王婶,也说不上来是什么感情。死了老伴,儿女少见,年近七旬,也许是老伴生前也胖也爱笑?亦或许是王婶性情温和唤醒他对昔日家庭温暖的回忆?老刘懒得费脑子思考,他只是单纯在这个闲暇时刻想一会王婶的微笑,然后搬个小凳子,到院子里择择菜。老狗又懒洋洋地从窝里走出来,但不会离太近,就趴在老刘和老窝之间的水泥地上。这个时间点老狗很清楚,那片水泥地正好有阳光。院前有一颗大石榴树,几乎遮住了院子里所有的晨光,老刘知道哪里有阳光,老狗也知道哪里有阳光。老刘和老狗,一人一片光。
老刘择完菜,接下来去洗菜,一手拿着一小筐择好的菠菜,一手拿着尚存余温的椅子,一摇一摆的崴着坡脚,用拿着小椅子的手磕磕绊绊打开门,椅子脚磕在门上,“当”一声,砸出一个积年累月的坑。老狗一动也不动,老狗知道,老刘一会还要回来。老刘回来时,拿着扫把撮箕篓,扫扫地上择下来的菜叶,又照例把院子打扫一遍。老刘眼里容不下沙子,老刘的院子里没有一粒沙子。
切好里脊和豆腐,准备好油锅和作料,把被子抱出去晒着,然后老刘看一眼墙上的表,才10点半。老刘手上有块表,但是每回看表要翻起衣袖,老刘就图方便抬头看墙上的表。老刘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带上手表,因为几十年前他有块表,天天带,所以几十年后老刘起床戴表,还是以前那块表。老刘回到房间拿起收音机,听了一会广告。老刘不敢调频道,上次调频道出现吱吱声,吓坏了老刘,媳妇紧皱的眉头和娴熟的手,是老刘的噩梦,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站在老师办公室一样,满脸羞愧不安,手不知往哪放。
老刘听会广告就好了,他头晕,听不了太久。十年前老刘喜欢易经野史之类的东西,常常看了几本书就出去和小区里的老头老嫲子谈天说地,器宇轩昂。老刘从来不回家说这些,孙女会无情的打脸,告诉他他连最基本史实都不懂。老刘不敢说话,老刘一辈子要面子。老朋友纷纷去世,老伴也死了。老刘听听广告就好,然后嫌耳鸣头晕,就关了。
坐一会就好,什么也不想,或者想想耳鸣头晕这件事,想想近来听到的广告又推荐了什么药方,想想自己还有什么毛病,还需要哪些治疗,一会儿找个机会一起告诉儿子儿媳。不不,他不敢告诉儿子,儿子忙,一听这种事就会冲他发火,说你懂什么,闲着发急去信那些垃圾广告。他更不敢告诉儿媳,媳妇都是外人。更何况他的儿媳是个干练的初中老师,经常吵他,教育他要长点头脑,少听广告少找事。
老刘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打开收音机都会听到广告,也许那个时间点就只有广告,也许那个频道就是播广告的。老刘知道儿子儿媳孝顺,因为信赖才把他从乡下接到城里一起住。老刘的儿子儿媳很孝顺,老刘也在庆幸这点。老刘做饭扫地就行了。老刘衣食无忧。老刘很庆幸地舒了口气。但不一会儿老刘又想起自己百病缠身的事,心头又不舒服起来。
还记得十年前,老刘在门口散步时捡到一份健康时报的报纸,上面诉说了患糖尿病、心脏病、冠心病、高血压等一百多种病的前期症状,老刘细细一看,一一对应,惊觉自己竟然全部都有!就连他闻所未闻的什么神经性结膜炎都出现在他的世界里,吓得老刘从此郁郁寡欢。有一回终于壮起胆子告诉儿子儿媳,却被他俩齐声怒斥,并告诉他往后别看这些没用的东西,早睡早起就行了。老刘执拗地指着报纸上的字,脸红脖子粗。儿子气得上前要夺去报纸,被儿媳拦住。老刘的报纸上就是这么写的,老刘知道要坚信自己,老刘相信报纸,老刘知道自己没错——有错怎么会出现在报纸上!这可是一份报纸啊!老刘的儿子儿媳根本不理他。老刘把上面的字铭记在心,生怕哪一天报纸丢了找不回病状。老刘自知自己一天比一天病重,老刘消极怠工。
等到11点半的时候,老刘就从板凳上站起来,“哎呦”两声,他从报纸上知道自己有腰病,他腿疼,还有点关节炎,牙疼,还神经衰弱。他还没到11点半就在那里等候了,盯着墙上的表从11点走到11半。老刘等到11点半,站起身,去做饭。儿子儿媳12点下班,过去孙女在家的时候,12点下课。11点半开始炒菜做饭,时间很准的,老刘知道。
孙女以前在家的时候要等孙女、儿子和儿媳一起回来才吃饭;孙女上大学走了后,午饭要等儿子儿媳回来才开饭。孙女以前在家的时候会谈论学校里的风趣故事,老刘偶尔插两嘴,儿媳会很不高兴地打断老刘“腐朽封建”的看法或评价,儿子也怪他多嘴,老刘于是不敢吱声。孙女上大学走了后,儿子儿媳谈论二胎、新交通法和十九大会议精神,老刘不懂也不敢多问,更没兴趣也没资格。孙女以前在家的时候,孙女、儿子和儿媳吃完饭,大腿一翘就走了,老刘洗碗擦桌很欢喜,至少还有点事儿做。孙女上大学走了后,儿子儿媳吃完饭,大腿一翘就走了,老刘洗碗擦桌很欢喜,至少还有点儿价值。
老刘望望天,不知不觉春天又飘回到身边。
这天老刘出门买豆腐,路上到点儿该想王婶了,谁知刚从王婶的发梢想到弯弯的嘴,只听一声“哎呦”的呻吟,打断了老刘的思绪。老刘有点恍惚有点迷,几十年了,从没人在这个时间点打断他的思绪。他就像被石块敲中脑袋的木头,不疼,但至少有点震动。脚步没停,他试图继续把如打碎的水中月般的,王婶的影像找回脑海,他提着豆腐、里脊和小菠菜,闷着头往前走。
“哎呦!”
老刘彻底愣住了,定睛只见脚前几步处歪倒着一个老太太,约摸着也是个七旬的光景,她顶着半灰白的头发,瘦却不显单薄,脸色微白,可以看出身子骨还算健朗。老刘打量着这个从天而降的老太太,歪斜着身子,被压在自行车下面,捂着一条腿呻吟。表情略有些难看。期初见她时,老刘还没意识到这份宿命。
“哎呀呀,帮我一把哟!”老太太冲老刘呼救。
老刘很生硬地走上去,却不知道豆腐、里脊和小菠菜该放在哪。地上吧,太脏;拿着吧,又腾不出手帮别人。最后他尴尬僵硬地提着袋子,用两个拳头扶起了自行车,又撅着屁股用拳头称扶起了老太太。老太太的连声道谢他没听见,恍惚间,老刘又回到了19岁那年。19岁的老刘雄姿英发,考取中专,直接晋级村支书干部,也是全村唯一琴棋书画样样拿得出手的少年才子,多少姑娘朝思暮想,多少媒人踏破门槛。那年19岁的老刘爱上一个长发姑娘,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依恋在年轻刘的胸口。他们初识的那个午后,老刘就是这样笨手笨脚地扶起摔倒的心上人的。此时的老刘也笨手笨脚,不过是因为太久没有过这样超出惯例轨迹的生活了。那电光石火的一刻,老刘像如梦初醒了一般,但很快烟花冷下,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老太太眼里带泪,乍一看,水灵灵的宛如十多岁的少女。老刘在老太太的恳求下送她回家。一路上老太太叽叽喳喳说个没完,活像一个几岁大的孩子,天真,活泼,可爱动人。老刘愣住了,呆呆地看着她。老刘觉得今天活得像梦一样,又或者说,今天活了过来,以前的所有相同的日子活得像梦一样。老刘现在哪也不疼了,腰也不酸了,腿也不崴了,过去广播上一一对症的病全都烟消云散。老刘看看老太太。老太太看看老刘。
很快,他们成为了朋友,在年轻人眼里这就是男闺蜜和女兄弟情。老太太爱说话,喜欢笑,一笑起来咯咯哒哒的,像个下蛋的老母鸡——老刘这辈子见过的最可爱的下蛋的母鸡。老刘有时也会被逗乐了,但他好久没笑了,有点生疏,狰狞地咧咧嘴。老太太叽叽喳喳,老刘气鼓鼓地让老太太消停会儿,但语气里听不出责怪。老太太有些黏人有些多儿事,东扯西扯些什么东家女儿上了学、西家鹦鹉没了舌头之类的闲话。老刘一开始不理她,只静静听着,进而开始学着笑,挣扎的笑,但越笑越笑得像真的一样。渐渐地,老刘学会了笑。时间就这么一点一滴的地流逝着,早晨清爽的阳光和暖洋洋的午后。
偶尔雨天或者下雪,他们会在家里打电话联系。没什么年轻人你侬我侬的情话,也没什么卿卿我我的言辞,有的只不过细心体贴问候,告诉对方天冷该加衣服了。从此老刘的世界里开始出现了家门口的月桂树,黄昏时的醉霞,小鸟的歌声和树梢的风,小草是翠意欲滴的,游鱼是活泼灵动的。
在老太太的强烈推荐下,他还开始出门钓钓鱼、下下棋,偶尔陪着老太太散散步。老太太说,她儿女很少在身边,老太太说,她自己可以给自己买菜洗衣做饭,老太太还说,她老伴去世很久了。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一个想法在老刘心底扎根,从骨子开出花来。抬头看天,那遥远的星辰,寄托着一颗可爱的灵魂,和一枚燃烧的心愿。
也就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中午,老刘做好了饭,等儿子儿媳回来。儿子说着地板上灰多,米饭没煮熟,儿媳讲着被子没晒,客厅很乱的言辞。老刘一句没听进脑子里去,神情惘然,带着深情,以及对未知的恐惧。嘴唇蠕动了两下,却没发出声音。儿媳恍惚间提到了什么去医院和B超,他也左耳进右耳出,确切地说,老刘只剩下一个臭皮囊瘫在这里。儿媳扭头走了,儿子推开饭碗也随之离去。老刘懵懵的,不知发生了什么,但心情很好,他想着早上的时光,唇边绽开了朵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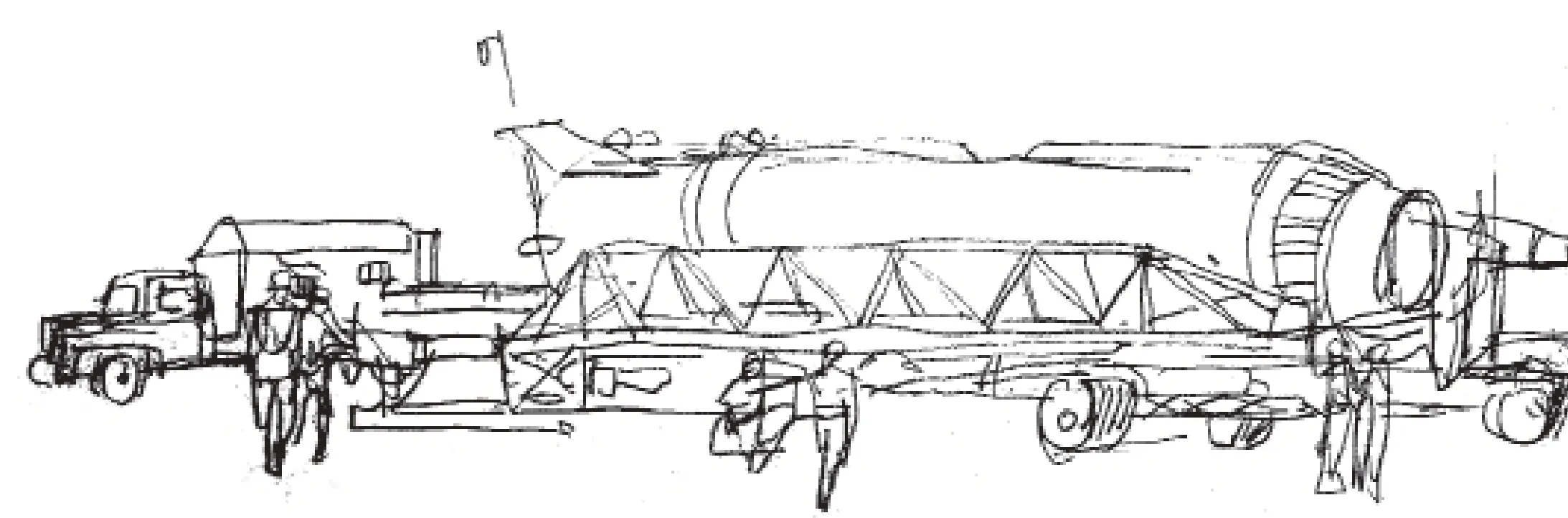
终于,几天后的一个下午,老刘跟儿子儿媳宣布了自己要成婚的消息。儿子一口茶喷了出来,儿媳被菠菜噎住,叶片瘫在嗓子口,叶茎上的丝儿却挂在大牙上。和那条街的老太太,老刘说。儿子看了一眼儿媳,儿媳也看了一眼儿子,谁也没说一句话。老刘很紧张,怕他们不同意,但是转念一想反正我自己有退休金,微薄但至少够维持生计。老刘这话本来没打算说,但是在没人说话气氛太尴尬,老刘干瘪的嘴唇怯怯地哼出几个字,又赶紧回想自己说过的每一个用词,生怕说错了什么又会挨骂。
儿子儿媳说他们要先商量商量,又给老刘布置了多到做不完的事情后,抽身进屋。老刘像做错事的孩子,默默地低头垂泪,呆坐在那里,等两人离开后才默默起身收捡残羹,喂了老狗,洗刷碗筷,转身回房。
儿子倒是看得开:“我觉得行,他老来无伴,也是寂寞。”
儿媳脸色一黑,像蒙上了一片黑纱:“你个蠢猪头,咱们马上就有二胎了,到时候老爷子有了新欢,哪还有闲工夫照顾孩子?”
儿子一摊手,不以为然:“有何不可?多一个老人多一份照顾……”
儿媳一挥手打断了他,马脸一样扯得老长:“你也不看看邻家小王的儿子,自从小王的爹续了弦,他家娃被门磕肿了脑门他也不知道,孩子拉肚子也来不及及时送到诊所看病,小王夫妇回家后饭还没开始做!都不知道心神被谁分走了。”
这时儿子才一拍脑门:“对啊,他们还捣鼓上什么‘老年大学’,装得像对儿正儿八经的学生似的,听说有什么听书课程和集体散步时间。”
“那你可不!到时候谁来管我们孩子?现在请保姆多贵啊,费钱还不安全……”
小两口叽叽喳喳,从中午讨论到深夜,在老刘还浑然不觉之中,把其幸福扼杀在摇篮里。
“这还不都是为了他好!”儿媳理直气壮道,“保不定那老太太是看中了我们家什么呢!”
“对对对,而且她什么样的人还不知道,万一是个暴躁婆子,咱们以后还咋过日子呢?”儿子也下定了主意。
老刘和老太太在同一个城市的不同窗口同一时间抬起头,看见了同一片夕阳下晃动着的不同的树梢,却没听见风中的叹息。
从那以后,老刘和老太太只靠打电话联系,双方儿女都不同意,他们就只靠打电话联系。
“今天可好啊?”
“明天有雨,去买菜小心点呦!”
“冬至啦,吃上饺子了吗?”
“清明也要开开心心的,别哭坏了身子。”
……
但是不久,儿媳又跟儿子吹枕边风,说什么电话费也是钱,再说这样联系下去,不照样是没空照顾以后的小婴儿吗?儿子点点头觉得说得在理。自此,老刘再也没接过电话。偶尔铃声响起,他跑去看看来电显示,眼泪吧嗒吧嗒流,直等到铃声落下才开动沉重的步伐,回到自己的小屋里独自垂泪,他一遍一遍安慰自己,告诉自己照顾未来的孙子才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在多少个寂寞的夜晚舔舐自己的伤口。不接电话的老刘只看来电显示,看着来电显示,心里想着打电话的人。老刘看着来电显示,就好像接了电话一样,脑海里是老太太聒噪的叨叨和她的笑脸。老刘不接电话只看来电显示。老刘家的电话渐渐很少响起。老刘渐渐很少再有机会去看来电显示。
……
老刘中午做好饭,正好12点半。老刘等儿子儿媳一起吃饭。老刘的儿子儿媳吃完饭,大腿一翘就走了。老刘等他们走后,一个人收拾碗筷,喂了老狗,蹒跚回屋。老刘回屋后照例坐在凳子上听一会儿广告,对应对应症状,想想自己的病,揉揉酸痛的腰,摸摸嶙峋的臂膀,他感觉自己是腰间盘突出。颈椎很疼,腿也不好使唤,走路一崴一崴的。牙疼,用冷酸灵也没用,吃消炎药也止不住,想拔牙,儿子又吵他。老刘忍着痛,呻吟着。耳里广告声吵吵嚷嚷,他也不关上,因为平常也就一直开着听广播。
等到下午2点半,他看了一眼表,知道自己听厌了,关了收音机,开始想王婶。王婶卖的豆腐只有老刘买,王婶的豆腐很干不好吃,王婶爱笑,笑起来肉乎乎的左脸上有一个酒窝,满脸的皱纹被硬生生拉直。老刘喜欢她笑,也只有王婶冲他笑。
老刘搬个小凳子,到院子里晒晒太阳。老狗懒洋洋地从窝里走出来,离得不算太近,它就趴在老刘和老窝之间的水泥地上。老狗很清楚这个时间点哪里有阳光。院前有一颗大石榴树,几乎遮住了院子里所有的午后暖阳,但老刘知道哪里有阳光,老狗也知道哪里有阳光。老刘和老狗,一人一片光。
直到下午4点,老刘照例走出房间,拿起扫把扫扫客厅,打湿抹布抹抹桌子,把晚饭的米淘洗好,清理一下院子的落叶和灰尘,将老狗的饭盆摆正,抱回晒好的被子和晾干的衣物。
老刘走进院子扫落叶,那条讨人厌的老狗走上来迎接了他,一条跟了他10年的老狗。老狗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调皮过,挨了打,老了后很稳重成熟,任劳任怨,但老刘讨厌老狗,正如讨厌当年那个调皮的小狗。老狗恹恹地甩甩尾巴,列到一边去。惯例如此。
老刘出现,老狗上前,老刘骂老狗,老狗转身回去。
老刘不理老狗,老刘只看着手里的扫把。老狗也不理老刘,老狗只看着自己的狗爪。老刘的扫把扫啊扫,扫尽了院子里的落叶和尘埃。老刘眼里容不下沙子,所以院子里没有沙子。老狗照例转身回窝,趴下看着蹒跚的老刘,扫把一挥一挥,扫走秋天,扫来春天,然后再扫走秋天,扫来春天。老刘把扫把放好,拍了拍手上的灰。老狗下意识地抬了抬头。老刘看看老狗,老狗看看老刘。老刘扭头进屋,老狗回身进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