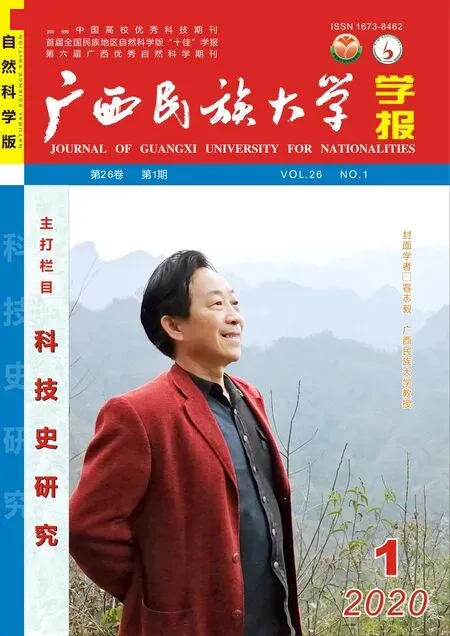李约瑟与竺可桢往来书信(1950-1951)*
2020-03-03王淼,赵静
王 淼,赵 静
(1.浙江大学 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8;2.李约瑟研究所,英国 剑桥CB3 9AF)
1943年2月-1946年3月,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1900-1995)受英国文化委员会委派赴中国担任战时情报和宣传工作的专家.[1]在中国期间,他创建中英科学合作馆并担任馆长,足迹遍历中国抗战大后方10个省,访问300余个文化教育科学机构,接触到上千位学术界知名人士.[2]在大力推进中英科学家和科研人员的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他也在积极为酝酿中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以下简称“SCC”)写作计划做着前期准备工作.1944年4月及同年10月,李约瑟两次到访因抗战而西迁贵州办学的浙江大学,与时任校长竺可桢建立并保持长达近30年的深厚友谊.
对于竺可桢和李约瑟的学术交往历史,利用竺可桢日记以及两人间的书信等史料,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3-6]然而,学界关于1950-1951年期间竺可桢和李约瑟的学术交往活动提及较少,究其原因,在于该时间段竺可桢日记对此记载较为简单,而往来书信则知之者甚少.2017年10月,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向浙江大学捐赠了一批与浙江大学以及竺可桢相关的珍贵史料扫描件,[7]其中就包括1950-1951年竺可桢和李约瑟的四封书信.它们承载着两人鲜为人知的学术交往故事,对于今人了解这段经历及当时学人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态度和锲而不舍的学术追求精神不无裨益.这四封书信均为英文,目前学界少有论及.①在这四通往来函件中,1951年9月李约瑟致竺可桢信函的部分内容及竺可桢于次月的回信已收入《竺可桢全集》第24卷(参见[7]),而1950年10月李约瑟致竺可桢的信函及1951年2月竺可桢的复函原文则尚未见到记载.[8]文章将四通书信全文予以翻译,并对其背景和内容做简要分析及考释.
1 李约瑟1950年10月致信竺可桢的背景及其内容
李约瑟于1943年2月抵达昆明,开启了他在中国抗战大后方开展中英科学交流与合作事业的旅程.事实上,竺可桢在李约瑟来华前的三四个月,已经通过报纸及教育部函件等渠道获知相关信息,包括拟到浙江大学参观考察并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安排计划.1943年3月起,竺可桢曾多次与李约瑟在重庆共同参加“中央研究院”有关学术活动.不过,对于李约瑟来说,“我第一次认识竺博士是在贵州,即当时浙江大学的疏散地.在那里,我开始熟悉他在天文学史方面所做的很有价值的工作”.[9]11从此,两人在促进战时浙江大学国际科学交流与合作以及支持李约瑟SCC编写工作等方面,保持密切交流和沟通,并且建立了深厚友谊.
1948年初,竺可桢促成浙江大学赠送李约瑟编写SCC所需的一批书籍,即为两人深厚学术情谊的典型例证.李约瑟于1946年3月离开中国赴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1948年4月从巴黎返回剑桥大学,不久就收到了这批图书.1954年,在正式出版的SCC全书第一卷[10]“志谢”中,李约瑟称竺可桢为“最慷慨的赞助人”,他写道:“我们最慷慨的赞助人是著名的气象学家、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博士.在我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他劝说许多朋友检寻书籍副本,因此在我回到剑桥后不久,整箱整箱的书就运到了,其中包括一部《古今图书集成》(1726年)”.[9]12那么,李约瑟在收到这批书籍以后,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方面取得了怎样的进展?这批图书对李约瑟写作SCC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应当是竺可桢教授当时心中挂念的问题.从竺可桢日记来看,1948年初他在杭州将这批图书交由迁至上海办公的英国文化委员会转送李约瑟之后,直到1949年1月收到李约瑟从英国寄来《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11]竺可桢于2月复函“谢其寄渠夫妇所著Science Outpost一书”,[12]但均未获知关于那批捐赠图书的跟进信息.从目前资料来看,直到李约瑟于1950年10月26日写给竺可桢的书信中才谈及此事.
这封信的全文如下:[13]
亲爱的竺教授:
正在我国访问的中国友好代表团,特别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涂长望,为我们架设了令人感激的桥梁.借此机会给您写信,主要想谈谈中国科学史、科学思想史及技术史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您知道我在二战以来一直致力于此.到现在为止,这部著作已经完成大约六成,我想恐怕不止于一卷.目前,我正在致力于天文学部分的写作.这里,我愿意附带提及,您的[二十八宿]研究工作①由于信件系打印副本,信中遗漏了“二十八宿”几个字,译文中做了补充并将其置于方括号[]之中.对我来说具有重要价值.
随函附上这部著作的目录,它列出了章节和次章节的内容.写在白纸上的那些部分已经完成(业已形成约900页的打印文件),而写在黄色纸张上的那些部分尚在准备之中.我已为所有章节准备好了大量材料.自从返回欧洲后,我将一切可利用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这本书的调研工作上.
基于同样的想法,我已经写信给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博士,请求他能够将我的这份目录译成中文,并通过某种合适的方式让更多的中国学者知晓.如果任何人有任何与本人工作相关的重印本、小册子或者手稿,我恳请他们心怀友好和善意将其寄送给我,以使我的著作尽可能完整,而不遗漏任何重要的内容.对于通过这种渠道为我提供过帮助的所有人,我将在书中致以诚挚的谢意.如果您能提供任何帮助,在中国学者中推广我的工作,我将感激之至.
我不会忘记告诉您的是,在我离开中国后,浙江大学慷慨捐赠给我的那些图书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这是一份厚礼,我们经常甚至每天都会用到它们,这一点当然会在书中提到.
我确信,您和同事将会赞同这样的看法,即创作这样一部著作是非常必要的.即便在中文著作里,尚且没有一部涵盖这个领域的作品.世界各国都应当了解中国早期文明在科学思想和技术发明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此外,由于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以我将会尽力采用将中国科学技术史置于社会-经济背景中开展研究的进路.
顺致良好祝愿.
您的忠诚的朋友
[李约瑟]②这封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收藏的信札系打印副本,函末没有李约瑟的签名.
1950年10月26日
这是目前所知新中国成立后李约瑟和竺可桢之间的第一通书信.李约瑟在信中所写的竺可桢收信地址仍然为浙江大学,由此可见,他对竺可桢从1949年4月起不再担任浙江大学校长,而自该年10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务尚无准确的认识.正如信中所言,这封信写于1950年中国友好代表团应英中友好协会(Britain-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的邀请访问英国之际.代表团成员涂长望是中国近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国气象局首任局长.[14]他这次访问英国,应邀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活动,还与李四光共同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5]他是李约瑟和竺可桢结识多年的“共同的朋友”.这次访问活动,为开启新中国成立后李约瑟与竺可桢等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交流与合作,“架设了令人感激的桥梁”.正是在这样的友好氛围中,李约瑟专门致函竺可桢以加强联系,延续多年前业已形成的深厚学术友谊.
李约瑟写这封信时,距离从巴黎返回剑桥写作SCC已历经两年多的时间,写作计划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此情形下,他在信中主要向竺可桢通报了全书的写作目的、特点、研究进路、内容框架、目录和最新进展状况.李约瑟写作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计划酝酿已久,他在这里明确表达了写作的目的在于“世界各国都应当了解中国早期文明在科学思想和技术发明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在选题特点方面,主要体现在它所具有的全面性和综合性的特色,涵盖了整个“中国科学、科学思想及技术史”,因为当时“即便在中文著作里,尚且没有一部涵盖这个领域的作品”.从研究视角和研究进路来看,一方面尽量占有和挖掘科技史料,“不遗漏任何重要的内容”;另一方面则将视野扩展至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尽力采用将中国科学技术史置于社会-经济背景中开展研究的进路”.经过两年多的集中思考与写作,李约瑟已经形成一份比较成熟的内容框架,并已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李约瑟此信的主要目的是向竺可桢通报SCC写作计划的有关情况,尽力争取获得对他的写作计划的支持,并通过竺可桢让更多的中国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解研究计划进展,以在更大范围内征询意见.
李约瑟在信中还特别提到,1948年竺可桢促成浙江大学捐赠的那批图书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价值”,“甚至每天都在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他在信中还诚挚地表达了请更多中国学者帮忙搜集中国科学技术史相关文献资料的委托,“任何人有任何与本人工作相关的重印本、小册子或者手稿”都将受到欢迎,“以使我的著作尽可能完整”.
总之,这封通信的主题是围绕SCC写作计划展开的,既包括写作方法的思考和研究工作的进展,又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史文献资料的搜集.
2 竺可桢回信的背景及内容
竺可桢何时收到李约瑟写于1950年10月26日的信函,在竺可桢日记等文献资料中没有找到明确记载.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迟至1951年2月16日竺可桢才正式复书李约瑟.
20世纪50年代初,在国家政府的支持下,中国科技史研究受到关注和重视,[16]而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和撰著SCC的想法与此一拍即合.竺可桢于1951年1月13日“与仲揆谈李约瑟寄来《中国科学文化历史》(即SCC——引者注)目录事,因此谈及中国科学史应有一委员会,常川注意其事,以备将来能成一个研究室,而同时对于各种问题,如近来《人民日报》要稿问题,可以解决”.[17]269-270由此可知,竺可桢对李约瑟的来函极为重视,专门与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原名李仲揆)讨论SCC写作框架目录.并“因此谈及”成立中国科学史委员会乃至研究室的设想,一来“常川注意其事”,即连续不断地专门开展中国科技史研究工作;二来“可以解决”“近来《人民日报》要稿问题”.在接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竺可桢召集或参加了多场中国科学史活动.比如,1月15日,“与吴有训、丁瓒、严济慈、何成均等商议,拟成立《中国科学史》编辑委员会”;[17]271月25日“下午《人民日报》发起举行中国科学史座谈会”,[17]277“讨论如何发扬宣传中国古今科学上之成就,以激励爱国精神”;[17]2782月12日“召集中国科学史座谈会,参会人员有傅种孙、叶企孙、钱临照、张子高、刘先洲、张含英、乐天宇、王重民、赵万里、向达、叶公绰、李涛、陈援庵、王天木、范文澜、郑振铎、冯家升、马衡(叔平),共十八人.陈援庵主张出《中国科学史资料丛刊》,向觉民主张图书馆以科学史为重心搜集图书,刘仙洲主张增加食品工程和陶磁(瓷)①这里“磁”系“瓷”之误.工程,叶企孙主张召开座谈会”.[17]289
在召集或参加如上所述多场中国科学史学术活动以后,竺可桢于1951年2月16日正式回函李约瑟,全文如下:[18]
亲爱的李约瑟博士:
很高兴收到您于1950年10月26日的友好来信,以及即将问世的SCC的目录.我在中国科学院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仔细阅读了您给我的目录,几乎所有人都赞同您现在编撰的著作所具有的全面性特色,并对您完成这部传世之作的进展之快而感到惊奇.
为了使这部著作更具有权威性,除了您所熟悉的数学领域李俨和钱宝琮以及天文学领域刘朝阳外,我建议您函询下列被公认为中国国内某些领域的权威学者:
中国医学史 李涛 北京大学医学院
中国建筑史 刘敦桢 南京大学即前中央大学
中国工具及机械史 [刘仙洲]①信函原稿此处遗漏了姓名,应为“刘仙洲”.李约瑟在信上用英文亲笔加注“大概是刘先洲”.清华大学
中国农学史万国鼎 北京 闲居
中国水利史张含英 北京 水利部
您的忠诚的朋友
竺可桢(签名)
1951年2月16日
从竺可桢的回信可以看出,虽然文字比较简短,但内涵却十分丰富.首先,他告知李约瑟,已提请中国科学院多位朋友和同事研读SCC全书框架目录,广泛地征询意见和建议.其次,对写作计划所具有的“全面性”特色予以充分肯定.第三,推介国内中国科技史领域多位专家学者,包括李约瑟较为熟悉者在内共计八位,他们分别是:李俨、钱宝琮、刘朝阳、李涛、刘敦桢、刘仙洲、万国鼎、张含英.这些专家的科技史研究工作涵盖了中国数学史、天文学史、医学史、建筑史、工具及机械史、农学史及水利史等领域,各有特色.通过函询这些专家学者,无疑会使SCC“更具有权威性”.从后来陆续出版的SCC各卷来看,上述多位中国科技史家的研究成果对其多有助益,而竺可桢所起到的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3 1951年9-10月往来书信及其内容
竺可桢回信四个多月后,竺可桢和李约瑟在波兰华沙(Warsaw)共同参加波兰科学会议期间得以会面.1951年6月29日,在第一届波兰会议开幕式的外国代表致辞环节,竺可桢和李约瑟分别代表中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致辞,[19]会议晚餐后李约瑟向竺可桢“辞行”.[17]386
在华沙会议会面后两月余,1951年9月9日,李约瑟致函竺可桢:②李约瑟致竺可桢函,1951年9月9日.浙江大学档案馆藏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捐赠史料,2017.
亲爱的竺博士:
不久前,我们分别代表各自国家科学院参加在华沙举行的第一届波兰科学会议,很高兴与您会面.
另外,我收到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图书管理员的收条,告知我上百包甚至更多的科学期刊已经在数月前顺利寄达北京.我们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现在,我想和您接洽一个不同的话题,就是在北京购买书籍,用于我自己在中国科学史、科学思想史和技术史的研究工作.我知道,在中国科学院,包括其他成员在内,您熟悉这项工作计划,数月前我已经将目录寄到北京.目前进展顺利,我们正在忙于物理学部分的写作.我的研究助手王铃先生已经获得利弗休姆基金(Leverhulme Foundation)的资助,使他能够留在这里直至这部著作的完成.
此外,我诚挚地感谢您,之前赠送的那些精美图书是一份厚礼,对于我们所从事的这项艰巨事业来说是无价之宝.
数月前,我从北京法国书店预订了大约250英镑的一批图书.随函寄上两份账单(一份最优先考虑,另一份则次要考虑).您从账单上可以很快看出,在我的工作中仍然需要哪类参考书目和经典文本.但是,最近不为国际所知的事,使得我对于从法国书店购书产生了疑虑.您能否告知我,他们的工作目前是否仍然在中国支持下运转,我是否应当继续向前推进?
其次,我也想询问,在获得中国政府关于这批图书的出口许可方面,是否会遇到困难?我猜想使用英国货币或其他强势货币不会遇到困难,但是,如果这家书店不能将这批图书寄给我,我自然不会急于向前推进并汇出款项.如果您能咨询合适的部门,保证我可以得到必要的出口许可,我将十分感激.
在帮助我购买这批图书方面,您做的所有工作都令人感激不尽.
我们目前正在着手撰写光学部分,其中墨家光学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时,合作者肯尼思·罗宾逊(Kenneth Robinson)先生正在致力于篇幅较大的声学部分的写作.此外,将会讲述磁罗盘的故事,还有汉代的“[司南]杓”③“司南”系引者所加.李约瑟所说的“[司南]杓”和“磁罗盘”,均为中国古代发明的磁性指向器.前者为指南针的原始形式..我希望王振铎博士安好,并期待了解他目前所从事的工作.
热切盼望不久后有另外的机会再次相见.
致以良好的祝愿.
您的忠诚的朋友
李约瑟(签名)
1951年9月9日
附言:烦请将随函所附的账单返还给我,因为在履行我国进口控制的要求时,我可能需要这些副本.
在这封信中,李约瑟再次提及1948年竺可桢促成浙江大学捐赠的“厚礼”,对于他们研究和写作SCC来说是“无价之宝”.他提到了为中国科学院寄送大量科学期刊的工作,因获知已顺利寄达北京而感到“由衷地高兴”.他传达了近期在写作SCC的新进展,已经着手进行全书物理学部分的写作,包括光学、声学、磁学等分支学科,光学部分由合作者肯尼思·罗宾逊(Kenneth Robinson)撰写.在这封信中,李约瑟还提到他在剑桥写作SCC的协助者王铃获得利弗休姆基金资助的信息,并对王振铎的近期工作动态表示关注.
当然,这封信最主要的内容是关于在北京购买写作SCC所需的一批图书资料的问题.李约瑟在信中详述拟从北京法国书店购置所需中文图书遇到时间延宕的经历,并寻求竺可桢帮助成功购买这批图书.“数月前”从北京法国书店预订的图书,长时间杳无音信,难免引发疑虑和担忧.法国书店是否正常运营,中文图书寄往海外是否会遇到出口许可的限制,这是李约瑟内心牵挂的主要问题.李约瑟之所以寻求竺可桢的帮助,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竺可桢“熟悉这项工作计划”,深知图书资料对于完成工作计划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两人结交已有十几年,一贯气息相通,互相帮助,不计得失,友谊深厚.李约瑟的正当诉求,又恰当利用长期保持友好互助的人际关系,合情合理,理应获得竺可桢的支持和帮助.
果不其然,竺可桢在10月17日即复信李约瑟,详述了解到的有关情况并告知解决购书问题的办法:①竺可桢致李约瑟函,1951年10月17日.浙江大学档案馆藏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捐赠史料,2017.《竺可桢全集》第24卷编入了这封信函.
亲爱的李约瑟博士:
1951年9月9日大函收悉,包括在法国书店订购一批中文图书的账单.法国书店在一段时间以前已经停业,我争取在北京国际书店为您罗致这批图书.我已经将您的订单与地址交给这家书店,在不久的将来您应该会收到这家书店的信件.
您问询王振铎先生近况,他目前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刚刚完成一个新的张衡地动仪模型.烦请告知王铃先生,我们希望他完成目前的工作后能够加入中国科学院.
向您和夫人致以良好的祝愿.
您的忠诚的朋友
竺可桢(签名)
1951年10月17日
附:法国书店账单.
在这封回信中,竺可桢对李约瑟来函中提到的事项给予了积极的回应,表达了如下三层意思:其一,竺可桢已经了解邮购图书遭遇时间延宕的相关情况并做出妥善安排.由于北京法国书店已经停业,所以竺可桢将李约瑟的图书清单交给了北京国际书店.其二,竺可桢请李约瑟转达希望王铃完成在英工作后回国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信息.此后,竺可桢又多次发出邀请,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国科学院正在积极开展科学史研究工作,希望他通过协助李约瑟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进而提高研究水平,然后回国工作成为科技史研究的骨干.[14]其三,他还向李约瑟介绍了王振铎的近期研究动态,“刚刚完成一个新的张衡地动仪模型”.顺便提及,第二年,李约瑟在离开中国六年以后来华访问,[4]166-190在北京度过了那一年夏季的大部分时日,其间得以与王振铎会面,“共同讨论体现了他的结论的精美模型”.[8]11
4 结语
从上述对竺可桢和李约瑟的四通书信的解读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在20世纪40年代建立起来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在1950-1951年继续得以保持和发展.在这一时期的交往过程中,两人聚焦的共同目标是推进中国科学技术史事业的发展.一方面,1948-1951年恰逢李约瑟进行SCC选题策划的重要阶段,[12]无论在文献资料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亟须征询中国科学家和科学史家的意见,了解和把握最新进展和研究动态,以增进研究著作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特别提倡爱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包括竺可桢在内的中国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推进中国科技史研究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事实表明,两人在这段时间内的通信,无论对于李约瑟写作SCC,还是对于竺可桢推进科学史在中国走上建制化之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回顾这一时期两人学术交往的点点滴滴,可以深切认识到,李约瑟和竺可桢为了共同的目标,超越个人友谊,保持密切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体现了其时学人孜孜不倦和锲而不舍的学术追求精神,足令后人肃然起敬,由衷赞叹.
致谢:2017年10月,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教授将该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收藏的与浙大和竺可桢相关史料扫描件捐赠浙江大学档案馆,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莫弗特(John Moffett)馆长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本文写作过程中,莫弗特馆长、浙江大学档案馆编研展览办公室张淑锵主任曾阅读初稿并提出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