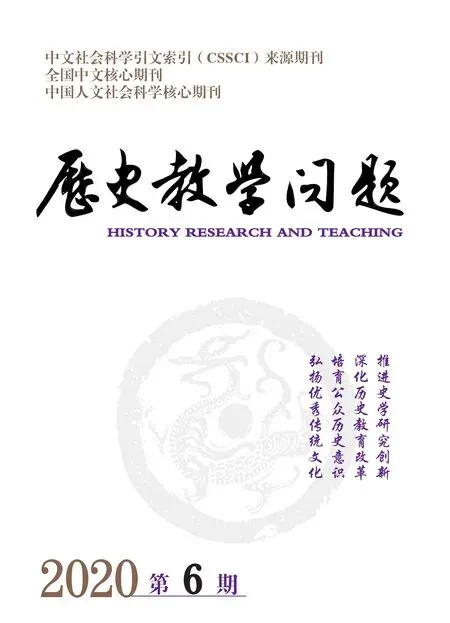论曹魏的刚烈之君曹髦
——兼辨司马昭弑君事件
2020-03-03朱子彦
朱 子 彦
司马师死后,司马昭继位,曹髦居然亲自率领殿中宿卫和奴仆数百人讨伐司马昭,若不是贾充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弑杀曹髦,司马氏苦心经营的基业几乎毁于一旦。陈寿在《三国志·魏书》中撰《三少帝纪》,三少帝分别为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陈留王曹奂。曹魏王朝至三少帝时,已经到了末世,故三少帝的事功已不为史家所重视,相关的论著颇少。但三少帝中的高贵乡公曹髦却卓尔不凡,若非他生于曹魏末世,且在司马氏的掌控之中,很可能有一番作为。虽然曹髦寿不永年,又死于非命,但他所说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却成为千古名言而留传至今。司马昭一生功业卓著是毋庸置疑的,但其弑杀魏主曹髦之举却最为世人所诟病,并留下了千古污名,然而司马昭为何要弑君?是其故意为之,还是出于无奈?自古及今,学人似乎尚未就此问题展开探讨,笔者不敏,拟就司马师废立君主,曹髦一生事功及司马昭为何弑君略谈个人管见,①史家对曹魏末世的三少帝很少措意,有关曹髦被司马昭所弑事件仅略见于三国通史类著作中,且大都均一笔带过,而未作具体分析。三少帝时代的相关人物,如述及司马师、司马昭的主要论著,有仇鹿鸣:《司马师功业论》,载《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朱子彦:《论司马昭》,载《史林》1987 年第4 期。以求正于同好。
一、司马师废立君主
如果说,高平陵事件揭开了司马代魏的序幕,那么,司马师废曹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就有力地表明了司马家族代魏的进程已加快了步伐。司马师杀李丰、张缉,废皇后张氏后,魏主曹芳眼看司马师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故他不肯束手待毙,欲作最后一搏。史称“天子以(夏侯)玄、(张)缉之诛,深不自安”,②《晋书》卷二《景帝纪》,第27 页。于是他准备夺取兵权,诛杀司马师兄弟。嘉平六年(254)秋,“姜维寇陇右。时司马文王镇许昌,征还击维,至京师”。曹芳在平乐观阅兵。中领军许允与左右亲信谋划,欲趁司马昭请辞之时将其诛杀,然后夺取司马昭所指挥的部队攻击司马师。③“臣(裴)松之案《夏侯玄传》及《魏略》,许允此年春与李丰事相连。丰既诛,即出允为镇北将军,未发,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乐浪,追杀之。允此秋不得故为领军而建此谋。”《三国志》卷四《魏书·齐王芳纪》注引《世语》及《魏氏春秋》,第129 页。诏书已经写毕,等到司马昭觐见,曹芳正在吃栗。“优人云午等唱曰:‘青头鸡,青头鸡。’青头鸡者,鸭也”。①《三国志》卷四《魏书·齐王芳纪》注引《世语》及《魏氏春秋》曰:“此秋,姜维寇陇右。时安东将军司马文王镇许昌,徵还击维,至京师,帝於平乐观以临军过。中领军许允与左右小臣谋,因文王辞,杀之,勒其众以退大将军。已书诏于前。文王入,帝方食栗,优人云午等唱曰:‘青头鸡,青头鸡。’青头鸡者,鸭也。帝惧不敢发。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谋废帝。”第128 页。“鸭”的谐音是“押”,这是提醒曹芳赶紧在诏书上画押并诛杀司马昭,但曹芳因恐惧而不敢实行。事情败露后,司马师大怒,决定废立,但废立必须得到太后的首肯,于是司马师“乃密讽魏永宁太后”。
魏永宁太后即郭太后,郭太后与司马氏家族关系密切,且有婚姻作为纽带,史称:“司马景王辅政,以女妻德。妻早亡,文王复以女继室,即京兆长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结于郭后,是以频繁为婚。”②《三国志》卷五《魏书·后妃传》注引《晋诸公赞》,第164 页。师、昭兄弟先后将己女嫁与太后从弟,才具平庸的郭德,为的就是借助郭太后的地位来控制曹芳,因此在司马师废立事件中,郭太后充当了司马师废主的工具。
嘉平六年(254)九月,司马师与朝中公卿大臣上奏郭太后,言曹芳年长不亲政、沉湎女色、废弃讲学、侮辱儒士,与优人、保林等淫乱作乐,并弹打进谏的清商令、清商丞,乃至用烧铁重伤令狐景,太后丧母时不尽礼等罪。请依霍光故事,收其玺绶,废其帝位。郭太后遂下废曹芳令:“皇帝芳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沈漫女德,日延倡优,纵其丑谑;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日亏,悖慠滋甚,不可以承天绪,奉宗庙。”于是遣曹芳“归藩于齐,以避皇位”。③《三国志》卷四《魏书·齐王芳纪》,第128 页。
从以上史料来看,曹芳被废似乎是罪有应得,且得到郭太后的支持。其实不然,郭太后虽为女流,且与司马氏关系不错,但她并非弱智,曹芳虽非其亲子,但与她已有十余年的养母子关系。更为关键的是,郭太后在宫中已有数十年,与朝政国事多有涉猎,她不可能不懂得,一旦曹芳被废,曹魏江山就将岌岌可危,她将成为魏朝的千古罪人。其实郭太后并不同意废曹芳,她曾为曹芳向司马师求情,但遭到司马师断然拒绝。郭太后在司马师武力威胁下,才被迫下令废曹芳。然而,此事涉及司马师挟持太后,废主立威、一手遮天,故陈寿不敢触碰西晋统治者十分忌讳的这道禁区。所幸鱼豢所撰《魏略》提供的史料才澄清了历史的真相,使我们知道在司马师废主事件中郭太后真实的政治态度。《三国志·齐王芳纪》注引《魏略》曰:“景王将废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与帝对坐。芝谓帝曰:‘大将军欲废陛下,立彭城王据。’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将军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备非常,但当顺旨,将复何言!’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口有所说。’芝曰:‘何可见邪?但当速取玺绶。’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玺绶著坐侧。芝出报景王,景王甚欢。”
曹芳被废,立何人为帝?司马师与郭太后发生了争执,司马师本打算拥立曹操之子彭城王曹据为帝,但郭太后认为辈份不当,且又不属于魏明帝这一支脉的后裔,故坚持要求立明帝之弟东海定王曹霖之子曹髦,④案如果立曹据,郭太后就从太后成了侄媳,是一件很尴尬的事。立曹叡之侄曹髦,她就是皇帝的伯母,仍可为太后。在郭太后的坚持下,司马师被迫接受了曹髦,于是派使者迎立曹髦到洛阳登基。《晋书·景帝纪》颇为翔实地记载了此事。司马师“与群臣议所立,帝曰:‘方今宇宙未清,二虏争衡,四海之主,惟在贤哲。彭城王据,太祖之子,以贤,则仁圣明允;以年,则皇室之长。天位至重,不得其才,不足以宁济六合。’乃与群公奏太后。太后以彭城王先帝诸父,于昭穆之序为不次,则烈祖之世永无承嗣。东海定王,明帝之弟,欲立其子高贵乡公髦。帝固争不获,乃从太后令,遣使迎高贵乡公于元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司马师所立的曹髦其实是一位非同凡响的君主。曹髦字彦士,乃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其生于正始二年(241)。正始五年被封为高贵乡公。嘉平二年(251)十二月,其父曹霖去世。嘉平三年,司马懿镇压王凌后,将曹魏宗室王公均置于邺城以便监视,曹髦亦被移置邺城。曹髦从小好学,才慧夙成,有祖父曹丕的风范。且性格刚烈,对司马氏专权极为不满。
嘉平五年(254),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后,准备立他为帝,此时他才14 岁。作为一名曹魏普通宗室成员的曹髦,当得知自己意外地被皇太后看中,即将登上九五之尊的帝位,并没有表现出欣喜若狂的姿态,而是相当地从容、淡定。史载:“公卿议迎立公(即曹髦),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馆,群臣奏请舍前殿,公以先帝旧处,避止西厢;群臣又请以法驾迎,公不听。”曹髦初入洛阳时,群臣迎拜于西掖门南,曹髦见此阵容,立即下舆回拜还礼。礼仪官说:“按礼仪,君不拜臣。”曹髦回答道:“吾目前仍然是人臣,应该回拜。”曹髦进城至皇宫止车门,就下舆步行,左右对曹髦说:“您完全有资格坐舆进皇宫。”曹髦说:“吾被皇太后征,未知所为!”遂步行进入太极东堂,拜见皇太后,“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
由此可见,曹髦虽然年幼,但胸中很有城府,也很有政治头脑。他充分汲取了西汉昌邑王刘贺只当了27 天皇帝就被霍光所废的教训。在未即位之前相当低调。他在群臣面前仍以藩臣自居,谦恭谨慎,彬彬有礼,大方而稳重,以博取朝野对他的好感。不出所料,曹髦即位之日,“百僚陪位者欣欣焉”。①《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髦纪》,第132 页,第132页,第133—134 页,第139 页。
二、志在中兴曹魏,视死如归的刚烈之君
曹髦即位之时,司马氏已经完全掌控了朝政,司马氏的党羽遍布朝堂,朝政大计都由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作主,曹髦已沦为十足的傀儡君主。面对如此的局面,曹髦并不甘心垂拱而治,任由司马氏摆布,为了挽救曹魏王朝,曹髦颇有心计地展开了一系列收拾人心的工作。他即位不久就“遣侍中持节分适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察冤枉失职者”。同时,他自己率先垂范,“减乘舆服御,后宫用度,及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②《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髦纪》,第132 页,第132页,第133—134 页,第139 页。曹髦还多次下诏,对战死的将士和饱受战火创伤的地方表示哀悼和抚慰。正元二年(255),魏雍州刺史王经被蜀将姜维击败,魏军死伤惨重。他下诏曰:“洮西之战,至取负败,将士死亡,计以千数,或没命战场,冤魂不反,或牵掣虏手,流离异域,吾深痛愍,为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农及安抚夷二护军各部大吏慰恤其门户,无差赋役一年;其力战死事者,皆如旧科,勿有所漏。”③《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髦纪》,第132 页,第132页,第133—134 页,第139 页。从史料记载来看,曹髦颁发的此类安抚性质的诏书,其数量大大超过前任君主,这其中显示的用心恐非单纯用个人喜好与否来说明,而是曹髦要让臣下知道他并非是司马氏手中的玩偶,而是实实在在的大魏皇帝。
曹髦喜好文学,擅长诗文,精通绘画,曾亲赴太学论道。讲《易》毕,复命讲《尚书》《礼记》。他经常邀请一些大臣进宫,或宴请、或纵论、或私谈,曹髦常与司马望、王沈、裴秀、钟会等大臣在太极东堂讲经宴筵并作文论,他称裴秀是“儒林丈人”,王沈是“文籍先生”,司马望和钟会也各有名号。史书记载:“帝性急,请召欲速,(裴)秀等在内职,到得及时,以(司马)望在外,特给追锋车,虎贲卒五人,每有集会,望辄奔驰而至。”④《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髦纪》注引傅暢《晋诸公赞》曰,第138 页。注引《魏氏春秋》,第132 页。曹髦与诸臣读诗书礼易,并非仅仅是求学论道,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别有一番政治上的用意,他“广延诗赋,以知得失”。并要求群臣“皆当玩习古义,修明经典,称朕意焉”。⑤《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髦纪》,第132 页,第132页,第133—134 页,第139 页。实质上他是借讲学考察臣下的心态,拉拢、争取和疏远不同的对象。
曹髦的这些举措是瞒不过一些效忠于司马氏朝臣的。侍中荀顗对司马师说:“今上践阼,权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⑥《晋书》卷三九《荀顗传》,第1150 页。中书侍郎钟会也看出曹髦并非是寻常之主。《魏氏春秋》记载了司马师与钟会的一段对话:“公(曹髦)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罢朝,景王(司马师)私曰:‘上何如主也?’钟会对曰:‘才同陈思,武类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⑦《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髦纪》注引傅暢《晋诸公赞》曰,第138 页。注引《魏氏春秋》,第132 页。钟会说曹髦“才同陈思(曹植),武类太祖(曹操)”。这个评价何其高也,而司马师说“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这显然不是由衷之言,他很可能十分后悔废曹芳后不该立曹髦为帝。于是司马师对曹髦更加严密监控,并加快了代魏的步伐。
在司马兄弟的威逼下,曹髦不得不将司马师比之于殷商名臣伊尹与辅佐周成王的周公旦。他下诏曰:“(大将军)内摧寇虐,外静奸宄,日昃忧勤,劬劳夙夜。德声光于上下,勋烈施于四方。深惟大议,首建明策,权定社稷,援立朕躬,宗庙获安,亿兆庆赖。伊挚之保乂殷邦,公旦之绥宁周室,蔑以尚焉。朕甚嘉之。夫德茂者位尊,庸大者禄厚,古今之通义也。其登位相国,增邑九千,并前四万户。进号大都督、假黄钺,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赐钱五百万,帛五千匹,以彰元勋。”⑧《晋书》卷二《景帝纪》,第29 页。此时的司马师虽然总揽朝纲,但他知道朝臣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忠于魏室,代魏时机远未成熟,于是他固辞相国,但曹髦的其余赏赐则一概受之,自此司马师“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较曹芳时威权更甚,成了名副其实的权臣。
曹髦虽无实权,但并不甘心碌碌无为,而有志于中兴曹魏。他尤其推崇中兴夏朝的少康,他在与侍中荀顗、尚书崔赞、袁亮等人评论历代帝王优劣时称:
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创业者皆优,绍继者咸劣也。汤、武、高祖虽俱受命,贤圣之分,所觉县殊。少康、殷宗中兴之美,夏启、周成守文之盛,论德较实,方诸汉祖,吾见其优,未闻其劣;顾所遇之时殊,故所名之功异耳。少康生於灭亡之后,降为诸侯之隶,崎岖逃难,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谋,卒灭过、戈,克复禹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非至德弘仁,岂济斯勋?汉祖因土崩之势,仗一时之权,专任智力以成功业,行事动静,多违圣检;为人子则数危其亲,为人君则囚系贤相,为人父则不能卫子;身没之后,社稷几倾,若与少康易时而处,或未能复大禹之绩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汉祖矣。①《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髦纪》注引《魏氏春秋》,第134—135 页。
在曹髦看来,商汤王、周武王及汉高祖刘邦等创业之主未必皆优,他们尚不及夏代的中兴之主少康。言下之意,他将效仿夏朝的少康,从司马氏手中夺回大权,中兴曹魏王朝。
淮南地区历来是曹魏对付吴国的军事重镇,有重兵戍守,戍守淮南的将领都是曹魏久历戎机、畅晓军事的名臣宿将。司马懿在世时,虽然常为方镇大帅,掌握一部分兵权,但从来没有染指过淮南,一直到司马师执政,司马氏的力量还是无法渗透到淮南。自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后,淮南遂成了唯一能向司马氏势力挑战的强大力量。司马师目无君主,擅权废立,激起了曹魏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的愤怒。正元二年(255),毌丘俭、文钦矫郭太后诏,在淮南起兵讨伐司马氏。朝中大部分人认为只须派遣太尉司马孚征讨诸葛诞即可,只有尚书傅嘏和太常王肃力劝司马师亲自前往征讨。当时司马师新割目瘤,身体尚未恢复,听到傅嘏的话,如醍醐灌耳,猛然惊醒,遂奋起而言:“我请舆疾而东。”②《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傅嘏传》注引《汉晋春秋》,第628 页。司马师遂以傅嘏守尚书仆射,一起前往东征。
司马师击破毌丘俭、文钦后,因目疾加重而去世。一时间,曹魏政权的最高权力出现了真空,不甘心当傀儡皇帝的曹髦认为,此乃天赐良机,可以从司马氏手中夺回权力。史载:“毌丘俭作乱,大将军司马(师)景王东征……卫将军司马(昭)文王为大军后继。景王薨于许昌,文王总统六军,钟会谋谟帷幄。时中诏敕尚书傅嘏,以东南新定,权留卫将军屯许昌为内外之援,令嘏率诸军还。会与嘏谋,使嘏表上,辄与卫将军俱发,还到洛水南屯住。于是朝廷拜文王为大将军,辅政。”③《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钟会传》,第785 页。《魏书·诸葛诞传》,第773 页。曹髦诏敕司马昭驻守许昌,不让其返回朝廷,其目的就是乘机剝夺司马氏的兵权,至少不让司马昭弟承兄位,入朝辅政,从而改变政权在司马氏家族内部传递的局面。曹髦又令尚书傅嘏率领大军返回洛阳,其意在分化司马氏集团。然而,傅嘏不为所动,他与钟会一起劝说司马昭带兵,即刻从许昌返回洛阳。司马昭用傅嘏及钟会之计,公然抗旨,自己率军回京,从而迅速地稳定了政局。司马师死后,傅嘏居中调度,使司马家族很快地渡过了危机,曹髦计划落空,无奈之下,不得不对司马昭加以笼络,遂拜司马昭为“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政,剑履上殿”。④《晋书》卷二《文帝纪》,第33 页。司马昭弟承兄位,完全掌握了朝廷大权。
司马昭掌权后,曹髦的境遇没有得到丝毫改善。甘露二年(257)忠于魏室的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再次于淮南起兵讨伐司马昭,是为淮南第三叛。司马昭遂率领大军,亲自前往淮南征讨诸葛诞。临行前,司马昭为防止自己离开京师洛阳之后,曹髦与郭太后勾结,乘机剥夺他的权力,遂上表声称:“昔黥布叛逆,汉祖亲征,隗嚣违戾,光武西伐;烈祖明皇帝乘舆仍出:皆所以奋扬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暂临戎,使将士得凭天威。”⑤《晋书》卷二《文帝纪》,第33 页。司马昭的话说得如此冠冕堂皇,曹髦并无任何理由加以反驳,无奈之下,只得与郭太后随同司马昭南征。从曹髦内心而言,他是寄希望诸葛诞打败司马昭的,但由于双方实力对比的悬殊,忠于曹魏的诸葛诞终究不是司马昭的对手,司马昭攻破寿春,“(诸葛)诞窘急,单乘马,将其麾下突小城门出。大将军司马胡奋部兵逆击,斩诸葛诞,传首,夷三族”。⑥《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钟会传》,第785 页。《魏书·诸葛诞传》,第773 页。随着诸葛诞的失败,其勤王救驾的目的也落了空,同时也扑灭了曹髦借诸葛诞之力摆脱傀儡君王的希望。
曹髦性格刚烈,是个自尊性很强的帝王,司马昭的飞扬跋扈,以及种种约束和看管,皆引起他强烈地不满,但又无可奈何。甘露四年(259),地方上奏曰:井中出现黄龙,“咸以为吉祥”。但曹髦却说:“龙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数屈于井,非嘉兆也。”之后,曹髦作《潜龙》诗影射司马昭,“司马文王见而恶之”。⑦《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髦纪》注引《汉晋春秋》,第143 页。
在采取了多种措施,冀图摆脱司马氏控制皆无效之后,曹髦遂不计后果,亲自率众讨伐司马昭。其直接原因,是他难以忍受司马昭擅权、皇权日渐式微的局面,而且担心自己与曹芳命运相似,遭遇被废黜的结局。其导火索,则可能是曹髦被迫对司马昭进行的封赏和司马昭的矫情推脱。曹髦曾于甘露三年五月封司马昭为晋公、建立晋国并设置相应的公府机构、加九锡、升相国,司马昭九次推辞,改为在原爵位高都公中增加万户、三县的食邑,无爵位的儿子都封为列侯。甘露五年(260)四月,曹髦被迫再次进行前述封赏,此时距离弑君事件的爆发仅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一次,司马昭并未像先前一样“前后九让”,加以推辞,而这可能是司马昭与曹髦关系彻底破裂的直接诱因。
此外,卢弼根据《晋书·文帝纪》的记载,推测当时司马昭的确有废黜曹髦的图谋,①《三国志集解》卷四《魏书·高贵乡公髦纪》卢弼按:“据晋史所载,当时实将有废立之事,昭之密疏或即为此。郑小同之鸠死,虑其漏泄也。”第161 页。而《魏氏春秋》记载的郑小同被毒杀,②《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髦纪》注引《魏氏春秋》云:“(郑)小同诣司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厕还,谓之曰:‘卿见吾疏乎?’对曰:‘否。’文王犹疑而鸩之,卒。”第142 页;《后汉书》卷三五《郑玄列传》注引《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贵乡公时为侍中。尝诣司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厕还,问之曰:‘卿见吾疏乎?’答曰:‘不。’文王曰:‘宁我负卿,无卿负我。’遂酖之。”第1212 页。也正是缘于司马昭担心自己废立君主图谋的泄露。据《魏晋世语》《晋书·石苞传》记载,③《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髦纪》注引《世语》云:“甘露中,(石苞)入朝,当还,辞高贵乡公,留中尽日。文王遣人要令过。文王问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明日发至荥阳。数日而难作。”第147 页;《晋书》卷三三《石苞传》载:“苞因入朝,当还,辞高贵乡公,留语尽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数日而有成济之事。”第1001 页。时任镇东将军石苞曾觐见曹髦,被曹髦挽留了很久。司马昭向石苞了解情况,石苞说:曹髦乃是“非常主也”。次日石苞就离开洛阳,不数日即发生司马昭弑君事件。
据《三国志·高贵乡公髦纪》注引《汉晋春秋》载“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王经劝阻曹髦说:“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曹髦从怀中拿出“黄素诏”,扔在地上说:“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
曹髦说完,就进内宫禀告郭太后。王沈、王业要王经与他们一起告密,但被王经拒绝。王沈、王业遂奔出宫殿,疾驰禀报司马昭,使得司马昭得以有所防备。
甘露五年五月初七(己丑,6 月2 日),曹髦拔出佩剑登上辇车,率领殿中宿卫和奴仆数百人,鼓噪着出击。此时,司马昭之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和司马昭心腹、中护军贾充均率兵向皇宫进发。司马昭之弟司马幹想从阊阖门(系曹魏宫城正门)入宫,被时任大将军掾满长武(满宠之孙)、孙佑等劝阻,改走东掖门;参军王羡也被满长武阻拦。曹髦在东止车门遭遇入宫的司马伷及其手下,曹髦左右之人怒声呵斥他们,司马伷的兵士吓得四散而逃。
曹髦率众继续向相府前进,至皇宫南阙,贾充率兵士数千人在南阙阻拦曹髦。曹髦手持利剑,称有敢动者灭其族,贾充的部众“莫敢逼”,甚至想要退却。
骑督成倅之弟成济,担任太子舍人,在贾充麾下,见此情景问贾充说:“事急矣,当云何?”贾充说:“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④《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髦纪》注引《魏末传》,第145 页,第145 页。又曰:“(司马公)蓄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也,无所问也。”⑤《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髦纪》注引《汉晋春秋》,第143 页,第144 页。成济兄弟又问:“当杀邪?执邪?”贾充说“杀之”。⑥《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髦纪》注引《魏末传》,第145 页,第145 页。于是成济立即抽出长戈上前刺杀曹髦,戈刃刺穿了曹髦的身体而从其后背露出,曹髦当场身亡。
三、弑君事件检讨
从弒君事件本末来看,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了解到事件真相,即司马昭废曹髦之意或有,弑君之举实为被迫无奈。在儒家忠孝思想被大力宏扬,忠君观念深入人心的汉魏社会,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弑君”都被看成是十恶不赦之罪,将引发朝野震动,甚至是人神共愤。东汉清议最盛,士风激浊扬清,极重名节,君臣之间的关系一旦确立,忠君意识便成为士人伦理中最为重要的准则。司马昭出身于世代为宦的诗礼之家、阀阅门第,不可能不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退一步讲,司马昭即使想加快代魏步伐,也不会主动采取这种弑君的极端手段,因为这会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司马昭的弑君之举甚至导致了两晋诸帝在日后一百五十余年政治上的被动地位。我们从东晋宰辅王导与明帝的一段对话即可看出此事过去数十年之后,即使是司马氏的后裔子孙也为祖上的弑君之行感到羞愧万分。
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司马昭)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①《晋书》卷一《宣帝纪》,第20 页。
如何来解读“司马昭弑君”事件呢?笔者以为,从另一种视角来看,司马昭弑君并非是为了加快代魏步伐,而是为了保全其家族。曹髦突然亲自出马讨伐司马昭,事起仓促,司马昭猝不及防,毫无准备,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弑君”实属被迫无奈的自卫之举。司马昭虽在政坛历练多年,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但百密一疏,他万万未曾料到年仅二十岁的曹髦性格如此血性、刚烈,居然仅凭“僮仆数百”,就敢“鼓噪而出”,前来与自己“拼命”。然而即便曹髦“宿卫空阙,兵甲寡弱”,但其贵为九五之尊的天子威严仍然具有极其强大的震撼力。曹髦在讨伐司马昭时,曾声称:“(吾)何所惧?况不必死邪!”其言虽太自信,但也不无道理,因为当众人看到天子曹髦手执宝剑,亲自披挂上阵,来势汹汹的气势,连司马昭之弟司马伷及其手下军士都震惊了,居然不作抵抗就“伷众奔走”。可见,当时情势之危急。
虽然贾充是司马昭弑君事件的头号帮凶,但细思贾充之言:“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有种乎?”亦不无道理。司马氏专权多年,在政治上已是曹魏王朝的死敌,一旦失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必遭倾宗覆族之祸。受其株连,其党羽如贾充、成济等人亦必遭诛戮。所以此时此刻,司马氏和曹氏的斗争已是你死我活,没有半点调和的余地。当成济问贾充,对曹髦“当杀邪?执邪?”贾充毫不犹豫地回答“杀之”,其言虽然狠毒,但在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生擒曹髦之后,如何处理呢?是审判?还是幽禁?或者释放?都是极大的麻烦。事情到了这个程度,双方的矛盾就是死结,无法解开,所以贾充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果断地命令成济弑君。
从司马懿开始发端,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传承,历经二代父子三人的苦心经营,司马代魏无疑已成了历史的必然,然而代魏是否要以弑君作为代价?这就值得商榷了。曹髦被弑,不仅曹魏江山从此万劫不复,作为胜利者的司马氏也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与司马氏家族有通家之谊的陈泰当廷痛哭高贵乡公之死,固执地要求司马昭追查弑君元凶。《资治通鉴》卷七七,“景元元年五月”条曰:“(司马)昭入殿中,召群臣会议。尚书左仆射陈泰不至,昭使其舅尚书荀顗召之,泰曰:‘世之论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乃入,见昭,悲恸。昭亦对之泣曰:‘玄伯,卿何以处我?’泰曰:‘独有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进于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复更言。”
不仅陈泰要追究弑君的罪行,连司马昭之叔司马孚也觉得其侄司马昭弑君有悖君臣之道,故“枕尸于股,哭之恸,曰:‘杀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临终前他一再声称自己是“大魏之纯臣”“有魏贞士”,②《晋书》卷三七《安平献王孚传》,第1084、1085 页。对司马昭弑君、司马炎受禅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由于司马昭的弑君行为触及了儒家的道德伦理底线,所以饱受士人诟病。司马昭秉政以来,未建重大功业,欲行禅代,恐人心不服,难孚天下之望。其时三国鼎峙的局面依旧,故司马昭弑君之后,图谋借伐蜀来建立功业,以摆脱弑君所带来的道德危机。总之,这件事带来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司马昭亦为此留下了千古骂名。
当然,曹髦是司马师选的君主,责任不全都在司马昭身上。司马昭的失误是他对曹髦的性格缺乏深刻的了解。按照以往历史上的成例,凡为傀儡君主者,大都性格比较怯懦软弱,凡事皆由权臣摆布。例如,汉献帝终其一生都不敢对曹操的挟天子之举有丝毫反抗。当董贵人及亲生皇子被杀时,汉献帝仍然沉默不语,只是在伏皇后被害时,才对御史大夫郗虑言道:“郗公,天下宁有是邪?”又对伏后说:“我亦不知命在何时!”③《后汉书》卷一〇(下)《皇后纪》,第454 页。还是不敢对曹操反抗。
但曹髦与以往这些任由权臣掌控的君主截然不同。在曹髦看来,既然司马昭篡魏之心已定,废辱他只是旦夕之事,自己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最后一搏;与其苟延残喘,不如壮烈一死,否则,曹魏社稷断送在自己手中,还有何面目去见九泉之下的太祖曹操与文皇帝曹丕。面对这么一位刚烈过人颇有乃祖之风的君主,司马昭太疏忽、太缺乏警惕心了,他未采取诸如在宫庭中安插耳目,或干脆将曹髦软禁于皇宫之中的任何防范措施。更令人惊讶的是,平时周密布署、心细如发的司马昭居然失策到让曹髦明目张胆地来讨伐自己,最后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措手不及,只能迫不得已,在大庭广众之下让贾充指使成济公然弑君,此事令天下人震惊与愤怒,这个责任司马昭是难辞其咎的。
成济替司马昭杀死曹髦,也不免被作为替罪羊,而遭灭族惨祸。①《晋书》卷二《文帝纪》载司马昭上奏郭太后:“故高贵乡公帅从驾人兵,拔刃鸣鼓向臣所,臣惧兵刃相接,即敕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令者以军法从事。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入兵阵,伤公至陨。臣闻人臣之节,有死无贰,事上之义,不敢逃难。前者变故卒至,祸同发机,诚欲委身守死,惟命所裁。然惟本谋,乃欲上危皇太后,倾覆宗庙。臣忝当元辅,义在安国,即骆驿申敕,不得迫近舆辇。而济妄入阵间,以致大变,哀怛痛恨,五内摧裂。济干国乱纪,罪不容诛,辄收济家属,付廷尉。太后从之,夷济三族。”第36—37 页。在曹髦被杀后,司马昭伪装成“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②《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髦纪》,注引《汉晋春秋》第144 页,第146 页,第143 页。“评曰”第154 页。又说自己得悉这个噩耗是“哀怛痛恨,五内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陨坠?”③《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髦纪》,注引《汉晋春秋》第144 页,第146 页,第143 页。“评曰”第154 页。极尽虚伪做作之能事。但紧接着,司马昭却授意郭太后下诏,罗列曹髦的种种“罪状”,曰其“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数呵责,遂更忿恚,造作丑逆不道之言以诬谤吾,遂隔绝两宫。其所言道,不可忍听,非天地所覆载。吾即密有令语大将军,不可以奉宗庙,恐颠覆社稷,死无面目以见先帝。大将军以其尚幼,谓当改心为善,殷勤执据。而此儿忿戾,所行益甚,举弩遥射吾宫,祝当令中吾项,箭亲堕吾前。吾语大将军,不可不废之,前后数十。此儿具闻,自知罪重,便图为弑逆,赂遗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药,密因鸩毒,重相设计。事已觉露,直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出取大将军”。④《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髦纪》,注引《汉晋春秋》第144 页,第146 页,第143 页。“评曰”第154 页。罪状中云曹髦要谋害郭太后,显然是无稽之谈,甚至是弥天大谎。那么,郭太后为何要编出如此谎言呢?毫无疑问,这是她在司马昭胁迫下的无奈之举。
曹髦虽为曹魏末世的傀儡之君,在位时间较短,在政治上亦无大的作为,《三国史》作者陈寿批评曹髦是“轻躁忿肆,自蹈大祸”。⑤《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髦纪》,注引《汉晋春秋》第144 页,第146 页,第143 页。“评曰”第154 页。但他无所畏惧,奋起抗争,敢于与权臣司马昭拼死一搏、视死如归的精神还是十分可贵的。有这种精神、勇气、胆略的皇帝在中国古代帝王群中毕竟不多,所以在民间获得了不错的口碑。《三国志·高贵乡公髦纪》注引《汉晋春秋》曰:“丁卯,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下车数乘,不设旌旐,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由此可见,民间百姓为曹髦死于非命鸣不平,并抱有深深的同情。
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在赞叹曹髦的同时,也无意以此来贬低司马昭。诚然,司马昭欲盖弥彰、杀成济作替罪羊,罗织曹髦罪名的所作所为确实狠毒虚伪。但是,玩弄权术是古代政治家的惯用伎俩,不足为奇。由于政治风云的诡谲多变,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政治家不用心计,不施手腕何以立足?而且这与司马昭平定淮南,攻灭蜀汉,奠定统一天下的功绩相比,无疑是次要的。⑥司马昭的历史功绩可参阅拙文《三国后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司马昭》,《孝感师专学报》1996 年第4 期。正如吴丞相张悌所说:“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⑦《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皓传》注引《襄阳记》,第1175 页。因此我们不应以弑君之事来否定司马昭。正如评价曹操一样,曹操也是个杀人魔王和精于权术的老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功业的充分肯定。
必须指出:司马代魏和曹氏代汉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魏晋易代之际,儒家倡导的忠君思想已遭削弱。旧的两重君主观影响仍然存在,⑧参阅拙文《论先秦秦汉社会的两重君主观》,《史学月刊》2004 年第2 期。在皇权衰落的境况下,大臣极易操纵和控制才具平庸之君,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取而代之,登上九五之位。司马昭之后,南北朝君主纷纷效尤,其夺位手法如出一辙。直至隋唐以降,莫不如此,甚至被誉为一代英主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发动玄武门之变,弑兄杀弟,逼父退位;宋太祖赵匡胤正是通过陈桥兵变,才得以黄袍加身。历朝历代,弑君夺位者不可胜数,因此我们绝无必要单单诟病“司马昭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