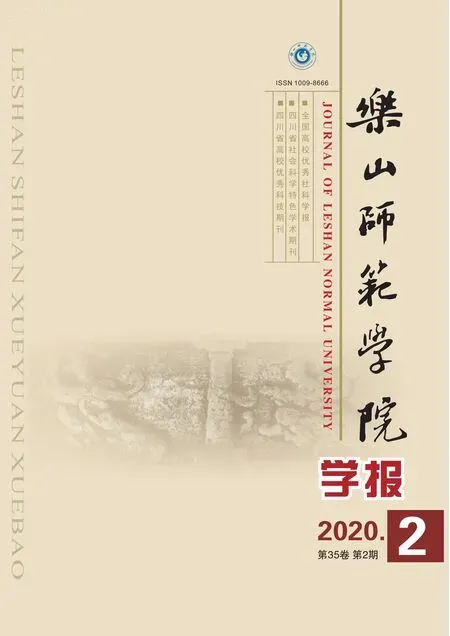新中国成立以来“九一八”纪念述论
2020-03-03胡丞嗣
胡丞嗣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的开端,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国耻日,其直接影响虽只存在于彼时彼刻,但有关“九一八”的历史记忆却一直绵延至今,并通过相关纪念活动得到集中阐释。柯文曾言:“周年纪念可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筑起一条情感桥梁。”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发展,纪念对象会经历一个被不断阐释和意义重构的过程,以适应现实需要[1]。“九一八”纪念显然也符合这一规律,无论是抗战时期的“九一八”纪念,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九一八”纪念,皆是沟通过去与现实的管道,且有着独特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功用。目前学界对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多侧重于事件本身,而于“九一八”纪念虽有所探讨,却多集中于抗战时期,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关史实鲜有所涉。①事实上,“九一八”纪念并非战时的独有现象,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依然发挥着建构国耻记忆的特定功用,若欲切实把握国耻记忆的完整诠释脉络及其在不同时局下的特定意涵,就有必要对和平局势下的“九一八”纪念加以考察。此外,以往“九一八”纪念的相关研究囿于史料和视角,多侧重于纪念活动和纪念话语的考察,甚少言及纪念的制度设计层面,然而,作为纪念日核心部分的制度设计恰恰却是纪念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相关档案文献、日记及报刊资料,集中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与“九一八”有关的制度设计、纪念活动、纪念话语,这不仅可以增进国家与社会对这一纪念日的认知,还能为今后纪念日的规划运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九一八”纪念日的设计
纪念日的设计是纪念日周期化、程式化的基础和前提,相关规定不仅会涉及纪念日的时间、仪式等常规内容,还会着重强调相关注意事项,以确保纪念活动的正常开展以及纪念功用的合理释放。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于战时几乎每年都会举办“九一八纪念会”,届时边区群众都会“佩着符号与会”[2],甚至在“日治时期”的香港,中共也召开过纪念“九一八”的群众大会[3]。当时的国民党也有一套自己的纪念仪式,河南省档案馆的一份馆藏档案或可为我们呈现战时国民党“九一八”纪念大会的大致程序:1.全体肃立;2.主席就位;3.唱党歌;4.向党国旗暨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5.主席恭读总理遗嘱,全体同时循声宣读;6.静默三分钟;7.主席报告开会意义;8.特约讲演、自由讲演;9.呼口号;10.散会[4]。有时,“九一八”纪念还会与其他纪念合并举行,以扩大影响,1939年国民党的“九一八”纪念即与总理纪念周合并,在中山公园举行扩大纪念仪式[5]。1940年中共的“九一八”纪念也与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合并举行,场面可谓蔚为壮观[6]。除各党政军警机关、各学校、各团体分别集合纪念外,国民党还会“组织宣传队至乡村宣传,按照当地情形酌办”[7]。
如上所述,抗战时期的“九一八”纪念因符合战时动员需要而备受各界重视,各方在纪念时亦制定有完善的程序和仪式。但在新中国初期,随着政权更替和社会局势的变化,“九一八”纪念被简单化处理,党和政府在周期性的“九一八”纪念中已不再召开纪念大会,仅以发表社论或纪念文章代替。笔者曾遍查建国初期的相关报刊、领导人日记和文选以及包括《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等在内的史料集,却未寻得建国初期筹办“九一八”纪念大会的踪迹,政务院亦只在《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对“九一八”纪念作了简单规定,将其归为“其他各种纪念节日”,不予放假[8],后来几次修订的版本对“九一八”纪念的规定并无太大的变化,只是将“九一八纪念”改为“九一八纪念日”。民国时期的“九一八”纪念为激励国民抗战精神也未放假[9],故新中国成立后对“九一八”这一带有志哀色彩的纪念日做出不予放假的规定实属情理之中,但未按战时那样定期举行纪念大会着实令人顿生疑窦,当时的党和政府也未曾给出明确说明。不过,我们或能从相关史实中探出些许纪念活动从简的内中根由。早在1946年,国民党即以“抗战已获胜利,自无须再举行该项纪念仪式”为由从官方层面废止了“九一八”纪念,而代之以“九三”抗战胜利纪念[10],此后即便民间在“九一八”当天亦会如约举行相关纪念活动,规模也已大不如前,而各界关注的焦点无疑已经转到与“九一八”同月的“九三”上来。新中国初期亦高度重视“九三”纪念,政府每年皆会发布纪念“九三”的通知,规划相关事宜[11]。“九一八”纪念在新中国初期的从简显然与国民党从官方层面的废止不无关系,不过,更为重要的还是因为带有志哀色彩、拥有战争动员功用的“九一八”纪念已经失去了抗战的原初环境,在和平建设时期再举行国耻纪念大会似乎颇显不合时宜,因而其地位很快被带有志庆色彩的“九三”纪念所取代。
“九一八”纪念在新中国初期的从简也应与当时处于过渡和建设时期,财力有限有关。因为即便是政府重视的“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也并非每年皆会举行集会,尤其是1955年“九三”这样盛大的“逢十”纪念,政府居然做出了不举行纪念集会、仅发表纪念文章的批示[12],这显然与当时的时势不无关系,此亦可视为“九一八”纪念从简的又一缘由。不过,从简并不等于遗忘,事实上,承载着国耻记忆的“九一八”符号也不可能被世人忽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九一八”纪念虽没有了抗战时期战时动员的功用,但在建构集体记忆以及构筑民众对国家及民族的认同方面则更加彰显价值和意蕴。由于与“九一八”事变本身相隔数十年,党和国家在建国伊始即面临着如何更好地保存国耻记忆的问题,只不过当时由于诸多因素一切从简,但一旦有了经济实力的支撑,便会对“九一八”纪念再次重视。
1991年,为更好地铭记那段历史以及传衍国耻记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沈阳建成了“九一八”事变纪念馆,并于“九一八”六十周年之际对外开放[13]。1999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纪念馆改名为“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为该馆题名[14]。与博物馆同时制成的还有警世钟,警世钟正面铸有“勿忘国耻”的字样,背面则记载了九一八事变的经过,自此以后,撞钟鸣警、放飞和平鸽成为沈阳每年纪念“九一八”的独特活动[15]。政府花费大量资金投资建设该博物馆足以看出国家对“九一八”纪念的重视。就性质而言,“九·一八”博物馆已然成为九一八事变的纪念空间,它与普通博物馆不同,具有一般博物馆无可比拟的神圣性。也正如陈蕴茜所言,纪念空间具有“调动情感、引发思考的功能”[16],人们在游览“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时即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受到国耻记忆感召的同时形成对历史、国家、民族的认同,进而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当中。
除营造纪念空间外,沈阳市政府还决定从1995年开始,每年的9月18日晚22时20分(当年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时间)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示勿忘国耻[17]。后为方便更多人参与将时间改为了晚21时18分,从2011年起又将时间改为上午9时18分。无论是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时间,还是与“九一八”谐音的九时十八分,均有着特定意涵,而将时间改为白天无疑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进而增强纪念功效和社会影响。在进入新世纪后的第一个“九一八”周年纪念活动中,作为“九一八”纪念中心的沈阳再次丰富了纪念仪式,除全市鸣警以外,电视台及广播电台也中断了正常节目的播放,插播“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画面,全市正在行驶的车辆自觉停车鸣笛,直至仪式结束[18]。如此大规模、全员参与的纪念仪式可以建构出难以忘却的“集体记忆”,并通过日后的反复加以强化,进而释放纪念功用。有关“九一八”纪念空间的建成以及对“九一八”纪念仪式的规定标志着对“九一八”的纪念进入到新阶段,每年皆按时举行“九一八”纪念活动成为定制。
二、“九一八”纪念活动的形式演进
纪念主旨的表达有赖于各种纪念活动的举办,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九一八”纪念活动,其纪念形式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到多元的变化,同时,纪念区域也呈现出以沈阳为核心逐步向全国扩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地区和民众乃至海外人士都会在“九一八”当天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国耻日”的志哀之意。
新中国初期的“九一八”纪念延续了抗战时期乃至解放战争时期的政治动员方式,纪念活动明显充满“革命”意味,不过,特殊时期可以有特殊的宣传形式,客观来讲,当时的“革命”宣传不失为稳定国内局势、规范意识形态的较好办法。这一时期的纪念活动受多种因素影响略显单调,以发表社论或纪念文章为主,而无论是文章标题还是内容中,均可窥见蕴含的意识形态色彩。因建国初期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故此时的“九一八”纪念具有明确的政治性,侧重于“警惕军国主义复活”、“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宣传。以《人民日报》为例,其在“文化大革命”前发表有《反对今天远东的侵略者——美国帝国主义!——纪念“九一八”十九周年》、《从我的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纪念“九一八”事变三十周年》、《不许新的“九一八”事变在亚洲重演!》等社论或纪念文章。文本话语成本低廉,形式灵活,传播广泛,因而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九一八”纪念活动的主要形式,也是首选形式。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工作重心并未放在文化建设上,对“九一八”的纪念活动几近停滞,就连原本形式单一的社论在这一时期也较为鲜见。改革开放后,国内和国际局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日两国关系业已走向正常化,该时期“九一八”纪念的情况也迥异于建国初期。在纪念活动上,除延续建国初期发表社论或文章的纪念形式外,更多的纪念形式纷纷呈现。如1991年纪念“九一八”六十周年时,林业部在北京举行了座谈会,数十位青年工作人员与经历过“九一八”事变的老同志一起重温了这段历史,会后,大家即表示“一定要不忘国耻,振奋精神,不断推进林业改革和建设。”[19]座谈会这种形式有固定的空间场所及正规的纪念程序,因而能形成较好的氛围并达到理想的感召效果。此外,学术界也以文本或图片的形式对“九一八”进行纪念,刘庭华即著有《“九·一八”事变研究》,他表示研究这段历史就是为了“吸取教训,避免悲惨的历史重演”[20]。沈伟一等人也编有《九一八事变图片集》,其初衷就是在纪念“九一八”的同时亦可“用以教育后人”[21]。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以特殊方式纪念国耻的同时,于深化学界对于“九一八”事件本身的研究也有诸多裨益。有些民众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九一八”事变的真相,控诉日本军国主义当年在东北犯下的罪行[22],对“九一八”加以纪念,他们以亲历者的身份对九一八那段屈辱的历史进行回忆和陈述,无疑比一般文本更具说服力。
20世纪时,更多只是沈阳一市在纪念“九一八”,迈入新世纪后,纪念区域则以沈阳为中心不断延伸。2006年的“九一八”纪念,辽宁省的14个城市首次同时鸣响警报,自是遂为定制[23]。2011年的“九一八”纪念更是不再由辽宁一省单独举办,而是改为由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合办[24]。当年的九一八事变虽发生在沈阳,但却是事关整个东北命运的重要事件,东北三省一同纪念“九一八”标志着继上世纪“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建成后,“九一八”纪念再次迈入新阶段。这一举动反映出东北三省在“九一八”纪念的重要性和意义等方面达成一致,不过,无论是时人还是笔者看来,纪念“九一八”不应仅是东北地区的使命,而应成为全国化的活动。2003年“九一八”纪念前夕即有相关人士呼吁将“九一八”纪念全国化、正规化、法制化,每年的“九一八”举办国家级纪念大会,并由领导人发表讲话,全国大中城市也应同时鸣响警报三分钟、下半旗致哀[25],但这一建议并未被采纳,全国化的纪念迄今仍未实现。不过,“九一八”纪念虽未实现全国化,却已显露出全国化的趋势,新世纪以来,即有许多城市自觉加入到纪念队列当中。比如石家庄就于2007年决定将防空警报日由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纪念日)改为每年的9月18日国耻日,民众均认为这一天拉响防空警报更有意义[26]。在2011年“九一八”80周年纪念日时,全国更是有100多座城市拉响防空警报,共同纪念“九一八”[27]。
除上述大规模的群众纪念外,新世纪的“九一八”纪念更呈现出日常化特征,社会各界通过各式载体表达铭记历史的情愫,即使不在“九一八”当天也可对其进行纪念。灵活化、日常化的纪念方式使得国耻记忆无处不在,更能达到理想的纪念效果。为更好、更方便地纪念“九一八”,2003年团中央等机构特意开通网上九一八事变纪念馆,给了人们更为灵活的凭吊空间[28]。2005年的“九一八”适逢中秋节,即有民众打算做一个重达9.18公斤的月饼,在赏月的同时强调勿忘历史[29],次年沈阳市场上更是出现了“勿忘九一八”牌面巾纸,包装上印有较大的“勿忘九一八”字样[30]。另外还有一些年轻人通过向行人发带有“勿忘九一八”字样的传单提醒人们勿忘国耻[31]。新生一代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很多人对“九一八”感触不深,甚至大部分中小学生完全不了解九一八事变的基本史实[23]。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日常化的纪念向广大青少年反复重申那段屈辱的历史就显得尤为必要。
拉斯金认为,历久常存的建筑可将“被遗忘的年代与未来时代联系在一起”,并在社会中维系一种延续性和认同感[32],多种形式的“九一八”纪念活动显然也有着类似功用。纪念“九一八”,一方面可借此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另一方面也起到了保存、唤醒国耻记忆的功能,许多人虽未亲身经历过九一八事变,但身处庄严肃穆的场景中必定会受到洗礼,进而增进其历史及民族认同。有学者认为“2000—2009年此十年”的“九一八”纪念活动比之“1931—1940年的十年”有相当的淡化[33],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新中国初期各式的纪念载体和纪念仪式表明,无论是国家还是群众均没有淡化国耻记忆的倾向,反而对“九一八”纪念越来越重视,有更多的城市和群众渐次加入到“九一八”当天的纪念仪式当中。
三、“九一八”纪念话语的主旨嬗变
纪念空间、纪念活动皆是纪念话语的载体,社会各界营造纪念空间、举办各式的纪念活动,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阐发纪念的内涵主旨,进而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九一八”纪念话语的意涵,大致随着时势演变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从最初的“革命”宣传最终衍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与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紧密相连。
新中国成立初期,纪念话语侧重于“革命”宣传,“警惕军国主义复活”、“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等标语和口号充斥于大多数“九一八”纪念文章中,“粉碎美国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34]则几乎成为这一时期“九一八”纪念时的必提口号。在纪念“九一八”三十周年之际,北京所有的报刊更是刊载纪念文章,“警告说要防止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和战前野心复活”[35]。对于这些话语,不宜将其从原初语境中剥离出来,而应与新中国初期的内外形势相联系,明确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革命”话语衍生的内中根由。“九一八”纪念中“革命”话语的流行是由当时政治形势决定的,于此我们无需过多苛责。
“文化大革命”时期因纪念活动几近停滞,也就没有了纪念话语表达的通道,不过,1971年的“九一八”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中倒是出现了一个新境况,那就是长期以来矢口否认“九一八”的日本社会出现了反思军国主义、纪念“九一八”的现象,这或可视为“九一八”纪念话语转变的分水岭。当时日中友协(正统)、日本社会党发表声明称:“日本人民决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再次走上侵略中国和亚洲的老路。”[36]还有部分东京的学生和市民在集会示威时表示“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以阻止‘九一八事变’的重演。”[37]日本此时出现纪念“九一八”的高潮固然包含在野党和社会各界谴责佐藤政府的政治意图,但同时也折射出中国国力的强大使得日本部分党派有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意向[36]。承认“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的客观事实并对此深表歉意,实是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日本部分政党和社会团体向中国抛出的橄榄枝,其在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同时也有助于“九一八”纪念话语的“去革命化”叙述。
在逐渐“去革命化”的基础上,改革开放后的纪念话语为适应社会参与已回归理性,不再以意识形态宣传为主要目的,而是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由此前的“反美亲苏”转变为“以史为鉴、珍爱和平”。不同于以往追忆国耻之后痛陈日本罪行的作法,该时期的“九一八”纪念文本在结尾所倡导的往往是中日友好,强调要“排除一切妨害两国关系的因素”,使两国人民的友谊一直保持下去[38]。纪文在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十五周年时也强调正视历史、捐弃前嫌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合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39]。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苗头,此时的“九一八”纪念话语侧重于追求和平诉求的表达,各类文章屡次提醒日本官方不要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而应认真汲取历史的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世界各国。新中国主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由“反美”到“和平”纪念口号的转变是国际局势变化的反映,同时也折射出中国外交理念的更新。
新世纪“九一八”纪念话语的政治色彩较改革开放初期更为淡化。在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后,党和国家在纪念中也愈发展现出大国胸怀,更多地关注人类和平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有意识地淡化政治色彩,宣传重心转移到历史本身的作用与世界的和平大势。针对新世纪日本右翼势力屡次歪曲历史、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党和政府“九一八”纪念时即立足史实予以反击,着重强调日本国内要警惕右翼势力的抬头,并表示愿与日本在和平友好中增进两国关系[40]。发展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前提是日本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过去那段历史,这是新世纪以来“九一八”纪念中我国多次强调的话语之一,同时也是党和政府在新世纪秉持的“以史为鉴,珍爱和平”理念的反映。除批驳扭曲历史的行为外,新世纪的“九一八”纪念话语中亦蕴涵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诉求[41],国耻记忆在纪念中得到升华,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十八大以来,“努力实现中国梦”随着“中国梦”概念的提出也逐渐成为纪念时的重要话语,纪念“九一八”就是要从这段历史中汲取力量,“为实现伟大中国梦不懈奋斗!”[42]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发展变化,纪念话语也呈现出新的面相,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载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九一八”纪念活动由政府主导转为社会广泛参与,纪念形式亦日渐丰富。“九一八”纪念的内涵主旨随时代发展呈现出嬗变之势,从最初的“警惕军国主义复活”、“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转变为“以史为鉴,珍爱和平”,再到新世纪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十八大以来更是与实现“中国梦”紧密相连。“九一八”纪念随着时代发展而演进的同时,俨然已经衍化为一个特殊符号,人们言及“九一八”,必定会首先想到1931年的那场事变及其所承载的国耻记忆。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九一八”纪念的制度设计在日臻完善的同时仍有诸多值得深思之处。一直以来,不断有各界人士倡议将“九一八”定为国难日,并将“九一八”纪念上升为国家行为[43],但这一愿景迄今仍未实现,与“九一八”纪念日属同类性质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均有国家级的纪念活动,而“九一八”更多只是东北地区在纪念。九一八事变是“十四年抗战”的开端,把“九一八”纪念上升到国家层面和全国范围无疑有其必要。新生一代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对其印象较为模糊,甚至有些中小学生都不能准确说出九一八事变的具体日期,这不仅能反映出对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不足,亦能说明“九一八”纪念在亟待国家化、制度化的同时也应日常化。换言之,“九一八”纪念不应只存在于九月十八日当天,日常化的国耻记忆无疑可以更好地“引导未成年人弘扬民族精神,增进爱国情感”[44]。保存国耻记忆有赖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只有不忘历史才能开创未来。
注 释:
①相关文章有白玉:《从<中央日报>看全面抗战中九一八纪念活动的社会记忆》,《档案与建设》2014年第10期;苏全有、邹宝刚:《对九一八国耻日纪念的考察与反思》,《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王春林:《国难中的九一八纪念——以东北流亡民众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1期;陈文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九一八事变的纪念》,《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杨巧:《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难纪念中对国家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以“七七”与“九一八”纪念仪式为例》,《甘肃理论学刊》2017年第5期;陶祺谌:《日方档案所见中共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活动》,《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7期;王晓园:《试论<新华日报>有关“九一八”纪念报道的话语表达》,《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郭辉:《抗战时期“九一八”纪念的历史考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2期。其中,仅苏全有、邹宝刚的《对九一八国耻日纪念的考察与反思》涉及到了新世纪的“九一八”纪念,但所涉时段仅为2000—2009年,并未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九一八”的纪念活动和纪念话语做系统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