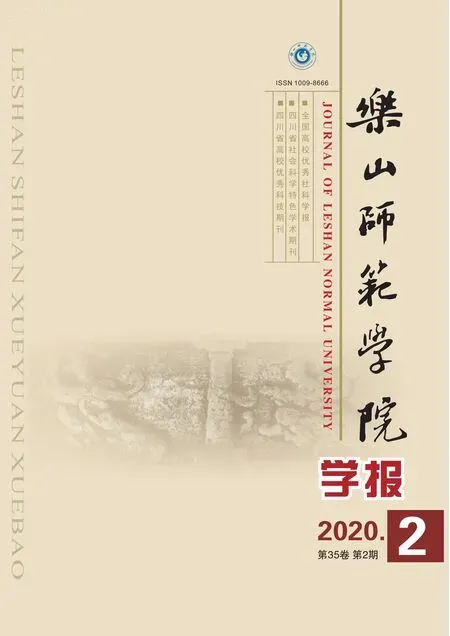生态翻译视域下许渊冲英译唐诗中的意象词处理方式探讨
2020-03-03王雪群
王雪群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唐诗是中国古代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部分。古代诗人为了在有限的几行诗内传达诗歌深远的意境,表达诗人的浓厚感情,他们往往运用意象词。文化意象词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深刻理解诗歌中的意象词含义能帮助读者感受诗歌所表达的精神实质和意境。因而,在诗歌翻译过程中,如何巧妙地翻译意象词是展示原诗意境之美的重点与难点。
中外学者们对意象词的研究从未停止过,他们从不同角度对意象词加以研究,A.Waley[1]68认为意象词是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在翻译诗歌时,应避免随意增减意象词,避免破坏原诗的意象。G.Palmer[2]163从文化语言学角度研究了意象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国内学者们主要运用许渊冲教授的诗歌翻译“三美”理论来探讨意象词的翻译,如:周文革、叶少珍[3]118对比研究了不同版本的英译唐诗《静夜思》中意象词翻译处理方法,并指出唐诗英译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原诗意象词的传达与原诗风格的保留上;丛滋杭[4]80运用许渊冲的“三美”理论对比研究了翁显良、许渊冲和丁衡祁三位翻译家在意象词翻译上的异同点。当然,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运用其他翻译理论剖析诗歌翻译中的意象词。如:丛滋杭[5]68对诗歌中的意象词翻译做了系列研究,她指出当今学界对古诗中意象词的研究太乱、太杂,因而,有必要从历史学角度重新研究意象词的来源,让读者明白古诗中的意象词有其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谢天振[6]29曾说过,在翻译中国古诗中的意象词时,经常用到直译法、意译法和省译法等。
综上,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古诗中的意象词翻译研究由来已久,成果颇丰,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新的理论不断涌现,意象词翻译仍有值得研究的领域与视角。本文拟从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作为理论框架对许渊冲教授翻译的《唐诗三百首》中的意象词处理方式加以研究,意图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添砖加瓦。
一、生态翻译视域下的许渊冲英译唐诗中的意象词处理
生态翻译学是在胡庚申教授2004年提出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上发展而来的,该理论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中的“适应生存、自然选择”学说与翻译研究相结合,在该理论解读下,翻译被定义为“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7]11。
根据生态翻译学理论,翻译过程被描述为由译者主导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8]204。翻译方法即被解读为“三维”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语言维上的适应性转换、文化维上的适应性转换和交际维上的适应性转换。
众所周知,唐诗中意象词颇多且联想丰富,何为“意象”?根据《朗文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第七版), “image refers to a word or phrase that describes something in an imaginative way”[9]216。古人将意象分为“意”和“象”两部分。“意”指人的思想,“象”指物的表象。这里的“象”即存在于世间的万物之表象,只有当物象与人的主观思想、主观情感相结合才有意义,才能让读者展开联想。同时物象又需要通过语言来表达它所蕴含的意义与联想。意象的运用使诗歌言近旨远、含蓄幽深,字面之下蕴藏着无限宽广的象征与暗示空间[10]106。
许渊冲教授[11]99认为译诗要像原诗一样打动读者的心,达到意美意境。而要打动读者的心,诗歌意象词的翻译非常重要。
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强调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翻译生态环境因素所左右的选择活动。这样的选择行为发生在翻译活动的各个方面,存在于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出现在翻译转换的各个层次。当翻译过程中的“意美、形美、音美”难以共存时,其中孰轻孰重,舍谁保谁,最终要取决于译者,在选择适应特定翻译生态环境基础上,由译者自主地作出判断,作出适应性选择。当然,译者的适应性选择既要有责任尽量保持并转换原文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和交际生态,又要有责任尽量使转换过来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和交际生态能够在译入语的翻译生态环境中“生存”和“长存”[8]234。
在翻译唐诗中的意象词时,许渊冲教授就在力求译诗的“意美、形美、音美”时,作出了适应性选择,主要通过在“三维”转换得以实现,即,语言维上的转换、文化维上的转换和交际维上的转换。
(一)语言维上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根据胡庚申教授的生态翻译学理论,翻译过程中语言维上的转换表现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就许渊冲英译唐诗中意象词处理方法而言,他在语言维上的转换主要体现在对诗歌音美、形美和修辞方法的追求上。许教授采用了恰当的翻译方法来翻译唐诗中出现的意象词,特别是在翻译中西方文化内涵相同或相似的意象词时,他尽量保持原诗的风格,只作简单的转换。
1.字面直译
人类的认知模式总有相似之处,这是人类社会语言交流与翻译创作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有些意象词给人的心理反应是相同或相似的,而不受限于生活地点与文化背景的影响,比如花开使人愉悦、落叶让人忧愁等等。对于这类可能在目标语读者和原语读者心中产生相似的心理反应的意象,许渊冲一般采取字面直译的方法,保留原诗的文化意象与修辞方法[10]123。
如下面的诗句摘自王维的《使至塞上》:
(1)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王维《使至塞上》)
译文:Like tumbleweed I leave the fortress drear;
As wild geese I come under Tartarian sky.
In boundless desert lonely smokes rise straight;
Over endless river the sun sinks round.[12]16
这首诗通过一系列的意象描绘,向世人展示了诗人出塞途中的所见所闻。其中,归雁、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这类意象词在特定的诗歌语境下,会激发中英文读者产生相似的景物联想与情感抒发,读者能从这一系列意象中领略到一派黄沙莽莽、苍茫辽阔的边境风光。因而,许渊冲教授在语言维上只作简单的转换,尽量保留原诗的意象之美。他把“归雁 ”译为“wild geese”,“大漠孤烟”译为“boundless desert,lonely smokes”;“长河落日”译为“ endless river, the sun sinks”。
2.在直译意象词的基础上,添加意义提示语
在中国古诗中,还有些意象词蕴含着典型的中华民族委婉深厚的文化内涵,而这些意象词亦能在英语中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但在英语文化里也许与中文的情感联想截然不同,直接进行字面翻译之后可能会忽略其对诗歌意境的重要烘托作用,甚至产生相反的情感,同时在英语里又找不到更好的替代意象。在翻译这类意象词时,许渊冲教授则在直译意象词的基础上,增加了简短而又必要的意义提示语,点明这些意象词的内在特征及其激发的感觉与情绪,以确保英文读者在阅读时能正确领会该意象词所蕴含的象征和隐含意义,实现中西文化交流。
例如:“杜鹃”或“子规 ”是古诗词表达悲痛伤心与满腔愁怨情绪的传统意象,不少伟大诗人都借用“杜鹃”或“子规 ”来抒发心中情感,如:
李白借月夜子规的哀啼来描述渲染蜀道之奇险难攀,让读者更深刻体会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心境:
(2)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李白《蜀道难》)
李商隐在杜鹃悲鸣中寄冤禽托写恨怀:
(3)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李商隐《锦瑟》)
处理这种对烘托诗的意境起着重要作用的诗歌意象词,许渊冲教授一般仍是采取字面翻译为主,但考虑到中英文读者的不同认知与思维模式以及文学思想沉淀,就会加上必要的意义指示词或表示情感的搭配语,以引导英文读者对诗意的正确解读,以免产生误解。如对于李白的诗句:
(4)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译文:All willow-down has fallen and sad cuckoos cry,To hear you banished southwestward beyond Five Streams.[12]194
许教授在翻译时添加了“sad”一词,成功地传达了“子规”这个意象词所承载的悲伤幽怨的情感内涵,否则英文读者可能误解该诗句的情感基调,因为在英语文化里,“杜鹃”的意象经常给人以春天的欢快和勃勃生机,是充满喜悦的意象词,而笔者前面叙述过,“杜鹃”在中国古诗中是充满悲怨的情感意象。
许渊冲教授的这种翻译处理方法也正体现了生态翻译学里一直强调的保持“文化生态”:译者有责任在适应性选择转换时尽量保持原文和译文的文化生态平衡,在传播中华文化的同时,使英美读者能在心理上接受中华文化,同时不破坏他们的文化生态。
3.保留诗歌的音韵之美,“以诗译诗”
在翻译唐诗里的意象词时,许教授在语言维上的转换还体现在他尽量保留诗歌的音韵之美,强调“以诗译诗”,尽量做到押韵。众所周知,唐诗以严格的押韵而著称,中国古诗很多都要求押韵对仗,诗歌的韵律可以让读者感受到诗歌的“音美”。诗人亦能通过诗歌的韵律表达情感,而读者相应地从中感受到诗人的情感。为了尽可能保留译诗的音韵之美,许渊冲教授在语言维转换时,做了相应选择。比如:
(5)参差连曲陌,迢递送斜晖(李商隐《落花》)
译文:Here and there over the winding way, They say goodbye to parting day.[12]132
这两行诗从空间、时间两个角度描绘落叶的场景,在诗中“斜晖”是十分重要的意象词,诗人借此意象词表达出内心的无奈与伤感,使诗歌的意境无限凄美。许教授在翻译这首诗时,既想传达意象词“斜晖”的引申义,又想保持诗的“音美”,使其押韵,平衡句子结构。因而,他在语言维转换上大胆地做出选择,把意象词“斜晖”译成“parting day”,使其尾韵〔ei〕与上句”way”的尾韵相同。而且“斜晖”与“parting day”的意象文化内涵相似,在不改变诗歌意境的前提下兼顾了译诗的文体效果。
类似的转换方法还体现在翻译李白的《蜀道难》:
(6)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李白《蜀道难》)
译文:Guided by one, and forced by none.[13]104
许教授直接把“万”译成“none”,其尾韵与上一句最后一词“one”的尾韵相同,既做到意义的传达,又保留“音美”。
许教授的译法正说明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当“意美、形美、音美”难以共存时,译者在选择性适应特定翻译生态环境基础上,可以由译者自主地作出判断,作出适应性选择。许教授的做法是舍弃“形美”,保留“意美”与“音美”。
(二)文化维上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由于原语文化生态和译语文化生态在性质和内容上往往存在着差异,为了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译者不仅需要注重原语的语言转换,还需要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文化生态,并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即“文化维的适应性转换”[8]270。
如前所述,唐诗中的文化意象词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为诗歌创造唯美的意境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英美读者对此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知。有时,诗歌唯美意境的传递并不在于意象词字面意思的翻译,而在于其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许渊冲教授在文化维上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处理得十分成功,他为了尽量保留原诗的“意美”,有时使用替换意象的翻译方法。如果某些意象对整首诗的意境体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又承载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和约定俗成的联想意义,这时许渊冲教授会将诗中的意象转换成英语文化中功能对等的固有意象,这样就能简洁而又有效地激发译语读者产生与原诗读者相似甚至相同的心理反应和情感共鸣。
例如: 在翻译张祜的《何满子》时:
(7)一声何满子,
双泪落君前。(张祜《何满子》)
译文:Singing the dying swan's sweet lay,
Oh!How can she hold back her tears![12]323
诗中,“何满子”是人们广为流传的历史人物,相传,沧州歌者何满子,临刑前高唱此曲以赎死,而皇帝并没有因为她的歌感人而赦她免死。后人以此作为词牌名,但英美读者对此完全陌生。许渊冲在翻译“何满子”时,借用了英语典故“the sweet sung by the dying swan”。在英语典故里,垂死的天鹅发出的甜美歌声与“何满子”被处死前歌唱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虽然在译诗语言表现形式上,二者差异较大,但二者的文化内涵相似。英美读者在读这首译诗时,能体会到原诗的意象与意境。
再如:中国古诗里常出现“东风”意象,“东风”意即春风,象征着春天与春日的和熙,然而,在英美文化里,“东风”却是寒冷,冰冻天气的象征。因而,在翻译中国古诗里的“东风”意象时,许渊冲教授巧妙地运用意象替换法:
(8)东风不为吹愁去,
春日偏能惹恨长。(贾至《春思》)
译文:The vernal wind cannot blow my sorrow away,
My woe increases with each lengthening spring day.[14]92
该诗写于诗人被贬时期,心情郁闷,诗人希望象征春天的“东风”能吹走他郁闷的心情。许教授用“vernal wind”(春风)替换“east wind”,意义明了,避免英美读者在读此诗时由于文化上的理解不同误解诗的意义。
许渊冲教授对中国文化研究颇为深入,因而在处理唐诗中中西方文化内涵不一致的意象词时,他能信手拈来,在文化维上的适应性选择处理得得心应手,既传递原诗意象,又能让译语读者轻易接受。
(三)交际维上的适应性选择
翻译过程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指的是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既关注原语系统里作者的总体交际意图是否在译语系统里得以体现,是否传递给了译文读者;又关注原语系统里包括原文语言、文化形式、文化内涵的交际意图是否传递给了读者,原文和译文的交际生态是否得到了最佳的维护和保持。[8]270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语言维、文化上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最终是为了实现交际维上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唐诗中,很多意象词文化内涵丰富,而英语里并没有相应的意象词与之对应,也无从替换,这时单单依靠语言维、文化上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已无法完成诗歌的翻译,抑或借助累赘的解释,也严重破坏了原诗的意境与形式之美,影响欣赏者的阅读兴趣。此时,就要通过交际维上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来完成翻译任务。 许渊冲教授在交际维上的转换通过以下具体方法实现:
1.具化意象词
(9)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李白《江上吟》)
译文:“If wordly fame and wealth were things to last forever,
Then northwestward would turn the eastward flowing river.[12]629
诗中,李白把功名利禄比喻成汉水,汉水向西北倒流是不可能的,比喻功名利禄不可能长久拥有。在诗中,“汉水”是地理类意象词,有其特殊指向,如果只是简单地翻译成“Hanshui River”,那么,它就成了一个普通的地名而已,或者直译之后加上累赘的解释,也必然影响诗歌的形美,影响读者兴趣。许渊冲在翻译时,进行了交际维上的适应性选择,采用“具化”的处理方式,直接把“汉水 ”译成”the northwestward”,传递其文化指向,完成读者与原诗的信息交际。虽然译诗中没有出现“汉水 ”的字面意思,然而它的深层文化内涵却得以全面展示,读者轻易便领悟到诗人对功名利禄的藐视。
再如:
(10)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杜牧《秋夕》)
译文:The steps seem steeped in water when cold grows the night,
She lies watching heart-broken stars shed tears in the skies.[13]322
“牛郎织女”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英语读者却不然。如果译者把“牵牛织女星”简单译成“Qianniu Star”和“Zhinu Star”,那么,英语读者必然把它们当成天上两颗普通的星星,丝毫感受不到个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同时,由于是诗歌翻译,译者亦不可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加注这两颗星暗含的爱情传奇故事,因而,这样的翻译影响了原语读者和译语读者之间的交际目的,无法实现交际维度的转换。许渊冲教授在翻译时,仍然采用具化意象词的做法,把“牵牛织女星”译成“heart-broken stars”,这样,既传神地译出了这两颗星蕴含的意义,又巧妙地实现了原语读者和译语读者之间的交际维度转换。
2.弃象译意
“砧”是中国古诗中的常见意象。古时,秋天一到,家家户户都会捣衣寄给远方的征人,所以秋天村妇捣衣时,捣衣之声响彻一片,此情此景最能引发读者思亲人怀故乡的情感。李颀在《送魏万之京》中这样写道:
(11)“关城树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李颀《送魏万之京》)
这首诗饱含着离愁别绪。“砧”的英语是“anvil”,但此词学术性太强,是中国特色文化物品,缺乏生活气息,英语文化中没有此物,故英语读者便不知“砧声”为何物,即使译者勉强将其解释出来,译文必然累赘臃肿,这与许渊冲教授追求的“三美”原则相离甚远,更不要期待读者会因此体味到诗中忧伤凄美的意境。故他将上面两句诗译为:
“Yellow leaves hasten the cold to come near.
Could washerwomen's song reach their men's ear? ”[12]180
如此一来,译者避免了对于“砧”这种中国特色文化物品的字面直译,而是直接将砧石的使用者引入译诗中,将“砧声”间接地表述为“捣衣妇人的哀歌(washerwomen's song ),“弃象译意”,转换了叙述角度,使诗歌译文更简洁明了,主题更鲜明突出,实现了读者与原诗的交际目的。同样,在翻译其他诗中的“砧”时,许渊冲教授采用同样的方法,“弃象译意”,转换了叙述角度,如:
(12)“玉户帘中卷不去,
捣衣砧上拂还来”(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译文:“She rolls the curtain up and light comes in her bower,
She washes butcan't wash away the moonbeams there.”[15]150
类似的译法在许渊冲教授英译的《唐诗三百首》中比比皆是,如:“布衣”译成“unknown talents”, “丝竹”,译成“melodious”, “婵娟”译成“beauty”,等等。
显然,“弃象译意”在某种程度上会折损诗歌语言的生动性和唯美感,然而是翻译就必有所失,译者不可能在毫无损失的情况下将作品译成另一种文字。所以,诗歌翻译过程中,在中西文化和文学传统交汇的有限空间里,译者有时只有以保全诗歌的整体意境为重,挣脱语言上的束缚,才能促成读者与原诗之间的交际顺利进行。实现交际维适应性转换的翻译就是成功的翻译。翻译本来就是一个创作的过程,译者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在此需要指出,虽然本文侧重强调了许渊冲教授在唐诗翻译中对意象词“语言、文化、交际”的“三维”适应性选择转换,这样处理只是为了便于把问题阐述清晰,翻译过程的适应性选择是多维度、多层面的,需要适应的因子也是多种多样的;而且,不同维度、不同因子、不同方面之间的适应与选择又都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
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解读了许渊冲教授在唐诗英译过程中对意象词的处理方式,旨在通过这种全新的诠释为许渊冲的唐诗翻译注入新鲜血液,也把翻译学研究推向深入。虽然在胡庚申教授提出“生态翻译学”理论之前,许渊冲教授已经进行了长期的诗歌翻译,但在他的诗歌翻译生涯中,早已有生态翻译的意识与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