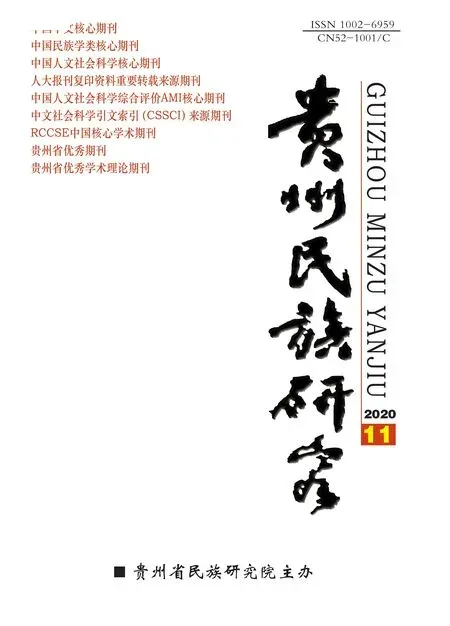文化共享视角下传统医学与现代知识融合探析
——以西南民族医教体系为例
2020-03-02邓玉函陈子华
邓玉函 陈子华
(1. 云南大学,云南·昆明650500;2.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南宁530006)
迈入“人类世”以来,人类对文化的探索已不再满足于辨识国家、民族之间的异同,而是逐渐步入知识与文化交糅、膨胀并拥有力量改变环境、改造自身的时代。与此同时,文化间差距也在相互依存、彼此参照中无可争议地缩小并走向交融。面对这一趋势,已有人类学者敏锐地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文化共享”的阶段,摒弃二元划分,消减彼此冲突、借鉴彼此特质将会成为文明发展的趋势,这终将会为人类通达彼此、启迪他者贡献力量与智慧[1]。事实上,这种文化层面的交流与互鉴并非新兴产物,其共享理念在近代史上也能看到类似的表达。如19世纪末,就有有志之士以“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为夙愿试图救国图存。在这样的社会思潮推动下,如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先后在20世纪早期被引入中国,并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始终以“西学”如何“本土化”服务于国家社会为己任,形成有别于西方的研究习惯[2]。随后衍生出的如发展人类学、科技人类学再到新近提出的乡村人类学,实际上也都是针对“传统与现代应当如何共存”这一世纪难题而形成的分支学科。
在这些讨论中,如何破解医疗知识体系中传统与现代对立关系是一项艰巨且又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有赖于从社会文化、生物文化、政治经济等视角对其进行整体地审视[3]。从生物视角来看,其挑战在于中、西医均拥有自身独特的生态与个体认识,这使得二者在医学理论、经验积累、教学传承上都存在差异;从社会视角来看,中、西医体系的认同也会因地、因人、因病不同而有差异。这些难以调和的差异使社会对中、西医学体系的取舍持有一种焦虑、恐慌与困惑的心态。如许多都市人虽身居现代环境,却在患疾时排斥西医,同样视中医为落后的也大有人在。而当我们从文化共享理念审视这一现象时,就会发现这些争议与困惑实际上都是产生于医学文化“因然”层面的不充分认识,人为地制造了二元划分的枷锁而忽视了医学人文特质中具有共性的一面。如果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的“多彩、平等、包容”文明观去看待二者,则会发现传统医术与现代知识具有能够彼此分享、合作的文化内蕴。也正是因为两套医学知识的互鉴并用,新冠肺炎疫情才能够在中国得到极为有效地控制[4]。因此,在民族医学已纳入国家科技、社会事业发展战略的今天,思考如何在继承传统医学精神、理论的基础上,推动民族医学与现代知识结合显得尤其重要。本文就想以西南民族医教为例,从人类学、民族学学科视角出发,对民族医学知识与现代知识协同发展途径进行探讨,以期对医疗教育改革、医学人才培养、社会响应等问题筹谋献策。
一、西南民族医学知识体系的传承特质
与藏族、蒙古族相对成熟、系统的医教体系不同,云、贵、川、桂等地民族医学知识由于民族分布、历史环境等缘故在过去仍处于一个零散、杂乱的态势。改革开放后,随着医学、民族学发展,西南民族医疗相关研究获得了较大地突破,医教体系取得相当进展,逐渐形成重视田野搜集、理论百家争鸣、师传与高校并存的特色教学体系。
(一) 民族医教重田野实践搜集
田野实践是民族医学教育、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别于西医重实验、重理论的研究模式,民族医学研究鼓励学者、学生进入西南、西北等民族地区,通过访谈、采集等方式进行医学探索工作,认识、厘清民族医疗体系,继而进一步探索医药的相关性、独特性。重实践的医教模式非常适合流散于民间的中医知识传承,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民族医学人才培养的实践模式,同时其教学实践过程本身也是对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过程。
从医教传承意义来看,田野实践的重要性可体现为3个方面。首先是在民族医学文化习得上。如成都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张丹就以藏彝民族走廊为研究区域,采用多点田野方法花费数年对嘉绒藏、羌、彝、纳西等民族的医药文化进行实地调研,揭示了生态、生物、文化多样性与地方医药知识发展的关系,其博士论文可谓是今天民族医药教育成果中的佳作[5]。其次是在药方、配料、草药的研习上。如研究生陈泂杉走访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深入调查了当地将玫瑰花作为药食同源植物的习俗,为其医药原理进行科学验证,验明当地玫瑰有抑菌、和血、解酒、美颜等医疗及康养的价值[6]。最后是对医学手艺的研习上。如本科生尹莉莉以云南大理白族传统正骨术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观察、访谈等方法分析了“飞龙正骨疗法”的形成发展历程[7],等等。可见,田野教学过程本身也是传统医学文化传承的过程,是人才培养中必不可少的“成人礼”,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与提升。
(二) 民族医学知识体系的理论百家争鸣
学科教育体系的形成取决于学科知识体系的搭建。今天来看,民族医学知识体系在学界数十年努力下已经初步摆脱混乱、模糊的态势,逐渐建构出基于民族自身话语的理论体系,为医疗教育规范化、系统化的开展创造了先决条件。然而,当前民族医学教育体系的构建并不均衡,而是因历史、环境、前期发展不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
第一种是形成相对独立的医教体系。其中,壮族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代表,如著名壮医学者黄汉儒经过多年调查与搜集,将壮医理念提炼为“阴阳为本、三气同步、三道两路、毒虚致病”等理论,奠定了壮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黄汉儒2001 年撰写的《中国壮医学》一书也不断重编再版加印,成为壮族医药教学中的重要基础读物[8]。就目前来看,壮医虽未形成藏、蒙那样的独立医学院校,但已经纳入地方中医学院成为区域医学理论的自然组成部分。第二种是以区域为单位囊括数个人口较少民族的医教体系。这一类研究中成果最多的要数云南地区,如苏玲丽在对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将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傈僳族、德昂族医药知识作为一个体系进行研究,其成果《德宏世居少数民族医药概观》已经纳入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民族研究特色课程指定教材[9]。此外,还有学者对如湖南、贵州的土家、苗、瑶、侗医药体系进行系统研究,提炼出具有区域特色的医药理论体系,这里不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种民族医学知识体系“百家争鸣”的态势存在发展不均衡、不完整的问题,但必须要承认这是地方知识在全球化文化影响下自我发展的体现,是地方文化提升与完善的必然阶段,与构建协调、统一的国家民族传统医疗体系实际上并不矛盾,具有“美美与共、和而不同”文化内蕴。
(三) 祖传、师传仍是民族医教的主要模式
在目前来看,虽然当代学院教育已成为少数民族医教的重要途径,但祖传、师传等民族医药的传承方式仍然不可忽视。赵富伟等在2008年时曾对黔、滇民族医学传承人进行调查,发现以祖传、师传方式习得的比例相当高(侗族85.3%、苗族85.7%、彝族88.9%)[10]。笔者认为,祖传、师传方式虽被现代社会视为一种落后、封闭的教学方式,但从民族学视角看,就会发现在文化层面上其对今天医教改革具有相当的启发作用。
首先,这一传承模式超越了技艺、药方知识传承的局限,能够在医教过程中起到西医难以企及的形塑个人修为的作用。如师门祖训中“六不治”原则,习“华佗之术”,对药材“死”“活”区分等等,这些理念教诲的重要性甚至高于药方、手法的传承,塑造了传承者术、德并举的崇高精神。正因如此,民族村落里有较大成就的医者,其个人文化修养也都是较高的,往往也是乡土村落中德高望重的人士。其次,祖传、师传模式能够更好地保证地方文化的完整性。由于传统医术形成与传统文化是同根同源的,祖传、师传过程实际上就是民族自身文化保护传承的过程。例如,韩玉茹等对西南苗医进行研究,指出其“一技一法、口耳相传”教学方式不仅是技巧、禁忌的相传,实际上也是对自身苗族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的讲述,保证口述药史的完整即是苗族自身生态伦理思想的延续[11]。最后,传统医学中经验性的一面决定了师传、祖传教学模式存在的必要性。如医药理论对气候环境、植被、爬虫、动物的认知,对病理的辩证观察,对治疗仪式的掌握等都有赖于对生活实践进行总结。总的来说,祖传、师传模式纵然因缺乏标准、神秘性等而被诟病,但其形成也有着文化层面上的必然性,正确、客观认识这一模式背后的文化机理是处理好传统医学知识传承与创新的关键。
二、现代知识对民族医疗教育的冲击
纵然民族医教具有诸多符合地方文化逻辑的特质,但在当下也难免陷入传统与现代技术二元对立的关系中,在发展中遭受不公平、不平等待遇,并呈现出传承的不适。从民族医学学科体系建设、学科社会认同等方面来看,其面临的社会挑战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首先,现代科学体系难以支撑民族医学教育的发展。医学人类学者凯博文曾指出,亚洲医疗体系是民间信仰、活动、观念、知识的统合,它们既包含了神圣的仪式,也包含了世俗的草药认知,是不可分割的[12]。同理,民族医药如果在发展中缺失了如苗族“树、土、水”三界生态论,以及壮族龙母文化思想,那么其传承与发展无疑就面临缺乏基础知识支撑的窘境。另一方面,在生物、解剖、化学等近代学科知识发展下逐渐形成的西方医学则具有庞大、系统、严谨的科学背景。从大学系统教育来看,西医不仅有基础、临床、卫生、药学门类下的数十个二级学科,还与生物、化学、病毒、制药等学科关系密切。相比之下,民族医药教育不免显得“势单力薄”,部分院校民族医药教育仅归属于民族学门类下,关联学科极为缺乏。
其次,现代技术优势使民族医教陷入“内卷”态势。“内卷化”最早是形容传统文化面对外来冲击下陷入一种虽然不断精细化,却难以突破框架的困境[13]。对于传统医学教育体系而言也是如此,民族医药辩证方法繁多,其保护与传承处于“口传心授”“多经验少科学”的态势[14],虽然目前来看,各民族医学看似都构建了自身知识的话语体系,但这对构建一个标准化、系统化医疗教学体系也同样会带来极大挑战。另一方面,现代医学技术具有标准统一的优势,这既体现在诊断流程、治疗设备上,也体现在药剂研发、生产上,这极大地方便了医学教学体系的搭建与实践,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能够在疾病研究中相互交流,谋求合作、创新与发展。相较之下,传统医术却因缺乏系统体系而缺少对外交流,甚至时而有产生理念、门系、路数之间的争斗。
最后,当代新兴健康问题对民族医疗带来新的挑战。受历史、经济、社会等要素制约,当今民族医学的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其医学临床实践主要停留在发祥地而少有在外地大城市扎根。据卫计委调查所示,90%以上的民族医院集中在西部地区,而较少在沿海发达城市[15]。其医教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停留在搜集、整理、验证民间方剂上,科研成果很少有发表在非民族院校的期刊上。这导致传统医疗知识面对都市社会新的健康疾病问题(如现代社会压力导致的心理疾病,化学污染导致的诱发疾病等) 时因其理念滞后、观念偏差而难以作出及时的应答,难以累计足够的临床经验,人才培养逐渐偏离时代需求,继而致使人们面临健康问题时不得不转而求助于现代医学。
三、民族医疗传统与现代协同的发展机制
现代知识体系对传统知识教育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医学被现代知识更新或替代。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发布《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就从标准化、需求化、人才化等方向明确了深化医教改革的路径。与此同时,如张伯礼等医学专家也在积极地对中西医诊疗过程中的跨界结合、互补进行详细的探索,肯定了二者医疗技术层面整合的积极意义[16]。对此,笔者想从民族学、民族医药教育的角度出发,对民族传统文化体系在后疫情时代的传承、创新做出进一步讨论。
(一) 现代知识对增强民族医教实践的寓意
田野调查往往因其不确定性、缺乏科学依据而被看作边缘化的“迂腐”教学方式。然而,在时代带动下,今天的田野调查早已摆脱“认识他者”的第一阶段,也超越了单一维度“自认科学”的第二阶段,步入了“反思科学”的第三阶段[17],旨在以开放、多元精神的寻求传承创新的结构性突破。
对于民族医学来说,这种田野反思意义在于它让实地调查从单纯的药剂、药方研究转为对遵从天人合一、传统信仰等民族文化内涵的研究,为民族医药文化自信寻找根基,让调查本身成为民族社会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对此,庄孔韶教学团队的凉山彝族研究是个很好的例子,其针对民族地区禁毒、防艾问题进行研究,搜集的资料展示出民族医学知识背后的民间信仰与文化,揭示出民族文化自信才是医学知识背后的真正的支撑体系[18]。另以笔者自身教学经历为例,笔者教学团队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西南民族地区疫情防控进行研究,发现除了民间医药实践运用外,如民族熟人社会、民俗信仰、自然观念等也都在疫情阻断过程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如广西侬峝村就在疫情早期时通过鸣响炮等仪式希望能驱散病魔,阻隔疫情。响彻整个村落的炮声不仅是表示着群众的集体决心,更传递出防控疫情的重要意识。又如龙州一带民间艺人还将抗疫措施与壮医药中康养要点相结合改编为山歌,以当地人耳熟能详的方式将疫情防控的重要讯息传递给人们。这些乡民的自发行为看似虽不属于医学,但事实上却是民族医药大健康理念下社会实践的衍生,同时又是民族医药知识的文化支撑,所折射出民族精神的文化机理更是不容忽视。
(二) 以现代知识带动民族医疗体系的整合
全球化使人们越来越多地遭遇到一些不曾有过、或者不曾那么严重的健康问题,这对于陷入“内卷”发展的民族医药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挑战,但这同时也赋予了民族医学突破“各自为政”态势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从而促使不同民族知识体系在解决共同社会问题上彼此互鉴互补、并构共生。
在人类学来看,这种传统知识体系突破自我框架越界交流、发展并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突破“内卷”的过程,是地方知识在外界冲击下做出的积极响应的表现[13]。以各民族医药知识体系对“亚健康”问题的介入为例,亚健康概念起源自20世纪90年代社会工作压力、环境污染、安全恐慌下的集体性焦虑态势[19],其虽源属现代社会新兴健康问题,但实际上却与民族医学中“末病”“阴阳失调”概念相似。围绕亚健康问题进行民族医学研究,能促使各民族医学中存在认知差异(如语言、措辞、环境、草药认知差异) 的知识体系得到整合,进一步在医教过程中对亚健康问题进行药方、诊断、康养的讨论,以便能够使医教体系获得系统化的突破[20]。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同样赋予了民族医药理论体系系统化的契机。疫情期间,如广西中医药大学、云南中医药大学等就积极投入民族医药方剂研发,深入走访地方,制定符合民族文化的治疗方案,采用如壮、瑶医药方剂提升群众自身免疫力抵抗病毒,这不仅为西南地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中医药力量,也为地方医药方剂、民间医学理论创造了整合与创新的机遇,促使医教改革迈上新的台阶[21]。可见,现代知识的冲击虽然对民族医药带来了新的挑战,但不同的诊断与理论体系也得以凭借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交融在一起,从而在彼此互鉴、交糅的态势下实现医学知识体系的整合与创新。
(三) 现代知识推动民族医教体系的创新
人们往往认为民间知识与信息化、智能化关系不大,然而,只要运用得当,诸如大数据、区块链、云处理是能够为民族医药教学改革做出贡献的。就目前来看,许多民族国家都已开始对其自身的民族医教信息化体系进行研究。如Sinkala对非洲部落草药信息体系建设进行研究,指出云端技术极大地提升了传统知识向市场知识转化的效率,其经济回报是难以估量的[22];Finetti对印度传统知识电子图书馆进行研究,指出其在云端整合了阿育吠陀、尤那尼、瑜伽等疗法,将传统医疗知识汇编成为系统文献,从而方便了印度医疗的传承与创新[23]。
对于中国民族医教来说,信息化、智能化也已经初步融入学院教育当中,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各医学院校就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课堂在线教学,当然,教学信息化的应用并非仅限于此。笔者认为,这种医教云端化将会有3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节约民族医药教学资源。对于民族草药、药方搜集、整理方面,云端化能够在教学、研究过程中节省人资物资方面的成本。如曾商禹指出,信息化平台对于藏药、彝药不仅有数据储存优势,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因炮制、别名、译名带来的麻烦[24],避免了教学资源的浪费,意义颇大。二是在医疗实践上对教学带来了帮助。采用区块链技术的教学模式,能够让学生通过处方的链接对比发现其中的规律,分析民族处方的各类信息特征,提炼出理论经验中蕴藏的新理论、新方法、新知识,实现对少数民族医药技术的有效总结与传承。从实例来看,赵艳青团队就在科研过程中通过数据链对比中医358首方剂,最终让传统医学在制约抑郁症上获得了突破[25]。三是在医药教学成果创新上获得突破。据悉,如广西、云南中医学院就在传统教学中开办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和医学信息工程专业,在课程中引入了模块化机器人编程课、VR虚拟现实药材互动设计课、医院HIS(PACS) 系统实践教学课,这些信息化手段的介入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启迪有了很大的帮助[26]。
总而言之,提升民族医学知识的文化价值,寻求其传承、发展途径是今天民族学、医学界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对民族医学知识的保护与传承既不能简单地拒绝现代知识体系,更不能一味否定传统文化,而要从更高的“文化共享”层次出发,认识到传统与现代社会交融互鉴的可能性。鉴于此,从田野实践到知识体系,再到医教体系,寻求传统医学与现代相契合的协同发展机制,则能够适应当代人才培养与社会健康形势的需求,并由此使民族医疗传承创新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