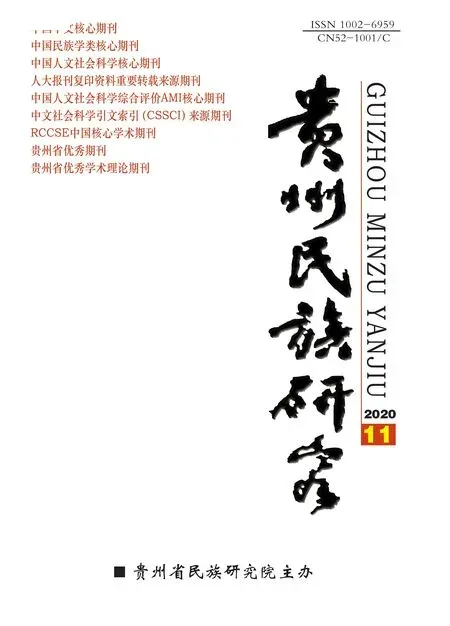组织再造与文化接续:后脱贫时代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研究
——以广西上林县壮族F村为例
2020-03-02何明方坤
何 明 方 坤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昆明 650091)
一、问题的提出
2020 年是我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关键节点,后脱贫时代乡村振兴将面临与脱贫攻坚紧密相连而又迥然不同的发展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伟大成就,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累计减贫9348万人,年均减贫1335万人[1]。随着越来越多贫困村脱贫出列,脱贫村基础设施、治理能力、农民技能都得到很大提高,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基础[2]。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实现后,以“第一书记”为主导的驻村帮扶机制将逐步转化为村落内生活力驱动机制,乡村振兴内生动能转化和特色文化发展目标将更为凸显,“留住乡村”成为了新时代“三农”问题的关键议题。民族地区分布着大量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脱贫村,是影响我国乡村振兴整体推进的重要板块。推动社会工作介入民族村落乡村振兴,不仅可以帮助脱贫村摆脱对政府资源的依赖,而且能够激发村落内生活力和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这是后脱贫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确立以贫困村瞄准为重点推进的开发式扶贫后,社会工作开始逐步介入“老少边穷”地区扶贫项目,相关学术研究也逐步兴起。一是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扶贫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社会工作能够克服传统救济式扶贫的不足、提升扶贫对象能力,在农村扶贫中有广泛需求和空间(向德平、姚霞,2009年)。当前农村脱贫攻坚要建立政策安排、政府能力、贫困群体能力各方协调的制度-能力整合模式,社会工作在关系协调、精准性、可持续性方面有重要作用(王思斌,2016年)。打赢脱贫攻坚战为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机遇和发展空间,社会工作在理念、方法等层面有着专业优势与功能(李迎生,2016年)。但也要认识到农村贫困问题的复杂性,以便推动构建适合社会工作发展的多层次制度体系,从而克服“无能可扶”与“无业可扶”下的优势视角失效(庞飞、陈友华,2019年)。二是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农村扶贫的原则与方法。内源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原则,强调尊重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文化建设、生产发展、协同治理是培育农村贫困地区内源发展动力的基本途径(芮洋,2018年)。运用社会工作的个案、小组、社区等方法能够与各民族文化习惯有效对接,推动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的贫困治理(胡阳全,2013年)。要发展以主体性培育、能力建设、组织建设和文化建设为内容的农村反贫困社会工作,形成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共治的农村贫困治理新格局(钱宁、卜文虎,2017年)。三是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农村扶贫的实施路径。社会工作为民族村寨精准扶贫提供人本、文化、发展、优势等多重视角,民族村寨精准扶贫需要从价值原则、工作方法和评估机制等方面全方位借鉴社会工作(岳天明、李林芳,2017年)。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扶贫需要在主体参与、社区营造、社会支持网络上发挥专业功能,在扶贫理念、理论视角、过程管理上拓展价值伦理,在人才培育、服务补位、发挥系统效应上实现与精准扶贫的良性互动(席晓丽,2018年)。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扶贫要坚持以赋权增能与系统建构为核心的实务模式(徐立娟、刘振、田雄,2020年)。
以上既有的研究肯定了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扶贫的功能和价值,但也存在拓展空间:一是多着眼于整体层面的原则、方法、路径分析,缺乏对民族地区具体实践的个案观照;二是认识到社会工作在与民族文化对接中的优势,但并未呈现具体民族文化特性对农村扶贫的影响及相关对接过程;三是多关注社会工作对农村扶贫的长效作用,但缺乏对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化情景下社会工作介入机理的探讨。因此,本文将以广西上林县壮族F村为例,通过对K社工机构介入该村脱贫攻坚的过程、方法的深入挖掘,立足壮族村寨传统文化整体特性,梳理社会工作与村寨文化对接的具体逻辑,探讨后脱贫时代社会工作介入民族村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为此,课题组于2019年7—8 月、2020年5月多次赴上林县民政局、F村进行实地调查,对相关民政局干部、F村村民与村干部、社会工作者进行了多次深度访谈,并运用参与式观察法在F村搜集了诸多一手资料,力图了解K 社工机构参与F村脱贫攻坚的整体过程与实效。
二、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践:F村的过程表达
K 社工机构是受上林县民政局委托,以项目形式介入F村脱贫攻坚的。项目运行始终围绕村落整体展开,并对村落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 F村概况与社工项目的村落基础
F 村是“十三五”广西整村推进的贫困村,是2018 年脱贫攻坚摘帽村。截止2020年初,贫困人口剩余15户39人。该村位于上林县Z乡东南部,地处大石山区,距乡政府12公里。全村均为壮族,有8 个经联社,17个自然庄(屯),24个村民小组,736 户3045人。
一是产业基础。耕地面积1521.04亩,其中旱地1468.75亩、水田52.29亩,人均耕地面积0.5亩,主要种植蚕桑、果树、水稻和杂粮。除了传统的种桑养蚕和玉米种植产业,还建成光伏发电项目、扶贫车间、肉牛、生猪和黑山羊养殖等多种特色产业。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外出务工,常年有600余人在南宁、北海等地从事装修和建筑业,201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500元。
二是文化基础。该村流传至今的“霸珠之恋”传说,是上林传说中大明山名称由来、大明山北麓形成、重阳补粮添寿习俗的重要源头,为这一区域壮族群体广泛熟知。“重阳补粮”习俗作为壮族孝老文化重要仪式部分,属上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该村得到较好保护传承。“八狮成佛”故事糅合壮族族源传说和佛教教义,将该村起源与周边八座山峰相联系,形成每年固定的舞狮文化仪式。围绕这些传说和仪式,该村培育形成2个民间表演艺术团,经常应邀到东南亚国家及港澳等地演出。
三是治理基础。该村现有党员44名,其中女党员7名。村“两委”组织完备,共有“两委”干部7人,并在每个自然屯配主任1人,由屯内“五老”人员兼任。南宁市政协为该村帮扶后盾单位,国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光明地产) 为结对帮扶企业。
(二) 社会工作介入的过程表达
K 机构全称“南宁市K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依托广西X大学社会工作系师资力量成立的一家为城乡弱势群体提供专业服务的机构。该机构于2018 年5月中标承担上林县民政局委托的总价30.5万元的“上林县Z乡F村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项目”,要求在2018年6月至2020年6月期间协助地方政府完成F村脱贫攻坚,并总结出可在全县推广的经验模式。
K 机构的介入可分为6个步骤:一是目标规划。K 机构在接到项目中标信息后,即派人与F村“两委”联系,了解村落整体概况,根据项目合同要求制定更为详细的目标规划与实施细则。二是走访建档。2018年6月,K机构在F村村委会租用场地设置社工服务站,派遣4名专职社工人员,对贫困户人员的个人、家庭、生产系统状况进行走访排查,了解其基本信息、工作生活、社会保障、社会评价、社会参与、优势资源状况并建立档案,形成需求调研报告。三是社工行政。从项目开始K 机构就不断加强与F村村委、Z乡政府、上林县民政局的信息沟通,主要是报告社会工作服务总结,请求获得相关支持。四是社工服务。主要运用个案、小组、社区等专业社工方法为F村贫困户和相关村民提供具体服务。五是资源整合。借助上林主流媒体进行项目宣传,在F村内外获得普遍认同后,积极进行相关资源整合,在村内动员村委会、村小学、文艺队和居民参与服务活动,在村外向所在高校志愿服务队、相关慈善公益基金和地方政府寻求人力物力和资金支持。六是社区营造。一方面,积极培育青少年志愿服务团队、“五老”协会和中老年文艺服务团队,夯实村落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围绕“八狮文化”进行故事挖掘和演绎,开展相关文艺活动,提升村民文化自信。
(三) 项目效果及对F村的影响
项目运行至今,取得了较好效果。一是服务对象对扶贫政策的认识、个体人际交往能力、生产生活技能、自主性意识和自信心等均得到较大的提升,并有部分服务对象转化为村落志愿者。二是村民对社工职业定位清晰,村落志愿服务氛围初步形成。通过社工对其职业有意识的传播和项目服务引导,村民对社工职业有了清晰认识,并对社工人员及其服务产生信任,积极配合、参与社工服务,形成较好的志愿服务氛围。三是社工引导下的村民自助互助平台和行为出现,以“五老”为主体的传统村落权威得以凸显,村民在种桑养蚕交流中形成相对固定的团体,社工在二者中的行为和作用都逐步弱化。四是村落传统文化得到传承,村民自信得以增强。通过社工引导村民挖掘村落“八狮文化”,结合村落文艺活动进行社区文化营造。
三、组织再造:村落权威的内生力量激活
K 机构能够顺利介入F村脱贫攻坚并取得较好成效,在于契合了村落自身的组织化发展需求。随着“打工经济”兴起,F村也面临着人口“空心化”困境,村“两委”自治组织和传统寨老组织均有所涣散。在“第一书记”推动强化村级党组织和自治组织建设后,K机构介入则进一步提升了F 村组织化程度,并激活了村落内生力量。
(一) 村落组织再造的基础
K 机构在F村脱贫攻坚的介入是以“第一书记”对村“两委”组织重建为基础的。在南宁市政协派驻“第一书记”莫某的推动下,F村于2015年配齐了“两委”干部,并对17个自然屯主任人选进行重新确定。K机构掌握的该村产业状况和贫困户第一手材料,就是“第一书记”带领驻村工作组和村“两委”组织搜集的。在K机构的整个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村“两委”和各屯主任在联系村民、协调村外资源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K 机构介入初期的F村脱贫攻坚主要依靠村“两委”正式成员和各屯主任,未能将村落其他党员、“五老”、中青年能人纳入相关组织。“八狮”文艺队和“佛子”文艺队是村落两个主要社团组织。
村落组织基础重建离不开村级权威,其分布符合韦伯提出的权力、财富与声望三种类型划分。与村“两委”干部这种正式权力权威类型相对应的是传统“五老”、村医村教、新兴致富能人等非正式权威。F村作为壮族村落,其传统孝老文化得到很好传承,寨老和其他“五老”在各屯日常生活中具有很高道德权威,尽管中青年大量外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长老政治”的组织基础,但道德权威的组织动员能力依然较强。随着种桑养蚕、果树种植和肉牛、生猪与黑山羊养殖等特色产业而发展起来的致富能人,兼具种养专业技术知识和外部市场关系与适应能力,是F村的财富权威。同时,村医村教因其专业知识提供的公共服务,积累起良好声望,也属于地方权威之一。
(二) 社会工作介入村落组织再造的内在机理
一是以村“两委”干部为主体的组织动员。在社会工作项目介入初期,上林县民政局购买方的身份,使K机构在村落中被视为与“第一书记”同等的官方代表。这种被“误读”的角色强化了K 机构的村落权威性,村“两委”干部在信息提供和组织动员方面都给予了社会工作站很大程度的配合。在对贫困户入户调查和个案工作阶段,村妇女主任被指派协助社会工作者开展相关工作。正是妇女主任作为村落正式权威代表的“在场”,使得社会工作者及其服务内容为村民所接受。在政策宣讲、技能培训、安全教育等小组工作中,村支书和其他“两委”干部也积极按照社会工作站的需求参与活动。各屯主任也在社会工作者赴本屯开展服务的过程中全程在场。这些村级正式权威主体的支持,有效推动了社会工作服务中的组织动员,确保了K机构的顺利介入。
二是发挥寨老和“五老”日常道德权威作用。F 村村民日常生活多以单姓自然屯为单元展开,每屯均有其寨老,壮语称“波板”,至今依然负责组织本屯社会治安、纠纷调解、神灵祭祀。寨老每三年选举一次,由本屯人从“五老”中推举产生,被视为是屯内最高荣誉。孝老文化传统保证了寨老在屯内日常事务中的权威性,尤其在屯内纠纷调解中具有不容置疑的话语权。其余“五老”则配合本屯寨老和主任进行相关事务处置,而日常参与中累积的个人声望则有助其在下一轮选举中成为寨老。社会工作站将寨老制进一步整合为老年协会,鼓励普通老人积极参与屯内日常事务,增强老年群体组织性和对屯内困难老人的救济。
三是凸显致富能人的产业带头作用。F村致富能人有5位,其中2位分别是蚕桑、肉牛的种养能手,2 位是演艺团体负责人,1位是建筑队包工头。社会工作介入后,服务人员在村干部帮助下,积极动员这些致富能人将帮扶对象从本屯扩展至全村,进行种养技能、文艺才能、建筑装修技能方面的培训和就业带动。尤其是种养合作社和演艺团队对贫困户的吸纳,进一步增强了贫困群体的自信心和交往及生产生活能力。
四是重视贫困户群体意见领袖的培育。社会工作者将贫困户分为留守青少年、困难妇女和老人等三类群体,根据不同群体需求组织相应的个案辅导、小组活动和社区活动。通过小组活动将原本分散在各屯的贫困户组织起来进行心理疏导、政策宣讲和技能传授,发现意见领袖。通过社区活动,将贫困户与本屯普通村民融为一体,培养意见领袖组织和帮扶贫困户的社交能力。除老年协会外,蚕桑、肉牛这两个种养合作社也产生了以中青年已婚妇女为主的意见领袖,强化了贫困户在合作社的组织参与。
五是强化村医村教的参与。F村现有村卫生所医生2人、村小学教师12人,均位于中心屯,村医村教活动也集中于此。社会工作者介入后,积极动员村医赴各屯为妇女进行卫生健康讲解和对困难老人上门诊治,陪同教师对儿童进行留守家访和课后及假期义务辅导,强化村医村教在村落公共生活中的参与。
(三) 各主体行动的动因与逻辑
一是社会工作组织的专业引导。社会工作者在村落服务中为凸显其专业性,往往刻意强调其非官方背景和与“第一书记”工作内容及方式的差别,“其实就是合同任务驱使着在做,辛苦肯定是蛮辛苦,但我们有专业理念和优势,有成就感”。可见社会工作者的动力主要在于专业理念和任务压力,而专业方法带来的优势是其行动的重要支撑。
二是村落非正式权威的荣誉感与责任感。对寨老、“五老”这类传统权威而言,孝老文化赋予其在村落中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服务村民是其维护既有地位和实现声望“竞争”的重要方式。“屯里大大小小都这么看重你,不做点事,自己也觉得不好”。被认同的荣誉感和责任感驱使这一群体积极担任“两委”干部、屯主任之类角色或配合这些角色为村民服务。致富能人和贫困户意见领袖这些人主要在社会工作者引导下参与对困难群体帮扶,被帮扶者的感激和认同成为其持续行动的重要来源。这些非正式权威力量的激活,强化了村落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是贫困户和普通村民改善自身状况的诉求。贫困户普遍存在心理自卑、社交能力差、技能缺失的困境,而普通村民也存在一定的心理焦虑和技能需求,社会工作者提供的专业、具体、微观的服务方式和内容,更能给予个体以情感关怀和社会支持,因而容易为村民所接受和认可。贫困户和普通村民对社会工作者的态度普遍经历一个从疑虑、好奇到信任的过程,这个心理变化过程是以其自身需求满足为基础的,因而其参与具有很强的需求导向性。
四、文化接续:在地文化资源的社区营造
社会工作以项目形式介入脱贫攻坚,不仅要帮助贫困户脱贫出列,还要考虑防止返贫与参与社区发展问题,这些都指向村落整体的社区营造。社区营造重在促进社区自组织生成,以此自主解决社会福利、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等问题,需要政府诱导、民间自发、社区组织帮扶[3]。对F村这样的山区脱贫村而言,社区营造更是构建“韧性社会”的过程,使社区具有足够的恢复力来应对灾难和反常规现象的威胁[4]。
(一) 村落文化资源分布与社区营造的基础
社区营造的本质就是构建社区共同体,包括建筑景观构成的物理空间和历史文化认同构成的心理空间。K机构通过邀请X大学青年志愿者团队到F 村支教调研,绘制了村落资源地图,摸清了该村景观、习俗、信仰等在地文化资源分布,成为社区营造的基础。
一是“霸珠”“八狮”景观及其传说。F村所在上林壮族群体也将大明山主峰称为“霸珠”山。当地口头传说认为,天庭龙珠遗落大明山主峰,长成巨型山脉,后为智慧之神拉克发劈进山体,进而有八狮跃出,吼声震天,即为今大明山(大鸣山) 和F村周边八座山峰。后来八狮为保护F村免遭山洪侵袭,形成今日拱卫村庄态势。F村现有拉克发神祠一间,位于中心屯最西端,有2名师公兼职打理,是村落祭祀和重要活动场所。
二是良好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化资源。F村中心屯位于拉克发河与母狼河交汇处,来马高速路穿村而过,其余16个屯则在2条河下游沿河而居。山谷河流汇聚处优良的生态环境孕育了传统稻作农业模式,周边山腰地带则以果树、桑树和玉米、红薯种植为主。因山地开发难度较大,人口聚居在河流谷地,八狮山上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这也为村落发展牛、羊、猪养殖业提供了基础。
三是寨老制的社区结构与孝老文化规范。F村17 个屯均每三年一次选举寨老1~2名,相邻或同姓的3~5个屯之间每三年选举联屯寨老1名,村级层面同样三年选举联村寨老1名。寨老有时由村屯干部或师公兼任,其职责主要在于社会治安、纠纷调解、神灵祭祀,主要依靠个人道德权威和人格魅力说服。壮族孝老文化为寨老制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F村每年都会在拉克发神祠为村中60岁以上老人举行重阳补粮添寿仪式,为老人祈福消灾。
四是村落舞狮文化传统。F村凡有重要节庆或活动必定舞狮,并形成了两个以舞狮为主的民间文艺团体。这两个团体分别由拉克发河与母狼河的几个屯联合组建,规模均在20人左右,带有一定的村内竞争性质,外出演出则以同一团体身份前往。
(二) 社会工作介入村落文化营造中的内容与方式
F 村的社区营造是在当前主流模式基础上,立足村落既有文化资源而形成的。从民政部《关于做好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通知》 (民函[2006]288号) 发布以来,各地开始借鉴相关先进经验开展农村社区营造,台湾“行政院”2005年核定的产业发展、社福医疗、社区治安、人文教育、环保生态、环境景观“健康社区六星计划推动方案”逐步成为人们广泛认可的模式。F村的实践正是以此为蓝本,提出了生态种养、互联共享、互助互乐、乡土空间、乡风文明5个方面的营造内容。
一是生态种养,致力于老品种、老农技传承和构建农业生态循环链。社会工作者借助K机构外部资源,积极将F村的土豆、红薯以及土鸡、土鸭、土猪、黑山羊等推介至X大学“教师吃货群”以及周边菜市场,以此带动村民采取传统农业技术种养老品种。同时,针对蚕桑、猪牛羊养殖、水稻种植等各自为政的局面,以及种养合作社规模扩大后带来的牲畜粪便污染问题,K机构积极联系N大学农业系,为F村引入红蚯蚓和黑水虻进行牲畜粪便腐熟消耗,腐熟后的牲畜粪便用于水稻、杂粮和桑树施肥,红蚯蚓和黑水虻作为养鱼饲料,蚕沙作为猪牛羊饲料添加,桑叶残渣加入牲畜粪便腐熟后肥田,实现村落种养生态循环。
二是互联共享,强化合作社组织村民生产和连接城乡集市。K机构针对前期蚕桑、肉牛这两个合作社组织松散、技术滞后、市场能力差的困境,积极引导合作社进行股份化改造,鼓励贫困户以劳动力或土地、厂房、蚕桑、肉牛等生产资料入股,强化集中种养和清洁生产,引入N大学农业系和上林县农业局开展技术培训,协助合作社负责人开辟周边集市销售渠道。同时,针对蚕桑一年两季、肉牛一年一季特点,K机构积极协助上林县农业局专家引导村民错时发展生猪和黑山羊养殖合作社,充分利用全年农时增加村民收入。合作社内部关系理顺后,生产流程更加规范,城乡集市也逐步打开,村民也能顺利共享合作社发展的成果。
三是互助互乐,发展志愿服务和激活三大困难群体互助。按照合同要求,K机构要培养至少2名本地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K机构采取适当补贴形式,已吸纳本地青年女教师1名和已婚女青年2名成为社会工作者,并由这3名本地工作者牵头组织固废垃圾清扫、贫困妇女茶话会、留守儿童安全培训等社区和小组活动多次。以各屯寨老和“五老”为主体的老年协会,也在村落纠纷调解、生产生活互助、文艺活动中起到主导作用。
四是乡土空间,增强公共空间文化氛围。K机构联合“第一书记”向南宁市政协、光明地产和相关慈善基金募集到20万元资金,用于村落篮球场、拉克发神祠、村小学体育场和村主干道的修缮,为村民公共活动提供便利。尤其是联系X大学美术系师生赴F村写生创作,将相关作品在篮球场周边宣传栏持续展出,美化村落公共景观,提升其文化艺术氛围。
五是乡风文明,强化历史记忆与现实生活的接续。K机构将村史、村神、文艺的传承,作为F村乡风文明建设的重点。在村史整理上,结合当地老人口述,先后梳理出“霸珠之恋”“八狮成佛”“重阳补粮添寿”等传说文本,并已经创作出相关文艺演出剧本。在村神作用上,协助师公、“五老”等整理拉克发神传说、进行八狮山命名和文化挖掘、组织相关仪式活动,尊重村民对拉克发神和八狮的信仰,注重仪式对村落文化的凝聚作用,以及信仰传说对孝老文化的传承。在村落文艺上,鼓励舞狮文艺团体成员带领村民在篮球场和各屯空地开展广场舞、演艺排练,组织村民进行八狮山拍摄和“最美狮山”评选等活动,活跃村落文化氛围。
(三) 多元主体参与下的文化生态延续
F 村的社区营造是在K机构引导下,由项目购买方、帮扶部门、帮扶企业、城乡集市、村“两委”和村民共同推动的。整个营造过程以村民尤其是贫困户的组织化参与为前提,重视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接续。一是项目购买方的实际支持。上林县民政局作为购买方提出了F村脱贫攻坚具体目标,帮助K机构进入F村,并协助机构向Z乡寻求帮助,其权力背景保证了社区营造顺利进行。二是帮扶部门和企业是外部资源重要的供给者。在公共设施修缮、贫困户资助等大项支出中,南宁市政协和光明地产均为主要出资者,尽管其资助行为是政治压力下的被动选择,但仍对项目实施起到重要作用。三是城乡集市是村落外部连接的重要渠道。社会工作者引导下的城乡集市连接,不仅保证了村落产品销售和产业价值实现,而且促进了村民与外部现代文化的交往。四是村“两委”和村民是社区营造的中坚力量。村民的需求和意愿决定了社区营造的方向,“过美好日子”愿望和孝老文化、寨老制等丰富传统资源的存在,使得村民必然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追寻现代生活方式。村“两委”领导下的老年协会、合作社等组织兼具现代形式和传统关系,作为营造活动中的主要参与形式,也决定了村民行动中传统与现代并重。五是社会工作者是社区营造的关键引导。K 机构带来的“助人自助”理念,对村落的组织再造、产业优化、志愿激活、文化培育,都是为形成社区共同体意识,增强村民的社区认同感和互帮互助能力。整个项目过程中不断培育本土社会工作者、组织权威、意见领袖,就是为了以组织化方式增强村民尤其是贫困户自我能力,实现村落自身互助文化生态的激活和延续。总之,F村社区营造离不开多元主体参与,尤其是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引导。但整个项目实施也是逐步凸显村民主体和其他力量渐次退出的过程,村民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组织化的互帮互助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接续,增强个体和群体适应现代生活的能力。
五、留住乡村:后脱贫时代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反思
通过对社会工作介入脱贫攻坚过程的考察,以及对多元主体行动的基础与逻辑的分析,我们发现社会工作对乡村文化资源的重视,以及专业工作方法的运用,使其在乡村组织化和社区营造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能有效弥补政府单一主导下精准扶贫治理所存在的困境,从而为后脱贫时代乡村振兴提供一条新路径。
社会工作介入脱贫攻坚是一种典型的参与式发展方法,尊重弱势群体意见,维护当地人文与生态环境,将对“他者”的关怀落到实处[5]。社会工作组织及其成员在脱贫攻坚中并不是绝对主导,而是理念和方法的引导者,通过对弱势群体自主意识唤醒、自主能力激活,达到改变自身困境的目的,并通过重建社区支持系统以满足其对发展的需求。F村多名贫困户都是在社会工作者进行的个案工作咨询中,重新认识和评价自我,发现自身优势,走出悲观情绪,并利用社会工作者整合的村落就业机会进入种养合作社,实现对村落生活的重新融入。小组、社区等工作方法的运用,则帮助贫困户重建社会支持系统,进一步增强其社会交往能力和生产生活能力,通过个体增能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强调对贫困户个体意识与能力的双重提升,达到了精准扶贫所要求的“扶志”与“扶智”之目的。
社会工作介入脱贫攻坚的有效实践,离不开“第一书记”主导下精准扶贫提供的前期基础。在“第一书记”主导下,村“两委”组织、村落基础设施、贫困户境况都得到很大改善,为社会工作介入脱贫攻坚提供了重要基础。尤其是村“两委”这一正式组织的强化,使村落恢复有序状态,为社会工作机构介入村落及引导建立其他非正式组织创造了必要条件,进而为整体社区营造提供了可能。组织再造始终是社会工作介入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只有将村民组织起来,才能重建贫困户的社会支持系统,实现个体增能。无论是“第一书记”还是社会工作机构,村落组织重建都是其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二者不同的权力背景决定了各自在参与村落组织重建中的作用的差异。“第一书记”的政府部门背景决定其在精准扶贫中的绝对权威地位,但也限制其与村民交往的灵活性,因而只能高度依赖村“两委”这一正式组织进行资源输入,在后脱贫时代的内生活力激发上很难发挥有效作用;社会工作机构的非官方身份及其专业理念与方法,使其能够与村民平等交往,从而能够引导村民自发成立各种非正式组织以实现内生活力激发,但这一功能发挥必须以村“两委”正式组织的有效行动为前提。
社会工作介入脱贫攻坚要注意其适用限度。K 机构能够有效介入F村,是地方政府单一主导下精准扶贫的治理困境与成本考量、后脱贫时代乡村主体凸显与乡村振兴内在需求、农村社会工作的内在优势等因素共同决定的,这也表明社会工作介入具有明显的补位色彩。社会工作方法的优势在于个体增能和群体组织化,对乡村空间、产业、生态缺乏直接功效,其引导下的社区营造也只能更多着眼于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乡风文明的塑造。后脱贫时代乡村主题无疑将从“脱贫出列”转为“留住乡村”,以特色文化为主的社区营造将成为下一阶段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在后脱贫时代,政府在乡村振兴中的直接行动必然会随着“第一书记”的逐步“退场”而有所弱化,但这并不表明社会工作机构就能完全取代政府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政府的主导者、投资者和保障者的角色不能缺位,尤其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更要加大对乡村的资源输入与保障力度,做好空间规划、产业扶持、生态恢复等基础环节,这样才能为社会工作在社区营造中的优势发挥提供基本条件。同时,也要注意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习俗和少数民族特性[6]。不同民族文化属性往往导致组织化的类型和方法差异,这是社会工作中需要充分注意的,而这也直接关系到社会工作介入脱贫攻坚的经验能否从村落试点走向全县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