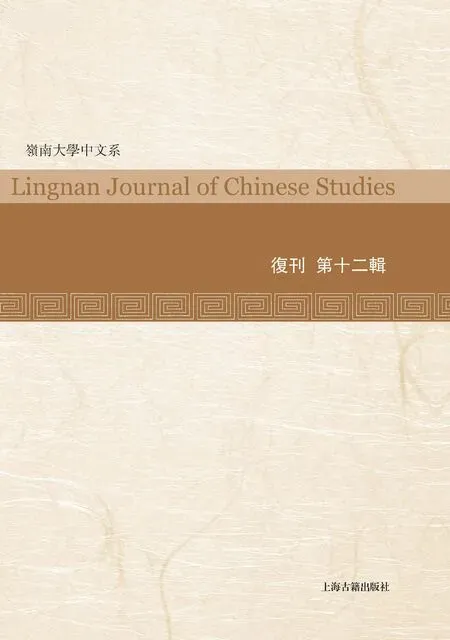“學詞”與“詞學”:晚清民國的詞法論述與詞學演進
2020-03-02龔宗傑
龔宗傑
在傳統文學批評中,作為一種以文學創作論為導向的概念,“法”一直佔據著重要的位置。就分體文學而言,所謂“文法”、“詩法”,均在南宋以後被不斷討論並逐步形成較為完備的體系。詞體晚出,針對“詞法”的系統研討自然相對滯後。至清末民初之際,伴隨著詞學體系建構的起步,詞法總結始被納入相關的建設序列。清光緒七年(1881),江順詒纂輯、宗山參訂的《詞學集成》刻成,欲以源、體、音、韻、派、法、境、品八個類目來支撐起古典詞學的框架。至少從名目的確立上來説,所謂“詞法”已被列為單獨的分支。陳鋭於清宣統三年(1911)撰成《詞比》,分“字句”、“韻協”、“律調”三目,來闡説詞體“確乎具有法度”①陳鋭:《詞比》自序,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稿本,第1頁上。,作詞有法可循。自此,作為一種相對獨立且完整的知識形態,詞法正式得到嚴肅且頗具規模的討論,成為推動晚清至民國詞學演進的重要資源。
上世紀初,隨著“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的先後頒布,具備現代人文學科形態的“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學史”始被納入到本國的教育體制,詞學也在中國文學的近現代轉型中逐步實現其學科的獨立。1917年,北京大學召開改訂文科課程會議,在該年12月2日的“會議議決案”中,決定於“中國文學門”下設“唐五代詞”、“北宋人詞”、“南宋人詞”②王學珍、張萬倉:《北京高等教育文獻資料選編:1861—1948》,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01頁。,以作為區别於詩、曲、小説等其他文類的科目,意味著至少在教學層面,詞學已獲得相對獨立的位置。次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了謝無量的《詞學指南》;1919年,王藴章《詞學》被收入《文藝全書》由上海崇文書局出版。與上述二書相對應,謝無量另有《詩學指南》、《駢文指南》,而《文藝全書》除《詞學》外,還收録孫學濂《散體文》及《駢體文》、費有客《詩學》、許德鄰《曲學》。表明在研究領域,以文學分科為趨向,詞學正探索一條具有現代意義的發展路徑。自20年代開始,探討詞法、研究詞學的研究著作與普及讀物層出不窮,如吴莽漢《詞學初桄》、徐敬修《詞學常識》、劉坡公《學詞百法》、顧憲融《填詞百法》及《填詞門徑》、傅汝楫《最淺學詞法》、梁啟勳《詞學》、吴梅《詞學通論》、任中敏《詞學研究法》、劉永濟《詞論》、余毅恒《詞筌》等先後在二十多年間撰成或印行;另外如吴梅《論詞法》收於羅芳洲《詞學研究》,夏承燾《作詞法》收於胡山源《詞準》,唐圭璋《論詞之作法》刊於《中國學報》第一卷第一期。從中可看出,儘管晚清以來有關詞學的建構有著不同層面的聚焦,但其中一個引人關注的焦點,正是上引諸多詞學文獻在不同程度上都涉及的“詞法”,簡言之,即陳匪石所説的“其論詞之著,皆示人以門徑”③陳匪石:《聲執》自序,載於《詞話叢編》第5册,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921頁。。在某些語境下,有關學詞、作詞的焦點甚至被放大到涵蓋了詞學大部分内容,成為20世紀初期人們研討詞學的重要著力點。由此便不難理解,為何後來龍榆生、詹安泰在探索詞學研究路徑時,都有意強調“詞學與學詞,原為二事”④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頁。,旨在界分“學詞所有事”與“研究詞學之能事”①詹安泰著,湯擎民整理:《詹安泰詞學論稿》,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頁。,並以此邏輯來調整詞學研究的内部結構。學界對民國時期的詞學建構雖然已作了諸多討論,但對上述文獻涉及“詞法”討論的部分,則缺乏足夠的重視。因此,本文希望通過分析詞法這一知識形態在清末以來的系統生成、衍變與最終定型的過程,梳理當時“學詞”與“詞學”的互動關係的基礎上,更好地去把握晚清至民國詞體觀念與詞學的演變軌跡。
一、晚清以降的詞法撰述與詞學體系初構
關於詞法,從歷史上看,南宋後期詞人論詞已開始講究法脈相承。對此,吴熊和先生在《唐宋詞通論》中曾指出這種講習與傳授詞法之風,“始於姜夔,而備於張炎”②吴熊和:《唐宋詞通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99頁。。南宋以來有關詞法的討論,同樣見於詞話、詞論,張炎《詞源》已談到詞之句法、字法,指出“詞中句法,要平妥精粹”,“句法中有字面,蓋詞中一個生硬字用不得”③張炎:《詞源》卷下,載於《詞話叢編》第1册,第258—259頁。;《詞源》末附楊纘《作詞五要》,分為擇腔、擇律、按譜、押韻、立意;沈義父《樂府指迷》則論及詞之起、過、結以及用事、造句、下字等各類作法。明人所論,則有俞彦《爰園詞話》闡述作詞法中的“遇事命意”、“立意命句”及“綺語”、“對句”④俞彦:《爰園詞話》,載於《詞話叢編》第1册,第400—403頁。。降至清代,論者漸多,孫麟趾《詞徑》有“作詞十六要訣:清、輕、新、雅、靈、脆、婉、轉、留、托、澹、空、皺、韻、超、渾”⑤孫麟趾:《詞徑》,載於《詞話叢編》第3册,第2555—2556頁。,沈祥龍《論詞隨筆》提出“詞有三法”、“詞有三要”⑥沈祥龍:《論詞隨筆》,載於《詞話叢編》第5册,第4049—4050頁。,另如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況周頤《蕙風詞話》亦有數則論作詞之語。陳匪石在其作於1949年的《聲執》自序曾對此情形作過描述:“遠如張炎、沈義父、陸輔之,近如周濟、劉熙載、陳廷焯、譚獻、馮煦、況周頤、陳鋭、陳洵,其論詞之著,皆示人門徑。”⑦陳匪石:《聲執》自序,第4921頁。儘管如此,晚清以前涉及詞法的“論詞之著”,形態依然相對零散,呈現出傳統批評樣式的條目化和印象式的典型特徵,正如陳鐘凡在所撰《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指出的“論文之書,如歷代詩話、詞話,及諸家曲話,率零星破碎,概無統系可尋”①陳鐘凡:《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中華書局1927年版,第9頁。。
晚清民國之際詞人對詞法“統系”的梳理,恰好是伴隨著詞學格局的新建而展開的。清代以來,隨著詞人的大量創作實踐和對詞體邊界的不斷反思,作為一種知識與經驗的總和,詞學在自身容量擴張的同時,其内部結構也逐漸呈現出清晰的面相。一般認為,由江順詒纂輯、宗山參訂的《詞學集成》,是傳統詞學在晚清實現其體系建立的重要標誌。根據書前題識,《詞學集成》的編纂最初由江順詒進行。他認為詞道自兩宋以下“漸至紛紜歧出”,因而“尋源競委,審律考音,取諸説之異同得失,旁通曲證,折衷一是。所以存前人之正軌,示後進之準則”②江順詒、宗山:《詞學集成》卷首題識,清光緒七年(1881)刻本,第1頁上。,可見其編纂目的還是在於授人填詞之法,指示門徑。宗山所作的工作,是“為之條分縷析,撮其綱,曰源、曰體、曰音、曰韻,衍其流曰派、曰法、曰境、曰品,分為八卷,以各則麗之”③江順詒、宗山:《詞學集成》卷首《凡例》,第1頁下。,將原本被江順詒稱為“詞話之流”的資料彙編,各歸其類,並更名為“詞學集成”。儘管從内容上講,《詞學集成》只是前人詞序、詞話及詞論的類選,偶附江氏按語,並未有多少理論創見,但以“集成”為名,並希望通過上述八個類目來整合及歸置古典詞學資源的思路,實際上為此後的相關研究提供了一種劃分詞學内部結構的最初樣板。另外值得關注的就是“法”被獨立為一個單元。宗山在卷首的題識末尾,還撰有“序目”,用以解説全書類編的思路。“詞法第六”的序目曰:“法立文成,旋周旋折。異曲異詩,非莊非謔。變必歸宗,反而能縮。一氣轉圜,是謂中則。”④江順詒、宗山:《詞學集成》卷首題識,第1頁下。可見其基本觀點是以法為詞,並且肯定詞體擁有區别於詩和曲的獨立文體特徵,以及呈現這些特徵所須遵循的法則和規範。因此就作詞法的角度來説,該書同樣可被視為我們討論清末民初詞法體系建構的起點。
如果以《詞學集成》所設定的基本架構為參照,可以看出,20世紀初期詞學研究之演進,大體上是圍繞“學詞”與“詞學”這兩種對詞學不同層面的理解而展開的。其一,詞學理論的建設繼續以上述基本架構作為模板,逐漸向著内部構造清晰、初具現代形態的體系發展轉變。其二,針對創作實踐的詞法授學,以創作為導向的詞法書寫所占比重逐漸加大,並開始吸收音韻、聲律、格式等詞學内部之分支,推動了“學詞”話語體系的擴張。
如所周知,1917年底北京大學《文科改訂課程會議議決案》在“中國文學門”下,始列“唐五代詞”、“北宋人詞”、“南宋人詞”三個科目,這一舉動被認為是詞學作為獨立學科進入大學教育體系的標誌。此後三年,三本命名均帶有“詞學”的著作相繼問世,分别是謝無量《詞學指南》(1918年)、王藴章《詞學》(1919年)及吴莽漢《詞學初桄》(1920年)。謝無量《詞學指南》分為“詞學通論”與“填詞實用格式”二章:通論一章下又細分為“詞之淵源及體制”、“作詞法”、“古今詞家略評”和“詞韻”;實用格式分為“小令”、“中調”和“長調”,亦可視為詞譜。儘管此書的編寫思路大致按照詞源、詞體、詞法、詞評和詞譜為框架,但就性質而言,與同年出版的謝氏《詩學指南》一樣,是提供“為學者實用之式”①謝無量:《詞學指南》,上海:中華書局1918年版,第59頁。,屬學詞的指導用書。吴莽漢的《詞學初桄》八卷,編寫目的同樣是“以惠來學”②吴莽漢:《詞學初桄》卷首李聯珪序,上海朝記書莊1920年鉛印本,第1頁下。,性質雖屬詞譜之類,但觀其卷首“緒言”以下,分述原始、律譜、製曲、審音、用韻、换叶、集虚、煉句、詠物、言情、使事、宜忌、難易、轉折、名義、例言十六則,似有意引入包含源、律、音、韻、法在内的詞學内容,實際上也具備著接近《詞學指南》“通論”和“格式”二分的特徵。相比而言,王藴章的《詞學》更契合前述《詞學集成》所設定的框架。王氏《詞學》分為溯源第一、辨體第二、審音第三、正韻第四、論派第五、作法第六,恰好與《詞學集成》前六目的源、體、音、韻、派、法完全對等。不同之處,除《詞學》未設置境、品二目外,最值得留意的是與《詞學集成》論“派”相對零散隨意不同,王藴章在“論派”一目中,似乎是以一套自唐五代至清的“詞史”邏輯線來串聯歷代詞人。如下是他在“論派第五”一目的解説文字:
論唐詩者,有初、中、盛、晚之别。惟詞亦然,其派别所在,不難條分縷晰。兹以時代為斷而論定之。首唐五代,次宋,次清,而明人不與焉。明之詞如詩之晚唐,而彌復不逮。一二才異者,非不欲勝前人,而中實枵然,取給而已,於神味全未夢見,但知為貌襲耳,故略之。金、元間不少作者,則附於宋後,以為閏統。雖評論未必盡當,初學得此,亦庶幾略識其途徑矣。①王藴章:《詞學》卷三,《文藝全書》,上海:崇文書局1919年版,第47頁。
據此我們應該可以清晰地看到王藴章是“以時代為斷”的詞史叙述模式,來考量歷代詞人。在具體撰述中,他還於每個時段的標目下,附有一段折衷前人論説的文字。如論“唐五代”,引清人馮煦“詞有唐五代,猶文之先秦諸子,詩之漢魏樂府”的説法;論“宋”,則引朱彝尊“詞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的論調,來概括各個時代的詞體特徵。但此書的缺憾在於,一是這種略去明詞的思路直接承襲自清人,未有改良,二是撰述目的是仍然為初學作詞者指示門徑,囿限於學詞,因而尚不足以視為一種具有自覺意識的詞史觀念。
總的來看,20世紀初詞學論著的撰述,大致以晚清之際所設定的叙述框架為參照,一改以往詞話一類的零散方式,嘗試向著有“統系可尋”的路徑繼續探索。事實上除了上述三種著作外,另外可補充的例子,如徐珂的《詞講義》,雖為未定稿,但據其目録可知,該書也分為“詞曲總論”、“詞之淵源”、“詞之辨體”、“詞之正韻”、“詞之分派”和“詞之作法”②徐珂:《詞講義》,載於《歷史文獻》第1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8頁。;孫人和《詞學通論》二卷,分“詞之起源”、“詞之體制”、“論音律”、“填詞法”與“唐五代兩宋名家詞”③孫人和:《詞學通論》,載於孫克強、和希林主編:《民國詞學史著集成》第8卷,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頁。;徐敬修《詞學常識》(1933年)列“總説”、“歷代詞學之變遷”、“研究詞學之方法”三章,但細考其内在的叙述理路,可知確如書前提要所言“本書關於詞之起源,以及詞與詩、樂、曲之關係,歷代詞學之變遷,均詳細叙明,末附填詞之方法,及詞譜、詞韻,以備研究詞學者知所取法焉”④徐敬修:《詞學常識》,上海:大東書局1933年版,第1頁。,同樣可解析為源、體、史、法、譜、韻幾個類目。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無論是《詞學指南》,還是《詞學常識》,雖冠以“詞學”之名,卻都是以“學詞”為其標的。至於像《詞學常識》第三章“研究詞學之方法”,細分為“填詞之入手法”、“填詞之格式”、“詞韻”與“詞書之取材”,似乎是一種將“填詞”理解為“研究詞學”的一種認知錯位。
出於對學詞的重視,詞法在上述幾部論著中已是頗具分量的内容。至20世紀30年代前後,有關詞法的論述在詞學論著中的比重逐漸加強,同時出現了一系列談論作詞法的專書。1928年,上海世界書局出版了劉坡公的《學詩百法》和《學詞百法》,二書專為學習作詩詞者指示門徑。《學詞百法》分音韻、字句、規則、源流、派别、格調六個部分。若合字句和規則二目為狹義之詞法,實際上這六個部分可分别對應詞學框架中的韻、法、源、派、譜。對於這幾個部分的内容,劉氏採取的是一種法度化的處理方式,如第一部分“音韻”,細分為“審辨五音法”、“考正音律法”、“分别陰陽法”、“剖析上去法”、“檢用詞韻法”、“配押詞韻法”、“變换詞韻法”、“避忌落韻法”,對此,書前“編輯大意”略有解説:
音有清濁,韻分陰陽,學詞之法,音韻最嚴。本書廣徵博引,不特考其源流,正其是非,而尤注意於辨音叶韻之道,庶幾初學倚聲者,可無落韻失腔之病。①劉坡公:《學詞百法》,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26頁。可見作者是將“音韻”視為學詞法之關鍵。另外如述“源流”,同樣分“探溯詞源法”、“辨别詞體法”等五類,自稱“本書於詞曲之分合,體制之異同,詞學之源流,調名之緣起,應有盡有,不憚詳述。學者細細翻閲,於填詞之學不難思過半矣”②劉坡公:《學詞百法》,第126頁。,也是以“填詞之學”的角度來考量詞體及其源流。
劉坡公《學詞百法》的編寫很可能參照自顧憲融《填詞百法》一書。《填詞百法》初刊於1925年,由上海崇新書局印行,此後數年間曾多次再版。該書分上、下兩卷,卷上列“四聲辨别法”、“陰陽辨别法”至“宫調溯源法”,凡50目,卷下列“詞派研究法”、“李太白詞研究法”以至“王半塘詞研究法”,凡49目。兩卷内容基本涵蓋音、律、譜、法、源、派等,並以“法”來統合這些詞學要素。1934年,上海大東書局出版了傅汝楫《最淺學詞法》,該書實可視為《填詞百法》與《學詞百法》二書的沿襲之作。如《最淺學詞法》書前“編輯大意”解説音韻一條:“韻分陰陽,音有清濁。本書廣徵博引,言之綦詳,不第考其淵源,正其是非,而尤三致意於叶韻辨音之道,庶幾操觚之時,可無落韻失腔之失。”③傅汝楫:《最淺學詞法》,上海:大東書局1934年版,第1頁。基本承襲了上引《學詞百法》的説法。關於《最淺學詞法》的綱目,書前也有説明:“本書定名‘學詞法’,專就淺近立説,為已解吟詠,而欲進窺倚聲者,指示門徑。……分列七章:曰尋源,曰述體,曰論韻,曰考音,曰協律,曰填辭,曰立式。由淺及深,依次遞進。學者得此,可無躐等之弊。”①傅汝楫:《最淺學詞法》,第1頁。可見傅氏所輯,也是將源、體、韻、音、律、法、譜七要素統系於“學詞法”之下。
30年代前後的研討學詞之風,與近代國文學科建立對古典詩詞教學的重視自然有所關聯。而在詞學體系内部,如顧憲融在《填詞百法》自序中所言“我國文章之事,至詞而極其工,至詞而極其變”②顧憲融:《填詞百法》自序,上海:中原書局1931年版,第1頁。,當時人們對詞體之推尊、詞藝之講求,也推動著詞學向現代形態的學科不斷完善和發展。1935年,上海中央書店又出版了顧憲融的《填詞門徑》,與前作《填詞百法》相比,可明顯看出其改良的痕跡。此書分上、下兩編:上編“論作詞之法”,分緒論、論詞之形式、論詞之内容三章;下編“論歷代名家詞”,分論唐五代詞、論北宋詞、論南宋詞、論金元明詞、論清詞五章。可見“詞法”在這本仍以指導填詞為宗旨的書中依舊佔據相當重的分量。不同之處在於,其一是若與前述王藴章《詞學》相比,以往通常被列為“派”的歷代名家詞,此處單列為一編,且並未略去明詞,呈現出一種相對完整的詞史叙述。其二是在論作詞之法一編,將句氏、詞韻、詞譜歸為“形式”,而把意内言外、先空後實、佈局章法等涉及詞體風格、審美特徵的部分列入“内容”,當可看出滲透在其中的西學觀念。諸如此類,也折射出古典詞學在近現代轉型過程中對新知的吸收。
二、“文學藝術之一種”:詞體觀念及詞法論述的新變
晚清以來,作為一種外力,西方文學資源的大量引入,推動著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學的觀念反思和研究重估。如前引顧憲融《填詞門徑》以形式和内容區分作詞法,顯然是借用了一套與以往不同的話語來考量詞體。顧實《中國文學史大綱》第一章“太古文學”第一節“總説”,也曾以形式與内容這兩個方面來討論中國文學研究之方法:
要之,文學史者,就一國民,依秩序而論究其文學之發達者也。今標題曰“中國文學史”,其研究之對象,即為中國之文學作品,不待言也。大凡所謂藝術,以形式、内容兩方面之調諧,最為上乘。故中國文學之研究,亦於此兩者,不設輕重之别,一也。一切藝術之作品,因於時代共通之思潮,與個人獨特之癖性,結合而形成焉者,故於文學之内容,又恒不能不截然區别此兩者,二也。①顧實:《中國文學史大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第6頁。
顧實認為文學作為“美之藝術”,是形式與内容相互調和的產物。這一觀點,來自他所接受的西學理論:“最近美國摩爾登(Moulton)著《近世文學之研究》(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亦分六類。要之,此六類者,皆當以‘美之藝術’為標準,其有美之藝術之價值者,文學也。……雖詩詞歌曲,然且非於美之藝術有價值,即亦不有文學之價值也。”②顧實:《中國文學史大綱》,第5頁。若推而廣之,顧實所接受的這種以藝術標準來衡定文學價值的學理與方法,實際上與“五四”以來純文學觀念的興起有很大關聯。包括他提到的莫爾頓(H.G.Moulton)的觀點在内,20世紀初的中國文學界對歐美文學理論的接引,如吸收温徹斯特(C.T.Winchester)《文學評論之原理》所概括的思想、感情、想象、形式諸要素,促成了文學觀念向純文學方向的轉進。
處於這種西學東漸大背景下的詞學,同樣受到外來新知的衝擊,並且主要是在純文學觀念的影響下,翻新著人們對其文體價值和功能的認知。概括地説,其一是就文體觀念而言,詞體確立了在文學,尤其是韻文文體序列中的獨立地位,如上引《填詞門徑》論詞與詩文之關係,指出“詞者,我國文學中之一體”③顧憲融:《填詞門徑》上編,上海:中央書店1935年版,第1頁。;其二關涉作詞法,基於“純文學”的觀念來強調詞體的抒情傳統,重視詞體的情感表達功能,因而在作法上更講求所謂表現“意境”、“情感”的“描寫之筆致”與“表現之方法”④顧憲融:《填詞門徑》上編,第1頁。。
上述兩個方面的新變,或許皆應從比顧憲融《填詞門徑》稍早的梁啟勳《詞學》説起。梁啟勳(1879—1965),字仲策,廣東新會人,梁啟超之弟。早年師從康有為,後考入上海震旦學院,此後赴美國學習。回國後先後在青島大學、交通大學任職。除完稿於1932年的《詞學》外,梁啟勳的詞學著述還有《詞學詮衡》、《稼軒詞疏證》,此外《中國韻文概論》和《曼殊室隨筆》均有詞論部分。梁啟勳的文學觀念,深受西方美學論的影響,同樣是以“美之藝術”為標準。他在《曼殊室隨筆》“詞論”部分曾討論藝術與美:
藝術乃一概括名詞。以空間言之,是多方面的;以時間言之,是無止境的。若欲以一語包舉之,則曰“唯美”。美亦多方面的,無止境的。有天然之美,有人工之美。思如何而後可以模仿天然,補助天然,改造天然,此等工作,謂之曰藝,而成功則有術焉。①梁啟勳:《曼殊室隨筆》,載於《民國叢書》第三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48年版,第19頁。以文字組織而形成的美,梁啟勳認為是需要“複雜”而“調和”的,“得調和之韻味”是他品評古人詞句的標準。如指出:“柳耆卿之‘楊柳岸曉風殘月’,是三種天然景物集合而成,但美感無限,傳誦千古。秦少游之‘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是四種天然景物集合而成,晁无咎謂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此無他,亦曰調和而已。可見美感不外調和,形色如是,聲音亦復如是。著意調和,是即藝術之所謂‘術’。”②梁啟勳:《曼殊室隨筆》,第21頁。通過“術”以達藝術之美,也是梁啟勳通過《詞學》所表達的詞體觀念和詞法理論的核心。
《詞學》分上、下編,梁氏自述“此書之作,上編乃與人規矩,下編乃示人如何而後可以謂之巧”③梁啟勳:《詞學》例言,北京:中國書店1985年版,第1頁下。,“上編既論詞之本體,下編試進論詞流之技術”④梁啟勳:《詞學》下編,第1頁下。。具體來説,上編為詞體論,講解詞體特徵,分總論、詞之起源、調名、小令與長調、斷句、平仄、發音、换頭煞尾、漫近引犯、暗韻、襯音和宫調十二目;而下編為詞法論,示人以作詞技巧,分概論、斂抑之藴藉法、烘托之藴藉法、曼聲之回蕩、促節之回蕩、融和情景、描寫物態(節序附)、描寫女性八目。因此從結構上來看,該書也是由通論和詞法兩部分組合而成。
首先就詞體觀念來看,梁啟勳認為詞屬文學,具備藝術的本質,最適合用來表達人類的情感。在《詞學》“例言”中,他明確指出“詞為文學藝術之一種,就表示情感方面言,容或可稱為一種良工具”⑤梁啟勳:《詞學》例言,第1頁上。。在該書下編“概論”,梁啟勳對此作了進一步論述:
文學乃一種工具,用以表示情感,摹描景物,發揮意志,陶寫性靈而已。詞亦文學之一種,其藝術之本質,對於此四項工作,或許有一二為彼所特長,為他種文藝之所不能及,亦未可知。所以自唐以訖現代,千餘年間,詞之在文學界,幾以附庸蔚為大國,非無因也。①梁啟勳:《詞學》下編,第2頁。
所謂“幾以附庸蔚為大國”,當暗含梁啟勳推尊詞體的傾向。而這種傾向是以肯定詞體擁有比其他文類更擅長的功能作為支撐。以此返觀清人以集部為核心的傳統文類序列為參照系,將詞體納入到“《三百篇》變而古詩,古詩變而近體,近體變而詞,詞變而曲,層累而降”②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下册,第1087頁。的文體正變譜系,當可看到梁啟勳的詞體觀念中呈現出的新因素。梁啟勳雖也認為詩變為詞,但他更看重的是詞體本身所具備的“為他種文藝之所不能及”的特質,運用一種近代以來西學觀念影響下的文學體裁作為參照系。如以“工具”説來揭示詞體的文學功能:“詞之在文學中,大抵作用表示情感,摹描景物之工具,最為相宜。非謂他種文藝之不能表示,不能描寫也。技術之優劣,當然存乎其人。但運用之難易,問題則在於工具矣。”③梁啟勳:《詞學》下編,第2頁下。認定詞是最適合用來寫景和抒情的文體。
梁啟勳對詞體本質的認識,當與他接受的歐美文學理論尤其是純文學的觀念不無關係。在《詞學》的例言中,他自稱是以“嚴整的科學方法”來研究屬於純文學的詞體。《詞學》完稿後,梁啟勳開始撰寫實踐其純文學觀念的《中國韻文概論》,包括騷、賦、七、駢文、律賦、詩、樂府、詞、曲九類文體。在第一部分總論中,梁啟勳試圖以“知識作用”和“精神作用”來嚴分雜文學與純文學,指出“純文學則有時專為作文而作文,其所作之文並未打算與他人讀,乃至不希望有人讀”④梁啟勳:《中國韻文概論》,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第2頁。,此類具備“精神作用”的文章,其價值有時甚至超過具備“知識作用”的工具之文。由此自然可以理解梁氏為何推尊以“表示情感”為特長的詞體,以此返觀晚清的詞體觀,我們也可以看到,伴隨著差不多同時的純文學觀念的引入,此際國人對詞這一文體的認識已有了更為明確的價值取向。
再看詞法論述的新變。如上所論,梁啟勳同時視詞為藝術,並認為須通過“術”以達藝術之美。《詞學》下編專論“詞流之技術”,並分别對應情、景兩大分支。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思路當受其兄梁啟超之啟發。1922年,梁啟超在清華學校作《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的演講,指出韻文在情感表達方面有“奔迸的表情法”、“回蕩的表情法”以及“藴藉的表情法”等幾類,並強調奔迸的表情法不適用於詞:“詞裏頭這種表情法也很少,因為詞家最講究纏綿悱惻,也不是寫這種情感的好工具。”①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75頁。而在回蕩的表情法一類,又有四種不同的方式,分别螺旋式、引曼式、堆疊式、吞咽式,前二種概括為“曼聲”,後二種則是“促節”。梁啟勳《詞學》下編即以此為基本思路來設定論述框架,表示情感一類剔除不適用於詞體的奔迸的表情法,分含蓄藴藉、迴腸盪氣兩種,含蓄藴藉之下再分斂抑與烘托,迴腸盪氣之下再分曼聲與促拍;摹描景物一類分融合情景、描寫物態兩種。
至於具體論述,梁啟勳運用的方法是先以一段總論略作説明,後附數首作品再作闡發。如論“烘托之藴藉法”:“此種技術,是將熱烈之情感藏而不露,用旁敲側擊之法,專寫眼前景物,把感情從實景上浮現出來。”②梁啟勳:《詞學》下編,第10頁上。此後選周邦彦《夜飛鵲》(河橋送人處)一詞為例詳細解説,並録柳永《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姜夔《八歸》(芳蓮墜粉)、張炎《鬥嬋娟》(舊家池館尋芳處)、周密《法曲獻仙音》(松雪飄寒)等詞作為補充。如指出烘托法另有“將自己之情感藏著不寫,而寫對方。不寫我如何思念他,先寫他如何思念我”③梁啟勳:《詞學》下編,第10頁下。,以此將自我的感情更自然地表現出來,並借用柳永“想佳人、妝樓凝望”、姜夔“想文君望久,倚竹愁生步羅襪”等句為例,來闡述運用此法可將感情表達得更為濃厚。總的來看,梁啟勳的詞法理論,是以表現情、景的藝術之美為核心,並通過分析具體作品來抽象出一種審美原則及寫作方法,以此來指導詞的創作。這與此前諸如謝無量《詞學指南》、劉坡公《學詞百法》、顧憲融《填詞百法》等書均以整合傳統詞學的各項要素為基礎,來提供一套基礎且全面的法式與規範相比,已可看出明顯差别。
對於這種“創獲”與“因襲”的差别,不妨結合出版於1935年的任中敏《詞學研究法》來作詮解。在該著的第一部分“作法”中,任先生系統梳理了自晚清《詞學集成》以來詞法編撰的總體情況,將作詞法之研究歸納為“揣摩前人之作”與“歸納前人之説”二途。對於後者,任先生認為:“自來論詞法者,創獲少而因襲多,而因襲者,每好貌為創獲,凡所立説,其實本多於古人……至於近日坊間所有《指南》、《捷徑》、《百法》等書,孰非撏撦古人之言,編成章次者?”①任中敏:《詞學研究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2頁。有意指出前揭《詞學指南》、《學詞百法》之類詞法書籍多因襲前人論説編纂而成,並進一步説明這種搜集、歸類的詞法撰述方式肇始於《詞學集成》:
歸納前人之説者,宗旨在集思廣益,其事為搜輯,為分類,為排列,為省察,為論斷。因前人之業中,與此一事,尚未成有專書(僅一《詞學集成》似之,頗嫌簡陋)。學者於今日欲享其利,必自己一切從頭做起,至於所以揣摩前人之作者,不外兩事,一乃讀選本以博其趣,一乃專一家以精其詣。……是吾人今日欲從事揣摩,於選本專集,二者具有成書可用,略有採擇,即可逕為省察論斷,不須再如歸納詞説者從事搜輯矣。②任中敏:《詞學研究法》,第18—19頁。
據此可知,任中敏在這裏強調的作詞法之研究模式,是通過細讀詞文本並加以思考領會,以求得所謂“作者意境之所在,與其文章之所成”③任中敏:《詞學研究法》,第19頁。。具體的“揣摩”方法,該書分為通解文字、確定比興、體會意境和認真詞法四類,並舉“前人之作”為例詳加闡説。如舉温庭筠《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一首,指出該詞意境是通過“交相印”三字托出,章法是由地及人,進而由事及情,層層遞進,前後一貫,修辭法則包括“擇舉精要”、“情事融合”以及比興手法。總的來説,任中敏的詞法論述,強調的是“活法”,即不囿於前人論説,應有所創獲,但同時他也主張歸納與揣摩的“二者能兼至”,是一種更為融通的法度觀念:
揣摩前人之作者,但知有書中文字,與心内主張,由我立説,有詞為證,其作法如何,得之親切,用之亦必透澈;所失者不免一人偏見,一時誤解,足以自陷於歧途耳。歸納前人之説者,採取須博洽,評斷須貫通,所得每較浮泛,用之亦不易入細;然其長處在所得理法,經過多人體會,必不至根本大謬也。倘二者能兼至,則於作法之研究,尚有間言乎?①任中敏:《詞學研究法》,第29頁。
任中敏在此針對詞法研究所總結的兩條路徑,恰好對應了晚清以來的詞學演進,體現在詞法論述方面的歸納成法與揣摩活法這兩條基本線索。前者以清末《詞學集成》為樣板,經由謝無量、吴莽漢、徐敬修、顧憲融等人的推衍,至上世紀初形成探討作詞法的學風;後者則有梁啟勳等人不拘定舊説的探索,另外像同時期的吴梅《詞學通論》第五章“作法”強調“有一成不變之律,無一定不易之文”②吴梅:《詞學通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第41頁。,劉永濟《誦帚堪詞論》卷下“作法”也注重“下己意引申證明之”③劉永濟:《誦帚堪詞論》,國立武漢大學1936年鉛印本,第1頁上。,均體現出上世紀30年代詞法研討的一種自覺意識。
三、“學詞”與“詞學”:古典詞法的定型與詞學的現代轉型
《詞學研究法》在總結作詞法研究方面的貢獻,除提出上述歸納與揣摩二途,並探索一套“由我立説,有詞為證”的詞法論述模式之外,另外值得留意的就是在歸納層面,作者通過修訂前説,部勒異同,總結出了一套相對完備的古典詞法體系。
任中敏首先羅列了歸納詞法的應該遵守的五項原則,分别是説明出處、直載原文、標舉要旨、部勒異同、自加論斷。在具體編排中,第四項部勒異同最為關鍵,他強調説:“歸納之道,尤首重標題。有標題,方有綱領,而前人紛紜之説,方有以包而舉之。此所謂部勒異同,猶是就每一題目内而言,若許多題目之間,更不可不具系統,以相維繫。”④任中敏:《詞學研究法》,第3頁。可見任氏對傳統詞法資源的整合,是以標題界分其系統内部的各個板塊,進而實現對“前人紛紜之説”的系統歸類。借助這樣一種較為嚴整的方法,他最終梳理出了一套“以供實際歸納作詞法者參考”的完整框架:
從上引綱目來看,任中敏的分法,較之此前如謝無量《詞學指南》、王藴章《詞學》等更為詳整,又比顧憲融《填詞百法》之類更具體系。他自稱:“此項歸納之功既竣,可以名其所成之編曰‘詞法’,與前人所謂《詞律》者並峙。蓋《詞律》言聲音之律,此則言文章之法也。”①任中敏:《詞學研究法》,第5頁。可見,正如該書目次把作法與詞律、詞樂分列,作者是有意識地構建一套屬傳統辭章學層面、不包括聲律之學的詞法體系。因此可以説,儘管《詞學研究法》僅提供了一套詞法論述的整體思路以及操作原則,並未形成如作者所説可以題名為“詞法”的全部文本,但其框架之嚴整與合理,實非此前諸多詞法著作所能比擬。《詞學研究法》之後,雖仍有詞家關注作詞法,如唐圭璋《論詞之作法》,分“作詞之要則”、“詞之組織”及“詞之作風”②唐圭璋:《論詞之作法》,載於《中國學報》1943年第1期,第55頁。,俞感音《填詞與選調》(《同聲月刊》1941年第2期)、吴世昌《論詞之章法》(《國文雜誌》1943年第4期)等,但多傾向於就詞法體系内的某些層面作更細緻的考察。
與詞法探討頗具規模差不多同步,詞學也在30年代迎來其轉型之關鍵。與此前所謂“詞學”與“學詞”兩種話語形態相混雜不同,作為一種知識體系的内部調整,現代意義上的詞學恰好是以通過與作詞法之間的對話來實現其體系建構。
1935年,龍榆生在《詞學季刊》第一卷第二號發表《今日學詞應取之途徑》,明確指出:“詞學與學詞,原為二事。”③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第113頁。關於二者之差别,他在前一年同樣發表於《詞學季刊》的《研究詞學之商榷》一文,已作了如下闡説:
取唐、宋以來之燕樂雜曲,依其節拍而實之以文字,謂之“填詞”。推求各曲調表情之緩急悲歡,與詞體之淵源流變,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謂之“詞學”。①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第94頁。
結合兩篇文章展開來説,龍榆生所區分的“學詞”與“詞學”,實際上分屬於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兩個領域。對於填詞,龍榆生認為在歌法尚存時可以即席而作,在歌法已亡後也可依據圖譜進行填寫,是富有才情的文人學士所擅長的。在作法方面,他指出:“學詞者將取前人名製,為吾揣摩研練之資,陶鑄銷融,以發我胸中之情趣。”②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第113頁。又與前揭任中敏的揣摩法以及梁啟勳的表情法頗為相近。關於詞學,他強調“乃為文學史家之所有事”,並通過梳理宋元以來的“詞學成績”,歸納出“圖譜之學”、“詞樂之學”、“詞韻之學”、“詞史之學”、“校勘之學”五項,又結合近代以來的研究動向而别立“聲調之學”、“批評之學”、“目録之學”三項,由此劃分出詞學研究的邊界及其内部結構。
如果對上述詞學架構稍作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龍榆生建構詞學體系的特點,一是嚴守“詞學”與“學詞”為二事的立場,二是持“文學史家”的觀念。首先就其詞學立場來看,龍榆生以上述八項内容為基本架構所建立的體系,明顯不包括詞法。他對歷代詞學論著的梳理,同樣是以區分詞學與學詞作為基本思路,如指出詞之有學,始於張炎《詞源》一書,但仍強調該書下卷“兼論詞法,屬於填詞方面之事”③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第95頁。,而與專論宫律,屬於詞樂方面的上卷有所界分。其次是隱於其詞學體系中的文學史觀念,認為歷代詞家“皆各因其環境身世關係,以造成其詞格”④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第114頁。,這一點多為研究者所忽視。如關於“批評之學”,龍榆生針對前人治詞學,多忽視時代環境關係而導致所下的評論“率為抽象之辭,無具體之剖析”,提出了修正的方法:
今欲於諸家詞話之外,别立“批評之學”,必須抱定客觀態度,詳考作家之身世關係,與一時風尚之所趨,以推求其作風轉變之由,與其利病得失之所在。①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第105頁。
在“目録一學”的詞家品藻一項,他又重申考察身世關係與時代風尚對於揭示“某一作家或某一時期之真面目與真精神”的重要性。我們知道,以泰納“時代、環境、種族”學説為理論支撐的文學史叙述模式,在上世紀初藉由日本而引入中國,當時的國人對本國文學史的研治,多以時代精神、社會環境與文學之關係為叙述思路②參見陳廣宏:《中國文學史之成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62—266頁。。就具體表述而言,龍榆生對詞學研究的思考,同樣帶有這種時代、環境論的意味。如《今日學詞應取之途徑》一文也談到:“各種文學之產生,莫不受時代與環境之影響,即就詞論,何不獨然。”③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第113頁。後舉柳永、辛棄疾與姜夔三派之詞,指出三派之不同詞風,與他們所處兩宋的不同時代環境、政治格局不無關聯。
在“學詞”與“詞學”關係上,如果説龍榆生將二者嚴格區分,是為有意濾去詞法來保持詞學作為學術研究的獨立和純粹性的話,那麽詹安泰《詞學研究》對“學詞所有事”與“研究詞學之能事”的界分,則是希望以此來建構包含二者在内、從低階到高階相銜接的詞學體系。詹安泰在《詞學研究》緒言中詳細闡説其詞學體系的框架:
聲韻、音律,剖析綦嚴,首當細講。此而不明,則雖窮極繁富,於斯道猶門外也。譜調為體制所系,必知譜調,方得填倚。章句、意格、修辭,俱關作法,稍示途徑,庶易命筆。至夫境界、寄託,則精神命脈所攸寄,必明乎此,而詞用乃廣,詞道乃尊,尤不容稍加忽視。凡此種種,皆為學詞所有事。畢此數事,於是乃進而窺古今作者之林,求其源流正變之跡。以廣其學,以博其趣,以判其高下而品其得失;復參究古今人之批評、詞説,以相發明,以相印證: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其有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者,為之衡量之,糾核之,俾折衷於至當,以成其為一家言。夫如是則研究詞學之能事,至矣,盡矣。④詹安泰:《詹安泰詞學論稿》,第3—4頁。
結合緒言末尾所附目録,可知:其一,詹安泰所謂的“學詞所有事”,實際上包括論聲韻、論音律、論調譜、論章句、論意格、論修辭、論境界、論寄託八項,“研究詞學之能事”則為論起源、論派别、論批評、論編纂四項。就“學詞”來説,詹安泰討論的範圍更廣,龍榆生“學詞”所對應的,當只是與章句、意格、修辭相關的“作法”,屬傳統辭章學層面的詞法内容。其二,詹安泰認為詞學研究當以學詞為根柢,所謂“畢此數事,於是乃進而窺古今作者之林”,意味著“詞學”為“學詞”之進階。
總的來看,儘管龍榆生與詹安泰在詞學體系的框架設置上各有側重,但不管是删汰“學詞”來建構的“詞學”,還是以“學詞”為基礎的“詞學”,他們的共同傾向都是有意識地去探索現代形態的詞學體系,較之此前統系於詞法之下、以示人門徑為旨歸的詞學研究已有了很大的拓進。
晚清民國詞學的建構,正是在上述不同立場與話語的對壘中進行的。有關詞學内部結構的討論,最終形成“學詞”與“詞學”兩種形態鮮明的體系。而交織於二者之間的詞法,經由人們的不斷探討和總結,也建立起相對完整的框架,使得詞學研究逐漸呈現更為清晰的面向。通過梳理詞法這一知識形態的生成、衍變與完型,除了有助於觀察晚清以來詞學演進的複雜格局及其走向之外,還能讓我們更真切地體會近代諸多詞家所作的探索和努力,並以這些經驗為基點,思考今天詞學研究的更多可能性。
四、餘論:“學詞”與詞學研究
百年前,北京大學發佈《文科國文學門文學教授案》(1918年),指出文科國學門設“文學史”及“文學”兩科,兩者目的不同,教授方法亦有所區别:“習文學史在使學者知各代文學之變遷及其派别;習文學則使學者研尋作文妙用,有以窺見作者之用心,俾增進其文學之技術。”①王學珍、郭建榮:《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1912—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9頁。作為一種對教學與學科建設的回應,文學研究亦分為二途,如“詞學”與“學詞”便可分别嵌入這兩條脈絡中。伴隨現代學術體系的發展,以闡述文學各體及作家流别、變遷的“文學史”研究模式漸成主流,而深入作品以探析其“文學之技術”的研究則趨於消弭。上世紀80年代,程千帆先生也曾指出,應重視這種久被忽視的從作家作品中“抽象出文學規律和藝術方法”並指導創作的傳統做法①參見程千帆:《古典詩歌描寫與結構中的一與多》,載於《古詩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頁。。
就詞學研究而言,一方面,伴隨著文本細讀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獲得重視,當今學人已開始注重對詞作的文本分析,著意從詞作的字句、章法、修辭、意境的細緻考察入手,或闡發詞人的成就與創作特色,或論證詞家創作與其詞學理論的關係,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向著如任中敏“揣摩”法等前賢研究傳統的一種歸返。另一方面,即如詹安泰的以“學詞”為基礎研究“詞學”,也不應忽視支撐這種研究方法的學識根基與文學修養。因此從這個層面來説,以詞法這種知識體系為考察對象,探討晚近學界對它的論述及其中的成果、經驗,或許有助於推動我們對延續“學詞”法脈與拓展“詞學”空間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