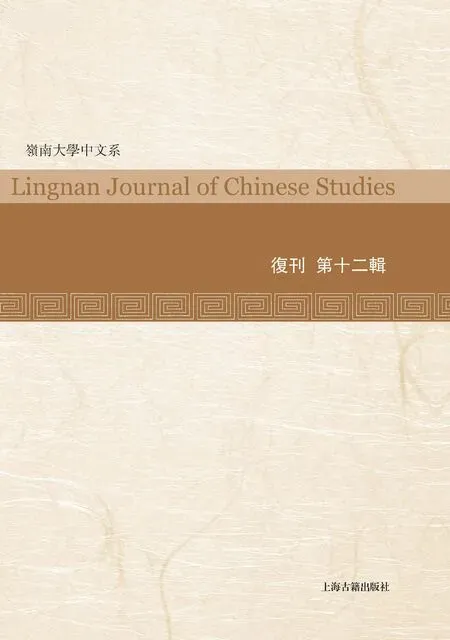從叙事角度看抒情傳統説
2020-03-02傅修延
傅修延
叙事與抒情是一對緊密聯繫的範疇,無論研究的是前者還是後者,都不妨换個立場從對方角度看問題,這就像是兩座燈塔相互照見自身下面的暗處。陳世驤先生的“中國文學傳統從整體而言就是一個抒情傳統”之説(下稱抒情傳統説)①陳世驤著,楊彦妮、陳國球譯:《論中國抒情傳統:1971年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比較文學討論組致辭》,載於陳世驤著,張暉編:《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陳世驤古典文學論集》,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6頁。按,抒情傳統説在海内外學術界產生了較大影響,董乃斌在《中國文學叙事傳統研究·導論》中對此有詳細梳理。參見董乃斌主編:《中國文學叙事傳統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6—7頁。,對叙事學和當前的叙事傳統研究構成了無法回避的挑戰。經過一段時期的反躬自省,筆者個人覺得這一觀點實際上有助於叙事學突破與生俱來的學科局限,建構起更具包容性的理論體系,叙事傳統研究亦可以其為鏡窺見自身不足。為便於説明問題,本文擬先釐定叙事與抒情之間的關係,再從中西差異角度探析抒情傳統説的發生緣由,最後歸納此説給叙事學和叙事傳統研究帶來的諸多啟示。
一、叙事與抒情的多重考量
叙事在漢語語境中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叙事與抒情並列,這是内地從中小學語文課到大學寫作課一直灌輸的觀念,其影響範圍甚為深遠。廣義的叙事則覆蓋了抒情,在叙事學家看來,這是一個捲入因素與涉及層面更多的能指,故事講述人在用包括語言文字在内的各種媒介叙事時,除了傳遞事件信息外,還會或隱或顯地披露立場觀點,或多或少地發表議論感慨,或詳或略地介紹人物與時空環境,等等。不言而喻,除了有意為之的所謂“零度叙事”外(實際上很難做到),這些活動都有可能伴隨著一定程度的情感抒發,就此而言抒情實際上附麗於叙事之中,兩者之間為毛與皮的關係。在這一意義上,“叙事”一詞經常從記叙文寫作課堂上那個内涵狹窄的技術性概念中脱穎而出,變成整個講故事活動的代稱。討論這個問題還應聽取故事講述人的意見,深諳叙事奥秘的汪曾祺主張“一件事可以這樣叙述,也可以那樣叙述。怎樣叙述,都有傾向性”,他不喜歡一些年輕作家“離開故事單獨抒情”,認為還是應該“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筆觸叙事”①汪曾祺:《晚翠文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44—45頁。。隨著小説、電影等叙事門類成為文學的主力軍,叙事在當前已是最重要的文學行為,人們經常用“叙事能力”作為判斷作家水準高下的標準,這些都顯示廣義叙事的運用超過了狹義叙事。
叙事在人們心目中由小叙事向大叙事演變,與叙事學興起的大背景有密切關聯。叙事學(narratology)一詞係從海上舶來,學科意義上的叙事學誕生於20世紀60年代的法國,當時屬於結構主義文學理論的一個分支,其代表人物致力於歸納與叙事有關的種種規律和規則,因而又稱結構主義叙事學或經典叙事學。經典叙事學誕生後不久便因結構主義退潮而失去活力,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和歐洲的一些學者又使這門學科恢復了生機,後經典叙事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戴衛·赫爾曼宣稱自己“是在相當寬泛的意義上使用‘叙事學’一詞的,它大體上可以與‘叙事研究’相替换。這種寬泛的用法應該説反映了叙事學本身的演變”①戴衛·赫爾曼主編,馬海良譯:《新叙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4頁。。“叙事學”與“叙事研究”可以相互替换之説,把叙事學從理論家專屬的象牙塔中解放出來——只要符合“叙事研究”這個更為寬泛的定義,不管是規律探尋、現象研究還是作品分析,統統都可歸入叙事學名下。大陸學界一貫跟風,新世紀以來一股勢頭強勁的叙事學熱潮開始湧動:學術期刊上以叙事為標題的論文觸目皆是②經查中國知網資料庫,2009年3月4日至2019年3月4日這10年中,篇名中包含“叙事”一詞的學術論文共有35 254篇,年均量為3 525篇;篇名中包含“叙述”一詞的學術論文有18 918篇,年均量為1 891篇。兩者相加,年均總量為5 416篇。,高校每年大批量生產與叙事學相關的本科、碩士與博士學位論文。使用頻率的提高還導致了叙事一詞的所指泛化,在此問題上“講好中國故事”這一流行語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覷,一些文章中出現的“叙事”,只有將其理解為“創作”、“歷史”甚至“文化”纔能讀得通。
由此又要提及後經典叙事學的另一標誌性特徵——跨學科趨勢。羅蘭·巴特宣稱“叙事遍存於一切時代、一切地方、一切社會”③羅蘭·巴特著,張寅德譯:《叙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載於張寅德編選:《叙述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頁。,以往人們只在小説、戲劇、影視、歷史和新聞中看到叙事,如今法學、醫學、教育學和社會學等學科也開始了自己的叙事研究,人類學甚至把叙事看作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大動力。《人類簡史》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説智人淘汰尼安德特人的主要原因是會講故事④“如果一對一單挑,尼安德特人應該能把智人揍扁。但如果是上百人的對立,尼安德特人就絶無獲勝的可能。尼安德特人雖然能夠分享關於獅子在哪的信息,卻大概没辦法傳頌(和改寫)關於部落守護靈的故事。而一旦没有這種建構虚幻故事的能力,尼安德特人就無法有效大規模合作,也就無法因應快速改變的挑戰,調整社會行為。”尤瓦爾·赫拉利著,林俊宏譯:《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頁。,牛津大學的人類學家羅賓·鄧巴更指出叙事是人類的獨家本領,其作用是“把有著共同世界觀的人編織到了同一個社會網络之中”⑤“文化中有兩個關鍵的特性,顯然為人類所獨有。這兩個特性一個是宗教,另一個是講故事。”“講述一個故事,無論這個故事是叙述歷史上發生的事件,或者是關於我們的祖先,或者是關於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裏來,或者是關於生活在遥遠的地方的人們,甚至可能是關於一個没有人真正經歷過的靈性世界,所有這些故事,都會創造出一種群體感,是這種感覺把有著共同世界觀的人編織到了同一個社會網络之中。”羅賓·鄧巴著,余彬譯:《人類的演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74頁。。如果説這些研究有什麽共同點,那就是它們都在顯示叙事非文學所能專美,站在這樣的立場,可以看出跨學科趨勢這一提法不夠準確——許多學科本身就與叙事有千絲萬縷的牽連,人們從叙事角度提出問題來研究是遲早的事情。從神話時代起,世界各民族的先民就懂得用講故事的方式來闡釋外部世界和分享個人體驗,把挑選出來的事件按某種邏輯加以編排,聽故事的人便會在不知不覺之中受到影響。讓鮮活的故事來闡述觀點説明問題,效果要強於使用枯燥的數位、圖表和冰冷的理論,這或許就是許多非文學的學者紛紛開口講故事的原因。叙事的外延擴大到如此地步,令《叙事》雜誌的主編詹姆斯·費倫也感到驚訝,他在論及於此時不無譏誚地使用了“叙事帝國主義”(narrative imperialism)這樣的表述①James Phelan,“Who's Here?Thoughts on Narrative Identity and Narrative Imperialism”,in Narrative 13.3:pp.205-210.。
在“叙事帝國主義”這樣的語境中,叙事顯然無法“屈尊”與抒情平起平坐,不僅如此,要想在叙事學的學科體系中為抒情覓一席之地亦非易事。叙事學總體上屬於形式研究,這門學科的創立者最初是想模仿語言學模式歸納出一套置之四海而皆準的叙事語法,而語言學又是以追求“精深細密”的自然科學為師,這就使得經典叙事學在研究態度上也向語言學甚至是自然科學看齊,努力保持冷靜客觀無動於衷。筆者閲讀範圍有限,目前只看到叙事學中的主觀叙述(subjective narrative)中或有容納抒情的位置,傑拉德·普林斯認為主觀叙述來自文本中的顯性叙述者(overt narrator)與故事中的人物,主要體現其思想、情感和對事物的判斷②傑拉德·普林斯著,喬國強、李孝弟譯:《叙述學詞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20—221頁。按,克林斯·布魯克斯與羅伯特·彭恩·沃倫《理解虚構小説》一書中的相關論述,是普林斯劃分主觀叙述與客觀叙述的理論基礎。參見Cleanth Brooks&Robert Penn Warren,Understanding Fiction,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Inc.,1979,p.513.。顯性叙述者為讀者可以明顯察覺到的叙述主體,這個類别中介入叙述者(intrusive narrator)的聲音最為響亮,但此聲音既可能打動讀者,也可能形成對故事講述的干擾。歐美叙事中,介入叙述與事件講述不相融合的現象屢有發生,不耐煩聽宣講或宣洩的讀者,很難忍受亨利·菲爾丁《湯姆·瓊斯》、雨果《悲慘世界》和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中撇開事件進程的大段議論。與此形成鮮明對照,受“寡事省文”精神的影響(詳後),中國叙事中介入叙述和事件講述“兩張皮”的問題很少發生,講完故事後來一段畫龍點睛般的“君子曰”、“太史公曰”或“異史氏曰”,可以起到很好的“卒章顯志”作用。“寡事省文”也導致古代作家在寫人時多用惜墨如金的白描手法,而西方從古希臘羅馬時期起就喜歡以直抒胸臆的長篇獨白來塑造人物,阿波羅尼奥斯《阿耳戈船英雄記》中的美狄亞和奥維德《變形記》中的密耳拉都是受愛火煎熬的人物,她們近乎譫妄的喃喃自語使兩位情感豐富的女性形象躍然紙上①前者見Robert Scholes、James Phelan&Robert Kellogg,The Nature of Narrativ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338;後者見奥維德著,楊周翰譯:《變形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237頁。。對於主觀叙述中的情感氾濫,W.C.布斯在《小説修辭學》的“控制情緒”一節中有過警告,他希望作者專注於講自己的故事,不要動不動就直接介入,應當讓人物來發揮影響讀者的作用②布斯著,華明等譯:《小説修辭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頁。。
從上可見,普林斯、布斯等人只是在説到主觀叙述與介入叙述時旁及抒情,並未對其展開正面討論。在這方面更進一步的是中國的叙事學學者譚君強,他把抒情問題納入叙事學的總體框架,提出了抒情主體這一概念。衆所周知,叙事學領域的許多理論突破都與其擅長的二元區分有關:把“話語”與“故事”分開,為研究故事是怎樣講述出來的開闢了新天地;把“作者”與“叙述者”分開,解釋了令人困惑的“不可靠叙述”現象;在此基礎上把“誰看”與“誰説”分開,有助於辨識叙述中“感知”與“聲音”之間的複雜關係。沿用這種二分法,譚君強試圖將抒情主體從叙述主體中剥離出來:“叙述主體與抒情主體二者是相對而言的,是就其在不同文類中所起到的主要作用而言的。在有些融叙事與抒情為一體的作品中,這樣的主體同樣可以融為一體,或許可稱之為叙述—抒情主體,或抒情—叙述主體。”③譚君強:《論叙事學視閾中抒情詩的抒情主體》,載於《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48卷第3期(2016年5月),第128頁。如果説在小説中,讀者更多察覺到叙述者及其聲音的存在,那麽在以抒發情感為主的詩歌中,為讀者所感知的主要是抒情人(lyricizing instance)及其聲音。譚君強認為較之於叙述者,抒情人與作者的關係要密切得多,有時甚至與作者難分彼此。譚文在論述中以拜倫的《堂璜》為證,愚以為這方面最典型的還是他的《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長詩中出現了一位動輒以大段議論打斷叙述進程的抒情人(學界過去稱抒情主人公),故事主人公——旅行者恰爾德·哈洛爾德的風頭完全被這位喧賓奪主的抒情主人公蓋過,最後一章中哈洛爾德的形象已經黯淡到可有可無的地步。拜倫在長詩序言以及相關信件中,多次提到自己與哈洛爾德以及那位“用自己的口吻説話的作者”之間的關係①拜倫著,楊熙齡譯:《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頁、第193—198頁。按,拜倫自序與相關信件均收入該書。長詩第四章以拜倫致約翰·霍布豪斯的信為開篇,信中云:“關於最後一章的處理,可以看出,在這裏,關於那旅人,説得比以前任何一章都少,而説到的一點兒,如果説,跟那用自己的口吻説話的作者有多大區别的話,那區别也是極細微的。事實上,我早已不耐煩繼續把那似乎誰也決不會注意的區别保持下去。”,這些内容為研究叙述—抒情主體提供了寶貴材料。從叙事學角度研究抒情問題目前已掀開了序幕,不久的將來這方面一定會有更多成果湧現。
二、從中西差異角度看抒情傳統説的提出
叙事學和“叙事帝國主義”均為西方語境中的產物,西方叙事以神話、史詩和戲劇等為先導,這些基本上都可歸入文學藝術範疇,所以亞理斯多德會把對它們的研究稱為《詩學》,此一事實決定了西方叙事傳統從一開始就有如鹽在水般的詩性成分。而中國文學研究領域之所以會把抒情傳統單獨拈出,或許是因為我們歷史上的史官文化先行,這種狀況導致叙事一詞首先從政治與歷史領域中產生,也就是説古人的叙事概念最初不是發端於文學。
為了更準確地把握“叙事”一詞的所指,需要對這個漢語詞彙的本義和形成作點歷史考察。古代文獻中“叙”與“事”二字連用,筆者看到的一個出處是在《周禮·春官宗伯》中: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
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掌叙事之法,受訥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内史讀之。王制禄,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内史掌書王命,遂貳之。②鄭玄等注:《十三經古注》第3册,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502—504頁。
這裏的“叙事”實際上是依序行事的“序事”——古人筆下“叙事”與“序事”常常可以换用,所謂“掌叙事之法,受訥訪,以詔王聽治”,指的是按照尊卑次序行事的法則,接納臣下謀議,轉告國王處治。《周禮》中與“事”相連的“叙”字,差不多都有“依序而行之”的内涵:如“地官司徒”中的“凡邦事,令作秩叙”①鄭玄等注:《十三經古注》第3册,第413頁。,其中的“秩叙”即秩序;“天官塚宰”中的“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進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會,六曰以叙聽其情”②鄭玄等注:《十三經古注》第3册,第363頁。,説的也是以官府的六種序次,來規範、約束官員的爵禄權柄。
從上可見,叙事一詞最初屬於政治或曰行政範疇,與講故事活動貌似風馬牛不相及,然而從實質上看,最初的叙事與後來的叙事之間距離並不遥遠:發生在朝廷官府之中的那種依序而行之的叙事,其主要表現應為天子、大臣、諸侯周圍的奏事與論事,一旦這個詞從政治領域轉移到日常生活中來,它的所指必然更多對應為對“事”的傳播。再則,我們祖先選擇叙事這個詞作為符號也是切中肯綮的,叙事是一種沿著時間箭頭單向單線開展的連續性活動,所謂單線是指同一時間内只能叙述一個事件,如此一來事件的叙述次序就成了至關重要的問題,叙事謀略、智慧和技巧往往具體體現在這個次序上。後人劃分的一些叙事類型,如順叙、倒叙、插叙之類,也是根據次序來劃分。對秩序問題的重視與古代禮制有關。“禮”在古代中國的作用是“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因此一切社會活動都要依序而行,即便是在今天,人們仍在根據“以叙正其位”的精神安排各種座次。正因為有這樣的文化環境,纔會有“叙事”、“序事”這類富於秩序感的名稱,可以説這個名稱極具封建社會的特色。對“叙”、“事”二字還應分而析之。“叙”在《説文解字》中給出的意思是“次第”,段注中補了一句——“古或假序為之”,這些與上文完全吻合。“叙”字的“記叙”、“叙説”等含義出現得也不算太晚,《國語·晉語三》有“紀言以叙之,述意以導之”的提法③左丘明撰,韋昭注:《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09頁。,其中“叙”已微有“述布”之義。“事”這個高頻字則出現得晚一些,《説文解字》中“事”與“史”同部,王國維認為殷商時尚無“事”字,故以“史”為“事”①“古之官名,多由史出。殷周間王室執政之官,經傳作卿士,而毛公鼎、小子師敦、番生敦作卿事,殷墟卜辭作卿史,是卿士本名史也。又天子諸侯之執政,通稱御事,而殷墟卜辭則稱御史,是御事亦名史也。又古之六卿,《書·甘誓》謂之六事。司徒、司馬、司空,《詩·小雅》謂之三事,又謂之三有事。《春秋左氏傳》謂之三吏。此皆大官之稱事若吏即稱史者也。”王國維《釋史》,載於《觀堂集林》第1册,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69—270頁。。史學界對“史”字的解釋雖有些分歧,但都未越出“職司記述的官員”這個範圍,故《説文解字》釋“史”為“記事者也”。“叙”與“事”兩字合成一詞後,“有秩序地記述”之義更為顯豁。
史官文化先行帶來的一大影響,便是叙事在很長時期内被看成是專屬於史家的行為,劉知幾在《史通·叙事》中以《尚書》與《春秋》為例,提出叙事的原則是“寡事省文”:“夫國史之美者,以叙事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②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頁。《尚書》是中國最早的歷史文獻,《春秋》為古代編年體史書之祖,從它們當中提煉出來叙事原則,應該説更適用於史學領域的叙事。“寡事省文”要求惜墨如金,按照這一標準,不但揮灑文字的主觀抒發要被驅逐,就連講述的事件也須儘量精簡。文學究其本質是一種靠情感和體驗去感染讀者的藝術,如果一味删削儉省,擠乾掉一切多餘的“水分”,那麽剩下來乾巴巴的東西就不是文學了。史官文化先行意味著後起的文學叙事要向前面的歷史叙事看齊,在“史貴於文”價值觀的支配下,我們過去總是用史家的標準來衡量所有的叙事:“史才”即講故事的本領,一部小説若是被譽為《春秋》、《左傳》,一位作家若是被説成“史遷”、“班馬”,不啻是對其作品和叙事能力的最高褒獎。這種唯史家馬首是瞻的語境,使得叙事傳統在人們心目中更多指向史家之文,事實上這一傳統也是在《尚書》、《春秋》等史著中初露端倪。至此我們能夠理解,在叙事傳統之外提出抒情傳統,在西方或許没有多大必要,在中國則有某種“去蔽”意義——有助於今人穿透史官文化的影響,從詩學而非史學的角度去尋找我們文學傳統的真正源頭。亞理斯多德在《詩學》中説史家與詩人所叙之事有“已發生”與“可能發生”之别③亞理斯多德著,羅念生譯:《詩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28頁。,兩者之間既有這種質的不同,用同一個標準來衡量便不合適。
史官文化屬上層建築,中西之間更為根本的差異還在於經濟基礎或者説生產方式。西方人傳統的海洋、遊牧和狩獵活動,使其習慣於在大海、草原和大漠之間穿行,因此他們的文學從古到今都不缺乏旅途故事。希臘神話中尋找金羊毛的傳説以及荷馬史詩對遠征與還鄉故事的講述,打開了流浪漢叙事的閘門,從這道閘門中湧出的既有中世紀外出遊俠的騎士傳奇,還有16世紀拉伯雷的《巨人傳》、17世紀無名氏的《小癩子》、18世紀笛福的《魯濱孫漂流記》、19世紀馬克·吐温的《哈克貝利·芬歷險記》、20世紀凱魯亞克的《在路上》以及今年剛獲奥斯卡獎的《綠皮書》等。連方興未艾的太空遨遊電影也在這個序列之中——身著宇航服的太空漫遊者看到的宇宙景觀固然神奇,但其主要行動仍然不外乎奔向遠方和返回家園,這與伊阿宋尋找金羊毛以及俄底修斯回家没有本質差别。需要特别指出,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雖風塵僕僕地奔波於旅途,卻幾乎都不以旅途勞頓為苦——魯濱孫心中總有“偏向虎山行”的衝動,霍爾頓不斷地想著要“離開一個地方”①“但是我(按即魯濱孫)的倒楣的命運卻以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逼著我不肯回頭。儘管有幾次我的理性和比較冷靜的頭腦曾經向我大聲疾呼,要我回家,我卻没有辦法這樣做。這種力量,我實在叫不出它的名字;但是這種神秘而有力的天數經常逼著我們自尋絶路,使我們明明看見眼前是絶路,還是要衝上去。”笛福著,徐霞村譯:《魯濱孫飄流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頁。“我(按即霍爾頓)流連不去的真正目的,是想跟學校悄悄告别。我是説過去我也離開過一些學校,一些地方,可我在離開的時候自己竟不知道。我痛恨這類事情。我不在乎是悲傷的離别還是不痛快的離别,只要是離開一個地方,我總希望離開的時候自己心中有數。”塞林格著,施咸榮譯:《麥田裏的守望者》,桂林:灕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5頁。,文化基因決定了他們無法老老實實地待在家中。
相比之下,農耕生活導致國人更為留戀身邊的土地家園,故土難離雖為人之常情,但戀土情結已成為中國文化最為突出的標誌。費孝通《鄉土中國》的英文標題為Earthbound China(此名得之於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這個書名直譯出來就是“綁在土地上的中國”。這種安土重遷的文化中,不可能孕育出西方那種以浪跡天涯為樂的旅途叙事。或許有人會説中國古代也有許多遊記,但若仔細分析,便會發現旅行者只是在範圍並不太大的空間内移動,就連張騫的“鑿空西域”從地圖上看也未向西走出很遠。卡爾·雅斯貝爾斯注意到人類各大文明中心分佈的範圍都未超出北緯25度至35度區間②卡爾·雅斯貝爾斯著,柯錦華等譯:《智慧之路》,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頁。,在這個由西南歐洲、北非綿亘至東亞的狹長地帶上,西邊的各文明中心相互間靠得較近,呈現出一種以地中海為中心的抱團狀態,這意味著西方人作跨國乃至跨洲的旅行並不是那麽困難,遠方對他們來説也不是真正的遥不可及——荷馬史詩提到一陣風就把船隻吹到另一個國家甚至是另一片大陸。而在這個長條狀地帶最東邊的華夏文明,處在與地中海文明群相對疏離的狀態,東臨茫茫大海、西有“世界屋脊”的地理格局,使我們祖先的空間移動——尤其是東西向移動受到很大限制,跨越洲際的長途旅行對他們來説更是難以想象。至於那些涉及遠方和異域的小説如《西遊記》與《鏡花緣》等,其中的叙述往往顯示出作者不知道什麽是真正的遠方和異域——《西遊記》講述的是西天取經的故事,走在西天路上的唐僧師徒仍為中華景觀所環繞①《西遊記》所寫西天國家的風土人情、社會結構、政治體制乃至城池街道等皆與大唐相似,更有趣的是作者為了省事,常將我們這邊文人的寫景狀物詩詞“植”入書中,結果造成西天路上出現許多東土事物。如第八十八回取經人進入玉華國:“三藏心中暗喜道:‘人言西域諸番,更不曾到此。細觀此景,與我大唐何異!所為極樂世界,誠此之謂也。’又聽得人説,白米四錢一石,麻油八厘一斤,真是五穀豐登之地。”吴承恩著,黃肅秋注釋,李洪甫校訂:《西遊記》(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1076頁。;《鏡花緣》中多九公、唐敖等人雖然到了海外,他們看到的君子國、兩面國和犬封國竟與《山海經》中的陌生人想象同出一轍。遠方的風景與陌生人既然不是古人生活中的常態,自然也就不會成為文學的主要表現對象,強己所難的“硬寫”難免會露出諸多破綻。
以上就農耕與海洋文化所作的中西比較,讓我們想到本雅明所説的“遠行人必有故事可講”:“人們把講故事的人想象成遠方來客,但對家居者的故事同樣樂於傾聽。蟄居一鄉的人安分地謀生,諳熟本鄉本土的掌故和傳統。若用經典原型來描述這兩類人,那麽前者現形為在農田上安居耕種的農夫,後者則是泛海通商的水手。”②瓦爾特·本雅明:《講故事的人》,載於漢娜·阿倫特編,張旭東、王斑譯:《啟迪:本雅明文選》,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96頁。參照這一説法,中西叙事傳統或可分别用農夫型和水手型來形容。水手與農夫的叙事各有千秋難分高下,但兩者的區别也是非常明顯的。水手飄洋過海見多識廣,對外部世界的萬千殊象見慣不驚,而農夫因為對熟人社會多有依賴,一旦離開自己的田園故土與父老鄉親——這是免不了的事情,便容易表現為情感上的動盪與心理上的不適。講故事主要是講述主人公的行動,任何人都不可能永遠待在原地不動,因此如果要問中國文學中什麽氣息最濃,人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鄉土氣息;要問中國抒情傳統“抒”的是什麽“情”,人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抒發離愁别恨。漢民族從某種意義上説是一個鄉愁的民族,中國文學史上充滿了吟詠“單寒羈旅”之作①“日來漸慣了單寒羈旅,離愁已淺,病緣已斷。”冰心:《往事》(二),載於《冰心文集》第三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頁。按,“漸慣了單寒羈旅”一語出自近代詞人譚獻的《金鏤曲·江干待發》。,古人不管是望月、憑欄、聽笛、賞花和觀柳,總是會勾起對故鄉和親人的無邊思念。《鹽鐵論》卷七“備胡”對此有生動描述:
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絶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我今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②桑弘羊撰,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定本),下册,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497—498頁。
《鹽鐵論》為辯論記録(郭沫若稱之為“對話體的歷史小説”),此處對戍卒及其家人的心理書寫卻近乎抒情。漢民族歷史上少有遠征,也没有像西方那樣的史詩,引文對此提供了一個文化角度的解釋:離鄉背井有違農耕民族的天性,我們的古人因此視異域為畏途,而世界上那些海洋與遊牧民族的史詩,都不乏長途遷徙與大規模征戰的背景。早在“群經之首”的《易經》中,就有一些以旅途為險境的卦辭,如“征夫不復”(《漸》)、“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明夷》)和“旅瑣瑣,斯其所取災”(《旅》)等。後來的屈原因有流放外地的親身經歷——現在看範圍並未超出湖北湖南一帶,更把去國懷鄉之情抒發到極致。詩中的抒情主人公一方面意識到世界之大無所不具,(“思九洲之博大兮,豈惟是有其女。”)另一方面又承認自己不可理喻地“獨懷故宇”。(“何所獨無芳草兮?爾獨懷乎故宇?”)“獨懷故宇”説白了,就是故土之外雖有世界,卻不是屬於自己的世界③“蓋屈子心中,故都之外,雖有世界,非其世界。”錢鍾書:《管錐編》(二),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910頁。,根植於農耕文化的這種心理從古代一直蔓延下來,直到工業化運動來臨之後,我們這裏纔湧動起一股嚮往遠方的熱潮④“詩與遠方”一語如今在網上屢屢出現,許多人都在談論“一場説走就走的旅行”,實現“世界這麽大,我想去看看”的願望。。
鄉愁或曰鄉情雖然只是人類需要抒發的情感之一,但在鄉土社會中,人們的各種思慮和牽掛均與其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傳世作品多有對鄉人、鄉情、鄉景、鄉音、鄉食和鄉味的精彩描寫,給人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世説新語·識鑒》中的張翰因為想起了老家的菰菜羹和鱸魚膾,立馬決定辭官千里還鄉①“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世説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93頁。;《法顯記》寫法顯乘船回國時偏離航線數月,最後登岸時“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②釋法顯撰,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46頁。。這兩則鄉愁叙事中,“蓴鱸之思”和“藜藿依然”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鄉愁一般來説指向人們的生身立命之處,但這種指向並不是完全固定的③“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劉皂《旅次朔方》,一作賈島《渡桑乾》。,同村、同縣、同市乃至同省之人都在“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之列,而到了遠隔重洋的國外,鄉愁又可以發散到整個神州。古人將“社稷”作為國家的代名詞,“社”為地神,“稷”為穀神,因此國家就是土地莊稼的集合。漢語中“家”與“鄉”不僅緊密相聯,它們還與“邦”、“國”等字組成覆蓋範圍更大的搭配——“鄉邦”、“家國”之類的詞語,顯示“家”、“鄉”乃是“邦”、“國”的細胞和基礎。家國情懷之所以被視為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因為有這種把家園和邦國視同一體的認識傳統,這種傳統使無數小家聚攏成血脈相連的鄉邦,無數鄉邦匯合為“和合萬邦”的華夏。屈原眷戀的“宗邦”只指向楚地,而在後世被其感動的五湖四海讀者心中,這個“宗邦”代表的是整個中國。愛國不是一種抽象的情感,它一定要落實到具體的人和物上,對許多作家詩人來説,腳下這片土地上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是家鄉和祖國的符號和化身,這些對象的吟詠者因此也往往被視為愛國詩人④域外文學也有這種情況,萊蒙托夫《祖國》一詩所謳歌的,都是農舍、馬車和林間小路之類的鄉村景物。。
三、抒情傳統説對叙事學與中國叙事傳統研究的啟示
抒情傳統説給叙事學帶來的啟示,是這個領域過去忽視了對情感的研究。如前所述,叙事學是由一群傾慕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法國學者所創立,他們口口聲聲説以語言學為師,其更深的意圖還在於向物理學等“硬科學”看齊。亨利·詹姆斯最早用“窗洞”來形容後來成為叙事學基本範疇的視角概念,他強調“如果没有駐在洞口的觀察者,换句話説,如果没有藝術家的意識,便不能發揮任何作用”①亨利·詹姆斯,項星耀譯:《一位女士的畫像·作者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7頁。。然而這一警告並未引起足夠重視,語言學模式後來雖逐漸從叙事學中淡出,西方學者的“物理學欽羨”(physics envy)並未有所減弱,“精深細密”至今仍是許多人不懈追求的目標。國内叙事學在西方影響下也有明顯的形式論傾向,一些人甚至把研究對象當成解剖桌上冷冰冰的屍體。然而叙事本身是有情感温度的人際交流,人類學家把講故事看成是一種抱團取暖的行為,而要讓有體温的人真正靠攏到一起,便不能不動之以情②傅修延:《人類為什麽要講故事:從群體維繫角度看叙事的功能與本質》,載於《天津社會科學》總第221期(2018年第4期,2018年7月),第127頁。。由此可以得出這樣一種認識,講故事不是一種“無情”的行為,叙事學因此也不應是“無情”之學。
“無情”給叙事學造成的損害,是這門學科至今仍未有效地幫助人們理解叙事現象和闡釋叙事作品。經典叙事學如前所述對語言學亦步亦趨,大衛·赫爾曼一針見血指出其弊端所在:“語言學並不對具體言説做出解釋,而是對符合語法的形式和序列得以產生和處理的可能條件進行一般性的説明。同樣,叙事學家們也認為,不應該將叙事的結構分析看作闡釋的侍女,從根本上來説,叙事學的目的就是做分類和描述工作。”③大衛·赫爾曼著,馬海良譯:《叙事理論的歷史(上):早期發展的譜系》,載於詹姆斯·費倫、彼得·J·拉比諾維茨主編:《當代叙事理論指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頁。對闡釋的蔑視以及對叙事語法的狂熱追求,導致這門學科使用的範疇不斷細化,概念與術語隨之層出不窮。莫妮卡·弗盧德尼克據此諷刺叙事學是一門派不上用場的“應用科學”:“叙事學既是關於叙事文本的一門應用科學,也是一種理論。作為一門應用科學,叙事學面對的批評挑戰是:‘這又能怎麽樣?所有這一切細分再細分的範疇對於理解文本有什麽用呢?’”④莫妮卡·弗盧德尼克著,馬海良譯:《叙事理論的歷史(下):從結構主義到現在》,載於詹姆斯·費倫、彼得·J·拉比諾維茨主編:《當代叙事理論指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頁。然而後經典叙事學這方面的糾偏並不徹底,叙事學如今雖然已與叙事研究等義,但是西方學者建構理論大廈的熱情一時半刻難以熄滅,筆者曾戲謔地説後經典叙事學提供的理論工具箱依然沉重,結果“只有那些理論上的大力士纔能拎得起來”①傅修延:《中國叙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7頁。。
“無情”造成的另一損害是與創作實踐的脱節。應該承認,西方叙事學在剖析“叙事是什麽”上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績,這是其“精深細密”追求的正面效應,不過弄清楚“叙事是什麽”應當是為了回答“怎樣叙事”,一些開宗立派者卻因自己的理論自負而對後一問題不予理睬。19世紀在西方便有“批評的世紀”之稱,20世紀以來批評理論的生產更趨繁榮,不少人覺得自己創建的理論體系具有完全的獨立自足性,不屑於再像過去的批評家那樣與具體的創作實踐掛起鉤來。這方面羅蘭·巴特一度走得最遠:“叙述者和人物主要是‘紙上的生命’。一部叙事作品的(實際的)作者絶對不可能與這部叙事作品的叙述者混為一談……因為(叙事作品中)説話的人不是(生活中)寫作的人,而寫作的人又不是存在的人。”②羅蘭·巴特:《叙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第29—30頁。“紙上的生命”没有温度,將作品中鮮活生動的表述視作蒼白的幻象,把真實的作者排除在研究視閾之外,不啻是公然宣佈與創作方面井水不犯河水。我們無法想象《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中的抒情主人公(即巴特所謂“説話的人”)與拜倫之間没有關係,前者直抒胸臆的滔滔議論難道不是與後者在上議院發表的激烈演講同出一轍嗎?筆者個人一直覺得叙事學的許多成果可以為創作和闡釋方面所用,叙事學作為“一門關於叙事文本的應用科學”未獲應用,主要責任不在他人還在這門學科自身。
抒情傳統説對叙事傳統研究的啟示,在於提醒我們關注自身文脈中不同於他人的個性。陳世驤先生説:“當我們説起一種文學的特色為何時,我們已經隱含著將之與其他文學做比較了。而如果我們認為中國抒情傳統在某種意義上代表東方文學的特色時,我們是相對於西洋文學説的。”③陳世驤著,楊彦妮、陳國球譯:《論中國抒情傳統》,載於陳世驤著,張暉編:《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陳世驤古典文學論集》,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3—4頁。筆者理解這是説東方文學“相對於西洋文學”更重抒情,並非否認中國文學中叙事傳統的存在,要知道全世界没有哪個民族没有自己世代相傳的講故事傳統,所不同的只是講故事的方式。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對抒情傳統説作一點自己的詮釋:東方叙事的特色在於更重抒情,用前引汪曾祺的説法就是更傾向於“用抒情的筆觸叙事”。劉鶚在《老殘遊記·自叙》中説馬和牛因缺乏靈性而不會哭泣,人類則因靈性而生感情,這就有了宣洩感情的各種哭泣:
《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為蒙叟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為杜工部之哭泣;李後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於《西廂》,曹雪芹寄哭泣於《紅樓夢》。王之言曰:“别恨離愁,滿肺腑難陶洩。除紙筆代喉舌,我千種想思向誰説?”曹之言曰:“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意?”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萬豔同杯”者,千芳一哭,萬豔同悲也。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鴻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①劉鶚《自叙》,載於劉鶚著,陳翔鶴校,戴鴻森注:《老殘遊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頁。
值得注意的是,引文列舉的宣洩形式不僅有小説,詩詞辭賦乃至戲曲繪畫俱在其中。劉鶚用“哭泣”指代傳統叙事的抒情傾向,這一妙喻畫龍點睛,勾勒出史上一系列故事講述人的悲戚神情。事實確是如此,古往今來訴諸文字、聲音和圖像的文藝叙事,凡能傳世的大多像是哭泣、流淚或歎息,從屈原的“長太息以掩涕兮”到八大山人的“墨點無多淚點多”,給人留下的都是長籲短歎的印象。
抒情傳統説還有助於開闊叙事傳統研究的視野。一味強調叙事,我們的目光就會只盯著小説和前小説、類小説這樣的散體文學,實際上詩體文學對叙事發育亦有孳乳之功,董乃斌先生目前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國詩歌叙事傳統”包含了這一内容,其主編的《中國文學叙事傳統研究》列有“古典詩詞的叙事分析”、“漢魏隋唐樂府叙事論”和“唐賦叙事特徵述論”等專章②董乃斌主編:《中國文學叙事傳統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董乃斌先生的研究以抒情與叙事兩大傳統的“交響共鳴”為出發點,這一提法有利於避免只從“抒情”或“叙事”角度看問題的片面,筆者個人從中獲益尤多。有了“交響共鳴”這一意識,我們就會發現作者所叙之事固然重要,叙事中滲透的情感亦為作品的價值所在。從前述鄉土叙事中可以看到,人們對自己生身立命之處的娓娓講述,無不浸染著對那方土地的憐惜與愛重。筆者在《人類為什麽要講故事:從群體維繫角度看叙事的功能與本質》一文中提到,講故事的最終目的在於用情感紐帶維繫著自己所屬的群體,不管是民系、民族還是國家,所有“想象的共同體”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吴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的建構與維繫都有叙事的一份功勞。最後要説的是,如果説“想象的共同體”是建構出來的,那麽不管是抒情傳統還是叙事傳統,也與研究者的建構甚至是“發明”有關,《傳統的發明》一書就主張許多傳統是被後人“發明”出來的②霍布斯鮑姆、蘭格編,顧杭、龐冠群譯:《傳統的發明》,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有鑑於此,筆者覺得還是公允一點好,兩大傳統“交響共鳴”這一提法似乎更能體現中國文學的本來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