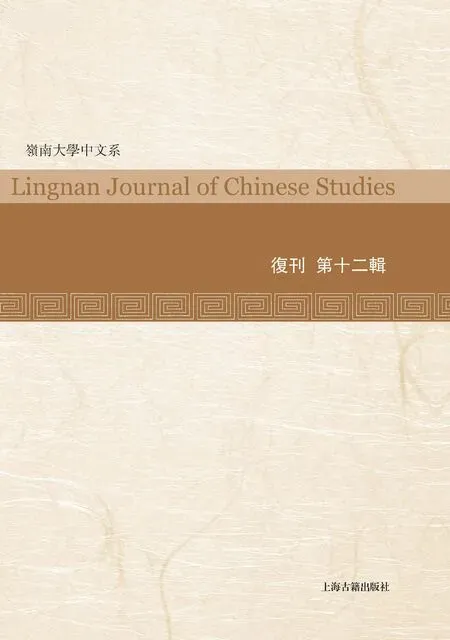叙事與抒情:《紅樓夢》詩學中的風格論
2020-03-02歐麗娟
歐麗娟
一、前 言
《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傳統説部的巔峰,集叙事技巧與人性内涵之大成,此已為後世所公認,被稱為“叙述美典”;而其作為一部淪肌浹髓的“情書”,其濃厚的抒情性固亦毋庸置疑,欲觀其中抒情與叙事的交響共鳴,自有諸多角度可以切入深論,例如當今學界在探討所謂“抒情傳統”的看法裏,清朝的《紅樓夢》、《儒林外史》便被視為該發展過程中高峰式的總結①高友工:《中國叙述傳統中的抒情境界》,載於《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版。此説尚非定論,詳見龔鵬程《成體系的戲論:論高友工的抒情傳統》,載於《清華中文學報》第3期(2009年12月),第155—190頁。。單單以創作形式觀之,小説與詩歌的結合甚至構成了“奇書體”的特徵,是為明清六部長篇章回小説的共同性之一②詳參浦安迪(Andrew H.Plaks)講演,陳玨整理:《中國叙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可見叙事作品中的詩歌自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價值。
尤其是,詩歌作為傳統文人抒情言志之主要載體,標誌了精英文化的高等位階,不僅是中國抒情文學的精華,特别在《紅樓夢》中更是不可或缺的内容構成,與人物的性格、命運、生活處境緊密結合,於是成為情節發展的動能之一。可以説,曹雪芹以其詩人的才分,將傳統詩詞的精髓融入叙事中,有機地參與了叙事範疇,更與人物塑造相互作用,彼此形成完美的融合,堪稱説部第一的成就。而該等境界之所以無出其右,導因便在於此一嵌入詩詞的做法不僅是“奇書體”通見的一種美學策略而已,更應該注意者,即曹雪芹作為“降格”的創作者,在對小説文類的反省中,通過宣揚貴族之禮教文化,包括才媛之文化教養,以提升《紅樓夢》所屬文類的階級地位,維持菁英階層的創作尊嚴。這一點,實為曹雪芹與其他奇書體小説家本質上最不相同之處,而《紅樓夢》也不宜與其他奇書的格調混為一談③詳見歐麗娟:《論〈紅樓夢〉對小説文類的自我反省》,載於《成大中文學報》第62期(2018年9月),第45—86頁。。
倘謂《紅樓夢》乃是以事為體、以詩為魂,運詩心以叙事,並不為過,深諳其創作旨意的脂硯齋道:“余所謂此書之妙,皆從詩詞句中泛出者,皆係此等筆墨也。”④甲戌本第二十五回評語。脂硯齋等評,陳慶浩輯校:《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增訂本)》,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478頁。以下所引脂批,皆出自此書,僅標示版本、回數與頁碼,不一一加注。可以説,把握書中的詩詞筆墨,乃是真切領略“此書之妙”的必要法門。不僅此也,通覽全書,可見《紅樓夢》中針對詩歌創作的評論甚多,包括體裁規範、題材特徵、結構布局、用字遣詞、摘句批評,對於限韻、分韻、聯句等各種創作競賽亦充分呈現,甚至安排了長達兩回的香菱學詩,展現了完整的詩學體系①詳見歐麗娟:《詩論紅樓夢》,臺北:里仁書局2001年版。。而小説中透過各方人物對於詩歌風格的多次討論,更是《紅樓夢》詩學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再度證成曹雪芹為提升小説所灌注的心血。
因為,在包括詩歌在内的藝術分析中,“風格論”不僅是其中的一環,甚至更堪稱最具有涵蓋性的範疇,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指出:“談論風格,是談論藝術作品的總體性的一種方式。”②蘇珊·桑塔格:《論風格》,載於蘇珊·桑塔格著,程巍譯:《反對闡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頁。若將此一總體性加以拆分,J.Middleton Murry將表現技巧(technique of exposition)、作家個性(personal idiosyncrasy)與文學最高成就(the highest achievement of literature)同列為風格的三個層面③J.Middleton Murry,The Problem of styl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0),p.8.,涵蓋了作品、作家、批評三個範疇,幾屬全面。衡諸書中衆釵在詩歌創作現場所涉及的風格表述,也大致都有所符應,足以形成專門議題,助成吾人對《紅樓夢》詩學内涵的完整認識。以下即分論之。
二、“體”:風格的呈現
在中國傳統文論中,其實已經出現“風格”一詞,見諸《文心雕龍·議對篇》謂仲瑗、長虞、陸機等人“亦各有美,風格存焉”④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版,第462頁。,此處的“風格”已頗接近現代的意義。此外,與風格有關的重要概念,即為“辨體”論,而對於文學創作中“體”之功能與認識,誠為中國古典文學理論之重要關目⑤其先行研究可見諸徐復觀:《〈文心雕龍〉的文體論》,載於《中國文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版。關於“體”字之分析,可參顔崑陽:《論“文體”與“文類”的涵義及其關係》,載於《清華中文學報》第1期(2007年9月),第9—43頁。,《文心雕龍》的分體論法又為其中之大者,此後影響深遠的宋代嚴羽《滄浪詩話》,更系統地論列出自六朝至宋代的“長吉體”、“元嘉體”、“永明體”、“齊梁體”、“南北朝體”、“唐初體”、“盛唐體”、“大曆體”等等不同風格,洋洋大觀。
在《紅樓夢》的多處風格表述裏,正有一處是以“體”論之,見第七十回:
寶玉一壁走,一壁看那紙上寫著《桃花行》一篇……寶玉看了並不稱贊,卻滾下淚來。便知出自黛玉,因此落下淚來,又怕衆人看見,又忙自己擦了。因問:“你們怎麽得來?”寶琴笑道:“你猜是誰作的?”寶玉笑道:“自然是瀟湘子稿。”寶琴笑道:“現是我作的呢。”寶玉笑道:“我不信。這聲調口氣,迥乎不像蘅蕪之體,所以不信。”寶釵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首只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不成!一般的也有‘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媚語。”寶玉笑道:“固然如此説。但我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句,妹妹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衆人聽説,都笑了。①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5年版,第七十回,第1092頁。以下所引小説文本,皆出自此書,僅隨文標示回數,不再一一加注。
此一長段對話,隱含了關於風格成因的幾個重要思考,層層曲折辯證,有待一一擘析。首先可以看到,作為寶玉、寶琴、寶釵三人討論的焦點,林黛玉《桃花行》所呈現的鮮明特色,成為與衆不同的專屬風格,足賴以區隔於其他。而與之構成差異、對比的“蘅蕪之體”,其中所謂的“體”乃是中國傳統文論的專有語彙,根據王運熙《中國古代文論中的“體”》一文中所闡述的看法,“體”乃“指作品的體貌、風格,其所指對象則又有區别,大致上可以分為三種。一是指文體風格,即不同體裁、樣式的作品有不同的體貌風格。……二是指作家風格,即不同作家所呈現的不同體貌。……三是指時代風格,即某一歷史時期文學作品的主要風格特色”②王運熙:《中國古代文論管窺》,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版,第24頁。又載於《中古文論要義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頁。。很明顯地,小説家所謂的“蘅蕪之體”,指的是作家風格,以反映寶釵所專屬的創作特色。
更精細地説,此處所用之“體”,乃就其原始訓詁字義“聯類延展”為一般性概念,可指一切實在事物由直觀所認識到整體表象性的“式樣姿態”,是為“樣態義”;而所謂的文章“樣態”,指的是作品完成之後,整體直觀所呈現的“式樣姿態”,實乃融合了語言形式與題材内容所成之“美感形相”,可用各種形容性語彙加以描述,例如典雅、清麗、雄渾、平淡等③參顔崑陽:《論“文體”與“文類”的涵義及其關係》,第13、18頁。。於是因其樣態之特殊而成為一家的主要面貌。《紅樓夢》詩學中“體”的概念於此明揭而出,而既有由薛寶釵所專屬的“蘅蕪體”,自也包括其他各種不同的“體”,在該叙述脈絡中,便隱含了由林黛玉所建構的“瀟湘體”,推而擴之,實還有由史湘雲所代表的“枕霞體”,以及由薛寶琴所形塑的“寶琴體”。
果然,小説中其他各處所演繹的風格論,雖未使用“體”字,卻承襲了傳統常見的風格表述,展示各個詩家的文筆殊異之處,諸如第四十九回:
寶釵因笑道:“我實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個香菱没鬧清,偏又添了你這麽個話口袋子,滿嘴裏説的是什麽:怎麽是杜工部之沉鬱,韋蘇州之淡雅,又怎麽是温八叉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放著兩個現成的詩家不知道,提那些死人做什麽!”湘雲聽了,忙笑問道:“是那兩個?好姐姐,你告訴我。”寶釵笑道:“呆香菱之心苦,瘋湘雲之話多。”湘雲、香菱聽了,都笑起來。
此處清楚可見,歷代積澱成形的唐詩風格説直貫而下,成為閨閣才媛的基本詩學常識,史湘雲所叨念的唐詩描述,可追溯於詩話大興的宋代論壇,嚴羽早已拈出“太白之飄逸”、“子美之沉鬱”之語①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臺北:里仁書局1987年版,《詩評》,第168頁。,在此基礎上推而擴之,形容各詩家特殊風格之最有代表性者,乃如明代高棅《唐詩品彙·總叙》所云:
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大曆、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温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②高棅編選:《唐詩品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頁。
很明顯地,此説即為湘雲論唐詩風格的直接根據,兩説如出一轍。而類似的表述法也頻頻再現於小説裏兩次詩社競賽後的評比活動中,如第三十七回詠白海棠時,諸詩家共以同題分韻的規範尋思擬句,全數完成後並排展列、評比高下,社長李紈發揮盟主的詩學權威,道:“若論風流别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稿。”黛玉、寶釵之作各有千秋,因此脂硯齋在黛玉海棠詩“倦倚西風夜已昏”一句旁,批道:
一人是一人口氣。逸才仙品固讓顰兒,温雅沉著終是寶釵,今日
之作,寶玉自應居末。①己卯本第三十七回批語,第582頁。
並進而否定其他小説中對詩詞的僵化運用,謂:
最恨近日小説中,一百美人詩詞語氣,只得一個豔稿。②己卯本第三十七回批語,第580頁。
此所以清朝評點家張新之呼應云:
書中詩詞……其優劣都是各隨本人,按頭製帽。故不揣摩大家高唱,不比他小説,先有幾首詩,然後以人硬嵌上的。③張新之《紅樓夢讀法》,載於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版,卷三,第156頁。
後續到了第七十回重建桃花社的《詠柳絮詞》一場,衆人分拈詞牌各自填詞,當寶釵的《臨江仙》完成後,衆人拍案叫絶,都説:
果然翻得好氣力,自然是這首為尊。纏綿悲戚,讓瀟湘妃子,情致嫵媚,却是枕霞,小薛與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於此,寶釵以絶佳的翻案功力再度奪魁,次則黛玉、湘雲並列,同時獲得了相關的風格評述,彼此各擅勝場。
統觀這兩次評述的用語遣詞,應可整合出這些閨閣詩人各家之“體”的具體内容,即寶釵的“蘅蕪體”是為“含蓄渾厚”、“温雅沉著”,而黛玉的“瀟湘體”是為“風流别致”、“逸才仙品”、“纏綿悲戚”,至於“情致嫵媚”則構成了湘雲的“枕霞體”。
除此之外,更可以注意寶琴之作的特殊印記,亦塑造出另一種風格體式。首先乃第五十一回《薛小妹新編懷古詩》一段,該組十首詩以古蹟為題、内隱十物,又涉及古人史事的評論,實為傳統詩歌中懷古、詠史、詠物三種不同類型的匯融,展現出罕見的大膽突破與創新①詳見歐麗娟:《論〈紅樓夢〉中的薛寶琴〈懷古十絶句〉——懷古、詠史、詠物的詩類匯融》,載於《臺大文史哲學報》第85期(2016年11月),第45—90頁。,故在小説現場上,得到了衆人給予“新巧”的讚賞並皆“稱奇道妙”。
然而,寶琴對自己的心血結晶卻自稱“粗鄙”,其故安在?倘非無謂的自謙,應有其他詩學評價的意義在内。從作品内容來看,細觀該十首詩的筆調,確實帶有淺白、甚至俚俗的語言特徵,例如其九《蒲東寺懷古》的“雖被夫人時吊起,已經勾引彼同行”者尤為如此,這是“粗鄙”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則另須求諸懷古題材的類型特點以得之,可參照第七十回衆人對寶琴所作《西江月》的評説論價。該詞云:
漢苑零星有限,隋堤點綴無窮。三春事業付東風,明月梅花一夢。 幾處落紅庭院?誰家香雪簾櫳?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離人恨重!
其實,比觀此前先已展示的黛玉、探春等金釵之作,本闋表現出極其類似的離散氣息,這種充滿飄泊無根、零落無著的描寫,綰合柳絮飄轉翻飛的物性特徵,卻也體現出傳統的主要感應模式,因此寶釵接著便總結道:“終不免過於喪敗。”微妙的是,在場諸人對寶琴這闋詞的關切焦點卻是其中所開展的空間無限性,所謂:
衆人都笑説:“到底是他的聲調壯。‘幾處’、‘誰家’兩句最妙。”
可見其實同中有異,在“過於喪敗”的通性中,寶琴獨樹一格的妙處即在於“聲調壯”,而從上下脈絡加以推敲,這種“聲調壯”的性質既是來自於“幾處落紅庭院?誰家香雪簾櫳”的悠遠渺然,進一步言之,其中所藴含的空間延展性又是基於首兩句的“漢苑零星有限,隋堤點綴無窮”而來,“漢苑”、“隋堤”展延了江南江北的具體地點,恰恰正是懷古詩常見的古蹟所在,寶琴於其新編的“懷古十絶句”中也曾有所觸及,即其五《廣陵懷古》最為顯著。
於是乎,所謂的“聲調壯”應與其懷古性質有關。猶如傳統詩論所認為的,懷古題材所主導的風格特點,就其所含攝悠遠的時間、遼闊的空間而容易產生一種壯闊蒼涼的感受,清代王士禛即指出:
古詩之傳於後世者,大約有二:登臨之作,易為幽奇;懷古之作,易為悲壯,故高人達士往往於此抒其懷抱,而寄其無聊不平之思,此其所以工而傳也。①王士禛著,張宗柟纂集、戴鴻森校點:《帶經堂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卷五《序論類》,第128頁。
朱庭珍亦云:
凡懷古詩,須上下千古,包羅渾含,出新奇以正大之域,融議論於神韻之中,則氣韻雄壯,情文相生,有我有人,意不竭而識自見,始非史論一派。②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三,載於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7頁。
而此一“雄壯”、“渾含”、“雄壯”的氣韻胸襟,豈非正是寶琴詞作之“聲調壯”的風格成因?至於其所自謙的“粗鄙”,則是因為高度自覺於迥異閨閣纖柔秀麗的習氣而言,再從評比結果來看,確實也屬不受青睞的創作取向。如此一來,衆姝的創作風格也可以增加一種由寶琴所建立的“寶琴體”,在“一人是一人口氣”、“自與别人不同”③己卯本第三十七回批語,第582頁。的情況下彼此各擅勝場,增益風格表現的多元光譜。
至此為止,在創作成果的“辨體”上清楚顯示所謂的作品風格,是指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表現出的各種格調特色,誠如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説,體“既指風格(style),也指文類(genres),及各種各樣的形式(forms)”④宇文所安著,王柏華、陶慶梅譯:《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頁。,而曹雪芹對詩歌風格的把握,亦包括相關項目。以前述的“寶琴體”而言,其構成因素即是懷古的文類特性⑤Genre之概念源於法文,指文學藝術作品的類型、體裁、流派和風格,簡稱類别。見蘇紅軍《類别》,載於柏棣主編:《西方女性主義文學理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頁。,而黛玉被用以辨識的“瀟湘體”,則如前引第七十回關於寶玉對“體”的表述脈絡中所示,寶玉對“體”的判斷是由“聲調口氣”而來,其依據在於《桃花行》中“有此傷悼語句”、“作此哀音”,此即意味了林黛玉的詩風乃透過“傷悼語句”、“哀音”所形成的“聲調口氣”。這也符合了現代的風格論,作為一個與“體”接近的西方概念,風格(style)的狹義即指文學語言的特徵,廣義則指某人部分或全部的語言習慣,或一群在某時内部分或全部的語言習慣①David Crystal and Derek Davy,Investigating English Style(英語文體調查)(London:Longman,1969),pp.9-10.,而黛玉的作品恰恰正是以“傷悼語句”、“哀音”為主要的語言習慣,這也與“纏綿悲戚”之為“瀟湘體”的構成要素相一致。
這種執一以求的風格描述具有簡明清晰的判别作用,反映了傳統詩評的偏好,但另外應該注意的是,小説中對於風格的相關討論還提到多元風格的表現。一般而言,上述所提及的單一風格説展示衆姝彼此之間鮮明易辨的詩風,在小説描述裏,曹雪芹也不斷以此對諸釵風格特色的分殊多所展現。但是除此之外,小説家同樣看到多元風格並存的創作事實,前引第七十回對風格歸屬的討論中,寶釵用以反駁寶玉之推測者,即為此故,所謂:“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首都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媚語。”此一多元風格論,即是以杜甫為案例,抉剔出杜詩中綺麗秀媚的詩句,突破了傳統詩論裏“杜工部之沉鬱”的典型表述,以平衡“體”的歸納對於詩人創作整體所造成的化約傾向。
而薛寶釵所謂杜甫詩兼備“媚語”之説,誠然十分符合杜甫的創作實況,也反映了傳統的杜詩評論。如杜甫《月夜》以“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兩句大膽涉入宫體的叙寫範疇,使用了豔情詩所特有的感官筆觸,被論者認為:“三聯句麗,上參六朝,下開温、李。”②范輦雲:《歲寒堂讀杜》,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4年版,卷三,第147頁。該兩句詩的宫體性質,以及杜甫之豔體書寫,詳參歐麗娟《杜甫詩中的妻子形象——地母/神女之複合體》,載於《漢學研究》第26卷第2期(2008年6月),第35—70頁。而楊倫評杜甫《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之二亦云:“妍麗亦開温、李。”③杜甫著,楊倫評注:《杜詩鏡銓》,臺北:華正書局1990年版,卷一一,第502頁。所謂的“妍麗”,乃是就其中“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江檻俯鴛鴦。日晚煙花亂,風聲錦繡香”之類的詩句而發。又《琴臺》一詩云: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杜詩鏡銓》卷八)就此,黃生注云:杜公此詩“清辭麗句,攀屈、宋而軼齊、梁。”①黃生:《杜詩説》,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版,卷四,第142頁。邵子湘指出:“‘野花’十字,已開温、李。”②參見杜甫著,楊倫評注:《杜詩鏡銓》,卷八,第352頁。諸説對應的創作風格,所謂的“妍麗”、“清辭麗句”,即來自上起“齊、梁”、下迄“温、李”的豔體書寫,其實比寶釵所引述的“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等詩句更有過之,最屬所謂的“媚語”。寶釵捨此而取彼,純以風景描寫者為例,蓋因其身為未出閣的閨秀千金,萬萬不宜涉及男女風情之故③有關傳統貴族大家對少女之婚戀的禁忌問題,筆者將另文撰述。,這也十分精密地照應到小説人物的階級身分,不易為現代讀者所察知,特於此拈出,以顯其義。
其次,值得進一步深究者,乃此一多元風格的實踐往例,在文學史上非獨杜甫為然。以陶淵明為例,其詩集中充滿“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④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之四,狄寶心校注:《元好問詩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卷一,第48頁。的性情書寫,誠如葉燮所謂的“多素心之語”⑤葉燮《原詩·外篇上》,載於丁福保輯:《清詩話》,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版,第597頁。;然而,正如鍾嶸所言:
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於“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⑥鍾嶸著,楊祖聿校注:《詩品校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頁。
陶詩在“省淨”、“質直”的主要特點之外,猶存“風華清靡”的另類風格,不為單一所囿限,遑論其作品集中同時存在著一篇旖旎浪漫、綺麗戀慕而充滿求女之思的《閑情賦》,與其整體詩風格格不入,一旦跨越不同的文類,更顯出作家風格的懸殊迥異,堪稱背道而馳。既然缺乏考證的有力支持,無法將此篇章以偽作的理由加以删除,從而維護陶淵明風格的一致性,於是《閑情賦》一篇便被追求單一風格者視為“白璧微瑕”⑦蕭統《陶淵明文集序》云:“白璧微瑕者,唯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惜哉,無是可也。”載於陶淵明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版,《附録一》,第614頁。,表達出一種來自缺陷的深切遺憾。
至於中唐時期,被蘇軾評為“元輕白俗”①蘇軾《祭柳子玉文》,載於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卷六三,第1938—1939頁。的元稹,於其詩風輕淺、人品輕薄的作品中,依然也存在著《遣悲懷三首》如此纏綿悱惻、動人心扉的悼亡詩,而此組詩卻又是在他“納妾安氏”之際所作,亦即孕生於既深情緬思舊人、同時卻展臂迎納新人的奇特情境,這尤其是集矛盾為一體的最佳例證,足以推翻“功名之士,絶不能為泉石淡泊之音;輕浮之子,必不能為敦龐大雅之響”②葉燮《原詩·外篇上》,載於丁福保輯:《清詩話》,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版,第597頁。這類單一而絶對的推衍理路。
由上述諸例可知,單一作者之多元風格在詩歌史上並不少見,既然如此,則何以寶釵卻單舉杜甫為例?細繹其理,實亦有跡可尋。其一,杜甫乃詩歌集大成的巨擘,以地覆海涵的廣博著稱,其多元創作風格最為顯明可徵,以之例示更是順理成章,也證據力十足,充滿説服力,此理顯而易見;其二,或許還可以參考的是曹雪芹家學淵源的影響,因為在唐詩諸家中,最被曹寅奉為典範者即為杜甫,清人姜宸英序其詩集云:
楝亭諸詠,五言今古體出入開寶之間,尤以少陵為濫觴,故密詠恬吟,旨趨愈出。③姜宸英《楝亭詩鈔序》,曹寅:《楝亭詩鈔》,載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4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27頁。就此而言,杜詩堪稱為曹氏的家學淵源,形成了祖孫之間一脈直承的詩學根柢,亦應是寶釵獨標杜甫為説的一個原因。
不僅一人可以兼備衆體,甚且“體”的多元展現還可以並存於一篇之内,於廣幅長卷的古風體中構成抑揚交錯的章法節奏。參照第七十八回賈寶玉應父命即席作《姽嫿詞》的一大段情節,其中所隱含的風格觀亦足以作為補充。當時於寶玉即席創作的整個過程中,除了後半段是一氣呵成之外,其前半段乃是透過工筆細剖的方式,讓衆位幕賓門客一一摘句以呈現其藝術價值之所在,而不同的風格也隨之展現。其中,他們讚美第三句的“穠歌艷舞不成歡”是“古樸老健,極妙”,再則認為“丁香結子芙蓉縧”這一句“也綺靡秀媚的妙”,可見該篇鎔鑄各種不同的詩歌風格,或是“古樸老健”,或是“綺靡秀媚”,前後交織在詩歌脈絡之中,使得此一長篇作品展現得更加跌宕生姿。如此一來,透過表現技巧所呈現的多樣風格,也成為一首詩的組織手法了。
然而,種種構成風格的語言習慣又絶不僅是文字的表現技巧而已,往往還更奠基於作家的個性;同樣地,看似純由懷古題材所建構的“寶琴體”,又豈只單單源自文類的要素所致?使之採用此一文類的個人性,是否乃更為深層的關鍵因素?而此種個人性又非僅天賦所能涵蓋,後天的成長經驗及隨之所養成的意識形態,皆必然參與了風格的形成動力。據此,關於風格的成因,稟賦、經驗與意志等構成人格的複雜因素,也都是決定風格表現的條件,必須進一步深論。
三、風格的成因
一如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所説:“藝術作品所提供觀照的内容,不應只以它的普遍性出現,這普遍性須經過明晰的個性化,化成個别的感性的東西。”①引見朱光潛:《西方美學史》,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年版,下卷,第130頁。而在個性化的過程中,便會形成標示作品特定面貌的風格,因此風格總與品鑑人物有關,也往往立足於作家的個性。例如西方自從法國的布封(Buffon)在1753年提出“風格即本人(Le style est l'homme meme.Style is the man himself.文如其人,風格是人)”②轉引自J.Middleton Murry,The Problem of styl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0),p.14.之後,“個性”説亦成為西方風格論的重要一派,如Flaubert説:“風格是作家思考或觀察事物的獨特方式。”(Style is the writer's own way of thinking or seeing.)③J.Middleton Murry,The Problem of style,p.14.
然而,個性又來自何處?一個人對事物的觀察角度、思考方式,並非單純地與生俱來,所謂的性格也深受後天際遇、社會價值的影響,而曹雪芹於第二回《冷子興演説榮國府》中,已透過賈雨村所代言的“正邪兩賦”論説明先天、後天因素對個體材性的影響一樣地重要,形諸創作,乃交錯輔成、兩面俱全,非可偏倚。因此,曹雪芹在關於“體”的風格論述中,也一定程度展現出這些不同範疇的成分,以下即分别加以考察。
(一)先天成因:氣質稟賦
首先,曹雪芹對於人性之先天論的認識和剖析,充分表露在第二回裏由賈雨村所代言的一大段氣論中,反映出某種意義上的先天決定論①詳見歐麗娟:《〈紅樓夢〉“正邪兩賦”説的歷史淵源與思想内涵——以氣論為中心的先天稟賦觀》,載於《新亞學報》第三十四卷(2017年8月),第1—56頁。。衡諸小説中對人物性格的設定或塑造,確實往往可見先天稟賦的痕跡,也直接構成了詩詞風格的主要因素。
以林黛玉而言,其前身本為西方靈河岸邊的絳珠仙草,因受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恩,含銜不忘,以致同赴塵世還淚作為償報,則既為還淚而生,今世勢必自尋煩惱、好哭盈淚,以完成此一天賦使命。所以應該説,曹雪芹精心擬造這一則仙草還淚的神話,乃是為黛玉多愁多病之感傷性情而量身訂製,以説明或合理化其好哭之性格特質。非由此,不足以解釋其處於優渥順遂的境遇中,卻不斷陷溺自苦的現象。是故,其詩篇中斑斑點點的淚痕,主要即是天賦性氣的展現,是為“風流别致”、“逸才仙品”、“纏綿悲戚”的“瀟湘體”。
至於史湘雲,則恰恰與黛玉適得其反,彼此形成了天賦影響的兩個極端對比。試看第五回太虚幻境所演奏之《紅樓夢曲》中,關於湘雲的《樂中悲》一闋説道:
襁褓中,父母嘆雙亡。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幸生來,英豪闊大寬宏量,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
究實言之,湘雲的現實處境艱困於黛玉不知凡幾,然而卻不曾感傷哀切、以淚洗面,從曲文中的“幸生來”一詞,證明此一“英豪闊大寬宏量”與“霽月光風耀玉堂”的性格根本是源於天賦自然,乃能在窘迫的環境中保有豁達明朗的豪邁心胸。而這不但暗示她與黛玉的性格差異,也點出其來自性格因素的言語特徵,性格影響了風格,其詩詞創作中便多舒爽之氣,處處顯露出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以及熱愛人生、珍惜光陰的積極樂觀,以“枕霞體”别樹一格。諸如:
卻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第三十七回《白海棠詩二首》之一)
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第三十八回《對菊》)
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第七十回《如夢令》)湘雲以其毫無陰霾的清亮雙眸放眼望去,只見春光多嬌、秋色明淨,於是不肯自陷於寂寞心緒中虚度光陰,乃鼓舞雅興以欣賞感應世界的美好,較諸黛玉的傷春悲秋何等懸殊!同樣地,對於坎坷起伏的人生際遇,湘雲自有一種瀟灑豁達的坦然以對,所謂“也宜墻角也宜盆”(第三十七回《白海棠詩二首》之二),此一舒朗、開闊、坦蕩、豪爽的風格最為與衆不同。是故,即使湘雲的作品也同樣以夕陽、柳絮等為基本素材,但其風格卻截然有别與衆釵,自成專屬的“枕霞體”,則此一“情致嫵媚”的風格成因只能歸諸天性。
再觀寶釵的“蘅蕪體”,其“含蓄渾厚”、“温雅沉著”的詩詞風格表現,自不能免於天賦的影響,如脂硯齋所言:
瞧他寫寶釵,真是又曾經嚴父慈母之明訓,又是世府千金,自己又天性從禮合節,前三人(案:指寶玉、黛玉、湘雲)之長並歸於一身。①庚辰本第二十二回批語,第446頁。
此中所謂的“曾經嚴父慈母之明訓,又是世府千金”,確指後天環境的陶冶塑模,至於“天性從禮合節”一説則顯係與生俱來的稟賦。由此可見,寶釵那“含蓄渾厚”、“温雅沉著”的“蘅蕪體”,也藴含了個人風格的天賦影響,是為其個性的一部分,而恰恰與黛玉、湘雲分别體現出非人力強致的不同風格來源。
(二)後天成因:經驗與意志
就創作風格的後天成因而言,第二回中賈雨村所代言的正邪兩賦論,也清楚説明後天因素對個體材性的影響一樣地重要,家庭作為最關鍵的成長環境,甚至主導了先天稟賦正邪兩賦者之分化為“情痴情種”、“逸士高人”、“奇優名倡”的決定性因素②詳見歐麗娟:《論〈紅樓夢〉中人格形塑之後天成因觀——以“情痴情種”為中心》,載於《成大中文學報》第45期(2014年6月),第287—338頁。。則創作風格又豈只是純任天性流露,不受經驗的影響?而這又構成了影響作品風格的重要因素。
故J.Middleton Murry謂:“風格無疑體現了作家的個性,因為風格是個人經驗模式的直接表現。”(Style naturally comes to be applied to a writer's idiosyncrasy,because style is the direct expression of an individual mode of experience.)①J.Middleton Murry,The Problem of style,p.19.就此而言,曹雪芹的風格論也有所呼應,於前引第七十回的對話説明中,寶玉所謂“這聲調口氣,迥乎不像蘅蕪之體,所以我不信”的説法,初步根據了“單一風格”的推論,但從後續對話往返的過程,其實又經過了數次理路上的轉折,充分顯示風格論述的複雜層次:
首先,寶玉固然是從單一風格的角度,不為薛寶琴戲謔的冒名頂替企圖混淆視聽所動,而直指林黛玉“傷悼哀音”的特殊詩風以為辨識的依據,所言便觸及了風格與際遇的内在關聯,所謂“曾經離喪,作此哀音”,便説明生平際遇對創作的影響。林黛玉幼年即遭至親亡故,家族單薄無依,雖係名門閨秀,卻孤身存世,於是此一“離喪哀音”便隨著吟詠抒情而成為作品主調,是為“瀟湘體”。學者認為:“曹雪芹還進一步把作品的風格與作者的生活境遇、思想感情、身分地位、性格特徵聯繫起來,指出作品風格均符合作者之’聲調口吻’,是作者思想感情、生活境遇的綜合表現。”②翟勝健:《曹雪芹文藝思想新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8章,第133頁。主要便是就此而言。
類似地,所謂的“寶琴體”雖然是懷古格調的表彰,然而,若非寶琴具有當代才媛罕有的“離心式”生活經驗,自幼跟隨父親游歷大江南北,親履包括塞北、南海在内的各省古蹟遺址,又豈能操觚寫下《懷古十絶句》,並將此一心胸視野融入詞之豔科媚韻,而產生“聲調壯”的風格③詳見歐麗娟:《論〈紅樓夢〉中的薛寶琴〈懷古十絶句〉——懷古、詠史、詠物的詩類匯融》,第45—90頁。,形成所謂的“寶琴體”?衡諸其他金釵,皆欠缺、也不宜有懷古之作,實為“非不為也,乃不能也”的必然結果,參照一生足不出户的黛玉只能在書房中閲讀遥想,而寫出《五美吟》之類的詠史詩,更突顯出經驗、際遇對風格的重大影響。
據此,或者也可以説,當寶釵和寶玉論較《桃花行》的風格歸屬時,舉杜甫在“叢菊兩開他日淚”之類的沉鬱風格之外,尚有“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之類的“媚語”為例,而以多元風格推翻寶玉的單一風格論,卻缺乏反駁力道的原因,便在於忽略了性别、成長等後天影響的強烈制約。單獨抽象地看,多元風格論自屬合理也符合歷史事實,只不過,詩聖之博大固然有以致此,但千金閨秀的詩藝養成畢竟缺乏相關的發展條件,因此,閨秀才媛下筆時大多以“本真性靈”直接流露,猶如道、咸年間之戈如芬於《學詩》中所云:
聽慣吟哦侍祖庭,唐詩一卷當傳經。花紅玉白描摹易,筆底還須寫性靈。①沈善寶:《名媛詩話》,載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70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卷九,第662頁。
此一現象於《紅樓夢》中亦然②詳參歐麗娟:《〈紅樓夢〉之詩歌美學與“性靈説”——以袁枚為主要參照系》,載於《臺大中文學報》第38期(2012年9月),第257—308頁。,實質上衆家才媛仍以單一風格貫穿全場,這不能不説是閨閣所限。
更值得注意的是,寶釵以杜甫“多元風格”為例的質疑,在原理上仍是有力的,足以將單一風格論壓倒,因此寶玉立刻承認“固然如此説”,以致支持單一風格論的理由瓦解不復存在。於是後續寶玉乃改弦更張,用以自我辯護的理由也不再僅以“聲調口氣”作為演繹法則,换從其他的“動力因”強化自己的推論結果。
試觀寶玉在聽了寶釵的多元風格論之後,笑道:“固然如此説。但我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句,妹妹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此一説法申述在風格形成的過程中,除了來自個性、遭遇、環境的影響之外,還有一般人所忽略的意志選擇和價值判斷的制約因素,並不限於單一風格論者所持之“作品反映個性與遭遇”如此素樸的推理。
確實,人類並非客觀世界的被動反映以致淪為環境的產物,如主體心理學(subjective psychology)所指出,在人的成長發展過程中,主體能動性乃是影響主體心理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並與教育、環境一同構成主體心理發展的三維結構模式;其中,主體能動性作為主體與世界相互作用的主導潛能③詳參鄭發祥:《主體心理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134—135頁。,可以説更是探求人格型態的核心。因此,所謂意志選擇和價值判斷的制約因素,指的是作者在創作過程中,除了被動地反映其生平遭遇與存在處境所形成的“自然風格”之外,還會因為個人美學品味的嘗試或社會普遍價值觀的影響,而進行對自我風格的積極調整與主動取捨,從而極端者甚至會產生與個人稟氣大相逕庭的作品。這就加入了意志選擇和價值判斷的理性因素,進一步提出有關詩歌風格論的複雜辯證。
其中所涉及風格的動力因(efficient cause),即詩人的主體意志,連帶含攝了思想價值觀,那並非經驗的被動反映,而是經過思考、探察、判斷等等取捨之後的刻意選擇,誠所謂“每一種風格都具體表現出一種認識論上的決定,以及對於我們理解什麽與如何理解的一種解釋”①Susan Sontag,“On Style,”in Against Interpretatio n(New York:Delta Book,1966),p.35.。再參照法國現象學家米蓋爾·杜夫海納(Mikel Dufrenne)論及藝術家的風格時所説:
風格是作者出現的地方。其所以如此,是因為風格含有真正是技巧的東西:某種處理材料的方式……為了創造審美對象,風格非要材料這樣安排、簡化或組合不可。……這些技術手段還必須顯得是為一種獨特的想法或看法服務的。……對作為欣賞者我而言,技巧和學説都不足以確定一個風格。技巧和學説,還必須在我眼裏顯得出是出於某種世界觀的需要,這種世界觀把創作當作一種冒險和自由。……當我發現人與世界的某種活生生的關係,感到藝術家正是這種關係賴以存在的那個人時,就有了風格。……技巧模式不只是創作作品的一種手段,而且還是表現一個世界的手段。所以技巧就是創作者的一種標記,比如……某一詩人的某一慣用詞。②詳見杜夫海納著,韓樹站譯:《審美經驗現象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145頁。
其中所謂的“世界觀”(a certain vision of the world),即“人與世界的某種活生生的關係”(a certain vital relation of man to the world)③詳見 Edward S.Casey,Albert A.Anderson,Willis Domingo,Leon Jacobson trans.,The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Illinoi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3),pp.105,106;該書譯 自Mikel Dufrenne,Phénoménologie de l'expérience esthétique(Paris,Franc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3).,是為藝術家對社會生活世界的觀照或對生命存在的感知。
以此衡諸黛玉所慣用的“傷悼語句”,包括意象偏好與詞語選擇,正代表著一種負面的殘缺悲思與死亡的幻滅觀照,黛玉正是把創作當作一種悲劇性生命的實踐,以致執拗地固持人生中的某些哀痛時刻,頑強地抗拒遺忘、淡化那些過往經驗的人性本能,而集中地、持續地、濃烈地陷溺於傷悼情緒裏,於字裏行間處處散發一片哀音,從而構成了鮮明可辨的瀟湘體。可是,從理論上來説,瀟湘體固然是開放的藝術嘗試,可以成為詩人創作實踐時的典式之一,但事實上並非人人如此,也不應個個皆然,寶玉所另行援取的理據,所謂“我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句,妹妹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即是從不同的世界觀加以補充,以強化黛玉與瀟湘體的唯一連結,肯認《桃花行》必為黛玉手稿的版權專屬。其重點有二:
其一,這段説法暗示了某種風格之塑造,乃是可以透過刻意的排拒而形成,所謂“不許”、“不肯”都顯示出意志選擇和價值判斷作用過的痕跡,説明了在創作表現上,會因為某些禁忌的考慮而有所取捨,也連帶影響了風格表現,此即反映了傳統“趨吉避凶”的詩讖觀。猶如《禮記·孔子閒居篇》引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在“詩言志”的創作表達下,自魏晉以降逐漸形成了“詩為命運之預言”的認知,於《紅樓夢》的詩歌創作活動上亦多所反映①詳見歐麗娟:《詩論紅樓夢》,第1章《緒論》第2節“‘詩讖’——命運之載體”。;配合一般“趨吉避凶”的心理,於是詩人在若非出於身世遭遇之深切浸染、感傷性格之耽溺沉湎,而在強烈情思之不容已的情況下寫出傷悼之句,所謂“為情而造文”如林黛玉者,便往往會刻意避開頽喪傷感之哀音,以免干犯忌諱或招致禍端。明朝徐師曾就此曾感慨道:
自詩讖之説興,作者遂多避忌:沉逆驚喪,不堪贈遠;短促凋哀,詎宜稱壽;卑降免失,忌獻於達官;落下遺出,惡聞於始進。推此類也,能無病於言乎?②徐師曾:《詩體明辯》,臺北:廣文書局1972年版,《論詩》,第43頁。
换言之,在“詩可以反映未來命運”的詩讖思維下,諸如“沉逆驚喪”、“短促凋哀”、“卑降免失”與“落下遺出”之類的負面語句,極容易成為詩人下筆時迴避割捨的部分,以致在此無形的規約下便容易形成特定的詩歌風格。這纔是促使寶玉做出寶釵“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句”、寶琴“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之判斷背後的真正原因;所謂“斷不許”與“斷不肯”的認定,無一不反映出這種趨吉避凶之詩讖觀點的介入,以免一語成讖地步入不幸。
這種“詩讖”思維,形同把創作當作一種對命運的護航,發揮文字的導航功能,以避免人生航道上的阻礙,而確保順行暢通的機率,由此所致的風格傾向自然與瀟湘體有所乖離,因此成為寶玉的判斷標準。
其二,若更仔細進一步推敲,所謂“妹妹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的”一説,似乎又不僅只是詩讖觀念之下的刻意迴避。畢竟“趨吉避凶”的務實思維,在寶釵身上固然是長輩的好意,就寶琴個人則未免流於俗氣,與其不食人間煙火的脱俗仙姿並不切合。連結下文緊接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這兩句一體並觀,可以推知寶琴“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的原因,應該更是一種不願為了藝術效果而虚情矯飾假擬的自我堅持。誠如袁枚所言:
明鄭少谷詩學少陵,友林貞恒譏之曰:“時非天寶,官非拾遺,徒托于悲哀激越之音,可謂無病而呻矣!”學杜者不可不知。①則以寶琴的皇商家世、行旅天下的見識胸襟,而集萬千寵愛在一身、未曾經歷“離喪”之苦痛遭遇的境況,倘若字字哀切、故作楚楚可憐之態,實未免“為文而造情”的虚矯,而招致識者的無病呻吟之譏,如此將何等地自失身分!寶琴自己之所以“斷不肯作”,自應以此為最大的可能性。
至此,寶玉以“曾經離喪”與否的個人遭遇,以及預言吉凶的“詩讖”觀點,再加上不肯“為文造情”的誠懇原則,確立《桃花行》與黛玉的唯一連結,其所謂“斷不許”與“斷不肯”的説法,都告訴我們:風格的展現有時可以是出自意志選擇之後的結果。風格之塑造可以是刻意追求所致,包括因應外在需要而進行排拒、削減而形成,隱含了現實得失和價值判斷的作用。
至此,關於風格的成因,包括稟賦、經驗與意志等皆與其力,足見《紅樓夢》詩學中對“風格”的把握堪稱全面。
(三)形式因:意象、體裁、技巧
除了上述在“作者”方面的先天、後天因素之外,攸關風格之形成者,尚
①袁枚:《隨園詩話》,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4年版,卷六,第196頁。有作品本身作為一種藝術表達方式,於組構方式上所產生的形式因(formal cause)。如艾布拉姆斯(H.M.Abrams)主編的《簡明外國文學辭典》所言:“風格是散文或詩歌的語言表達方式,即一個説話者或作家如何表達他要説的話。分析作品或作家的風格特點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作品的詞藻,即詞語的運用;句子結構和句法,修辭語言的頻率和種類,韻律的格式,語音成分和其他形式的特徵以及修辭的目的和手段。”①阿伯拉姆編,曾忠禄譯:《簡明外國文學辭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風格”條。卡頓(J.A.Cuddon)於《文學術語辭典》中亦指出:“文體是散文或詩歌中特殊的表達方式;一個特殊的作家談論事物的方式。文體分析包括考察作家的詞語選擇,他的話語形式,他的手法,以及它的段落的形式——實際上即他的語言和使用語言方式的所有可以覺察的方面。”②J.A.Cuddon,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New York:Wiley-Blackwell,1976),“Style”條。引自楊暉:《古代詩“路”之辯:〈原詩〉和正變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頁。就此,可以黛玉的瀟湘體為例,由意象選擇、文體組構兩方面加以説明。
猶如寶玉所點示者,瀟湘體的主要特徵便是充滿“傷悼語句”、“哀音”,由此構成“纏綿悲戚”的風格,而那些“傷悼語句”即包括了學者所觀察到的:
她詩中常出現“訴”與“憐”二字(如“花解憐人花也愁”,“紅消香斷有誰憐”,“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醒時幽怨同誰訴”,“嬌羞默默同誰訴”等句),證明外界環境對她而言是太強了……因之她作品裏全是一片哀音,像是“無告之民”,又像是受盡委屈的孩子。在詩中她一直以弱者之姿態出現;她雖性傲,實則她的孤傲乃是弱者用以自衛的保護色,暗示内心的恐懼與空虚。③傅孝先:《漫談紅樓夢及其詩詞》,載於《無花的園地》,臺北:九歌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頁。此一發現,更清晰地抉發出風格形成的形式要素,離不開特定的語言習慣,包括用字遣詞以及使用頻率。除此之外,林黛玉的作品中經常出現“淚”的淒涼、“風雨”的蕭瑟,以及暮春、深秋、夕陽、殘月、落花、飛絮、枯葉等廣義的死亡意象,正是瀟湘體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不僅如此,林黛玉獨處時所吟詠的抒情詩,大都採用了長幅的古風歌行體,淋漓盡致地一唱三嘆,包括第二十七回的《葬花吟》、第四十五回的《代别離·秋窗風雨夕》、第七十回的《桃花行》,各篇皆透過頻繁的轉韻,以及换韻時必使用“逗韻”的技巧,製造出“流利飄蕩”的抒情韻致①“流利飄蕩”一詞出自第七十八回,寶玉應命作《姽嫿詞》時即採用同一做法,其意趣可以相通。關於小説中古體長詩的格式布局、審美效果,詳見歐麗娟《詩論紅樓夢》,第4章《長篇詩歌之創作理念》,第4節。,也助長了長歌放聲的淒楚之音。此一現象也可以證明,風格的形成確實還包括體裁所提供的助力。
至於寶釵的“蘅蕪體”,除了句句所流露的大方沉穩之外,還有一處透過翻案技巧所達到的效果可兹説明。如果就衆金釵之作的意象偏好與詞語選擇而言,在第七十回《柳絮詞》的詩社競賽中其實出現了高度的同一性,正如當場薛寶釵所觀察的,諸作“終不免過於喪敗”,非獨黛玉之作為然,連寶琴所作“聲調壯”的《西江月》一闋,其實同樣不免出現類似於“瀟湘體”的飄泊離恨,所謂“三春事業付東風,明月梅花一夢”,“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離人恨重”等等皆屬之,擴而及於全部詩詞,甚至可以整體概括出《紅樓夢》的詩歌風格趨向於“中晚唐”②相關論證,詳參歐麗娟:《論〈紅樓夢〉與中晚唐詩的血緣系譜與美學傳承》,載於《臺大文史哲學報》第75期(2011年11月),第121—160頁。。此所以寶釵别出心裁,説道:“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根無絆的東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説好了,才不落套。所以我謅了一首來,未必合你們的意思。”果然該闋詞篇一反飄零沉墮的趨向,刻意向上飛升、夷然不為聚散所動,所謂:
白玉堂前春解舞,東風捲得均匀。蜂團蝶陣亂紛紛。幾曾隨逝水?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頻借力,送我上青雲!
其中固然也有詩讖意識使然,但更多的乃是一種充實自如的君子胸懷,包括“幾曾隨逝水?豈必委芳塵”的抗拒主流,“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的淡定自在,以及“好風頻借力,送我上青雲”的超然昇華,都透過翻案技巧而更加顯露,故被衆口一致喝采為“翻得好氣力”,公推得魁。則“蘅蕪體”的風格表現,同樣可以藉由形式技巧而助成之。
四、結 語
《紅樓夢》作為一部“詩性小説”,往往“從詩詞句中泛出”種種叙事妙處,因而可以為各個鮮明可感的人物、場景追蹤出脱胎的詩詞來歷,至於曹雪芹之以作詩填詞的活動穿插其間,不但不是情節的中斷,以減緩叙事的節奏,更不是高才文人在傳統“文化負擔”之下的運用,以上這兩種解釋都屬於形式上的考量,是外加的介入而非内在有機的促發;毋寧説,那是一種對貴族階層精英文化的如實再現,在數代累積的大雅文明下,談詩論藝本身便是日常生活的自然展演,第四十八回《慕雅女雅集苦吟詩》所集中叙寫的“香菱學詩”一段,甚至綿延到第四十九回纔因寶琴的莅臨而終止,可為其證,因此可以幾近全面地鋪陳傳統詩學的内涵,“風格論”便是其中的一個環節。
從上文的討論可見,透過論詩的生活場景、尤其是詩社活動過程中小説人物的往返論較,曹雪芹對於傳統文論中有關風格的掌握是很足夠的,他以“體”字表達一種具有個人特徵的特殊創作樣態,其中涵攝了詩家的稟賦、經驗與意志等因素,對於形成、塑造風格的種種動力因可謂掌握周延;此外,也透過詞藻、意象等詞語的運用,以及篇章的組織方式強化了“瀟湘體”的特徵,從修辭語言方面具體展現出風格形成的形式因。至此,《紅樓夢》之詩學論述的涵蓋面也益發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