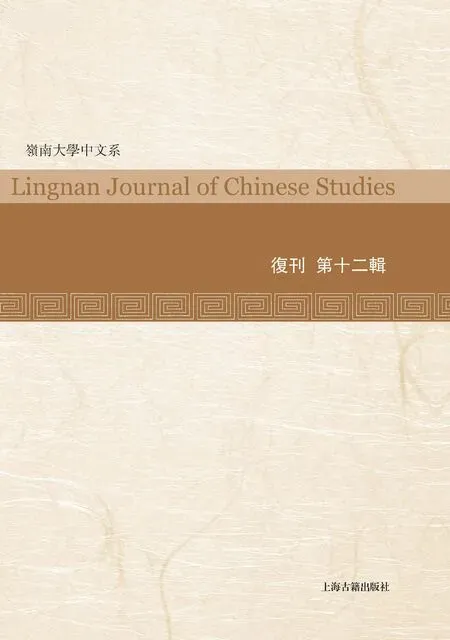《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中的物觀
2020-03-02曹建國易子君
曹建國 易子君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是《毛詩》名物訓詁的重要著作①本文引陸《疏》以羅振玉《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新校正》為底本,《歷代詩經版本叢刊》第2册據民國間上海聚珍仿宋印書局排印本影印,濟南:齊魯書社2008年版。個别條目參考清代丁晏《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校正》,《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講多識之學者,固當以此為最古焉。”②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20頁。概言之,後世《毛詩》名物的研究成為專門之學,當推此書首創之功。它的作者是三國時吴郡人陸元恪①關於陸氏之名,前人説法不一,或以為“機”,或以為“璣”。顔慧萍在《陸璣及其學術考述》一文中對此有比較完整的總結,今大都以為陸璣更可信。而夏緯瑛先生在《〈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的作者——陸機》一文中從古人所取名與字之間的關係入手,認為“恪”與“機”恰好含義相反,並以新發現的日本舊藏古本《一切經音義》和《玉燭寶典》中的相關文字為參考,認為《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的作者名當為陸機。綜合諸多因素,本文採信“陸璣”説。,生卒年及生平事跡均不詳。學界目前關於《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以下簡稱“《草木疏》”)的研究尚不多,多是著眼於作者考辨;或是關於文本的歷史衍變及現今可用版本的分析與搜羅;或是對全書體例、内容分類、成書特點及對後世《詩經》學的影響等方面加以整體介紹;或是從語言學的角度對其中的名物進行方言、詞源、詞彙等方面的整理與探討②相關代表論文主要有:夏緯瑛《〈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的作者——陸機》(載於《自然科學史研究》1982年第2期,第176—178頁);徐建委《文本的衍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辨證》(《上海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第67—78頁);羅桂環《古代一部重要的生物學著作——〈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古今農業》1997年第2期,第31—36頁);顔慧萍《陸璣及其學術考述》(《社科縱橫》2008年第2期,第172—174頁);華學誠《論〈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的名物方言研究》(《徐州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第53—56頁,下轉第61頁)等。此外,一些專門性的《詩經》研究著作、碩博士論文也多涉及陸璣的《草木疏》,尤其是那些以鳥、獸、草、木、蟲、魚為研究對象的專題研究碩博士論文,如李曼曼《〈詩經〉中的食物及烹飪研究》(吉林大學,2018年)、趙利傑《〈詩經〉中的蔬菜研究》(鄭州大學,2016年)等等。由於篇籍衆多,不再詳細出注。上述前賢時哲的研究,對於本文的寫作多有啟益,一併致謝。。但這些研究似乎對文本本身的關注還不夠,細緻的文本梳理也不多見。而從具體内容分析可以發現,《草木疏》中保留了大量的魏晉時期的民俗文化,其中涉及到飲食、醫學、生產、娱樂、宗教與方術等諸多方面。這些記載猶如一幅幅豐富多彩的風俗畫,向我們展現了漢魏時人真切可感且趣味十足的生活面貌和精神情趣。與此同時,其經學意旨與文學趣味也涵寓其中,反映出魏晉人獨具的“物觀”。
一、飲食與醫療
(一)飲食習慣
飲食是《草木疏》現存文本中占比例最多的部分,其中可供食用的動植物種類涵蓋範圍廣博,展現出的飲食方式花樣繁多,從這些文本描述中,今人可以大致了解魏晉,尤其是三國時期的些許飲食習慣。以下擇要對此進行展現。
1.生食。這種最原始也最簡單的食用方法在《草木疏》中有相當多的記載,其中有些種類是流傳至今、且依然普遍為人熟知沿用的,如荷及其果實(“有蒲與荷”條),陸氏稱:“其(荷)實蓮,蓮青,皮裏白子為的,的中有青長三分,如鈎,為薏,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的五月中生,生噉脆。”其中的“蓮的”即今人食用的蓮子,“薏”即蓮心,今人也常生吃。但更多的生食對象是今人絶少食用甚至難以識别的,或者説即使食用也必定經過烹煮處理,如蔞蒿的旁莖(“言刈其蔞”條),陸氏稱:“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蔞蒿,又稱蘆蒿、藜蒿、泥蒿、水蒿等,從古至今都是一道不可或缺的美食,但今人大都將蔞蒿與其他肉類火炒、或者是入沸水焯透後涼拌食用,如《草木疏》中記載不經任何處理、即取即食的方式則幾近於無①蘆蒿的食用歷史悠久且吃法衆多,可參閲胡畏《話蘆蒿創“蘆蒿宴”》一文。。除荷與蔞蒿二者外,其餘的就基本屬於今人食用範疇之外了,如蒲“生啖之甘脆”(“有蒲與荷”條),它學名水燭,與蘆葦相似,除非饑荒等特殊情況,想來決計不會成為今人的生食對象。粗略統計,書中直言可以生吃的生物不下13種之多,活吃動物倒是没有,主要集中在“草”“木”兩類,除上述荷、蔞、蒲諸草,還有苹、蘩、莪、薇、芑、苕、莫等野草的莖葉②高智《〈詩經〉裏的菜園子》一文介紹了薇菜、荇菜、卷耳、水芹、芣苡等五種蔬菜。,以及鬱、樹檖、枳枸等樹木的果實,可謂豐盛。
儘管《草木疏》中並没有一一指出究竟是哪一社會階層在采用這種吃法,但仍然可以從當時的社會環境著眼考慮其中的原因:雖然魏晉較前代在飲食方面進步不少,更加精細繁瑣,也有大量食經出現,但是魏晉時期天災不斷,政權更迭,戰亂更是家常便飯,普通百姓往往流離失所,農耕荒廢,即使有了短暫的安定生活也會遭到貴族門閥的盤剥,在吃食上没有條件也没有資格講究,也正是由於這種大的社會背景所限,《中國風俗通史·魏晉南北朝卷》在考察比較後也認為:“以糧食和蔬菜為主的素食結構是民間普遍的食俗。”③張承宗、魏向東:《中國風俗通史·魏晉南北朝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頁。所以在物質豐富的今人看來不可思議的、這麽大範圍的生吃對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2.蒸煮。這一食用方法在《草木疏》的“飲食”内容中所占比例最大,上述可供生食的絶大部分品種都可同時通過蒸煮食用。具體而言,可供“蒸”食的包括蘋、萍、蘩、莪、蔞、葍、芑、萊等草類,其中有一點需稍加注意,那就是“糝蒸”,書中記載“(蘋)季春始生,可糝蒸以為茹”(“于以采蘋”條)。這種植物就是常見的水上浮萍,它根莖一體,頂端有四片對稱的小葉,是細嫩柔軟的好食材,《禮記·内則》稱:“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①《十三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8頁。此處的“糝”應當是肉和米麵而成的一種糊狀物。《莊子·讓王》也曾有言:“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成玄英疏言:“藜菜之羹,不加米糝。”②陳鼓應注譯:《莊子今注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813—814頁。此處指無米以和菜羹的情形,“糝”又著重指明了米糊一點。雖則“糝”究竟為何隨著時代變化而難以説清,但總體而言,《草木疏》所言應當是指將蘋草與少許米麵混合成湯糊狀,然後加以蒸食,至於有無肉類尚未可知。可供“煮”食的包括芣苡、杞、卷耳、薇、匏葉、莫、芄蘭等草類,“其葉如榆,瀹為茹,美滑於白榆”的樞等木類的葉子(“山有樞”條),以及“其肉甚美,可為羹臛”的鴞等鳥類(“翩彼飛鴞”條)。
不僅蒸煮的食材豐富,而且菜品繁多,僅湯類菜品就又可細分為羹、臛、韲數種,這其中便涉及了羹、臛、韲,尤其是羹、臛的分化與異同問題,直到東漢王逸注《楚辭·招魂》“露雞臛蠵”時尚有明確分别:“有菜曰羹,無菜曰臛。”③洪興祖撰:《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08頁。但到了北魏賈思勰時就已經是羹臛混稱了,《齊民要術》中就没有將其分别列目而總稱“羹臛法”,王子輝認為:“古代的羹與臛是没什麽嚴格區别的,只是有菜、無菜的微細之分。但這似乎只在歷史的短暫時期是如此。後來的發展變化,早已使這個微細的區分失去了意義。至少在南北朝時期,羹與臛的命名已不是按照肉羹中有菜與否來區分了。”④王子輝:《中華飲食文化論》,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頁。而《草木疏》中則將其平行羅列:“(梅)煮而曝乾為腊,置羹、臛、韲中,又可含以香口。”(“摽有梅”條)同時,文中提及作“羹”的有杞、薇、莫、菲、匏葉五種,全是菜類,無一有肉,而魚肉類鱣又直言其“可蒸為臛”(“有鱣有鮪”條)。可見,至少這三種、尤其是羹臛,在三國時代仍然是按有菜、無菜加以比較嚴格的區分的。至於韲類菜餚,文中僅一帶而過,此處也不再多説。
除上述兩種使用最廣泛(至少從占《草木疏》内容比例來看如此)的食用方法外,該書還記載了另外一些别有風味的飲食樣式。
3.燒烤。這一食法在古代被稱為“炙”,《説文》解釋為“從肉,在火上”①許慎撰、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91頁。,就是以火燒烤原料後食用。關於“炙”這一烹飪方法,文獻多有記載,漢畫像也能見其蹤跡②張鳳:《漢代的炙與炙爐》,載於《四川文物》2011年第2期,第58—60頁。。《草木疏》中記載别有一例燒烤野菜:“蒿,青蒿也,香中炙啖,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菣也。”(“食野之蒿”條)菣也即香蒿,是青蒿的一種,後世沈括云:“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常蒿色綠,而此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黃,此蒿獨青,氣稍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此為勝。”③沈括撰、胡道靜校:《夢溪筆談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873頁。其中所指大概就是此處的“香中”青蒿。另兩處均為肉類,其一是鳥類鴞,别稱鴟鴞或貓頭鷹;其二是蟲類,蜉蝣形似有翅膀的甲蟲,陸氏稱它“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蜉蝣之羽”條),雖在“蜉蝣”條下,卻可見不僅是蜉蝣,燒烤蟬蟲同樣是一道美味,在當時烤吃蟲子的尋常程度超過今日。事實上,魏晉時期燒烤食譜之豐盛程度遠不止這一二點,根據今人統計研究來看,因為游牧民族大量進入中原,所以燒烤相對普及且原料品種很多,除羊肉、豬肉等外,不乏黃雀、鵝、牛心、牛百葉及其他動物内臟等頗具特色的炙類菜餚④邱龐同:《魏晉南北朝菜肴史——〈中國菜肴史〉節選》,載於《揚州大學烹飪學報》2001年第2期,第26—27頁。張承宗、魏向東《中國風俗通史·魏晉南北朝卷》,第37—38頁。。
4.醋泡。醋在古代典籍又被稱酢、醯、苦酒,《傷寒雜病論》中有一“苦酒湯”流傳至今,專治咽喉發炎腫痛甚至不能發聲的疾病,當中的“苦酒”就是指米醋。傳統工藝中糧食經過發酵等程序可以轉化為酒,在醋酸菌的作用下可以進一步發酵為醋酸,所以自古存在“釀酒不成反成醋”的情況,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内“苦酒”都是醋的代名詞。《草木疏》中留存的醋泡食物品種包括蒲、荇、蘋等草類,或煮後醋泡,如蒲“䰞(煮)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笋法”(“有蒲與荷”條);或直接醋泡食用,如荇“䰞(煮)其白莖,以苦酒浸之为菹,脆美,可案酒”(“參差荇菜”條)⑤可參閲趙禕缺《説“荇菜”》一文。、蘋“可用苦酒淹以就酒”(“于以采蘋”條)。而這些醋泡後的菜品竟大都用作“案酒食”,可見今人以醋泡涼食為下酒菜或開席前小菜這一傳統也算是由來已久了。此外,陸氏還記載了一種更加有趣細緻的改良版的醋泡方式,名字叫做“蜜度”①羅振玉本“蜜度”作“蜜”,此條據《齊民要術》補正。:“(楙)欲啖者,截著熱灰中令萎蔫,淨洗以苦酒、豉汁蜜度之,可案酒食,蜜封藏百日乃食之。”(“投我以木瓜”條)繆啟愉在校釋《齊民要術》引用此一句時將“蜜度”解釋為:“‘度’,通‘渡’,就是在醋(‘苦酒’)、蜜等調和的液汁中作短時間的浸漬。”②賈思勰撰,繆啟愉校釋:《齊民要術校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年版,第224頁。姑從此説。將洗淨後的萎蔫木瓜在酸甜汁液中浸泡食用,算得上做工比較精細了。
5.炮。上述提及將生木瓜放入熱灰中的處理方式統稱為炮,《齊民要術》中便記載了一道由波斯傳入的魏晉時期名菜,在热坑中放入羊肚及肉煨熟,名作“胡炮肉”。事實上中國早有此法,鄭玄注《禮記·禮運》“以炮以燔”説:“炮,裹燒之也。”③《十三經注疏》,第1416頁。炮豚也是周代的八珍之一。炮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比較繁瑣精細的,先用泥、麵、荷葉等把食物塗裹後再置於火中煨烤,有的甚至以熱灰覆蓋後再以傳遞後的火温煨烤。另一種就是《草木疏》中提到的比較簡單的,直接把食物放在火中或带火的炭灰裏煨熟。上述木瓜在熱灰中炮熟後,還經水洗淨再處理,而葍草根則是“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温啖之”(“言采其葍”條),熟後徑直食用。後一種簡單吃法與現今農村火坑灰堆中埋番薯、土豆、荸薺等物,待炕熟後食用的方式類同。
除上述幾種外,陸《疏》中提及的食用方法還有鮓、醬、醃、曝曬等。另有花椒葉和“豉”這種魏晉始創的調味品,熊白、狼油等珍奇美味,以及用樗樹葉子作茶並用椒樹葉與茶葉合煮做香料的情形。然而這些陸《疏》都一帶而過,此處也不便再延伸。總而言之,三國時期的食材範圍相當廣泛,肉類、蔬菜類、瓜果、調料等應有盡有,食用方法也是多種多樣。此外,還有兩點更大的進步:其一,一物多吃,物盡其用,充分挖掘並發揮一種食材在不同生長階段的食用價值,如鱣魚既可以蒸了作臛,又可以作魚鮓,魚子又可以作醬;匏葉、莫等草類在剛生長時食用,而荼亦即苦菜在霜降後食用更加甜脆可口;有的要在春天吃,有的只能在秋天吃,都各有講究。其二,同一食材在不同地區的口感有不同及高下之分,不同品種也有優劣之分。如同樣是吃榛子,也就是山板栗,《草木疏》中就詳細記録了漁陽、范陽地方的甜美味長,倭、韓國諸島上的短味不美,還比較了奥栗、茅栗、佳栗等不同品種,可見對“吃”之重視及觀察體驗之細緻。不難看出,這一時期的社會飲食生活十分豐富,而這要歸功於農林牧副漁業的發展,肉類、蔬菜、瓜果等買賣市場的興旺,科技進步帶來的食品加工、保存方法的多式多樣等多方面的因素①劉春香:《魏晉南北朝時期飲食文化的發展及其原因》,載於《許昌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第47—50頁。。這一時期的人們普遍關注食物本身的食用價值和人在味覺上的享受,有意識的從審美以及文化的層面對待飲食活動。並且上至宫廷貴族,下至黎民百姓都願意在“吃喝”上仔細鑽研以求花樣百出。藝術或文化地“吃”,同樣是魏晉時期思想文化自覺、多元時代精神風貌的重要體現。
(二)醫藥養生習俗
漢末三國時期的醫學和藥學都有了較大的進步,相關代表人物和著作也不在少數,今人耳熟能詳的如張仲景及其《傷寒雜病論》和華佗及其失傳的《青囊經》,前者重理論與方藥記載,後者善外科治療;此外還有他們的後輩,如樊阿以針灸聞名,吴普和李當之都精於藥性,並分别著有《吴普本草》和《本草經》傳世。《草木疏》中主要記載了五種可入藥的動植物②《詩經》中的藥用植物遠不止此,可參閲劉昌安《從多維視角看〈詩經〉植物的藥用價值及文學功能》一文。,其中蝱即是藥草貝母,鼉是作為合藥用的鼉魚甲。這兩種僅一帶而過,剩下三種記録較詳。但又可分為兩種情況。其一,特定用藥。芣苡這種植物因為喜歡在牛腳印中生長,所以又被稱為馬舄、車前、當道,中藥名為車前子,屬於現代植物分類當中的車前科。陸氏稱“其子治婦人難產”(“采采芣苡”條),該功用為後世各類《本草經》徵引。《草木疏》中雖未像藥書一樣指明車前子有利水清熱、明目祛痰等藥效,但仍可見車前在難產等特定場合中作為治病藥材使用而非平常服用。
其二,日常養身。蓫菜别稱羊蹄或倒水蓮,嫩莖葉可做蔬菜食用,根部肉質肥厚,洗淨切片(塊)曬(陰)乾後可入藥。入藥的蓫菜名為商陸,口服能逐水消腫、通利二便,外用可解毒散結。《草木疏》稱其“多啖令人下氣”(“言采其蓫”條),“下氣”即中醫所説的“矢氣”,指腸胃鬱結而排
洩氣體,《雜病源流犀燭·諸氣源流》有言:“所納穀食之氣,從内而發,不得宣通,往往上行則多噫氣,上行不快,還而下行,因復下氣也。”①沈金鼇撰,李占永、李曉林校注:《雜病源流犀燭》,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頁。陸氏所載蓫菜的藥用價值是通過吃用食物的方式達到的,而這種採取食療而非用藥的方法在後世便有了更多更複雜的用法,比如《聖濟總録》記載的“商陸豆方”:“生商陸(切如麻豆)、赤小豆等分,鯽魚三枚(去腸存鱗)。上三味,將二味實魚腹中,以綿縛之,水三升,緩煮豆爛,去魚,只取二味,空腹食之,以魚汁送下,甚者過二日,再為之,不過三劑。”②彭懷仁等主編:《中醫方劑大辭典》第9册,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年版,第584頁。可治水氣腫滿、通大小便,與“多啖令人下氣”有異曲同工之妙。無獨有偶,杞樹形如臭椿,一名苦杞,一名地骨,它的果實應當是所謂的枸杞子,根莖皮是藥材地骨皮。《草木疏》記載“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集於苞杞”條),可見其與使用芣苡方法不同,芣苡是作為助產的一味藥材,而杞作為日常食用的養生食材,這種意識在後世的文獻記載中就更加詳細了。唐代孟詵在《食療本草》中認為枸杞“堅筋耐老,除風,補益筋骨,能益人,去虚勞”③孟詵、張鼎撰:《食療本草》,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頁。。宋代的《聖濟總録》、《太平聖惠方》等也對枸杞保健方有所記載:“枸杞葉一斤,羊腎一對(細切),米三合,蔥白十四莖。上細切,加五味煮粥,如常法,空腹食。”④彭懷仁等主編:《中醫方劑大辭典》第9册,第119頁。這道食療方名枸杞羊腎粥。或者不加羊腎:“枸杞葉半斤(切),粳米二合。上藥以豉汁相和,煮作粥,以五味末、蔥白等,調和食之。”⑤彭懷仁等主編:《中醫方劑大辭典》第9册,第113頁。這只是單獨的枸杞粥,但它們都能達到治陽氣衰和五勞七傷等病患,具有陸氏所説的“輕身益氣”的功效⑥可參閲孫鵬哲《枸杞頭及藥膳三例》一文。。由此可見,“行醫如做廚、吃藥不如食補”的中醫養生觀及養生方法,至少在陸氏時代就已經深入人心了。貧寒的普通百姓儘管不能如同世家貴族一樣有閑錢和暇時以求養生延年,不能通過服寒食散、尋求仙藥、煉製金丹、修煉氣功等去追求長生不老,但他們仍然可以利用這些天生價廉、隨處可見的植物,稍加處理以作日常食用,同樣能達到養生保健的功效,充分體現了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
二、生產與娱樂
(一)生產製造風俗
雖然漢末三國這一時期戰爭不斷,社會經濟遭到了巨大的破壞,但是兩漢數百年時間的積累終究還是為人們的生產生活帶來了一些新面貌,《草木疏》中的相關記載就展現了以下三個重要方面。
1.農業。《草木疏》中記載的這方面相關内容,主要體現在農民的家庭副業發展方面。前文所述飲食部分當中提及的野菜野果,其中有些就是當時的人們自家栽種的。如檖這種樹,它俗稱赤蘿或山梨,原本生長在齊郡廣饒縣堯山和魯國河内共北山中(今河南、山東一帶)。但因為它結出來的果實像小型的梨子,十分甘甜可口,所以“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者”(“隰有樹檖”條),説明當時已有人為移植野生植物,並且還能培育得非常成功。事實上,從其他古籍中也可知道,魏晉時期的不少人們都習慣在門前屋後種菜養雞,以此豐富日常飲食或貼補家用。除此外,牛的飼養在當時也非常受人重視。《草木疏》中保留了三條與牛有關的記録:蒹“牛食之令牛肥強”(“蒹葭蒼蒼”條),芩“為草真實,牛馬皆喜食之”(“蘞蔓于野”條),這兩樣都是天生天長的優質牧草;此外還有蘞草,别稱野紅薯、山地瓜、山葡萄秧等,葉子茂盛細長。從醫理上來看,它有清熱解毒、消癰散結的作用,陸氏時代的人們就把它的莖葉用來“䰞(煮)以哺牛,除熱”(“蘞蔓于野”條),這是關於牛病的比較常見易操作的醫治方法。當然,《草木疏》表現出的對牛的特别關注,可能不僅僅是因為牛耕的重要性,極有可能還有牛車影響。文獻記載,東漢末年以來,牛車這一出行方式在貴族階級中風靡一時。
2.漁獵產業。“食魚與稻”自古就是多山川河流湖泊地區的重要生活方式,而漁業在農耕時代也還是重要經濟來源之一。《草木疏》記載一種名作鱣的魚,出自江海地區,每年三月中旬便逆流而上,因為鱣魚身形和龍相似,當時有人“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有鱣有鮪”條)。無獨有偶,魴也是一種美味的魚,遼東、梁水等地的魴魚尤其肥厚,遠優於中國其他地方的魴,所以當時就有“居就糧,梁水魴”(“維魴及渼”條)的俗語,表明了梁水邊人就地取材、以魴魚為食的生活特徵。與鱣魚、魴魚不同,鱮也即現代所説的鰱魚在古代並不受待見,認為它厚而頭大,味道不美,有里語“網魚得鱮,不如㗖茹”(“維魴及渼”條),説的是倘若想吃魚卻捕得了鱮魚,那還不如吃野菜。
漁業之外,狩獵也同樣如此,前者靠著江河湖水,後者依託的則是山林叢野。獵物包括鳥、獸兩類,按《草木疏》記載,鳥有鷮、鴻鵠、雁、鴞等,它們大都肉質鮮美,其中因為鷮肉甚美,所以當時的林慮山(位於今河南省林州市石板岩鎮)中人還常有“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有集維鷮”條)的説法。相比鳥類,獸類獵物的用途更廣,除了肉可做食物之外,它們的毛皮或内臟也多有用。比如熊的脂肪經過提煉後便可獲得熊白,俗稱熊脂膏,與熊類似且稍大的羆,包括黃羆、赤羆等也可提煉出羆脂,此二者既可作為藥材,也是一種珍貴的食材。而狼的脂肪又稱狼膏,《草木疏》稱“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為裘”(“狼跋其胡”條),狼肉可做食物,狼皮可做衣裘,狼膏同熊白一樣,既可作藥材,也可作為食用油。狼膏的藥用價值,外用可潤膚,《本草綱目》稱:“(狼膏)主治:補中益氣,潤燥澤皺,塗諸惡瘡。臘月煉淨收之。”①李時珍:《本草綱目彩色圖鑑》,北京:軍事醫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4頁。獸類獵物大都可以一物多用,而且無論是肉、皮還是脂肪,都十分珍貴。所以與通過行獵以娱樂身心的貴族不同,普通百姓們借此貼補家用甚至以此為生,而於此正可見陸《疏》平民化的日常生活觀。
3.手工業。《草木疏》中涉及到的手工物品種類不在少數,主要包括:
(1)製造車馬相關工具,古人根據木材的不同特性,分别做成車的不同部件。條樹又稱槄樹,俗稱山楸,現代學名楸,它“材理好”(“有條有梅”條),是一種質地緻密的木材,所以被用來做車板。其他類似的,梀樹皮薄而白,材質堅韌,被用來作車轂(“隰有杞夷”條)。栵樹“木理堅韌而赤”,被用來做車轅(“其灌其栵”條)。栲樹“皮厚數寸”,被用來做車輻(“山有栲”條)。檉也即河柳的樹皮“正赤如絳”有些微裝飾美,所以被用來作馬鞭及杖(“其檉其椐”條)。
(2)製造兵器。同造車一樣,根據不同兵器的材質需求選擇不同的樹木。前面講到的白桵木不僅可以用來做犢車軸,還可以用來做成與犢車軸粗細長短類似的矛戟鎩木桿。杻樹又稱檍樹,是做弓弩桿的好木材(“隰有杻”條);甘棠木緻密堅韌,所以也常用來做各種器具,《草木疏》記載其也可做弓桿(“蔽芾甘棠”條);蒲柳常被用來做箭桿(“揚之水不流束蒲”條)。除草木之外,還有魚服,一種用水生動物原料做的武器裝備。魚服是魚獸的皮,“魚獸似豬,東海有之,一名魚貍,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一説魚貍即現在的海豚,《草木疏》記載其皮可用來包裹“弓鞬”、“步叉”、“矢服”。它不僅作為盛裝箭矢的器具,而且還是一種利用空腔接納聲音原理的軍用竊聽器,《夢溪筆談》有言:“古法以牛革為矢服,臥則以為枕。取其中虚,附地枕之,數里内有人馬聲則皆聞之,蓋虚能納聲也。”①沈括撰、胡道靜校證:《夢溪筆談校證》,第628頁。戰鬥時以矢服盛箭,竊聽時則取出箭矢,吹足氣並繫住袋口的繩子使其中空,人頭枕於其上,可聽見幾里以外人馬的聲音(“象弭魚服”條)。
(3)紡織。依据張承宗等人的研究,漢末魏晉時期政府在徵收銀錢之外格外徵收絹棉②張承宗、魏向東:《中國風俗通史·魏晉南北朝卷》,第410頁。。而當時的人們為了完成賦税,除了養蠶以獲得繅絲外,他們更善於利用天然的草木直接獲取材料。紵,現代學名苧麻③以苧麻織布的歷史與技術流程可參閲鄧陽春《沅江縣苧麻生產情況調查》一文。,是古代五麻之一,它莖部位的韌皮纖維細長而又強韌,有光澤而易染色,優點很多,因而是重要的紡織作物和優質紙原料。《草木疏》中記載了以苧麻織布的前段步驟,“今官園種之,歲再割,割,便生剥之,以鐵若竹刮其表,厚皮自脱,但得其裏,韌如筋者䰞之,用緝,謂之徽紵,今南越布皆用此麻”(“可以漚紵”條)。事實上,苧麻布的完整紡織工藝包括種麻、浸麻、剥麻、漂洗(日曬夜露)、績麻、成線、絞團、梳麻、上槳、紡織等12道手工工序。此外,陸氏還記載了當時的雲南牂牁人以桐樹,以及江南人以榖桑④榖與穀(簡化字為“谷”)形近,《説文解字》中一作木部、一作禾部,該書各版本訛誤甚多。金口《“穀紙”非“谷紙”》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但可能是印刷原因,此文仍然將“榖紙”錯作“穀紙”。也即現代的枸樹皮“績布”(“梓椅梧桐”條、“其下維榖”條)的例子⑤夏緯瑛先生認為此處講到的泡桐的木不可能用來績布,是“桐花為布”的傳説造成的誤解,而陸氏把棉花與桐花(舊有棉音譯“古終”,與“桐”音進)弄混淆了。此説恐有不據。從《後漢書·南蠻傳》開始就有了“織績木皮,染以草實”的記載。《通典》卷一八八引三國吴康泰、朱應《吴時外國傳》(又稱《扶南土俗傳》等)稱“春月取其木皮,績以為布”。《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引《抱樸子》稱:“夷人取此木華績以為布,其木皮赤,録以灰煮治以為布,但粗不及華,俱可以火浣。”樹木的花或皮應當都能績布,桐樹未必不可。。這門手藝傳承至今,在現代被稱為“黎族樹皮布製作技藝”,已經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了。其成布過程,包括選材剥取、壓平浸泡、捶打成片、晾曬、縫合等步驟。現在樹皮布僅留存於海南黎族且近乎絶跡,但可以想見在陸氏時代,因為原材料豐富且易於採集,而成品又經久耐用、柔軟白淨,樹皮成為一種重要的紡織材料。
(4)除車馬工具、兵器、紡織外,《草木疏》中還零星記載了一些其他頗有趣味的小物件,品種繁多。第一類是文房用品,如韜筆管,“韜”字從韋從舀,意為刀、劍不斷出入的皮套,在此處指毛筆套。尹灣漢墓曾出土過兩支毛筆套在“一個由雙管組成並分兩截的木胎漆管内”,除尹灣漢墓的木質筆管外,168漢墓、西郭寶墓也出土過竹製筆管①馬怡:《一個漢代郡吏和他的書囊——讀尹灣漢墓簡牘〈君兄繒方緹中物疏〉》,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9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101—132頁。。《草木疏》中記載,萇楚又稱羊桃,也即後世熟知的獼猴桃,它枝莖細弱卻根系發達,所以古人“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脱之,可韜筆管”(“隰有萇楚”條),這是以植物莖皮做成韜筆之管,簡單易尋且成本低廉,是普通百姓的重要筆管來源。又如防書蠹粉,把蕳草也即蘭草“著粉中”,可以“藏衣著書中,辟白魚也”(“方秉蕳兮”條),“白魚”就是書蠹,俗稱書蟲。此外,還有榖桑樹皮造出的榖皮紙,白桐為琴瑟、鼉皮冒鼓等樂器。第二類是閨房物件,如染髮劑。苕又名紫蕤,即古書中所説的凌霄花,花朵外橘黃而内鮮紅,七八月份為紫色,形似紫草,此時用凌霄花染皂並經水煮過後洗頭髮,髮色變黑,是當時的一種純天然染髮方法(“苕之華”條)。又如楛樹枝條“揉以為釵”,陸氏記載的揉楛樹枝莖而成的釵,應該也是所謂的“荆釵布裙”中“荆釵”的一個變種,一般為普通老百姓或者説是貧家婦女們所常用。這種製作首飾的方式還引來了一則笑談:上黨人(今山西東南部)調笑當地婦人,問:“買釵否?”曰:“山中自有楛。”(“榛楛濟濟”條)這一風俗展現了當時普通百姓苦中作樂,雖然生活艱難卻仍可以就地取材、尋找生活情趣的樂觀處世態度。第三類是一些日常瑣碎事物,如穫樹、貝殼做成的杯具及盛物器皿,以蕭草為蠟燭,臺草為蓑笠,菅草、穫樹皮為繩索、甑帶,以枸樹、條樹為函板及棺材板等。
(二)休閑娱樂風俗
《草木疏》不僅記録了當時人們的生產製造生活智慧,還涉及到他們的休閑娱樂形式與活動,體現了漢魏時期人們的生活趣味。該書主要談到了以下兩方面。
1.園林藝術。中國古代園林從“囿”開始,如周文王的靈囿,圈定一塊地域,或築界碑,大都是原生態,基本没有什麽設計内涵。秦漢出現了宫“苑”,如漢武帝時擴建的上林苑,造亭築橋,種植花木,苑已經突破了簡單原始的囿,有了進一步的風景組合,人為痕跡明顯增加。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園”,被普遍認知為中國園林發展史中的重要轉折時期。這一時期的私家園林大規模出現,與皇家園林並立成為古代園林的主體之一。其崇尚自然並以再現自然山水為建園思想,是自然山水審美觀念形成時期的重要表徵之一。《草木疏》中記載了五種作為園林景觀的草類、木類植物,涉及兩種性質的園林。
其一是宫中園林。蕑草也即蘭草,被孔子譽為“王者香草”,因其外形美觀、氣味芬芳及内涵久遠美好,所以成為了園林植物的首選之一,陸氏稱“漢諸池苑及許昌宫中皆種之”(“方秉蕑兮”條)。
其二是“官園”。薇草是山菜的一種,可供宗廟祭祀;紵也是草本植物,可用來緝麻布;二者被當時的“官園種之”(“言采其薇”條、“可以漚紵”條)。木類植物如常棣、杻樹和枸樹,其中杻樹在官園中正名“萬歲”,其别稱“檍”樹包含了“億萬”的好兆頭,加之本身枝繁葉茂,所以它被廣泛種植(“隰有杻”條);而枸樹枝繁葉茂,在官園中别號“木密”(“南山有枸”條)。《草木疏》中的“官園”所指究竟是哪種園林呢?根據張渝新的研究,“官家園林是以官署園林為主體”的、有别於皇家、私人、寺觀等的官產園林。它們依靠“地方政府和各級官府的長期經營”而得以留存,並主張將官家園林提升到與皇家園林、私家園林和寺觀園林三大主流分庭抗禮的地位①張渝新:《川派古典園林是中國官家園林的典型代表》,載於《中國園林》2003年第19期,第68—70頁。。在論述過程中,作者將這種類型園林的出現時間定位於漢至兩晉時期,並將之和“亭”這一基層行政機構相關聯,比如兩晉時期的新亭與蘭亭。後來又有崔志海認為“公園”一詞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作品中的廣泛出現“側面反映出了官家園囿的興盛”②崔志海:《近代公園理論與中國近代公園研究——讀〈都市與公園論〉》,載於《史林》(滬)2009年第2期,第165頁。。而《草木疏》中對“官園”的記載,似乎可以為二人觀點提供又一佐證。
2.飼養寵物。古人對動物的寵愛與飼養具有相當深厚的歷史傳統,耳熟能詳的如衛懿公愛鶴失國、王羲之愛鵝贈字、林逋“梅妻鶴子”等。中國歷史上與寵物有關的趣聞軼事數不勝數,《草木疏》中對此也有記載。
一種是鶴:“今吴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鶴鳴于九皋”條)魏晉時期的愛鶴名士中有兩位代表,一是羊祜,《世説新語·排調》中記載了他教導鶴舞蹈的故事;一是支道林,《世説新語·言語》中也記載了他將雙鶴放生的言行。二者略有不同,前者是將鶴作為“人工飼養”的對象,後者“不願意束縛它使它成為寵物”,但從本質而言他們對鶴的喜愛是一致的。據阪井多穗子的研究,鶴作為寵物不獨魏晉時如此,而且是與中國的整個士大夫群體都“有著特别密切的關係”①阪井多穗子:《中國士大夫與作為寵物的鶴》,載於《中國典籍與文化》2000年第1期,第112頁。。為什麽鶴會受到他們如此的青睞呢?一方面是因為它的外形漂亮,舉止優雅。陸氏曰:“鶴,形狀大如鵝。長腳,青翼,高三尺餘。赤頂,赤目。喙長四寸餘,多純白,亦有蒼色,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同上)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至少自《詩經》時代始,鶴就被賦予“高逸”的象徵意義。《詩·鶴鳴》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②《十三經注疏》,第433頁。這裏以鶴來比喻宣王求取的“身隱而名著”的“賢人之未仕者”,此後歷代詩歌更是將鶴作為文人“追求隱逸”、體現其“生命意識”的重要意象③董艾冰:《唐詩中的鶴意象研究》,廣東:暨南大學學位論文,2016年,第84頁。。宋人陳巖肖《庚溪詩話》更是稱讚道:“衆禽中,唯鶴標致高逸;其次鷺,亦閑野不俗。”④陳巖肖:《庚溪詩話》,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第2552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第20頁。依照陸氏所説,魏晉時期的士人養鶴應該是有了比較大的規模,而這一時期獨特的社會風氣也使得鶴在“賢者”、“高逸”之外,又增添了“成仙”、“長生”等與道教相關的内涵。
另一種是鷺:“鷺,水鳥也。好而潔白……大小如鴟,青腳,高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餘。頭上有長毛十數枚,長尺餘,毿毿然與衆毛異,甚好;將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吴人亦養焉。好群飛鳴。”(“值其鷺羽”條)白鷺頸長腿長,通體潔白,外形典雅,這一意象在唐及其後的文學作品中廣泛出現,並逐漸與白鷗結合並稱“鷗鷺”。魏晉時人有將其和“鵠”並舉者,如張華《遊獵篇》“鵠鷺不盡收,鳧鷖安足視”⑤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970頁。,它們都是體大羽白的水鳥。或者是更廣泛的並稱,如左思《吴都賦》“鳥則鶤雞鸀鳿,鸘鵠鷺鴻”⑥蕭統編,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03頁。,它們大體都被賦予了淡泊、高潔、自由、超然等内涵。事實上,陸氏所記載的“鶴”與“鷺”具有極大的相似性,它們都有美好的外形和超越世俗的寓意,寄託著魏晉時代士人們的審美追求和價值取向。值得注意的是,《草木疏》中記載的這些寵物屬於貴族階層休閑娱樂對象,和平民百姓無關。其他的,諸如牛、雞、馬、鷹犬等動物,是貴族間用來相互競比的道具,魏晉時期賽牛、鬥雞、馴虎表演等風氣盛行①。如此一來,貴族階層對其所飼養動物的要求,不在其實用性,也不像普通百姓那樣用來貼補家用,而是看中它們觀賞性或娱樂性,以此來體現出他們對風雅的追求,彰顯他們放浪形骸,希冀超越世俗束縛的形象氣質與精神追求。所以,即使都是作為寵物,他們也是更加青睞、讚賞“少家畜性、多寵物性”的動物②,就如《草木疏》中所提到的鶴、鷺一類。
三、宗教與方術
從漢末以來,由於社會動盪,局勢不穩,人們總是感覺命運難料,充滿了人生的幻滅感。因此魏晉時人多放浪形骸,將脱離苦海的希望寄託於縹緲之物、宗教神鬼之説。張承宗等人認為“萬物有靈是這一時期人們普遍的信仰”,民間信仰形式衆多且層出不窮,“整個社會中煽揚著一股迷信之風,彌漫著一股妖異的氣氛”③。《草木疏》雖是描述草木鳥獸蟲魚,但涉及宗教與方術類的内容卻不在少數,而這些内容大都充滿了奇幻且有趣的色彩。具體説,這些内容大致可以分為下面三種類型。
(一)祭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自古以來都備受重視,魏晉時期同樣如此。現存《草木疏》中記載與祭祀有關的内容共計4條,都和草有關,它們的使用方法和用途則各不相同。“薇”是一種山菜,現代學名大野豌豆,别名大巢菜,它的“藿”也即豆葉可作羹湯,所以“今(三國時期)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言采其薇”條)。這種草是做成羹湯後充作祭菜,用來祭祀先祖的。植物作為祭品,除了供神食用外,還有香氣誘神的功效,“蕭”草,現代學名荻,别稱荻蒿,根據“士以蕭,庶人以艾”的説法可知,它與艾蒿别為兩物,但因為同屬於香草有香氣,所以被用來“祭祀以脂爇之為香”,“爇”就是燃火焚燒的意思,《詩經》當中還有鬱金香、蘭芝、薰草、艾等植物與蕭的此種用法相同。與上述兩種直接充當祭品的草類不同,白茅則充當祭具。陸氏記載稱“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白茅包之”條),“縮酒”有兩種解釋,一是指祭祀時以茅濾去酒中糟粕,另一種是指在祭壇前面立一束白茅,把祭酒澆在茅上,酒水漸漸滲入草中,就好像所獻之酒已經被神明享用了。但此茅究竟為何,存在白茅、青茅、香茅、苞茅等多種爭議。最後一類的“葍”俗稱牽牛花,地下根莖較大且富含澱粉,可以充飢。但是它隨處蔓生,危害農作物,並且有臭氣,所以鄭玄認為葍是“惡菜”。陸氏記載其“漢祭甘泉或用之”(“言采其葍”條),不具體,怎麽用,用哪一部分等都不清楚,且根據也不清楚。姑存其説。
(二)誌異及傳説。《草木疏》中記載了幾種比較奇怪神異的生物。比如蜮,這種神話中的害人蟲形狀似龜,有三隻腳,别稱短弧、射影、水弩。蜮生性狡詐,“人在岸上,影在水中,投人影則殺之”,今有成語“含沙射影”説的就是這種生物。陸氏記載當時的南方人是這樣應對它的:“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如鬼如蜮”條)陸《疏》中還提及了螟蛉和蜾蠃之間的糾葛和文獻的誤書。螟蛉俗稱稻青蟲、粽子蟲,身體細小而呈青色。一直被古人們認定為是螟蛉最終成為了蜾蠃的兒子,所以有成語“螟蛉之子”,代指義子。《詩經·小雅·小苑》中説:“螟蛉有子,蜾蠃負之。”①《十三經注疏》,第451頁。從那時起古人們便以為是有雄無雌的蜾蠃因為無法生育後代,所以纔辛勤銜回螟蛉並背負其上作為自己的兒子,如此煞費苦心,螟蛉終於“七日而化為其子”,就好像螟蛉真的成為了蜾蠃的兒子。而實際的情況是,螟蛉的天敵蜾蠃這種寄生蜂將螟蛉捉回巢中,並用尾刺將其毒至半死,最後在螟蛉身體中產卵,新生的蜾蠃就會以螟蛉作為食物。真相直到後來的陶弘景親身觀察纔得以揭開,但陸氏時代人尚没有揭開謎底,仍然蒙蔽在螟蛉能化為子的迷局中。陸氏記載了時人根據這種現象想象出的一句里語:“咒云:‘象我,象我’。”(“螟蛉有子”條)只是今天我們已無法得知這句話用於什麽場景,以及具體的情形,和人們在最終未能“象我”後思維實際情態。
除上述充滿靈異色彩的描述外,《疏》中還收録了幾則傳説故事。芑在《詩經·小雅·采芑》中是一種類似苦菜的可食用野菜,陸氏稱“西河雁門芑尤美,土人戀之不出塞”(“薄言采芑”條),“土人”一作“胡人”或“詩人”,西河、雁門之人流連於當地的芑菜之美以致不願出塞,如張季鷹莼鱸之思,也算是當時的一段美談了。另有一則與魚有關的傳説故事,鮪魚又稱吞拿魚,現代學名金槍魚,陸氏稱此魚是樂浪尉仲明溺水身亡所化,所以當時的東萊、遼東人又喚此魚為“尉魚”或“仲明魚”(“有鱣有鮪”條),這一傳説不知源自何處,後世的《毛詩多識》認為這一説法“近於怪”,應當是“鮪”“尉”音進而導致的牽強附會之説,對陸説予以否定。
(三)迷信方術。不僅是受到前文提到的社會背景的影響,兩漢以來讖緯之學的發展和興盛同樣對這一時期的人們的認知方式產生了重大影響,所以《草木疏》中不可避免的記載了一些與迷信方術相關的文字,這部分的内容比較豐富,大致可以概括為兩種類型。
1.將鳥獸草木蟲魚的某些特性或行為與人類社會的吉凶禍福聯繫在一起,類似現今人們常常認為的“烏鴉頭上過,無災必有禍”,“門前喜鵲叫,好事要來到”等觀念。蟏蛸這種蟲子是吉利福慶的兆頭,它又稱喜蛛或蠨子,體多細長,與蜘蛛相似,古籍中稱其為“長踦”或“長腳”,《草木疏》稱“此蟲來著人衣裳,有親客至,有喜也”(“蟏蛸在户”條),因此荆州、河内之人叫它“喜母”,幽州人乾脆喚作“親客”。除此外,另有兩種預示凶禍的鳥類。
《草木疏》中記載了一種名叫鸛雀的水鳥,形似鴻雁但體型更大,有極長的紅色尖喙,以及細長的腿和細長的帶蹼的爪子,一般是白色身子和黑色尾翅。這種鳥在西方國家被視為可以“送子”的吉祥鳥,還是德國的國鳥。陸氏筆下的鸛鳥十分有靈性,它的“卵如三升杯”(“鸛鳴於垤”條),見有人來就把幼鳥按住趴伏在地上,藉此來保護自己的孩子;此外鸛雀在池水邊搭築泥巢,把捕來的小魚放到就近的池邊淺水處,以便幼鳥食用,可見“愛子”和水居同為鸛的兩大天性。可能正是由於這兩方面的習性和特點,陸氏時代的人們認為“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如果殺掉了鸛雀的幼鳥,那麽整個村莊就會遭遇旱災。無獨有偶,《拾遺記》中也有言:“多聚鸛鳥之類,以禳火災,鸛鳥能聚水于巢上也。”①王嘉撰,孟慶祥等譯注:《拾遺記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5頁。這些都是賦予了鸛以掌水、滅火及致旱方面的能力。
如果説鸛雀是因為人類主動招惹“殺其子”纔帶來全村遭旱的後果,那麽鴞則屬於只要“來者”即為“不善”的鳥了。這種俗稱鴟鴞、貓頭鷹的鳥類是夜行類的猛禽,具有極其鋭利的鉤狀喙和爪,《草木疏》稱其為“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翩彼飛鴞”條),《詩經》於“翩彼飛鴞”處稱它食用了主人家的桑葚心存感激,最終變惡聲為善音。而他處則稱“(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流離之子”條),按文獻記載,流離即梟,與鴞為一物。儘管現代動物學研究已經為它平反,但在千年的時間裏,貓頭鷹始終被認為是在幼鳥階段便會啄母親雙眼作為食物的“惡聲鳥”、“不孝鳥”。賈誼在《鵩鳥賦》中所寫的“野鳥入室,主人將去”①蕭統編,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第256頁。,這一不吉祥的報喪鳥也是貓頭鷹。經《嚼文嚼字》整理得知,很多朝代都有以消滅貓頭鷹為重任的例證。漢武帝時期還用“梟羹”作為“除凶”佳品以賞賜群臣,這種情景就是後來蘇轍所説的“百官卻拜梟羹賜,凶去方知舜有功”②韻洲:《貓頭鷹千古“蒙冤”》,載於《咬文嚼字》2014年第9期,第24頁。。值得注意的是,《豳風·鴟鴞》中也有一鳥名作鴟鴞,“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③《十三經注疏》,第394頁。,此處的鴟鴞别稱鸋鴂,是一種十分殷勤的吉祥鳥,又被稱為“巧女鳥”,和這裏講到的“鴞”並不是同一種。
2.通過某些特性或行為來隱喻政治或道德方面的得失。如鴇鳥這一稀有候鳥,陸氏描述它是“似雁而虎文,連蹏④羅振玉本蹏作啼,據丁晏本改正。”(“肅肅鴇羽”條),此鳥因不善飛行而常遭獵殺,所以陸佃説它們“性群居如雁,自然而有行列”,認為他們正是由於不善飛行所以纔“以其類集聚衆羽而成翼,集聚衆翼而成行”⑤陸佃《埤雅》,清康熙年間顧棫校刊本《埤雅》卷九,第376頁。,天性不休止於樹木,而一旦它們休止於樹木,必定是因為處於極為危苦的境地,所以《詩經》用它來比喻君子疲於征役,十分危苦的情形。至於蜩螗,螗是蟬蜩的一種,陸氏認為它是“蟬之大而黑色者”,這類生物被賦予了“文、清、廉、儉、信”這“五德”(“如蜩如螗”條),理由正如陸雲在《寒蟬賦》中講述的:“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食,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⑥韓格平等校注:《全魏晉賦校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31頁。蟬就這樣被人為的賦予了美好的君子之德,被盛譽為“至德之蟲”,歷來受文人们的推崇。
以上兩種情況還只是人們將内心的某種情感與期許投射到動植物身上,下面的就更接近於天人感應、陰陽災異之説了。螟、螣、蟊、賊,舊説都是同一蝗蟲,陸氏認為它們各有不同,但總體來説都是一種對莊稼有損的害蟲,《疏》引許慎之言稱“吏冥冥犯法,即生螟。吏乞貸,則生蟘。吏祗冒取人財,則生蟊”(“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條),將官吏貪贓枉法與蝗災聯繫在了一起。這是因為當時的人們相信萬物有靈、俱有所感,自然界會對人類社會的行為做出反應,就好像國家一旦出現異象或發生自然災害,當權者便需反省自己是否有為政失德之處。與之相對應的,如果是為政清明,那麽就會出現祥瑞以表示上天的獎勵,這類文字記載在緯書中大量出現。作為祥瑞之物,有現實生活中本身存在的,如甘露、禮泉、嘉禾、名珠等,更多的只是存在於人類想象中、極為罕見的神物。《草木疏》中便有兩例涉及此類神物,一是麒麟,它集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蹏於一體,從頭到腳、一舉一動都暗合某種道理,善良而聰慧過人,古人相信“王者至仁則出”(“麟之趾”條),王者的仁政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上天必有所感並派下麒麟這樣的瑞獸。與麒麟類似的還有騶虞,也是古代傳説中的一種仁獸,“君王有德則見,應德而至者”(“于嗟乎騶虞”條),它同樣是君王德至百姓及至草木鳥獸的象徵。
總之,魏晉時期人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水準還有一定的局限,他們無法像今天這樣科學的察明動植物與生俱來的某些自然特徵和某些看起來怪誕詭奇的習性。不安定的社會現實使人们深感命運無常,加之兩漢流傳而來的天人感應、讖緯之學等,在多重因素影響之下,陸氏時代的人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想象,賦予了自然界生物以種種人類社會中充满奇幻色彩的意義。這是他們出於對自然之物的敬畏,也是對天地、日月星辰、氣象、山川水火、動植物、祖靈等現象的崇拜與嚮往。當然,今存《草木疏》並非完帙,其中所記載的描畫的内容或許只是魏晉人豐富心靈世界的冰山一角,而我們卻也由此得以體會其喜樂之情和人生百態。
四、從“多識”到義疏:《草木疏》中的物變
从《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文本的具體内容來看,本書雖然篇幅不長,卻藴含了豐富多樣的文化内容,生動具體地展現了魏晉時期的某些社會面貌:他們重口腹之欲,菜品樣式繁多且别出心裁,貴族們自然是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普通百姓們也能充分就地取材、力所能及的做出花樣;醫藥學固然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有了進一步發展,然而更引人注意的是他們對養生保健以致長生的重視,昂貴的寒食散、金丹不是人人都能獲得,但具有某些藥性的植物卻是觸手可及,平民們把它們製成沖飲品或菜品,一樣能夠實現日常養生的功效;生產製造行業有了很大進步,農業和漁獵繁榮,尤其是手工業,魏晉時期的手工製造產品涉及到紡織、交通運輸工具、兵器製造、造紙、文房閨閣用品等方方面面,表明這一時期人們的物質需求及生活不再如先前時代那般貧乏;與豐富的物質生活相對應的是人們休閑娱樂方式的多樣有趣,這一時期大量自然山水官園的修建、飼養寵物以供欣賞或競技成風等現象,展現了貴族閑暇生活的極度享受與縱欲;崇尚萬物有靈的社會風氣讓整個社會的信仰文化都帶上了迷幻的成分,讓魏晉時人在認識動植物時附加了許多充滿神秘和奇幻色彩的想象和内涵。
《草木疏》中展現的雖僅僅是完整的魏晉時期社會面貌的一隅,然而這些片面仍然可以反映出:一方面,魏晉時期政治動蕩,戰亂天災頻繁,人的命運無常,所以享樂放縱之風盛行,人心逃避現實而寄託於虚幻縹緲之事,而貴族門閥林立,他们與普通百姓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形成了明顯的等級差異;另一方面,魏晉時期的經濟情況畢竟是有了較大的進步,而且還在有條不紊的持續發展,民族之間的交流日趨緊密,這些為他們豐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奠定了物質基礎,並促進了文化自覺的產生乃至文化的繁榮。
當然,《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依然是經學的支脈,並且帶有鮮明的學派屬性,不然它就不會冠以“毛詩”。但與此同時,我們自然也承認它的獨特性,它不僅專疏草木鳥獸蟲魚,而且較之傳統經學,其感興趣的“物”也帶有強烈的經變色彩。
自孔子以來,《詩經》草木蟲魚之説解秉持的文化精神一直是“多識”。《論語·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然何謂多識,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以為“事父”、“事君”為人倫之大者,因為《詩》中人倫之道無所不備,故二者“舉重而言”。相比之下,“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之事,其作用在於“資多聞”而已①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78頁。。然孔子説“多識”和現代意義的生物學無關,也非學有餘力之閑事,故朱子的解釋並非確詁。相比之下,我認為錢穆先生的解釋得夫子論“多識”之精髓。其曰:
詩尚比興,多就眼前事物,比類而相通,感發而興起。故學於詩,對天地間鳥獸草木之名能多熟識,此小言之。若大言之,則俯仰之間,萬物一體,鳶飛魚躍,道無不在,可以漸躋於化境,豈止多識其名而已。孔子教人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廣大其心,導達其仁。詩教本於性情,不徒務於多識。①錢穆:《論語新解》,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325頁。錢穆先生所謂“小言之”、“大言之”也就是歷代《論語》注釋中對“興”的兩種不同闡釋路徑,一者曰取譬連類,再者曰感發志意。前者涉及説詩方法,後者涉及詩之價值功用。此二者無論是徵之於《論語》還是徵之於漢代《詩》學闡釋,無不契合。
徵之於《論語》,我們可以用孔子與子夏論《詩》作為例證。子夏問女子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義,孔子答以“繪事後素”,而由此子夏明白了相比於忠信之質,“禮”則相對為“後”的人生哲理,故孔子許以“可以言詩”,且稱自己受到了啟發。整個討論《詩》的過程既有引譬連類,也有感發志意之倫理功用。但獨獨没有關於女子美貌的討論,比如何謂巧笑,何以能倩;又何謂美目,何以能盼。
徵之於漢代《詩》學闡釋,我们以《毛詩》為例。《毛詩》是唯一完整保留下來的漢代《詩》學闡釋著作,我們可以通過它來討論漢代《詩》學對《詩》中鳥獸草木蟲魚的解釋。事實上,我們在《毛詩》的解釋中看不到他對鳥獸草木蟲魚的具體描述性解釋,只有大概的一個分類,比如《邶風·簡兮》之“山有榛,隰有苓”,毛傳:“榛,木名。”又曰:“苓,大苦。”此外諸如“草名”、“菜名”,大抵皆從分類學角度予以解釋。然毛公注《詩》獨標興體,多數情況下是“興+類名”的方式,如《唐風·椒聊》“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毛傳:“興也。椒聊,椒也。”有時乾脆就不對鳥獸草木之名作解釋,而直接標明“興”。據此我們可以認為毛傳最為關注的是“興”或物的興義,意在告訴讀者讀詩之關鍵。而所謂的“興”義都超越物本身的道德倫理意義,如雎鳩,毛傳:“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别。”依據毛傳,你並不能了解雎鳩到底是怎樣的一種鳥。因為毛傳並不關心這一點,它只想告訴你這是一種“摯而有别”的道德之鳥。但到了陸璣的《草木疏》,這一切都發生了變化,《詩經》中的鳥獸草木蟲魚等生物學意義上的動物和植物都展示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我們稱之為“物變”。具體地説,《草木疏》也有可能會關注到物的道德意義,但這絶不是它的重心,它的重心在於更清楚地説明這是一種什麽樣的物,以及它的實際價值功能,比如可以治療什麽樣的病或怎麽吃。
我們以蟬為例加以説明。中國人對蟬認識得很早,紅山文化遺址中就發現了玉蟬,青銅紋飾中也有蟬形紋飾。《詩經》中也有一些詩篇提到了蟬,如《七月》之“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小弁》之“菀彼柳斯,鳴蜩嘒嘒”,《蕩》之“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等。但毛傳對蟬的解釋並不在於蟬的本身,只是蜩、螗、蟬在稱名上互訓,而不作其他解釋。相對來説,對於蟬的興或比的意義更加關注,如《小弁》之“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毛傳曰:“蜩,蟬也。”鄭玄在毛傳的基礎上作了發揮性闡釋,曰:“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聯繫《毛詩序》對《小弁》詩義的解釋,曰“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則“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正以“大者無所不容”反諷“王總四海之富,據天下之廣,宜容太子,而不能容之,至使放逐”,從而提升了《小弁》之詩的道德鏡鑒意義。而到了陸璣的《草木疏》,蟬的意義或形象顯然發生了變化。其曰:“鳴蜩,蟬也。宋、衛謂之蜩,陳、鄭云蜋,海、岱之間謂之蟬。蟬,通語也。”又曰:“螗,蟬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文、清、廉、儉、信。一名蝘虭,一名虭蟟。青、徐謂之螇螰,楚人謂之蟪蛄,秦、燕謂之蛥蚗,或名之蜒。”(“如蜩如螗”條)又《草木疏》疏“蜉蝣”曰:“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蜉蝣之羽”條)故《草木疏》原本也當有關於吃蟬的記載。
首先我們可以看出,《草木疏》對物的異方俗名很感興趣,往往採取排比的方式,把一種物的所有不同稱謂告訴讀者。事實上,比它更早的是《方言》。我們同樣以蟬為例,《方言》:“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陳、鄭之間謂之蜋蜩,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䗁。其大者謂之蟧,或謂之蝒馬;其小者謂之麥蚻,有文者謂之蜻蜻,其鴜蜻謂之尐,一大而黑者謂之䗃,黑而赤者謂之蜺。蜩蟧謂之蜩。謂之寒蜩,寒蜩,瘖蜩也。”①華學誠:《揚雄方言校釋匯證》,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713頁。《草木疏》與《方言》相類。探討《草木疏》對異方俗名如此感興趣的原因,包括後來郭璞的《爾雅注》,我們認為和經學版圖的變化有關。早期某經的傳授基本上限於一地,以《詩》為例,《魯詩》的開山祖申培是魯人,《齊詩》的轅固生是齊人,《韓詩》的韓嬰是燕人,《毛詩》的毛公是趙人。根據《史記·儒林列傳》和《漢書·儒林傳》的記載,這些《詩》家起始或居家教授,或多授同國同郡。他們的弟子通常與經師有地緣方面的關係,如申公早期的著名弟子或為魯人,或是魯附近的人,如鄒、碭、蘭陵等地①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122頁。。而轅固的弟子皆為齊人,《史記·儒林列傳》記載“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②司馬遷:《史記》,第3124頁。。同樣,韓嬰的弟子皆燕趙間人,“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③司馬遷:《史記》,第3124頁。。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史書記載他的學生只提到了貫長卿,貫長卿應該是河間國人④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3614頁。。當某經附於某經師而流傳於某地時,它的經義訓釋尤其是鳥獸草木蟲魚之俗名稱謂會帶有地域特徵,如《詩經·葛覃》之“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其鳴喈喈”,毛傳曰:“黃鳥,摶黍也。”而“摶黍”只是齊地對黃鳥的稱名,毛傳反映的只是齊地《詩》學闡釋的背景和傳統。這樣的例子在《詩》學訓詁中並非特例,而隨著人們腳步的移動和眼界的擴大,經學的區域性小傳統正逐步向更大範圍的“天下”傳統轉變。也就是説,不管是立於學官的還是没有被立於學官的,隨著交通的發達,交流程度的加深,原本在小範圍流傳的經義闡釋傳統越來越不能適應經學傳播範圍擴大之後的格局,因而需要增加異方俗名以滿足更為複雜的地域背景經學傳播的需求。上引《毛詩》釋“黃鳥”只提到它的齊地稱謂“摶黍”,而《草木疏》則曰:“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也。幽州人謂之黃鶯,或謂之黃鳥。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關西謂之黃鳥。”(“黃鳥于飛”條)“摶黍”只是稱謂之一。而異方俗名正是地位提升,立於學官之後,《毛詩》面對不同地域的經學弟子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其次,對物的觀察趨於細節化和具體化。我們同樣以蟬為例,毛傳將蟬、螗、蜩互訓,並不在意細節。而《草木疏》在吸收《方言》關於蟬的異方俗名内容的同時,也採納了一些細節化描述,比如蟬、螗、蜩三者之間的區别,比如相較於作為通名的蟬,專名的“螗”是“大而黑色者”。作為經驗,我們都知道,人類在童年時期對物本身的興趣更大,觀察也更加仔細,解釋的因素也更加多樣化。蟬作為一種鳴蟲,它是怎麽發聲的,人們自然有興趣了解,就好比《七月》之“斯螽動股”和“莎鷄振羽”。但漢代的《詩經》闡釋學有没有關於蟬如何鳴叫的訓釋,文獻闕佚,我們不得而知。原本《草木疏》有没有,我們也不清楚。但許慎的《説文解字》確實提到了這一點,其曰:“蟬,以旁鳴者。从虫單聲。”①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281頁。所謂“以旁鳴”描述的是蟬的發音部位,此特徵《周禮》已言之,故賈公彦曰:“蟬鳴在脅。”②賈公彦:《周禮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925頁。
人們從來都不缺乏對物的瞭解欲望和觀察物的耐心,只是在傳統的經典釋義傳統中,這樣的内容没有屬於它的位置。就《詩》而言,它與《爾雅》一樣,尊奉的均是源自先秦以來的經義闡釋傳統。一旦人們的興趣發生了轉變,微言大義之外,對物本身也產生了追問的興趣,物本身自然就會進入人們的視線。限於資料,我們没有辦法考述漢代的經學著述從什麽時候開始關注物本身,因為絶大部分著述和著述的絶大部分都已經亡佚了。但是《爾雅》所代表的經學詮釋傳統似乎受到了挑戰,一種重視物本身的新的訓詁理念正衝擊著舊傳統,比如《方言》、《説文解字》等等。《方言》的重點還主要在異方俗名,而《説文解字》確實已經表現出對物的濃厚興趣,其涉及鳥獸草木蟲魚的文字,有許多關於物形態及其功用的内容。如“貂,鼠屬,大而黃黑,出胡丁零國”③許慎:《説文解字》,第198頁。;“蚺,大蛇,可食”④許慎:《説文解字》,第278頁。等等。而漢末的另一部訓詁學著作《釋名》則直接把鳥獸草木蟲魚的解釋和博物學觀念聯繫了起來。大家知道,劉熙言作《釋名》目的在於“名之於實,各有義類”,而“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所以他作《釋名》二十七篇只釋名物制度,不涉及鳥獸草木蟲魚,鳥獸等則“欲智者以類求之博物君子”⑤劉熙:《釋名·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與之相類,我們在存世的漢代經學之外的訓詁學著作中,可以找到大量涉及博物學的例子,比如《淮南子》的許慎注、高誘注。兹舉幾例。許慎注,《文選·辯命論》“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李善注:“《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蛾。’”⑥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52頁。檢今本《淮南子·道應訓》有“朝菌不知晦朔”句,許慎注:“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如蠶蛾。一名孽母,海南謂之蟲邪。”①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410頁。二者幾乎相同。至於“朝菌”、“朝秀”之别,則當為後人依據今本《莊子》文所誤改。當然,重要的是,許慎注“朝秀”詳其生死之期及生活情狀、異方俗名,完全是博物學的視角,與《草木疏》相類。《淮南子·説林訓》“蝯狖之捷來乍”,高誘注:“蝯,狖屬,仰鼻而長尾。”②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第566頁。假使在毛傳,其極有可能注曰“蝯,狖屬”,就好比注《角弓》“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曰:“猱,猨屬。”③孔穎達:《毛詩正義》,第491頁。《時則訓》曰仲夏“半夏生,木堇榮”,高誘注:“半夏,藥草也。木堇,朝榮莫落,樹高五六尺,其葉與安石榴相似也。是月生榮華,可用作烝也。雜家謂之朝生,一名蕣,《詩》云‘顔如舜華’也。”④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第170頁。“顔如舜華”出《詩·鄭風·有女同車》,毛傳注以“舜,木槿也”,别無多言。而高注指出其花期、葉型,作用以及雜家(土方)俗名,還稱引了《詩》,可謂非常詳盡。《草木疏》曰:“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曰椵,一名曰及。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莫落者是也。五月始生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顔如舜華”條)與高誘注相類。總之上述許、高注釋《淮南子》都具有濃厚的博物學傾向,注重對物的細節觀察和比較,如“狀如蠶蛾”、“葉與安石榴相似”等。
最後,我們看人們對物之功用及價值的重視,這方面主要涉及日常生活所需,尤其是飲食和醫藥。在中國人的觀念世界中,飲食從來都是人與生俱來的最重要事情,此所謂“食色,性也”。並且在中國人看來,飲食不是簡單的吃吃喝喝的問題,而是一個龐大的知識系統。飲食不僅關乎營養,也可用以治病。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無妄》之九五曰:“無妄有疾,勿藥有菜。”而馬王堆帛書《周易》及今傳本《周易》都作“無望之疾,勿藥有喜”。菜是可以吃的草,“有菜”就是強調飲食的治療功效。同樣,馬王堆帛書本《周易》以及傳世文獻作“有喜”,這裏的“喜”當讀為“饎”,解為酒食,也關乎飲食,和“菜”義類同。不僅如此,飲食藥用也關乎此生與來世。在已發掘的墓葬中,醫書、藥方、養生方並非鮮見,包括藥物以及養生性質的食物也很常見。比如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醫書藥方有《五十二病方》、《養生方》、《雜療方》等;出土的藥物包括三大類,即植物類、動物類和礦物類,如大棗、桂皮、花椒、牡蠣和硃砂等①何介鈞主編:《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280頁。。就傳世文獻看,我們的古人對動植物的食用價值、藥用價值不僅很早就知道,並且有很深入的了解,如《黃帝本草經》。同樣在許慎《説文解字》、劉熙《釋名》這種帶有很強烈的輔經旨趣的書中,也有很多這方面的記載。《説文》:“蒲,水艸也,可以作席。”“芺,艸也,味苦,江南食之,下氣。”②許慎:《説文解字》,第17、18頁。又《釋名·飲食》解釋食物得名或食物做法,如“酪,澤也,乳汁所作,使人肥澤也”,“血䐄,以血作之,增有酢豉之味,使甚苦,以消酒也”③劉熙:《釋名》,第62、64頁。。
儘管就漢代經學闡釋而言,其有著穩定而強大的釋義傳統,但我們仍然可以強烈地感受到東漢中期經學釋義的轉向。就《詩》而言,鄭玄雖然緊承毛傳釋義,尤其是他對“興”的解釋。但鄭箋已然有了日常生活化的色彩,尤其是人情的體驗。這樣的例證比比皆是,如《陳風·澤陂》:“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毛傳曰“興也。陂,澤障也。荷,芙蕖也”,不作過多的解釋。而鄭玄則將蒲與荷分釋為男女容貌,所謂“蒲之草甚柔滑,荷之莖極佼好。女悦男云:汝之體性滑利如蒲然。男悦女云:汝之形容佼大如荷然。聚會之時,相悦如是”。毛傳只作道德釋義,以“傷之如何”為詩人指斥之語,故曰“傷無禮也”。而鄭玄雖以蒲、荷興男女,但也有“蒲,柔滑之物。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之物性的依據及人情的體驗,故訓“傷”為“思”,有“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之細膩體貼④孔穎達:《毛詩正義》,第379頁。。後來孫毓作《毛詩異同評》,認為箋義為長⑤孔穎達:《毛詩正義》,第379頁。。其言固有理,卻也正是魏晉《詩》學之風尚。
依據文獻的記載,我們知道,漢人的腳步已經邁向了遠方,也有大量的異域奇珍進入了傳統的“中國”。而此時佛教已經傳入,文化的碰撞和交流越來越頻繁,這些都促使人們要睜大眼睛去打量這個日趨擴大也日漸陌生的世界。與此同時,這種個人化或日常生活化傾向,使得經學闡釋者的目光慢慢下移,也慢慢擴大,以往不為人所關注的内容漸漸納入經學闡釋者的視野,包括寫新鮮的事物。經學的説解開始吸納各種知識解讀經書中的物,表現出博物學的傾向和日常生活化的旨趣。這應該是陸璣《草木疏》這樣的解經著述得以出現的重要誘因,甚至在陸璣之前,這樣的解經方法已經出現。建安七子之一的劉禎曾作《毛詩義問》,這是一種全新的注釋體例,它不是通解著作,只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發問。《毛詩義問》已經亡佚,尚有隻言片語保存在古代類書或注釋之書中,如“郁,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①孔穎達:《毛詩正義》,第391頁。,“蟏蛸,長足蜘蛛也”等等②李昉:《太平御覽》,第4207頁。。儘管如此,我們仍不難判斷,劉禎《毛詩義問》和陸璣《草木疏》原來是一類的著作。再結合此前與經學釋義密切相關的訓詁學著作《説文解字》、《釋名》等,我們可以説漢末魏晉的《詩經》學或者整個經學出現了一些新的趨勢。一方面《詩經》中包含了草木、鳥獸、蟲魚,以及天文、地理、宫室、器具、服飾、車馬、地名、職官等包羅萬象的名物,因為政治變遷、時間輪轉、方言各異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後人對其進行理解研習過程中的“今昔異名,年代迢遥,傳疑彌甚”③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第120頁。的局面,因而解讀《詩經》需要針對名物方面的專門研究。另一方面,兩漢以來一系列訓詁學著作,如《方言》、《説文》、《釋名》等相關的問世,以及類似吴普《本草》等本草學著作的興起,為《草木疏》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知識基礎。當然更重要的是,經學注疏自身的也在悄悄發生變化,當面對經學中的動植物身上附著高深義理時候,人們也想知其所以然,這是一種什麽樣的物竟能承擔起如此重大的責任,人們對還原物有著極大的興趣。隨之而來的便是經學注釋日趨生活化和個人化,人們重視實物、實地考證、以博涉多通為尚。在經典的訓詁過程中重視名物的客觀屬性及其相關的風土人情或奇聞趣事,在傳統的微言大義闡釋傳統之外,開闢新的真知識領域。基於上述種種,《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在魏晉時代應運而生④郝桂敏在《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有關問題研究》一文中還提到了東吴統治者對古文經學的重視與三國時期儒學衰微兩點原因。。至於為何是出自魏晉時期的吴國陸璣之手,又應當分作兩層考慮:其一,“吴國人”,之所以是魏晉時期的吴國人,夏緯瑛先生從地域分佈角度略有提及,他認為“三國時吴國的疆域已達到我國亞熱帶地區,其地之動植物資源當已有地志之類的著作詳加記載,《草木疏》中著重描述各種動植物的經濟用途,似與此類著作不無關係”①夏緯瑛:《〈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的作者——陸機》,載於《自然科學史研究》1982年第2期,第178頁。,此應當是指兩漢以來興起的地記、圖經之學,還包括異物志、水道記、山水記、風俗記等,代表作是三國吴人徐整纂修的《豫章舊志》;其二,“陸璣”,之所以是吴國人中的陸璣此人,應當同他的家學、師學、交游等有關,可惜的是關於陸璣的生平資料實在太少,不能進一步詳細考察,但通過《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中的内容可以確定的一點是,陸璣應當是親身游歷了大量地區尤其是黃河流域,並仔細考察了各地的動植物及與之相關的生產知識,否則難成此書;雖然以上兩點尚不足以充分説明《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成書於陸璣之手的必然性,但誕生於魏晉時期確是大勢所趨。
魏晉時期經學注疏的知識化或博物化傾向對後世的經學闡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就《草木疏》而言,它給《詩經》學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首先,單純作為一部博物學著作,書中較為詳細的記載了大量動植物的形態特徵、生長習性、地域分佈及使用價值,為後世關於本草、農業、氣候環境、生態、地理等的研究及其著作如《齊民要術》等,提供了許多珍貴的資料;同時它還反映了魏晉時期的部分生產狀況和風俗民情,又是很好的關於古代文化史、社會史、地方史研究的重要輔助性資源。當然我們也可以從文學角度去解讀陸璣《草木疏》身上的文學價值。它和漢代以來的賦體文學創作理念、創作方法,尤其是詠物賦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雙方形成很好的互動,即它們都是用“觀”的方式對待物本身,然後逐一鋪排。與此同時,《草木疏》本身也是很有趣的文學文本,張華的《博物志》和王嘉的《拾遺記》都直接或間接從《草木疏》中取材,如上引《草木疏》中對鸛鳥的記載,大致相同的内容也見諸《拾遺記》。
其次,是作為一部注解《詩經》的訓詁典籍,它開創了《詩經》名物訓詁這一新的學術傳統,如隋唐年間有現已亡佚的《毛詩草蟲經》和《毛詩草木蟲魚圖》二書,重義理輕考據的宋代有蔡卞《毛詩名物解》、王應麟《詩地理考》、陸佃《説魚》《説木》和楊泰之《詩名物篇》等書篇傳世,元代許謙受朱熹影響著有《詩集傳名物鈔》,明代有馮應京的《六家詩名物疏》和毛晉的《毛詩陸疏廣要》等,此類著作在重考據名物而輕義理的清代更是數不勝數、蔚為大觀,代表作品如毛奇齡《續詩傳鳥名》、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姚炳的《詩識名解》、顧棟高的《毛詩類釋》、牟應震《毛詩名物考》、陳奂《毛詩九穀考》、俞樾《詩名物證古》再到近代的陸文郁《詩草木今釋》等等,此外尚有徐鼎《毛詩名物圖説》及天文、地理、禮制等其他方面的考訂著作,以及焦循、趙佑、丁晏、羅振玉等直接針對《草木疏》的校疏。總之,《草木疏》的出現為卷帙浩繁的《詩經》學研究開闢了一條别具特色的學術分支,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後人更好理解《詩經》的需求,同時這種名物研究和其他《詩經》研究方向如音讀、詩譜、文學品鑒等一起,反映了魏晉時期人們精神自由開放從而另闢蹊徑,突破兩漢以來經學一統、重政治倫理比附習氣的《詩經》研究,開啟了更廣泛的《詩經》學術研究新傾向,這些創新和解放無疑為後來的《詩經》學乃至整個經學研究注入了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