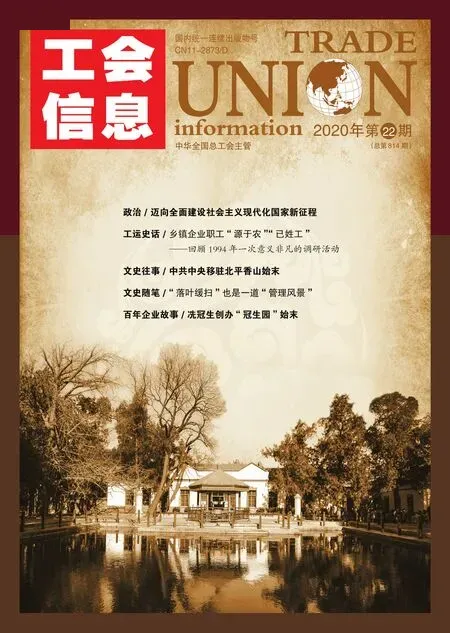臧克家:“生活是诗的土壤”
2020-02-28冯晓蔚
◆文/冯晓蔚
1930年,臧克家考入了国立青岛大学(后改名为山东大学)。在这之前,他经历了革命失败的悲愤痛苦,逃亡生活的艰辛磨难,更加了解了人生道路的坎坷曲折。因此,在入学考试的作文《杂感》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
而他的恩师,著名诗人闻一多,正是从这一节《杂感》中认识了臧克家。在初学新诗时,臧克家只知道闻一多的名字,并没有读过他的作品。而在臧克家授业于他之后,因识其人,也就渴望读其诗了。臧克家向他借来了《死水》,一读就入了迷,佩服得五体投地,大有对于一位令人心折的人物相见恨晚的心情。《死水》读了一遍又一遍,有些诗篇不是一下子就懂透了的,它需要咀嚼、琢磨、品味,一经完全懂了,则好似看名山的奇峰,云雾消尽,其悦目赏心的容颜便显现在眼前,而且越看越美,永远在心中保持它动人的青颜。
闻一多的诗,字里行间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苦难人民的深切同情。读着它,仿佛能看见一颗热爱祖国、热爱土地、热爱人民、热爱自然的炽烈的血心。
闻一多的诗同他的为人一样严谨。他的诗,在技巧的磨炼上所下的功夫,所付出的心血,足以使一个初学者消解浮浅的“自是”心,拉回乱放的野马,觉得新诗不是草率可以成功的。因此,读了他的诗,臧克家把自己的一本过去的习作交给了火。
读了《死水》,臧克家觉得,过去自己像个小孩子,酸甜苦辣都吃,也都以为可口,今天,自己才有了一个自己的胃口。
他向闻一多先生和他的诗学习着怎样想象,怎样造句,怎样去安放一个字。在以前,臧克家不知道什么叫想象,知道了,也不会用它。抓住第一个跑到自己心上的它的浮影,便宝贝似的不放松,把它用到自己的比喻,隐喻,形象上去了。而不知道打开心门,让千千万万个想象飞进来。之后,苦心地比较着好坏,像一个吝啬的女人和一个小气的小贩把一个铜板作为这场买卖成败的关键那样认真地计较着。然后,用无情的手把所有的想象都赶出去,只留下最后的一个。因为,没有插着翅膀的想象,会永远把你的诗拖累在平庸的地上。
臧克家曾说:“下字也难。下一个字像下一个棋子一样,一个字有一个字的用处,决不能粗心地闭着眼睛随意安置。敲好了它的声音,配好了它的颜色,审好了它的意义,给它找一个只有它才适宜的位置把它安放下,安放好,安放牢,任谁看了只能赞叹却不能给它掉换。佛罗贝尔教莫泊桑的‘一字说’,每一个有志于写诗的青年都不应该看轻它。”这时候,臧克家的创作兴致很高,用心也很苦!每得一诗,便跑到闻一多的家中去。闻先生住在大学路的一座红楼上,门前有一排绿柳。他每次走进闻先生的屋子,都有一种严肃的感觉,也许是闻一多那四壁的图书和他那伏案的神情使然吧。这时候,闻一多正在致力于唐诗,长方大本子一个又一个,每个本子上,写得密密麻麻,看了叫人吃惊。然而一旦开始谈诗,空气便完全不同了,他马上从一个学者变成了一个诗人。臧克家吸着闻一多递给他的“红锡包”(他总是吸红锡包烟),两人这时仿佛不再是在一间书房里了,他们像师生,又像朋友一样地交谈着。闻一多指点着臧克家这篇诗的优点、缺点,哪个想象很聪明,哪些字下得太嫩。同时,又到书架上抓过一本西洋诗打开,找出同臧克家的想象字句差不多的想象字句来比较着看。有时,一个句子,一篇诗,得到了闻一多的心,闻一多古井似的心上(他久已把诗心交给一堆故纸了)立刻泛起澎湃的热流,眉飞色舞地读着它,同时,把一个几乎是过分的夸奖给了臧克家。闻一多,每每在某些诗句上划了红圈,那些诗句恰是臧克家最得意的,他俩的眼睛和心全被诗连在一起了。
有一个暑假,臧克家把《神女》这一篇诗的底稿寄给闻一多看了,其实是在做一个试验,其中有一个句子臧克家最喜欢。闻一多的复信来了,臧克家心上的那个句子:“记忆从心头一齐亮起”,果然单独地得了那个红圈。臧克家不禁高兴得狂跳起来。
在这时,王统照也给了臧克家很大的关心和帮助。有了新作,臧克家常常跑到观海二路13号---他的寓所里去,用热情激动的调子背诵给统照先生听。王统照给了臧克家许多有益的意见,当然还有鼓励。王统照告诫臧克家,写诗,不要趋向尖巧,而需要更深进,更远大,更朴厚。
臧克家拼命地写诗,追师,他的生命就是诗。推开了人生的庸俗,拒绝了世俗的快乐,他宁愿吃苦。看破了世事人情,臧克家才觉得事业是唯一“不空”的东西,它是一支精神的火炬,虽在千百年后也可以发热发光。一切皆朽,唯真理与事业同存。诗,就是臧克家以生命全力去倾注的唯一事业!
臧克家的每一篇诗,都是经验的结晶,都是在不吐不快的情形下一字字、一句句地磨出来的,压榨出来的。他觉得仿佛天下的苦难都集中于一身,肚子里装满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像雍塞的淤泥。被压迫、被侮辱地生活在最底层的形形色色的人们——特别是贫苦农民的形象,乡村的大自然风光,地主官僚的丑态,一齐在臧克家心中鲜亮了起来,用它们的颜色,它们的声音,它们要求表现的希望打动他,鼓舞他,刺激他,使他把曾经看到过的,感受过的,统统化作诗。诗,可以兴,可以怨。诗是冲破郁塞的一道激流,诗是心头火焰的一个喷射口。
这一时期,臧克家写了《老哥哥》《洋车夫》《难民》《贩鱼郎》《神女》《炭鬼》……这黑暗角落里的零零星星。臧克家正眼在瞪着人生,然而没抓住大处、要害处,只抓住了这一星点。虽是这样,然而,在象征诗风吹得乏力的时候,这也能如照耀现实生活的一盏小灯,给了黑暗中的人们一点光亮,一股生活的力。
1933 年,卞之琳在北平自费印了他的《三秋草》,他鼓励臧克家印一本诗集,臧克家便把新旧作品挑选了一下寄给了卞之琳,取了其中一篇诗的名字《烙印》作为诗集的名字。这时候,闻一多已经到“清华”去了。经过了他们的一番精选,闻先生又写了序言,就付印了。式样、印刷等,一切全托给了卞之琳。闻一多、王统照及另一位朋友慷慨解囊,一次印了400本,臧克家的第一本诗集——《烙印》,在众人的鼎力相助下终于问世了。
《烙印》出版不久,茅盾、老舍、韩侍桁诸先生在《文学》《现代》等杂志上写了评介文章,给了臧克家很大的鼓舞力量。于是,他这个为新诗呕心沥血多年的文艺学徒,以“青年诗人”的头衔,与艾芜、沙汀等另外5人成了“1933年文坛上的新人”。
这样,臧克家在青岛找到了“自己的诗”——也就是说,臧克家多年的血汗苦心终于铸造出一个结果——“风格”。战斗的生活,痛苦的磨难,叫臧克家用一双最严肃的眼睛去看人生,并且以敏感的神经去感受生活,以强烈的火一样的热情去拥抱生活,以正义的界线去界开黑暗与光明,真理与罪恶。总之,这时候,臧克家的思想和人生观已经找到了自己固定的位置,臧克家已经定了型。因而,臧克家才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臧克家找到了“自己的诗”,臧克家走了新诗的道路。“这得要感谢家庭的熏陶、朋友的帮助、恩师的指点。然而,更重要的,这得要感谢生活。因为,生活,是诗的土壤。”这就是臧克家如是说。
高唱战歌——诗文里奔腾爱国血液
1937年,日寇入侵。臧克家望着国土一寸寸地沦陷,悲痛万分。抗战爆发后,他奔向硝烟弥漫的战场,将烈火雄心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臧克家在《血的春天》中痛斥敌人——
抗战!抗战!将敌人的脚跟,从我们的国土上斩断。诗人们呵!请放开你们的喉咙,除了高唱战歌,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
第二年4月台儿庄战役打响,战事紧张惨烈。臧克家一身戎装,深入战地进行采访。冒着日寇敌机轰炸的危险,不怕死的他3次来到战区的前线。他看到了敌寇的凶残,看到了中国人民在流血、牺牲,更看到了中国军人高昂的士气和意志……经过7天夜以继日的不懈创作,《津浦北线血战记》这部长篇通讯报告集完成了,它以铁的事实和激昂悲壮的爱国之情,向世人最迅速最及时地揭示了中华民族浴血抗战的战地实录和与敌寇不共戴天的民族气概和精神。

臧克家采访台儿庄战役后去郑州
臧克家跟随着部队,在前线一待就是5年。为了保家卫国抵御外侵,他怀着始终不变的战士信念和责任感,用自己的作品,尽了一份战士应尽的责任。在5年的战地生活中,他写下了《泥沼集》《走向火线》《随枣行》《淮上三千里》等一篇篇著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解放战争时期,臧克家多次参加“呼吁停战、实现和平”签名等进步活动,在重庆,曾应邀出席毛泽东同志在张治中寓所举行的文化界人士座谈会。在上海,他主编了《侨声报》文艺副刊《星河》、《学诗》和《创造诗丛》、《文讯》月刊等书刊,团结了大批进步作家;激愤于政治的黑暗腐败,他创作了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和政治讽刺诗,出版了《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冬天》等诗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8年12月,由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被迫潜往香港。
1949年3月,臧克家由中共党组织安排来到北平。5月在《人民日报》发表组诗《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表达了他到解放区后的喜悦心情。
全国解放后,臧克家继续坚守在文学阵地上,为了向广大读者介绍中国优秀古典文学和其中的名篇佳句,讲述自己对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学传统的体会感悟,臧克家陆续写了许多有关古典诗文的赏析文章,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后来这些文章结集为《臧克家古典诗文欣赏集》出版。

1960 年10月臧克家(右)与徐迟(中)、葛洛(左)商谈《诗刊》工作
1949年7月,臧克家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1956年,臧克家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1957年至1965年臧克家任《诗刊》主编。经他联系,由《诗刊》创刊号首次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十八首,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期间,他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组织领导工作,在《诗刊》的创刊与发展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繁荣诗歌创作、加强诗歌队伍建设中,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同时满怀对祖国、对党、对人民的无限热爱之情,笔耕不辍,勤奋创作,以热情、多产的诗人形象活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上,迎来了他创作的又一高峰,相继出版了《臧克家诗选》《凯旋》等诗集和长诗《李大钊》。其中,《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毛主席向着黄河笑》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多次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1957年,他和周振甫合著的《毛主席诗词讲解》,对毛泽东诗词的传播和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1966年,臧克家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1972年,臧克家回到北京。1976年1月《诗刊》复刊,臧克家担任顾问兼编委。年逾古稀的臧克家文思泉涌,又迎来了创作的春天。他把心底的颂歌唱给了社会主义新时期,出版了《忆向阳》《落照红》《臧克家旧体诗稿》等诗集;《怀人集》《诗与生活》等散文集;《学诗断想》《克家论诗》《臧克家古典诗文欣赏集》等论文集。
凝结着他一生汗水和心血的十二卷本《臧克家全集》于2002年12月出版。
自沐朝晖意葱茏,休凭白发便呼翁。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
臧克家一生历经世纪沧桑,锤炼品格心胸,成为一位伟大的时代诗人。2000年1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国诗歌学会授予“世纪诗翁”臧克家“中国诗人奖终身成就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