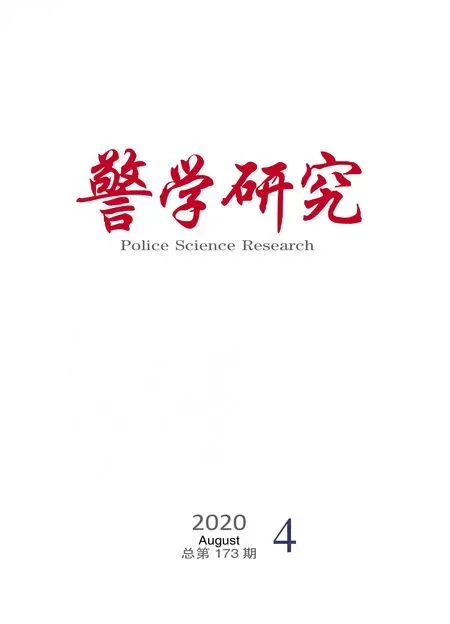保险诈骗罪的适用与刑法干预的边界
——以李某航延险诈骗案为视角
2020-02-28
(同济大学,上海 200092)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6月9日,南京市公安局发消息称,当日南京市鼓楼区警方成功破获一起航班延误险诈骗案。犯罪嫌疑人李某自2015年起,通过虚构自身行程在购买900多次航班延误险后获得超过300万元的理赔金。警方认为,李某“涉嫌在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时,故意捏造根本不存在的被保险对象,骗取保险公司保险金,客观上存在刑法评价中的诈骗行为,同时诈骗金额已达到保险诈骗罪的追诉标准。”6月12日,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再次发出通报,称“李某多次伪造航班延误证明等材料,虚构航班延误事实,骗取巨额保险金。”此案一出,迅速引发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讨论,且各路观点莫衷一是,有认为确属保险诈骗,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者;亦有认为李某行为乃民法规制范围,保险公司当以民事诉讼的形式追回损失者;更有认为李某获得理赔金是“个人能力体现”,无须承担任何责任者。
对案件性质的界定无疑应当基于准确的事实。不过,目前来看,对本案案情的披露主要源于各家新闻报道及微信公众号等,且大多为一些语焉不详的碎片化信息。同时,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负有保密职责,自然难以将案情“大白于天下”。在此,我们提取各家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描述,剔除主观评价部分[1],尽力最大程度地还原案情如下:
1.李某曾从事过航空服务类工作,对航班信息较为了解;2.李某曾花大量时间、精力去网上筛选延误率较高的航班;3.李某手中持有多位不同亲友的护照与身份证信息(借得或瞒用尚未知);4.李某使用上述身份信息多次购买目标航班的大量机票与延误险;5.李某在航班起飞前实时观察天气与航班动态,但并不准备实际乘坐该航班;6.若航班正常起飞没有延误,李某会于起飞前退掉所有购买的机票;7.若航班实际发生延误,李某则会对购买的多份延误险申请理赔,所得理赔金由其一人占有;8.自2015年至今,李某共通过900余次延误险获得超过300万元的理赔金(不排除有些次数不成功)。
而就在此案之前,上海警方刚刚告破一起保险诈骗案。与李某案类似的是,犯罪团伙也是根据已掌握的航班延误信息购买对应航班机票,分别投保多份“航延险”,隐瞒自己不准备实际出行的事实,并使用私刻的航空公司及机场印章,伪造多份航班延误证明分别向各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骗取保险理赔金。近年来连续作案数千起,涉案金额2 000余万元。该案核心问题在于,私刻印章、伪造延误证明属于“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构成保险诈骗罪的五种情形之一,与此案不同的是,李某只是假借他人信息多次购买延误险,并对真实延误的航班申请理赔,是否应当构成保险诈骗罪就值得研究。
二、保险诈骗案的出罪与入罪之辩
自李某航延险诈骗案曝出后,短短一周内,就有数十位理论学者、实务专家对此案进行讨论,但大多以公众号或报刊评论为主,未得详细展开。笔者选取其中二十余篇,对其中观点进行总结、提炼,尝试性地分为入罪派①入罪派主要有:董晓华:《航班延误险诈骗,这次我挺控方》,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ArjBAW3QS316JWhZVPTHsA;郑飞:《恶意利用规则漏洞骗取航班延误险理赔,应构成犯罪》,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qou9OykMFJljQSeKMdRnvw;戴稳胜:《利用航班延误索赔保险金到底构不构成诈骗》,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THvYm6eVvdO57jOz3oxt8A;赵森:《利用航空延误险理赔能不能入罪?》,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xMnpv6oNLCLXGAL2-g2C_A;张召怀:《300万航延险诈骗案:愿赌服输没有错,但关键是“糊牌”了没有?》,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JxigNR3gBg0lsHfiId0yjA;张赛:《900次航班延误获赔300余万元,幸运的“倒霉蛋”为何进了监狱?》,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LWEdUgXBFRoYY6ZIamD1bA;魏远文:《到底是合法利用规则透利,抑或使保险成为博彩的工具?》,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gFOCZu8I—yXJMUIuasSG7w;等等。与出罪派②出罪派主要有:金泽刚:《买飞机延误险被抓:“虚假” 未必是诈骗犯罪》,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 797879;邓学平:《购买航班延误险理赔被抓?这可能真不涉及犯罪》,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r8S—rqnjeGZ6mqUn9kyJEQ;吴伟召:《女子利用航空延误险规则理赔入罪难》,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N2sC1VUDg—Zl2XkmqrjtrA;肖文彬:《利用航班延误获取300万理赔金,构成诈骗犯罪吗?》,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bJSQVgelFtre0N190Hkcsw;金宏伟:《叙说南京女子涉嫌航延险诈骗案》,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Q—fO3D1yVylUWaIZkAgjeg;等等。两方。
在入罪派内,尽管各方均认为李某的行为已达到入罪标准,但在罪名的指向上却有分歧。部分观点与南京警方一致,认为李某涉嫌构成保险诈骗罪,主要理由为:(1)是否实际搭乘航班属于合同的重要事项,而在重要事项上进行欺骗的,会影响对方作出处分的决定,处分财产的行为和欺骗的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2](2)航空旅程延误保险合同明确规定本合同的保险标的是因航空延误对被保险人造成的损失。李某没有乘坐飞机行为,飞机延误不会对她造成损失。所以李某并没有保险标的,签订保险合同完全是虚构了保险标的;[3](3)假如肯定李某赔付行为的正当性,就会使延误险由保险的属性滑向博彩,甚至赌博;[4](4)即便不认可李某有虚构保险标的的行为,在发生航班延误,出现保险事故后,李某将无损失说成有损失的理赔行为,属于对发生的保险事故夸大损失程度,仍然成立保险诈骗罪;[5](5)本案中行为人明显是故意选择回避合法的过程,只追求非法利益的结果,因此她的行为上有选择的可能性,不能够形成刑法上的免责事项。
在入罪派中,还有部分观点认为,李某之行为并不符合《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的保险诈骗罪的五种类型之一,但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保险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存在法律竞合,是诈骗罪的特殊法,优先于诈骗罪适用……显然,李某的行为并不符合保险诈骗罪的五种行为模式,行为也不构成保险诈骗罪,但这并不等于李某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6]“诈骗罪的实行行为主要包括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两种方式,虚构事实显然是一种作为;隐瞒真相,则是指行为人负有告知真相的义务却故意不告知的行为,这显然可以是不作为。关于保证人地位,李某和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后,其作为合同的缔约方,具有保证人的地位,该保险合同可以成为其不作为的欺骗的作为义务来源。故而李某的行为可能构成不作为的诈骗罪。”[7]同时,也有少数观点认为李某可能涉嫌构成盗用身份证件、非法经营等其他罪名。[8]
不过,此案一出,为李某辩护的声音亦有不少。总结来看,出罪的理由主要基于以下几点:(1)航空延误险作为财产险,保险人承保的对象是本次航班行程准时性或者准时性承诺,这一财产性利益,不可能是被保险人本次行程有无乘机,有无实际损失的客观行为。不管乘机与否,只要购买行为一旦完成,保险合同成立,财产险之被保险对象的利益便客观存在,不存在捏造“保险对象”;[9](2)保险诈骗罪构成要件行为的核心是:虚构保险标的或者编造、制造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在本案中,保险标的是航班是否延误,保险事故是航班延误。而李某并不能控制和左右航班是否延误,因此不可能虚构保险标的、制造保险事故;[10](3)李某确实购买了机票和延误险,航班也确实延误了,保险公司的理赔也是依据其合同约定而进行的,因而也没有基于刑法意义上的错误认识而处分财物;[11](4)李某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的确想占有保险公司的保险金,但渠道是通过国家立法确认的保险制度、保险合同、保险事故(本案中指航班延误的事实)等一系列合法手段获取财产;[12](5)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推算出这个航班延误的概率,这种“意外要素”正是保险合同的本质特征所在。李某购买保险意图获赔的行为,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果博错了的话,她自己投进去的保费全部打水漂。这也是不同于诈骗的本质所在。[13]质言之,在客观方面,李某只是根据公开的气象和航班资料来研判飞机是否会延误,没有虚构保险标的、制造保险事故;在主观方面,李某是想通过合法签订的合同获取理赔金,充其量只是想“钻空子”,而不是“非法占有”目的。
然而,在出罪派内部,虽均认为李某不构成犯罪,但对于应否承担其他责任或承担何种责任仍未统一。其中,大多观点认为,应当厘清“欺骗行为”与“诈骗行为”,李某案的本质是对合同效力的民事判断,不应上升到刑事层面。保险公司如认为理赔有问题,可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合同无效,让李某返还所得的保险理赔金。也有学者从行政法的角度,考虑对李某适用行政处罚,以及从行业的角度,比如说航空公司可以把李某列为黑名单,保险公司也可以把李某列为黑名单,不再卖机票或保险给李某。[14]换言之,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活动,一般不需要国家“拔刀相助”,而由其自身寻求权利救济或相应的惩戒。当然,也有少数观点认为,李某的行为至多受到道德的非议,尚不足以上升到法律层面,因而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可见,即便对于公安机关的官方通报,质疑声同样不断。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热点案件的讨论,不是对司法公信的质疑,而是法治进步的体现,近年来从山东于欢案到福建赵宇案,都是最好的例证。尤其在刑事案件中,刑罚会留下永恒的烙印,每一次定罪、量刑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家庭的命运。对罪与非罪的界定,我们需要更为细致地查明,更为严谨地把握。因此,在李某航延险诈骗案中,我们不能简单的因为营利金额巨大就按图索骥,草草定性。对保险诈骗罪的认定,必须回归到法条的具体规定之中,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要求。
三、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一)、(二)项的理解与判断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认为李某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观点值得商榷。众所周知,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帝王原则”。从合同的角度看,双方当事人应当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应当真实,既不违反法律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反公序良俗。再具体到保险业,其适用的不仅是诚信原则,而且是最大诚信原则。“对于保险人,应以最大的诚信进行产品的设计,规则的制定,提示和说明,并及时赔付;对于投保人,在不同类别的保险中,应承担如实告知自身情况(人身保险),财产状况(财产保险),责任状况(责任保险),按规则投保并申请赔付等义务。”[15]在航延险中,是否有真实出行意愿、是否会亲自乘坐航班等,应当是诚信的内容之一。换言之,即便李某没有瞒用他人身份证,没有伪造天气状况与延误信息,其行为也难以接受诚实信用原则的检验。因此,在民法的角度,至少存在合同无效的余地,李某似乎难逃民事责任的追究。
问题在于,民事优先,刑事是否就会紧随其后呢?与民法中的欺骗不同的是,刑法中诈骗行为的界定更为严苛。通说认为,诈骗类犯罪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产生(或继续维持)错误认识——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害。[16]其中,刑法中的“欺骗”是一种使对方陷入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的行为。虽然欺骗的手段、方式没有限制,但如果欺骗行为没有左右对方处分财产的决定,就不是刑法所规制的“欺骗”。体现在保险诈骗中,《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已经将“欺骗”限定在以下五种方式:(1)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2)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3)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4)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5)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
而回到李某一案中,由于航班确实发生延误,保险事故真实存在,加之航延险不涉及人身伤亡条款,故而上述(3)(4)(5)项可直接排除。换言之,李某是否构成保险诈骗罪,考察的重点应当为李某是否虚构保险标的,或是否夸大了损失程度。
(一)虚构保险标的的判断
保险犯罪的法定犯本质决定了其具有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双重违法性特征。若构成保险犯罪,须首先违反了保险行政法律规范。[17]因此,保险诈骗罪的认定,始终离不开《保险法》规定的保险原理与规范。
有学者认为,航延险看似是财产保险,但“时间延误”并不可被精确地估量,有违财产保险的“损失补偿”原则,不算是财产损失,故而未必属于《保险法》中的“保险”,实际上只是一种保险公司基于大数定律研究出来了一种与投保人的对赌产品,因此,“愿赌服输”,不可能对李某追究刑事责任。[18]
我们认为,虽然航延险存在一定的对赌色彩,但仍未脱离“保险”的范畴。《保险法》第12条明确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其中,“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①因航延险不涉及人的寿命和身体,明显不属于人身保险的范围,故本文在讨论时会将人身保险的内容予以剔除。可以发现,《保险法》在“财产”后特地加了“及其有关利益”。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财产”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除传统货币等实物财产外,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也慢慢被纳入其中。航延险是伴随着交通不断发展而来的新产品,我们不能因为时间延误带来的财产损失难以量化就不予承认,如此无异于因噎废食。因此,航延险应当属于财产保险的一种,受保险行政法律规范的调整。
问题在于,“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具体应作何理解呢?我们认为,保险标的即为保险对象,也就是受保险而保障的对象。保险标的应当具备“三性”:其一,价值性。保险标的应当具备一定价值,其可以由保险人和投保人双方约定并于合同中写明,也可以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按实际情况估值。保险标的的价值决定了保险金额的上限。其二,风险性(不确定性)。保险标的的风险性体现于财产存在可能遭受损失的风险。保险人也正是基于这种风险来决定是否承保以及保费的高低。其三,合法性。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应当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不得隐瞒真相、骗取保险人同意承保。
一般而言,对保险标的的虚构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恶意夸大”。即在投保时虚构保险标的价值,使保险金额远超实际价值,以在发生保险事故时获得巨额保险金。二是“以次充好”。风险必须是不确定的,而非必然发生的事项。“以次充好”大多体现在人身保险中,如隐瞒被保险人身患绝症的事实进行投保。在财产险中则是对必然会遭受的财产损失进行投保。三是“虚构利益”。即将他人财物虚构为自己的财物进行投保,如卖家对已卖出的物品进行投保,后谎称被盗以骗取保险金。四是“事后骗保”。即行为人本身未购买保险或保险已到期,在发生事故后予以隐瞒,重新购买保险并将事故伪装成后来发生,以骗取保险金。
具体到航班延误险,其保险标的为航班的准时性,或称航班是否延误。如前所述,时间本身就具有价值性,延误必然带来损失,此不证自明。且延误与否乃概率事件,受天气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可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故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在此基础上,当投保人通过合法渠道购买航班延误险时,只要已经购买同班次机票,合同就已经成立。保险人承保的对象是航班的准时性,属于一种间接性财产利益,而非被保险人有无真实乘机、具体造成多少财产损失。换言之,当投保人购买行为完成时,保险合同成立,保险对象(保险标的)就已经客观存在。在李某案中,其所购买的航班均确实发生了延误,并非为李某“虚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航班延误险属财产险,而财产保险的标的不可能是人。因此,无论用谁的身份信息购买航班延误险,都不构成虚构保险标的。至于登机材料等信息,充其量仅为理赔条件之一①甚至多家保险公司对航延险的理赔均未要求提供登机材料。,更不是保险标的,自然也不属虚构保险标的。
综上所述,即便李某伪造了部分证明材料,但只要虚假行为不足以导致航班真实延误,均不构成虚构保险标的。
(二)夸大损失程度的判断
夸大损失程度与虚构保险标的中的“恶意夸大”有一定类似性,应注意区分。如前所述,“恶意夸大”是在投保时虚构保险标的价值,使保险金额远超实际价值,以在发生保险事故时获得巨额保险金。“恶意夸大”发生在投保前,是对保险标的价值的夸大,目的在于促使保险人提高保费的上限。而《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项中的“夸大损失的程度”发生在投保后,以合同成立为前提,乃保险事故发生后对自身损失的夸大,目的为理赔时在原定上限内获得尽可能多的保费。
有观点认为,李某实际上没有任何出行意图,不会因为保险事故产生任何损失,却故意声称损失存在。因此,即便不认可她有虚构保险标的的行为,在发生航班延误,出现保险事故后,李某将无损失说成有损失的理赔行为,属于对发生的保险事故夸大损失程度,仍然成立保险诈骗罪。[19]对此,笔者不能赞同。
在夸大损失类案件中,保险标的确实发生了保险事故,事故也属于赔偿范围,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受益人等)为了牟取更多的保险金而恶意夸大标的的损失程度,在判断是否夸大了损失程度时,须从形式和数额两个层面予以判断:
一是在形式上,夸大损失程度主要有虚假申报和恶意蔓延两种。前者指部分保险标的其实并未受损,但行为人将其一并计算在损失内。如车辆损失险中,行为人的车辆发生事故后前桥并未受损,却向保险公司虚报前桥受损申请理赔。②2013年4月16日,冉某及其女友驾驶车辆行驶至重庆市巴南区巴滨路时发生事故,车辆驶入路旁排水沟受损。冉某在事故未造成车辆前桥受损的情况下向保险公司虚报前桥受损的情况,并开具虚假的维修前桥部件的发票及结算单合计43 696元,连同本次事故造成的正常维修费7 768元向保险公司索赔。后保险公司赔付维修费51 464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冉某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作为被保险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夸大损失的程度,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保险诈骗罪。参见:〔2016〕渝0103刑初173号判决书。后者是指行为人在保险标的受损后,人为加重损失程度,以牟取更多的保险金。之所以将其纳入夸大损失的范畴之中,是因为保险事故发生后,相关人员有义务采取各种手段控制损失,以使损失较少或不扩大。当行为人在意图得到更多补偿金而没有采取相关措施造成损失扩大,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夸大损失然后索赔。[20]
二是在数额上,夸大损失程度骗取的保险金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真实的损失数额,另一部分为超过真实损失的夸大部分。如上述交通事故案中,行为人事故车辆的维修费用为4万元,却串通4S店开具6万元的发票并以此金额申请理赔,则为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金。需要注意的是,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对真实损失部分本来就具有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所以,判断是否“数额较大”,构成保险诈骗罪,应仅以超过真实损失的夸大部分为基准,来确定犯罪数额,以使刑事立法与保险行政法律规范相协调。
再回到李某航延险诈骗案中,基于前文论述,对于李某是否夸大了损失程度,以下逐一判断:首先,由于航班确实延误,故而保险事故已经发生,保险标的(航班的准时性)必然遭受损失,所以排除李某“虚假申报”的可能性。其次,在航班延误后,延误多久、何时起飞均要视天气或管制状况而定,不受李某左右,因此李某根本无从对延误的时间损失“恶意蔓延”。最后,根据报道情况来看,李某虽数年内共获取理赔金300余万元,但每一次在申请理赔时,均以航延险中的实际金额为理赔数额,并未超额理赔,故而不存在夸大部分骗取保险金。综上所述,李某没有实施《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项中的“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行为。
四、从刑法的第二次性质看这起保险诈骗案的处理
在“刑民交织”类案件中,应坚持由轻及重、“先民后刑”的判断方法。对于事实清楚、但法律关系复杂或技术问题难以判断的案件,可以以民事上的权利确认及法律关系判断作为基础,进而作为刑事程序的先决依据,以保证法秩序的统一性。[21]在民事上,保险标的的确定须以保险合同为基础。而“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枷锁”,既然投保人签了自动生效的保险合同,双方已将保险标的约定为航班的准时性,且未将实际乘坐航班作为理赔要求,则投保人是否候机、是否乘机、是否故意不乘机等均不对保险标的产生实质影响。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前文的刑事判断,就不难得出李某不构成保险诈骗罪的结论。
事实上,主张对李某的行为进行刑事干预是“刑法万能观”的体现,有公权力干预市场之嫌。甚至有学者认为,刑事不法与民事行为无关,刑法是一个闭环而自洽的体系,犯罪成立与否仅应在犯罪构成的范围内进行考察。即便是保险诈骗,其定罪量刑的基础规范是刑法,无需用保险法进行分析。[22]我们承认,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变化,刑法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治理工作中。但这种参与始终体现着二次性,即作为事后法与第二位阶法,刑法需要在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部门法律不足以保护法益、维护社会整体秩序的情况下再挺身而出,运用刑罚措施,恢复被破坏了的社会秩序,维护公众对社会规范(法律规范)的确信。[23]
换言之,社会关系的调整分为两次:当矛盾出现时,第一次调整应当由非刑事的保护性归责完成,其依托是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一系列部门法的法律责任条款;第二次调整则是由刑事法律法规完成,即“刑法在民事法、行政法等第一次法规范对正常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基础上,通过追究刑事责任、裁量和执行刑罚的方法对第一次法调整无效的严重不法行为进行第二次调整。”[24]即刑事违法性以前置违法性为基础,如果某行为可由前置法进行调整,刑法就不必要加以干预。刑法的这种特性也被称为刑法的第二次性质或刑法的第二次性原则,也是解释刑法应当遵守的准则。
在当代法治国家,刑法谦抑性及其所宣扬的理念与精神已成共识。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 (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 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其表现为刑法的紧缩性、补充性和经济性三个方面。[25]犯罪一般以刑罚为后果,而相较于其他法律责任的承担而言,刑罚具有更明显的严厉性,也会对人的社会化进程产生影响,无论从必要性还是经济性考虑,刑罚的适用都必须审慎。因此,无论是行政还是民事等法律行为,只有当其严重破坏既定的社会秩序,达到触犯刑法的地步,才存在刑罚干预的余地。
在民事法律行为中,我们鼓励合同自由、合同至上。尤其在民法典已经到来的时代,国家鼓励市场主体积极发挥能动性与聪明才智,平等市场主体间的权利义务由民事法律关系所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反对个人赚钱,刑法也应当尊重市场规律,严守站位底线,而不可将刑罚之“手”伸得过长。与其千方百计将李某的行为嵌入保险诈骗罪,不如认真考虑一下如何弥补保险产品的设计漏洞,引导保险行业步入正轨,这样更加有益于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也会是一种双赢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