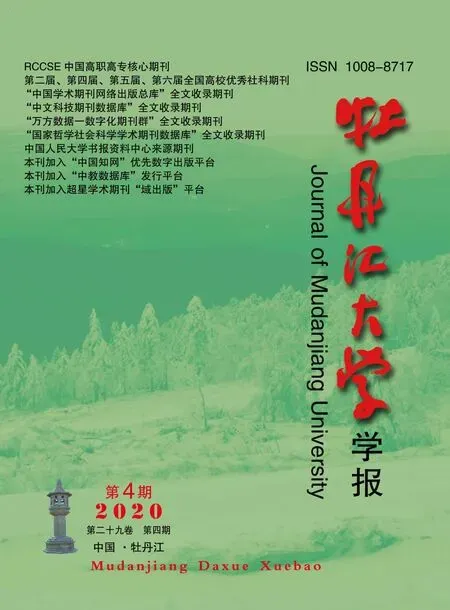元杂剧“兀的、兀那”的方言流变探析
2020-02-28张建华
张建华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榆林学院文学院,陕西 榆林 719000)
一种戏曲在传播过程中总会给所经之地留下一些痕迹,这些痕迹在历史长河中或者消亡,或者发生语义、语音演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且这种演变往往与传播地区本土文艺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
一
熟悉元杂剧的学者大都知道,元杂剧里经常出现“兀的”“兀那”这两个词语。著名的《西厢记·长亭送别》里[叨叨令]中写道:“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什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则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揾作重重叠叠的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久以后书儿、信儿,索与我凄凄惶惶的寄。仅一本《窦娥冤》中,“兀的”就出现了9次,“兀那”出现了6次。元杂剧各注本所释“兀的”一词的主要含义是:“这,那”,或者是发语词,无意义。“兀那”,指示代词,那,那个,可指代人和事。“也么哥”戏曲中的衬词,无意义。但以笔者陋见,“兀的”还有“实在”“真的”这个意思。“兀那”中的“那”是指示代词,“兀”是一个发语词,或者象声词,或者叹词。这不但在古代文学中可以说得通,现代方言也可以找到例证。
现以《窦娥冤》《西厢记》《汉宫秋》等元明清部分作品为例,考证“兀的”“兀那”的意义。
(一)兀的
1.这等,你是我亲家了。你本利少我四十两银子,兀的是借钱的文书,还了你;再送与你十两银子做盘缠。亲家,你休嫌轻少。(《窦娥冤》)兀的,意思是指示代词,这。
2.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西厢记》)兀的,可以解释为“这”,这不闷死人了吗?也可以解释为“实在,的确”,副词,实在闷死个人了呀!这个句子可以看作是把前一个反问句改为陈述语气。“也么哥”意思是语气词“了呀”。
3.(张驴儿做扯正旦拜科,正旦推跌科,唱)兀的不是俺没丈夫的妇女下场头!(《窦娥冤》)
兀的,意思是的确,确实。这的确是俺没丈夫的妇女下场头。
4.(孛老云)我吃下这汤去,怎觉昏昏沉沉的起来?(做倒科)(卜儿慌科,云)你老人家放精细着,你挣扎着些儿。(做哭科,云)兀的不是死了也!(《窦娥冤》)兀的,指示代词,这。句子意思:这是死了啊。
5.(卜儿哭科,云)窦娥孩儿,这都是我送了你性命。兀的不痛杀我也! (《窦娥冤》)兀的,意思是实在,的确。实在痛死我了呀。
6.俺婆婆若见我披枷带锁赴法场餐刀去呵,(唱)枉将他气杀也么哥,枉将他气杀也么哥!告哥哥,临危好与人行方便。(《窦娥冤》)也么哥,了呀,语气词。
7.(卜儿哭上科,云)天那,兀的不是我媳妇儿!(《窦娥冤》)兀的,指示代词,那。
8.孩儿放心,这个老身都记得。天那,兀的不痛杀我也!(《窦娥冤》)
9.有鬼,有鬼。兀的不吓杀老夫也!(《窦娥冤》)兀的,副词,实在,句子意思,实在吓死老夫了呀。
在这里,兀的+不+闷(烦、痛、恼)杀人+也么哥,也成了一种固定的反问模式,通过副词“兀的”表达反问语气,表达的正是肯定的意义。
(二)兀那
1.兀那弹琵琶的是哪位娘娘?(《汉宫秋》第一折)兀那,指示代词,那。
2.孩儿然后去兀那坟前,也拜几拜。(《清平山堂话本·合同文字记》)
一般文献认为“兀那”是指示代词,那。也可以解释为,兀,发语词,无意义。那,指示代词。
3.兀那都头不要走。(《水浒传》第十四回)兀那,叹词,表呼唤。
4.来到此处,东也无人,西也无人,这里不下手,等甚么?我随身带的有绳子。兀那婆婆,谁唤你哩?(《窦娥冤》)兀,叹词,表示呼唤。
5.兀那婆婆,你无丈夫,我无浑家,你肯与我做个老婆,意下如何?(《窦娥冤》)兀那,兀,叹词,表呼唤。那,指示代词。
6.(张驴儿云)我们今日招过门去也。帽儿光光,今日做个新郎;袖儿窄窄,今日做个娇客。好女婿,好女婿,不枉了,不枉了。(同孛老入拜科)(正旦做不礼科,云)兀那厮,靠后!(《窦娥冤》)
兀那,兀,叹词,哎。哎,那个小子,往后走。
7.(刽子做喝科,云)兀那婆子靠后,时辰到了也。(《窦娥冤》)兀那,兀,叹词,那,代词。哎,那老婆子往后走。
8.兀那鬼魂:老夫是朝廷钦差,带牌走马肃政廉访使。(《窦娥冤》)兀那,哎那。
9.兀那鬼魂,你道窦天章是你父亲?(《窦娥冤》)兀那,哎那。
虽然这三个词在语言的长河里逐步失去了语言活力。然而他们在这些经典文学作品里出现频率如此之高,使其颇具研究价值。
此外,这几个词在现代汉语方言里仍然在使用。比如“兀的”在甘肃凉州就仍然存在,只是其语义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总的看来,主要有三种新的语义产生。一是指“最终,终究”;二是象声词,模拟声音;三是指 “突然”。后者的语义和现代汉语偏义词“突兀”的“兀”意义相近。与此同时,“兀的”通常具有贬义情感色彩,而且通常跟“儿”结合,这种结合并非北方方言里的儿化现象,而是一种固定组合。甘肃凉州方言里“兀的”使用范例如下:
1.这个坏怂,兀的儿把人家骗了。最终还是把人家骗了。一般具有贬斥的情感色彩。
2.长城那面野河滩里有兔子,跑得快的很,“兀的”一哈就不见了。兀的,象声词,相当于“嗖”地一哈,用来模拟声音。
3.兀的来了,兀的去了,你搞啥名堂着哩,把人头都绕晕了。兀的,突然。突然来了,突然去了的意思。
4.那个无赖缠磨了三五个月,兀的儿把王家的姑娘整得木办法了,只好嫁给他了。终究把王家的姑娘整得没办法了,只好嫁给他了。此处也是带有贬斥的情感色彩。
“兀那”也是甘肃凉州方言里常用的词,其意义跟古代文学里的意义相较,变化并不大。只是目前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少见了。早期常见于凉州西部金山乡(山区)、凉州区金沙乡、高坝乡(今俱已设镇)新关村一带,因为农家人通常会隔着山茆茆和田埂老远互相喊话,“兀——那个扛铁锨的,等我一哈。”相当于“哎——,那个扛铁锨的等我一哈。”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甘肃凉州人也会说:“你找个谁哩?哦,张嫂子吗,兀——那不叫嘛。”意思是说,“你找谁着哩,张嫂子吗,那——不是嘛。”“你干撒起(去)哩?”“我走个兀——那——些起(去)哩。”通常用上“兀那”表示张嫂子距离对话的两个人距离较远,所以说话时发声者会辅以一定的肢体动作,比如缓缓抬起脖颈,然后向右或者向左转动头部,并以眼睛光线追踪所示之人。
不仅如此,跟元杂剧相较,凉州方言中的“兀的”通常会有儿化现象。普通话儿化韵的功能通常有三个:区别词义,区分词性,表示细小、轻松或者亲切、喜爱的感情色彩。而凉州方言里儿化韵的表义表情作用则大大减少,只依附在前一个词上面表示程度增加或者减少的附加意义。回到本文主要词语“兀的”上,“兀的儿”就表示经历的时间过程很长,最终结果出现了,但是这个最终结果是很长时间的各种因素集合得来的,并非一朝一日。
这种儿化现象并非“兀的”单有,而是在上世纪90年代凉州方言中普遍存在,目前60岁左右的老人还会常用此词,40~50岁左右的人群偶尔会用,40岁以下的人群已基本不用这个词语表义。以下用五度标记法和兰银官话河西小片[1]标识方言的读法,以探究其意义及其与北方方言儿化韵的区别。例如:
1.他兀的儿把他老子气死了。兀[V41]的[ti21]儿[ɤ52],兀,唇齿音,下唇和上齿结合发音;的,音同底,音高与底有区别;儿,与北京儿化韵相较,其发音方法由卷舌央中不圆唇变化为不卷舌元音[ɤ52],舌位明显前伸,舌尖抵下齿,发音时有摩擦,“儿”在此处不表义。
2.你悄悄儿底,不料说话。悄45悄,“儿”依然是不圆唇不卷舌前元音,只不过在语流中调值又有变化,实际调值是[ɤ22]。
3.娃娃乖乖儿底,你逗着娃娃嚎哩嘛?!
4.你轻些儿[ɤ44]着,小心叫人家听着,不丢人吗?这里的“儿”调值再次发生变化。
5.慢慢儿走,不料急,急着抢银行去哩吗?
在这些儿化韵前面,通常会有一个叠音词出现,表示程度增加或者减少,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语音现象。在这里的“儿”的调值会根据语音环境发生一定的变化,并非只有一种调值。语流音变,类似于普通话里的“啊”的语流音变。
二
无论是“兀的”的语义演变还是语音演变,这种变化跟凉州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不无关系。凉州自古以来是边疆重镇,文化活动十分繁荣,元杂剧在百姓生活中可能并不陌生,但是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兀的”和“兀那”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或深或浅的变化。
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不可能凭空出现或突兀消失,都是有渐进的痕迹存在于文学史,元杂剧亦然。至于变化的基础以及流变的区域及路线,目前由于资料匮乏,笔者并不能有效地勾勒其图谱,只能做一些粗浅的梳理和探索。
我们首先从宗教领域来探究一二。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寺塔记上》云:“佛殿内槽东壁维摩变,舍利弗角而转睐,元和末,俗讲僧文淑装之,笔迹尽矣。”又唐段安节《乐府杂论·文叙子》:“长庆中,俗讲僧文叙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宋代佛教》:“还有俗讲变文一向在流行,并演变为唱曲。”[2]这说明由俗讲变文而至唱曲,是有线索可查的。凉州贤孝就是包含简单故事的“曲”,当时没有案头记录,仅靠口耳相传,因之大多已佚。近些年有学者将其搜集整理出版了部分。而后,逐步发展出有文字记录的稍微复杂的宝卷,然后出现更复杂的金院本和诸宫调,继之元杂剧登场。曲子瑶也认为:“元代是中国古代在民俗文化发展上呈现出难得的比较开放和多化元特征的时代,元杂剧的创作也深受这种民俗文化娱乐性发展风气的影响,给元杂剧等戏曲艺术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创作和生长环境。”[3]
众所周知,元杂剧最初流行于大都(今北京)地区。学界也有共识,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下,融合了各种表演艺术形式,并在唐宋以来话本、词曲、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创作出了比较成熟的文学作品。据载,高昌国佛教盛行。“依《出三藏记集》卷八所载道安《摩诃波罗蜜经抄序》言,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正车师前部王弥第来朝,其国师鸠摩罗跋提献胡本《大品》一部。及北凉沮渠蒙逊领有此地后,高僧辈出,译经风气大盛。麴氏王朝成立后,佛教受历代诸王外护,佛法隆盛。玄奘西游途中,路经此地,国王麴文泰率全城欢迎,热情款待,并请求永留其国。玄奘婉拒,唯停留一个月,并为将《仁王经》。及回鹘移往后,除潜信摩尼教外,亦信奉佛教、景教、祅教等。”[4]“佛教从陆路和海路传入中国,而陆路即今印度北部途经中亚、今新疆、河西走廊传到中原。”[5]敦煌这个名称,据考证是“诵经处”之义。[6]由此可以做出推断:由于佛教的传入,敦煌变文和俗讲从敦煌一带逐步流徙至凉州,在当地大行其道,凉州贤孝和凉州宝卷派生,而后宋代讲史讲经话本流传,接着金院本和诸宫调亦出现,然后兼备各种体系的元杂剧诞生,线索为“俗讲、变文——贤孝和宝卷——话本——金院本诸宫调——杂剧”,如果这个发展线索成立,那么凉州贤孝和宝卷就可以称得上是元杂剧的祖宗之一了。凉州贤孝《丁郎刻母》(张天茂演唱)里有一段唱词是这样的:“活着不给穿,把妈妈打着木式样,死掉强如你给发大丧啊。活着你不给吃不给穿你死了发丧……。”这一段演唱中间是情绪色彩特别浓烈的三弦伴奏和击板,然后出现一句唱词:“哎……啊……,大慈大悲……呀儿……啊。”正说明这种戏曲形式脱胎于佛教俗讲和变文。《赵氏孤儿变文》中,程婴手拿画卷上场并遗弃台上以引起孤儿注意,孤儿果然找了程婴要细问图上(变相)所示因果。待听完图上故事时,孤儿不禁大叫:“兀的不气煞我也!”[7]既然此句在唐宋时期就出现了,且又是元杂剧中最常见的一个感叹句,可见元杂剧在河西乃至凉州出现并有广泛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而“兀的”在变文和宝卷等作品里出现,便是明证。
继之我们也可以从凉州贤孝、宋元话本和元杂剧的异同来梳理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渊源关系。
第一:场地。凉州贤孝和宝卷、宋元话本和元杂剧都是以市民阶层的聚集地为搬演场所,如,现今凉州贤孝的搬演地址如文化广场茶摊、东关核桃园等地,这里往往围起一个较大的帐篷,内有茶馆,艺人在简陋的台上演出,台下百姓悠然自得喝茶听戏,说说家长里短,聊聊古今往事,也有聚精会神听戏暗自垂泪思考的老人。这样的场景神似宋朝的勾栏瓦舍和元朝的杂剧戏场。
第二:演唱、传播。凉州贤孝、宝卷一般都是一人主唱,偶有三、五人对唱,以三弦为主要乐器。形式上有说白,有唱词,韵散结合,一般是口耳相传,无固定唱词,同样的故事,唱词可以依不同的传承人的口授及徒弟的记忆和改编而有较大差别,目的都是把故事搬演完整;宋元话本,本是说话的底本,一开始也是口耳相传,后来有了简单的陈述故事梗概的案头文字,既然是话本,说书人自然也是一个,且韵散相间、对白和唱词相佐,虽也是口耳相传,已经有了许多刻意描述的痕迹;到了元杂剧,经过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影响,曲词和结构已经宛如天成,美不胜收。中外戏剧史上有两个较为明晰的发展线索,欧洲的戏剧如莎士比亚等,因为统治阶级注重文艺享受,他们的戏剧大都是有宫廷传向民间的;而中国的文艺形式,从《诗经》、五言诗、民歌到唐诗、宋词,基本都是从民间发端,再逐步被文人重视,进而参与其中,使得这一艺术形式从俗到雅,从单纯到多样,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发展到顶峰。事实上,这些从变文俗讲发展而来的贤孝和宝卷为元杂剧做了很好的故事准备,也为元杂剧一本四折,一人主唱的形式奠定了基础。所以,许多论者都认为凉州贤孝是清朝一个姓盛的秀才从关外传来的,这一说法事实上并无实据,仅是道听途说。倒是从敦煌这一路传来的俗讲变文结合河西各地的地方娱乐项目,最后发展演变为杂剧更有说服力些。
第三,故事内容。宝卷和贤孝的故事内容都比较简单,但二者应该是从敦煌俗讲变文演变而来。李凤英认为:“河西宝卷是至今还活在河西人民中间,为河西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间俗文学,是敦煌文学的活样本。宝卷的前身敦煌文学中的变文。在宋初变文被皇家明令禁止以后,民间就出现了代替它说经、劝善的宝卷。”[8]俗讲最初的意义就是劝人为善,宣讲因果报应。魏宏远认为,“宝卷作为民间说唱艺术,在明清时多从小说、戏剧吸收养料,通过对一些历史故事、佛经故事、民间故事的宣讲,将教化、娱乐、文学等多项功能融为一体。《赵五娘卖发宝卷》就是接受了《琵琶记》的故事梗概,并将原来赵贞女故事的‘惩恶’主题改为‘劝善’主题。”[9]这一点贤孝和宝卷都很好地继承了下来。贤孝的名称本就为劝贤立孝,故事里经常有因果报应的内容出现,说明这是俗讲的继承开拓者。只不过,贤孝的内容大都粗浅简单,一出场就交代人物,绝不拖泥带水,如《王哥放羊》《丁郎刻母》《绣荷包》等。《王哥放羊》一开始就介绍王哥单身的可怜处境,并没有东拉西扯。这是跟当地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爱听贤孝的大都是些有家有口的中老年人,家里大都有所牵绊,不可能长时间在戏场上徘徊不去,但是又颇好此道,只好叼空去场上听一场,一场一毕,许多人不得不恋恋不舍离去。如果故事太长,又不能有效分段的话,艺人不好记忆,听众就可能没有耐心听长篇大论旁枝斜逸,让他们总听一些没头没尾的故事也不过瘾,这就使得贤孝艺人不得不缩减太多的修饰和转圜成分,抛却较为复杂的开场和转折,直接上故事。这是符合民俗文化接受需求的。至宝卷出来,可能已经有比较好的条件传播故事,故此宝卷的内容就要稍显复杂一些,虽然也并未逃脱俗文化的熏染,但是有些甚至已经有比较完备的细节了。比如《赵五娘卖发宝卷》赵五娘吃糠这一节,唱词云:“……巧媳妇,做不出,无米饭菜;家贫穷,怎做到,美味香甜?不一时,只觉得,腿软手酸;肚又饥,吃谷糠,泪洒胸膛。别人家,那谷糠,猪狗不尝;奴却要,吃肚内,来救性命。……”而高明《琵琶记》则曲词工整优美,文白相间有度,达到了艺术与生活的高度统一。魏宏远认为,“宝卷发展至明清其故事来源存在‘多祖’现象。”[10]实际上,笔者以为,杂剧才是从宝卷、贤孝等多个世系的祖先复杂承变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