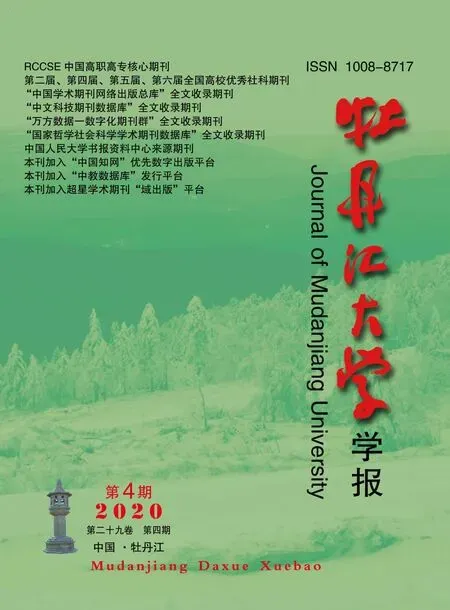无声的呐喊
——福勒对“花语”意象的书写和超越
2020-02-28张辰
张 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71)
引言
美国女作家萨拉·玛格丽特·福勒(Sarah Margaret Fuller,1810-1850)是超验主义的杰出代表,也是女性主义的先驱。与十九世纪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丰富的经历为福勒增添了多重耀眼身份:她是《日晷》杂志的第一位编辑,是美国妇女权利运动的倡导者,是爱默生、霍桑和奥尔科特的密友,是勇敢跨越美国西部土地的探险者,是投身于意大利革命的战地记者。[1]3
福勒所处的十九世纪,是西方女性解放运动兴起的时期,也是女权运动真正开始之时。女性思维逐渐受到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新兴观点朝气磅礴地取代着旧式思维。尽管女权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女性的地位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提升。[2]339作为同时代卓越女性的代表,福勒写出众多极具哲学性和思考价值的作品,用以鼓励女性独立思考,发挥自己的特点,充分展示个人潜能,提升精神世界,积极地为女性自立作辩护。
福勒的文学作品包含很强的自我意识,明确表达了她对女性生存状态的看法。[3]113她在《十九世纪的女性》(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这部书中阐释道:“在两性结合之前,男女都必须是独立的个体。女性要想保持独立性,一方面,需要男性去除他们的主导力;另一方面,女性自身也要宣称独立,力图从男性的影响中解脱。”[4]197这部著作直至今天仍被西方学术界奉为“美国第一部重要的女权主义宣言。”[5]103
《十九世纪的女性》一书奠定了福勒在女性主义领域的地位。除此之外,她在其他众多作品中反复运用“福勒式的书写方式”,突出强调自己的女性主张。“花语”意象就被福勒用来作为大胆表达女性诉求的工具。福勒在花与女性之间构建了复杂的、立体化的关系。在其文学作品及私人信件中,她毫不吝啬地表达了对“花”的挚爱。在一封写给好友威廉·亨利·钱宁(William Henry Channing)的信中,福勒写道:“我仿佛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与花的联系:她有对花的爱,我有对花的诠释。我对它们的描写不是源于我的幻想,那是它们自己的私语。”[6]97-98
沉默的女性在无声的花园里默默地摆弄、照料着各类花草是十九世纪美国女性生活的典型写照,福勒借助“花语”意象勾勒出如花一般的女人们自己的故事。花语虽无声,无声胜有声:花儿本身是无声的存在,它们以无声的身份陪伴着女性,见证了社会中无数平凡女性的平凡生活;女性虽然有发声器官却又扮演着无声的角色,鲜少在家庭、社会中表达自己的声音,致使这一群体始终被包裹着沉默的外壳。在福勒的笔下,富有灵魂的“花语”转而成为一种媒介,传递那些沉默着的女人们应有的声音和思想,突破了女性“以花传情”的传统寓意,开启了女性“以花言志”的先河。
一、福勒对传统“花语”意象的超越
“花语”在人类文明史上享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古希腊罗马神话中,随处可见花的影子:风信子是阿波罗的挚爱,风花是维纳斯的追求,水仙花是回声女神的热忱……它们分别代表着爱与美的不同形式。[7]17,66伊丽莎白·华盛顿·沃特(Elizabeth Washington Writ)曾写道:“很少有一份礼物能比一束鲜花更令女士感到愉悦。如果献花人愿意给这束花赋予更广的意义,那么,他的智慧和情感都可以反映在这束花上。”[8]4在美国文化中,“花语”有其独特性——关注道德品质。“花语”在19世纪拥有众多如:哈丽叶特·比切·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和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等知名的女信徒,她们经常把道德健全的女人与美丽的花等同起来。[9]49芭芭拉·威尔特(Barbara Welter)在《真正的女性》(True Womanhood)中将“虔诚、纯洁、顺从和顾家”定义为一个女性应该具备的品格。她认为,女性不仅与花园里需要打理的空间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与花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的联系。花和女性都具备优雅天真的气质和精致的外表,使得这两者在本质上拥有更为密切的相似性。[10]165“花语”的传统涵义常为女性带来依赖的气质,作家用“花语”代表女性,以表现女性群体在思想和身体上的双重脆弱。[11]17
福勒对自己的“花语”作品持有甚为谨慎的态度,她并不希望自己的“花语”仅仅被当作普通女性读物的雷同品。[12]VX她对无声“花语”意象的再塑造突出表现为将其丰富化、拟人化和神话化,将单薄的“花语”意象编织在一个个生动的神话故事中,用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为读者呈现出不同“花语”意象所展现的饱满的女性形象,自然地建构起“福勒式美国神话故事”。她很少直接遵循花语字典的固有意义,而是为其赋予新的灵魂和思想。在莎拉·黑尔(Sarah Hale)的辞典中,西番莲的花语是“对宗教的热情以及神圣的爱”[13]143,福勒在《西番莲》(The Passion-Flower)一诗中将它塑造为虚伪爱情的象征;大丽花的花语即永恒的爱[14]86、优雅和尊严,[15]54在《对话》(A Dialogue)一文中,福勒为其勾勒了一个富有讽刺意味的女性形象:大丽花毫无羞愧地邀请太阳“洒落”在她身上,只因满足她想要夺人眼球的私欲;在散文《庞恰特雷恩湖旁的木兰》(The Magnolia of Lake Pontchartrain)中,福勒诉说了一个“独特的女性故事”。散发着“极具穿透力却并不腻人”气味的木兰将一位骑马而过的男性深深吸引。[16]300象征着广大平凡女性的“她”向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他”讲述了自己从一棵平凡却丰饶的橘子树转变为独立且高贵的木兰的故事。
查尔斯·卡珀(Charles Capper)在谈到福勒的花语作品时曾说:“这样深奥难读、讽喻无情的故事,通常让学者们感到无法解读,更不用说消化。”[17]44在福勒存留的文本中,“花语”意象的使用处处彰显着坚定感与信念感,它们自然地表露于字里行间之中,明确表达了她对女性地位和发展状态的看法和态度。福勒独特的书写方式旨在用女性熟悉的、喜爱的物品为载体,吸引女性阅读。无声的“花语”不无例外地展现出女性特有的气质,这种气质不仅诱发女性群体开智,认识到并渴望发掘自己的潜在价值,也让男性从这位不平凡的女作家的视角重新审视女性的力量。
二、福勒 “花语”意象对超验主义的超越
作为超验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超验主义思想内涵常常贯穿福勒作品的始终,其“花语”作品也印证了这一特点。散文《庞恰特雷恩湖旁的木兰》首段写道:“星星把它们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了花儿。”[18]299在超验主义大家爱默生看来,“星星”是发挥积极作用的事物,能给人以崇高感:“倘若你想追求一份孤独的感觉,那么你就抬头看看星星……那从遥远天国射来的光线,将会把你和周围的琐事隔离开来。这些传播美丽的使者每晚都会出现,他们用劝解的微笑点亮了整个宇宙。”[19]256福勒似乎借“星星”向花儿的诉说向读者群体发出暗示:对于人类而言,研究宇宙的奥妙是一种徒劳,因为任何一个伟大的秘密都将会或已经揭示在大自然当中。在此,福勒间接地强调了直觉的重要性,这与超验主义的核心观点保持高度一致。超验主义理论崇尚直觉,强调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凭借自己的直觉向周围的自然世界寻求启示,从而直接认识真理。人的存在是神的存在的一部分,人在一定范围内就是上帝,自然界是神对人的启示,人可以从自然界认识真理,了解物质发展规律,得到精神道德原则方面的启示。[20]3
值得注意的是,福勒的“花语”意象并不仅仅停留于超验主义思想的表面,她尝试以无声的“花语”意象为依托,以为女性发声为目的,启迪当时的美国妇女自主思考、自我完善,继而从全局意识的视角推动男性群体、全社会对女性群体的认知。[21]5因此,这一意象的建构与女性主义思想具有高度的互融性。超验主义思想与女性主义思想在福勒“花语”意象的书写中并存,其女性主义思想根植于超验主义思想,又服务于超验主义思想。
例如,“冥想”本是超验主义获取真理的重要途径,福勒将其用于促进女性的智力发展。在《庞恰特雷恩湖旁的木兰》一文中,象征着奉献、孕育的橘子树经历了“冥想”这一过程,使其在无声的环境中凝聚精神,从内心真正渴望实现自我的突破。福勒在文中六次提到橘子树和木兰对安静环境的偏爱,足以见得无声寂静的、适合思考的空间在福勒脑海中的重要程度:
“我终于找到了她,南方女王,在孤零零的凉亭里,她独自歌唱。一个君主独处的时候,就是她最威严的时刻;因为那时就没有任何干扰能阻止意识的力量。”[22]299
福勒尝试运用超验主义的理念,帮助女性解决自身问题,在实践层面指导女性走向自立,实现了对超验主义理论的超越。因而,在理解福勒的“花语”意象时,需要同时从超验主义思想和女性主义思想相结合的视角进行解读,真正体会这个站在时代前端的女性在思想上的超越性,不使之只流于形式。
三、福勒“花语”意象对女性自立的建构
福勒对女性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了自己的女性观点。她以超验主义思想中的自我完善为前进方向,以社会进步为最终目标,向无声的女性群体发出最强号召,鼓励她们争取实现自我价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女性。福勒借花言志,在《庞恰特雷恩湖旁的木兰》一文中,从认识自己、相信自己和成为自己三个阶段递进,逐步指导女性在实践中走向进步。
1.认识自己:于无声处积聚力量
在福勒看来,解决女性问题的必要前提就是认识自己。[23]148长久栖居于无声环境的女性,只有经历自我审视的过程以及受到社会的认可,才能打开心门了解自己,重视自我感受,于内心处真正渴望发声。福勒眼中的认识自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女性对自我本身的认识,二是社会对女性的认识。[24]55在女性漫长的发展史中,双重认可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鼓励女性群体充分思考、培养问题意识和揭示价值。
在萨拉·黑尔(Sarah Hale)的“花语”辞典中,“橘子树”象征着“女人的价值”,它与家庭生活密不可分。[25]139福勒笔下多产的橘子树暗指女人结婚后担负的传宗接代的任务,以及女性必须塑造一个为社会所期待的既慷慨又无私的好母亲、好妻子的形象。橘子树第一次孕育出果实时,也曾发出欢呼:“我是多么幸福!”然而,无尽的硕果带给母体本身的却不是对等的喜悦:
“商人指望我的果实赚钱,新娘指望我送她花环,贵族指望我送他豪华的装饰,穷人指望我送他钱财……不分你我,我属于所有人,我没有一刻歇息的时间,因为我从未属于过我自己。”[26]302
此时的橘子树已经初步具备了自我审视的意识,它开始思索存在的意义:一味地孕育果实,一味地馈赠果实,一味地奉献果实是否是生命的真正价值?这棵橘子树宛若一面镜子,镜中满是夜以继日忙碌着的女人们的身影,无偿地向丈夫、孩子们给予着她们能力范围内的一切。橘子树的寡言无私与无声的女人们保持着高度一致性,她们一生都处于默默奉献多于受到重视的状态,不得不为依赖她的那些人赠予更多。当橘子树开始自我审视那一刻起,福勒为橘子树注入了灵魂,意味着她将主动思考自己面临的无奈与窘境,她终将在深思熟虑过后,在牺牲所有和走向自立之间做出忠于内心的抉择。
除了女性需要对自我进行审视之外,福勒同样认为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对女性认识的不足也会阻碍庞大女性群体及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十九世纪的女性》一书在颠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定义后,福勒呼吁社会重新认识女性。[27]115《庞恰特雷恩湖旁的木兰》中唯一的男性角色是一位骑马过路的男性,他是福勒眼中同时代男人们的缩影。他为木兰身上未曾熟知的气味所着迷便下马寻找,实际上,他与眼前的木兰并非初次谋面,当木兰还是一棵橘子树时,他们早有交集。可男性薄弱的洞察力使他忽略了脚下广阔自然大地的提示,忽略了本就熟悉的木兰,也忽略了同时代女性的力量和能力。由此而展现的男女两性间巨大的性别角色差异,让福勒的“花语”意象更具深刻性。19世纪的妇女其主要角色仍是家庭主妇,她们在政治领域,几乎没有权利可言;在经济领域,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妇女只能从属于男人,处于受男人支配的地位。[28]80而新生的木兰就在这些男人们的脚边悄然生长,俨然一位正处在启蒙过渡期的女人,她向读者暗示道:当男性能认识到女性的能力时,女性会有更大的潜力。
于无声处积聚力量,继而悄然生长是女性实现个人发展的独特成长方式。无声的生存环境注定了当时女性认识自我的方式同样是缓慢的、细腻的。在沉默中思考,在思考中抉择,充分体现了超验主义思想对个人能力的强调,对女性智慧开启的探索。
2.相信自己:于无声处沉淀力量
福勒认为,女性在充分认识自我之后,必须坚信自己的判断,以自我为依靠,听从内心意识的指引,从而使积聚的力量加以沉淀,以期实现良好的助力。[29]55
橘子树给无数人带来无穷无尽的花儿和果实,后来的她终于意识道,她对别人的慷慨换回的却是别人对她毫不在意的掠夺。无声的夜晚,橘子树信念坚定,期待凭己之力取得改变:
“我不再期待从他们身上得到任何东西,我要把目光转向远方的星星。我想,我可以储藏一些我的果汁,直到我长得足够得高,那么,我可能会触到那些遥远的看起来沉默又神圣的星星,我可以在无尽疲惫的生活里松一口气。在冬天结束的时候,我会找到自己的春天。”[30]303
相信自己是解决女性问题的重要支撑。橘子树正经历着从无私奉献到精神独立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阶段的过渡:她坚信自己具有某种价值,愿意为此而坚持。橘子树的信念中充满了热忱与希望,她逐渐向上寻求心灵寄托,将星空当作灵魂的栖居处,不断给自己加以鼓励和暗示:总有那些闪烁的力量在无尽的暗夜中助力沉淀,使自我成为更有力量的存在。
有学者认为,《庞恰特雷恩湖旁的木兰》是福勒在得知好友安娜·巴克(Anna Barker)结婚后,所遭受的“情感与想象的混乱”[31]75。福勒担心安娜陷入繁重的婚姻生活后,会遗憾地放弃学术追求。在福勒眼中,她和安娜拥有一定的学识,时刻进行自我反省,能发挥社会上少数女性拥有的才能。因此,当安娜结婚后,友谊的疏远给福勒蒙上了巨大的分割感和孤独感,打破了福勒一直渴望的知识分子的交际圈,她将自己孤身一人的感受隐藏在作品中。正如福勒在文中描绘的木兰一样,她已经与她的姐妹们分开了:
“我的确是你喜爱的花里的一员,但我是孤独的。在我的家里,尽管我的根和花园里其他的花一样,但我没有同心的姐妹,没有开出和她们一样的花来,在森林里的唱诗班中,也没法儿把我的声音和她们的声音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一个人住在这里,也从没想过要和谁说我那孤独的秘密。”[32]302
橘子树和木兰代表着女性的两种生活状态和选择——单身与已婚,这是大多数女性会经历的人生阶段,它们彼此不同却又合而为一。木兰的前身——橘子树象征已婚的安娜,福勒担心好友被婚姻限制了思想自由,即将或已经处于被男性奴役的状态;木兰则代表了福勒自己在无伴状态下的独立。在这里,两类“花语”意象的交替使用不仅象征着长久沉默的女性因自己的抉择而可能遭受挣扎且痛苦的煎熬,也暗示了坚定信念,终会迎来点点星光般的希望。福勒坚持教导女性用更加坚定的意志来沉淀信念,永远相信自己内心深处灵魂的感召,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判断力,做出自己的判断,回归自我。
3.成为自己:于无声中爆发力量
福勒坚定地认为,女性只有在获得内心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前提下,才可以真正理解生命的意义。[33]56她们既要充分发挥女性潜能,又要平衡发展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最终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增强表达欲望,成为完善的个体。
突然而至的冷风将橘子树这棵昔日的“花园骄傲”吹成了“黑乎乎的、毫无生气的”[34]303一片,她被旁人无情抛弃,标志着橘子树多产的时代结束了。然而,她的身体焕然一新,又重新将灵魂扎根在理想的驻地——一棵清冷的木兰上。重获新生的木兰自由地伸展着茂密的枝干,开出一朵朵洁白的花蕾。与橘子树不同的是,木兰从不结果,人们也无法把花枝折下插进花瓶。这样的木兰“纵然自身变得灰黄,也仍要拒绝保留那些使她变得耀眼的色彩,她就像一位被囚禁在敌人监狱里的公主”[35]300。
在福勒的超验主义思想中,“女性身体”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福勒看来,身体即自我本身,身体是知识的载体,只有身体与思想相统一,才能最大程度地提升女性自我。[36]4木兰从外表来看并不惹人怜惜,“庄严的碧绿之塔,枝繁叶茂,像威严的女祭司一样”[37]300。女祭司是古罗马炉灶和家庭的保护神——维斯塔,她终身未嫁,代表着女性的贞洁和独立。福勒将木兰比作女祭司,旨在将女性的价值从生殖能力中分离出来。女祭司是福勒眼中独立女性的榜样,她在《十九世纪的女性》中曾激励女性选择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不是经营婚姻和孕育子女,而是不断增加学识以及习惯性的自我反省。[38]99
除了为女性的自我发展开辟新道路之外,福勒为木兰塑造的新女性的形象提供了鲜明的视觉隐喻:一个坚强女性的象征。生长于美国南部的木兰以高大挺拔而出名,它打破了传统“花语”所代表的娇嫩、脆弱的女性形象。木兰意象的使用不仅为了让读者看到一个全新的灵魂,而是借此让读者感悟同样无声的木兰却能依靠自身的特性实现自身独立的最终目标。“成为自己”这一阶段肯定了女性自身的价值和主观能动性,通过对自己内心的认识和精神的感知从而获得新生,乃至获得真理。
结论
木兰是福勒女性主义思想的结晶,这位充满想象力的女性作家尝试着重构“花语”意象以表达自己不拘一格的思想,力求在性别压迫的社会现状下,以“花语”意象为依托构建“福勒式美国神话故事”,塑造一种尊重个性的独立女性观,引导女性向更佳的状态发展。福勒超越了传统意义上“花语”与爱和死亡之间的联系,频繁使用生动的对话体形式,强调个体间的差异性和交互性,多角度地展现女性从语言、形象到意识形态的特点,在自己的神话故事中讲述了“她”的故事。
福勒对“花语”意象的书写并非只是强调“成为自己”时用自身的成功转变爆发出“走向自立”的最强呐喊声,每一声呐喊实则都在无形中贯穿于从认识自我到相信自我直至成为自我的各个阶段;每一声呐喊都以不同形式存在着,它们或积聚或沉淀或爆发。福勒笔下的“花语”意象向社会呐喊出声声重要讯息:女性同样可以在气质和精神方面提升自己,成为具有个性的独立女性,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福勒对“花语”意象的塑造并非只是强调女性个体的成长,她的立足点关注到整个女性群体的发展,号召女性群体通过保持自立,从而实现男性与女性的和谐共处,促进社会更加完善。
作为一名思想超前的女性作家,福勒用自己的书写方式赋予“花语”以灵魂,从全社会、全人类的角度思考女性问题、解决女性问题。通过探究福勒的“花语”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女性长久的无声状态与理想的有力发声之间存在一条浩大的鸿沟。但她坚定地鼓励女性大胆跨越,在认识自我、相信自我和成为自我的过程中逐渐开启智慧、大胆质疑、更新观点。福勒的“花语”作品同时也为男性读者了解女性世界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通道,使大众从新的视角关注女性问题,成为促进沉默女性为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发声的强大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