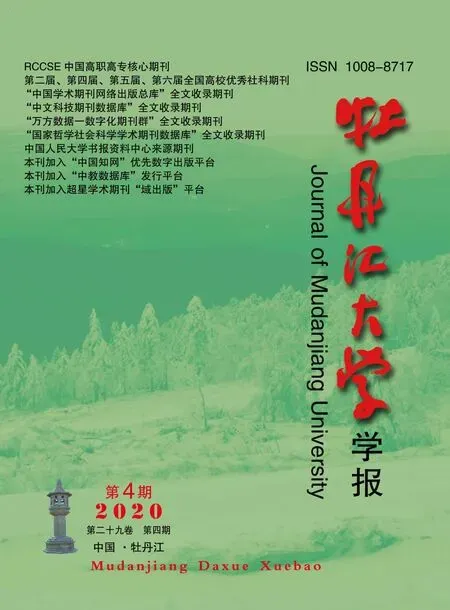时代背后的无声呼唤
——《陆犯焉识》的文本隐喻分析
2020-02-28张欣欣
李 英 张欣欣
(喀什大学人文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所谓隐喻,美国语言学家莱考夫等人认为:“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1]从另一个角度解释,隐喻是某一事物在特定环境下所暗含的另一种意思,即交流中产生的语言现象。同样,一名优秀的小说家不会将文本的潜在含义浮在表面,而是通过对特定场景中特定人物的描绘,来暗示具体时代背景下人物的现实生活。严歌苓在《扶桑》《小姨多鹤》《芳华》等多部小说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隐喻性”讲述方式,在《陆犯焉识》中,更是处处展现出高超的隐喻技巧。小说中,作者将“历史叙事”与“人物形象”结合起来,赋予人物特定的情感,使其拥有浓厚的历史记忆,给当代小说隐喻技巧提供可参考借鉴的文学价值与意义。
一、意象隐喻: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
从读者阅读的一般经验出发,小说以《陆犯焉识》命题,想必陆焉识在文本中必然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是细读文本,作者直接对陆焉识的正面叙述描写却少之又少。然而这并不影响严歌苓隐喻智慧对小说整体隐喻系统的建构,作者精心挑选了众多细小却耐人寻味的意象,留给读者解读文本和发挥想象的空间。
(一)荒凉自然环境:人生的无奈与多难
意象是现实存在的延伸物。它既可以作为一种描述存在,也可以作为一种隐喻存在。“如《诗经·桃夭》中的诗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盛开的桃花与新嫁娘之间有某种相似性,以桃花表示新嫁娘,就是隐喻。”[2]在《陆犯焉识》中,作者开篇就写道“据说那片大草地上的马群曾经是自由的”,但实际上文本呈现出来的却是“大草漠”和它周围诸如“祁连山的千年冰峰”和“昆仑山的恒古雪冠”意象构成的隐喻系统成为大草漠一景。作者选取“千年冰峰”和“恒古雪冠”两个独特的意象,从加入“冰峰”和“雪冠”自然性标志字眼中,为我们展现出大草漠自然环境的恶劣残酷。从描述的一系列自然意象中,读者便可察觉大草漠并不自由,而有层层无形的束缚,是政治钳制下犯人的日常生活。荒凉的自然环境就如同冷漠、冰冷的人性一般,时时压制着犯人。同时,对“马群羊群狼群大规模迁徙”“一大批罪犯见啥吃啥”等行为活动的细致描写,与其说是大草漠少见的一个生活迹象,不如说是那个年代日积月累形成的,几近墨守成规的,大草漠特有的生存常规。于外在故事叙述和描写的基础上,“冰峰”和“雪冠”作为自然物象,已经超越了描述的性质,犹如禁锢犯人的牢笼,将政治与人生互渗,使犯人一刻也无法懈怠,成为一种读者能感知的隐喻,让读者能顺着作者向下叙述的脉络,感受文本渲染出的压抑伤痛。
在对隐喻的建构中,严歌苓注重对犯人周围生存环境的描写。她在文中写道:“当时陆焉识跟管教干部邓玉辉正抬着一个冻死的犯人钻出帐篷,突然听见远处刷拉刷拉的响声:清亮的月光照在雪原上,几百只狼的灰褐色脊背滚滚地从低洼处涌动,滚成一股浊流。”[3]陆焉识同管教干部抬着冻死的犯人钻出帐篷,不经意间描述出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每天都有人死去。一个“冻”字,便潜移默化地暗示了犯人生存的艰难犹如特殊时代背景下不合理意识形态对人的瓦解与迫害。犯人即便死去,也只是抬出帐篷,任由野兽豺狼叼去的近乎荒诞的悲剧性命运,无形中显示出知识分子的激烈变故,从而引发读者对家国创伤的深思。从文本整体来看,极寒的天气便是政治悖论的隐喻。政治的是非与人生的是非相互缠绕,当政治与人生碰撞时,政治统帅着一切。而当陆焉识一类政治犯人面临严苛的自然环境时,他们或许坚持着最后的守望与等待,或许意识早已麻木与呆滞,或许还进行着人性最后的思考与回味;这些都是他们所面临的政治选择。
(二)动物被迫迁徙:“人”的“变异”与“悲惨”
“几百条狼的大迁徙。清亮的月光照在雪原上,几百只狼的灰褐色脊背滚滚地从低洼处涌动,滚成一股浊流。”[3]作者通过对几百只狼的大规模迁徙行为的描写,探究出像“陆焉识”一样的大批犯人来到荒漠后对原生态物种的伤害影响;展示出原生态动物对“失去自由生物”(罪犯)的惧怕而失去了它们在大草漠的千古自由。“活物被吃光,枯骨他们都吃”,让传统的动物感受到黑潮(一大批犯人)到来的凶猛,并且逐渐远离大草漠,开始迁徙之旅。“源源到来的大‘嘎斯’卡车让狼也待不住了,惹不起躲不起地开始了迁徙。”牺牲它们千古的自由,只为逃离这一群早已丧失人性的物种,从侧面展现出环境的恶劣冷酷,人性的变化莫测。狼本是荒漠之“王”,是暴虐和凶猛的代表物,而在丧失人性的罪犯面前,它们也惧怕不已。以“狼迁徙”隐喻自然环境的变异,让读者了解特殊时代背景下罪犯所处的艰难环境给人、给动物带来的无限磨难,让读者感受到西北荒漠的荒凉凄清,以及为后来一大批犯人逃离大草漠埋下伏笔,让读者逐渐感受到政治钳制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罪犯即使来到荒漠,也无法脱离现实处境,求得一份安稳。而那些难以承受自然挑战的犯人,最终只能默默死去。同时,一旦形成一个或多个像“狼群迁徙”这样的自然意象,它不可不受其他意象的牵扯和制约而独立存在,也不可以脱离传统环境的孕育而发扬光大,也就是说自然意象的存在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环境做基调,才能清晰描述当时的自然环境,发挥感染读者的作用。与此同时,“干旱的湖滩成了规模极大的坟场”,也暗示隐喻着大多数犯人经受不了残暴环境的摧残,渐渐死去,以“坟场”暗示罪犯的归宿,留给读者深深的沉思。
二、形象隐喻: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意识形态制约下的个人生存总是处于一种被摆弄的尴尬处境中。但古往今来又有无数知识分子为了夺取自己生存的希望,与不合理的现实政治搏斗以期回归原本美好的理想生活。小说《陆犯焉识》正是塑造了一个在主流政治话语扭曲的时代中,为重新回到妻子冯婉喻身边而不屈从荒谬现实中挣脱的知识分子“陆焉识”形象。严歌苓作为当代的一名小说大家,擅于从女性的角度叙写故事,而这部小说是严歌苓少见的,以男性作为第一叙事对象的小说,但它又与一般的“知识分子”小说不同。小说在人物形象的隐喻和艺术方式等方面都有着不可小觑的价值和意义。小说中,陆焉识是以一名“知识分子”的角色出现的,在小说前文中便介绍陆焉识留过学,会写文章,20岁便当上教授,可谓是天资聪明、才华横溢。但也正是因为几篇直抒胸臆、畅所欲言的文章使陆焉识被打上政治犯的旗号,远走大荒漠,在严苛的环境中,以犯人的身份度过了人生本该辉煌的时光。
“艺术形象与被表现对象之间的隐喻、象征关系具有直观具体的形似性、抽象间接的相似性。着重考察表现抽象情感、理念的艺术形象的隐喻、象征特点。”[4]小说隐喻技巧的运用,是小说成功的重要因素。陆焉识作为故事的主人公,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描绘陆焉识“知识分子”的形象。作为一名知识性人才,陆焉识并不敢违背恩娘的意愿,听从父母之命,迎娶了小恩娘冯婉喻。当婉喻进入陆家时,他烦闷、冷漠、无情、不把她当一回事儿,只是名义上将其当做自己的妻子。但不可否认,在这样的情况下,陆焉识却同冯婉喻生儿育女,潜在的隐藏了陆焉识并不是完全的讨厌冯婉喻。当进入大荒漠后,陆焉识开始回忆以往同冯婉喻的点点滴滴,偶然醒悟,自己最爱的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不在意的妻子冯婉喻。在小说中,作者反复强调陆焉识是在坐牢后通过回忆爱上婉喻的,这也许是对主人公的一番嘲讽。作为知识分子,性格与心理的弱点,让陆焉识不能认清现实,无法发现冯婉喻的美好与优秀,直到获罪发配到西北大漠,在非正常的生存环境乃至绝境中,才能明白生活的真谛,为其成长付出了惨痛代价。但在特殊的环境下,政治钳制着日常生活,平常人的执拗并不能改变什么。政治的是与非制约着陆焉识,只能在困境中,默默持续着文人的坚持与守望。于是乎,小说的主旨正如这本书的编辑张亚丽所说,严歌苓“将知识分子陆焉识放置在中国20世纪严苛的政治环境中,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传奇的个人经历熔于一炉,从而谱写了一曲政治与人性之歌”。[5]作者通过大量描写陆焉识在大草漠的生活常态以及身体心灵所遭受的非正常迫害从而悟出人生的真谛。有了陆焉识的成长,才有了后文陆焉识对冯婉喻的深厚怀念,想要在往后余生尽力弥补曾经留下的遗憾,却无法逃离始终错过的悲剧性命运。在小说中,陆焉识作为一名罪犯,他本能像刘胡子一样,默默的死去,也可以像梁葫芦一般,下贱的活着,但是这些都不是陆焉识的选择。在现实的背后,他想的只有一点,活着回到冯婉喻的身边,弥补曾经对婉喻的伤害。
当我们反复探究陆焉识这个“知识分子”形象时,发现陆焉识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知识分子”形象,而是一大群像陆焉识一样,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时代洪流而不得不遭受苦难的知识分子群像。也许每一个人不尽相同,但却不乏有相似之处,从中瞥见历史的一角,见识在荒谬环境下知识分子的艰难选择。我们从陆焉识的遭遇中看到的是一大批知识分子在巨大的创伤下,顽强不屈,不放弃,从而展现了一幅“知识分子”的成长历史图。
故事的叙述者是陆焉识的孙女冯学峰,在对小说的叙述中,远不能完整的把握故事的主要内核,但正因为此,陆焉识在大荒漠的遭遇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给文本留下一个个想象空间。文本的一开头便是陆焉识逃跑去厂礼部见女儿冯丹钰的叙述,作者采用倒叙的方式,将视角一下拉近,这对人物形象的把握多了一份感情色彩。陆焉识作为父亲,在面临逃跑被抓严惩的情况下,毅然找寻机会,历经千辛万苦去看自己女儿的演出,展现一个父亲对女儿深深的爱。但同时,作为一个政治犯人,陆焉识在明知逃跑的后果时,依旧坚持初心,又从侧面展现了像陆焉识一类的“知识分子”在面临政治的高压下,依旧会选择挣扎一番,而不是一味的服从强权,听从安排。正是从这一系列的事件中,一系列的形象刻画中,“可以将《陆犯焉识》谓之为‘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磨难史与家族史’”[6]从更深层的含义中把握小说的核心内容。
三、整体隐喻:政治与人生的互渗
小到意象,大到人物形象隐喻手法的使用,使《陆犯焉识》的文本构造了一个整体隐喻,引发了读者透过文本表层结构深入到深层的文化内涵对像陆焉识一样的一批知识分子进行反思和思考。“陆焉识”所隐喻的深层内涵是作为一种历经岁月洗礼沉淀而不断挣扎向上的知识分子形象,作为特殊政治背景下的被束缚人物要么在艰难的自然环境下默默死去,要么不断的在间隙中顽强挣扎,寻求逆袭的机会。这仿佛成为了老一代知识分子不得不直面的生存发展规律,正如人类的生存困境一般,是矛盾和荒谬的。这是政治背景下民众与社会洪流的关系,也是他们存在所面临的生存挑战。严歌苓正是怀着对老一代知识分子在特殊环境下寻求生存希望的终极关怀热望和思考。
作为知识分子的陆焉识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人们的关注与义不容辞的尊重与爱戴,但特殊时代背景下生存的现实困境,生活状况的巨大改变,让作为知识分子的“陆焉识”也不禁感到前途渺茫,无所适从。冯丹钰作为知识分子的后人,已经成年了,但却被迫因为政治犯父亲的原因,不得不放弃自己喜爱的舞蹈,干着自己不喜欢的职业。这孩子面对政治犯的父亲该如何选择,是该遵从孝道,原谅自己的父亲?还是为了自己的职业前途,断绝与父亲一切的联系?政治风云变化太快,让她来不及认真的做出选择,便作为政治的附属品,被生活折磨得丧失了热情。这样的政治选择困扰着陆焉识和无数个冯丹钰,将永远在生存中被思考和深思。这也是作者通过隐喻手法的使用所要引起读者对特殊环境下政治给人带来的苦难的深刻思考。
作为主人公,陆焉识则不仅带有大荒漠被困罪犯的集体意识,还有对未来政治变化和生存希望的个人意识。作为罪犯,陆焉识和梁葫芦、刘胡子都是同一属性的存在,被关在没有范围的牢笼里,每日靠着仅有的几个土豆过活。而陆焉识与他们又有所不同,他有了对未来出路的思考,对自己出逃计划的详细谋划,并且对冯婉喻深深的思念;正是以陆焉识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中进行摸索和寻求生存进行思考和探索的过程。陆焉识的存在,潜移默化的隐喻了那个时代一大批知识分子在政治洪流下的无奈,具有了过渡人物所有的二元性。他既是大草漠想要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代表,又是罪犯中的一员,每天在大草漠只能依靠稀少的食物维持生命。同时,他还有罪犯所缺乏的保护自我的先见性,利用口吃来伪装保护自我,来缓解人们对他的关注,在严苛的环境下,努力保持自己的尊严。然而陆焉识性格中的复杂性并未通过情节冲突凸显,而是通过种种日常行为矛盾来得以展现。如陆焉识在劳改农场的一个深刻场景,“用轮胎片把饭舀出来,这样可以吃得更多。”[3]陆焉识是何等知识分子,但却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这些无足挂齿的地方,明显展示出陆焉识一类知识分子命运的悲惨。
从一个个小的意象,再到陆焉识丰满的人物形象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政治对知识分子的摧残,隐喻时代风云变化之时,知识分子近乎荒诞的悲剧性命运。而知识分子的性格是扁平的,他们对国家,对人民都是忠诚不二的,他们遭受的磨难都是当时政治背景强加给他们的,但是他们无法反抗,只能不断牺牲,才能缓解社会的激烈变故,达到政治与人生的统一。而严歌苓通过对特定时代下坚持自我、怀有希望的知识分子形象陆焉识的书写,向那个暗潮涌动的时代投入了深深一瞥。在那个时代,陆焉识既是一个个体,同时也象征了一个时代坚持自我、与不合理意识形态做斗争的知识分子群像。在荒谬的时代和动荡的社会大潮中,陆焉识自始至终以顽强不屈、满怀希望的姿态挺立其中,他自身便是对时代的隐喻。
而整篇故事的构造,严歌苓是以自己的祖父严恩春作为原型创造的。虽然故事不乏夸大的成分,但也可从中了解那个时代人们现实境况的艰难,将祖父的人物情感赋予到陆焉识身上,以陆焉识的各种经历来凸显时代的变换给人们带来的不同程度影响,也间接隐喻了对那个时代的控诉。并且,作者也希望借用陆焉识这个人物形象,让读者更加深刻体会特殊意识形态下人们的现实生活,从而启发民众珍惜现有生活,努力奋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终身。
四、结语
“隐喻是心智的产物”。[7]小说题目本身就是一种双重隐喻,一方面既是指故事主人公这一类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则是暗指混乱荒谬的时代。小说借助人物形象的书写,指向了众多在特殊时代,被时代所遗弃,留下深刻创伤的一类人。以陆焉识、梁葫芦、冯婉喻等为代表的阶层,他们因为外在环境的特殊,自身情况的柔弱,一点一点被社会所吞噬,伤害;而具有坚强意志力的他们,在政治的洪流中顽强的活了下去,一步一步寻找未来的出路,生的希望。正是从陆焉识等一行人的命运中,我们看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逐渐失去社会价值,无法挣脱命运枷锁的深层原因,看到了无法改变现状的无力感和悲剧性以及环境对知识分子的压迫性。严歌苓的小说将这种悲剧性延展开来,在社会更替的变化中实现了对社会结构固化的批判。从而实现了从人物形象“隐喻性”角度对整个社会现状的揭示与反思,明白了老一代人们在特殊时代背后所隐藏的深刻文化内涵,留给人们深深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