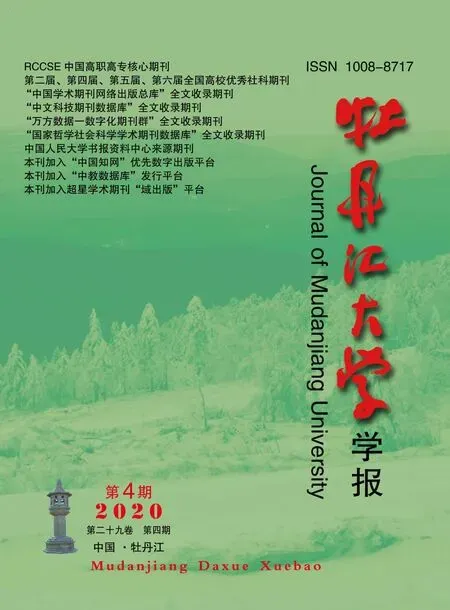《认罪书》:忏悔无力后的死亡救赎
2020-02-28袁雪
袁 雪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
一、文学中的“罪感意识”
“罪”这个定义不是中国人首创的,中国的儒道思想没有教人去检讨自身的罪恶,所谓的“每日三省吾身”,也是与道德教化和仕途经济挂钩,算不上是自我的深刻反省。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认罪”基因,孔子的“人性本善”论蛊惑了中国人数千年,既然性本善,又怎么会“犯罪”呢?横向纵观世界文学史,最早萌发“罪感”意识的是来自于17世纪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因贫穷和生计所迫,杀死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抢走了她的金钱和首饰,继而又狠心地灭口了她的妹妹,一系列的天时地利让拉斯柯尼科夫幸运地逃脱了法律制裁,但是却没能逃脱另一种惩罚——道德与良心的谴责。他虽然逃脱了罪,但是心灵上的惩罚却一直跟随,让他无法解脱,最后投案自首后才获得了真正的解脱。《罪与罚》中“罪感意识”的深刻性和反省性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独特地位,罪恶与惩罚是一朵双生花,犯罪的实施,惩罚会一直相伴左右。
有关“罪”的阐述,在《圣经》中也有所记载。基督教义中称每个人都是有“原罪”的,“原罪”是始祖犯罪所遗留的罪性和恶根,人人生来有罪,人必须带着这种罪感活着,来到尘世就是为了赎清罪恶。与“原罪”相对的,还有另一种罪——“本罪”:各人今生所犯的罪。要想赎清自己的“本罪”,中世纪教会以收纳钱财的方式作为“中间人”,向上帝传话,以此减免犯罪人的“本罪”,钱财的多少成了“赎罪”的衡量尺度。卢梭的《忏悔录》是真正有代表性的“罪感意识”自省录。他坦率真实地披露了自己的一生;忏悔了青年时期偷缎带事件;成年时期遗弃自己的孩子没有尽到父亲的职责;老年时期遇到从前有恩于他的心上人华伦夫人贫病交困而无动于衷,以及对杜德托夫人产生了不合时宜的爱情。在卢梭看来,他直言不讳本身就是一种补赎,只有洗涤了罪孽,才能正视那个迷途知返的自己。
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除《红楼梦》之外,普遍缺乏道德伦理约束下的忏悔罪感意识。周作人在《文学中的俄国与中国》中说:“俄国文学有一种特色,便是赋予自己谴责的精神。......在中国这自己谴责的精神似乎极为缺乏:写社会的黑暗,好像攻击别人的隐私,说自己的过去,又似乎炫耀好汉的行径了。这个缘由大抵由于旧文人的习气、以轻薄放诞为民流,流传至今没有改法,便变成这样的情形了。”[1]五四之后,以鲁迅为代表的罪感文学异军突起,发展迅速,《祝福》中体现最为明显。《祝福》里的祥林嫂想赎清自己的罪,让自己在阴间不被两个男人撕扯,以“捐门槛”来赎罪,祥林嫂的“罪感意识”也是封建伦理道德下的畸形产物,对于自己罪恶的认知更多的是封建伦理对她的施压,算不上深刻的自我剖析和正确认知。真正的“罪感意识”出现在巴金的《随想录》中对于“文革”的尖锐剖析,他的反思认识不是浅尝辄止,触及表面的,亲历者的直观感受用力拉扯着他的内心,他饱受煎熬地带有“罪感意识”去观照自身个体。经过“文革”十年浩劫之后,中国文学的罪感意识才真正出现。
刘再复在《论新时期文学主潮》一文中曾批评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文学存在着严重的弱点。从总体上来说,这时期的文学是“谴责有余”而“自审不足”,即缺少文学的忏悔意识。[2]这一时期,许多当代作家都开始从政治、社会层面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谈忏悔,谈反思,反思文学开始涌现。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古华《芙蓉镇》,张炜的《古船》都是此类文学的代表。上世纪80年代的“罪感文学”,作家的“忏悔”只限于他人,而不指向自身。莫言在一次谈到《蛙》这部作品时说:“从80年代开始,尤其到了90年代以后,“忏悔”,实际上变成了我们知识分子口边特别热的,特别俗的,最后要滥到泛滥成灾的那么一个词儿。每个人都在要求别人忏悔,甚至逼着别人忏悔,很少人要对自我进行忏悔。”忏悔成了一个热名词,作为70后的作家乔叶创作了《认罪书》,但缺少对于“文革”直接亲历观感,她没有对“文革”进行反复咀嚼,而是以对历史想象和追踪的视角,运用文学虚构,向内自我观照,创作这部作品。
二、“个体小恶”与“群体大罪”的双重交织
《认罪书》以金金这个复仇女神作为原点,以“个体小恶”照见了“群体大罪”。金金在去讨伐个体的仇恨时,牵引出了群体所犯的大恶。“个体小恶”与“群体大罪”拧成了不能解开的死扣,解开个人罪恶就必须探究历史的始末。要想寻找梅梅的身世,就会牵扯到上一代的恩怨与历史,看似碎片化的不同人物的回忆,多重叙述的口吻环环相扣组成了一个类似于探险追踪的故事,金金由个体的小的仇恨转化为对于整个家族甚至“文革”中施暴者的仇恨。她在这场复仇拉锯战中,像一个女战士,有着和梅梅相似的眉眼,带着前世今生的影子,去找寻她的前世,在找寻的过程中,她看到了梅好,梅梅,以及自己,因果循环在这里得到了印证。金金不同于单纯的梅梅和梅好,她有手段,有心机,不达目的不罢休,甚至还带有恶,不同的性格导致了不同的归宿。金金用她的手段直接或间接地让他们承认了自己的恶,惩罚的过程中自己身上也背负了许多的恶,她只能认识到他人的恶,却认识不到自己身上的恶。金金自己偷情,伤害梁知,不认哑巴做父亲,她对待亲情是冷漠和防备的,而且自以为没人知道她的恶,所以在书的封面上这样写道:“那时的我,嗜恶如命——当然,仅限于他们的恶。”“谴责有余”与“自审不足”的双面金金在“伐恶”和“犯恶”之间游走,欣慰的是金金在死前认了罪,向哑巴立了牌位。
“个体小恶”与“群体大罪”的双重交织,当众人的小恶聚集,就会累变成群体的大罪。梅梅与母亲梅好的毁灭就是群体沉默后的推波助澜。梅梅因为与梁知相爱,被后母张小英作为梁知的“晋升礼物”,送到了钟副市长的家里做保姆,钟副市长对有着和梅好相似眉眼的梅梅心生邪念,用手段玷污了梅梅,并答应给梁知获得了升官的机会。梅梅清白的牺牲却让梁知对她越来越厌恶,甚至直接用恶语刺激她,间接逼她自杀。他对于梅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不仅只限于梅梅,对金金他也是亏欠的,与金金偷情,生下安安,安安的生病离世和弟弟知情后的车祸而死,这些都是他所犯下的“罪”。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沉默是他的最大帮凶。对于母亲的“羊入虎口”安排的沉默,对于梅梅被玷污后的沉默,对于梅梅找孩子悲痛的沉默,到最后他发声了,这次的发声,就像是抹满毒药的利剑,直插梅梅心脏。他沉默地旁观着梅梅的死亡,就像梁文道看着梅好走进群英河一样,沉默地看着悲剧发生,以求自己的解脱。在这场对于梅梅的“杀害”中,每个人都难辞其咎。很多时候恶的升级正是因为旁观者的冷漠无情。秦红因为心里也爱梁知,所以她对于梅梅是嫉妒的,她推波助澜地对梅梅说:“只要给过了,那再给谁都一样,都没关系。”[3]秦红对于梅梅的错误引导,也使她一步步错下去,陷进去,单纯的梅梅开始对钟潮顺从,导致怀孕。梁新作为受害者和施暴者的双重身份,对于梅梅的死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对梅梅说尽了残酷的话,他对姐姐说出:“姐,我最后叫你一声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呢?”[3]梅梅被自己的弟弟伤透了心,丧失了活的信心。这样伤人的话语,他的话就像是已经上了膛的枪,等待着梁知去扣响它。包括在外地的打工仔赵小军,都是梅梅死亡的帮凶,他们见证着梅梅一步步向死亡迈近,甚至是她的幕后推手,在这场毁灭里,旁观者罪大恶极。
“看客”旁观罪恶,又不用对此负责。作为梅好悲剧事件的“旁观者”钟潮,他清楚地知道“旁观者”是不需要为罪恶买单的,他把自己由毁灭事件的参与者移到了窗外,成了“旁观者”。钟潮亲手帮助王爱民,让她把毛笔插入了梅好的身体里,在整个过程中,他都是亲眼所见并实施了行为。钟潮对于梅好身体的着迷,把这种畸形的迷恋转化到了梅梅身上,他玷污了梅梅,他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还把伤害代代相传,把伤害给了梅梅。在毁灭梅好的事件中,人人都有罪,但人人都拒不认罪。无论是沉默者还是旁观者,甚至亲身参与者,他们所做的都是洗净自己的关系,否认,辩解,拒不认错。“文革”并没有对他们有所惩罚,在毁灭梅好的过程中,甲乙丙也应该认罪,对于这些拒不认罪,归罪集体的人,正如参与者甲说的那样,他们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集体活动嘛,我也就是集体的一分子嘛,我这个平头老百姓还不就是跟着集体混嘛。跟着集体混的好处,就是不孤单嘛。咱要是对了是集体的功劳,咱要是错了是集体的责任嘛,是不是孩子?”[3]其实“文革”中,毁灭的又岂止梅好?个人不认罪,集体就无罪的心理,让造反派为自己的罪开脱,把自己的犯的大罪怪到集体和政策上,盛春风不停地为自己开罪,认为申明一直抓住他不放是为了博取关注和噱头,他急于想摆脱申明,便装出一副积极革命的姿态,摆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将过错向上推。“文革”浪潮过去后,法律上造反派并没有受到实质的惩罚,甚至从中获利,他们没有思想,道德上并不折磨着他们去赎罪,内心没有愧疚。双重的开脱让他们逍遥法外,怡然自得。就像张小英和甲一样,到最后还一直为自己狡辩。人类所以会不断重复历史错误,不断重演灾难性的悲剧,正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把历史罪责推到“替罪羊”身上,而自己却未从历史事件中汲取教训与道德营养。
个体小的恶与群体的大罪是分不开的,社会的冷漠就是因为沉默的大多数。申明引用了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无论谁死了,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3]沉默的大多数是由于集体沉默不发声导致的。集体无意识是群体罪恶的主要原因,荣格对于集体无意识有过一个这样的比喻:“高出水面的一些小岛代表一些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部分;由于潮汐运动才露出来的水面下的陆地部分代表个体的个人无意识,所有的岛最终以为基地的海床就是集体无意识。”[4]在大灾难过后,有一部分人开始觉醒,去认领自己的罪,如单姓老者,还有对恶追究的申明,他们被自己的恶所折磨,不愿归结为集体的错,自己主动认领自己的罪,但是大多数集体呢?他们忘掉了自己的罪恶,向虚无的“上面”和抽象的集体推脱。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在人的整个一生都从未被认识到。集体的沉默让罪更加悄无声息,集体的沉默想要造成的结果就是让罪永远不被揭开。“文革”并没有对他们有所惩罚,在毁灭梅好的过程中,罪恶总是跟随着善良单纯的人,善良成了犯罪者最好的土壤和养分。“文革”中的受害者正是这些单纯善良的人,不懂得变通的人注定会被时代吞噬,善良的人却不得善终。单姓老者年少时与同学一起欺负李老师,李老师一生清廉,关爱学生,作为李老师的得意弟子,虽然单姓老者站在外围,也不是运动的发起者,但也伸出了罪恶的手推了一把,他的内心一直饱受煎熬,幸运的是他的罪得到了认领,有了救赎,在最后他见到李老师,向他说了当年推他的事,心里的罪得到了认领,但并没有得到救赎。小说中间还穿插了一部分有关重建旅游胜地的荒唐事,在诉说“文革”那段历史时,曾经经历过的人能云淡风轻地用戏谑的方式讲述,还妄想能够用此发财,“文革”虽然过去了,但是当时犯下的恶与罪呢?《认罪书》的诉说力度要比想象中的强大,更像是暴风骤雨般的正面强攻。
三、罪与罚的死亡救赎:忏悔才是认领恶的方式
罗素认为:“有大型的历史学,也有小型的历史学,两者各有其价值,但它们的价值不同。大型的历史学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是怎样发展成现在的样子的;小型的历史学则使我们认识有趣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推进我们有关人性的知识。”[5]宏阔的社会大历史有其存在的价值,而文学更偏爱以个人的角度来建构属于个人的历史记忆。在一场灾难和悲剧来临后,对于复杂人性的变化与认知,更应该引起人的关注,作为主要的参与者,个人的心理烛照和态度更应引起深思。开篇的极力“伐恶”,正面强攻的态度去揭示罪恶,不留一丝的余地,但是在结尾处却没看到罪的归属,忏悔的缺席也是全篇的遗憾之处。
全篇的忏悔意识是在有罪者快要走向死亡,才开始出现,复仇者金金对于自己的赎罪意识更是如此。金金以惩他人恶为名号,最后自己却没有赎清自己的罪。《认罪书》的个体救赎的手段过于单一,死亡成了解脱的唯一方式。作者乔叶以这样的方式作为赎罪的终结过于仓促和表面化,死亡本身所要达到的救赎意义被弱化,死后的灵魂没有得到解脱。作者以认罪的方式开篇,却以无法救赎的方式结束,死亡的方式更像是作者在无力驾驭文本后抛向读者的一个新问题,她无法去惩治个人的恶,便让他们以各种死亡方式仓促的赎罪,无论是车祸而死的梁新,患癌症的张小英,甚至带着愧疚自杀的梁知,他们的死是无力而又苍白的,我们没有看到救赎本身,惩罚也只有死亡。除此之外,对于人性的揭露,她的关注度也不够,她更像是侦探而并不是医生,只“探病”不“医治”的态度,让小说本身也缺乏思想的深度。乔叶就曾在访谈时谈及:“她的创作无关政治,无关社会问题的解决,她只是对于个体在社会中心里活动感兴趣。”个人的政治生活、社会关系映照的正是整个时代人性的直观烛照。文学作品中的灵魂,归根结底,应当是个体的灵魂,也就是体现在每个生命个体身上的灵魂,而不是群体性的民族之魂。若将政治问题与人性进行全面分割,那么不同时代的人也将失去个体特性。在灾难来临时,具体的人性在时代面前更加突出。人性的恶是没有边界的,只认罪的程度达到的是表皮的先觉醒,觉醒后难道还像鲁迅笔下先觉者无路可走的绝望吗?乔叶想驾驭故事,但被故事驾驭了自己。
个体在以自身的方式救赎上,无一都指向了死亡。梁知则怀着对于梅梅的亏欠,对着有着和梅梅相似脸的金金无限的宠爱,看似在赎上一段的罪恶,实际上自己又犯了一宗罪,这宗罪的惩罚就是弟弟的车祸死亡和安安的配型失败离世,沉重的打击之后,他无法选择,只能去死,死亡是他走向新生的方法吗?忏悔意识与灵魂的自我对话,就像他在最后说的那样,“人如果有罪的话,是不能自己原谅自己的。自己原谅自己,这是不行的”。[4]梁知的死亡救赎是亲人接二连三离去后的无力与失望交织,他承受不住现实的惩罚,死便成了唯一解救方式。在走向死亡之前,他的忏悔意识乍现,他将带着这样的心走向新生。而无罪的“梁新”,也难逃死亡的惩罚,他被最爱自己的哥哥和自己最爱的金金同时欺骗,沉浸在被编织的美梦里,梦醒后注定无路可走,现实的巨大冲击让他无力承受,只能走向死亡。张小英也无反省意识,一直为自己辩解,她自以为得病死亡之后把房子和遗产留给金金,就赎清了对于梅梅的亏欠,却从未实现自我的救赎。
个体的恶的不追究,死亡成了唯一救赎方式;群体“恶”的终点通向遗忘,而不是心灵自我的真正认知。正如巴金在《随想录》里说:“那么回头看‘文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它的遗迹?才过去二十年,就有人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看作是遥远的梦,要大家尽早忘干净。”[6]《认罪书》的出现何尝不是一种提醒呢?历史会过去,“文革”遗留的危险精神却没有完全消失,历史的罪开始向现世罪转移:环境污染,“瘦肉精”事件,虚假新闻的随意报道,“文革”故地被重新打扮成为旅游胜地。“文革”以一种危险的因素影响着现世生活,因缺乏罪感意识,救赎和忏悔还很遥远。只有真正地了解才能抵达罪恶本身。也许,只有先去真正的理解,才能抵达真正的谴责。我们所讲的忏悔意识,便是无罪之罪的意识。这不是法律所指向的罪,是属于自身心灵的“罪感意识”。申明在访谈后所说的“我相信,如果有一天,有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忏悔,就会知道,忏悔所意味的绝不仅是个人良知,也绝不仅是自我洗礼和呵护心灵,更不仅是承认过错请求谅解的姿态,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忏悔意味着我们自身的生存质量,意味着我们对于未来所负起的一种深切责任。”[3]“文革”的错是私欲和政治交织产生的恶,时代怂恿着人犯恶,为他们撑起了保护伞,施暴者便可以为非作歹,胡作非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平时自己不敢欺负的,尊敬的人变成了低一级的人,人人都可以踩上一脚,说上一嘴,灾难面前,人人的小心思就显现出来了,拼命抓住这个机会,争着举报打倒。乔叶在书写“罪”的时候,泥沙俱下,狂风暴雨,她像是一个英勇的战士,手拿利刃拼命惩恶,但是对于认罪后的自我救赎和心里描写层面关注不够,难免虎头蛇尾,用力过猛。而且在救赎上的力度和方式上太过于苍白无力,恶的惩戒不是罪的终点,“认罪”—“赎罪”—“忏悔”的结构意识并没有贯穿全文,认罪后,却不救赎,罪恶没有得到归属,死亡的方式不是解脱,忏悔才是最终的救赎。只有认清罪恶,抵达忏悔才能获得救赎。
四、结语
乔叶作为一个70后的作家,虽然少了作为亲历者经验书写的遗憾,但难能可贵的是她能站在追踪者的角度,运用文学的虚构与历史的认知结合后产生新创作,再认识“文革”对于当代的现世意义。作为“文革历史”间接非直观的再书写,忏悔意识的重建和人性的深度挖掘,《认罪书》跳出了作为一个女性单纯的复情仇的简单故事,由个人的复仇作为原点,所引起对于历史和时代的追罪,是其金玉所在。灾难后的创伤感不止局限于短暂的十年,时时的阵痛会伴随着整个中华民族去回望历史。在灾难面前,没有人能够完全袖手旁观,强大的民族更要坦诚认罪,懂得忏悔。《认罪书》作为当代文学中少数的异类,敢于认罪,懂得忏悔的姿态更是难能可贵,知罪后认罪,懂得认罪,才能更好的直射人性,照亮人心。《认罪书》无疑也为中国的当代忏悔文学的进步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