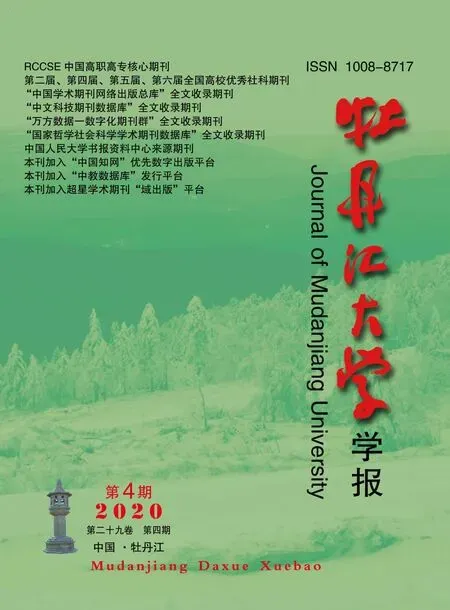从集体到个人:新中国家庭生活的变革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读书札记
2020-02-28张融
张 融
(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一、引言
从人类整体的历史发展来看,家庭生活历经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也即家族依附性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个人不断代替了家族,成为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1]96-97在此过程中,个人的地位得到了不断地彰显,个人逐步成为法律所考虑的主要对象。然在部分西方学者看来,此过程并不适用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他们认为自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家庭生活便成为合作社模式,也即家庭是由完全理性的,明白自己利益之所在的成员所组成的经济单位,所有人的收入都必须投入家庭的大锅里,不得单独开小灶。[2]15简而言之,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步消减,取得代之的是集体主义或家庭主义。对此观点,美国加州大学阎云翔教授在其著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中并不这么认为,其通过常年累月的田野调查发现,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家庭生活中,其也正在经历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
二、中国家庭生活的变革
阎云翔教授在其著作中选取了中国黑龙江省下岬村作为田野调查点,其通过访谈以及亲身经历,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即便是集体生活对家庭生活产生了巨大地影响,其也难以改变整个人类历史上“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规律。在此规律中,个人的地位得到不断地凸显,具言之,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结婚对象的选择上,个人的意愿逐步得到重视。在建国前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下岬村的青年人在结婚对象的选择上主要是遵循父母或家庭的意愿,换言之,村里的年轻人对婚姻无自主权,婚姻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安排的。[2]63在当时的婚姻中,父母对后辈的婚姻具有无上的权威,即便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开展相关的个人解放运动,年轻人也没有争取到多少婚姻的自主权。[2]63此种以家庭为主的婚姻直至上世纪60年代后期才逐步消解,这是个人解放政治运动持续开展的必然结果,传统宗族主义的旧观念被逐步破坏,个人权利在此逐步得到彰显。阎云翔教授对此总结到,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后,个人意愿在婚姻缔结中逐步占据主要地位,即便子女与父母的意愿相左,子女的意愿往往仍会占据上风,而父母没有子女的同意一般是很难逼迫其结婚的。[2]70这种个人主义倾向在改革开放以后更加凸显,在婚姻缔结中,父母的意见已形同虚设,子女可以完完全全地决定他们自己的婚姻,假使被外部势力阻挡,他们可能还会选择私奔。[2]72-73
其二,在家庭结构中,逐步以平等的夫妻关系为主。传统的家庭结构一般为主干家庭,也即家庭中至少包含着两代人的家庭。在主干家庭中,一般往往是作为长辈的父母当家,在家庭关系中则体现为以父子关系为中心。[2]128在此之下,各家庭成员的地位并不平等,父亲具有极大地权力。此种家庭结构一直存续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随着政治运动的持续开展以及经济的发展,一种更为简单的,以夫妻关系为中心的家庭结构开始产生。[2]107此种家庭结构又可称之为核心家庭,夫妻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而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2]130在此家庭中,夫妻双方的个人意见往往是家庭决策的主要来源,依据个人能力的不同,在核心家庭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性别分工,在此之下,主内或主外的一方一般为男女双方中的一方,这样可以有效避免意见相左时的冲突,从而维护家庭的稳定。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过程中,妇女的地位得到了不断地提高。
其三,在住宅的设计上,个人隐私权不断得到重视。从整体上说,在改革开放之前,下岬村在住宅设计上并无个人隐私可言,具言之,整个家庭基本上由一个大通铺组成,一般是一家子人挤在上面,包括吃饭、玩耍等在内的家庭生活都在通铺上进行,每个人在通铺中有固定的位置,年老的家庭成员一般睡在通铺靠近炕头的位置。[2]136室内的私人空间缺乏,每个人的生活都暴露在其他人的眼皮底下,但大家并无不好意思之处。[2]137此种住宅布局直至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以后才有所转变。受到城市住宅建设布局的影响,下岬村的住宅设计也逐步改变了以往没有个人隐私的通铺布局,在住宅布局中出现了客厅和房间,同时火炕的面积也有所缩小以便为房间腾出空间,这使个人拥有更多的私密空间。[2]140-141自从客厅出现以后,公共生活对家庭的介入也仅限于客厅之中了,与公共事务相关的事情一般在客厅中进行,而房间则成为了个人的“独立王国”。对此现象,西方有学者认为这是之前中国受家族文化影响的缘故,但阎云翔教授认为,这实质上是经济影响的结果,因为即便在传统家族文化占主流地位的社会,经济较为优越的精英阶层在其住宅设计上仍会有诸多的房间以确保必要的隐私,换言之,隐私是君子的特权,从来都不会下至理应受治于君子的庶人,阎云翔教授对此总结为隐私的阶级差异。[2]158-159
其四,在家庭财产分配上,个人财产逐步从家庭集体财产中析出。个人财产的析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彩礼的支配上,二为分家。传统上,男女双方结婚所得彩礼一般由大家庭支配,换言之,彩礼通常是从新郎家向新娘家转移的资产,它的作用在于敲定两家之间的婚姻契约,而使妇女从一家转手到另一家。[2]172这是结婚家族本位的体现,在此个人意愿不仅在婚姻缔结中难以得到彰显,而且对于婚姻所得财产亦无支配权利。自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批判家长权的政治运动的持续开展,彩礼不再是两个家庭之间礼节性的礼物交换或者支付手段,而是财富从上一代到下一代转移的新途径。[2]181换言之,结婚彩礼所得一般由婚姻缔结的男女双方支配。与此同时,由于集体化运动的开展,家庭中原有的私有财产被集体化,每个人的个人劳动都被记成工分。[2]183在此之下,青年人的劳动工分显然比老一辈的父母要高,这使其在家庭关系上不再听从及依赖父母,由此不仅促进个人意识的觉醒,而且也导致了分家的提前化。这与传统中要求人们尽可能推迟分家的时间相悖。[2]166此种从父居传统格局的改变实质上是个人意识觉醒和父权衰落的结果,其使年轻人敢于挣脱家庭的束缚而去追求自己的生活。
其五,在老人赡养方面,孝道逐步衰落。随着个人主义在下岬村的持续影响,在村里出现了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的的思想,这使传统家族主义中的一些优良传统被舍弃,在其中体现得最为典型的是孝道的衰落。在中国历史上,孝道一直被奉为治国之本,国家的法律保护老人对下一代的权力,这是家族主义的使然。在此之下,父母可以告儿子不孝而不需要任何理由。[2]208这使子女不敢置父母于不顾。虽然现行《婚姻法》亦强调了孝顺的重要性,但是受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法律的规定在实践中难以获得实效,其中的一个原因亦在于在此方面的制裁措施较少。这直接导致了下岬村不孝子女的增多。从阎云翔教授的访谈来看,不少子女不同意生孩子本身是恩情、儿女需要终生报答的观念,父母一旦把孩子生下来,就有责任把孩子养大。[2]200在此舆情之中,孝顺父母不再被视为一种责任与对恩情的回报,父母养育子女仅仅是一种自然行为,为人父母显然已经失去了过去那种至高无上的神圣与权威。[2]200
三、中国家庭生活变革的主要因由
从上述的家庭变革来看,下岬村的家庭无疑历经了一个从家族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过程。此过程不仅在下岬村出现,而且在中国的其他乡村亦有存在。对此,阎云翔教授将此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政治和经济的影响。
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历次打破传统父权的政治运动,国家鼓励青年人去和传统的父权观念作斗争。[2]264但由于集体主义的存在,即便在建国伊始对父权的强烈批判,个人也并没有在公共领域中获得多少独立的自主权,在集体劳动生活和户口的制度下,个人从原来依附于家庭的父权转换为依附于集体组织。[2]264这为以后个人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农村中原有的集体公社转为家庭生产,公共权力对私生活的过度介入突然减少,这使家庭领域中的关系调整出现权力真空,原有传统的父权制度被消灭殆尽,而又未有新的权力加以介入。此时受外来的个人消费主义、电视文化中个人主义等因素的影响,个人欲望合理化现象出现,在此过程中甚至出现了极端的个人主义。[2]265阎云翔教授认为,如果农民能够在权力真空阶段参加公众生活,或许这就有可能产生另外一种在强调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强调个人对公众与对他人之义务的个人主义。[2]265
经济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变革上,这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的体现。具言之,经济基础对于理念等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是这些上层建筑存在的根源,是第一性的,这些上层建筑不过是经济基础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表现,是第二性的。[3]482也即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将会有什么样的理念。在家庭生活中之所以会出现个人价值逐步凸显的过程,实质上可以归因于经济的发展,例如在前述核心家庭的产生上,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工业化与都市化所导致的大家庭解体,具言之,经济的发展使家庭与其它亲属单位变得疏远,家庭关系主要集中在核心家庭的夫妻同孩子身上,父权家庭在此逐步瓦解。[2]130又如随着现代经济模式的建立,生产效率较之于以前有了更大的提高,个人不再局限于土地之中,这使家庭共同财产的来源渠道更为广阔,而传统中以上一辈财产继承为家庭财产主要来源的方式逐步消解,这使长辈对晚辈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降低,对此有学者总结到,倘若家庭的财产是阖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父亲的地位就会大大下降。[2]183这也使得个人的价值得到了更多地彰显。
可见,家庭生活的变革并非自发产生的,而是由政治和经济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从根本上说,经济因素在其中起决定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不同政治制度下存在相似的社会发展过程的根本原因所在。此发展过程诚如英国法学家梅因所总结的,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也即是一个个人价值得到不断彰显的过程。
四、中国家庭生活的未来发展
从整体而言,全书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通过分析下岬村家庭生活的变革,借以推断整个中国的家庭生活变革。对此变革,阎云翔教授总结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国家推动了私人生活的转型,并由此出现了近年来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的急剧发展,这种家庭文化的新型个人在最大程度追求个人权利的同时,却忽视他们对社会或者他人的道德责任。[2]243对于家庭生活的未来发展,阎云翔教授认为,未来这种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割裂还要继续下去。[2]266换言之,个人主义仍将会继续影响家庭生活。对此观点,本文亦不否认,但认为未来家庭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应为有限制的个人主义,也即是一种兼及社会利益的个人主义。此为经济发展的规律使然。随着经济持续地发展,对个人自由的过度放纵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由此在世界一些发达国家中,出现了以社会利益为名义限制个人自由的法律。在此也逐步影响到家庭生活领域,在其中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出现最为典型,而这在我国的婚姻立法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婚姻法》第2条特别规定了儿童利益的保护原则,第36条规定了离婚自由在子女利益面前的限制等等,相信此种对社会利益兼顾的理念在未来将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更广泛地影响我国的私人家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