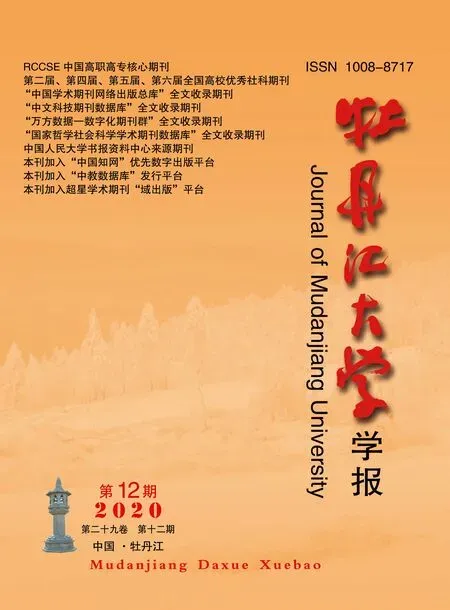贾平凹《高兴》英译本中乡土语言模因英译研究
2020-02-28刘红见
刘红见
(西安翻译学院英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5)
一、引言
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国家战略。而中国文学的翻译传播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主要载体,乡土文学是中国文学主要组成部分,乡土文学主要通过乡土语言表征来呈现,因此,乡土语言的翻译对中国乡土文学对外传播起着重要作用。贾平凹是中国当代乡土文学代表人物,贾平凹作品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都具有浓重的地方色彩,尤其是陕西地方方言土语的使用。[1]方言土语的使用体现了作品的乡土风格,乡土语言的翻译是乡土文学作品进入异域文化的关键。[2]国内学界有关贾平凹及其作品探讨成果丰盈,但对作品中乡土语言翻译研究数量太少,而且没有形成专题性、系统性研究。本文以翻译模因论为理论基础,以贾平凹《高兴》中乡土语言为研究对象,梳理英国汉学家韩斌(Nicky Harman)翻译贾平凹《高兴》(Happy Dreams)英译本中乡土语言的翻译策略,总结行之有效的乡土语言翻译策略,以期推动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海外传播。
二、乡土语言及其翻译研究现状
乡土语言是乡土文学的精髓,研究乡土文学的翻译势必会遇到乡土语言的翻译问题。乡土语言指具有地方特征、通俗精炼并流传于民间的语言表达形式,乡土语言蕴含了谚语、熟语、方言、惯用语、歇后语、俚语、成语、格言和警句等,乡土语言是对于这些说法的高度概括。[3]笔者认为乡土语言的基本表征是乡土色彩,重点体现在“土”和“俗”,“土”和“俗”能够凸显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叙事特色。谢天振阐述“土的掉渣的语言让中国读者印象深刻,但是翻译后它的土味荡然无存,不易获得目标语读者接受和传播效果。”[4]因此,怎样才能有效的传译文学作品中乡土语言,学界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者首先肯定了乡土语言翻译的研究意义,但对文学作品中乡土语言翻译研究只有寥寥数篇。汪宝荣(2016)阐述中国当代乡土小说乡土语言英译原则和策略。[5]周领顺(2017)从葛浩文以中国译者对比的视角探讨汉语乡土语言英译的译者模式。[6]任东升(2017)从审美理论的视角分析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乡土小说乡土语言表征,指出乡土语言英译策略。[7]冯正斌、党争胜(2019)以葛浩文译贾平凹作品《废都》英译本为例,探讨译本中乡土语言前景化翻译策略。[8]综上所述,学界从译者对比、审美、前景化等理论视角来探究文学作品中乡土语言的翻译问题,但尚未有学者从翻译模因视角来探析贾平凹《高兴》英译本中乡土语言翻译。本文将聚焦翻译模因视阈下贾平凹《高兴》译本中乡土语言的翻译策略,旨在推动多维视角下的乡土语言翻译研究,助力贾平凹作品对外译介传播。
三、乡土语言模因的翻译传播
模因是类似基因的基本遗传单位,是文化传播单位或模仿单位,是文化进化中的复制因子。[9]作为研究模因的理论,模因论是关于模因这个文化信息表征单位及其系统的复制、传播和变异规范的系统理论。模因论揭示了文化进化的规律,研究模因及其传播规律就是研究人类文化及其进化规律,模因论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进化论。[10]语言是模因的载体,作为文化复制单位的语言模因,靠传播而生存,任何形式的词汇、句法、语义及语篇经过复制和传播都有可能成为语言模因。语言模因要进行跨文化传播和交流需要借助翻译,翻译是语言模因跨文化、跨疆域生存载体,于是就有了翻译模因。
切斯特曼把模因论引入翻译研究,他指出翻译研究就是模因论的一个分支,翻译模因、翻译规范、翻译策略都可以看作是翻译模因理论,翻译过程就是原语模因以译文为表达方式向译语模因传播过程。也是翻译模因经历遗传、解码感染、编码和传播的翻译过程。根据切斯特曼观点,何自然将翻译模因类型分为基因型和表现型,前者是指源语模因至目标语模因转化是一种等值等效过程,后者是指原语至译出语转化是非对等的复制传播。[11]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乡土语言就是一种语言模因,在乡土文学的翻译中,翻译首要任务就是乡土语言的模因化。[12]根据翻译模因类型,乡土语言模因化主要取决于译者是留存源语模因的内容,还是使译文面向目标语读者。乡土语言的翻译一方面要求译者尽可能保留源语文化的内涵,另一方面寄希望译者能把源语模因的文化精髓被目标语读者理解、接受和传播。因此在乡土语言翻译过程中追求源语模因与目标语模因等值等效传播,是乡土文学得到有效传播的根本要求。
四、《高兴》英译本中乡土语言模因翻译策略分析
《高兴》是一部典型的乡土文学作品,于2007年出版发行。作品主要讲述刘高兴和朋友五富进城务工,成为拾荒者的故事,揭示了工业化背景下农村土地流失,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社会问题,小说体现了作者一贯对底层人物角色关注。小说故事生动,人物形象逼真,人物语言和叙事语言带有浓郁的乡土色彩,方言、俗语、谚语、俚语与惯用语等乡土语言模因贯穿于作品之中。英国翻译家韩斌(Nicky Harman)翻译《高兴》(Happy Dreams),并 与2017年10月 在Amazon Crossing出版发行。
翻译策略是译者寻求产出符合规范译本的方法。翻译策略也是翻译模因中的一种,被译者广泛应用并成为翻译领域的标准概念工具。翻译模因中翻译策略涉及句法、语义和语用策略,句法策略包括直译、借词、移位、单位转换、改变词组结构、改变句子结构等。语义策略包括使用同义词、反义词、改变分布、解释等其它语义策略。语用策略包括文化过滤、局部翻译、编译、省略等其它语用策略。[13]笔者以韩斌《高兴》英译本乡土语言模因为研究对象,基于Chesterman 翻译模因论翻译策略类型,结合译本中的方言、熟语、俚语、谚语、惯用语及典故模因为例证,分析归纳乡土语言模因翻译策略如下:句法策略下直译翻译法,语义策略下的意译、解释、套用及语用策略下文化过滤翻译策略等。
(一) 乡土语言模因的直译法
模因直译法是指在目标语模因库能够直接找到源语模因中文化意象,是源语模因至目标语模因等值等效传播,属于翻译模因的基因型翻译类型。《高兴》中蕴含丰富的谚语、俗语、成语及惯用语模因,承载着乡土小说中特殊的文化内涵,译者韩斌采用了直译模因的翻译策略,将留存源语模因的“异质性”当成翻译的最高标准。如例(1)(2):
(1)如果我不蹬着三轮车,谁也看不出是个拾破烂的乡下人,说我是不显山露水,说我是藏龙伏虎,说我绝不是地上爬的卧的角色。[14]215
译文:If I wasn't on a three-wheeler, no one would know I was a trash picker from the countryside. There was more to me than met the eye. I was a crouching tiger, a hidden dragon, not some earthbound.[15]227
(2)因为我还没有与他很熟,远亲不如近邻,为了能与他和平相处,我还得观察他。[14]31
译文:I didn't know him too well yet. I felt I should keep him under observation for a while, and after that we could live in peace and harmony—as the saying goes, a good neighbor is more useful than a distant relative.[15]64
例1中的“藏龙伏虎”是成语模因,句中的“虎”和“龙”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有与其相对应文化意象的表达“tiger”和“dragon”。例2句中“远亲不如近邻”是一句典型的俗语模因,译者采用直译模因翻译策略传递了源语的文化内涵。而且,《高兴》中出现具有本土特色的地点名称,译者也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如:清风镇(Freshwind Town)、芙蓉园(Hibiscus Garden)、塔街(Pagoda Street)等。再者,作品中蕴含若干与陕西特色饮食文化相关的表达,译者也同样采用了翻译模因直译法,例如:面汤(noodle water)、胡辣汤(pepper soup)、油泼辣子(chili oil)、冰峰汽水(ice peak soda)等。译者韩斌采用乡土语言模因直译法将陕西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模因精髓有效传播开来。
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乡土语言模因直译法不仅能够传递源语模因形式和意义,而且能够使原语和译语在语义和语用上实现等效传递,能够使译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最终实现乡土文学作品的译介和传播。
(二)乡土语言模因的意译法
意译模因法是传达原语模因的含义而不拘形式的翻译策略。传达原语模因涵义是指再现原语模因的语理意义和语用价值,不拘形式是指保持原语的宏观结构表征,不受原语微观语言结构的束缚,达意重于保形。意译模因法属于归化策略下的翻译方法。熊兵(2014)指出意译法可以细分为两类: 解释法(译者对原语进行解释性翻译,但不是用目标语习惯用法来代替原文的词句)和套译法(借用目标语习惯用语来代替原语的词句)。[17]译者韩斌在翻译《高兴》中方言、俗语及成语时经常采用意译模因的翻译策略。具体如例(3)(4):
(3)八竿子打不着我 。[14]197
译文:Well, I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 What happened then?[15]214
(4)她说:跟啥人学啥人,我这也是拾破烂吗?我说:我请你吃饭![14]230
译文: "You know what they say; Birds of a featherflock together. Does that make me a trash picker too? "I am taking you out to dinner!"[15]368
上述例证中“八竿子打不着”是指二者关系疏远或者毫无关联。“跟啥人学啥人”形容环境对人的影响。译者在例3、例4中乡土语言模因分别采用了意译法下的解释法和套译法。这类方言土语源自普通百姓的民间生活,富含浓郁的乡土色彩和地域文化特征。也凸显了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和贾平凹的语言风格,贾平凹出生在商洛农村地区,乡土语言特征已经成为贾平凹文学作品的显著标志。《高兴》中的人物刘高兴和五富来自作者的故乡,其语言表达也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其中人物姓名的乡土气息通过意译法也充分体现出来,不仅译出人名本身的文化内涵,而且也让目标语读者感受到原文中人物特征,如瘦猴(Scrawny)、杏胡(Almond)、石热闹(Lively Shi)、种猪(Goodlies)等。韩斌曾坦言《高兴》翻译过程中的棘手问题之一是以主要人物刘高兴为代表的城市底层拾荒者的人物角色以及在译人语中恰如其分地表述文中大量的人物对话。[18]韩斌面对这些独具特色的人物性格表征及人物对话的乡土语言模因时采用了以“读者为归依”的归化翻译策略,不仅降低了源语模因中文化内涵的陌生化,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而且便利目标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三)乡土语言模因的文化过滤法
文化过滤是比较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文学交流中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对交流信息的选择、移植和改造,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影响时,接受方创造性接受而形成对影响的反作用。[19]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简单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而文学翻译中,目的语文化会对源语文化中的价值、信仰、风俗及典故等进行文化过滤,自然而然造成源语文本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改变。译者为了减少目的语读者阅读翻译作品的荆棘和整体的阅读体验,韩斌采用了文化过滤翻译策略,如例(6)(7):
(6)杏胡说:我只说我是苏三的苦, 没想还有个窦娥的冤![14]261
译文:"I thought I had a hard life,"Almond said. "Imagine there being another tragic beauty!"[15]182
(7)其实我说刘备是神来之笔,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各行各业的神,木匠敬鲁班,药铺里敬孙思邈,小偷敬思迁,妓院里敬猪八戒。[14]142
译文:Actually, it was divine inspiration that made me think of Liu Bei. Every trade has its patron saints, carpenters, pharmacists, thieves, they all do. Even brother keepers and hookers have Pigsy from the novel Journey to the West.[15]213[16]
译者在例(6)和例(7)中主要运用了文化过滤翻译策略,例(6)中过滤了源语中窦娥冤的典故。例(7)中的主要人物“鲁班”“孙思邈”“思迁”和“猪八戒”被文化过滤掉,但却保留了西游记的典故,从表面来看译者缺乏系统性翻译策略,但是事实上反映了译者所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及整体翻译观,为了让目标语读者领会源语模因文化内涵,保证目的语读者阅读效果和阅读体验,灵活运用文化过滤翻译策略对原文形式及内容作出改变,使译出语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源语文本的文化精髓,最终实现文学作品中乡土语言模因的跨文化传播。
五、结语
本研究基于Chesterman翻译模因论中翻译策略类型对贾平凹《高兴》韩斌译本中乡土语言模因的翻译策略进行探究。研究表明,《高兴》英译本中乡土语言模因的翻译主要以意译和文化过滤为主归化翻译策略和直译为辅异化翻译策略,充分展示了译者尊重源语文本的风格及文化内涵,同时也表明译者以目标语读者为中心,充分照顾到译出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兴趣,使独具匠心的陕西乡土语言模因被目标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在“中华文化走出去”和“文化自信”大背景下,研究贾平凹《高兴》中乡土语言模因的英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陕西文学“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