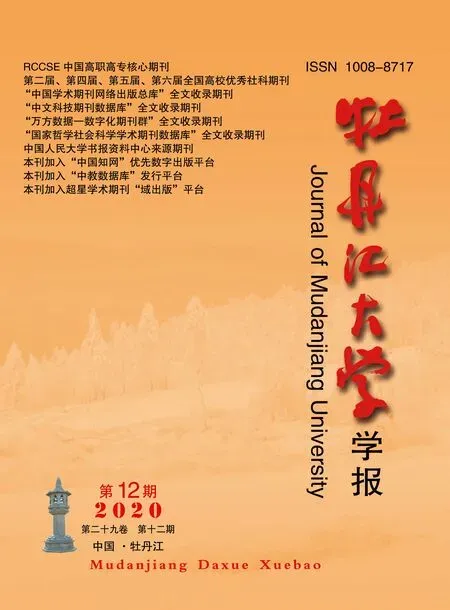文学文体学视角下小说翻译假象等值解析
2020-02-28杨卉卉
杨卉卉
(三江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2)
引言
文体学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是一门研究文体的学科,其最大特色是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文体特征。法国学者巴依(Bally)是西方现代文体学的开创人,他的研究对象是口语中的文体。德国文体学家斯皮泽(Spitzer)被尊为(文学)文体学之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1958年雅各布森(Jakobson)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召开的“文体学研讨会”上宣称:“倘若一位语言学家对语言的诗学功能不闻不问,或一位文学研究者对语言学问题不予关心,对语言学方法也一窍不通,他们就显然过时落伍了。”这次研讨会是文体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文体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诞生。在我国,早在1963年王佐良就发表了《关于英语的文体、风格研究》一文。而随着西方文体学的蓬勃发展,文体学流派纷呈,如“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话语文体学”“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文学文体学”“语言学文体学”等。我国学者也对西方文体学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不断地对文体学各流派的发展成果进行梳理,加入到国内的文体学研究中来。
一、文学文体学和小说翻译
文学文体学是连接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桥梁,它是以阐释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为目的的文体学派,集中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1]通常认为,文体是“由特定的人为了特定的目的在特定的语境下使用的语言方式”[2],而本文对文体的定义是“对主题意义和审美效果有动因的选择”[3]。将文学文体学应用到小说翻译中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也有其理论依据。文学文体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文本,不拘泥于使用哪一种特定的语言学方法,集中讨论的是文学作品在语言表现形式上的特征,结合文本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帮助读者从语言技巧和思想内容的关系这个角度去更加深入地理解、合理地解释和充分地欣赏作品”[4], 也可以帮助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更好地认识语言形式和文本内容之间的关系。
在文学文体学的视角下,小说翻译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堪称“假象等值”,它指的是“译文与原文看上去大致相同,但文学价值或文学意义相去甚远”[5]。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在进行小说翻译,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翻译时,通常不会特别在意其语言表达方式,因为现实主义小说相对现代主义小说而言,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并不是特别的偏离常规,并不能够引起文体学家的注意,也使得译者将关注的目光主要放在文中的“可意译的物质内容”[6]上, 却“往往会忽略语言表达形式本身的文学意义,把能够传递了同样的内容和意义作为判断等值的标准”[5]。小说的译文虽不乏精彩之处,但读者很容易被译者的文采蒙住了双眼,作出主观印象的判断。但需要指出的是,常规的表达方式亦有其文体特征和功能,而在翻译中如果忽视这些文体特征和功能,就会忽略这些文体特征对凸显主题意义和实现审美效果上的作用,很容易造成假象等值。申丹在《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一书中明确指出,小说翻译中的许多问题可以归纳到假象等值下,采用文学文体的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对于译者来说,将文学文体的分析方法引入到小说翻译活动中,可以帮助译者增强对小说文本语言特征的敏感性,更好地理解小说叙事语言的文本特征和文本主题意义及美学效果的关系,从而能够在翻译过程中有更多的参数去思考衡量,有根据地选择更好的翻译策略和表达方式,使译文和原文尽可能实现真正的功能对等或表述一致,提高小说翻译质量。从这一层面上说,文学文体学的分析方法对于小说翻译和小说翻译批评来说“无疑是评价翻译质量的一块试金石”[7]。
二、文学文体学对假象等值问题的分析和处理
文学文体学的分析方法常用来比较分析小说的多个现行译本,从而对照比较各个译本是否在选择语言形式的功能和效果上尽量忠实于原文,突出原文文本所要表达的主题意义并传递同样的美学效果,但其与小说翻译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笔者在翻译毛姆小说The Voice of the Turtle时,借助文学文体学的分析方法对译文进行了仔细的推敲,发现了不少词汇和句法层面的假象等值问题,并做了相应的分析和修改。本文探讨的假象等值问题主要包括词汇层面的语域和非逻辑性,以及句法层面的突出、节奏和平行对称。
1.语域
特定的场合要使用特定的语言,这是语言得体性的体现。语域就是指“语言使用者在特定情境下使用得当的语体”[8],不同的语域具有不同的文体风格特点,可以按不同的正规程度划分为口语和书面语、非正式语言和正式语言、非礼貌用语和礼貌用语以及标准语和方言等。[9]语域涉及的因素主要包括说话者、受话者、话题和交际方式(书面还是口头形式)。[10]在小说翻译中,译者尤其要注意特定语境下语言的得体性,要符合人物的身份与关系、交际的方式和谈论的话题;译者还要注意特定语境下语言不得体性所凸显的作者意图及所要传达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
例一:I read a few reviews. They contradicted one another freely. Some of the critics claimed that with this first novel the author had sprung into the front rank of English novelists; others reviled it.
原译:我看过一些书评。它们彼此针锋相对,任意自由。有些评论家称,该作者凭借其首部小说便已跻身一流英语小说家行列,另一些人则对该小说骂声不断。
改译:……,另一些则对该小说口诛笔伐。
这是小说中的文学评论界对青年作家梅尔罗斯第一部小说的评价。“revile”是一个比较书面的词语,正规程度较高,意思是“用责骂性的语言批评”。该词原译为“骂声不断”,强调一部分人对这部小说的严厉批评,但正式程度不够。考虑到文坛上文人间的争斗无论是口头上还是笔头上,都极为常见,也常常针锋相对,便将其改为“口诛笔伐”,比较书面正式,且有效实现了原文语域的得体性。
再看下一个表现为口语、较为不正式的语域译例。
例二:“All my friends have recognized me. I mean, it's the most obvious portrait.”
原译:“我的朋友们都看出是我。我的意思是,这明明白白就是我的画像啊。”
改译:“……,这明明白白就是照着我写的。”
该句是女主人公抱怨梅尔罗斯把她的私事写进小说里时说的话。女主人公其实是个喜欢津津乐道自己风流韵事的人,梅尔罗斯在小说中写的这桩事情实际上正是她自己声情并茂给大家讲述的。她并非真的在意这事被写到了小说里,也不在意别人看出她是人物的原型,此言种种不过是故作姿态,佯装生气兴师问罪而已。“portrait”的意思是“画像,肖像”,十分常见,并不正式,且在说话者角度上,该词实际上想要表达的是相像之意。初译为“画像”,一则不太符合当时口头对话的交际方式和说话者的口气,二则也不太符合通常的表达习惯。所以把这一句修改成“这明明白白就是照着我写的”,更加贴合该人物的口头表达习惯。
2.非逻辑性
非逻辑性(illogicality)指的是作者在陈述小说事实或刻画人物时所选择的语言表达方式不符合语法逻辑或人们的常规想法,但这同样是作者有动因的选择,目的是为了实现特定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而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有可能“将这些有违常情的表达进行情理之中的改动,并认为自己的译文形成了与原文更为合理的对应,实际上却损害了原文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5]。这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试看以下译例:
例:La Falterona wore pale-blue satin pajamas (she liked satin) and, presumably to rest her hair, a green silk wig; except for a few rings, a pearl necklace, a couple of bracelets, and a diamond brooch at her waist, she wore no jewelry.
原译:拉·法尔特罗娜穿着一身淡蓝色的丝缎睡衣(她喜欢丝缎),也可能是为了让头发稍事休息,她还戴了一顶绿色丝质的假发。除了几枚戒指,一条珍珠项链,两只手镯和胸衣上别的一只钻石胸针,她没有佩戴其他珠宝首饰。
改译:……,她什么珠宝首饰也没戴。
该段是女主人公的肖像描写,特别着重描写了她的服饰和珠宝佩戴。女主人公非常虚荣做作,尤其体现在她浮夸华贵的服装和珠宝上。“我”这个老朋友对这一切早就看透,只是不当面戳穿。不露声色却强烈的讽刺是这段描写所要实现的效果,而这一效果正是通过“非逻辑性”来体现的。在这一描述里,她明明佩戴了诸多的珠宝首饰,但最后却说“she wore no jewelry”,这显然不符合语法逻辑也不符合人们的一般观念,应该改为“she wore no other jewelry”。但这一不合逻辑之处正是为了让读者体会到了两相对照下强烈的讽刺效果。笔者初译时武断地修正为“她没有佩戴任何其他珠宝首饰”,虽然将这不合情理之处变得符合逻辑,但却极大地削弱了原文讥讽和嘲弄的效果。借助文学文体的分析方法,笔者意识到非逻辑性其实正是小说叙事表达中常见的一种方式,可以营造出讽刺、真实、强化或悬念等众多效果,因此便将其恢复为不合逻辑的状态,同时也恢复了该部分所要表达的讽刺效果。
3.突出
句法等级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呈现不同信息的不同重要性,因此句法在凸显或是弱化信息这一功能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面对一个长句中错综复杂的结构和各个结构所要传递的信息,译者应当联系上下文和主题意义对这些信息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弱化该弱化的,突出该突出的。如果译者未能敏锐地捕捉到该长句中作者最想要突出的重要信息,便只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单纯地将一系列信息理顺,无法选择最适合的句法结构突出该信息,看起来非常流畅通达,但却造成了假象等值。试看下例:
例:The satisfaction he gave me by his breezy attacks on reputations which for my part I considered exaggerated, but prudently held my tongue about, was only lessened by the conviction that no sooner was my back turned than he would tear my own to shreds.
原译:他欢快地抨击那些久负盛名的作家们,让我心满意足,因我个人也觉得这些人确实名过其实,只不过我一直都谨言慎行不做声罢了,可后来一想,我一转身他也会把我的名声也撕成碎片,说的一钱不值,我心里的这种满足才淡了下来。
改译:⋯⋯,可转念一想我便高兴不起来——因为只要我一转身,他这个人也会把我的名声也撕成碎片,说的一钱不值。
梅尔罗斯身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自以为是和锋芒毕露,但“我”却理解甚至有点欣赏这样心高气傲的年轻人。虽然对他的妄自尊大并不赞同,但“我”又觉得他的这番见解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甚至和“我”的想法颇为契合。该段描写非常巧妙地展现了“我”内心种种微妙的变化。原译文选择的句法结构虽基本传达了语义,但重心发生了转移,变成了“我心里的满足才淡了下来”,和原文所要凸显的信息明显不符。为了将这最为重要的信息突出,强化人物的性格特征,笔者选择使用破折号将该信息放在最后交代,让读者如实地领略到作者的用意,实现了小说叙事语言上的表述一致和功能对等。
4.节奏
“句法结构实际上就是组织思想的方式,它是由所要表述的思想决定的”[11],也就是说,句法安排是为一定的主题意义和美学目的服务的。长短句的选择或是一连串动作的表达方式都会加快或是放缓叙事者的叙事节奏。短句干脆利落,一连串并列的短句具有明快有力的节奏,不仅可以表现一连串外部机械行动,也适宜用来表现内部心理活动,特别适宜于表现一种迫切心情或急速的思维过程,其在修辞或是心理节奏方面的作用构成了文体特点,应当被译者所关注,才能避免假象等值。分别看以下两则译例:
例 一:It seemed to throb on the printed page like the pulse of life. It had no reticence. It was absurd, scandalous, and beautiful. It was like a force of nature. That was passion all right. There is nothing, anywhere, so moving and so awe-inspiring.
原译:它就像生命的脉动在书页上跳动,从不沉默,虽荒唐可耻,却非常美丽,像大自然的那股力量。那是激情啊,哪儿都没有这样令人如此感动、令人如此敬畏的激情。
改译:它似乎在书页上跳动,就像生命的脉动。它从不缄默。荒唐可笑,骇人可耻,却美丽动人。它就像大自然的一股力量,激情澎湃。没有任何东西,哪儿都没有,能如此令人感动,令人敬畏。
年轻作家梅尔罗斯作品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年轻人才具有的那份炽热的激情,而这也是最打动“我”的一点。作者有意识地使用一些短句和较多的逗号来模仿制造出那如同脉动的激情。初译时,笔者考虑较多的是衔接流畅,便进行了合并,忽略了短句和诸多逗号在此的句法功能和用意。 因此,在修改过程中,选择遵循原句句法短促的特点,通过使用短句和逗号营造出蓬勃悸动的节奏效果,给人带来心灵冲击。
再看下一例。
例二:One night they had a quarrel, high words passed, and some reference being made to the ring she tore it off her finger and flung it in the fire. The Crown Prince, being a man of thrifty habit, with a cry of consternation, threw himself on his knees and began raking out the coals till he recovered the ring.
原译:一天晚上,他们吵了一架,说了些气话,又提到了这枚戒指,她就把它从手上取了下来扔进了火堆里。王储素来节俭,惊骇之下大叫了一声,跪在地上开始耙煤块,直到找到了这枚戒指。
改译:一天晚上,他们吵了一架,说了些气话,正好提到了这枚戒指,她便顺手扯了下来,一把扔进了火堆。王储素来节俭,惊惧之下失声尖叫,慌忙跪倒在地,终于在煤块里耙回了戒指。
这段文字交代了女主人公和她曾经的一位爱人关于祖母绿戒指的故事,用一种非常欢快的节奏将整个过程描述得惟妙惟肖,一气呵成之中尽显嘲弄。初始译文基本遵循了原文的句法结构,但是在一些信息的连接上,节奏感和速度感跟不上。修改的译文使用了增译法,即在信息与信息之间合理地添加了一些加强人物动作节奏感的词语,比如“顺手”“一把”“慌忙”。这一系列的改动使得人物动作节奏和语言的表达节奏都更加贴近原文,在译文中比较如实地再现了原文表述上的效果和功能。
5.平行对称
平行对称结构是书面英语中一种常见的形式,它的形式平整,通过重复某些语法结构,对叙述的事情采取平衡的表达方式,不仅突出事实还便于读者理解。平行结构包含至少两个并行不悖的部分,是比较或对照两种事物或思想的有效形式。这一句法结构的功能也应当借助其表达方式在小说翻译中得到传递。试看以下两例:
例一:It depended on whether she was just an artist among artists, or a great lady among persons of noble birth.
原译:这都得看她当下的情况而定,看她是和一群艺术家们坐在一起的一名艺术家,还是和一些出身高贵的人们做在一起的一名贵妇人。
改译:这都得看她当下是和一帮艺术家谈论艺术,还是和一群贵族细说出身。
该句所在的上文是女主人公对其父亲身份的不确定,不知道他究竟是一名科学家还是一位匈牙利贵族,而她不确定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她真的不清楚,而是因为她的说法经常改变。她对自己家庭出身的选择其实取决于她当时和哪些人在一起,聊些什么话题。身为一名歌剧女高音,她身处艺术圈,经常出入上流社会。若是彼时和艺术家们在一起,她自然会选择作科学家的女儿,艺术家的身份,相得益彰;若是当时和贵族们在一块,她自然会选择作匈牙利贵族的后裔,出身高贵,不落下风。因此,这一平行对称结构非常简明含蓄地揭露了其虚荣虚假的一面,在鲜明的对照中不留痕迹也不留情面地讽刺了女主人公。原译也考虑了形式上的对称,但是更多的被“among”这个介词所困扰。英语表达简洁,但展现的信息量和画面感却非常丰富。笔者后来果断地放弃了对介词的过分关注,更加关注该文本的主题意义和讽刺效果,考虑了女主人公做出不同选择的深层原因,并把这个深层原因明示了出来,同时借助了对称的句法结构进行表达。虽然修改后的译文在含蓄性上有所欠缺,但是综合考虑起来,是更好的选择。
再看一例。
例二:On this subject she could be witty, vivacious, philosophic, tragic and inventive. It enabled her to exhibit all the resources of her ingenuity.
There was no end to its ramifications, and no limit to its variety. This subject was herself.
原译:但凡谈到这个主题,她总是机智、活泼、冷静、悲伤,独具匠心。它总能让她把她所有的才能智慧都展现出来。细枝末节,分门别类,没完没了,林林总总,末无边际。……。
女主人公总爱谈论自己,风流韵事也好,演唱事业也罢,喋喋不休。原文在结构和用词上都非常对称,突出强调了女主人公谈论起自己时的那股无所不尽其能的劲头儿和耐心。原译只传递了基本的内容和意义,却忽视了对称结构本身具有的突出对照功能,弱化了原文本的主题意义和审美效果。修改后的译文重新考虑了对称结构的表意功能和形式功能,也考虑了原文词语的意义,用“枝枝叶叶”(ramifications)对称“林林总总”(variety),为AABB的叠词形式,“没完没了”(no end to)对称“漫无边际”(no limit to),为工整的四字表达形式,不仅准确地再现了原文的内容和意义,还再现了原文的句法结构和相应的功能。
三、结论
不难看出,在小说翻译中译者如果不深入探讨原文文本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在译文中完全不考虑语言表达形式,或是未能有效地借助一定的语言表达形式,译文就会出现假象等值现象。从这一角度看来,文学文体学的分析方法是衡量文学翻译质量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对小说翻译的指导具有理论依据和实践意义。译者在翻译时必须同时考量小说的语言形式和内容,深入思考文本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在更多参数考量的基础上做出最佳的选择,才有可能使译文和原文尽可能实现功能对等或表述一致,避免假象等值,提高小说翻译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