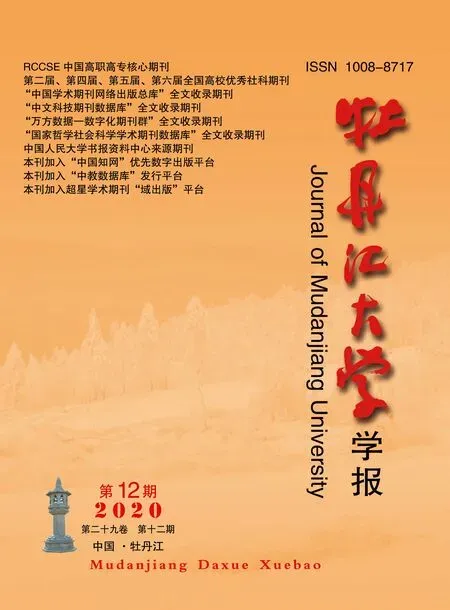林纾与林语堂的翻译意识形态研究
2020-02-28胡萍英
胡萍英
(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外宣与翻译研究所,福建 福州 350118)
一、引言
18世纪末,法国哲学家、启蒙思想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 1754-1836)提出ideology(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把意识形态定义为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他希望用科学的方法,探索思想或观念的源头与发展,所以他把意识形态称作观念的科学(science of ideas),其目的是为了重建社会和政治秩序。意识形态可根据主体范围分为个体意识形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或国家叙事(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翻译是两种语言及文化的话语实践活动,翻译过程及翻译作品不可避免地受译者个体意识形态的隐形操纵,因而香港学者庄柔玉(2000:123)[1]把翻译的意识形态定义为翻译背后的思想和解释系统。换句话说,译者受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形成对世界和社会的看法或潜意识观念,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翻译行为,因而译者思想观念(翻译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和译作产生显著的影响。译著是跨语言及跨文化交流的载体,对译入语社会发展和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晚清及近代历史上,福建籍翻译家林纾和林语堂(下称“双林”)分别以文化及文明的“引入者”和“输出者”两种不同的角色,在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中作出不懈努力和卓越贡献。林纾通过大量译介外国小说,把西方文化引入中国,为国人打开一扇开眼看世界的窗口,从而唤醒国人维新图强的爱国情怀,为当时开民智和求变革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发展、为启蒙思想和现代意识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学贯中西的林语堂倾毕生之力融通中西文化,他的翻译和英文创作主要以构建中国形象为目的,从不同角度刻画中国人在各种环境下的生活与思想状况(王少娣,2011)[2],向西方传播中国古代文明和古老的智慧。两位翻译家不同的行为表现是基于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及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因此,探析他们的翻译意识形态及其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梳理其翻译意识形态对翻译作品成功传播的积极影响,了解其译作对读者以及译入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反拨作用,对当今践行习总书记倡导的“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理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双林”翻译意识形态的异同
林纾和林语堂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尽相同、成长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不同,致使他们的翻译意识形态各异。“双林”翻译意识形态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翻译创作的思想动机都出于爱国,但是具体表现方式相去甚远,林纾的翻译意识形态是借助西方文化为精神武器,以唤醒国人维新图强的翻译救国思想;而林语堂的翻译意识形态是以“闲适”“性灵”“幽默”的风格,向西方传播中国古代文明和古老的智慧,让西方读者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
(一)林纾的翻译意识形态
林纾(1852-1924)出身寒微,但自幼勤奋好学,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其古文造诣深厚。林纾所处的时代,中国正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西方列强瓜分的对象,这种时代背景促使林纾翻译救国思想的形成。邓华祥等(1999)从五个方面概述了林纾的爱国维新思想。首先,他提倡治西学,向西方国家学习;其次,提倡振兴实业、发展工商、厚植国力;第三,提倡兴办教育,培育人才;第四,倡女权,兴女学;第五,存君主、立宪政。[3]林纾呼吁国人放弃民族偏见,学习借鉴外国的经验和长处,变革维新,实现强军强国;他重视启蒙和教化国民,开拓国人视野,主张民主民权,推动妇女解放运动。此外,林纾把语言文字看作是民族文化的根基,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权力关系和话语网络里,在与西方殖民文化的碰撞、交锋、抗拒、控制、角力过程中,林纾坚定捍卫古文地位,即便在晚年饱受批评乃至激烈的言辞攻击,他也未有丝毫动摇。林纾的爱国思想意识体现在他对原著选题、翻译策略和译作文体的选择和应用方面。在翻译救国意识形态驱使下,林纾特别重视译著的救世功能和启发民众智慧的作用,其译著的序和跋多数是为启蒙国民而作。林纾以古文译介外域小说,传播西方文化和先进思想,体现他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和反抗殖民文化侵略的思想意识。
(二)林语堂翻译意识形态
林语堂(1895-1976) 生长在一个和谐有爱的基督教家庭,自幼接受西方语言文化熏陶,受过良好的教育,游学美国和欧洲,成年后才开始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林语堂所处的时代,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战火连绵,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动荡的历史背景和老庄思想的影响使林语堂对人类生命的悲剧性本质有了充分的感悟,他推崇“闲适”“性灵”“幽默”的思想文化观念,旅居国外的经历催生了他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让西方人了解真实中国的译创思想。林语堂倡导人生与天地自然和谐,崇尚闲适和自然,重视心灵的宁静和升华,建议人们应该创造一种积极快乐的人生观,以消解人类在宇宙面前的悲剧感(王兆胜,2002)[4];受西方文化和道家思想的幽默精神影响,他倡导幽默文学,其幽默观夹杂着闲适超脱和性灵的审美情趣,使中西幽默在笑对挫折、化解烦闷、舒展心灵、应变人生达成一致。[5]在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现实中,他站在世界多元文化的立场,以宽容、调和的文化心态,接纳中西文化差异;借助幽默融通东西文化。简言之,中外文化的逆向接受顺序导致林语堂与众不同的思想文化观,在以革命和政治为衡量标准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他追求幽默、性灵和闲适的创译和创作风格;在以革除旧弊为主流的时代环境中,他坚持向西方传播中国古代文明和古老的智慧,以建构中国形象为创译的旨归(沈洁,2018)[6]。显然,林语堂这种基于个人潜在观念的意识和行为与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社会主流的斗争意识不相符,因而在内地受到冷落与排斥,但在海外研究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一位世界性的知名作家。
三、“双林”翻译意识形态的影响
20世纪末,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被引入翻译研究领域,美国学者勒菲弗尔提出了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大要素对翻译的影响,其中意识形态被认为是三者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王东风(2003)[7]形象地把意识形态比喻为“一只无形的手”,影响和操纵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种种选择,也影响读者对译本的接受程度,同时对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王晓元(1999)[8]认为,翻译是意识形态的产物,翻译的生产过程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翻译活动本身又在生产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与翻译活动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王友贵(2003)[9]指出,当译者个体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便会产生一些特殊的翻译现象,即译者采用一些非常规的翻译手法。总之,翻译意识形态源于历史文化背景,同时又通过译著对社会文化产生反拨效应。
(一)林纾的翻译救国思想及其影响
话语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语言表达具有意识形态的力量(Halliday & Martin,1993)[10],因此一切为意义所做的选择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动因,林纾的翻译与当时政治和社会改良运动紧密配合,他大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寻找先进的精神武器,以警醒同胞爱国保种、维新救国;西方文学中对于人的自然情感的推崇是让林纾动心的另一个因素。缘此,林译小说选题广泛,而且大多基于爱国醒世、维新图强的思想内容,他对小说情节的考虑超出了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其次,林纾采用“以中化西、西为中用”的归化翻译策略,[11]对原作进行有意创译,是符合当时国内读者期待的,达到了警醒和教化国人的目的。此外,林纾选用古雅的文言译介外域小说,既捍卫中国传统文化,抵御强势文化殖民,又缩短了翻译文本与接受主体(中国读者)之间的距离,降低国人对外国小说的陌生感和对域外文化的异质感,故能够吸引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之眼球。
林纾的个人意识形态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有机融合,促成了林译话语的社会建构作用。林纾译作向当时的国人传播了民族、民主、女权、实业等西方先进思想,顺应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然能够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对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其译作《黑奴吁天录》出版后,反响极大,激励了全国上下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甚至感染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陈玉刚,1989:68)[12]。另一方面,林译所传递的西方现代人文精神,成为孕育反叛封建传统的现代精神之温床,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走向,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在近代文化建设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众所周知,林译言情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不如归》等作品肯定了女性享有爱情和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梁桂平,2006)[13]。这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妇女观”的挑战,为当时的女性启蒙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林语堂的文化传播观念及其影响
林语堂闲适、性灵、幽默的文化观、人生观和审美观直接影响他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应用。他选择翻译以性灵和闲适为格调的作品,比如《浮生六记》等;他以向西方介绍真正的中国文化为己任,他选择翻译中国经典著作,比如《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等,向西方读者呈现一个丰满的、立体的、有血有肉的中国形象。为了有效传播中国文化,精通中西文化和中英两种语言的林语堂灵活使用多种翻译策略,并在归化与异化、增补与省略、精确与模糊这些相反的翻译策略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为了满足译作读者的文化审美需求和关照其阅读习惯,对作品的表现方式进行重构,重新编排译作文本顺序。总之,林语堂对中西文化关系格局及其对中国文本进入西方文化的屏障机制有深刻认识,故他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与东西方文化关系制约之间做出了理性权衡(吕世生,2017)[14]。尽管他热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但并未因传统文化而固步自封,反而能够睿智地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使其翻译作品符合译入语读者的期待,从而实现中国文化在西方的有效传播。可以说,林语堂译创的小说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比较文学现象,体现出鲜明的承续和超越特征。[15]
林语堂的翻译意识形态似乎与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不相符。当时的左翼作家主张战斗的文风,而学贯中西、兼通古今的林语堂却站在高于现实处,以超脱与悠闲的心境来旁观世情,以自由主义精神写“热心冷眼看人间”的智慧文章,[16]因而受到了鲁迅等左翼文人的猛烈批评,其作品也难以被国内广大革命读者所理解与接受。于是,林语堂利用自身得天独厚的生活阅历和外语能力,自觉化身为连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凭借自己对中国古老哲学的理解和内化,他对中国文化作了批判性和创造性的解读,使用通俗的英文向西方读者介绍自己的生活理念,他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阐述中庸、闲适与幸福生活的关系,在西学东渐的缝隙中做着东学西传的工作,从而使这种人生哲学有了世界意义。1938年,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当时的美国社会福利改革方面,鼎鼎有名的“罗斯福新政”恰似对严苛分工的制度性松绑,这无异于对林语堂闲适生活理念的呼应。[17]可见,林语堂“闲适”“性灵”“幽默”的文学观融汇了文明之智慧,把握中国文化和译入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平衡点,睿智地化解文学作品中的中外文化矛盾,跨越中西文化的鸿沟,因而他的作品为西方读者所接受,使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有了正确而深刻的理解。
四、“双林”翻译意识形态的启示
透过林纾和林语堂翻译及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我们看到“双林”翻译意识形态对中外文化传播和交流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化对外来文化都存在一种屏蔽机制,阻止外来文化入侵。这一机制对异质文化具有“删除”和“选择”两种“过滤”(filtering)功能。即删除或屏蔽不需要的异域文化内容;选择符合自我期望的东西”(Katan,2008:42; Gillespie,1999:7-9)[18-19]。无论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还是异域文化“引进来”,跨文化传播的理想与被译入语社会接受的现实之间需要一种理性的权衡。这种权衡的结果往往是:译者应该把满足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视为主要关切,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调整源文本的表现形式,以消减译入语文化对译著的过滤力量,促成译作被译入语社会所接受,实现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吕世生(2017)[20]指出,他者文化视角对于正致力于建构全球多元文化秩序的中国文化尤为重要。只有借助他者文化视角,才能更全面深刻地认识自我文化,正视中西文化关系现实,以及中国文化走入西方的制约条件。换句话说,即便我们对中国文化有强烈的情怀和自信,也不能减弱理性思维,更不能漠视弘扬中国文化的现实约束。“双林”的译著能够为当时的译入语社会所广泛接受,是两位翻译家就译著对原著形式上的“一致”和读者对译著内容上的“接受”这对矛盾作出了理性的权衡,最终均以适当“改写”原文本为代价,使译作的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符合读者的期待和译入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翻译意识形态操控下的林纾“有意创译”和林语堂“理性译创”等翻译策略是应对中西文化碰撞、实现异质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为中外文化传播提供借鉴和指导。因此,梳理“双林”翻译意识形态及其作用对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外民众的相互了解和理解,都具有积极意义。正如德国的文化传播论代表人物拉策尔所言,人类文化之所以有共性,是因为文化传播。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使民族的智慧变成人类的智慧;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然而,不同文明走出文化边界之后,难免出现“水土不服”,换句话说,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难免因文化差异而发生碰撞和冲突。为此,译者作为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的使者,首先应该学习林语堂先生“站在高于现实处”,即应该站在世界“文明共存和文明互鉴”的高度,融汇东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智慧,构建译者主体的理性意识,以便发挥翻译意识形态的“平衡杆”作用。其次,翻译意识形态必须与译入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译作话语的表达需要符合受众的期待。最后,要把握作品原文化和译入语文化中意识形态的平衡点,以“统一分析与理智重建的方法”[21],对作品的表现方式进行重构,既尊重原作的思想内容和审美气质,也照顾译入语读者的文化审美需求,实现文化的跨时空对接,这样既可得到译作读者的喜爱与文化认同,也能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播和文明的交流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