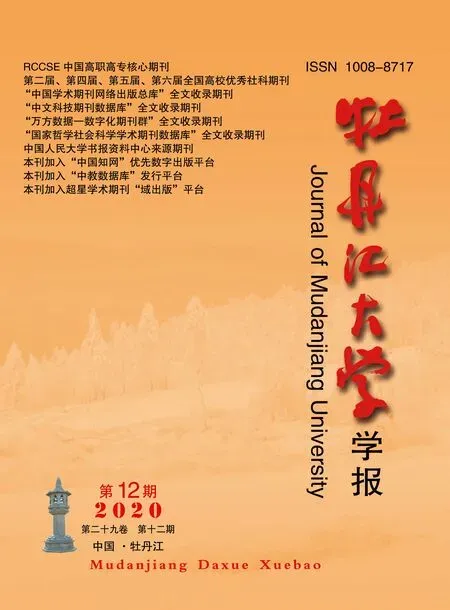他者幻象与自我认同
——从镜像理论视域看《借命而生》
2020-02-28覃心童
覃心童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000)
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社会有力冲击使得既有秩序出现松动,陈旧迂腐的不合理体系、观念相继瓦解,新的思潮在涌动,相互排斥或彼此交融,而在这样的“乱”当中,青年人作为学习知识、改良技术的中坚力量,要坚守什么样的信念,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如何在“乱”中成就自我?作家如何将时代风云与作品结合?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商榷。石一枫被定义为“70后”作家,生于改革开放的涌动浪潮,长于深化改革的社会转型期,作为作家在小说中体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感受,更多的是个人对于整个社会变迁的价值判断。《借命而生》这部作品以跨世纪前后期为写作时间跨度,以主人公杜湘东在理想与现实两个维度之间摇摆不停的心理体验,讲述他在历史变更的洪流中做出的种种选择,树立了一种新的信仰向度——个人英雄主义的成就。在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当中,历经了拉康镜像理论视域下的镜像阶段,主人公杜湘东从混沌走向停摆,最终实现自我认同的构建。石一枫在描述他者社会的大背景时,凸显的是乱世里摇摆不定的人物性格与其坚定的理想信念,为青年人提供了传统价值在新时代的新选择。
一、前镜像阶段:混沌中的摇摆人格
从石一枫早期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类人,正从时代滚滚向前的成长洪流中汲取养分,促成自身的个体成长,这一类人,笔者暂且定义为“摇摆人”。摇摆人,顾名思义,就是一类既想保全理想又想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位置,游移不定,两边摇摆的人。也有学者将这类人的文化性格称为“犬儒主义”,并认为犬儒主义在《B小调旧时光》《恋恋北京》《我妹》等文本里体现得较为明显,这类人拥有对金钱、权力、美色的欲望与诉求,但是却表现得桀骜不羁,呈现出淡然的处世态度。而笔者则认为这不仅仅是“犬儒主义”的概念划分,而是认为这些特征与后现代文化有所联系:后现代具有消解经典、解构历史的虚无感,在石一枫前期的作品当中,我们很容易找寻到关于消解历史厚重感的诙谐笔调,摇摆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游移不定,虚无感与不确定性推动作品情节发展。在这里,摇摆人的作用不是决定历史,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摇摆当中铺开叙述,主人公的摇摆与混沌状态便具有了拉康镜像视域下的前镜像认同性质。拉康认为,呱呱落地的婴儿处在前镜像阶段,他们不具备自我意识和自我身份、行为的认同,只能被动地接受外界带来的信息,并进行模仿。石一枫前期的一系列文本都有青春文学的感伤痕迹,主人公的摇摆人格具体体现在对同类人生活、行为、思想等各方面的模仿上,不具备自我身份、行为的认同,沦为乌合之众。在《恋恋北京》当中,摇摆人在一家“文化、传媒、时事网站”上班,其背景就像它的定位一样含混不清,与其为伍的“b哥”也是“互联网烧钱运动所造就的第一拨富人”[1]5,他们过着醉生梦死的颓废生活,时而与内心的一丝理想之光相伴,但是又很快游移到对现实的无力之中。在他们游移不定、混沌度日之时,有一个或几个女性拥有异于俗世的气息,使得摇摆人驻足凝望她/她们,与其发生爱情并激起摇摆人正义的保护欲,从而变得勇敢、担当,最后在爱情得意或幻灭之时走出混沌,停止摇摆。
在《借命而生》里,主人公杜湘东同样具有前镜像阶段的特征:被动接受信息并开始模仿。警校刚毕业的他被安排在郊县的看守所,他有点儿抵触,“我是行侦专业的,不让我到街上抓人,倒让我在号子里看人,这不是本末倒置吗。”[2]1原想说这样的安排是“大材小用”,又觉得这样有点狂妄,便将到嘴边的话换成了这种说辞。此时的他从学校习得不向权威挑战的思想,只会乖乖顺从安排,像一个孩子一样接受大人的指示。上面又抛出了一个条件让他考虑考虑:“异地生按理该回湖南原籍,如果答应去看守所,那就留京了。”[2]2杜湘东经过考虑,便答应了去看守所看犯人。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体制与城市经济改革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像杜湘东一样能够通过教育体制实现在北京入学、毕业并“留在北京”,对于一个没有背景的年轻人而言意味着认可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别人的观念与行为影响着杜湘东的思考与行为,他被动接受信息并模仿这些未经过鉴别的行为选择。然而,他并没有对自己现在的状态表示出很满意的样子。在看守所里尽忠尽职,在表彰会上不为所动。他的自我认同开始慢慢觉醒:“我觉得我不该干这活儿。”[2]3当初考取警校是为了破案立功,而不是为了在阴森森的看守所里巡视犯人的吃喝拉撒。于是,他就这样在理想自我与现实处境中混混沌沌,两边摇摆,等待着停摆的契机到来。
二、镜像阶段:自我与他者的碰撞
而在镜像阶段,婴儿在日常生活中,如果能够发现自己在镜中的身形已经能够任意的活动,可能就会在脑海中误认为自己的行动已经能够对自己的身体形成完整的控制。[3]婴儿,也就是认知主体,发现了镜子中的自己能够任意的活动,逐渐有了自我与他者的意识,便会误以为自己能够掌控自身的行为,调整自己在他者世界中的地位。杜湘东便是如此,他是个警察,准确地说他是一个警校刑侦专业毕业在看守所当监狱管教的警察。他在校期间的成绩形成了一份优秀的简历:各项考核成绩全队前三、擒拿格斗在省级比赛里拿过名次、与警校另一名优秀警员互争高下,这样的优良成绩让他误以为自己能够在刑侦大队一展身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配备了优异奖励于一身的青年才干,这样一个想成为叱咤风云的刑警的理想青年,却遭遇了现实无情的打击:他只能在一个看守所里当管教,空有一身超凡的刑侦技术和强健的身体素质。在整体社会环境中,他者对个人的欲望有着种种限制,启蒙时期那种认为理性可以支配统领一切的思维模式现如今已不再适应。“警察”这一职业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为了生存的需要,更多的是他精神价值的体现。他渴望着在工作中奉献自己,成就自己,哪怕是作为监狱的管教,他也要做得和别人不一样。看守所在理论上承担着协助侦查机关取证的任务,管教则有义务了解新犯人的基本信息以及犯罪事实,但是这些理论在其他人眼里就是个理论,而杜湘东偏要认真执行,来证明自己跟他们不一样。可见杜湘东作为主体,对自我的认知是出类拔萃,业界内的栋梁之材,在现实生活中却屡遭挫折,只能在摸索中寻找真实的自我。
除此之外,他觉得姚斌彬和许文革这两个新来的盗窃案犯人跟其他犯人不一样,他们眼神流露出来的情感像极了偶尔犯错的“三好学生”,而不是穷凶恶极的犯人。双方第一次见面就以“冲突”收场,姚斌彬撕心裂肺地哀嚎道:“我不该在这儿呀”[2]13,即便在监狱里这是一对管教者与被管教者的身份,但这句话还是激起了杜湘东内心深处的共鸣。同样是身怀绝技的人在此时惺惺相惜,哪怕彼时双方身份悬殊,以特殊的“管教”与“被管教”的身份存在。谁又该在这儿呢?雅克·拉康认为,主体的镜像阶段是主体的形成阶段,又是主体的本质,主体的认知和成长,是在与他者的相互联系当中产生的。[3]这两个犯人作为“他者”身份的出现勾起了杜湘东作为主体的“我”的意识,杜湘东觉得自己的优秀履历值得期待更好的工作岗位,但是在自我与他者的接触当中也屡屡碰壁,他作为主体的“我”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意识到镜像世界与他者的存在。
从生理学角度看,他者经历的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从镜像到他人再到语言。拉康对此做了区分,把他者分为大他者(A)和小他者(a)。小他者总是与感性的他者面容为伍,或者是镜像中的虚构的“我”,或者是他人(父母、亲人、朋友)的面容,但是小他者并不是一个其他的人,而是一个虚幻的存在,具有象征意味。对杜湘东影响较大的小他者形象寄托在其朝夕共处的妻子与他时常照料的逃犯的养母身上。在文中,第一个对他影响较大的小他者形象是杜湘东的妻子刘芬芳。这个忧愁的人说话之前习惯先叹一口气,业余爱好是通过读席慕蓉的诗和三毛的散文来温暖心灵。她出现在杜湘东的生活就给他带来了苦恼,使得他好不容易才学会的“享受寂寞”,如今却又勾起了对现如今生活的不满,试图逃脱。在他舍命追捕持枪逃犯姚斌彬归来的时候,英雄光辉笼罩下的杜湘东又意外收获了刘芬芳的爱情,这是小他者对主体精神自我的认同与赞赏。
第二个影响主体的小他者形象则是姚母——作为逃犯的母亲,她从出场就彰显着生命的坚韧与傲气。早期婚姻不幸,独身一人培养了姚斌彬和许文革两个技术型人才,即便身患脑中风和轻度瘫痪,生活难以自理,也因这两个孩子的“罪行”而再次步入寡居生活。杜湘东同情她的境遇,钦佩她的生命力,从调查姚母的“警察”变成了照顾姚母生活起居的人。哪怕婚后妻子喋喋不休地抱怨,也没能使他停下追捕逃犯的步伐,他将姚母的住所当成了自己理想人格的避风港,在这里,他是个好人,是个能够帮助姚母的“有用的人”,也是一个总有一天会寻到追捕线索的“刑侦警察”。主体的历史便发展在一系列或多或少典型的理想认同之中的。这些认同代表了最纯粹的心理现象,因为它们在根本上是显示出了意象的功能。[3]184
此外,大他者的社会环境则迅速转化为人物登场的历史背景。人的自我感知过程不是一个自动完成的过程,需要置身于一个社会环境当中,个人的成长深深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两个犯人仅仅是大他者当中的一个诱因。《借命而生》中的故事以社会转型期的巨变为发展线索向前推进,将小人物置身于时代的洪流当中,曾经罪大恶极的“盗窃案”在新世纪变成了普通的经济犯罪,主人公杜湘东对逃犯的追捕也深受社会环境的二次影响。一次影响是设施、人力的不齐全与制度的不完善导致逃犯逃之夭夭,二次影响则是伴随着社会转型,逃犯可以在金钱的推动下洗白自己的身份。因此杜湘东蒙上了“玩忽职守”的屈辱,看着曾经的警校同学飞黄腾达,自己只能在看守所里惶惶度日。为重拾尊严,在社会上立足,杜湘东必须有所行动,改变自己在社会舆论中的地位。主体的自我从小他者中认出自己,而大他者则是象征性的语言,是国家机器、制度、社会动向等大的社会环境,它将导致人的不在场或死亡。总体而言,他者对杜湘东的幻象形态,最终内化成了杜湘东的自我认同与追求。
可是快速流动且毫无情面的历史浪潮真的会给予这些“身怀绝技”的年轻人合理的现实安排吗?这同样也带来了一个历史疑问:他们真的能遂愿过上意气风发的生活吗?“‘人’从国家机器的控制下被解放了出来,是为了将其组织到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制度关系中去,组织到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中去。‘政治个人’在这一过程中被转化为‘经济个人’,早晚会接受‘市场经济’对‘个人’的新一轮异化。”[4]时代浪潮下的年轻人只有不随波逐流,坚定立场,凭着执拗的傲气,方可踏着稳健的步伐向前进。因此杜湘东在追捕嫌犯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精神探寻与重生,追捕逃犯的过程不再是捉拿归案的政治惩恶事件,更是杜湘东这一代年轻警察的自我认同与他者碰撞下的现实选择。
三、后镜像阶段:自我认同的构建
加缪认为,“除了没用的肉体自杀和精神逃避,第三种自杀的态度是坚持奋斗,对抗人生的荒谬。”[5]在人类生命当中不可回避的两个主题就是成长与死亡,成长更是人类个体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而成长又需要坚持奋斗。正如上文提到的,镜像只是一个幻象,并不是真正的婴儿自己,当婴儿触摸镜像时发现它并不存在,这样就实现了自我与镜像的对立,称之为“自我的异化”。主体的建立依赖于自我的异化,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地认同某个特性的过程,通过认同某个形象而产生自我,谓之为“成长”。在《借命而生》当中更是有不少涉及人类生命发展与成长的内容,1989年的一桩盗窃案,两名嫌犯一个就地正法,一个亡命天涯,追捕逍遥法外的逃犯许文革的过程使得杜湘东成为了镜像异化之后的“自我”。“逃跑事件让杜湘东旷日持久地憋闷着。”[2]71虽然追回了一名持枪逃犯,但是“玩忽职守”依然成为他职业生涯当中的污点,同事们明里暗里地抱怨他导致了大家停发奖金、被迫加班整顿,他的脊梁骨被人戳得隐隐作痛,曾经自诩奉献、敬业、怀才不遇的警察因犯人越狱的污点而从此矮了一截。而寻找自我的动力是人的欲望,从欲望出发,去将心中的形象视为“自我”,就会导致幻象,甚至是自我的异化,自我认同的丢失使得杜湘东在成长过程中沦为行尸走肉,异化成他自己都想不到的老无赖形态:放任妻子上街摆摊,蹭执法城管的车回家……当他得知逃犯许文革易名为刘春栗给姚母寄钱的时候,他按耐住内心的激动,得到刑警同学的协助之后,开始了只身一人前往大同的追捕之旅。在矿山中奋不顾身地冲向逃犯,差点葬身矿难,以身殉职。又在逃犯再一次逃脱之后,“杜湘东终于停止挣扎,后背蹭着对方的肚子和腿,缓缓地坐在了地上……好像一只丢了蛋的母鸡。”[2]152-153杜湘东的镜像人格重新浮现、挣扎,将自首伏法的许文革衣物、药品等随意拦截下来并进行私下销毁,目睹自己精神的另一个自我形态焦虑、痛苦、寝食难安。
而随着国家社会转型的实现,许文革在时代洪流的冲刷之下,祛除了逃犯的身份,变成了一个“成功”的人。多年之后的许文革投案自首,他也一直盯着他,这时候的他们不再是直接管教与被管教的关系,更像是精神支撑。杜湘东看到“复出”的许文革搞技术、开工厂、游走于权钱交易当中,一个人顶着自我和姚斌彬的命过着意气风发的生活。在许文革的身上,杜湘东看到了共同的时代风气之下,他和许文革这两个具有相同精神境遇的技术型年轻人过上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杜湘东的生活却每况日下,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穷人:职业生涯升迁无望,妻子病危无钱医治。不变的只有他自我认同里坚持的善良、执着与坚定,最终让杜湘东实现自我蜕变的节点在于他奋力救下了许文革,此时的许文革是杜湘东幻象中的理想人格,救下了许也救下了杜湘东自己昔日的追求。这个时候的杜湘东才从那个纵容妻子摆摊、占用城管便车、上班滋溜一口小酒的杜湘东,构建出了自我认同中的杜湘东:他不再颓唐与落拓,蜕变成了英勇进击、临危不惧的个人英雄,成了一位势必侦破案件、救下鲜活生命的人民警察。他突破了镜中幻象,成为了他追求的拥有价值尺度的自我。
成长离不开外部环境,成长中的个体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社会公众进行有意或无意的交流,正如哈贝马斯在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当中所论述的一样:“最初靠文学传达的私人空间,亦即具有文学表现能力的主体性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拥有广泛读者的文学;同时,组成公众的私人就所读内容一同展开讨论,把它带进共同推动向前的启蒙过程当中。”[6]杜湘东的个人性与社会公共性共同构建出一个新的价值主体,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其个人成长历程才会与历史融为一体,最终确立新的身份认同,以社会中的“新我”身份出现。
结语
石一枫在《借命而生》创作谈中曾经说过,“我能写的基本上是一些身边眼前的普通人,然而这些普通人却把自己的日子过成了史诗。”[7]杜湘东便是如此,他从混沌的摇摆人格中摸索自我与他者的异同,在镜像人格里摸爬滚打,最终实现从他者幻象上认识自我,将不属于自我的社会因素也内化成自我人格的一部分。从这个人物及其镜像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新社会的巨变对一辈小人物精神的碾压,超越于时代的思想与时代共生发展留下的精神辙迹。正如《恋恋北京》开篇所言,“因为一直藏匿于城市巨大的胸怀之中,我从来没有看清过它的真正面貌,现在,是时候睁眼、抬头、直直地凝视了。”[1]在镜像中找寻自我或他者设定的理想人格并为之努力,是青年人塑造人格的价值取向,是个人英雄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相生相随,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社会转型中的青年人格塑造与信仰重建有着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