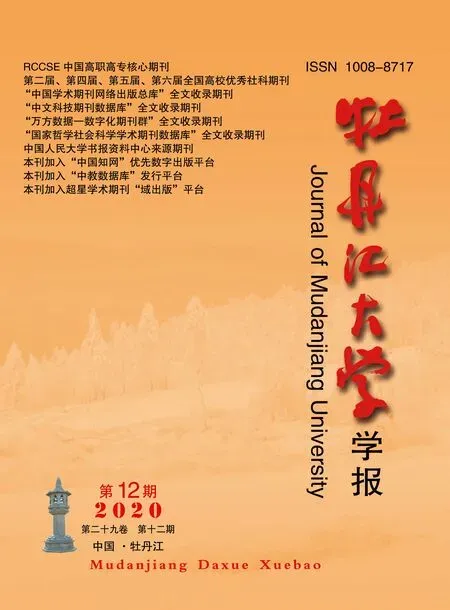《奇幻山谷》中的性别伦理研究
2020-02-28曹颖哲吕曼宁
曹颖哲 吕曼宁
(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谭恩美是当代一位非常重要且颇具影响力的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她通过创造华裔母女的感情纠葛和中西文化碰撞的故事表达自己对于华裔文化属性等问题的反思。她的新作《奇幻山谷》于2013年出版,小说由母女三代分别讲述,时间上从1897年到1941年跨越近半个世纪,空间上在中美两国间不断转换,讲述了母女三人在亲情、爱情及中美文化碰撞的困境中的爱恨纠葛。
小说一经出版便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中西文化的冲突与和解、女性的他者地位,以及作者对华裔小说的继承与超越等角度。以上研究无疑丰富了小说内涵,有助于增进读者对小说的理解。但除此之外,《奇幻山谷》中也蕴含着深厚的伦理思想,有待挖掘。“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就是教诲功能。”[1]14本文从性别伦理的角度切入,分析《奇幻山谷》中混乱的伦理环境、主人公伦理身份的迷失和通过伦理选择重建身份的历程,展现清末民初的上海女性挣扎求生的奋斗经历,表达作者对女性群体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怀,挖掘主人公曲折人生背后所蕴含的伦理意义。
一、女性伦理身份的丧失
(一)男尊女卑的伦理环境
“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分析和批评文学作品。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或伦理语境中去,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1]256小说的背景设立在清末上海。在中国封建社会,由父权制所决定的封建性别伦理观认为男性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女性对男性的绝对服从。这意味着女性一生都将处于男性的统治之下,被完全抹杀了主体意识,养成了自卑、怯懦的奴性心理,逐渐丧失了女性伦理身份。
男尊女卑的伦理环境对女性的迫害一方面表现为性别压迫跨越种族,外族女性也惨遭蹂躏与迫害,未能幸免。路西亚是一位独立大胆的美国女孩。她被陆成神秘的东方气质所吸引,孤注一掷地跟随他来到中国。路西亚有着独立的自主意识,坚信自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此时的她并没有意识到陆成心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事实上,陆成并未将她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个体,他喜欢的只是把自己视为“中国皇帝”的那个美国女孩的幻影,而不是现实中的路西亚。认清真相的路西亚对陆成逐渐感到失望。在听到无数的美国女性与中国男性结合后的悲惨下场后,路西亚意识到自己在这样男尊女卑的社会中所陷入的艰险境地。然而没有了家庭的依靠,巨大的恐惧令身在异国他乡的路西亚不知所措,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意识,只能把陆成视为她唯一可以依靠的“救命稻草”。因此,在得知陆成已经有妻子后,路西亚仍然以情人的身份与陆成生活在一起,卑微地希望能够得到陆家的认可与接受。路西亚的伦理身份由独立自主的女性转变为情妇,抛弃了自己独立的女性伦理身份。
另一方面,在这种男尊女卑的两性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女性还被传统性别观念所物化、商品化,沦为供男性取乐泄欲的工具。清末民初的上海租界内大烟馆、妓院林立,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伦理秩序混乱。“妓女除了要满足嫖客的色欲外,还要被包装成高档商品,满足都市有产者炫耀财富的精神需求。”[2]101与此同时,女性还要面对来自同性的压迫。她们是老鸨的摇钱树,许多人受到老鸨的剥削而陷入巨额债务,经常受到老鸨打骂责罚,忍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她们周旋于上流社会时,不过是富贵豪门的宠物;当她们一旦年老色衰,就会失去作为测定上流社会消费水准的尺度功能,”[2]103无人问津,过着孤寂贫苦的生活。在薇奥莱被迫沦为妓女后,宝葫芦细致详尽地向她讲述如何包装自己:要学习弹唱优美曲调唤起“恩客”的欲望;穿着能够勾勒身材的大胆衣裙满足追求者的虚荣心理;用尽手段让“恩客”为自己一掷千金。在长三书寓中,女性地位极其低微,薇奥莱只能故作柔弱、性感的姿态来迎合男性幻想中的虚假女性形象,换取相对有限的生存主动权。妓女的伦理身份对薇奥莱两性观念的健全和完整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薇奥莱在被卖入妓院后,伦理身份的转变使得她在与方忠诚的情感中无法建立独立平等的人格,这也导致她的女性伦理身份构建更加艰难。薇奥莱与方忠诚的伦理关系除了恋人关系外,还是妓女与“恩客”的关系。两人情感中掺杂的商业利益关系导致薇奥莱在感情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即使薇奥莱要求方忠诚对自己从一而终,但两人人格上的不平等导致方忠诚从始至终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无视她的要求,最终致使两人间争吵不断,感情破裂。而当薇奥莱在妓院中习惯了男性对女性的玩弄态度后,却对方忠诚充满感激,认为要求男人在感情中忠诚是无理取闹,荒唐可笑的做法。
由此可见,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身心进行着残酷的禁锢与迫害。男权社会这种充满性别压迫的伦理环境把女性的独立和勇敢一一消磨,使其逐渐变为失去自我、卑微怯懦的男性附属品。路西亚和薇奥莱一味地委曲求全,幻想着自己能够被男尊女卑的社会所接纳,却忘记了自身作为独立个体的力量,丧失了自己完整独立的女性伦理身份。
(二)母女关系的断裂
除伦理环境外,母女关系的断裂也是女性丧失性别伦理身份的重要原因。“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与伦理规范相悖,于是导致伦理冲突。”[1]263-264正是因为《奇幻山谷》中主人公没有遵守自己的伦理身份,违背母女伦理规范,才导致母女误解深重,关系破裂。“母女情感的特殊性对于女性成长为性别主体非常重要。”[3]91性别主体建构能够激发女性对自身力量的认可和自信,帮助其摆脱男权社会的压迫,寻求自由、独立的生活方式,从而建立完整地女性伦理身份。而母女间的伦理冲突则会造成母女关系的疏离,使女儿的主体建构历程愈发困难曲折。《奇幻山谷》中母女关系的疏远和母女过早的分离造成了女儿的成长断裂与迷失,无法建构完整的性别伦理身份。不同于谭恩美在其他作品中展现的由于文化认同差异而造成的母女冲突,这部作品中母女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母女在情感交流过程中缺乏沟通。原生家庭的缺憾和女性代际记忆的断裂导致母女互不理解,从而冲突不断,渐行渐远。
作品中,母女矛盾的首要原因是原生家庭的缺憾。原生家庭对个体的性格和主体意识建构有着密切联系,而原生家庭的缺憾则影响人的一生。路西亚成长在一个冷漠疏离的家庭环境中。父亲流连于多个情人之间,而母亲哈莉特则沉默寡言,喜怒无常,整日沉迷于昆虫琥珀,没有尽到母亲这个伦理身份所赋予她的责任与义务,忽略了正处在青春期敏感多疑的路西亚的心理,没有满足她对母爱的渴求。情感的淡漠导致母女间矛盾冲突日渐加深。母爱的缺失导致路西亚成人后也无法建构合理的母亲伦理身份,使得母女冲突在她与女儿薇奥莱的生命中重演。在男尊女卑的伦理环境中,路西亚为了生存每日忙于酒席应酬,无暇顾及薇奥莱对自己强烈的情感需求,造成了母女间感情的疏离。与此同时,薇奥莱种族身份的特殊性使她在成长过程中遭受了更多的烦恼和困惑,需要母亲更多的理解与关爱。但身为纯种美国人的路西亚却无法体会薇奥莱在双重种族身份间挣扎的焦虑,无法满足薇奥莱此时的心理需要,致使母女关系愈发疏远。而在妓院的悲惨遭遇更加深了薇奥莱对母亲的误解与憎恨。原生家庭的缺憾造成了母女间代际传播的矛盾与疏离,最终使路西亚和薇奥莱在男权社会的牢笼中迷失自我,丧失了自己的女性伦理身份。
引发路西亚和薇奥莱母女矛盾的第二个原因是女性代际记忆的断裂。女儿只有通过母系家族记忆才能进入母亲的世界,而母女代际记忆的断裂不仅造成女儿对母亲的误解与排斥,还造成了女儿自我认知的困难。路西亚在幼时被割去一根多余的手指后就决心捍卫自己“纯粹的自我存在”。[4]395在生下女儿薇奥莱后,路西亚也坚维护薇奥莱的独特性。但由于缺乏对母亲的理解,薇奥莱把母亲的爱误解为对自己的忽视。正因为路西亚从未对薇奥莱讲过自己的心酸往事,使得薇奥莱对母亲的过往经历一无所知,对母亲的冷漠充满了不满,指责母亲的冷酷无情,在母亲赶走宝葫芦时更是对她充满怨恨。她不了解父母间的感情过往,不理解母亲为了生存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更不懂母亲努力工作正是想要给自己提供一个安逸的成长环境。其次,路西亚对自己与陆成感情只字不提,给薇奥莱的自我认知造成困扰,导致她把母亲的冷漠归结于母亲对自己身上中国血统的憎恶,并认为母亲爱自小与其分离的弟弟胜于爱自己。母女关系的断裂使女儿无法认知自我,导致其在男权社会中无根漂泊,失去了自己的情感依托与精神家园,无法解决自己面临的困难,难以建立完整的女性伦理身份。
在男尊女卑的伦理环境中,女性即使努力反抗自己的命运,却还是不可避免地落入母辈的性别宿命。由于母女关系的断裂与男权社会的压迫,路西亚母女的命运不断轮回与重合,她们无法正确认知自己,逐渐丧失了性别主体意识,无法建构合理的女性伦理身份,在男性社会中挣扎求生。
二、重建自我的理性伦理选择
(一)独立人格的塑造
“伦理选择是文学作品的核心构成”。[5]72“人生活在伦理选择之中,既然文学作品描写的是每一个人的伦理选择,对文学的批评就自然是对文学作品的伦理选择进行分析。”[5]73女主人公路西亚和薇奥莱从痛苦、迷茫到醒悟、反抗的过程正是通过伦理选择重获自我的过程。她们选择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深厚的姐妹情谊的支持下,勇敢反抗性别压迫,实现人格独立和人生价值,并最终重建了自己的女性伦理身份。
在中国男尊女卑的伦理环境中,女主人公路西亚和薇奥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压迫,一度丧失了自己女性伦理身份。但这并没有磨灭掉她们身上独立自主,敢爱敢恨的品质。《奇幻山谷》正是展现了主人公通过理性伦理选择来争取经济独立、建立姐妹情谊,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人格独立和人生价值的历程。“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6]162在路西亚失去儿子并被陆成抛弃后,并没有一蹶不振、沉浸在痛苦中无法自拔。虽然在当时的旧上海,单身女性在社会上无法独立生存,但出于对女儿的爱,她并没有丧失生存的斗志。路西亚选择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永不认输的精神开办了上海最大的长三书寓,开拓出自己的生存空间,为薇奥莱创造出一片自由生长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路西亚实现了经济独立,正视自我价值,建立了坚强独立的自我价值观和女性伦理身份。
同样,薇奥莱重回上海后,并没有重操旧业。她在经历的一系列生活的艰辛后,告别了娼妓奢侈糜烂的生活,凭借自己双重民族身份的优势成为一名翻译,逐渐成长为一名独立自主的现代职业女性,实现了自己的经济独立与社会价值,终于在男性主宰的世界中找回了自我,实现了自尊自爱。而在女性自身价值实现的基础上,她与方忠诚的不平等的利益关系也不复存在,两人实现了人格上的对等。在方忠诚生病时,薇奥莱在他身边不离不弃,悉心照料。最后方忠诚不顾家族的反对,与薇奥莱结合。男女平等原则是家庭伦理的基本原则。方忠诚亲手为她敬茶的举动代表了他与薇奥莱尊重和平等的夫妻关系得以实现。女性自我意识能否建构取决于其在经济领域的解放程度。路西亚和薇奥莱在男尊女卑的伦理环境中,克服困难,排除障碍,“在社会的要求与自身的需求之间,在他人的期望与自己的欲望之间所产生的紧张关系中寻求生存之地。”[7]234她们抛弃男性附属品的身份,通过自强不息的理性伦理选择,成功建构主体意识并实现了自我价值。
此外,《奇幻山谷》也着力表达了同性之间的姐妹情谊对女性伦理身份建构的重要作用。“小说中姐妹之间的关爱往往都是超越于个体甚至种族之上的,并以此说明人类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关系是必须遵守的。”[8]106路西亚被陆成抛弃后,金鸽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她们开设酒吧,收集商业信息,最终成立了上海最大的“长三书寓”,凭借自己的能力在男人的世界中为自己开创出一席之地。在薇奥莱被卖入妓院被迫出卖身体来谋生时,宝葫芦如姐如母,尽心尽力教导她在这样悲惨残酷的环境中生存的方法;当薇奥莱决定嫁给常恒时,宝葫芦虽然极力反对,却还是选择义无反顾地跟随薇奥莱去了月塘村。在薇奥莱遭受常恒的暴力虐待时,宝葫芦挺身而出保护她,照顾她。她们的友谊正是源于在被压迫的悲惨遭遇中产生的患难真情。另外,“友谊是交往主体之间的自愿的平等关系。这种自愿的前提就是人格的平等和意志的平等。”[9]112在路西亚与金鸽、薇奥莱与宝葫芦的友谊中,虽然种族不同,但她们的友情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人格平等的基础上的。这种跨越国家与种族的深厚情谊带给女主人公巨大的精神支持和动力,支撑其战胜性别压迫、最终找回自我。这同时表明了女性要构建主体意识,就要努力实现经济与人格独立,并在此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母女伦理身份的回归
如果说母女对伦理规范的破坏导致自身伦理身份的丧失和自我认同的失败,那么女儿对母性谱系的挖掘则可以使母女关系和解,促成母女伦理身份回归,女性伦理身份也由此得以构建。“母亲们通过回忆把历史与今天相连,女儿们则是在母亲的回忆中寻根,寻找自我,确立自我。”[3]91母性谱系承载着母亲的历史记忆与生活经验,女儿通过对母性谱系的追问,看到了自己与母亲共同的命运和生命体验,感受到了母亲对自己的关爱,从而最终与母亲建立了基于血缘和性别经验上的深切认同。在对母系谱系的追问中,路西亚祖孙三人了解了这种代际传承的母女矛盾,看到了世代轮回的女性悲惨命运,认识到自己与母亲所共同经历的封建社会的迫害和自我挣扎成长的艰难历程,前所未有地体会到自己与母亲是命运相连的统一整体。
失去女儿后,路西亚回到美国。此时母亲哈莉特不再沉迷于昆虫琥珀,而父亲也斩断了露水情缘。母女对往事只字不提,互相关爱,路西亚最终理解了父母对自己的爱。路西亚向母亲讲述了自己在中国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在父母的安慰中疗伤,与母亲默默和解。薇奥莱一度将自己在中国14年的悲苦遭遇都归结于母亲对自己的忽视,对母亲充满怨恨。并且在得知母亲被骗认为自己已经死去后,向母亲隐瞒自己还活着的真相,将让母亲活在内疚与痛苦中作为对母亲的惩罚。而当薇奥莱在经历了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困惑、为人妻母的苦难人生,并被迫失去女儿芙洛拉后,她终于能够体会母亲的心情,感到了母亲的痛苦:“那痛苦深沉而挥之不去。”[4]491意识到靠自身力量建构主体意识的困难后,薇奥莱转而向自己的母亲寻求帮助,从路西亚的坎坷经历中获得精神力量与支持。为了寻找女儿芙洛拉,薇奥莱主动联系远在美国的母亲。通过频繁的通信,母女俩讲述自己成长过程中与母亲发生的矛盾,各自生活的困境、情感的挫折,互相分享生活中幸福的时刻。在母亲的讲述中,薇奥莱感受到母女跨越时空的血缘凝聚力,在母女代际轮回的宿命中找到了归属感,从母女间世代延续的人生经历中理解了母亲,认识了自己:“我的信通常并不是为她而写,而是写给自己,写给我精神的双生子。”[4]495在回忆与讲述中,母女俩达成了和解,伦理身份得以回归。路西亚以自己一贯的智慧和毅力帮助薇奥莱找回了被夺走的女儿。薇奥莱则从母亲的经历中感受到了勇气和力量,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母亲在孩子建构自身的主体性和实现自我的历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3]87母亲是女儿建构自我认同和女性伦理身份的一面“镜子”,女儿从母亲的人生经历和性别体验中获得经验、建立自我认同。母女伦理身份的回归使女儿认识到自己陷入的伦理困境,重新认识自我,反思女性的生存境遇。这种母女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能够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赋予女性群体冲破父权制的牢笼、反抗被压迫命运的勇气和力量,引导女性建立正确的性别伦理观和完整独立的女性伦理身份。
结论
《奇幻山谷》展现了母女三代在交错变换的时空中不变的女性悲剧宿命。她们的人生经历正是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女性群体苦难和挣扎的缩影。母女间世代轮回的命运和坎坷经历表明在男尊女卑的伦理环境中,女性无论种族、阶级都处于劣势地位,惨遭压迫,无法建构合理的女性伦理身份。同时,路西亚母女在性别压迫中挣扎求生的伦理选择也寓意着女性群体生生不息的反抗精神和坚韧意志,表明了作者对女性群体消除性别偏见、实现独立的努力充满希望和信心。“文学作品无论是描写某种身份的拥有者如何规范自己,还是描写人在社会中如何通过自我选择以获取某种身份的努力,都是为人的伦理选择提供道德警示和教诲。”[1]265本文通过对《奇幻山谷》的性别伦理分析表明女性只有深刻认识自己所处的伦理困境,并且通过伦理选择使女性群体团结起来,患难与共,树立完整独立的性别主体意识,才能展现女性强大的生命力与反抗精神,建构独立完整的性别伦理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