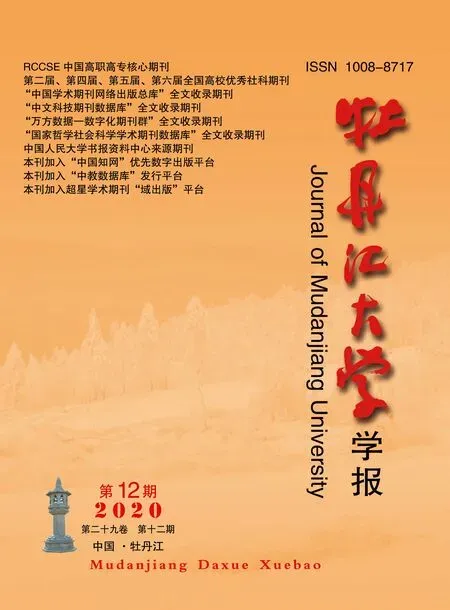解构与建构:中国现当代小说女性形象考论
2020-02-28徐汉晖
徐汉晖
(凯里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贵州 凯里 556011)
自古以来,女人虽然通常被淹没于宏大叙事的官修正史中,但在某些文学作品里,却不乏关于女性形象的深度书写,从创世神话中补天的“女娲”到《孔雀东南飞》中扼杀儿媳婚姻幸福的焦母,从“三迁”觅育儿环境的孟母到“刺字表忠良”的岳母,从《西厢记》中的老夫人郑母到《红楼梦》中封建家长贾母,等等,这些女性或勇敢、或恶毒、或有大爱、或强权,不一而足,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画廊。“五四”之后,在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笔下,女性形象的呈现更加丰富与立体化,与古代作家整体上认可与接受封建女德伦理观所不同的是,现当代作家对传统女德伦理整体上持解构与批判的立场。
一、传统女德伦理的荒诞性
在传统社会,封建“族权、父权、夫权”是压在女性头上的三座“大山”。女性从孩提时代开始,就被束缚在闺房之中,遵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与学堂无奈地绝缘,甚至还要根据男性的审美眼光去“缠足裹脚”;成年之后,她们还毫无婚恋自主权,只能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屈嫁自己,出嫁之后竟被视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到了婆家,她们必须承担延续香火、相夫教子和操持家务的重任,一辈子谨守“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封建社会的《礼记》《女戒》《女训》等伦理规约犹如“紧箍咒”牢牢扣在她们的身上。“父权制以来被压抑的历史处境,决定了她们的历史性沉默。她们没有历史,没有文学,只能听凭男人去描写她们。”[1]当女儿时,她们一出生就被告知地位卑弱,遭卧床下之羞,“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2];作为妻子时,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再也无力抗争命运与改变个人前途了。
因为在古代封建社会,“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3],女子一旦嫁错人,就没有任何重新选择的机会了,只能自认倒霉。《礼记》规定“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女性在婚恋中没有自主权,还被要求“妇人贞洁,从一而终”(《周易·恒》)。西汉刘向所著《烈女传》就收录了历代妇女守节的典范事例,以“榜样”的力量召唤天下女人“守节”;东汉班昭曾写过《女诫》,告诫女人从“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四个方面,去自我形塑“贤妻慈母”的形象。熟不知,在《烈女传》里,有多少女子背负贞洁的“美名”却一生血泪斑斑;熟不知,一部《女戒》捆绑与窒息了多少女子青春蓬勃的美好年华与珍贵生命。
宋代程颐甚至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4]的贞洁观,对女性的道德苛求到“违反人性”的程度。到了明清时期,女性贞洁伦理的思想进一步发展,诞生了《内训》《闺范》《女儿经》《教女遗规》《新妇谱》等一批“女德”伦理典籍。在传统中国,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君主可以“后宫佳丽三千人”,但作为女人,她们必须“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无论她的身份是女儿,是妻子,还是母亲,自始至终都被强大的“族权、父权、夫权”的伦理缰绳捆绑,身体被规训,言行被限制,她们没有经济权,没有主婚权,“更多地被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所创造、所规范,慢慢地被置换成一个道德的化身”[5],最终沦为“父”或“夫”的人身依附,一生毫无尊严、毫无自主性地默默生活,淹没于历史的荒野中。
二、解构:被规训的慈母与残缺的生命
慈母是与严父相对的一个概念,所谓慈母即为慈祥和蔼、尊老爱幼、善良宽厚并擅于持家的传统型母亲。中国文学关于慈母形象的书写有很多,家喻户晓的恐怕应是孟郊《游子吟》中“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几句名诗。有论者认为,女娲应是中国慈母的始祖,因为她“勤劳善良,顽强勇敢,居功不傲,任劳任怨,隐真德而顺自然”[6]。的确,中国历朝历代的慈母都有“勤劳善良、任劳任怨”的共性特征,她们吃苦耐劳、隐忍坚韧、心怀大爱,是女性中勇于自我牺牲而成就他人的道德楷模。
其实,在男权社会里,女人的一言一行必须符合男权文化中对女性规约的所有要求,慈母形象往往是封建伦理文化塑造出来的道德标本。在家庭中,慈母既要内辅夫君、外通亲戚,还要上伺公婆、中连妯娌、下育孩子,家族内外的利益关系奠定了每位成员对慈母的定位与期待。因此,慈母是男权文化对女性形象与女性道德的一种理想化的诉求与苛求。对于慈母而言,“女性生存‘作为母亲’和‘作为女人’的自我是分离的,受崇敬的母亲只是一个被抽掉母性生命内核的道德母亲和神性母亲,而不是一个血肉丰满的性别母亲。”[7]她们的生活往往多贫穷、多离愁,一生与辛劳、与苦难为伴,在伦理缰绳的捆绑下负重前行,彰显出“慈”的伟大光辉。
“五四”新文学首提“立人”的思想,吁求人的觉醒与解放是中国现代作家孜孜以求的创作主题。在中国现代小说中,作家们对“慈母”更多的是给予同情和反对,并不是赞同与赞美。鲁迅在《药》里书写了一位痛失独子的华大妈,她卑微柔弱,一生匍匐于大地辛劳,却难改多舛的命运;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叙述了被丈夫如同衣物一样随意典当的春宝娘,她勤劳如牛,顾家爱子,却难逃被典当给地主“借腹生子”的凄惨命运,沦为男权社会的生育机器;还有台静农《新坟》中的四太太,郁达夫《迟桂花》中翁则生的白发母亲,蹇先艾《水葬》中骆毛的母亲,等等,都是一群老旧中国苦难深重的慈母。这些母亲在强大的封建习俗面前弱不禁风、卑微渺小,她们拥有绽放人性光辉的慈爱,却无法拯救自己受压迫的命运。
这是因为自古以来,历史只是父亲的历史,社会只是男人的社会,“封建家长式的‘母亲’并非母亲,而只是父权意志的化身,若是抽出父亲意志内涵,‘母亲’只是空洞能指。”[8]在“家”天下的男权社会中,身为母亲的女性,她们很少有性别意识,在“三从四德”的规训下,养儿育女、服从丈夫、服务家庭,而迷失了自我。中国现当代家族小说塑造了若干典型的慈母形象,《家》中高觉新的妻子李瑞珏,《四世同堂》中祁瑞宣的妻子韵梅,《京华烟云》中的姚木兰,等等,她们善良内敛、通情达理、夫唱妇随,始终以家庭为生命的圆心,成为各自家族中模范的贤妻良母。
在小说《家》中,李瑞珏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她自从嫁入高家之后,处处以丈夫为中心,含辛茹苦抚养小儿子高海臣,面对家族内外的纷争,她从不议论,也从不参与。当丈夫遭受叔父、婶婶的非难和指责时,她总是温柔地化解丈夫的委屈,宁可退让,也不愿让大家庭失去和睦;当得知丈夫还有一个青梅竹马的表妹钱梅芬时,她默默理解,并与钱梅芬倾心相谈,十分同情钱梅芬的不幸境遇,从此与她以知心朋友相处。当自己怀孕面临二胎生产时,恰逢高老太爷逝世不久,灵柩还停在家里,高家长辈纷纷以避免“血光之灾”为由反对她在公馆内生产孩子,令她尽快迁出公馆,迁到城外去,最终她只得忍痛退让,以自己的善解人意换来了在城外难产而死的悲惨下场。在高公馆内,李瑞珏一直识大体、顾大局,忠厚贤惠,深得高家老老小小的认可。然而,在封建神权、族权等意识浓厚的高家长辈眼里,如此宽厚善良的“慈母”,即使已身怀六甲,却没一个死人重要。死人的灵柩可安然停放家中,作为临盆的孕妇,活生生的她只能让位于死者。可以说,高家的大男人主义与封建神权思想彻底葬送了李瑞珏的生命。反观慈母型的李瑞珏,她的一生总是自甘牺牲,自甘退让,忍辱负重,为大家庭默默操劳与奉献,却被封建家长主宰自己的命运,最后得不到善终,沦为被伦理“吞噬”的可悲典型。“在男权制的社会里,母亲们只有悲惨的命运,完全是封建文化制度的牺牲品”[9],李瑞珏的命运如此,韵梅的命运也如此。
老舍的《四世同堂》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写了老北平四合院里一群挣扎于底层的家族儿女。韵梅是祁家长孙瑞宣的妻子,她育有“小顺子”和“小妞子”一双儿女。在祁家,她既是孙媳妇,又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战事紧张,她以羸弱的身躯扛起祁家的生活重担,不仅要想办法筹措全家人的一日三餐,还要浆洗缝补,伺候老人,并调解家庭矛盾。当丈夫被捕,她冷静坚定,设法营救。面对寡廉鲜耻、好吃懒做的小叔子与小叔妇,她表现出极大的谦让与宽容。她孝敬长辈、持家有方,让全家所有人都满意,唯独自己过得并不快意。小说中有一段她的心理描写:“她心中始终有点不大安逸,……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用‘尽责’去保障她的身分与地位——她须教公婆承认她是个能干的媳妇,教亲友承认她是很像样的祁家少奶奶,也教丈夫无法不承认她的确是个贤内助。”[10]
很显然,韵梅懂得克己复礼。事实上,她也是这么做的。在祁家小院里,她时刻以传统的“妇德”要求自己,努力做一名让全家人都满意、都喜欢的贤妻良母,即使自己过得并不“安逸”,她也要尽职尽责去扮演慈母的角色,做好慈母的本分事。有论者指出,韵梅实际上是“伺候长辈、照顾子女、操持家庭为其全部价值的旧式女子”[11]。的确,当韵梅自觉地以传统伦理道德规训自己的时候,她一辈子都在为别人而活,没有自我的独立价值与生命尊严。
不难看出,以瑞珏和韵梅为代表的慈母,她们不敢质疑,也不敢僭越传统礼教的雷池半步,她们在不折不扣地践行着封建礼教精神,永远活在男权文化的阴影中,生命之花自始至终黯淡无光。实际上,她们恰恰是精神被异化的封建卫道士,可悲的是最后都沦为了封建伦理的牺牲品。
林语堂《京华烟云》中的主人公姚木兰也是一位贤妻良母。她出身富贵之家,嫁入曾府为媳妇后,迅速转换身份角色,把曾家府邸里里外外的事情管理得井井有条,赢得了公婆的高度赞可。姚木兰虽接受过新式教育,但思想却是古旧和保守的。传统的“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夫贵妻荣”“男主外、女主内”等观念对她影响深远。正因如此,她甚至能理解并支持丈夫“纳妾”,她认为:“一个合法的妻子的地位当然是极其分明,若是有一个‘副妻子’,就如总统职位之外有一个副总统,这个总统的职位就听来更好听。”[12]她认为在男权社会里“大老婆”犹如红花,“小妾”就是绿叶。中国旧式的慈母恐怕都如姚木兰一样,明明在丈夫面前地位卑微,却暗暗想当家庭的“一把手”,实在做不了“一把手”,能在同样是女人的小妾面前赢回几分尊严,也心满意足了。
这种类型的“慈母”都忠实地遵守与执行传统“妇德”,极力巩固丈夫在家族中的地位,甚至恨不得自己变成男儿身来主宰一切。表面上,她们很“仁慈”,实际上她们的精神早已被异化,执行着封建伦理之恶而不自知。在传统社会,曾有许多慈母型的苦媳妇一旦熬成了婆,就会对自己的新媳妇百般苛责和刁难,最终演变成“恶母”和“恶婆”。因为当她们依据男权社会的“慈母”标准去履行一个“慈母”的职责时,必然会泯灭自我个性,加上封建伦理有太多的禁锢压抑着她们,一旦时间长久,被外界裹挟的压力过大,“隐藏在母性背后的恶就会日渐凸显出来,表现出恶的一面”[13]。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就不乏恶母形象,典型的有曹禺《雷雨》中的繁漪,在家庭中她被霸道的丈夫压制太久,最终冲破伦理禁锢,以后妈的身份,与丈夫同前妻所生的儿子恋爱,表现出雷雨般的自我毁灭性人格。还有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由于出身寒微,被婆家视为“草鞋亲”,嫁入豪门望族姜家之后,她即使处处小心谨慎、处处提防,仍然备受冷眼和蔑视。原本善良的曹七巧,最终心理扭曲,亲手葬送了自己一双儿女的婚姻幸福。
无论慈母,还是恶母,在男尊女卑、门当户对等伦理思想为主导的传统社会里,作为女性,她们的生命都是残缺的。她们都必须背负“三从四德”的道德枷锁,必须剔除自由的灵魂与心性,泯灭自我,依附男人,要么人格被扭曲,要么精神被异化,最终成为忠实履行礼教的牺牲品。
三、建构:“娜拉”精神的推崇与时代新女性的书写
20世纪初,晚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大力兴办新学堂,新式教育的发展与新文学读物的发行,开启了民智,培养了一大批“有自主开放意识的新型的知识者群体”[14],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到了“五四”时期,随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一大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在报刊上疾呼“个性解放”,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使思想启蒙真正面向社会大众,造成了广泛的舆论影响。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也逐渐认清男权文化的虚伪,她们清醒的性别意识与独立的主体意识逐渐确立,不甘心沦为男人的附属品,大胆地走出家庭,争做经济自主、人格独立的时代新女性。
时代新女性当然不同于传统女性,传统女性认可与接受“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思想,她们受制于父权思想,束缚于家庭中,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被彻底剥夺,从经济到精神上都完全依赖男性,“不仅不能作为一类社会群体存在,而且被分散在没有自我的夫权家庭中,成为被‘物化’的人。”[15]对于时代新女性而言,她们受过新思想的精神洗礼,普遍接受现代的“自由、平等与民主”观念,首先把自己视为一个有生命尊严的人,再把自己确认为与男性地位平等的独立个体。在精神上,她们反叛父权制,敢于挑战权威,敢于冲破封建家庭的桎梏,富有叛逆性。
纵览中国文学,对于叛逆女性的抒写,从古至今并未间断。汉代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塑造了以死抗争与蔑视封建家长专制的烈女刘兰芝,即使被“休”回娘家,她依然不屈服于婆婆“焦母”和娘家兄长的压力,誓死要与相爱的人在一起。元代《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深受父母“严肃治家”的管教之苦,在佛殿巧遇张生一见钟情,之后她缘情反礼,虽遭遇重重阻梗,也要坚定地冲破礼教樊篱,无畏地追求个人爱情。明代《牡丹亭》中的杜丽娘,表面上她淑静温顺、服膺礼教,实际上她崇尚个性解放、反叛束缚,一旦遇到真挚的爱情,就“由唯唯诺诺的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发展到勇于决裂、敢于献身的深情女郎”[16]。清代《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虽寄人篱下于贾府,深感“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家庭氛围,但她清醒而孤高,率性而任情,看清了贵族之家等级、名分等礼、法、习俗的荒谬,始终不屈从于封建家族的礼教与大环境,默默追求自己憧憬的爱情。无论刘兰芝或崔莺莺,还是杜丽娘与林黛玉,她们骨子里并不认可封建礼教,深恶父权思想禁锢的专制家庭。
“五四”时期,随着文学革命大张旗鼓地深入发展,“文学历史进化论”“人道主义文学论”等文艺思想渐渐深入人心,文学创作大多充溢着觉醒的时代精神和人文关怀思想。1918年,以反专制、反传统、倡导个性解放为主旨的剧作《娜拉》在《新青年》发表,深受青年读者喜爱,影响甚大。“在人的觉醒与女性的觉醒的思潮中,娜拉的形象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原型。她的离家出走,构成了整整一代人的行为方式。”[17]娜拉离经叛道、蔑视传统伦理的独立精神,实际上是对自我命运的抗争。“五四”青年读了“娜拉”之后,认识到“家族制度与礼教是女性的天敌”[18],只有首先学会“娜拉”式的勇敢抗争,才有可能实现婚恋自主。在“五四”新文学中,就有不少作家刻写了叛逆女性的形象。胡适《终身大事》中的田亚梅、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凌叔华《绮霞》中的绮霞、白薇《炸弹与征鸟》中的余玥,以及丁玲笔下迷茫与反叛的“莎菲”、蒋光慈小说中果敢的“王曼英”,等等,这些女性拥有独立的女性意识,渴望追求自主的爱情与婚姻。因为不满父母主婚,田亚梅以离家出走进行抗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第一个具有“娜拉”精神的女性。子君追求恋爱自由,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权利干涉”的时代共鸣之声。
“五四”过后,很多作家继续抒写叛逆女性形象,《家》中的琴(张蕴华)、《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女士、《白鹿原》中的白灵小姐,等等,她们都具有“娜拉”式的果敢与叛逆,表现出非凡的独立精神。琴的母亲张太太是一位比较开明的寡妇,她送琴去女子学堂念书,不让琴遵从裹脚的旧习俗,使琴从新学堂中学到了男女平等的观念,由此奠定了琴的知识视野和女性意识。琴从小与表哥高觉民亲密友好,长大后两人产生爱情,不顾封建家长高老太爷的重重阻挠,她毅然绝然地支持高觉民起来反抗。巴金在小说里如是写道:“这两个人是怎样地被爱情和信赖支持着,在那里面找到希望和安慰,仿佛一切的阻碍都不能够分离他们。”[19]为了爱情,琴与高觉民共克艰难,表现出极大的独立意识和自主尊严。《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也是一位思想异常独立的女子,她虽与金燕西是自由恋爱结婚,但门第悬殊很大,金燕西出身豪门望族,她属于贫民子女。婚后的金燕西一反婚前的殷勤体贴,纨绔子弟的本性很快流露,经常夜不归宿,在外饮酒作乐,拈花惹草,不务正业,丧失了一位丈夫和父亲对家庭应尽的责任。冷清秋认清金燕西的本性之后,毅然带着孩子离家出走,并给金燕西送来离婚纸约,从此走上自食其力的人生道路,体现了时代新女性的基本特征。
《白鹿原》中的白灵更是一位桀骜不驯的新女性。她的父亲白嘉轩身为族长,满口仁义道德,却异常专制和顽固。作为白鹿村第一个进学堂的女性,白灵的“读书权”是靠自己争取过来的。她虽出生于封建宗法之家,却显现出与众不同的冷静、果敢。当白嘉轩以“父母之命”向她逼婚时,她坚决不从,并逃离出如牢笼般的家,与霸道的父亲决裂,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革命过程中,她遇到志同道合的鹿兆鹏,与之结为伉俪,从此相濡以沫、携手并进。她人生所走的每一步都是靠自己的独立选择,并朝着明确的目标前进,这正是觉醒的时代新女性不同于传统女人的地方。
持守传统伦理道德的旧式女子往往不能主宰个人的命运,她们一切服从封建家长或外在环境的安排,当生活不如意时,就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天生具有“听天由命”的悲观消极。自古以来,这些传统女性从不懂反抗,不懂得争取做人的权利,往往一生甘当奴隶。她们的悲惨遭遇,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也不乏记录,“曹丕的《出妇赋》、曹植的《弃妇诗》以及民间流传的弃妇诗如《白头吟》《怨歌行》等,都程度不同地揭示婚姻制度和传统伦理给女性带来的不幸和痛苦。”[20]
总之,作为时代新女性,无论田亚梅、子君,还是冷清秋、白灵,她们都具有“娜拉”式的独立人格,敢于反抗父权,勇敢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格尊严,而不愿意一辈子蜷缩于家庭之中行尸走肉,要以自己特立独行的叛逆精神来实现对传统女德伦理的彻底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