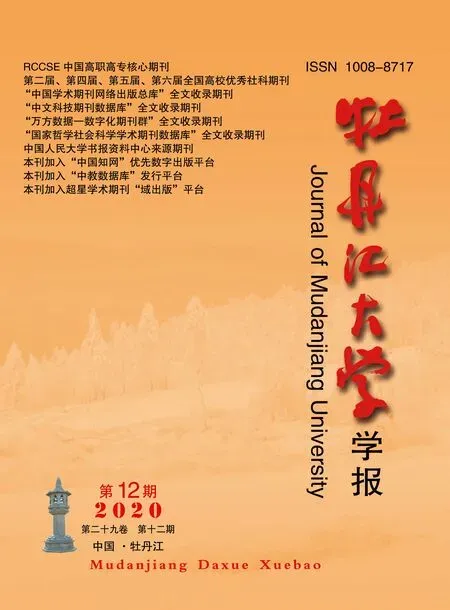社会转型时期语言腐败的性质与范围
2020-02-28邹晓玲
邹晓玲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时期,即“从传统社会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转型。”[1]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从农业大国迈入工业大国,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同质社会走向多元异质,从伦理走向法治社会等等。尽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在稳步、有序中前进,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社会失范现象,其中之一便是腐败。政治腐败、经济腐败、司法腐败、学术腐败、道德腐败、医疗腐败等不一而足。在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中,语言腐败尤其值得关注。本文以语言腐败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语言腐败的性质与范围。
一、语言腐败研究概况
“语言腐败”,又译为language corruption,corruption of language,decay of language等,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它源自人们对语言变化的认知,最初仅用来指称语言的历时变异现象,于十七和十八世纪便已得到广泛运用。”[2]20世纪50年代,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一文中抨击了西方政客利用腐败的语言牟取政治利益的现象,认为政治混乱与语言腐败密切相关。[3]随后,西方研究者多在政治范畴内探讨语言腐败现象,将语言腐败现象看作是政客们利用语言操控民意、愚弄民情的工具。
在我国,“语言腐败”这一概念由张维迎于2012年4月在中国绿色公司年会上正式引进。他提出:语言腐败“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认为,语言腐败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道德堕落、以及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4]随后,“语言腐败”逐渐进入国内学界视野。研究者从政治学、语言学、新闻学等视角出发,探讨“语言腐败”术语的来龙去脉及其内涵、语言腐败的表现形式、语言腐败的影响、语言腐败的防治等命题。如:丁立福(2012)梳理了“语言腐败”术语的来龙去脉,认为语言腐败的本质离不开权力与政治,有必要提高“语言自觉”意识、正当使用“话语权”、确保大众言论自由、增强语言规范意识;何洪峰、何璧珠(2015)分析了language corruption在英语世界的涵义及其在汉语中的译法;苏金智(2013)认为语言腐败的表现形式包括委婉语和语言暴力;吴滨(2013)将语言的失真、失范、失衡、失位现象作为新闻语言腐败的典型表现形式;周亚男(2013)分析了我国官员语言腐败现状、滋生的原因、对政治社会的危害、治理策略;郝宇青、李婧(2013)从政治学角度界定了政治语言腐败的内涵、表现形态、危害。
“语言腐败”虽已进入学界视野,但相关研究成果有限,且尚存在诸多分歧。如在语言腐败的界定上:或范围过窄,将语言腐败的主体局限于政府部门或官员,[5]将语言腐败的表现归结为词语色彩的乱用;[6]或范围过宽,将委婉语等现象也归于语言腐败。[7]此外,还有研究者明确反对“语言腐败”这一术语,如姜迎春(2015)认为“语言腐败”是自由主义改革论者提出的新名词,“实质是贬损、抹黑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8]
当前情况下,语言腐败范围界定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相关研究与实践。范围过宽,容易给人造成语言腐败无处不在的主观印象,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们心中的印象;范围过窄,则遗漏了语言腐败的多种表现形式,不利于其防治。因此,下文将专章探讨语言腐败的性质与范围。
二、语言腐败的性质
语言腐败,作为腐败的一种形式,必然有与其他腐败形式的相通之处;同时,作为一种非典型腐败,在某些方面必然也有别于政治腐败、经济腐败等传统腐败。因此,在借鉴政治学、经济学等有关“腐败”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本文结合语言腐败的实际表现,从语言腐败的主体、方式、目的、后果四个方面逐一探讨语言腐败的属性。
(一)语言腐败的主体
腐败的主体,即产生或制造腐败的行为者。以往研究者对腐败的主体多从政治学角度进行界定,认为腐败的主体为国家公职人员或政府官员,如孙恒山(2005)认为,“腐败的主体应为法律赋予或国家、政府授予或公众给予行使某种公共权力的党政干部、国家公务人员以及受机关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委托从事公共管理事务的人员。”[9]李晓明、张长梅(2008)也持类似观点。[10]
然而,就语言腐败而言,因其涉及到语言权、话语权,其腐败的主体与传统腐败的主体存在一定的差异。1948年12月,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这种自由便是公民的话语权。而这种话语权中的“权”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权利”与“权力”。前者指“一种运用话语的资格与好处”,后者指“支配话语的能力与程度”。“在一个以公民为主体的现代社会中,表达权和表达能力是公民实现自身公民资格的基本要求与条件,更是一个确认公民是否具有公民技能的基本尺度。”[11]
因此,话语权不同于其它国家权力,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尤其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有当“麦霸”的潜力,公民的话语权更不可忽视。因此,语言腐败的主体不能仅局限于国家公职人员或政府官员,也包括普通社会民众、团体或组织在内。以往有研究者在界定语言腐败的主体时,往往站在政治学角度,将语言腐败的主体局限于国家公职人员或政府官员,这实际上是将语言腐败政治化了。正如迈克尔·约翰逊(2000)所言:“腐败是一个政治热点:不管其道德方面的问题如何,它都作了政治化的处理,能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应。”[12]但我们不建议将语言腐败局限于公共政治领域。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相比于普通民众而言,公共政治领域的话语主体因其自身的特殊身份、地位及其对话语资源的掌控力度,其拥有的话语影响力往往更广,对话语支配的能力更高,舆论影响力更强。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少数公职人员的语言腐败行为屡屡受到媒体及公众的关注与批评。
(二)语言腐败的方式
“腐败的本质特征在于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利用,即对正当权力的扭曲和滥用。”[13]“腐败,从来都是权力腐败。没有权力,就没有腐败。”[14]腐败与权力密不可分,语言腐败也不例外。具体而言,语言腐败主体所拥有的权力为公民话语权。且这种话语权的使用场合限于公共场合,也就是公共话语领域,不包括家庭生活这样的私人场合。此外,这种公共话语领域不仅包括现实公共空间,如政府、学校、医院、企业、商场等场所,也包括虚拟公共空间,如微博、博客、论坛、微信等社交平台。
一旦话语主体在公共话语空间滥用公民话语权,造成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失衡,语言腐败即产生。此时,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趋向断裂或改变,能指原来所指称的唯一对象被新的非所指对象所代替,语言系统的平衡性遭到破坏。这在近年来的多起语言热点事件中尤为突出。如“躲猫猫”本属于西南方言,表示捉迷藏。2009年该词因云南青年李乔明“躲猫猫”事件而意外走红。“躲猫猫”的常规所指与能指关系发生断裂,产生了新的所指。
网络虚拟空间中这类语言腐败案例也比较常见。如“老实”增加了贬义色彩,暗含男人无情趣,而“孝顺”一词则暗含着男方在婚姻生活中,过分听从父母的意见,毫无主见,有贬义色彩。类似还有用“恐龙”指代相貌普通的女性;“青蛙”指代长相一般且经济条件不佳的男性;而“蛋白质”则集合了“笨蛋+白痴+神经质”的多重贬义色彩。此外还有“你妹”“查水表”“屌丝”“土肥圆”“矮穷矬”等。这些词语都属于消极词汇现象,产生于网络虚拟空间,每个词语都突破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既定关系,或者是能指与所指存在一对多的关系,或者是对原来指称关系的过度扩张、偏离。
(三)语言腐败的目的
“某种程度上来讲,腐败的目的就是谋取私利,即为个人、亲属及其所属的群体谋取利益。”[15]中国古代文人曾将各种贪腐行为赋予了有趣的别名,如“贼洗名”“斯罗”“浮收勒折”“三节两寿”“程仪”“使费”“部费”“别敬”“炭敬”“冰敬”“门敬”等,尽管其名目繁多,但腐败的目的不外乎都是为了一个“利”字。
语言腐败主体之所以制造语言腐败,归根结底也是为利益所驱使。但相比于传统腐败而言,语言腐败主体所追求的“利”范围更广,它不局限于传统腐败的权或财。在不触犯相关法律条文的情况下,语言腐败主体企图用欺骗、变质的语言来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他们或追求经济效益,或获取政治资本,或彰显权势与地位,或借机打击报复异己,或降低负面影响,或表讽刺与幽默,或追新求异,或彰显个性,或兼而有之。总之,语言交际的对象、场合不同,语言腐败的目的各异。
以政治生活中的语言腐败为例,某些官员不顾个人及国家形象,在公开场合随意发表“雷人雷语”,如“江豚好不好吃?不好吃干嘛要保护?”“警察不打人,那警察是养来干嘛的”等等,类似“雷人雷语”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少数官员心中的官本位价值观在作祟,他们企图利用语言资源在人前摆官架子、彰显权威、体现地位等。
(四)语言腐败的后果
古今中外,腐败现象的产生给国家、社会或他人带来了十分消极的负面影响。语言腐败虽为一种非传统腐败、隐性腐败,有的语言腐败现象被人们所忽视甚至习以为常,但尽管如此,其产生的消极后果却不容小觑。尤其是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当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呈几何级增长,语言腐败的负面影响更不可忽视。
从语言本体层面来看,语言腐败归根结底是对公民话语权的滥用,因此其对语言本体层面的影响最为直接。表现在:语言腐败破坏了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常规关系,造成名实不符,降低了语言符号的交际功能;语言腐败破坏了语言文字的传统内涵,不利于祖国语言文字的健康传播与传授;语言腐败损害了国家语言文字应用的规范性,不利于汉语书面语的健康发展;语言腐败破坏了国家语言生态文明,造成国家语言生态脏乱差的局面。
在政治层面,语言腐败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不利于中国国家形象建设;语言腐败助长了公职人员的不正之风,不利于培养廉洁与高效的政治生态;语言腐败伤害了官民关系,破坏了社会和谐。在经济层面,语言腐败传播了虚假消息,损害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语言腐败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语言腐败引发恶性竞争,扰乱市场秩序。在文化层面,语言腐败不利于国家廉洁文化建设;语言腐败滋生社会不良风气;语言腐败影响青少年健康价值观的培养;语言腐败破坏公民道德文化建设等。
总之,在对语言腐败主体、方式、目的、后果四要素深入分析之后,我们将语言腐败界定为:语言腐败是话语主体为谋取私利在公共话语领域滥用公民话语权,从而造成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失衡的消极语用现象。语言腐败的本质是语言欺骗和语言变色。倘若任由语言腐败蔓延,必将给全社会带来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语言腐败的范围
根据以上对语言腐败性质的探讨,语言腐败的范围包括以下几类:
(一)滥用词语感情色彩掩盖事实真相
词语的感情色彩包括褒义词、贬义词、中性词。感情倾向在语言运用中发挥着特殊作用,蕴含着巨大能量。词语感情色彩运用恰当,可以给语言表达增添光彩,提高语言运用的效果,反之,如果运用不当,轻则破坏词语的常规搭配,重则危及社会稳定。
如在2019年的香港暴乱中,少数图谋不轨的乱港分子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暗中支持下,无视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客观现实,叫嚣“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意图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他们打着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在香港为非作歹、横行霸道;他们明明手持利器攻击警察却对外声称“和平示威”“手无寸铁”,装出无辜受害平民的模样。他们人为破坏了这些词语的内涵与色彩,是赤裸裸的语言腐败行径。
此外,在当今语言生活中,有不少普通词语的色彩意义也发生了明显改变,由正面或中性意义转为负面意义,被腐败了。如“小姐”由身份尊贵变为低俗;“同志”变成了同性恋的代称;“表哥”“房姐”“房嫂”等已变成贪腐角色的代称;“干爹”成为不正当关系的代名词。话语主体出于不同的交际意图、情绪,随意改变以上词语的感情色彩,或刻意美化不正当行为或关系,或忽悠听众,或反讽不良行径。
需要注意的是,这类改变词语感情色彩的语言腐败不同于修辞学中的“易色”。前者是一种语言欺骗或变色现象,其目的不外乎是追求私利;后者是一种积极修辞现象,目的是增加语言的生动与形象。
(二)用模糊性语言混淆事情的边界
语言的模糊性指语言单位所指边界存在不确定性,也是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不确定性的表现。在公共话语领域,话语主体本来能够用明晰的语言表达某个事情或概念,但为了隐瞒真相、混淆视听,或追逐利润等,他们放弃明晰的语言,刻意选用甚至费尽周折地创造模糊性的表达方式。
如在官场话语中,有一类模糊性语言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如有官员将“这事我们知道了,还需研究研究”作为一种官场拒接的推辞,“研究”往往没有下文;“这事有规定”表委婉的拒绝;“意思意思”“走动走动”“加强沟通”则暗含话语主体的隐性期待。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达,有一部分官场模糊性语言因媒体曝光而意外走红。如:“临时性强奸”“礼节性收入”“试探性自杀”“轻度追尾”“破坏性试验”“保护性拆除”“维修性拆除”“自主性坠亡”“休假式治疗”等。这些模糊性表达形式均由话语主体在表述某个突发事件时临时创造,他们想方设法创造一些迂回曲折的表达方式,往往有掩盖事情真相、淡化事件负面影响的意图。
此外,在商业领域,模糊语备受商家青睐。如在商品广告语中,商家常套用模糊性限制语,如“史上最”“更”“顶级”“极品”等表示程度的变动语,“一部分”“大多数”“不少”“众多”等表示范围的变动语,还有“今天”“明天”“十年”“百年”等时间模糊词,有的广告语还通过句子成分省略、词语重复堆砌等方法来实现意犹未尽或语义强调的目的。在商品命名中,模糊性词语也被发挥到极致,为了体现产品的独一无二,“霸”“皇”“帝”“王”等极尽奢华的词语比较受商家欢迎。从商家角度来看,商业领域语言模糊现象的出现自然是为了追求商业利润和价值的最大化。但从消费者角度来看,商业领域中过多的语言模糊现象未必是好事,会诱导消费者过度消费,特别是当产品质量与宣传严重不符时,会造成消费者财力的浪费。这实际上等同于商业欺骗。
(三)用明晰性语言表达虚假空洞的信息
语言是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在信息表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明晰的语言有时却传递了虚假空洞的内容。
以新闻媒体为例,当前在传媒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有些媒体工作者逐渐放弃新闻真实性的准则,转而利用手中掌握的话语资源不惜人为杜撰新闻,制造流言与谣言,以此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类现象不仅存在于新兴媒体中,传统的专业媒体也不例外。如在《新闻记者》评选的2018年十大假新闻中,有一篇假新闻出自某中央级网站,六篇假新闻出自传统专业媒体。
此外,官场话语中语言的“假大空”现象也颇受诟病。有研究者曾将政治生态的恶化归结为两种腐败:一种是权钱交易的“硬腐败”,一种是“软腐败”,即语言腐败。并认为语言腐败是不良政治生态的典型表现,其突出特征为官员语言行为的“假大空”,即“在工作中说假话、报假情,对自己自吹自擂,对别人阿谀奉承;对问题视而不见,对成绩夸大溢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盛行。”[16]官场话语中“假大空”语言现象的屡禁不止,与官员思想、能力、行动上的不足有关,同时也与语言腐败的成本和风险相对较低有关。话语主体只需要用最小的成本、最低的风险来换取自身的政治利益,这种政治利益有时候会成为官员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有时候甚至可以变成一种职级进阶的保障。“一言以蔽之,当人们的言说行为背后处处暗藏着实用理性的精心算计,语言不能不成为第一个牺牲品,而文风问题的全部真相或许正在于此。”[17]
(四)用媚俗的语言博取他人眼球
元末明初著名诗人高启在《妫蜼子歌》中写道:“不诘曲以媚俗,不偃蹇而凌尊。”呼吁诗文写作中既不能媚俗也不能凌尊。然而,在今天的语言生活中,追求用语低级、庸俗的媚俗之风广为盛行,这在媒体语言中尤其突出。
考察当今媒体语言,不难发现,一部分媒体工作者为了尽可能追求新闻受众而使出了浑身解数,新闻作品中充满了星、腥、性等方面的语句,明星的私生活被揭露得体无完肤,各种灾难血腥的词语充斥各大报端,男欢女爱的情爱语句频繁登场。一时间,“范冰冰复出”“梁静茹离婚”“王菲怀孕”“鹿晗与关晓彤分手”“女子为捉奸报警”“陈羽凡吸毒”“宝马司机持刀砍人”“大学生遇车祸身亡”等语句频频进入受众视线。
此外,由于自媒体的繁荣以及网络语言的发展,当今媒体语言中还充斥着诸多粗俗、词品低下的词语,如“屌丝”“蛋疼”“装逼”“你妹”“无fuck可说”“WBD”(王八蛋)“草泥马”“矮矬穷”“狗带”“撩妹”“绿茶婊”“叫兽”“逼格”等,严重污染了健康语言生态。
(五)用狂妄的语言彰显自身地位
受“官本位”思想影响,有少数干部权力意识浓厚,政治觉悟不高,在工作中常摆官架子,好耍个人威风,讲话时气焰嚣张,肆无忌惮,用语极端,“最牛官腔”偶有出现。如:
“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中国广播网,2009-06-17)
“我的位子很稳,不用你操心!”(中国网,2009-11-06)
“警察不打人,那养警察干嘛?”(人民网,2013-07-02)
“我当这么大的官,你们要调查的那些事都不叫事;要查,每个人都有事,比我事大的也有。”(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11-10)
……
还有一部分“雷人雷语”是由干部亲属在公共领域发表,一时之间也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舆论,产生了不良影响,如“我妈是常委”“我爹是支队长”“我爸是丁局长”等。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已取得明显成效,党内政治生态得以明显改善,以上语言腐败现象纯属个案。尽管如此,但也不能忽视其客观存在。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公民的一言一行都需谨慎,尤其是对于公众人物来说,语言狂妄虽然彰显了自身地位与权力,但后果也相当严重。不仅损害了干部自身的个人形象,也伤害了干群关系,给党和国家形象带来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结语
张维迎(2012)曾认为:“语言腐败在当今中国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诸如真理、事实、谣言、道德、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宪法、选举、国家利益、爱国主义……这些词汇在一定程度都被腐败了。”[18]张先生有关我国语言腐败程度的言论是否属实尚值得商榷,但语言腐败在多领域的存在及其蔓延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本文集中探讨了语言腐败的研究现状,并重新界定了语言腐败的性质与范围。作为一种非典型腐败,语言腐败更隐蔽,腐败方式更灵活,更不为人们察觉,但其负面影响却不容小觑,为此,必须制定全面而科学的语言腐败防治策略。限于篇幅所限,这个专题我们将另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