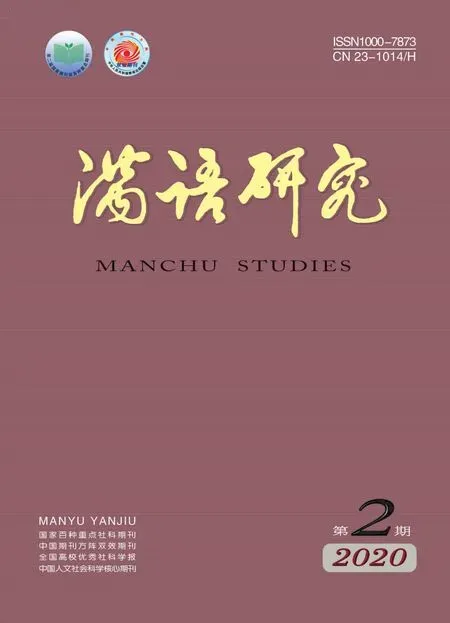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满文古籍述略
2020-02-28李雄飞顾千岳
李雄飞 顾千岳
(1.北京大学 图书馆,北京100871;2.清大文产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100000)
一、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满文古籍之“新”
北京大学图书馆是全国重点古籍收藏单位,富藏古籍150余万册,居全国第三,高校之首。不过,在此150余万册中,有近1/3未经编目,换言之,将近50万册古籍的数据是估算的,含有相当大的水份,并不准确。未编古籍中,含有满文、蒙古文、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形式的古籍。
据《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著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满文古籍仅有65条(1)实为63条,另有2条属于汉文古籍。参见黄润华、屈六生先生主编:《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版。,列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图书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今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今中国民族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今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之后,位列全国第14位。即便在北京地区,北京大学满文古籍收藏量也是靠后的。《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著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满文古籍62条(2)满文古籍藏量依然有失,参见吴元丰主编:《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与雍和宫并列北京地区第9位。1998年初,笔者摸底调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已编古籍中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北京大学图书馆已编满文古籍共计191部,远远超出《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两书的著录。此后,经过10多年对未编满文古籍的整理编目,截止到2016年,北京大学图书馆业已完成馆藏满文古籍编目900余条。再行计入新近发现的近400部未编的满文古籍,北京大学图书馆满文古籍藏量已达1300余条(部)。至此,北京大学图书馆满文古籍藏量径可跃升至全国第二位。
利用者尤其是校外利用者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满文古籍收藏情况的了解,始于富丽先生编纂的《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3)富丽编:《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3年版。,以及《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3部书目。尽管3部书目所展示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满文古籍馆藏数据不大,但依然阻挡不住学术界对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满文古籍的关注。北京大学图书馆鲜有公布馆藏满文古籍的数量和具体品种,但“声名显赫”的满文古籍来源遮挡不住。北京大学满文古籍收藏,与陈寅恪、福克司、今西春秋等名家有关,学术界、社会各界历来知晓此事,但有关满文古籍的具体数量和品种,却一贯不为人所知。
关于福克司和今西春秋的满文古籍收藏,现当代文献多有记载,这些数据与前述3部满文书目的记载相去甚远,无疑为北京大学满文古籍收藏蒙上一层神秘色彩。
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满文古籍特点
1.数量大
北京大学图书馆已完成编目的满文古籍数据足有900余条,另有已清理出、未编目者近400部(条),合计1 300余条,保守估计应有满文古籍实物1 200部左右,具体册数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统计。国家图书馆藏满文古籍的数量,据《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著录,为630余条;《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著录为850多条,稳居全国首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后来居上,以一千二三百部(条)相计,北京大学图书馆满文古籍藏数高居全国第二位。况且,现有统计数字并不代表最后的结果。
首先,900余条编目信息不尽准确。2009年前编目的条目,皆根据旧式卡片目录录入到数据库,其中情况各异。有些满文古籍未在卡片目录上标注语种,径行照录到数据库,以致其真实的“满文”语种无法呈现,故不在此900余条满文古籍目录之中。一些满文古籍虽在卡片目录上标注了“满文”,但在录入时漏掉,也未能纳入900余条满文古籍目录之中。其次,最初编制卡片目录时,编目员不识满文,误将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形式的古籍误注为满文,一并掺杂在900余条满文古籍目录中录入数据库,以致满文古籍数据本身也含有水分。还有个别情况,譬如,既非满文古籍,亦未在卡片目录上标注为满文,但在循例依据某条满文古籍书目的信息进行套录时,保留下“满文”项目,直接混入此900余条满文古籍目录之中。还有些编目员在修改北京大学图书馆原有数据库的信息时,把题名、版本相同的汉文本误认作满文本,擅自将汉文本改作满文本。如,《御制劝善要言》满文本和汉文本皆有顺治十二年(1655年)的版本记录,编目员未核对原书,想当然地将汉文本改作满文本。这三种情况有待于重新审订。所以,现有900余条满文古籍的数字也会发生增减。此外,变数最大者为未经整理编目的满文古籍。北京大学图书馆目前仍有约12万册古籍处于未编目状态,其中满文古籍尚有待发现。随着编目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满文古籍1 300余条(部)的收藏数据也会被改写。目前,业已整理出的近400部未编目的满文古籍,还有待进一步确认、整合,才能进行编目。另外,北京大学施行“大图书馆制”以后,各院系原有资料室大多纳入大图书馆内,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分馆。其中,历史系及外国语学院下属的东方学研究院(原北京大学东语系)均藏有满文古籍。特别是东方学研究院接收并收藏至今的今西春秋经藏的部分满文古籍,以及抗战胜利清华大学复校后陈寅恪先生受托售予北京大学的部分东方学图书(内含满文古籍),必将进一步增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满文古籍数量。北京大学原院系资料室的古籍数据均将纳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目录系统。北京大学虽未曾开设过满文相关专业,但拥有满文古籍如此巨大的藏量,实属难得。
2.质量上乘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满文古籍收藏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上乘。
(1)善本多。按照汉文古籍的标准,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产生的古籍实物被视为善本。当然,年代并不是确定善本的唯一标准。多年前,版本学界针对这一年代标准提出过质疑,提出将善本的年代下限划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说,“乾嘉学派”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流派,“乾嘉”两字并非指两个时代,而是紧密相连的一个时代,不能分割。满文古籍虽然不涉及善本年代标准,但与汉文古籍一样采纳乾隆六十年(1795年)标准,不仅比较合适,而且也符合满文的发展历史。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编目的900多条满文古籍数据中,善本数量约占40%。
(2)孤本多。1998—2005年间,笔者参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编辑工作期间,编委会提供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满文古籍孤本目录为13种(部)。20多年后,北京大学图书馆已编目满文古籍孤本数量已超出10倍,近130部,约占北京大学已编目满文古籍数据总数的14%。在已清理出的近400部未编目满文古籍中,保守估计也有50部以上的孤本。
(3)版本精。在版本较多的品种上,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版本往往是最早的,也是最好的。如,《御制劝善要言》在清代曾“殿刻”两次,即便在汉文古籍中亦十分罕见。两个殿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皆有藏录。而且第一个殿刻本藏品,实为满文本、汉文本俱全。
(4)稿本、写本、抄本多。满文作为清代通用时间较长的文字,其形成的古籍呈现出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截然不同的特点和流传方式,即刻本的数量远大于抄写本。因此,满文抄写本的收藏格外珍贵。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满文古籍中,稿本、写本、抄本计有近300部,占满文古籍总量的1/4。其中,既有《光绪二十九年时宪书》《宣统四年壬子时宪书》等开本宏阔、行字疏朗、字体隽秀、装帧华丽的精抄本,也有色彩斑斓、极其罕见的康熙间五色抄本《古文会编》。
(5)书品好。笔者参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编辑工作时,有幸目睹北京地区多家藏书单位的满文古籍,多方对比后发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满文古籍较为完整,残缺较少,而且书品普遍较好。
3.品种丰富
现存满文古籍的品种数量有多少,学界说法不同,一二三千种,众说纷纭。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距,究其原因是对古籍“品种”概念的错误理解。
目前,我们对满文古籍现存品种的了解,源自《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3部书目。其中,《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编印早,著录范围号称“世界”,但实际上只涉及几个主要的国家,著录的品种数量也十分有限。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编制这样一部书目,实属不易。而且《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应该是一部比较标准的品种目录。时隔8年《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出版,已经具备比较良好的编纂条件。时至今日,《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仍然是一部权威性的全国满文古籍专门目录,而且也是一部品种目录。时隔17年出版的《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则不属于品种目录。这3部书目相比而言,《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的品种统计最为准确。据该目统计,目前国内(不包括港澳台)存世的满文古籍品种约1 000余种。据2018年统计数字,国家图书馆藏满文古籍790余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470余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330余种,位居三甲。(4)此统计数字参见吴元丰、徐莉:《满文古籍版本研究》一文,载于中国民族图书馆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版本研究》,第185页,民族出版社2018年版。但这组统计数字应当源出《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的统计,但该书目不是品种目录,这一数据有待分析。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满文古籍品种为570余种,其中,近200部未经《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著录,实为孤本。而且,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满文古籍中,既有相当数量的孤本和珍稀品种,也有其时刊印数量巨大的品种,类别非常丰富。
4.版本类型齐全
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中,满文古籍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满文作为清朝的官方文字,有着其他少数民族文字无法比拟的地位和作用。但凡以数字衡量,满文古籍的数量、品种、类别、版本类型、刻本数量皆居上,远远高于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在版本类型方面,汉文古籍的主要版本类型为抄本、彩抄本、影抄本、写本、填写本、稿本、彩绘本、刻本、铅印本、钤印本、朱墨套印本、石印本、影印本、晒印本、油印本,这些版本类型在满文古籍均有相应的实物体现。而这些版本类型的满文古籍,北京大学图书馆均有藏本。
5.版本丰富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满文古籍收藏不仅品种丰富,每一个品种的版本也很丰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同文广汇全书》3个版(印)本,包括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北京刘顺尚德堂刻本、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北京刘顺尚德堂刻天绘阁印本、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金陵听松楼刻本(5)《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均未著录,《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只著录了两个版本,但未著录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御制劝善要言》一书,《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著录有6个版本(6)实际上,编号1252、1253的版本著录存在误差,编号1254、1256的版本著录也不尽准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5个版本。《御制增订清文鉴》一书,《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仅著录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武英殿刻本,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3个不同的刻本。
6.语种类型、文种形式齐全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满文古籍,具有纯满文本、满汉合璧本、满汉合集本、满汉文本、汉满文本、满汉对照本、满蒙文本、满蒙合璧本、满日文本、满蒙汉文三合本、满蒙藏文对照本、满汉藏文对照本、满汉罗马字母本、满汉日文本、满藏汉蒙四体对照本、满梵藏汉四体对照本、满梵汉蒙藏五体对照本、满藏蒙维汉五体对照本、汉文音注满语本,等等,语种类型和文种形式均很齐全。
7.编目质量上升
最初,北京大学图书馆满文古籍的编目基础不好,未配备满文古籍的编目员,因此,编目数据极其简单,错漏之处较多。笔者师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安双成先生学习满文,于1997年从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满文古籍的编目工作,在满文古籍编目工作深化了对满文、满文古籍的认识。仰赖全国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古籍著录系统的助力,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质量获得显著提高,满文古籍著录日渐转入规范、精细、完整、准确,这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满文古籍的专题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满文古籍来源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满文古籍数量大、质量上乘,得益于一位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和两位外国教员。1947年,经季羡林先生联络,陈寅恪先生将旧藏的满文古籍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这批书成为东方学研究的工具书,内含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武英殿刻本《御制增订清文鉴》、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刻本《清文补汇》等满文古籍,虽数量不多,但质量较高。关于陈寅恪先生向北京大学售书的具体情况,笔者已有介绍(7)参见李雄飞:《〈御制增订清文鉴〉刻本补叙》,载于《满语研究》2013年第2期。,此不赘述。
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满文古籍直接相关的外国教员,今时皆已名列“汉学家”,即德国著名汉学家福克司、日本著名汉学家今西春秋。福克司(Walter Fuchs,1902—1979)生于柏林,其父为汉学家,对中国民俗和历史地理有深入的研究。福克司自幼耳濡目染,对东亚和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1925年,福克司毕业于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毕业论文题目为《吐鲁番地区唐以前的外部变迁》。大学期间,他主修专业为汉学,旁及满文、民俗学、哲学等。1926年,福克司获得在中国沈阳医科大学教授德文、拉丁文的工作机会,从教20多年,至1947年被遣返回国。他比较留意清朝早期的历史资料,包括满文文献,对满文学习的追求也愈发精深。1938年,福克司应聘为北平辅仁大学教授;1940年,担任“中德学会”德方会长,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德国汉学家。除了参与编辑《华裔学志》外,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17—18世纪西方传教士协助绘制的中国地图,也在厂肆之间搜讨满文文献,收藏日渐丰富。1946年,福克司还与芮玛丽等人发起成立“清史研究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敦促中国政府将战败国在华官员,尤其是德国的纳粹党徒,皆行遣返回国,福克司被列入遣返名单。在芮玛丽及其丈夫芮沃寿的帮助下,福克司谋得燕京大学名誉教授一职,得以暂留北平,遂携其藏书转入燕京大学。1947年8月,福克司再次被列入名单,最终被遣返回德国。回到德国后,福克司先后在慕尼黑大学、汉堡大学任教,在慕尼黑民俗博物馆供职。1957年,被聘为柏林大学汉学教授。1960年,科隆大学设汉学系,福克司受聘为教授兼系主任,直到1970年退休。(8)福克司供职的“沈阳医科大学”即为辽宁医科大学的前身——奉天医科专门学校,参见 张国刚著:《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00-101页。
福克司留在燕京大学的藏书数量说法不一,素有一两万之多。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其文科和理科院系多并入北京大学,福克司留在燕京大学的藏书随之转归北京大学。如今,福克司藏书均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其内西文部分贮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古籍部分贮存在古籍部。遗憾的是,福克司收藏的满文古籍未能作为“专藏”“特藏”而得到集中保管,有些满文古籍可能混杂在未编书中。因此,福克司所藏满文古籍的数量不得确知。近20年来,笔者承担福克司所藏满文古籍的查找、编目、目录编制和研究工作,拘于各种原因,目前还不能梳理出清晰的书目,满文未编古籍的编目工作有待开展。福克司所藏满文古籍具有两个明显标志。第一,钤印。福克司私印共有5枚,其中,“福克司印”汉文阳文朱印(正方形小印);“雨读斋(9)雨读斋为福克司的室名。藏”汉文阳文朱印(长方形四格大印);“fuks/福克司”满汉合璧阴阳文朱印,满文为阳文,汉文为阴文(正方形小印);“福克司章”汉文阴文朱印(正方形大印);“福克司印”汉文阳文朱印(圆形小印)。这五枚印较为常用的是“雨读斋藏”“fuks/福克司”两枚,经常同时钤用,“雨读斋藏”印钤在下,“fuks/福克司”印钤在上。“福克司印”圆形小印,一般皆单独使用,多钤盖在抄本上。“福克司印”正方形小印和“福克司章”正方形大印,通常不单独使用,也不会同钤盖,而是分别和“雨读斋藏”、“fuks/福克司”两印组合起来使用,且钤盖在最下方。第二,汉文、德文铅笔注。福克司采用铅笔注写汉文、德文,或题于书之天头,或题于前后书衣内外侧,或题于函套内侧和函套的题签上,题于函套者,皆为四合套和六合套。福克司铅笔字有特点,易识别。
今西春秋(1907—1979),又名左传子、公羊、公羊子,日本著名满文文献学家。今西春秋的学术研究亦承其家学。其父今西龙(1875—1931),190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科大学,后入大学院,专攻朝鲜史。1914年始任京都大学副教授、教授、朝鲜总督府古迹调查委员会委员。1922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后赴中英等国留学。在北京留学期间,曾师从柯劭忞治学中国史。1925年,任朝鲜总督府朝鲜史编修会委员。今西龙主治新罗史、百济史,著有《朝鲜古史考》《新罗史研究》《百济史研究》等书。1933年,今西春秋毕业于京都大学东洋史专业,师从内藤湖南,主修明清时期满洲史。同年,入京都大学大学院,先后在内藤湖南和羽田亨指导下从事《明实录》满蒙史料的摘抄、校勘工作。1938年,赴中国调查、搜集满蒙史料。1940—1945年,在日本占领时期的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任副教授(10)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42年铅印本《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职教员录》记载,1940年,今西春秋进入到文学院所属史学系任教,与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学家和藏书家谢国桢先生同为该系副教授。。日本战败后,今西春秋继续留校任教,后被捕入狱10年,疑与1941年参与编刻《乾隆代京师城内河道沟渠图》《北京市内外城清代沟渠现位置想定图》有关。1954年,今西春秋被遣返回日本,随后进入天理大学任教,并在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等校兼课,后于196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今西春秋主要从事满文文献研究,专攻《满洲实录》《满文老档》《异域录》《五体清文鉴》,为日本战后的满文史料研究奠定下基础。今西春秋所藏满文古籍在卷端处钤有“いまにし”(今西)不规则形阴文朱印,还在前后书衣内外侧、卷端、书中天头处另钤有“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图书室”阳文圆形蓝印。
福克司与今西春秋颇有几分共同点,父子家学传承,热衷收藏与研究满文文献,具有在北京大学从教经历,最终均被遣返回国,且二人的藏书皆留存于北京大学。不过,福克司的研究偏重于史地,尤其是满洲部族早期的史地,故其收藏的满文古籍偏重于清代中前期(11)意指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福克司精通版本学,早年著有《满洲图书文献学研究》(12)福克司所著《满洲图书文献学研究》一书于1936年在东京出版,参见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01页。,所以,他收藏的满文古籍品种和版本皆属上等,由此奠定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满文古籍多善本、多孤本的基调。福克司旧藏满文古籍上的印章同样显露出文献学修养,皆位于卷端题名下的空白处,从不钤盖在书衣、内封、牌记等其他地方。而且遇有善本,福克司才钤盖印章,5枚印章也是各有用途。如,圆形小印单独钤盖于抄本,普通本见有铅笔注,但不钤盖印章。铅笔注也采用软铅写在于书的天头、版框外、书衣与函套题签、函套内侧的空白处,不覆盖文字;而且注文极简,多为版刻年代。每逢大段注文,福克司采用铅笔或黑色水笔写在10×20厘米的竖排小稿纸上,夹在书中所注叶。与其不同的是,今西春秋承继今西龙、白鸟库吉、羽田亨的语言天赋,更为精于满文文献译注。
福克司于1926年赴沈阳,1938年转至北京,一直致力于搜集满文文献。今西春秋则于1938年赴北京,同样全力搜集满文文献。在藏书的质量上,福克司藏书远高于今西春秋所藏。今西春秋所藏满文古籍以普通本和“大路货”居多,其印章钤盖在卷端题名右下方的空白处,且极少在书上批注。因被遣返,两人的藏书留于北京大学。福克司藏书比较完整地留存在北京大学,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今西春秋的藏书并没有全留在北大,有部分散落,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亦收有今西春秋的藏书。留在北京大学的今西春秋藏书,分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整理编目基础有所不同。
时至今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满文古籍不断“见新”,藏量居前,自当为语言学、文献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语料、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