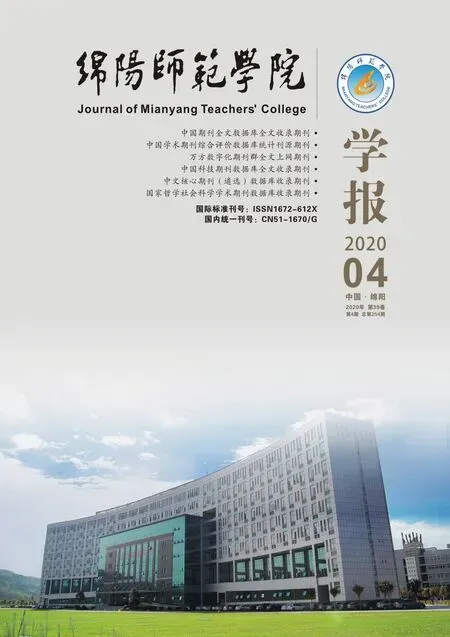论《考工记》中的“考工”内涵
2020-02-27梁宇
梁 宇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信阳 464000)
王安忆自“雯雯”系列小说开始,展开自己的理想化书写,而后描写知青回城的矛盾与苦恼,接着展开关于儒家仁义精神的寻根小说叙写,之后又开始了曾引起众多争议的“性题材”小说书写,再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长恨歌》对于上海弄堂的描写,以及2000年后《我爱比尔》《逃之夭夭》《富萍》等都市题材小说书写。纵观王安忆这些作品,不难发现其多以上海的日常景物为描写对象,着墨于女性角色,有意摆脱宏大的历史叙事,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来展现上海的城市风貌。可在新作《考工记》中作者一反常态,之前刻意避开的宏大历史叙事又回到作者笔下。虽然可以将其视为《长恨歌》之后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但它又与1995年出版的《长恨歌》泾渭分明,《长恨歌》以“上海小姐”王琦瑶的一生作为叙述依托,与张爱玲式写作颇为相似,即使窗外炮火连天,个体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一方天地;而在《考工记》中,窗外之事无法视而不见,宏大的历史叙述呼之欲出,个人想要“考工”修缮也只能随时势而为,好在历史的威严消解在纯良的人性之中,这才使得“顺其自然”成为“理所应当”。
一、宏大历史叙述下的城市精神
《考工记》与王安忆笔下的其他作品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以往作品大都将历史隐藏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中,无论历史怎样发展,上海市民的生活都是一种平静中的浮华。但是在这部作品中,可以明显感到历史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而这篇小说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上海这座城市的人,他们即使身处历史洪流中,也能展现出他们独有的城市精神和生存智慧。
(一)人的生存智慧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上海”就似乎成了“灯红酒绿”“珠光宝气”“摩登”等的代名词,然而上海远不止这些,上海更多的还是普通人的生活。当代上海一方面寻找文学一度失去了的气魄,一方面注目曾被忽略的日常生活的平凡、庸常性。王安忆的作品在这种意义上是对上海的有相当深度的文化透视[1]233。她笔下的上海,有其独特的魅力、独特的精神,她作品中身处上海的人,骨子里都有一种智慧,即生存的智慧。
上海这座城市作为人的精神依托而存在,无论是《长恨歌》中描写的弄堂,还是《富萍》中描写的那群寄居在上海的保姆,对他们而言,上海都是一座拥有魔力的城市。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有种不可抵挡的力量。他们中有些是上海本土人,还有一些是外来移民,如果想要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上海占据一席之地,她们必须拥有一种能使自己活下去的技能,这就是上海人的生存智慧。在《考工记》中,上海这座城市的生存智慧显得尤为重要。
整部小说将历史叙事贯穿其中,历史作为一条时间轴推动着事情的发展。“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小说主人公陈书玉不得不南迁,历时七年,终于回到了时隔多年的老宅;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国与国之间的形势尤为激烈,上海的日常变得艰难;当内战爆发时,国内形势异常激烈,后方人心不定,使得中产人家惶恐不安;在“全民狂欢节”中,陈书玉及其祖宅却能够在夹缝中安然无恙;在三年饥馑岁月中,上海的市民更是体验了生计的困难。城市在历史的洪流中演进,普通人的生活也因历史的变化发生改变,但是他们依然选择顽强地生存下去。小说中没有直接写到历史的演进给人带来致命的打击,而是间接写到大虞父亲被捕入狱等一系列事件,一番周旋回家之后全家迁回原籍,大虞面对此事只说“人没事就好,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这就是他们的生存智慧,在大事面前表现的是从容淡定的态度。体现在大虞身上就是他找人询问父亲的情况“不过一刻钟,大虞写完了,交给阿陈过目。一页纸,数百文字,先介绍其父姓名、籍贯、身份、营业,然后交代案由,再叙述事实,结句为‘请彻查真相,从宽仲裁’。言辞恳切,感情动人,但未有任何涉及旧交的暗示”[2]57。在那种人命关天的情况下,在不知求助对象是否是自己旧交的情况下,在不知世态发展动向下,大虞能够在短暂的时间里将事情缘由娓娓道来,一气呵成,还能做到言辞准确无误,实在是一种大智慧。
(二)精致的市民吃食
“吃”“穿”“用”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上海市民精致于吃食、讲究于穿着,越是小的饮食起居越能展现上海这城市的特色。小说中写到“生在上海,一个美丽的物质世界,无论精神多么旷远,现实都是结实和饱满”[2]37。无论什么时候,上海这座城,永远不会缺乏物质,也永远不会满足于吃饱,就算是饥荒岁月,他们对吃食也还是要讲究的。对上海这座城市而言,所谓的饥饿是相对的,口粮的定量和辅食供应虽然不足,但是还不至于危及生存。正因如此,他们有时间、有精力去追求吃食的精致,保持着上海人独有的精致生活。小说中关于陈书玉钟情于“葡国鸡”的描写非常详细,从刚开始写买鸡的艰难(鸡要从黑市买来,夜晚靠对口号交易),而后对于如何杀鸡、肢解、烹制、收干汤汁、吃完又如何去味,事无巨细,样样俱到。“杀鸡放血,除毛洗净,肢解成小块,钢精锅里放少许油,翻炒一遍,喷黄酒、撒葱蒜、兑清水,加盖闷炖……锅盖和锅沿碰响了,吐着水蒸气,差不多到火候了,于是,浇酱油,辣椒油、芹菜叶子剁碎,代替罗勒,最后加糖,再一轮翻炒,收干汤汁。”[2]136这一段描写在整篇小说中不得不予以重视,小说名曰“考工”,可是关于“考工”寥寥无几,关于吃食的描写却相当精细。可见上海这座城市,无论遭遇什么大风大浪,人的生活、人的吃食永远都是第一位。正是这最寻常的穿衣吃饭才显示出上海的独特。饮食文化背后潜藏着上海人的从容精神,这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时的上海不同,不是只懂得享乐的浮华的上海生活,他们的满足不必建立在庞大而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而是于平淡的生活中彰显不平凡的生活质量,这就是大多数上海人所追求的生活境界。
在宏大历史叙述下的上海有其独特的精神,在时代变迁面前不卑不亢,安于自己生存,即使是贫寒动荡中也不忍丢掉自己的精致生活。在艰难岁月中,他们有勇气坦然面对,有耐心应对一切,这就是城市精神面貌的反映,同时小人物的生活在城市的映照下也显得更加真实贴切。
二、历史“考工”下的真实内涵
(一)“考工”的涵义
《考工记》一书,作为《周礼·东官》的补遗而被保存,科学界一般认为《考工记》是“一部关于手工业技术规范的汇集”[3]108。在战国时期,《考工记》讲究天时、地气、材美和工巧的结合。《考工记》中指出,“天时”即为“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以死;石有时以泐,水有时以凝,有时以泽;此天时也”[3]。这充分说明天时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何为“地气”?《考工记》中也有记载:“橘逾淮而北为枳,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3]从现代科学来讲,应该包括地理、地质、生态环境等多种客观因素。“考工”实当一件严谨之事,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四者缺一不可。王安忆笔下的“考工”也是如此,陈宅最终以修缮无果结束,也正因为不具备“天时”“地气”“材美”与“工巧”之说。祖宅错过了最佳修缮时间,最后连懂得修缮的工匠也离开了,所以祖宅注定腐朽、颓败。王安忆笔下的《考工记》一方面遵循战国时期的“考工”方法,另一方面是展现对人精神上的“考工”。有评论者说《考工记》的当代意义并不在于在《长恨歌》的以城立人之外再添一部以屋立人的姊妹篇,而是通过陈书玉这个裸露于时代和历史风雨中的凡人泥胎,去追问个体如何在时间的形塑中完成自我精神的考工记[4]。在笔者看来,王安忆《考工记》中最主要的意义是延续历史的脉络,在作者以往创作经验上完成自己精神上的考工,一次精神上的升华。作者追求的是不变的东西,《考工记》是她创作上的延续,也是她一直默默探索的精神追求。因此,笔者认为在《考工记》中既是作者自身创作上的一次精神考工,也是书中人物陈书玉内心的精神考工,更是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考工。
(二)陈宅的“考工”
王安忆所写的《考工记》,初读题目, 容易被误导,以为这是一本记述房子以及房屋修缮问题的书,娓娓读来,恍然大悟,这才发现这本书虽然所考之工为陈家祖宅,但是记述并不在于“考工”、修缮问题,“考工”只是作者的一个幌子。书以“考工”为题,实当以所考之“工”为主线,究竟为何要考,以及如何考,甚至何人来考?细读后发现,小说六章之中,关于“考工”的记载少之又少。第一章写陈书玉历经周折,回到了南市老宅,发现昔日挤得满满当当的老宅,如今只剩空旷与落魄。第二章结尾处,陈书玉才觉察出这宅子是个隐患。第三章写到陈书玉主动要求上交宅子,结果因时事在宅子里开建瓶盖厂,陈书玉在自家祖宅里仍有一席之地。第四章,终于等到了修缮时刻,一老一小开始了一天的修缮工作,此时屋顶上的瓦早已断档,只能凑合着拼接,对于修缮细节也是言简意赅,不肯多写一字。第五章草草交待陈书玉面临抄家,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第六章仿佛是文章对“考工”的定论,所考之工,原本可顺利纳入文物保护系统,受国家保护,谁知在利益争执下,物是人非,修房计划只得作罢,就连大木匠也走了,事情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不同的是后进的房屋倒塌、木料被人拖走、北墙已有破洞,祖宅破烂不堪,最后只得一“煮书亭”石碑立于门前。
作者立题于“考工”,中间穿插了很多关于祖宅的隐喻,如“新气象之下,那宅子显得颓然。不是因为陈旧,而是不合时宜”[2]69,“新时代总是有生机,旧的呢,却在坍塌,腐朽,迅速变成废墟”[2]114。小说中所考“陈宅”也是上海建筑文化一隅,在这里陈宅不再是一个静止的房舍,而是作为上海的代表性建筑出现,祖宅里承载的东西是上海这座城市所承载的外化。“京味”小说家笔下的四合院、胡同就是北京文化的承载,对于上海而言,弄堂、祖宅就是上海文化的承载。祖宅在时代的发展中由最初富裕的象征到不断处于危险之中,以致时时透露出危机,小说中预示着祖宅的荒废无果是必然的,因为旧的、不合时宜的东西必然要被历史淘汰,新的时代在发展,新的生机呼之欲出,因此祖宅的颓败也象征着新事物、新时机、新历史、新精神的到来。作者由陈家祖宅的建筑“考工”衍生到城市精神的“考工”。
三、历史消解于纯良的人性
(一)艰难岁月中的纯良之人
小说开篇扉页道出了陈书玉的一生:“他这一生,总是遇到纯良的人,不让他变坏。”全文围绕西厢“四小开”陈书玉、大虞、朱朱、奚子展开叙述,大虞是陈书玉的挚友,无论何时何地,大虞都是陈书玉值得信赖的兄弟;朱朱带给陈书玉的是女人缘,尤其是朱朱的媳妇冉太太,甚至成为陈书玉一生的爱恋;奚子虽然在政府部门,无法给予他帮助,但奚子是无形之中的朋友;带他入门的王校长,让他有了工作,过上安稳的生活,为他指清道路;自称奚子“弟弟”的人对陈书玉也有深厚的帮助,解救朱朱于水火、为陈书玉推荐工作、咨询祖宅等问题;学校女书记让陈书玉佩服。陈书玉身边的人,不能说都是至真至善,但都是心性纯良之人,才让他在大时代面前不至于走偏路。面对大虞家的灾祸、朱朱被捕入狱、自己被抄家,甚至是自己身边的人被批斗、被降职,而陈书玉凭借自己的谨慎以及朋友的帮助,一次次地化险为夷。如果没有这些帮助,陈书玉怎能躲过一次次劫难?奚子和大虞代表着新派,朱朱和阿陈代表的是过去。但无论是过去还是新派,在历史风浪面前,他们都要被历史所掩埋,好在历史消解在“四小开”的纯良生活中。通常描写上海的文学作品,大都是写上海的浮华、夜夜笙歌、竞技场、歌舞厅,无论是茅盾笔下的《子夜》还是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都是如此。在《考工记》里,作者一反常态,叙述视角围绕着男性陈书玉展开,描写的是历史中普通人的生活,这正是王安忆对自己写作中“四不”之一的“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的真实书写。正如书中所言:“上海的正史,隔着十万八千里,是别人家的故事,故事中的人,也浑然不觉。”[2]14即使是生活在上海的正史之中,凭借着周围纯良之人的帮助,亦能开拓出一番新天地。
(二)发乎情止于礼的精神爱恋
王安忆在与陈思和的对话中指出:“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5]9所以她笔下的大量有关女性的作品,都会关注“性”这一主题。“雯雯”系列小说中是一种美好的爱情,不直接涉及性爱;在“三恋”小说中,她将性爱描写陈述于文本之中,但又不仅仅流俗于简单的性爱,而是冷静地展现人的本性;之后王琦瑶的恋爱则更加复杂,不能简单地用“性爱”解释清楚;富萍对于爱情知道的太少,所以面对爱情时不知如何选择,最后不是选择爱情而是选择生活。《考工记》中的恋爱在王安忆笔下虽不能说是一种全新的表现,但也是极其少见的一种,主人公陈书玉一生遇到三个让他产生好感的女人——采采、冉太太和夜校女学生。第一段以采采的追求无果转而嫁人告终,第二段是对冉太太的迷恋,甚至不能称得上是一段感情,第三段是将夜校女学生视为冉太太的幻影,最终破灭。小说中对陈书玉影响最深的是冉太太,陈书玉虽然极力掩藏自己对冉太太的爱恋,但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当奚子对阿陈说:“我看你喜欢冉太太!”阿陈大惊,跳起来连连道:“不可能!”“她是朱朱的人!”“阿陈昂起头,激辩道:‘不对,是冉太太不肯放,朱朱就跑不了;冉太太一旦握牢,永远不会离弃’!”当阿陈的心思被好朋友捅破后,他的一系列对话、动作、情绪再也无法掩饰了。虽然陈书玉迷恋冉太太,但也仅是发乎情、止乎礼的倾慕。小说中有很多关于陈书玉对冉太太的念想,如:
①陈书玉眼睛里只有一个冉太太,除此什么都看不见[2]115。
②在夜校对一名女性产生好感,甚至将其视为冉太太的化身,经人提醒后,失望冉太太的泡影破灭。再一次看见那女学生,不由心生厌恶,厌恶她玷污了冉太太[2]117。
③收到包裹领取通知单时,他心里浮出一个念头,虽然不敢深想下去,但还是抱有一丝期望[2]142。
④人啊,不动念头还好,动了念头再要消除,就不那么容易了[2]143。
⑤当他找女书记签字时,看到女书记剥烟丝,又想起了冉太太[2]145。
⑥去大妹妹家,低头换鞋时又想起了冉太太,她本该过着这样的生活,不禁感到惘然[2]159。
陈书玉一生并未娶妻的真实原因就是倾慕于冉太太,他不相信世上还有冉太太这样痴情的人。冉太太在朱朱入狱的时候不离不弃,想方设法解救朱朱,一个人带着三个小“拖油瓶”去狱中看望朱朱,那种深情、那种魄力、那种高大,是陈书玉欣赏的。在他看来,锦衣玉食长起来的冉太太,应对起大变故来,竟能够从容不迫,实在是令他又敬又怜。冉太太又是重情重义的,饥馑岁月,在人人难以自保的情况下,她还能不忘陈书玉昔日的帮助,从香港给他寄来许多食物,帮他渡过饮食难关。冉太太在陈书玉心中是一个完美的女人,这也是陈书玉在知道夜校女学生身份之后,觉得她玷污了冉太太的原因。
小说中为什么出现了这样一种精神恋爱的模式?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反观王安忆以往的小说,再结合她写“三恋”的初衷,答案便水落石出,她不是把“性”当做一种揭露社会的工具,或者吸引读者的手段,她真正想要的是对“性”本身的内在探索。她在与陈思和的对话中说:“爱情其实也是一种人性发挥的舞台,人性的很多奥秘在这里都可以得到解释。”[5]10笔者想在这部小说中表达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尤其是“性爱”中最纯粹、最美好的东西。正是这种美好的东西才让历史退居舞台之后,扮演幕后角色,使得历史消解于人性的美好,从而展现人的内在精神。
陈思和先生曾评价王安忆说:“在九十年代文学界的知识分子人文精神普遍疲软的状态下,仍有人高擎起纯粹的精神旗帜,尝试着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自我救赎。”[6]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以宏大的历史背景作为依托,虽然立题于“考”,所考之工着眼于来历不明确的陈家祖宅,但蕴藏着深厚的潜在意义,作者不仅展开了祖宅的建筑“考工”,更是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考工”,在两者的结合中也完成了属于作者个人的精神考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