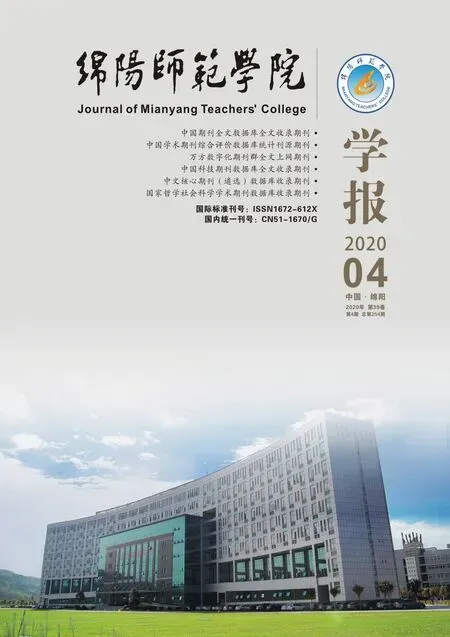战火中的人性图
——评贾平凹《山本》
2020-02-27马蔚
马 蔚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在《山本》的后记中,贾平凹写道“这本书是写秦岭的……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吧。”[1]248由此可见,作者的初衷是想要为秦岭立志。在地理上作为中国南北分界线的秦岭,是横贯中国中部的东西走向山脉,长约1 600多千米。要为如此浩瀚的山写志,表明了贾平凹的野心,其宏愿不得不令人钦佩,但这个愿望的实际操作难度可想而知,其可行性又有多少呢?其实,作者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并在实际写作中做了调整,“关于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终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使我改变了初衷,从此倒兴趣了那个年代的传说……”[1]248。虽然没能完整地实现自己最初的宏愿,贾平凹却巧妙地将秦岭之志分散于作品叙述的故事之中,在对以涡镇为中心的人和事的描写中,穿插介绍了秦岭的各种动物和草木,并借书中人物麻县长实现了在现实中没能完成的愿望。
《山本》中有两条线,一条以秦岭里最大的镇子——涡镇为主,对其中发生的人事的描写,展现了生活其中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另一条是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于陕西的国共斗争为主,描写了国民党与游击队的斗争。两条线齐行并进,共同演绎了民国时期动荡不安、生灵涂炭的历史。尽管作品充斥着打打杀杀,但这并不是一部写战争的书,其中既有对人性和欲望的暴露和展现,又有对革命的诅咒和反思,还有对秦岭博物风情的描写,可以说,它具有地方志和民俗史的价值。
一、《山本》的民间建构:独特的民俗描写
贾平凹是一位十分擅长民俗描写的作家,《山本》展现了以涡镇为中心的秦岭一带独具特色的民风民俗。首先,作者在言说中融入了当地的方言土语,如日弄、碎怂、恓惶、瓷怂、顶事、一愣一愣的……这些土语的运用恰切地表现了当地山民的性格。涡镇的村民们生在秦岭,就是秦岭里的人,也就决定了他们的模样和脾性。那里民风彪悍,人们说话粗俗,口无遮拦,如开凿石窟时,富贵人家暴露了殷实,有的人却一说石窟就来气“谁抢我呀?娘的个X,我还想抢他哩!”[1]8杨钟嫌阮天保糟践他,埋怨道:“河滩里稀泥糊汤的他让我往前爬,爬他娘个X哩!”[1]83吵架时,“动手不在于挨了几下,要的是气势上压倒对方,提裤子,挽袖子,吹胡子瞪眼,再是配上抄家伙的动作。”[1]9山民们说话做事大都直接、爽快,有啥说啥,生气了就直接干架,这些都体现出粗犷豪爽的性格特征。其次,在吃住方面也别有风味,他们的吃食有挂面、凉粉、蒸馍、地软、锅盔、扁食等,偏重于面食,住的则是炕、石窟。此外,他们的打扮也与其他地方不同,如陆菊人头上总是搭着一个帕帕,这是“关中十大怪”之一“手帕头上戴”,是陕西关中地区由来以久的风俗。由于关中地区地处北方,那里日照强烈,干旱少雨,而且风沙天气较多。所以农村妇女在劳作的时候,都要头顶着手帕,手帕既能防晒又能防风沙。另外,《山本》还展现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丧葬习俗和风俗活动。如井宗秀父亲死后,由于没地安葬,就没法埋,浮丘着,“按涡镇的习俗,浮丘指那些亡人殁的日子不好,犯着煞星,不可及时入土安埋。”[1]14井宗秀的父亲死得很怪异,死后竟无葬身之地。井宗秀当上团长后,涡镇山民们在庙山门的牌楼前耍铁礼花,这是中国民间的一种传统庆典狂欢活动。
贾平凹曾说:“我一直想走这个路子,精神境界吸收外来的东西,形式上用本民族的东西,一个是传统,一个是民间,也只有这两条路子。”[2]131《山本》正好体现了传统、民间与现代相结合的路子,作品中对民风民俗的描写体现了民间性的一面,一僧(宽展师傅)一道(陈先生)代表了传统文化中的佛教和道教,这是作品在形式上的特征,是属于中国的。《山本》的精神内涵,即贾平凹所要表达的东西其实已经和西方接轨,他写的是人性的不同侧面,人的欲望、混沌和迷茫,展示的是在军阀混战、战乱频仍年代山民们的生存状态和国民本性。贾平凹对人性的各个不同侧面进行了多维透视,对人的异化及人性的复杂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又具有西方的现代意识。
二、《山本》的精神内涵:人性的复杂及异化
贾平凹的原意是想为秦岭做志,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和动物记,但实际写作时发生了一些变化。草木和动物并没有成为小说叙述的重点,而是以另外的方式呈现了出来。麻县长作为一介文人,在战乱年代唯一的兴趣是收集秦岭的各种植物。文中写到:“麻县长来到涡镇后,先还是有许多治县的方略和想法,但下设机构不健全,那些干事有的压根没随他来,来的又差不多走掉了……麻县长就明白了一切,开始让王喜儒他们去山上挖草或折些树枝。”[1]164麻县长是秦岭西南双水县调到平川县的新县长,他不会长袖善舞,也不具备搞好政绩的条件,加上文人出身,在逛山、刀客频繁出没,国共对峙的战乱年代,他的政治抱负注定无法实现。他虽贵为县长,但只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并不拥有实际的军事领导权。涡镇在麻县长的安排下成立了预备团,选团长时,他有意让县保安队队长史三海当,但作为下级的史三海非但不愿意,还和麻县长争执,最后领着县保安队的人和各乡镇的打手走了,完全不把县长放在眼里。之后,麻县长既没有选背枪的阮天保,也没有选县政府的杜鲁成,而是让枪都没摸过的井宗秀当了团长,让阮天保和杜鲁成协助他。阮天保私下里用“挨了个肚子疼”表明他对这个结果的不满意,并感叹道:“唉,这世道,你不敢谦让,一谦让你就啥都没有了。”[1]81
麻县长在政治上不得志,却“兴趣着秦岭和秦岭上的植物、动物,甚至有了一个野心,在秦岭里为官数载,虽建不了赫然功绩,那就写一部关于秦岭的植物志、动物志,留给后世”[1]25。作者让书中这个人物去完成自己的未竟之志。小说中出现了几十种植物和动物,如斛草、荜拨、白芷、乌头、苍术、皂角树、痒痒树、婆罗树、贝母、天南星、赤地厘、肺筋草、狼尾花、油关草……这些植物有的是花草,有的是树木,有的是药材。动物有雕鸮、鸱鸺、鹖鸥、练鹊、百香、伏翼、鹭鸶、朱鹮、绶带等,这些是秦岭中的一些飞禽走兽。除了描写实际的动物外,小说中一些兽长着似乎是人的某一部位,“网上总是爬着蜘蛛,背上都是人面的花纹。偶尔树枝上站了猫头鹰,夜里啼叫,白天里一动不动,脸也是人的脸”[1]7,“突然一个人从半空下来就把老鼠抓走了。蚯蚓吓了一跳,那不是个人,是雕鸮,长着个胖老头的脸。”[1]78贾平凹坦言这样的描写是受到了《山海经》的影响。“《山本》借鉴了《山海经》的书写序法来描述秦岭植物动物的形状特性。”[3]与《山海经》不同的是,小说以动物喻人来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弱肉强食,这也是书中人物的生存法则。牛文治在卧牛沟被刘豹点天灯这一情节颇有意味。牛文治代表牛,到卧牛沟不仅犯了地名,还遇到了豹子,而豹子是吃牛的,注定他必死无疑。井宗秀属虎,遇到周一山,则是老虎上山。他有了周一山的帮助,办事更加得心应手,如虎添翼。吴掌柜和岳掌柜都是涡镇的大户,一直以来都在明争暗斗。岳掌柜是狼,想咬吴掌柜;吴掌柜是条蛇,蛇却想吞象,但他们都被老虎(井宗秀)收拾了。
小说中人所具有的兽性也巧妙地通过某些动物来隐喻。井宗秀既像老虎,又像鳖。他有鳖的忍耐又有老虎的残忍。他巧妙地借五雷的手铲除了涡镇的一个大户——岳掌柜,接了岳家的田地、屋院和店,将自己经营的酱笋坊扩大,一跃成为井掌柜。发现妻子不忠后,没有揭穿而是设计杀妻,一切做得滴水不漏。还把小姨拉下水,制造矛盾离间五雷和王魁,利用王魁除掉五雷后,又借麻县长之手除掉王魁。在王魁死之前,以土匪的名义将涡镇的另一个大户——吴家腾空,导致吴掌柜气得吐血而死。由此,井宗秀的奸诈、狠毒可见一斑。三猫和杜鲁成分别具有猫和狗的属性,猫比较狡猾,狗比较忠诚。小说中三猫因为记仇而背叛,杜鲁成则一直忠于井宗秀,正好印证了他们各自所属的动物性。阮天保的个性有些地方和井宗秀很相似,他也有当团长的野心,但最终没能如愿,又不愿屈居于井宗秀,于是出走。后来就和井宗秀对着干,两人慢慢成为敌人,并将涡镇也卷入腥风血雨之中。
在这里,涡镇就是秦岭的一个缩影。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背景下,秦岭战乱不断,战火蔓延之处往往有着各种飞禽走兽、魑魅魍魉。他们演绎着中国的人事,展示着中国的文化。涡镇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这里的山民有在人家办丧事时说风凉话的,有在别人出事时趁火打劫的,也有在人落难时主动去探监的。这里聚集的人有强悍的五雷、王魁,懦弱的吴掌柜,善良、机智的陆菊人,精明、奸诈又凶残的井宗秀,天真、活泼的杨钟,老实、厚道的杨掌柜……各色人等,一应俱全。贾平凹客观地展现了小说中不同人物的情欲、物欲、贪欲等各种欲望,将人性卑劣、粗俗、丑恶的一面都表现了出来,刻画了人性复杂多变的各个侧面。在结构上,《山本》摒弃了宏大叙事,以日常生活的描写将秦岭山区山民的普遍性格及其变异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山本》的哲学反思:对历史和人的考量
在作品中,贾平凹描写了各种人身上所显现出的本能和冲动,将人性的各种形态暴露无遗,在表现不同人性的同时,他还刻画了某些人性格中的多个侧面。作品的主人公井宗秀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个人物,在文中他被人们称为英雄。但井宗秀与其它革命历史小说中所塑造的正面英雄形象又有所不同,他更像是《三国演义》中曹操那样的乱世枭雄。革命历史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文艺政策和文艺传统的影响,无论是思想内容、人物塑造、叙事风格等方面都表现出类型化、模式化特征,其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大多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充满正能量的榜样人物。从客观上说,这类作品可以视为载道性质的文本。而《山本》则脱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真正做到了“我手写我心”。贾平凹在后记中坦言:“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首先是它的内容,和我在课本里学的,在影视上见的,是那样不同,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讳……我还是试图着先写吧,意识形态有意识形态的规范和要求 ,写作有写作的责任和智慧,至于写得好写得不好,是建了一座庙还是盖个农家院,那是下一步的事……”[1]284-285可见,贾平凹在创作之初也有过纠结和困惑,但最终他挣脱了正史话语体系,摒弃了意识形态对文本的约束,尽可能真实地呈现复杂的人性和历史。这样看来,与载道的革命历史小说相比,《山本》是言志的。
回到正题,井宗秀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贾平凹曾说:“我以前的小说都是人物一出场就基本定型了,《山本》的人物,尤其井宗秀和陆菊人,他们是长成的。而井宗秀、周一山、杜鲁成其实是井宗秀一个人的几个侧面。”由此可见,井宗秀的性格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变化和发展,作者从不同角度来刻画这个人物。在作品中正如贾平凹所说,井宗秀只是他自己的一个侧面,多谋善断的周一山、忠厚老实的杜鲁成则是他的其它侧面。总的来看,井宗秀这个人物让人觉得真实,但却不能简单地将他以好坏来论处。贾平凹写的是复杂人性的原始自然状态,他试图给我们呈现纯粹、真实的人性。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井宗秀被隐喻为城隍转世。城隍是中国民间和道教信奉的守护城池之神。预备团成立时驻进了城隍庙,成为团长的井宗秀是涡镇人期盼出现的官人,他被当地人当作保护一方的“守护神”,并受到大家拥戴。与此对应,陆菊人隐喻的是地藏王菩萨,属于佛教四大菩萨之一。她有一颗慈悲、善良的心,令众生衣食丰足。她同样被人认为是金蝉转世,可以聚敛财富,帮助井宗秀管理茶行,生意越来越好。在叙事上,作者既建构了涡镇的这两大神像,又对此进行了颠覆。一开始井宗秀作为团长罩着整个涡镇,但山民们并没有因为这两大神灵的庇佑而安身立命,而是不断有人死去,涡镇最后在一片炮火中彻底陷落。可以这样说,涡镇的人事变化皆因井宗秀和陆菊人而起。这在小说一开始就有所交代,“陆菊人怎么能想得到啊,十三年前,就是她带来的那三分胭脂地,竟然使涡镇的世事全变了”[1]6。井宗秀阴差阳错得到了陆菊人的胭脂地,陆菊人既气恼又无能为力,在对杨钟失望后,遂寄希望于井宗秀,并对他道出了胭脂地的秘密。从那之后井宗秀开始了发家致富、雄霸一方的戎马生涯。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性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精明变得狡诈、奸猾、自私,最后又变得冷酷、残忍、无情。文中一开始描述井宗秀时,说他是白脸,名字也比较女性化,到最后“井宗秀的脸真的虚胖着,没有了秀气,也不白净,发黑,像烟熏了一样”[1]219。在这里我们不免要问:井宗秀为何会变成这样?这到底是谁的错?井宗秀在涡镇算是个英雄,那么到底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笔者认为小说中正常的人其实都“不正常”,不正常的人才最“正常”。那些正常的人,人人都有私心和欲望。宽展师傅和陈先生虽是残疾(一个是哑巴,一个是瞎子),却世事洞明,对人世看得很通透。他们救治和超度着一个个生病和死亡的人,并有着自己的处世哲学。
《山本》以人性为点,以杀戮和死亡做线交织成一幅硝烟弥漫的战乱图画。民国时期国共斗争的历史与山民们在战乱年代挣扎、反抗的历史互相交织,共同构成了山本的故事。关于内战的情况,作者在叙述时没有明显的倾向,而是试图真实地呈现那段历史。其中有对党派斗争的暴露,也有对权力争夺的揭示。作品中到处都是枪声和死人,而且里面描写了各种残酷的刑罚,如点天灯、关禁闭、绑树上、活埋、剥皮等等,其中有很多都是极其残忍和有悖人性的酷刑。“《山本》的严肃性和批判性就在于深刻揭露了普通人性中的残酷基因。”[4]9作者有意描写了血腥的战争场面和惨无人道的刑罚,但他一再强调这不是一部描写战争的书,将这些暴露出来主要是为了批判人性和反思那段历史。贾平凹虽然不动声色地呈现了历史的闹剧,但他是以一种悲悯心态在写,“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只是我知道了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1]286事实上,作者自己也不愿面对那段历史,他也有无奈和恐惧,但是当他以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怀来展现它时,它就不会让人觉得那么沉重了。
那样一个战乱的年代,人们一个个死去,无论是普通人还是称霸一时的英雄人物,他们都死了,而且死得很平淡、很随意也很突然。贾平凹坦言死亡得越是平淡、突然、无意义,越是对那个时代的诅咒。小说中井宗秀的死很值得玩味,他是在某天夜里洗脚时死于非命的,作为书中的英雄人物,他的死很突然,也很随意。初看这一情节可能会觉得突兀,经过思索后发现又在情理之中,而这正是贾平凹的高明之处。在他的笔下,无论是英雄还是普通人,在战争年代死亡对他们来说是平等的,谁都有可能随时死去。同时,他以战争写人性,写得非常残忍,也更进一步也写出了时代的残酷性。《山本》让人性在历史中演绎,人和历史共同完成着彼此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