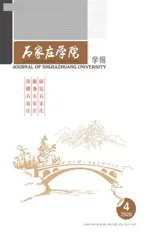“老三届”散文家的创作特点、贡献及局限
2020-02-26周纪鸿
周纪鸿
(海关总署驻天津特派员办事处 研究室,天津 300090)
所谓“老三届”,是20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在校的1966年、1967年和1968年三届初、高中学生的简称。当时这些中学生因“文革”的原因,造成了在学校的堆积,到1968年出现了史上绝无仅有的六届中学生同年离校的奇事。据统计,“老三届”中学生共达1 000万人,很多“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成为知识青年(简称“知青”)。“文革”结束后,“老三届”当中涌现出不少著名作家,如张抗抗、梁晓声、史铁生等,被称为“知青作家”。其中也有些作家虽是“老三届”,却没当过“知青”。他们因伤病、政策等原因免于下乡,有的当了工人、教师或者参军入伍,有的家在农村的成了回乡知识青年。
“老三届”散文家人才济济,硕果累累。这批作家先是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经受生活的考验,饱尝了底层生活的艰辛,然后用一支笔抒发情怀、寄托理想和希望。在当代文学史上,他们占据很重要的篇幅,国内外各种文学大奖上都留下了“老三届”们的名字。“老三届”散文家以其镌刻着底层生活烙印、富有个性化表述和开放社会印迹的作品,走向时代经典的史册,走上“朗读者”的舞台,走进各类教材,受到了当代读者的钦敬。多年来,对“老三届”小说家的研究较多,而对“老三届”散文家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本文把目光对准“老三届”散文家的创作实绩、特点以及在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和局限,是一件富有意义的事情。
一、“老三届”散文家的创作特点
(一)“老三届”散文家以小说家的笔触书写自己深刻的生活感悟
“老三届”散文家都不是单纯的散文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先是小说家或诗人,然后才是散文家。如竹林、肖复兴、梁晓声、张承志、史铁生、张抗抗、贾平凹、王小波、毕淑敏、北岛、舒婷等人,在散文写作之前,他们的小说、诗歌在当代小说、诗歌当中已经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获得了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小说年度奖甚至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等一系列大奖,得到了从普通读者到专业人士的广泛认可。
“老三届”们的散文创作,使风花雪夜、小桥流水、抒情式的散文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小说家的文笔恣肆、思路刁钻,其散文创作便一改单纯散文家常有的规范拘谨、视野狭窄、掉书袋等毛病,变得浮想联翩、灵动潇洒。他们的散文由于吸纳了小说家和诗人的智慧之光而丰富多彩。特别是“老三届”散文家由于底层生活的历练,蕴含了充足的地气,在回忆知青生活、抒发现实感触中,带有浓重的岁月痕迹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知青多舛的命运在“老三届”散文家的心灵上的烙印太深太重。他们急于反映自己患难与共的知青生活和命运,凭吊流逝的岁月,如肖复兴的散文《雪痕》《复兴随笔》和肖复兴、肖复华的《啊,老三届》等。历史使“老三届”成为特有的专用名词,在这普通的三个字中,谁又能理解其中所包含的痛苦与欢乐、泪水与笑容、失望与希望、失败与成功、惶惑与挣扎以及所走过的曲折的路?甚至可以说,特殊年代曲折跌宕的生活影响了“老三届”散文家一生的创作。
“老三届”散文家,由于有坚实的小说创作基础,因此他们的散文有人物和故事情节、有画面感,读起来耐人寻味,如舒婷的散文集《Hi,十七岁》、高红十的散文《十七岁我去插队》、史铁生的《我二十一岁那年》、张承志的《雪中六盘》、叶梦的《小溪的梦》《湘西寻梦》、苏叶的《怎不忆江南》等都是对知青生活的回眸以及对当时亲历民俗、乡情和悲欢离合的真实记忆。燃烧的激情之火和悲伤的泪水与辛勤的汗水,交融出滚烫的文字,留下了知青岁月五味杂陈的时代画卷。韩少功的《山南水北》是一部跨文体的长篇散文,期间夹有小说元素。事实证明,“老三届”小说家和诗人“加盟”散文,带给散文的不仅是数量的增多,而且使散文飞上了一重天。他们开阔的思维方式、高妙的审美品格和绚丽多姿的语言以及深刻的人生体味和不拘一格的行文气势,开拓了散文的新境界。
“老三届”散文家的作品,对曾经的农民生活和命运、地域风情、人文地理倾注了真挚的情感。叶辛笔下的贵州农村,张承志笔下的内蒙古草原,肖复兴、梁晓声和张抗抗等人笔下的北大荒,史铁生笔下的陕北窑洞,韩少功常忆起的在湖南插队“用油灯温暖着的岁月”,毕淑敏、高洪波对军旅生活的回忆,特别是张抗抗《最美的是“北大荒”》,这些都代表着“老三届”们真实而复杂的情感。“北大荒”悲壮的风雨,曾是浇灌一代人青春的源泉。当那时的焦躁苦闷、哀伤渴求如闪电旋风般纵驰又悄悄隐没在时光的烟尘之后,真正沉淀在她们记忆深处并刻骨铭心的却是荒凉寂寞的原野上一幅幅极为辉煌绚丽的大自然图景。张抗抗说:“无论我们多么厌恶、憎恨甚至咒骂过它,我们心中却留下了对它千丝万缕的眷恋。……正因为我们曾无数次地参与了那种美,在与美的瞬间交流中,渗透了我们内心最真挚的情感,我们才会觉得唯有这种美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它属于我们苦难生活的一部分。”[1]272
“老三届”散文家的作品具有底层生活的真实鲜活——毛茸茸、活生生、泪淋淋,显示着生活的质感,洋溢着青春的热情,令人荡气回肠。同时又有理想主义的光辉,记录着那个时代年青人迷茫的眼神、对未来的憧憬、对“诗与远方”的渴望以及对宏大理想的追寻。
(二)品味叙写特殊境遇下的酸甜苦辣,深刻体验和理解人间真情
“老三届”散文家有不少写到自己切身经历和父母至亲、朋友、老师等的回忆性散文,如泣如诉、真实可信。苦难是文学的灵魂,这句话适用于“老三届”散文家。
舒婷的散文《心曲千万端,悲来却难说——怀念父亲》,讲述了其父亲原本是白西装、打发蜡的银行家,在成为右派补遗后悲哀的命运,以及他对妻女的娇惯爱怜,真切动人。莫言的《妈妈的眼泪》,写困难时期,家里只剩下三棵白菜,原本留着过年包饺子用,但必须卖掉,在卖掉的时候,莫言多算了老太太一毛钱,妈妈失望与悔恨地流下了热泪。其情其景非常感人。竹林的长篇散文《挚爱在人间》14万字,讲述的是自己与被海峡分隔数十年的父亲从相逢、相别再到永诀的故事。散文以纪传体的形式和意识流的手法,在父女重逢的雨中、路上和家里,巧妙地穿插了他们各自的人生苦难、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这是一个被海峡彼岸的父亲长期遗弃在大陆的女性,失去父爱又意外得到短暂父爱的歌哭。学者父亲与作家女儿传奇般的聚散,使人们感叹天意的窅然与悠远。正如竹林对父亲的一片真情,在“老三届”散文家的笔下几乎都写过自己的父母亲情。如:梁晓声的《慈母情深》;张抗抗的《苏醒中的母亲》《母亲的精神财富》;张胜友的《父亲》;史铁生的《合欢树》是儿子对母爱的一首热烈真挚的颂歌,《秋天的怀念》表现了他对已故母亲无尽的爱戴以及对“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悔恨;贾平凹的《祭父》《我的母亲》;陈建功的《我和父亲之间》《妈妈在山岗上》等篇,通过作者与父母亲人之间的感情关系,使读者聆听到作家心的絮语,从而体味“老三届”散文家的精神慰藉。
“老三届”散文家大多数是十几岁、二十出头就离开父母亲人,到东南西北等边地上山下乡,在狂热的社会氛围下被赶到了社会底层。他们往往精神上困惑,肉体上饥饿,情感上缺失,心理上苦闷。当他们逐渐懂事的时候,最令他们想念的便是父母亲情。这种境遇下写的散文是他们最真实的体验和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些扣人心扉的亲情书写,带有自传色彩的散文,活泼灵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三)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关注社会民俗风情,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信念
肖复兴、史铁生、张承志、北岛、王小波等都是北京的“老三届”,史铁生和张承志还是清华附中的同学,而北岛1973年还和史铁生在一起,他们都喜好文学。陈建功是8岁从北海移居北京,在人民文学杂志社的大院里长大。肖复兴的《那一排钻天杨》、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承志的《四十年的卢沟桥》、北岛的《青涩记忆中的北京味儿》、王小波的《北京风情》、陈建功的《涮庐闲话》等篇,都是从各自的角度书写北京的人和事,写出了老“北京滋味”。他们投入生命的真切体验,超越现象,上升到文化意识的高度,成为不断发展、不断丰富创造的一环,抒发着他们的情绪感慨和眷恋思念。
“老三届”其实是整整六届中学生。“文革”将这些血气方刚的中学生卷入了历史的狂澜,他们“停课闹革命”,搞全国大串联,在北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政治风云席卷了“老三届”,让他们从年轻时候就关心国家大事、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梁晓声、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等“老三届”散文家,有着近乎相同的经历。梁晓声在北大荒兵团劳动,6年后被推荐到复旦大学学习;张承志到内蒙古草原插队,4年后到北京大学学习。不同的是,张承志1978年又考取了社科院研究生,并获硕士学位。梁晓声、张承志的散文凸显政治倾向和哲学思辨。梁晓声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我们的时代与社会》《我相信中国的未来》《中国人,你缺了什么》、张承志的《绿风土》《清洁的精神》《一册山河》《大地散步》等,都是以平民立场和底层关怀,关注国家前途命运、社会变化,思考国家责任,呼唤社会良知。他们的散文带着一种立场、一种姿态、一种饱满的激情、一种正义与良知的自我呈现、一种与庸俗现状永不妥协的战斗品格。
(四)“老三届”女散文家占据“半壁江山”,开创了女散文家创作丰收奇迹
“老三届”女散文家中的代表作家有张抗抗、竹林、毕淑敏、陆星儿、舒婷、吕锦华、叶梦、苏叶、周佩红等。正如戴锦华所说:“迅速崛起并不断更新的女作家群,是新时期重要的文化景观之一。事实上,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深刻的文化转型之中,女作家群成了这一文化、话语构造相当有力的参与者。”[2]138众多的女作家的作品不间断地以20世纪80年代特有的“文学的社会轰动效应,引发着文化转型中的微型地震:提请或负载着社会质疑或批判的主题”[2]138。
中国自古以来男尊女卑。虽然有零星女诗人的作品问世,但毕竟不能和男性作家平分秋色。100年前的五四运动中,出现了第一批女作家,有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凌叔华、苏雪林等。20世纪30年代后的抗战时期,涌现了丁玲、萧红、草明、杨绛、林徽因、张爱玲等又一代女作家。新中国成立后,又有茹志鹃、杨沫、宗璞等女作家。到了80年代,终于迎来了大批女散文家争奇斗妍的局面。她们以各具色彩的作品,掀起了女性散文的高潮。在这期间,“老三届”女散文家异军突起。如果说“老五届”散文家①“老五届”散文家是指1961年以后入学、1966年至1970年毕业的大学生中涌现出的一批散文家,以梁衡、余秋雨、卞毓方等为代表。参见拙作《试论“老五届”散文家群体》,载《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0期。群体还是以男性为主的话,那么,到了“老三届”散文家中,女散文家不但人数多、作品多,而且质量高、贡献大。据中国散文学会统计,自2000年设立“冰心散文奖”以来,获奖的女散文家占了一大半。“老三届”女散文家大量涌现,主要得益于文学环境的变化,破除了女性作家进入文学写作领域的障碍,反映出女性地位的提高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张抗抗、毕淑敏、叶梦、周佩红是“老三届”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女散文家。她们的散文文笔细腻、精雕细刻,大胆坦率、入木三分,使人们不得不对“老三届”女散文家的匠心独运肃然起敬。她们分别代表着从工农兵中成长起来的女散文家,虽经历不同,但殊途同归。张抗抗生在杭州,长在哈尔滨,落户北京。她的散文天然地具有宽阔的视野,如《牡丹的拒绝》以独特的求花不遇视角反题正作,在书卷墨香中完成了一次心灵的跋涉。而《一个南方人眼中的哈尔滨》《北佬看杭州》等体现了她像“新一代游牧民族”永无归宿的浪漫移民的复杂心绪,在极大又极小的世界里寻觅创造自己精神的家园。毕淑敏是军官后代,她的创作虽起步稍晚,但其学识渊博,既读北师大心理学研究生,又参加解放军艺术学院创作班,散文中既有医学、心理学专业的底色,又有新疆、部队、都市的浓重印记。她的《婚姻鞋》《素面朝天》《大雁落脚的地方》《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等散文集,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她认为,散文是蕴涵切肤之痛的标本。心的运行是透明的,它的脚印被语言固定下来,就成了散文。散文看起来很随意,其实有着戒律,它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感情的追述,在某种意义上就有了史的品格。读她的散文能读出一个活脱脱的毕淑敏来。由于毕淑敏本身丰富的阅历,从边陲到首都,从部队到大学,从学医到学文,从《拯救乳房》到拯救心灵的《你要学会好好爱自己》,她始终关怀的是人的生存状态。做女人、做母亲、做医生的角色,使她下笔从没有忘记治病救人的宗旨、普渡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德,她将对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作一种集道德、文学与医学心理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她正视死亡与血污,下笔常令人战栗,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企望和平安宁。她的《温柔就是对抗世间所有的坚硬》《恰到好处的幸福》等散文都属于此类。其实,毕淑敏与其说是一位散文家,不如说是一位心理学家,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是针对人们的心理疾患而开出的处方,这源于她的善良和对人的隐秘心理的洞穿和熟稔。叶梦初二便离校,当了11年工人。直到1987年,她才调至湖南作协从事创作,截至90年代末,她已出版了七部散文集,并获得了各类奖项。叶梦的散文更是充分女性化的,如:《月之吻》《不要碰我》写新婚性爱的愉悦颤抖,《创造系列》写怀孕、剖腹产、养育的神秘奇谲和喜乐悲苦……从生理到心理,大胆地写出了女人的真实感觉;《羞女山》高扬起女性不屈的精神自我,更张扬出女性充满创造之伟力的生命自我,也从一个侧面展露出女性散文成熟的曙光。周佩红既是“老三届”又是“新三届”大学生。她从华东师大毕业后,任《萌芽》杂志编辑。她既编散文,也写散文。其散文集《亲密关系》《内心生活》《我的乡村记忆》《上海私人地图》等,写的是现代都市人的心态,感受的是复杂人生阅历的底蕴,意犹未尽,具有新艺术散文的特点。苏叶的《能不忆江南》出手就语惊四座,《写给自己》反思自我,其深刻、坦诚几近残酷,文章全然不见《小窗日记》《总是难忘》里那种温雅聪灵的女性,从一个侧面呈现现代女性的矛盾心态。她告诉人们,这种心态的变异不是人生选择错误的悲剧,而是人生“别无选择”的痛苦。
随着视野的拓宽,中国与外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老三届”女散文家的思路也大开,在她们眼中,外面的世界不再陌生。她们的散文体现出感觉化、情绪化倾向,这与女性作家敏感细腻的艺术感觉有关。通过女作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她们的作品灌注了大量的感性、幻觉、无意识、情绪等心理因素,并采用“陌生化”等艺术技巧将这些感觉、情绪和思想有机融为一体,带领读者唤醒麻木的心灵。
二、“老三届”散文家的贡献
“老三届”散文家的创作对新时期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特别是对当代散文史的丰赡繁复、精神追求、文体探索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创作持续的时间长、跨度大,作品数量多、质量较高
如果从时间最早上看,贾平凹的散文《深深的脚印》1974年发表在《西安日报》;如果从影响最大上看,要算张胜友的散文《闽西石榴红》,发表在《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6日战地副刊头条,随后被选入《中学语文课外阅读文选》。这篇散文沿着革命老区的红色之旅,追寻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闽西留下的革命足迹。勃发的激情和铿锵昂扬的文字,显示出“老三届”散文家正直睿智、格调高昂、文采斐然的特点。继而,“老三届”散文家们的作品接踵而至。虽然受市场经济和社会阅读方式变化的影响,但“老三届”散文家的创作似乎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他们以顽强的意志,进行了长达40余年的散文创作,至今热度不减。
2018年是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在此时间节点上,肖复兴出版了回望青春的《北大荒断简》,将笔触集中在一个令他魂牵梦绕的北大荒大兴岛,写下了知青与当地乡亲的生活命运。肖复兴说,2018年是其前往北大荒大兴岛整整50年,这部作品既是送给自己也是送给一同去北大荒知青朋友的一个纪念,同时还是对我们这个国家半个世纪风雨兼程不凡之路的追忆与缅怀。饶有意思的是,在这部新书的发布会上,肖复兴和梁晓声同时出席。梁晓声认为此书充满了“温度”。
贾平凹是“老三届”散文家中高产高质的代表。截止2001年就出版了《月迹》《爱的踪迹》《心迹》《商州三录》《抱散集》和《贾平凹散文自选集》等46部散文集。其中:1989年,《爱的踪迹》获第一届全国优秀散文(集)奖;2005年,《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他的散文以其家乡陕西汉中的山川风物、人情世俗为主要书写对象,挖掘陕西地域文化和人文旅游文化,表达自己对人生、宇宙的感悟,质朴真诚,略带浓郁浑厚的黄土高原气息和原始野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贾平凹散文创作境界大变。之前,贾氏散文以精短为主,偶尔也写过长篇散文,如《老西安》长达9万多字,是他经典散文中最有价值的一部作品,是作家以文化学者身份透析历史文化名城所作的人类学方式的长篇散文。其中,既有城市史调查又有历史军事史研究,还有经济文化史研讨,纵横捭阖,田野考察、史料研究与个人感悟结合在一起。《秦腔》是从八百里秦川上大喊大叫的地方戏种,挖掘出秦地厚重的文化底蕴。“秦腔”不但是秦地天籁地籁人籁的共鸣,更成为贾平凹心中挥之不去的永恒交响。
2018年11月6日,由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举办“文章的复兴:贾平凹散文创作现象学术研讨会”,并为贾平凹散文集《自在独行》发行百万册庆功。如此大的发行量,在“老三届”散文家中应该是拔得头筹!“老三届”中比较活跃的一线散文家,大多都有几部甚至十几部散文集,有大量的读者和拥趸。他们的散文不仅是广大读者的精神食粮,也是文学出版界的“家常菜”。
(二)“老三届”散文家的散文创作不断追求艺术上的创新和探索
诗人北岛的散文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他的散文集《失败之书》、随笔集《时间的玫瑰》《青灯》《蓝房子》和《城门开》,以其鲜活有致、像珍贵的心灵绿洲让天涯孤旅得以栖居,文中充满幽默、观察、记忆与回应,纯净的文字不仅袒露自己更能洗涤众生。北岛2007年定居香港。多年漂泊海外的生活,加深了他对人性的洞察,又充满着对整个人世的悲悯。他有时采用隐喻、寓言似的国际化方式,拓展了汉字所能表达的空间。王小波的散文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与其说是散文,不如说是杂文。文字充满戏谑、幽默,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如:《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在黑色幽默之后潜藏着深刻机敏关怀的性格以及冷幽默面孔下的热心肠;《工作与人生》是一篇思想随笔,在行文中流露出幽默和反讽的语言风格。
散文是作家的心声,必须高扬个性。个性是艺术的生命。散文更加强调表现作家对生活的思想感受和真知灼见,比任何文学体式更直接袒露。“老三届”散文家在作品中大胆地敞开自己的胸怀,不装扮、不掩饰,直抒胸臆,豁然面对生活的剧变,真诚抒发自己的独特感受。贾平凹说:“没有在生活中独特的感受和发现,散文一个字也不敢写。”[3]96孙犁称赞贾平凹,“他像是在一块不大的田园里,在炎炎烈日之下,或细雨蒙蒙之中,头戴斗笠,只身一人,弯腰操作,耕耘不已的农民”。不单是贾平凹,梁晓声、史铁生、张承志、赵丽宏等“老三届”散文家也都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不断探索散文艺术创作的新路径,不断尝试新方法。“老三届”散文家总带有一股锐气和对生活的深层体验,在散文中表现出他们独特的生活生命轨迹和深刻的透视社会、认识世界、探讨人生、追寻真理的求索过程。
(三)“老三届”散文家是在用生命写作,他们的散文很多是一种无法命名的生命绝唱
有人说作家有三种:凭知识写作、凭才气写作、用生命写作。“老三届”散文家中,很多人的写作是“用生命写作”。他们很少在散文中掉书袋,或者引用历史文献、名人名言之类,更多的是强调作者对于写作的全身心投入,强调作家作为生命个体要深切地体验对象、独特地感悟人事物景、真实地表达生命体基于人性尺度的情感、思想和趣味等。史铁生、梁晓声、王小波、张承志、苏叶等“老三届”散文家以更加宽广的人类精神和情怀,追求恒久的意义价值。尤其是史铁生《我与地坛》《好运设计》和《病隙碎笔》等散文,深入地镌刻着他的生命意识。身体的残疾并没有给他带来心理的病态,他像健康人一样,皱着眉头,端详着地坛和北京胡同深处熟悉的一切人事景物,思索着美好的未来。正像王蒙所评价的那样,史铁生身体的不幸造就了他的悲天悯人,深邃追问,碧落黄泉,震撼通透,沉潜静谧。他以地坛为题的《我与地坛》和《想念地坛》,是感悟自我生命最为真实、最为深刻的作品,是借“地坛”来托物言志。地坛既是他倾述的对象、情感的寄托物,还是他放飞心灵的发射场。他在这里倾吐思绪,享受安静,思念母亲,思辨运命……“地坛”是他身边的“清平湾”,也是他寄托灵魂的墓志铭。他在这里向不公的命运做绝对的精神反抗,在这里精神升华到澄明的境界。
梁晓声的散文随笔集很多,越是到晚年越是老辣深刻。特别是《我想我看我论》《羞于说真话》《人生真相》《我的人生笔记》《梁晓声自述人生》《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以及《我们的时代与社会》等散文随笔集,代表着他独特的思辨特点和正直的解剖锋芒。以自己生命的言说,履行着“老三届”散文家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对民族的忧患意识,对人民命运的关心。他深刻地展示知青群体的痛苦与快乐、求索与梦想,真诚地礼赞他们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美好与情操,为“知青”一代竖起不屈的精神丰碑。他的写作始终秉持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情怀,始终高扬人文主义的旗帜,从不会因为所谓纯文学的原因而放弃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批判。而“韩少功更是富有思辨能力的好手,亦叙亦思,有描绘有分解,他的精神空间与文学空间纵横古今天地,耐得咀嚼,值得回味”[4]2。
“老三届”散文家中的北岛、舒婷和赵丽宏都是以诗歌见长的散文家。赵丽宏的散文入选小学、中学语文课本达到30多篇次,并且多次被选作语文试题。开始他作为“可教育好子女”中的一员,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他在崇明岛下乡,经历了“炼狱般的痛苦”,在《岛人笔记》中,清楚地记载了他的痛定思痛后的大彻大悟以及本真生命对荒诞政治文化的抗争和批判。他的散文《雨中》《望月》《周庄水韵》《致大雁》《诗魂》《与象共舞》等,体现了他对文本形式的精美打造,对美的内容与形式的追求,使其获得了“美文作家”的称号。赵丽宏不仅用“诗化”途径创作散文,在“新艺术散文”思潮中与时俱进,还借鉴小说手法,进行了林林总总“故事体”散文的审美创造。这就使得他的散文具有生气勃勃的前沿性和创造性。阅读“老三届”散文家的作品,是一个不断接近一个时代的过程,读者仿佛在与一群苦难深重的健朗有趣的灵魂建立链接,从而使自己对曾经的生活的理解不断丰富和深入。
(四)在散文文体上的突破和创新
我国文学史上有迹可寻的事实揭示了这样一条规律:问题的变迁引起了散文创作的发展,推动着散文艺术的繁荣。优秀的散文家都是文体家,他们的作品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而且有着问题的示范性、规范性。贾平凹用中国传统美的表现方法写了大量形式活泼的短文,如《关中论》《观菊》《商州三录》等,读后令人耳目一新。可贵的是,在“老三届”散文家中,除了贾平凹,史铁生、梁晓声、张承志、王小波等人的散文在语言和文体上也独树一帜,具有很高的辨识度,读者从文调和语言风格上便能辨认出是谁的散文。当然,贾平凹的散文在“老三届”散文家中是出类拔萃的,具有散文大师的格局和气象。张抗抗的散文,充满诗意的想象与深邃的哲理交相辉映;赵丽宏的学校教育系列散文,广受师生们欢迎;北岛的散文构思奇绝,视野开阔,常有惊人之语,令人拍案叫绝;而王小波的散文黑色幽默、风趣反讽又令人忍俊不禁。“老三届”散文家对问答体、日记体、序跋体、书信体、故事体等也多有尝试。无论是什么文体,散文乃是人生的沉淀,写散文本身也是一种人生追求。“老三届”散文家,不论是艺术的还是哲学的,不论是人生唯美的还是执着宗教的,都是从多角度、多层面观察与思考大千世界的窗口,其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在人生。“老三届”散文家在生命成长期留下的精神记忆、难以磨灭的生命情结,构成了文学创作的主题。
三、“老三届”散文家的局限
毋庸讳言,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影响,部分“老三届”散文家的文化积淀不够厚实。这一方面与“老三届”散文家过早地跌入社会底层、学业中断有关,略显“先天不足”;另一方面也与“老三届”散文家们没有把精力全部投放在散文创作上有关,所谓“后天失调”。古今中外的大散文家、文章家几乎都是学富五车、国学深厚的大家、通才。远的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唐宋八大家”,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方苞、姚鼐、刘大櫆,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在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座丰碑。现当代的散文大家鲁迅、巴金、季羡林、余光中、孙犁等,无不是思想家兼散文家。单纯的散文家很难具有突破前人的能力。因为文章写到一定程度,比拼的不仅是文字功夫,而是深邃的思想、深刻的洞察力、卓越的分辨力、超凡的叙事能力和自成一家的语言。散文需要生命的投入,才能闪现灵魂的光彩。“老三届”散文家们,在他们风华正茂的季节却在“红海洋”里折腾,在最需要吸吮文化乳汁的年代却突然断乳去荒原喝凉水。尽管有一部分“老三届”成为工农兵学员,或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或研究院,但参差不齐的底子显而易见。
“老三届”散文家在散文理论的开掘和创新上贡献不多,在散文批评上存在局限。一方面,散文批评零散单薄,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另一方面,在散文理论的研究上,既动力和兴趣不足又缺乏学术训练和理论基础。贾平凹算是“老三届”散文家中对散文理论贡献突出的代表。1992年,贾平凹提出“大散文”概念[5],1994年,又在《美文》杂志上撰文《弘扬“大散文”》。之后,在其主编的《美文》杂志上,在指导思想和编辑操作等方面,引导散文向大情、大理、大境界方面努力拓进,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此外,以贾平凹为首的老三届散文家,为其他散文作者的集子撰写序言,给当代散文创作评论添砖加瓦。如贾平凹不仅给匡燮、李佩芝等老散文家的集子写序,还给许多青年散文家作序、评论,给予鼓励。张抗抗、叶辛、梁晓声等也曾为青年散文家作序等。总体看,“老三届”散文家在散文理论与批评上热情不足,贡献也不够理想。
“老三届”散文家群体是继“老五届”散文家群体之后肩负历史责任并充满活力的一群,他们的散文沉重、深刻,有故事,有难以忘怀的伤痕,有红色浪漫的血迹,有带着盐碱的汗水,有滚烫的热泪,更有令人警醒的“发汗药”。他们是当代文坛承前启后的一茬人,是连接“小知青”①指1969年至1976年间下乡的知识青年。散文家和“新三届”②“新三届”是指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后的1977级、1978级和1979级的大学生。散文家之间的桥梁。在当代散文发展史上,“老三届”散文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作为一个散文群体,“老三届”散文家群体是松散的、各自为战的。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群体宣言和流派思潮意识,更缺乏以流派思潮为标志的论争,但他们是不可复制的一群散文大侠,更是不可替代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