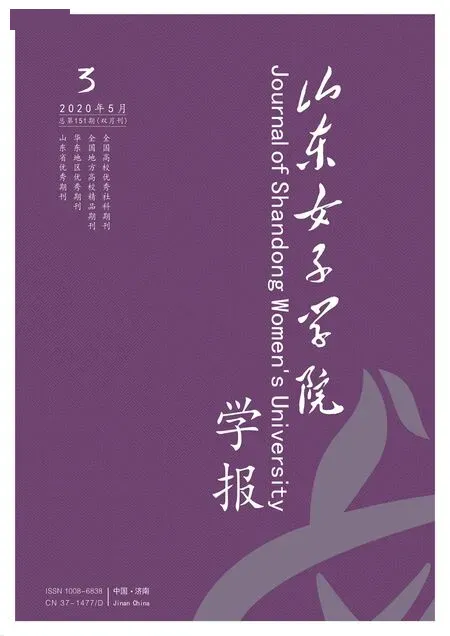赛博格与女性主义
2020-02-26刘思甜
刘思甜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一、赛博格与《攻壳机动队》
20世纪60年代,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两位科学家克林斯(Manfred Collins)和克兰(Nathan Crane)提出了一种大胆的设想,即通过机械、药物等技术手段对人体进行拓展,创造出拥有强大力量(男性)的身体,使人们能够探索尚未殖民的外层空间的疆界。为了更方便地阐明这一观点,他们结合“控制论”(cybernetics)与“有机体”(organism)两词造出了“赛博格”(Cyborg)这一概念。简言之,赛博格即机械化的有机体,是有机体与机械的结合,其中机械只是作为有机体(包括人与其他动物在内)身体的一部分,思考和动作均由有机体控制。《攻壳机动队》就是依据这一设想而来的一部未来科幻电影,但是由于主角素子是一个改造后的女性大脑和机械身体的结合,从而引发了一些女性主义的思考与争论。
在《攻壳机动队》背景所设置的未来时代,赛博格作为一种更为高级的有机体无处不在。人们热衷于用已有的科技来改造自己,像是克服不能喝酒的基因缺陷或是转换性别等等。乍一看这样的改造似乎是振奋人心的,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科技来治疗疾病,哪里有问题换一个机械的就好了,而且还可以比原本的更好用。可是真的是这样吗?作为有机体,人类身体的每个部分都是互相联系的,哪怕只是一小部分发生变化,也会引起整体的变化。所以,当我们身体的某个部位被改造之后,身体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从而进一步撼动我们的身份意识。就像影片中的素子,尽管她是如此幸运,通过身体的改造保留了自己的大脑得以存活下来。但是她的存在却令其自身和他人都感到困惑与害怕,因为她的改造的成功引发了一个长期以来都未得到合理解答的问题:人和机器的划分标准到底是什么?如果认为只要还拥有人类意识就算作人类,那么素子明显还属于人类的范畴;但是如果只有完全拥有人类身体和大脑才能被当作人类,那么显然素子不能再被纳入人类的这一范畴了。还有一种不那么科学的分类方式,即根据有机体自身的感受决定。由此来看,似乎也很难下最终的定义,因为素子在被改造后一直就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迷惑不解,这种没有归属的感觉一度使她陷入困境之中。但是这种迷茫又反过来证明了她的人性本质,正因为是人类,所以才会对所居住的身体所经历的社会、心理等变化感兴趣。这种身体转变的关键在于自我认同。就像现在有很多选择变性的人一样,有些即使不通过身体的改造也能确定自己的性别。所以,身体终究只是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而已,心灵上的认同也是十分关键的。这取决于身体改造的目的与自我强烈的认同感。因为素子被改造的初衷并非对一个生命体的怜惜,而是一种将她作为武器的希望,这也影响了素子对自我身份的看法。如果仅仅是作为人类或是其他有机体,是绝不可能被当作武器对待的,所以在这一层面上素子似乎不能算作是人类群体的一员了,哪怕她依旧拥有人类的大脑。但是正因为保留了人脑,导致她不可能完全像作为武器的机器人那样行动。素子有自己的想法,会对人类和其他动物有怜悯之心,这似乎证明了她其实内在还是属于人类的。这样混合的身体就导致了素子对自身的困惑,也导致了我们对这一困境的思考。如果机械身体可以给我们带来好处的话,我们到底能不能采用?当你获得一部分机械的躯体的时候,这意味着你和原本的人类不一样了,可能不再因为身体的疼痛而忧愁,但同时你的意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就像素子会因为自己的不同而感到孤独,会因为没有人和自己一样而难以建立社会关系,更不用说亲密关系了。不得不提到,在赛博格盛行的未来,人类的定义究竟还存不存在,会不会变化都是未知的。而彼此之间的交往也会有巨大变化,当你爱的人是和素子一样的赛博格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这段关系?而且,在这个时候,判断个体的基准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我们之前还会因为决定是不是你的标准是记忆还是行为而争论不休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确定证明你是你的标准仅仅是行为。因为在未来社会,个人的记忆很容易就被抹除甚至被替换,那么除了行动之外就没有什么是值得信任的了。但这样似乎会产生严重的结果主义导向,特别是当我们的道德判断没有了动机的辅助,只能依靠行为的时候,那么大脑的保留或许也仅仅是一种象征罢了。
此外,仔细思考素子出现的初衷与赛博格产生的目的,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呈现出的仍然是一种武力斗争的场景。而这种武力斗争不正是男权制的产物吗?所以赛博格的出现并非是完全的平等社会的曙光,还可能是进一步的霸权斗争的先兆。如果未来是真正和平的世界,又何以需要如此多的有战斗力的赛博格的存在?将这种身体改造作为争取平等与赋权的手段并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们依然需要探索更多的途径。但是这也不意味着赛博格的出现就只是一种幻想和不合理,它依旧有其意义所在。它让我们对为实现这些变化而采用的技术感兴趣,对由此产生和持久的变化的政治感兴趣[1]。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种改造确实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积极作用。完全的机器人作为一种机械,最终只是命令的传达与完成,很容易像影片中展现的那样被入侵大脑。所以即使在未来,人脑也依旧被看作是更为智慧的机体。影片中的反派也是利用了人脑来为自己创造信息网络,可见人脑的极端重要性。人脑之所以承担如此重要的作用,最大的原因在于其使得其所承载的身躯有了自己思考的能力,从而能够将自己与其他无机体相区分,并做出更合乎理性以及人性的行动。然而,拥有人脑真的意味着更好吗?答案是不一定的,否则,为什么素子一直在为自己的身份认同而困扰,而现在的我们也是一直为一些想法而疑惑、挫败。有时候,似乎不通过思考就将问题放任不管更为幸福,智慧的拥有同样会让人产生一些其他非人生物不可能产生的困扰。这样一看,做一个机器人似乎比做一个依旧保有人脑系统的赛博格要幸福。但是,那样一来人类就真的不复存在了。基于保留人性的考虑,赛博格似乎是一种更加折中和合理的选择。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如果能够通过科技来使得身体更加强壮甚至不用再作为繁殖的功能而存在的时候,肯定是更有利于自己的发展与自由的。素子之所以如此强大,能够作为武器,无外乎因为她拥有了最高配置:人脑和机械身体。而她的这一形象在女性被认为有着不一样的身体结构而显得柔弱的当代,可以说完全打破了性别界限,只要通过改造,女性就可以比任何生物都要强大。此外,原本的女性身体构造还有繁殖和养育下一代的作用,而机械身体则为其免去了这些“烦扰”或者说是性剥削的基础。机械身体的构造似乎更善于打斗而非生育,而没有痛感的身体更不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共情能力,这也打破了女性伦理思维的固有观念。总的来说,赛博格的出现将使得性别界限开始模糊起来,也使得自然与文化、人类和机器的区别不那么明显。因此,做一个保留着智慧大脑的赛博格似乎比做一个完全的人类要好,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
二、赛博格对女性主义的影响
对于赛博格与女性主义的关系,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赛博格宣言》中作了详细的阐述。在宣言中,哈拉维首先提出了“女性化”的概念。这一概念与波伏娃和巴特勒(Judith Butler)关于女性是社会建构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她指出在当代社会,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福利国家的衰退以及家庭工作经济(homework economy)的出现和发展,都使得一直占据社会等级中霸权地位的白种男性变成了在失业问题面前最脆弱的群体。相比之下,女性面临的状况反而有所改善:从比男人的状况糟很多,变成了不比男人糟多少。而且,在社会中,特别是职场中,似乎已经出现了一种群体的女性化现象。不管是什么性别都被当作后备劳动力而更少被视作具有独立自主性的工人。如果说先前我们的职场不但需要对女性进行社会性别划分,而且在女性内部还要将其分成“白人妇女”和“有色人种妇女”的话,那么现在所有依托于性别和种族等标准的划分都变得不再那么绝对化。可以想象在赛博格出现的未来社会,基于身体特征的人群划分会更加稀少,因为这一形象本身就是对各种基准的破坏与消解[2]。
在哈拉维看来,赛博格这一形象作为一种机械与有机体的结合体打破了男性与女性、人与机器、大脑与身体、自然与人工等二元论的界限,从而打破了本质主义的范畴。因为在赛博格的视域中,任何物体都可以合理地用拆分和组装的概念来思考,因而不存在固有的结构可以约束系统的设计。正因为此,女性作为一种生理性别也不再含有任何天然的约束条件。性别和种族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由于父权制、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将其可怕的历史经验强加于我们身上而形成。哈拉维之所以赞同将赛博格形象与女性主义相结合,就是因为这一混合体反对用一种本质主义的编码方式完美地阐释所有的意义。既然我们的生活从工业社会以来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向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科学与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得阶级、种族及性别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那么女性主义理论与妇女运动也应该随着社会与科技的变迁而变化,而不是始终停留在前两次女性主义浪潮的成果中沾沾自喜。考虑到通讯技术和生物技术是重建我们身体的关键性工具,它的发展产生了新型的社会关系,使得女性“被整合或利用进入生产/再生产的世界体系及被称为信息统治的通讯世界体系中。家庭、职场、市场、公共领域及身体本身——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用几乎无穷的和多形态的方式进行分散和连接,这给妇女和其他人带来了巨大后果——这些后果对不同的人产生的影响也十分不同,使具有强烈对立性的国际运动变得更加难以想象,并且对生存至关重要。重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处理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关键是构造我们想象力的神话和意义系统。赛博格是一种对后现代的集体自我和个人自我的拆分和重组,也是女性主义必须编码的自我。”[3]所以,我们需要把握赛博格这一形象,来推动当代女性主义的理论建构与妇女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而把握这一要求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意识形态主张,即纯粹的客观性。因为这种主张是植根于主客分离的,这种分离使我们支配自然和让我们自己的逻辑合法化[4]。
为了进一步扩大赛博格与女性主义结合的范畴,桑多瓦(Chela Sandoval)对作为身份的女性主义与赛博格视域下的女性主义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批判。在她看来,美国第三世界的女性批评常常被读者误解和低估,因为它被论述为一个人口统计学中的群体(有色女性),而不是作为其自身权利的理论和方法论[5]。而赛博格的女性主义的优点恰恰在于抵制了以本质主义为基础的科学术语强加给我们的边界,认为我们应该有自由通过逃避或是取消已经叠加在我们身上的类别来创建新的身份,而不是通过创造和使用更多的边界。例如,一个失去肢体的人可以通过使用假肢逃避残疾人的类别,或者一个人可能在手术和荷尔蒙的帮助下从一种性别转变到另一种性别。但这并不是说机器就必然比人类或是其他有机体更适合我们,如果我们过于依赖这些机器,那么它们或者说由机械构成的我们自身终将会削弱我们的存在价值。而且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又会浮现出来:机器到底会不会取代人类?赛博格这种混合体到底是偏向于人类还是机器,如何看待才是最好的?坦白地说,由于基因组学和纳米医学的发展需要非常强大的信息系统来管理和集成DNA测序数据、成像系统、医疗保健信息等,所以暂时还做不到完全的机械化,不可能创造出能够代替人类的机器。而且至今,科学家始终没有弄懂人脑到底是如何运行的,所以暂时还不会出现模拟人脑的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或是赛博格。而且对于担心复杂的自我、身份和技术问题,赛博格所能提供的帮助可以说比技术恐惧症或是技术友好主义似乎更多一些。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赛博格给女性主义带来的优点而克服其对有机体的潜在威胁,只要我们能够提早预见和解决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6]。
赛博格似乎成为了科学、科学幻想和科幻小说在女性主义客观性问题上的汇合点。我们对责任、政治、生态女性主义的希望,会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我们必须学会与之交谈的编码者或是创造者。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科幻电影的构想而已,不必当真。但是我们真的可以忽视这些虚构作品的作用,仅仅将其当作一种娱乐产物来看待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根据对情感的社会建构的相关研究表明,科幻电影或是小说里的虚构角色与情境同样可以影响人的情感甚至道德观念[7]。同样,关于赛博格的构想也能够影响女性主义,特别是对性别平等实现的途径的构思。可以想象赛博格肯定是对妇女解放有着积极作用的,至少身体上的改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生物意义上的平等,而身体对意识的影响又可以增加赋权,改变性别主义的观点,从而实现平等。但是需要郑重声明的是,我们要的不是女性对男性的压制,也不是对武力的崇尚,如果可以,我们更希望建立一个“圣杯”的世界,以关怀和共情来统领社会。
三、赛博格与身体政治
既然赛博格的核心在于对身体的改造,这就不得不引发关于身体政治的思考。身体作为有机体的必然构成部分,似乎只是在医学上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人们开始对身体与知识以及权力的作用进行研究后,其意义才被发现与探索。身体是主观和客观能够同时经验到的,它既属于个人,也属于更广泛的社会。而且,身体的形式不仅是一个自然的实体,也是一个文化概念[8]。就像不同性别的身体含义也有所不同,其既包括生理差异,也包括后天的社会建构对身体的改造。身体通过它的外观、尺寸和装饰的属性对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进行编码,身体的意象嵌入在意义的结构之中,这是通过一种文化在建构其主体的含义和位置时实现的。就像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骨架,甚至不同的头发颜色,不同的性别有不同的性征一样。传统的社会观念认为,身体是禁锢灵魂的牢笼,而福柯却持有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其实是灵魂禁锢了身体。纵观整个身体史,大都是身体被压抑、被宰制、被规训,甚至被糟蹋的历史。所以,在福柯看来,尽管身体才是我们真正的本原,却与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紧紧相关。似乎有一种对身体的权力学规定了人们如何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来控制其他人的肉体,从而使他人在各个方面都符合我们的期待与愿望。长此以往,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就被打造出来了。而当代社会就是座巨大的监牢,它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来对个体的身体进行规训。在这座监牢里,学校、医院和兵营等机构都是对身体进行规训的场所,企图生产出和流水线商品一样标准的人类[9]。在福柯对身体与权力关系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获得关于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的知识。从出生到上学,再到工作,最后结婚生子,女性似乎一直生活在性别规训的压迫之中。这些规训塑造了女性的身体,而身体作为知识的对象,反过来又构造了关于女性的知识,这些被塑造的知识最终变成了一种先天性的东西在女性身体上打下了烙印。而且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女性身体所承载的历史内容也是不一致的:18世纪到20世纪中期,女性的身体不仅有性别标记,还有种族和阶级的差异表现,使得女性运动与政治相结合,以推动更广泛的平等;到了20世纪,同性恋政治的流行和对性学的接受创造了一系列性解放的话语,并且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追求;到了现在,身体成了一种符号系统,被用来进行各种改造和革命。对生物医学的依赖,女性主义政治的要求以及消费主义的盛行都使得身体成了话语体系和权力构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对于女性身体来说,还有一个繁殖的终极问题要解决。而赛博格的自我复制和修复使得我们能够脱离有机体的繁殖过程,身体无须承担过多的压力与责任。我们无法预见具体的未来是怎样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需要担心因为繁殖和身体的衰弱引发的痛苦与阻碍,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由于身体构造而被企业拒之门外的事件将不再存在,而“玻璃天花板”也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赛博格,被部分改造过的有机体,无须经过这一系列的所谓社会塑造,更是消解了其所承担的那些文化、政治和符号意义[10]。所以,赛博格的出现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因此而产生的歧视和对发展的阻碍,也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身体政治的必要性。正如哈拉维所指出的那样,赛博格属于一种后性别社会的生物,它绝不考虑双性征、前伊底帕斯的共生现象、未被让渡的劳动以及对有机体的其他诱惑。所以,赛博格的存在并不需要像创世纪那样的神话故事来支撑起正当性,更不用虚构一个异性伴侣来保证婚姻家庭的合理性。赛博格在打破身份限制的同时也制造了一个制度消解的社会,那些区隔有机体的东西都不复存在了。所以,这是对女性主义性别平等目标的一种可选择的实现方式。赛博格们成了真正的平等主体,创造了一个至少是女性所向往的乌托邦[11]。
但是,赛博格也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当我们通过改造选择更为强壮的身体或是器官来成为赛博格的时候,我们所想的难道只是为了生存吗?这种更强的变化目的是不是也是一种男权思想?因此,也有女性主义者担心赛博格会传递原本的男权思想,使得改造后的人类依旧处于该统治的支配之下。回想《攻壳机动队》中的情节,这样的顾虑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可以接受身体的改造,但是思想上的改造也应该同步,难以想象依旧建立在男权思想基础上的赛博格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四、讨论
赛博格的形象展现了一条可以让我们走出二元论困境的途径,重新解释我们的身体和各种社会工具。但目前来看,这只是一种类似于科幻小说的想象而已,意味着对各种机器、身份、范畴和关系的破坏。同时,由于赛博格的实现依赖于科技的发展,因此也需要我们更注重科技发展的过程。科技不仅可用来推动我们的发展,同时也是我们追求真理的途径。对赛博格的探索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多有关人与机器、自然与文化、身体与心灵等关系的奥秘,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发现关于人类社会和未来的真相。因此,我们需要探索的不仅仅是赛博格给女性主义带来了什么,更是它给人类、给所有生物带来了什么,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追寻的前景。根据科技伦理的论调,既然我们已经对其有了预见,那么就需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其进行控制与发展,引导着赛博格向有助于人类和动物的方面前进,而不是像《攻壳机动队》中那样仅仅将其作为武器的扩充来引发新一轮的世界大战。人与技术的关系是永恒的话题,我们要做的是将人类存在价值的丰富性与我们技术的道德匮乏性进行对比,同时通过限制我们对知识的追求来限制那些太过危险的技术的发展。此外,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代科技领域依旧是男性占主导地位,因而需要加入女性视角以及性别平等的措施。历史告诉我们绝不是因为进入了哪个社会,原本的腐朽思想和制度就会消失。所以,对科技的约束是必要的,特别是从伦理的角度来对科技进行正确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