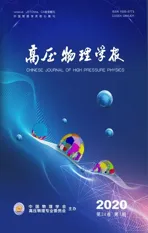钢筋混凝土墙抗冲击性能的数值模拟分析
2020-02-25宿华祥易伟建
宿华祥,易伟建
(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作为常用的工程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受到各种冲击载荷作用,例如碰撞、爆炸、水流冲击和恐怖袭击等。1968年英国Ronan Point公寓燃气爆炸引起结构局部倒塌,导致4人死亡、17人受伤。2001年9月,美国世界贸易中心先后遭受两架被恐怖分子挟持客机的撞击,在飞机撞击、爆炸冲击及燃烧的作用下,结构倒塌,此次恐怖袭击活动遇难人数高达2 996,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近1万亿美元。种种情况表明,意外冲击载荷引起结构破坏失效不仅会对人的生命安全和经济财产造成很大的危害,还会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由此可见,对于结构在冲击荷载作用下的研究有重要的实际工程意义,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现有文献中,已经有大量针对各种结构在冲击荷载作用下的动力响应研究。由于材料的率敏感性[1-2]及结构本身的惯性作用,结构的动力响应与静力响应明显不同。许斌和曾翔[3]利用落锤试验机对一组钢筋混凝土梁进行试验,研究了锤重、冲击速度、冲击能量对结构响应的影响。窦国钦等[4]对6根钢筋混凝土简支梁进行了试验研究,分析了高强混凝土梁在冲击荷载作用下的抗冲击行为。Tachibana等[5]进行了不同的锤重、冲击速度和截面尺寸的梁的落锤试验,并基于能量的角度提出了梁跨中最大位移关于冲击能量的经验公式。付应乾和董新龙[6]采用落锤三点弯曲试验方法对具有不同黏结强度的钢筋混凝土梁进行了研究,分析表明冲击力峰值与黏结强度无关,但是黏结强度对破坏模式的转变有影响。Kishi等[7]进行了27根不同剪跨比无腹筋混凝土梁的落锤冲击试验,提出用最大支座反力来评估梁的抗冲击能力比用最大冲击力更合适。窦国钦等[8]对6根钢纤维混凝土梁进行了落锤试验,试验表明加入钢纤维能够有效抵抗冲击作用下裂缝的发展。闫秋实等[9]通过对5根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梁和1根现浇钢筋混凝土梁进行落锤试验,分析了拼装位置和套筒灌浆饱满度对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梁抗冲击性能的影响。Zineddina和Krauthammer[10]对3种配筋方式不同的钢筋混凝土板进行了落锤冲击试验,试验数据表明钢筋混凝土板的响应受钢筋数量和落锤高度的影响。Özgür等[11]研究了边界条件对钢筋混凝土板抗冲击性能的影响;Bhatti等[12]研究了经纤维增强复合材料(FRP)加固的钢筋混凝土板在冲击荷载作用下的性能,试验表明在钢筋混凝土板背面加FRP可以增强板的抗冲击能力。赵春风等[13]研究了60°配筋混凝土板的抗爆能力,结果表明其抗爆能力与90°配筋板相比有明显提升。Zhang等[14]对现浇和预制钢筋混凝土柱进行了试验研究,结果表明预制钢筋混凝土柱由于其自恢复能力而具有更好的抗冲击性能。刘飞等[15]对有轴力的钢筋混凝土柱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了其破坏模式及转换机理。
目前关于钢筋混凝土梁、板、柱抗冲击性能的研究较多,对砌体墙的平面外抗冲击性能也有文献报道[16-17],而对于钢筋混凝土墙平面外抗冲性能的研究则相对不够充分。在剪力墙结构中,可能受到煤气爆炸及小型飞行器等冲击作用,但现有文献缺乏对钢筋混凝土剪力墙抗爆抗冲击的研究。此外,钢筋混凝土剪力墙作为应用广泛的关键竖向构件,在设计中并未考虑平面外的受力,一旦结构受到冲击破坏则将造成严重后果。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采用显示动力有限元软件LS-DYNA,对钢筋混凝土墙在锤体冲击作用下的响应进行数值模拟,分析轴压比、墙体宽度和边缘构件等参数对钢筋混凝土墙响应的影响,并研究不同参数对钢筋混凝土墙抵抗极限冲击荷载的影响。
1 有限元模型和材料参数
1.1 有限元模型
采用ANSYS建模,并用LS-DYNA计算钢筋混凝土墙在摆锤冲击作用下的响应。考虑到模拟墙体的对称性,采用1/2模型以减少计算量。钢筋和混凝土之间采用分离式共节点的方式建模,添加关键字*LOAD_BODY_Y对模型整体施加重力加速度,通过在顶梁上表面施加均布荷载为墙体施加轴力。墙体模型尺寸和配筋情况如下:墙宽有1.1、1.6和2.1 m三种,墙高2.1 m,墙厚160 mm,保护层厚度取为20 mm;采用双层双向配筋,墙身纵筋、分布钢筋直径及边缘构件中的箍筋直径为8 mm,边缘构件纵筋直径为16 mm,拉筋直径为6 mm并采用梅花形布置;墙体纵向钢筋配筋率为0.251%,纵筋钢筋间距为250 mm,当布置边缘构件时两端的8根纵向钢筋采用直径为16 mm的钢筋并设置箍筋,水平分布钢筋间距为300 mm。
总共建立24个计算模型,每个模型的编号由3部分组成:第1个字母A表示墙宽1 100 mm,B表示墙宽1 600 mm,C表示墙宽2 100 mm;第2个数字0表示无边缘构件,1表示有边缘构件;第3个数字表示轴压比,分别为0、0.2、0.4、0.6。例如B-1-0.2表示墙宽1 600 mm、有边缘构件、轴压比为0.2的墙体。图1给出了墙宽1 600 mm、有边缘构件墙体的有限元模型。墙底部梁体固接,顶部梁体可以竖向移动。

图1 钢筋混凝土墙有限元模型Fig.1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reinforced concrete wall
1.2 材料模型
在LS-DYNA众多混凝土模型中,混凝土塑性损伤模型(CSCM)能够很好地模拟混凝土结构的低速冲击行为[18],以及钢筋混凝土结构在冲击荷载作用下的弯曲和剪切行为。本研究中混凝土模型也采用MAT_CSCM(MAT159)。该模型引入损伤指标来模拟混凝土达到峰值强度后的应变软化和刚度退化特征,考虑了材料的硬化、损伤及率相关性。目前该模型在混凝土低速冲击领域应用广泛,不仅能够模拟钢筋混凝土结构在冲击作用下的大变形,也能模拟混凝土在低速冲击作用下的压溃[19]。
混凝土中骨料粒径取20 mm,混凝土强度取30 MPa。在CSCM模型中输入混凝土强度、骨料粒径等参数后可以考虑混凝土的应变率效应,程序将按照内置算法进行计算。此外,CSCM模型还可以考虑混凝土在冲击荷载下的侵蚀作用。采用侵蚀应变为0.1,当混凝土单元最大主应变超过此值时将被删除。
钢筋采用MAT_PLASTIC_KINEMATIC(MAT3)模型,即双线性弹塑性模型,可近似模拟钢筋的弹塑性阶段。钢筋材料的应变率效应通过Cowper-Symonds模型考虑。该模型能够考虑应变率效应对材料强度和失效应变的影响,强度公式为

式中:σ0为初始应力,为应变率,C为应变率参数,β为硬化参数,EP为塑性硬化模量,为等效塑性应变。
钢筋参数按文献[20]中的试验数据取值。模型中所用材料本构模型及相关参数见表1,其中:ρ为密度,E为弹性模量,ν为泊松比,fc为混凝土抗压强度,d为粗骨料最大粒径,fy为钢筋屈服强度,fu为钢筋极限强度,Et为切线模量。

表1 材料参数Table 1 Material parameters
1.3 模型验证
为了验证本研究所采用的有限元模型能否真实地反映钢筋混凝土结构在冲击荷载作用下的响应,分别对文献[20]中的梁、文献[11]中的板以及文献[21]中的墙进行模拟。
1.3.1 钢筋混凝土梁的有限元模拟
文献[20]中梁体总长3 m,净跨2.5 m,截面尺寸为100 mm×250 mm,上下各布置两根直径为16 mm的纵筋,箍筋直径6 mm、间距150 mm,混凝土保护层厚度20 mm。混凝土强度为30 MPa,骨料粒径20 mm,钢筋屈服强度490 MPa,极限强度656 MPa。
根据试验梁的情况进行建模,在支座中心处施加竖向线约束模拟试验中梁体的边界条件。考虑到模型的对称性,采用1/4模型并在对称面上施加对称边界条件。表2中列出了所有构件的最大位移的试验值和模拟值。图2中给出了梁A-1和梁A-2的跨中位移时程曲线与梁体损伤的对比,峰值过后模拟值比试验值大是由于模拟时对边界条件的简化造成的。对比结果可知,试验值和模拟值比较接近。

表2 梁跨中最大位移比较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maximum displacement in midspan

图2 A-1、A-2梁跨中挠度时程曲线(a)和损伤图(b)比较Fig.2 Comparison of deflection time history curves (a) and damage diagrams (b) of A-1 and A-2 beams in midspan
1.3.2 钢筋混凝土板的有限元模拟
文献[11]中利用落锤试验机对8块配筋相同的钢筋混凝土板进行了冲击试验。板的尺寸为500 mm×500 mm×50 mm,底部双向布置直径4 mm、间距50 mm的钢筋,钢筋屈服强度为256 MPa,极限强度为412 MPa,混凝土的抗压强度为25 MPa,保护层厚度为10 mm。试验中保持落锤质量5.25 kg、落高500 mm不变,直至板破坏。试验变量为板的边界条件,编号1~4的板用槽钢固定做固支约束,编号5~8的板直接将其边缘置于平台上不做约束。每组4个构件的支承条件分别为:四边支承、三边支承、两临边支承和两对边支承。
图3给出了板6(三边支承)和板7(两临边支承)的位移时程曲线的实验与模拟结果的对比。板6向下最大位移的模拟值和试验值分别为0.307和0.312 mm,误差为-1.6%;板7向下最大位移的模拟值和实验值分别为0.576和0.584 mm,误差为-1.4%。这说明所建立的模型能够准确模拟简支板在冲击荷载后的最大挠度,图3中曲线不能完全符合的原因应是试验中板在初始时刻支承情况不够理想。

图3 板位移时程曲线的实验与模拟结果对比Fig.3 Displacement-time curve comparison of the experimental and simulation results
1.3.3 钢筋混凝土墙的有限元模拟
文献[21]中对4块钢筋混凝土墙进行了摆锤冲击试验。试验中墙高2 100 mm,墙宽1 100 mm,墙厚160 mm,保护层厚度为15 mm。现浇剪力墙的纵筋和分布钢筋为 Ø 8 mm的HRB400钢筋,屈服强度为442 MPa,极限强度为614 MPa,纵筋和分布钢筋配筋间距分别为250和300 mm。拉筋为 Ø 6 mm的HPB300钢筋,采用梅花形布置。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30。为了提高计算速度,采用1/2模型,并在对称边界上施加约束。对文献[21]中A-1墙和A-2墙的冲击试验进行数值模拟,墙体中心位移峰值对比如表3所示。图4(a)和图4(b)分别给出了A-2墙中心位移时程曲线和损伤图的对比。

表3 墙板中心最大位移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maximum displacement at the center of wall

图4 墙A-2中心位移时程曲线(a)与损伤对比图(b)Fig.4 Comparison of time-history curve of central displacement (a) and damage (b) of wall A-2
由表3和图4的对比可见,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较为接近,试验中墙体受冲击后有水平和斜裂缝,模拟结果与试验呈现相同的破坏形式。
2 动态响应分析
对钢筋混凝土墙在理想边界条件下的冲击进行模拟。对1.1节给出的24块钢筋混凝土墙体,均用质量为2 t的摆锤以3 m/s的速度水平冲击墙体中心位置,冲击区域大小为300 mm×300 mm。
2.1 轴压比的影响
图5给出了轴压比对钢筋混凝土墙体中心水平位移时程曲线的影响,考虑到规范中对剪力墙轴压比的限制,对轴压比超过0.6的情况不再进行模拟。从图5中可以看出:冲击作用相同时,不同墙宽及有无边缘构件的剪力墙中点水平位移曲线呈现出相同的趋势;随着轴压比的增加,墙中心水平位移减小,且轴压比从零增至0.2时,位移减小的幅度最大;随着轴压比的增加,振动周期减小,频率增大,说明墙体的刚度增大。
此外,随着轴压比的增大,墙顶竖向位移逐渐减小。由于墙板在冲击荷载作用下发生变形,中性轴向混凝土受压区边缘移动,在墙板中形成压拱机制。在轴压比为零时,墙顶竖向位移不受限制;随着轴压比的增加,墙顶竖向位移受到限制,拱作用得到加强,因此在相同冲击荷载作用下墙体中心位移随着轴压比的增加而减小。同时,轴向压力的作用也使得墙体刚度增加,振动周期减小。

图5 不同轴压比下墙体中点水平位移比较Fig.5 Midpoint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comparison of the wall with diffirent axial force compression ratios
2.2 墙宽的影响

图6 不同墙宽时墙体中点水平位移比较Fig.6 Midpoint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comparison of the wall with diffirent wall widths
图6比较了在相同冲击作用下不同墙宽的墙体中心水平位移时程曲线。当轴压比相同时,随着墙宽的增加,墙体中心位移减小。显然增加墙宽使墙体平行于冲击荷载方向的横截面增大,截面抗弯和抗剪能力均有提高,从而提高了墙体的抗冲击性能。
2.3 边缘构件的影响
边缘构件配置4根直径为16 mm的纵向钢筋,同时配置封闭箍筋。图7比较了边缘构件对墙体中心水平位移的影响,可见有边缘构件墙体中心位移比无边缘构件墙体的中心位移小。

图7 有无边缘构件时墙体中心水平位移比较Fig.7 Midpoint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comparison of the wall with different boundary elements
同一墙宽条件下,有边缘构件的钢筋混凝土墙中心水平位移在相同冲击作用下比无边缘构件的钢筋混凝土墙的中心位移小,可从以下3方面分析:(1)加入边缘构件后,边缘构件位置有更大的纵向配筋率,使墙整体有更高的抗弯承载力;(2)在受到冲击作用时,由于跨中位置和墙体边缘位置的水平位移不一致,使得边缘处产生扭转,而边缘构件有更大的抗扭能力,因此加入边缘构件的钢筋混凝土墙有更强的抵抗扭转变形的能力,从而使墙的抗冲击承载能力提高;(3)边缘构件对中间墙体起到约束作用,在此种约束作用下墙板的薄膜效应增强。
当轴压比为0.2时,有边缘构件墙体比无边缘构件墙体的中心位移减小幅度比轴压比为零时小,其原因在于此时钢筋混凝土墙处在轴向压力与边缘构件的双重作用下。墙宽增加后,边缘构件对墙体中间位置的约束程度减小,锤体冲击位置为墙体中间的局部区域,因此1.6 m宽钢筋混凝土墙有边缘构件时的跨中水平位移减小幅度比1.1 m宽钢筋混凝土墙中心水平位移减小幅度小。
3 破坏模式分析
3.1 损伤图分析
图8比较了不同轴压比、不同墙宽和有无边缘构件的4块墙体在受到同样冲击作用后的损伤,墙体损伤图为软件中提取的应变云图。比较图8(a)和图8(b)可以看出,在相同冲击作用下施加轴压能够减轻墙体的损伤程度,损伤区域主要集中在墙体中部位置,结合2.1节说明轴压比在减小墙体中心位移的同时也能减轻墙体的损伤。比较图8(a)和图8(c)可以看出,墙B-0-0和墙A-0-0的损伤范围均较大,但墙A-0-0的损伤程度更重,说明增加墙的宽度能够减轻墙体的损伤程度。从图8(a)和图8(d)可以看出,墙B-0-0和墙B-1-0虽然损伤范围都比较大,但墙B-1-0在边缘构件处的损伤程度更大,且在边缘构件处的损伤延伸到两端梁体处,说明加入边缘构件后边缘构件承担了更多的能量。

图8 冲击荷载作用下墙体损伤情况Fig.8 Damage of the wall under impact loading
3.2 墙体变形分析

图9 墙体最大变形Fig.9 Maximum deformation of walls
图9比较了不同轴压比、不同墙宽和有无边缘构件的4块钢筋混凝土墙体在受到相同冲击作用后的最大变形。为了更直观地显示墙板各点的位移情况,把水平位移放大27.5倍并辅助等高线和投影。比较图9(a)和图9(b)可以看出,施加轴压力后墙体变形明显减小;比较图9(a)和图9(c)可以看出,墙B-0-0的变形比墙A-0-0小,且墙A-0-0更接近弯曲变形,说明增加墙宽能够提高墙体的抗冲击性能;比较图9(a)和图9(d)可以看出,墙B-1-0等高线的弧度更大,说明边缘构件的抗弯抗扭作用更强,使得边缘构件处水平位移更小,加入边缘构件后墙体倾向于发生冲切破坏。
图5、图6和图7分别通过轴压比、墙宽和有无边缘构件3个单一变量分析它们对墙体冲击性能的影响。为了进一步了解3个变量对结构响应的作用,通过图10分析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墙面中心为原点,水平方向为x轴,竖直方向为y轴,建立坐标系,图10(a)、图10(b)分别是墙体x=0和y=0位置的变形位移。由图10(a)可以看出,所有曲线除两端之外没有其他重合点,其主要控制因素为峰值位移,和前述分析一致。
考虑到墙宽和边缘构件的布置情况,关于轴压比、墙宽和有无边缘构件3个变量间的关系主要通过图10(b)进行分析。通过图10(b)可以看出:墙B-1-0变形折线的斜率比墙B-0-0大;而随着轴压比的增加,墙B-1-X(X=0,0.2,0.4,0.6)与墙B-0-X变形折线的斜率相差越来越小。对比墙B-0-X和墙B-1-X的板中最大位移可以得知,随着轴压比的增加,墙B-1-X最大板中位移与墙B-0-X相比的减小率逐渐下降。以上说明轴压比和边缘构件对墙体变形共同起作用,随着轴压比的增加,轴压比对墙体变形的影响逐渐增大,边缘构件对墙体变形的影响逐渐减小。比较墙B-0-X和墙A-0-X的变形可以看出,随着轴压比的增加,墙体变形形式改变并不明显,说明轴压比对墙体变形形式的影响不是主要因素。对比墙B-0-X和墙A-0-X在不同轴压比下的墙体中心最大位移得知,随着轴压比的增加,墙B-0-X的最大中心位移相比A-0-X的减小率变化不大,说明在此两种墙宽下决定墙体变形形式的主要因素是墙宽。

图10 墙体变形折线Fig.10 Deformation diagram of the wall
4 极限荷载作用下墙体的抗冲击性能
在落锤质量为2 t、冲击速度为3 m/s的冲击加载下,钢筋混凝土墙体产生了塑性变形,但所有墙体最终在给定的轴压作用下保持平衡,说明在冲击作用下墙体并未完全破坏。对于实际结构中的钢筋混凝土墙体:受到较小冲击作用时墙体产生变形,但是并未丧失承载能力;受到较大冲击作用时,墙体可能遭破坏而失去承载能力,墙体完全破坏后,荷载路径改变使得墙体原先承担的竖向荷载由其他竖向构件承担,情况严重时可能会引起结构的连续性倒塌。因此有必要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对钢筋混凝土墙体在极限冲击荷载作用下的响应进行分析。
4.1 极限荷载下构件响应阶段分析
为了研究墙体在极限冲击荷载作用下的响应,模拟了墙B-1-0.2在不同冲击能量作用下的响应,落锤质量为2 t,通过调节冲击速度来调节冲击能量,冲击能量每次增加1 kJ。在实际结构中剪力墙受到冲击作用后并不一定会立即失去承载力,可能会在二阶效应作用下持续一定时间并最终破坏。因此,在数值模拟中结合现实情况和计算机性能,确定计算时间为1 s。综合结构顶部竖向位移和墙体中心水平位移曲线分析,计算时间取1 s是可行的。
图11中给出了不同冲击能量作用下墙B-1-0.2的位移时程曲线,其中:图11(a)为墙顶中心处竖向位移时程曲线,向上为正、向下为负;图11(b)为墙体中心水平位移时程曲线。由图11可知,随着冲击能量的增加,墙顶中心竖向位移的最终值先为正、后为负,墙体中心水平位移逐渐增大。

图11 不同冲击能量下墙体位移时程曲线Fig.11 Time-history curve of wall displacement with different impact energy

图12 不同轴压比时墙顶竖向位移时程曲线Fig.12 Time-history curve of vertical displacement at the top of wall with different axial compression ratios
从图11中可以看出:在冲击能量为20、40和60 kJ时,墙顶中心竖向位移和墙体中心水平位移时程曲线最终均近似呈水平状态;在冲击能量为80和81 kJ时,墙顶中心竖向位移在振动几个周期之后近似线性慢慢变小,墙体中心水平位移在振动几个周期后近似线性慢慢变大;在冲击能量为90 kJ时,顶部向下的竖向位移和墙板中心水平位移均迅速增大,此时的墙体完全破坏失效。综上说明:在冲击能量较小时,墙体在冲击作用后能够保持平衡;随着冲击能量的增加,墙体受冲击作用后在二阶效应作用下逐渐破坏;当冲击能量足够大时,墙体受到冲击作用后迅速失去承载力而破坏失效。
在20和40 kJ时,冲击能量较小,墙体还处于“拱作用”阶段,所以此时的竖向位移为正。图12给出了墙B-1-X在冲击能量为40 kJ时墙顶竖向位移时程曲线。可见随着轴压比的增加,墙顶竖向位移逐渐减小,在轴压比为0.6时转为负值。墙顶位移转为负值表示“拱作用”已经消失,此时由墙体抵抗弯矩平衡轴向力产生的力矩。这说明在冲击能量为40 kJ时,轴压比的增加不利于提高墙体的抗冲击性能。
图13给出了墙B-1-0.2在落锤质量为2 t、冲击速度为9 m/s时,其顶部梁顶中心点的竖向位移时程曲线(Curve 1),以及边缘构件上方梁体顶面的竖向位移时程曲线(Curve 2)。由图13可知:0~27 ms,墙顶梁体向下移动一个很小的距离;27~34 ms,墙顶梁体向上移动;34~82 ms,墙顶梁体向下移动;82~1 000 ms,墙顶梁体位移来回振荡数次,随着时间增加,振荡的频率减小,逐渐趋于直线。由图11(b)可知:0~27 ms,墙板中心点水平位移的变化可忽略不计;27~82 ms,墙板中心点水平位移一直增大;82~1 000 ms,墙板中心点位移来回振荡,最终振荡频率降低并趋于一条逐渐上升的直线。对比两图可知:27~82 ms,墙面中心点的水平位移一直增加,墙顶梁竖向位移先增加后减小,墙板中心点的水平位移和墙顶梁体向下的位移最终都逐渐变大。
综上分析可以得出,钢筋混凝土墙受到冲击荷载作用后的响应分为以下3个阶段。
(1)压拱作用阶段。这一阶段墙面中心点水平位移增加,但由于钢筋混凝土墙在冲击荷载作用下开裂变形,中性轴向混凝土受压区边缘移动,形成压拱作用机制,墙顶梁体竖向位移为正,由压拱作用和墙体变形形成的抵抗弯矩共同抵抗冲击作用。此阶段轴压力起积极作用。
(2)冲弯作用阶段。这一阶段仍在冲击作用阶段,墙体受到冲击荷载和轴向压力的作用,顶部梁体竖向位移逐渐转为负值,墙板中心水平位移持续增加,仅由墙体变形形成的抵抗弯矩来抵抗冲击作用。此阶段轴向压力起消极作用。
(3)压弯作用阶段。锤头与墙体脱离,冲击荷载作用消失,钢筋混凝土墙体变形形成的抵抗弯矩和顶部压力作用形成的弯矩相互平衡。当抵抗弯矩小于压力弯矩时,墙面中心点位移持续增大,顶部梁体持续下降,最终墙体完全失去承载力而破坏。

图13 墙B-1-0.2在81 kJ冲击能量下顶部位移时程曲线Fig.13 Time-history curve of wall B-1-0.2 at the top of wall with 81 kJ impact energy
4.2 冲击作用下墙体破坏失效临界冲击能判别准则的探究
要确定冲击荷载作用下钢筋混凝土墙体失效时的冲击能,可以从以下3方面进行考虑。
(1)通过1 s后钢筋混凝土墙的变形来判别墙体是否会发生破坏失效。钢筋混凝土墙体在受到冲击作用后的1 s内,可能还处于破坏发展阶段,并没有完全失去承载力,经过较长时间后才会发生破坏,因此不采用此种判别方法。
(2)通过钢筋混凝土墙体中心水平位移曲线来判别是否会发生破坏失效。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是设定水平位移达到某一个值时,判定墙体破坏失效;二是通过水平位移最终的发展趋势来判断墙体是否会发生破坏失效。在水平位移达到某个数值后,墙体可能还处于平衡状态;若在冲击作用后水平位移不断变大,则说明墙体还在不断破坏,最终可能发生破坏失效。相比之下,采用水平位移的发展趋势进行判别更加可行。
(3)通过顶部梁体的竖向位移曲线来判别墙体是否会发生破坏失效。可以考虑两种判别准则:一是墙顶梁体竖向位移达到某个值,二是墙顶梁体竖向位移的发展趋势。当顶部位移达到某个值时,墙体可能仍处于受力平衡状态,因此将其作为判别准则不能很好地反映墙体是否破坏失效。通过图13可知,虽然梁顶不同点的竖向位移最终不同,但是在经过0.3 s后,两点竖向位移不断增大且差值保持不变,说明此时的梁体整体向下移动。通过图11(b)可看出此时墙体中心的水平位移也不断增大,墙体变形不断增大。以上说明,通过梁体竖向位移的发展趋势来判别墙体是否会发生失效破坏是可行的。
综上所述,采用墙体中心水平位移和墙顶梁体竖向位移的发展趋势作为失效判据均可行。本研究采用同时看两者的发展趋势来判别钢筋混凝土墙体最终是否会破坏失效,为了能定量分析,采用压弯作用阶段梁体下降速度是否大于0.5 mm/s作为墙体失效的判断准则。
4.3 墙体破坏失效分析
通过数值模拟分别获取墙A-0-X、墙A-1-X和墙B-1-0在不同轴压比作用下破坏失效所需要的能量,落锤质量保持2 t,通过调节冲击速度改变冲击能,冲击能每次增加1 kJ,当顶部梁体在0.5~1.0 s内的平均下降速度大于0.5 mm/s时,把此时的冲击能作为墙体破坏失效所需的冲击能。模拟时,每个墙体都取更大的冲击能量(与表4所列冲击能的相对偏差在10%以内),使墙体在1 s内即发生破坏。这也说明了所采用的破坏失效判据可行。

表4 钢筋混凝土墙破坏失效时的冲击能量Table 4 The critical impact energy of failure for reinforced concrete wall
由表4可知:随着轴压比的增加,钢筋混凝土墙破坏所需的冲击能量降低;有边缘构件的墙体破坏失效时所需的冲击能比无边缘构件所需的冲击能大;随着墙宽度的增加,钢筋混凝土墙的临界破坏能有较大增加。这说明减小轴压比、添加边缘构件和增加墙宽均能够增大墙体破坏失效所需的冲击能,对防止墙体在冲击作用下失效破坏有较大作用。在较小冲击荷载作用下,随着轴压比的增加,墙体的抗冲击性能提高,但是墙体破坏失效所需的冲击能却减小。
5 结 论
利用有限元分析程序LS-DYNA对钢筋混凝土墙的抗冲击性能进行了参数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钢筋混凝土墙在极限荷载作用下的响应,主要结论如下。
(1)在相同冲击能量(9 kJ)下,轴压比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时,可以提高钢筋混凝土墙的抗冲击性能,且随着轴压比的增加,钢筋混凝土墙体中心位移减小的幅度逐渐变小。
(2)增加钢筋混凝土墙的墙宽能够使墙体平行于冲击荷载方向的横截面增大,截面惯性矩增大,使得截面抗弯和抗剪能力均提高,从而有效地提高了钢筋混凝土墙的抗冲击性能。
(3)钢筋混凝土墙体加入边缘构件,增强了墙体的整体抗弯能力,同时增强了对墙体中间区域的约束作用,使得墙体的抗冲击性能提高。
(4)冲击作用相同时,有轴压的墙体的损伤较为集中,墙宽较宽的墙体的损伤程度较轻,边缘构件的加入能够有效分担冲击能量。墙宽是影响墙体变形的主要因素。
(5)在极限荷载作用下钢筋混凝土墙体经历3个阶段,分别是压拱作用阶段、冲弯作用阶段和压弯作用阶段;提出了用墙顶竖向位移的发展趋势作为墙体受冲击作用破坏失效的判别准则,并论证了其合理性。
(6)利用所提出的判别准则分析在极限荷载作用下轴压比、墙宽和边缘构件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轴压比的增加,墙体破坏失效所需要的冲击能量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