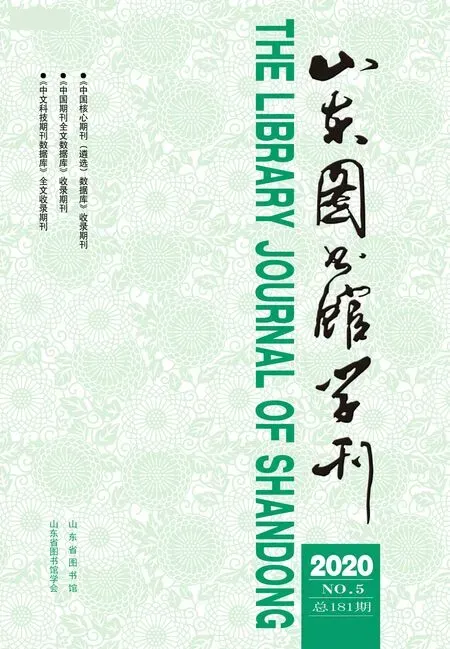古籍普查登记数据的审校与思考
——以安徽省博物院、安庆市图书馆数据为样本
2020-02-25舒和新
舒和新
(皖西学院图书馆,安徽六安 237012)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于2012年2月启动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目的是全面了解全国古籍存藏情况,建立古籍总台账,中心任务是通过每部古籍的身份证——“古籍普查登记编号”和相关信息,建立国家古籍登记制度;通过利用“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平台”建立全国古籍普查基本数据库,形成《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在此基础上,由省级古籍保护中心负责编纂出版《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纂出版《中华古籍总目》统编卷。截至2019年底,普查登记及数据审校工作基本结束。
1 审校的过程
2014年,笔者受聘为安徽省古籍普查登记数据审校人员。根据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的安排,笔者承担了安徽省博物院、安庆市图书馆两家古籍收藏单位普查登记数据的审校工作。从2014年12月中旬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将安庆市图书馆的4411条数据分配给笔者,到2019年底笔者将经过多次提交、返修的安庆市图书馆7090条数据最后提交给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历时五年。在审校过程中,笔者收获颇多,也产生一些思考。
审校过程之所以持续五年,是因为两家单位的普查登记的过程以及数据的提交都不是一次完成的。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分别在2014年底和2015年将安庆市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院的普查登记数据分配于笔者,笔者分别在2015年和2016年完成了两家单位数据的审校。此后,笔者又完成了对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三审安徽省博物院数据时提出问题的复核,国图出版社也已做好数据出版的准备。但出乎意外的是,安庆市图书馆提交的数据只是已经整理编目文献的数据,书库里还存放着众多未加整理的古籍。随着古籍普查志愿者的加入,2017年,安庆市图书馆启动了对未加整理古籍的分类编目、普查登记,这样不仅新增加很多数据,而且又合并一些数据,最终形成7090条数据,导致全部数据必须重审。安徽省博物院的情况也有点类似,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准备将其数据发排付印时,安徽省博物院也启动了未编古籍的分类编目、普查登记,在原有5741条数据的基础上,又增加了5060条数据。两家收藏单位普查登记数据的变化,致使整个审校过程到2019年底才完成。
2 数据反映出的古籍特点
在数据审校过程中,笔者深感这两家收藏单位的古籍收藏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高,并且很有特色。
2.1 古籍数量多、质量高
安徽省博物院、安庆市图书馆都是安徽省古籍收藏大户,其古籍收藏量分居全省古籍收藏机构的第三、四位。安徽省博物院审校过后的最终数据有10869条,前后有53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安庆市图书馆审校过后的最终数据为7090条,先后有9部古籍珍本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2.2 珍本古籍多
根据安庆市图书馆网站的介绍,其古籍善本有4321册[1]。笔者虽不了解其确定善本的具体依据,但从所审校的数据来看,其明代及以前的版本超过200种,稿本有14种;安徽省博物院更是有元版13种,稿本105种,其最早的文献是北凉神玺三年(399)道人宝贤抄写的《贤劫九百佛名品第九》,这是国内年代第二久远的抄本佛经。
2.3 地方特色突出
安庆是桐城派的发源地,也是曾经的安徽省会,安庆市图书馆的古籍收藏中包括桐城派名家手稿、地方志、家谱、地契等珍贵地方文献资料,其中有省志、州志、府志、县志等方志和山水志等200多种以及众多的族谱等谱牒,还有大量的安庆刻书、安徽省内刻书、医书、佛经等。作为安徽文物珍品的集藏地,安徽省博物院则汇集了更多的省内文献珍本,其中包括清末民国时期的的省内藏书家许承尧和他的朋友王立中的众多旧藏。许承尧(1874—1946),名芚,字际唐,号疑庵,安徽歙县人,方志学家、诗人、书法家、文物鉴赏家。清光绪三十年中进士,“末代翰林”之一;辛亥革命后,先后任职皖甘两省;藏书甚富,著述颇多。王立中(1882—1951),字叔平,号城南老人,安徽黟县人,文献学家、藏书家,曾任安徽通志馆委员,与蔡元培、许承尧等交往甚多,著有《俞理初先生年谱》《文中子真伪汇考》《城南草堂曝书记》等文献学著作。1951年,皖南人民文物馆征集了许承尧、王立中的藏书,这些藏书现在多收藏于安徽省图书馆和安徽省博物院[2]。
2.4 人文荟萃
安庆馆的收藏中,有很多是安庆地方人士、特别是桐城派的著述,包括张英、张廷玉家族,方苞、方宗诚家族,姚鼐、姚文朴家族,吴汝纶、马其昶等诸多名家的著述,让人深感安庆乃人文荟萃之地。安徽省博物院的古籍不仅汇聚了以安庆、徽州为主要代表的安徽历史文化名人的著述,而且具有更高的文献价值与版本价值。在审校过程中,笔者参照安徽省博物院在全国古籍普查平台上的书影,发现许承尧、王立中两先生的藏书不仅留有藏书印,而且几乎每种书都留有批校题跋,这些题跋往往介绍各书的来历及徽州作者的生平、学术等。
3 数据中存在的问题
李致忠先生曾说,古籍整理要完全不出错是不可能的。安庆市图书馆是文献学家蒋元卿先生(1905-1999)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古籍整理的基础工作比较扎实,但在笔者接收的安庆馆第一批数据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不过,除了少量版本、责任者认定方面的错误外,多数都只是著录规范方面的细节问题。在这第一批4411条数据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数据被修改或存有疑问,其中有374条数据需要核对原书。安徽省博物院两次提交的的数据整体情况比较好,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具体来看,两家单位的数据存在的问题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3.1 数据没有按照四部分类法进行分类排序,排列混乱
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由于文献上架时就没有分类,也可能是普查登记时时间仓促的结果。如果只是数据本身的顺序混乱,可以由数据著录者或审校者按四部法重新进行分类排序即可。问题是,在此前数据被报送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后,国家中心按照数据原来的顺序给出了普查编号。如果对数据进行重新排序,就会打乱普查编号,造成新的混乱。随着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结束,即将启动的《中华古籍总目·安徽卷》编纂工作将不得不面对这个难题。
3.2 民国文献与海外文献的问题
古籍普查登记的范围是我国境内各收藏机构或个人所藏,产生于1912年以前,具有文物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献典籍,不包括海外文献和民国文献。但在两家收藏单位的数据中,都包含了不少海外文献和民国文献,其中安徽省博物院提交的第一批数据共6070条,经审校后删除329条,只剩下5741条,被删除的数据绝大多数都是海外文献和民国文献。数据中包含海外汉文古籍一般都是对普查登记的范围没有完全领会的结果,笔者在2012年进行数据的著录时,也存在这方面的疏忽。而将民国文献纳入数据中,很大程度上是错误认定版本的结果。
在安庆馆的第一批数据中,包含有19部《安徽通志》的稿本或由安徽通志馆编、抄的文献,数据条目中都将安徽通志馆标注为清末,另外还有2条数据未注明抄写年代,但从数据反映出来的特征来看,很可能也是安徽通志馆的抄本。据笔者所知,清代虽有道光和光绪时期两次纂修《安徽通志》的过程,但并无文献记载清代设有安徽通志馆这个机构;人们知晓的安徽通志馆是民国时期的修志机构,1920年开始建立,1934年出版了《安徽通志稿》,1935年停止修志工作。因此,对于数据中这些与安徽通志馆相关的文献,笔者颇存疑问,先后请教了省内古籍界四位专家,得到的信息与笔者掌握的信息大致相同。由于安徽省图书馆存有相当多的民国安徽通志馆文献,当时任职安徽省图书馆的张秀玉博士还向笔者介绍了这些民国文献的基本特征。对照手中的数据,基本可以确定,安庆馆的安徽通志馆文献应该就是民国时期的,不应纳入普查登记目录。为慎重起见,笔者提请数据著录者对照原书重新核对这些数据,结果证明笔者的推测是正确的。
3.3 数据的题名卷数项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多数方志前都缺少纂修年号。按照著录规范,省志、州志、府志、县志要考证并著录纂修年号,并且要在考证出的纂修年号上加[ ],但安庆馆第一次提交的数据中,方志基本都没有纂修年号,如清嘉庆八年(1803)刻本《无为州志三十六卷首一卷》、清道光四年(1824)刻本《怀宁县志二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等;仅有的几条著录纂修年号的方志类数据中,考证出的纂修年号也未加[ ],如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刻本《望江县志八卷》。
二是多题名多著者的条目不符合著录规范。根据著录规则,在著录多题名多著者的古籍时,第一个题名著录在“题名卷数”栏,对应著者著录在“著者”栏;第二个题名及著者紧跟在前一著者后,也著录在“著者”栏中,以“&”符号间隔;其他题名及著者亦同。但在安庆馆第一次提交的数据中,有一部分条目把多题名都著录在“题名”栏、多著者都著录在“著者”栏。如“题名”栏著《孝经易知不分卷太极图说不分卷》,“著者”栏著“(清)马益撰 (宋)周惇颐撰”。
三是卷数为一卷、不分卷或残本卷数不明时,基本都未注明卷数。如在安庆馆第一次提交的数据中,清英秀堂刻本《脉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怀宁报本堂木活字印本《怀宁报本堂夏氏宗谱》(残)。虽然有关文献中对一卷和不分卷进了区分,但二者确实不容易掌握,数据中不予著录可能就是因此之故。笔者只得根据自己对文献内容的了解来确定一卷或不分卷;至于卷数不明的情况,只能请数据著录者核对原书了。
四是题名卷数错乱。在安徽省博物院的数据中,索书号14793的文献著录为《五代史记七十四卷》,其后的责任者则著录为“(汉)司马迁撰”。实际上,《五代史记》为宋欧阳修撰、徐无谠注。通过古籍普查平台进行检索,书影显示,这条数据的题名应该是《史记一百三十卷》。
3.4 数据的著者项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责任方式不明。在安庆馆第一次提交的数据中,出现有35个“其他”,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善成堂刻本《周易参同契分章注解三卷》的“著者”栏为“(汉)魏伯阳其他(元)陈致虚其他”。经与安庆馆数据著录者沟通,可能是在普查平台著录过程中,责任方式中著录“其他”选项未果,使得平台中的“其他”直接反映在导出的数据中。
二是少数责任者的朝代标注错误。如安庆馆第一次提交的数据中,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书林双峰堂刻本《活法大成十八卷》的著者著录为“(清)佘象斗编辑 (清)李廷机校正”。实际上,这里的佘象斗应为明代人余象斗,李廷机也是明代人。在安徽省博物院的数据中,索书号15180的《陶靖节先生诗四卷》,责任者著录为“(唐)陶渊明撰”。实际上,陶渊明是东晋人;而且,出版社还要求他的姓名著录为陶潜。
三是同时期多责任者的同一责任方式被反复著录。如安庆馆第一次提交的数据中,清道光二年(1822)三让堂刻本《熙朝新语十六卷》的“著者”栏著录为“(清)徐锡麟撰 (清)钱泳撰”。正确的做法是,只需要在最后一位责任者后注明责任方式。
3.5 数据的版本项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重刻本、仿刻本未按要求归并为刻本。安庆馆第一次提交的数据中,有120条数据的版本为重刻本、23条数据的版本为仿刻本,如明嘉靖八年(1529)武昌府儒学重刻本《朱熹集注十九卷》、明宝华堂仿宋刻本《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按照审校要求,重刻本、仿刻本都应归并为刻本,其重刻、仿刻所依据的原本也应该略去。尽管笔者对这一要求持有不同看法,作为审校人员,还是得按照审校规则行事。
二是明代国子监刻本的著录问题。如安庆馆第一次提交的数据中,包括有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国子监刻本《五代史七十四卷》。国子监是中国古代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明代国子监也是内府的刻书机构。由于明代在北京和南京分别设有国子监,其刻书分别被称为北监本和南监本,因而在版本著录中应该注明北监本或南监本。由于安庆靠近南京、这家单位收藏的古籍中也有很多南京刻书,因而笔者推测,这些监刻本多数为南监本。在安徽省博物院的数据中,不仅存在少量与安庆馆相同的问题,还存在很多监刻补修本被错误著录的问题,就是不仅没有著录为北监或南监刻本,反而依据补修时间确定版本,如索书号13029的北监刻万历补修本《北齐书五十卷》被著录为明万历刻本。
三是套印本前未标注“刻”。这是两家数据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安徽博物院索书号12500的《古文渊鉴六十四卷》,版本项著录为“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内府五色套印本”。实际上,正确的著录应该是“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内府刻五色套印本”。
四是部分历史年号与公元纪年换算错误。历史年号与公元纪年的换算错误是笔者没想到的,好在手边有过去参加国家中心培训时发放的《中国历史年代简表》这本小册子,查对起来很方便。另外,还有一种很少见的情况,就是文献版本项中存在的历史年号错误的问题,如安徽省博物院索书号14984的《史鉴提衡二卷》,内封标注为正德癸未年重刊,数据著录为明正德癸未年刻本。但明正德时期(1506-1521)并无癸未年,笔者推测,这个癸未年应该是明嘉靖二年(1523)。但这也只是推测,无确切依据,只能将版本改为明刻本。
五是排印本问题。安庆馆第一次提交的数据中,有313条数据中的排印本未按要求著录为铅印本,是全部数据中存在最多的问题,如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排印本《坤舆撮要问答四卷》。铅印本是用铅活字排印的,过去很长时间里也被称为排印本,但排印本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其它活字本也是排印的。
3.6 数据的备注项中存在问题
备注项中,存在有存卷或缺卷的卷数不符现象,如安庆馆第一次提交的数据中,清同治二年(1863)湖北抚署景桓楼刻本《大清壹统舆图》的存卷标注为“存二十九卷(南卷一至十、北卷二至十八)”。这里不仅存卷数不符,而且也未注明文献的原卷数。
3.7 数据中存在错别字
这一点在安庆馆第二次提交的数据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安庆馆第一次提交数据中的问题在审校时已被全面纠正,他们在对全部古籍文献进行普查登记后形成的数据基本都避免了这些问题,但可能是由古籍普查志愿者从事的数据录入工作存在大量的错误繁体字,包括“卷”错为“捲”、“札”错为“劄”、“采”错为“採”、“御”错为“禦”、“制”错为“製”、“朱墨”错为“硃墨”、“陸游”错为“陸遊”、“咸豐”错为“鹹豐”、“范”姓错为“範”、“郁”姓错为“鬱”、“余”姓错为“餘”、“岳”姓错为“嶽”、人名中的“斗”错为“鬥”、“朱熹”错为“硃熹”等。根据笔者的经历,造成这些错误的另一个原因是使用紫光华宇拼音输入法。这种输入法虽然具有记忆功能,但在某些固定词汇、用法上,无论使用者修改多少次,输入法始终保持固定的错误,如硃熹、鹹豐、硃墨、××捲等,实在不明白这种输入法的开发者怎么会犯如此荒诞的错误。
4 几点思考
4.1 关于古籍保护的经费投入
在安徽省内,已经有了9家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在这9家单位中,有6家单位在藏书数量、甚至藏书价值上都不及安庆市图书馆。安庆馆古籍数量多、价值高、有特色,在全国影响很大,现在已有9部珍本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已经达到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对于藏书量的要求,但却不是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原因很简单,缺少建设标准库房的经费。
经过多年的努力,2018年,安庆馆投入近80万元经费,建设了一个符合标准的古籍书库,于2019年申报第六批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目前正在主管部门审批过程中。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地区的古籍收藏机构来说,80万元显然不是一笔小数目。古籍是全民族的文化遗产,保护费用不应该完全由收藏单位承担。对于欠发达地区数量并不算多的有资格申报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的收藏机构,国家财政和文化主管部门可以以转移支付的方式资助一部分建库费用,以激励收藏单位投入配套经费、建设标准古籍书库。
4.2 古籍工作需要时间和耐心
由于经费和人才等方面条件的限制,各收藏单位的古籍工作人员都很有限,因而古籍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都很大,工作进展往往跟不上主管部门的要求。安徽省博物院、安庆市图书馆前些年都积累有大量的未编古籍,在普查登记的进度、时间压力下,只能提交已编文献的数据。后来由于时间后延和志愿者加入,两家单位才对未编古籍进行整理、分类、编目、登记,在第一次提交数据三、四年后,再次提交部分或全部数据。类似的情况并不罕见,安徽省图书馆曾编纂《安徽省图书馆馆藏章伯钧书志》,为章伯钧家人捐赠的第一批章伯钧旧藏撰写书志,同时作为建馆百年的献礼书目之一。由于存在时间压力,尽管在该书出版前,章氏家人已进行第二次捐赠,但已来不及在百年馆庆前为其续写书志,因而出版的《章伯钧书志》没能包含章伯钧家人第二次捐赠的章氏旧藏的书志,成为一大憾事。
其实,全国范围古籍普查工作开展以来的几次范围和重心的调整,也证明了古籍工作需要时间和耐心。
4.3 关于《中华古籍总目》
四部分类法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古文献分类工具,由于它无法完全涵盖清代后期的知识领域,今人根据古籍整理分类的需要,做出了适当的调整,并增加了部分类目,使得古籍分类工作更加规范,但也存在值得推敲之处。
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2019年11月编印的《中华古籍总目编目手册》所公布的《中华古籍总目》分类表与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的分类目录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华古籍总目》分类表的两个特点:一是类目更具体、更条理化;二是增加了部分新类目。
类目的具体化、条理化,对古籍的分类编目具有更明确的指导作用。如《四库全书》分类目录中的“经部”包括十类,其中的“礼类”笼统地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礼通义、通礼、杂礼书六属[3],而《中华古籍总目》分类表的“经部”分为十九类,其中周礼类、礼记类下都包括经文之属、传说之属、文字音义之属、分篇之属、专著之属等[4]。这种细致清晰的类、属划分使得分类编目工作有据可依、更加规范。
增加的新类目中,一部分实际上也是类目的具体化、条理化,如上述之周礼类、礼记类;但也有一些是新增的部类,如明确增加了类丛部,并将新增的新学类附于其后。增加的新类目能够涵盖一些新的知识领域,最明显的就是清后期大量出现的西学、新学著述。
修订后的《中华古籍总目》分类表虽然能为古籍工作者的分类编目工作提供更精细的指导,但也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
首先就是类目增加过多。在《四库全书》目录中,四部之下一共只有44个类目,而现在修订后的四部分类法中,把各部中的丛编项和新增加的类丛部各类加在一起,类目达64个,数量增加将近半数。其实,除了各部中的丛编项、子部中的工艺类、附于类丛部后的新学类之外,其它新增类目未必都是必须的。增列丛编项是因为古籍各部中都存在一些丛编文献;子部增加工艺类是因为古代社会轻视工艺技术,只有分列于术数类的杂技术之属和艺术类的杂技之属与其有点关系,不仅无以凸显工艺技术的重要性,而且难以涵括工艺类文献;增加新学类更是因为传统的分类法无法涵盖新的知识领域和技术领域。
其次,将新学类单独附于类丛部之后值得商榷。新学的内容就是新的知识领域、技术领域,这与子部中的各家学说、各类工艺是相似的,所以将新学类置于子部最后比较合适。可能有论者会质疑,新学既然不属传统的知识领域,置于子部就不合适。这种说法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前提:新学虽然不属传统的知识领域,新学文献却属古籍之列,这个分类表的名称就是《中华古籍总目》分类表。事实上,由中华书局编纂的《中国古籍总目》就是将新学类置于子部末尾。
再次,《中华古籍总目》分类表区分道家与道教的必要性存疑。在《四库全书》分类目录中,道家位于释家之后,是子部的最后一类[5],可以理解为将道家视为一种宗教,笔者并不认同这一做法。在《中华古籍总目》分类表中,除了丛编类、总论类,子部前两类分别为儒家类、道家类;在子部的宗教类目下,包括有道教之属、佛教之属、民间宗教之属。很显然,这是将道家与道教进行了区分。从内容上看,这种区分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在文献分类史上,道家与道教不加区分的传统已有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现在有必要进行区分吗?而且,儒家类下面有多种属,而道家从道教区分出来、作为单独的一类后,下面并无任何一属[6],因为其内容基本上只有《道德经》《南华经》《列子》及其注释、考订等。这种单薄的内容作为单独的一类有点勉强,不仅会增加编目人员的麻烦,也会给道家、道教文献的检索者造成困扰。笔者认为,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将道教合并于道家,在儒家类之后设置道家类。
保护古籍是为了传承传统文化,而四部分类法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现代人在对其进行调整、使其适应古籍整理需要时,应该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尽可能地保持原有结构;四部分类法本身就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因而也不存在剔其糟粕的问题。所以,大破大立不是对待四部分类法的应有态度,除了必须增加的少数几种类目外,其它具体化、条理化的调整应该置于部下之类或类下之属。
4.4 关于普查编号
各收藏单位的普查登记数据提交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后,国家中心就会给出普查编号。可这些有了普查编号的数据还需要进行审核,审核过程中有可能调整数据的排列顺序、甚至删除一些数据,这样就会打乱普查编号,笔者所审校的数据就存在这样的难题。而且,一些单位过去已经开始了平台普查,普查数据在平台中已经有了普查编号,而这些编号与国家中心给出的编号很可能是不一致的。2010年,“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安徽省服务器刚启用时,笔者手边正好有一部明王民顺刻本《临川先生文选二十卷首一卷》,出于试用一下普查平台的想法,就在平台上操作起来,没想到这就成了本馆古籍平台普查的第1号,编号为340000-1847-0000001;而在本馆按四部分类排序的古籍普查登记数据2012年提交到国家中心后,这部书得到的普查编号却是340000-1847-0000409。普查编号的这种混乱不利于以后工作的开展,也不利于读者进行文献的检索。笔者认为,应该在数据审校完成以后、结合平台普查中已经给出的普查编号来确定全部数据的普查编号。
4.5 审校数据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笔者所在皖西学院图书馆的古籍藏书比较有限,而且多为常见文献,因而笔者见识到的古籍也很有限。通过审校安徽省博物院、安庆市图书馆的数据,见识了很多过去所不知晓的文献信息。皖西学院位于安徽六安,在审校过程中,笔者了解到26种过去未曾见过的六安人写或刻的文献,其中8种是晚清理学重臣、六安人涂宗瀛的求我斋所刻文献。
在安徽省博物院的数据中,有一部索书号12340的清抄本《御定性理大全书》残本,其在古籍普查平台的书影上,钤有“文津阁宝”的朱红大印,这与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的“文渊阁宝”印颇为相似,因而存在该抄本属文津阁《四库全书》零种的可能。但各种文献记载都显示,文津阁《四库全书》是七部《四库全书》中唯一没有散失、保存完好的一部。笔者请教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又请教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萨仁高娃副馆长。萨仁高娃副馆长亲自入库查找出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对应文献,指出作伪抄本与文津阁《四库全书》原本之间的区别,并拍照进行对比,让笔者受益匪浅。可见,审校数据的过程也是一个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的过程。
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既需要专业知识,也需要敬业精神和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结合笔者自身在古籍普查登记过程中的经历,感觉此次审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希望本文的内容对今后的古籍工作能够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