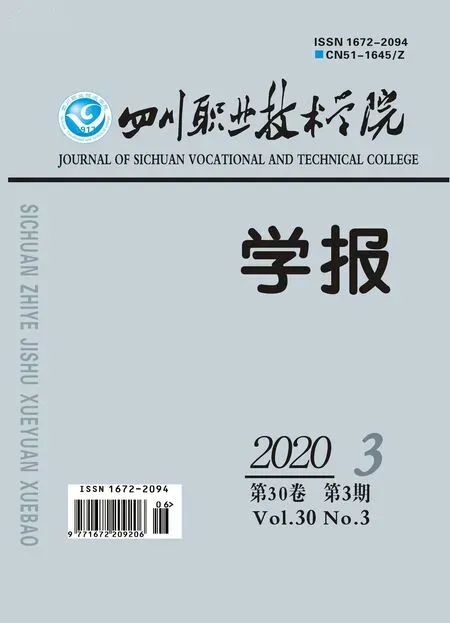异体字构形理据探析四则
2020-02-25吴长新邓章应
吴长新,邓章应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 400715)
关键字:构形理据;跨结构变化;层级构件化;强势构件
“犭”与“豸”经常混用,如“犲”作“豺”,《集韵·平声·皆韵》:“犲即豺。”“狐”作“”[4]583。《字汇·豸部》:“,同狐。”[5]98《6正字通·豸部》:“,俗狐字”。“貛”作“獾”[6]2244,《说文·豸部》:“貛,野豕也。”[7]182《7集韵·桓韵》:“貛,亦作獾。”“狸”作“貍”[4]147。《正字通·犬部》:“狸,同貍。”[6]74故“”即“”,《金石文字辨异》也把“”作为“豹”的异体收录[3]721。
无独有偶,还有其他字也有类似的演化轨迹。
构件发生跨结构讹变后,对于新的构件可能会赋予新的理据,这是前贤所言理据重构,得到理据重构后的字形往往也会得到传承,但因为“”不能重构为豸从亻从勺或从豸从仢的新理据,故“”中之“亻”一直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故后世也就逐渐淘汰了这一字形,仍主要写作“豹”。其他具有这一演变情况的字也都基本淘汰了从“亻”的异体形式。甚至于矫枉过正,将本来从“休”的“貅”也去掉“亻”构件写成“䝗”字。《类篇》:“貅,或省作䝗。”[11]34《8直音篇·䝗》:“䝗,同貅。”[2]53《1礼记·曲礼上》:“有前挚兽则载貔貅。”[18]唐陆德明释文:“貅,本亦作䝗。”其实应该是貅,䝗为其变体。将本来从“伏”的“”也去掉“亻”写成,《直音篇》:“,音伏,狐也。”[2]531
而带有构件“匡”的其他字也会出现相似的变化:
而第二步“∟”与“辶”的相似讹混在碑刻中多有提及,在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中提及“辶”的草率写法和“∟”相近,如“迷”,《元思墓志》中作“”,《高勾丽好太王碑》中作“”;“達”,《范国仁等造像记》作“”;“遷”,《谢温墓志》作“”[21]。
三、“渕”的构形理据
“渕”是“淵”的异体,收录在清刑澍《金石文字辨异·平声·先韵·渊字》[3]187引《北齐天统五年造丈八大像记》,原字形为“”。《中华字海·渊》[14]550、《敦煌俗字典》[20]520中亦有收录。该字意义虽明,但构形理据不明。
“渕”可以分析为从氵从关从刂,构件组成比较复杂,但可以从其形似字“”(唐武德三年《隋杨厉墓志》③)入手,其文字轮廓上可以看出“渕”是由“”丢失左侧“竖撇”笔画后形成该字。因为“冫”与“氵”为互通构件。
于是,我们便复原了异体字“渕”的构形理据,即第一步,“淵”字因构形复杂,在人们对汉字使用的求简心理下,先是按照笔势轨迹相似的简单符号“八”来代替“竖折”,形成“”,后期添加横画形成“”;第二步,为了追求汉字的对称美观,上半“八”字翻折,“”变为“”,又因“层级构件化”规律的影响,与其中间部分形似的“关”取而代之,“”字出现;第三步,新字形因笔画复杂,后期讹写变异程度高,在字形内部又添加了“竖画”,原有构形理据丢失严重,为了向外寻求新的构形理据,且“层级构件化”规律与其他强势构件的影响贯穿始终,形成“”,后直接丢失“竖撇”形成“渕”。
在第一步中,石刻文字里用“八”形符号来替代复杂构件是常见用法。在张海艳的《从重字符号替代到汉字重复构件符号替代》中也认为“丿”和“”是书写简单、笔形美观的文字重复构件的替代符号,但她把“繼”、“斷”与“淵”、“肅”中用“丿”和“”替代原有构件的成因混为一谈,而本文认为前者应该是用简单符号替代复杂构件,后者则是根据原有构件的笔势痕迹逐渐转写为“丿”和“”,两者形成原因并不相同。
此外,“淵”的一类为含有“关”构件的异写字变化过程中存在着三个值得注意的规律。
其一,字形构件内部关键笔画的添加、缺失、位移和变形导致了字形的跨越性变化。在不影响认读的情况下,整字中添加少量的多余笔画,减少少量的原有笔画或原有笔画的位移及变形并不会影响整体轮廓的构形,所以不会影响认读和识别,并且这些笔画的添加、丢失、位移和变形并不会导致该字理据层面发生改变。但是在字符中的某些部位,一旦出现关键笔画的添减、位移和变形,则会导致字形的进一步讹变,而经历重重讹变过后,形态新颖的异写字符便逐渐丢失了构形理据,并有可能发生跨结构变化,之后的构件组合形态便更加可能会无法还原其原有的构形理据。
其二,笔画组合的“层级构件化”。在石刻或写本文字中,许多原因会导致书写变异,笔画会直接向构件发生转变,我们称这种一步到位的过程为“简单构件化”。而有时候这些因书写变异出现的多余、省略、位移或变形的笔画往往会和原有笔画继续组合。这样的笔画组合形态新颖奇特,往往没有其构形理据,例如《鲁峻碑》中的“”字在后期被讹写成“”,或是原本的“匡”被讹写成《奚真墓志》中的“”字,以及“”的中间部分后讹写为“关”,均说明了这些毫无理据的形体变异的笔画组合在使用者的书写过程中往往会向与其形似但是构形理据较为明晰的强势固有构件发展,这就是笔画组合的“层级构件化”,可认为是文字变异的一种自觉现象。
其三,强势构件对于字形讹变的影响。首先我们必须区分的是高频构件与强势构件概念上的不同。高频构件是指那些高于平均构件频率的构件,是对于全体汉字字符构形而言的。强势构件是用来描述一组形似构件之间不同的强弱关系。那些构形理据更加明晰,或字符形体更为常用的构件更为强势,容易取代其他弱势构件。
如在陆明君的《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中解释“渕”(北齐《宋敬业造像》)右侧“短竖”的出现时,他认为“短竖”是将“”右侧构件的笔画重新组合而成,即由左侧的“丿”位移得来,但该原因无法解释“”、“”等其他同时出现“丿”和“刂”的字形组成原因,故本文认为“短竖”的出现应该为“”等复杂字形中所添加的偶然异写笔画,与长竖组合成“双竖”构件,虽构件“双竖”与“刂”相通,但由于“刂”作为构件的强势性,更容易取代“双竖”构件成为主流构件被人们所接受,这一强势性也同样影响了左侧“竖撇”或“竖勾”笔画的脱落,从而最终形成“渕”字。
在“渕”形成过后,与“关”形体相似的“并”、“屰”等与之相关的异写其他形体也常常代替“关”出现于“淵”的异体字符的变异中,如“”(南朝宋大明二年《爨龙颜碑》[8]3/112),“”(《龙龛手鉴・渊》[1]13),“”(中华字海・渊》[14]550),但由于构件偏离原始构形理据更远,构件“关”较之更为强势,故不如含“关”构件的异体多见。
强势构件对于弱势构件的替代,这往往就是异写字构形理据丢失的一大原因。替代的强势构件的理据模糊了原有字的构形理据,给人们对于新字形的理解造成困难,所以由各类强势构件组合起来的新字形也往往会因为理据丢失严重而更容易被使用者所抛弃,但少部分也会因形体简化或被重新塑造出新的构形理据被继续流传使用。
四、“剬”的构形理据
“剬”在《说文解字》中有收录,“剬,断齐也。从刀,耑声。”[7]170在后世字书如《字汇》[5]136、《类篇 》[11]157、《 玉 篇 》[9]320均 收“剬”为 齐 义 。《 正 字通》[6]196、《龙龛手鉴》[1]69中除用作该义外,收有“剬”与“專”字之异体“剸”互作。但在传世文献中常考释为“制”的古字,《韩非子・诡使》[26]:“所以善剬下也”记为制字同;《战国策・齐策三》:“夫剬楚者王也。”[27]吴师道补注:“史、汉作制字”。“剬”为何作“制”字异体现象在传世字书中多见,意义明确,但在《汉字源流字典》[28]641中收小篆及秦汉时期字形流变(秦)、(秦)、(汉)、(汉)均未体现构形原因,构形理据不清晰。
该异体字形成自己独有的构形理据后被世人接受,在后期碑刻中也常被使用:
并且在包含“制”的“製”字在使用中也受到字形类化而产生此类异体:(北魏神龟元年《邓羡妻李榘兰墓志》[8]4/384)、(北魏永安元年《唐耀墓志》)[8]6/235。
“制”变为“剬”的字形变化历程在汉魏六朝时期清晰可见,但实则在《史记》《战国策》一类汉代即成书的传世文献中则已多有用例,故大胆猜测这一变化历程早已在古今隶变时期就已发生,仅仅因材料缺失未见。
“层级构件化”规律是造成异体字不断丢失构形理据的一大原因,同时也是生成异体字的一种生产模式。在汉魏六朝时期“制”字的异体字变化过程中,其经历了两次“层级构件化”规律的叠加,由此造成了理据模糊的现象。
注释:
①若无特殊注明,本文拓片字形均出自毛远明先生《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检索标注格式为x册/xxx页。
②详见《北魏杨均墓志》(初拓本)。
③详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杨厉墓志》。
④详见顾专263《李渊造像记》。
⑤简又文《刘猛进碑考》综合他说,考为隋大业五年十一月立。
⑥详见国图墓志2974《崔蕃墓志》。
⑦详见洛阳博物馆藏《萧玚墓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