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2020-02-24李丽娇
李丽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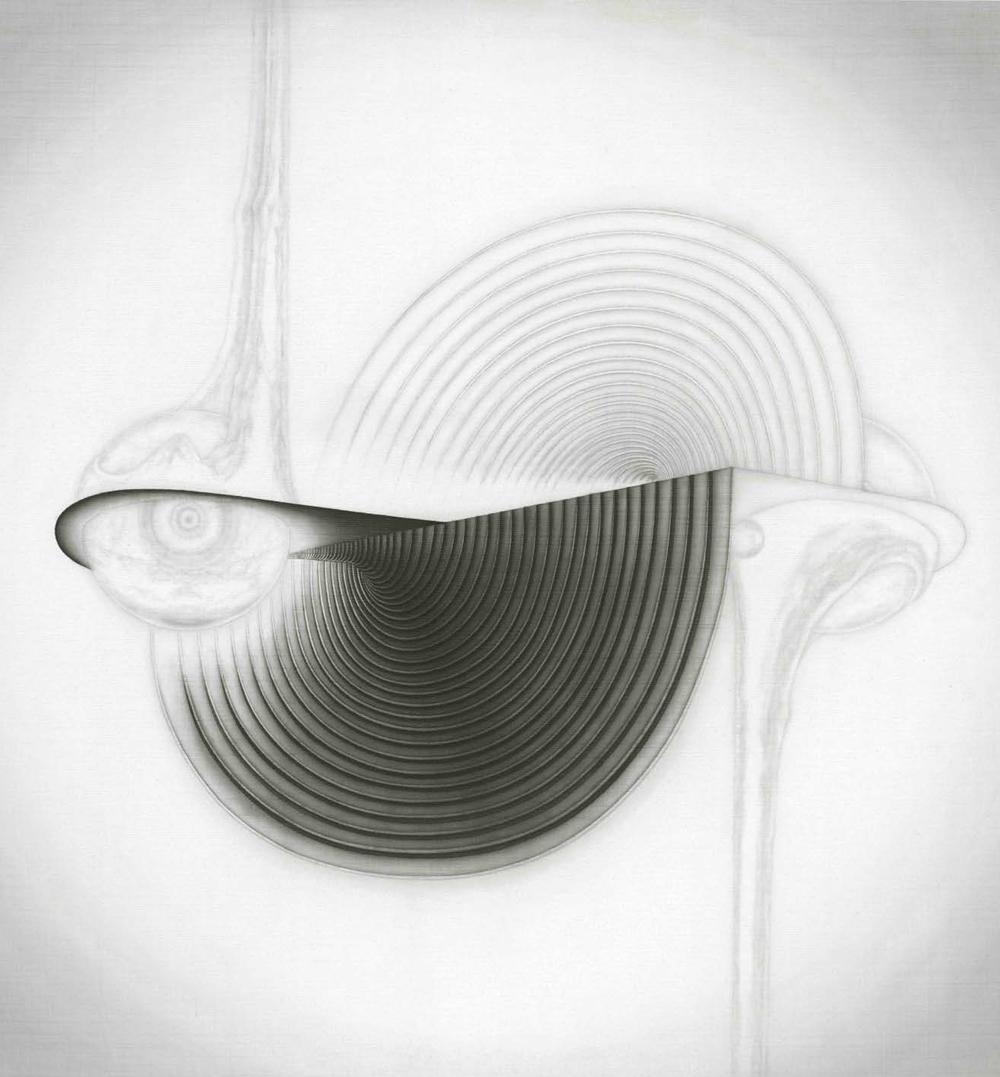
河池学院堆云文学社
广西河池学院堆云文学社成立于2004年3月14日,前身是中文系团总支学生会主办的《中文前沿》,该文学社是河池学院文传院主办并直接指导的纯文学社团,曾获得“全国人文百强社团”的称号。自立社以来,有多名社员的文章发表在《广西文学》《河池文学》《南丹文学》《丹凤文学》《宜州文学》《麒麟》等刊物上。
人生总是被无数个有形的无形的洪流推着走,一旦泄洪,就没有回旋的余地。我再也找不到能够表达我歉意的方式,无数个夜晚,我躲进暗沉的梦里,当我开始忏悔,便偶尔有光亮透进来。那些光,并不敞亮,但柔和有如月光,我便知道,我的灵魂需要这样一束光照耀。
写给父亲
我并不是一个擅长怀旧的人,除了刻骨铭心的,大体都模糊了。有关鱼塘与竹排的记忆,多半是温暖的。我的生命由水而来,母亲怀我的那一年,为躲避抓超生的人,情急之下跳进村里的一汪鱼塘,在水中憋着气,就在母亲以为撑不住时,那些人终于离开,我和母亲逃过一劫,这才有了现在的我。我出生后,父亲便承包了鱼塘,它陪我走过人生最初的十三年。
每年夏天,是父母紧张而又忙碌的日子。因为农村的夏天经常停电,池塘里的鱼在烦闷的夏季容易缺氧。为此,父亲动手做了一条大大的竹排,每日空闲时就划着竹排在鱼塘中转悠。我站在岸边,望着竹排推着水波,水波又推着竹排。
“丫头,上竹排来,我撑着你转转。”
“爸爸,我不敢。”他很少主动叫我,所以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拒绝了。
“不怕,有爸爸在。”父亲固执地喊我,我还低着头,夏天的热风吹在我弱小的身体上。我记忆中是这样的,傍晚的余晖与水交融着,波光荡漾,有鱼跳出水面,充满了诱惑。
“好!”我鼓足了勇气,跳上竹排。这是我少有的一次与父亲一起撑竹排。
年复一年,它仿佛永远年轻,而我,分分秒秒不同。
我喜欢走鱼塘的石阶,有时候蹲坐在泥上,有时候站着发呆。扒开杂草,它还是记忆里的老样子,当我仔细听着,仿佛还能听见一些琐碎的声音:早点回来啊。曾经小小的我隔着一汪池塘,对经常外出的父亲喊话,可是,这样的生活我还能再过一遍吗?
童年的日子,生活总是不富裕,但我们三兄妹却没有感到艰辛。父亲常常一碗饭几棵青菜果腹,长期劳累的生活和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他患上了肝病,好在他一直按时喝草药,每天还能生龙活虎地训斥我们,我总以为他会一直这样骂我们,直到老了说不动。但他还没老,便得了肝癌,四十二岁就离开了。一夜之间,池塘就跟着荒废了。
父亲开始病重,是我读初三那年的年三十,我们一家人窝在房间里看电视,我不记得当初看的是什么节目,只记得陆陆续续听到父亲咳嗽。我忙着看电视,没有回过头问候他一句。直到父亲咳了血,家人才手忙脚乱地送父亲去医院,之后,我才开始陷入无尽的恐慌。
第二天父亲终于回来了,大抵是看到了我的不安,不擅长微笑的父亲伸出大手揉了揉我的头发,笑笑说:“爸爸没事,医生说我的肝坏了,再换一个就可以了。”大抵是因为年轻,又或许是父亲说没事时的眼神过于淡定,他也从没有说过谎,我便相信了他的话。
父亲不善言辞,在最后的半年里,他换了一种方式与我告别。他开始变得挑剔,每每买回的果蔬,他总苛刻地让我遵照先泡上半个小时、然后认认真真地洗上三遍的准则。他不允许我喝饮料,买了一箱箱的矿泉水堆在家里逼着我喝。我顶嘴,他便暴躁地吼我:“你已经不小了,这些东西都不健康,别让我看到你生病,好吗?”大概是因为父亲最后那卑弱又无奈的两个字,我开始服软。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切实恨了他许久。父亲放在桌面上的一张五十块钱人民币不见了,那天我刚好进过他房间拿东西。
父亲认定是我拿的钱,问我:“为什么拿钱?想买什么东西,你可以先问我,我明明说过没有经过别人同意之前,不要乱拿东西。”
父亲不分青红皂白地责问,使我气昏了头,我冲他大喊:“你凭什么认为是我拿的,你这个自以为是的偏执鬼。”
父亲气得直喘气,他最看不惯孩子偷钱,小时候总是反复和我强调“小时偷针大时偷金”的老话。父亲罚我在祠堂前跪下,但钱确实不是我拿的,我担心他的身体,只能顺从地跪着。直到母亲回来,误会才解开,是母亲早上拿的钱,去集市买了些东西。知道真相的父亲局促地和我道歉,他充满希冀的目光看着我,等我的原谅。我扭过头,回避了他。父亲为了讨好我,给我买了心心念念的两条裤子,还买了从不允许我吃的零食。他不想把最后的时光浪费在跟我生气上。
第二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晚,而我也渐渐地察觉出父亲身体的异样。化验单、检测报告可以藏得住,可是一个人的消瘦是真真切切表现出来的。端午节放假,我回到家时,太阳将要落尽。我清楚地記得那个傍晚,父亲坐在院子里那个吱吱作响的椅子上,他削弱的身影,被风吹起的衣襟,在血红的背景下,犹如一幅残忍的画影。
父亲挥手示意我过去,我假装没看到,转身跑上楼。跨上最后一级阶梯时不小心摔倒,我的鼻血和眼泪同时流下来。我知道自己的举动一定深深伤害了他,但不见他是我花了许多勇气才做出的决定。我习得了父亲身上所有的优点,乐观、坚强、执拗,唯独没学会勇敢,我无法接受曾经伟岸的男人,此刻形同槁木的样子。
爸爸弥留之际,留给我们兄妹三人一人一张五十元的人民币,它很新,应该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在生命仅存最后一点意识时,他留了一句话:作为父亲,对不起。
我无法原谅自己。
那张五十元人民币被我沉沉地压在铁皮盒里,每晚都会打开望一眼,它在我的指尖发出清脆的声音。
一天晚上,我回房间躺着,照例打开铁皮盒,眼前的景象让我崩溃,几近发疯——它不见了。第二天找到“凶手”,是九岁的堂弟拿走了它,到街上换了零食和玩具。我冲九岁的堂弟咆哮,可那实际上是我的错,是我没有藏好它……
我去问店主,店主一脸茫然,得知那张五十元人民币对我的特殊意义后,他决定帮我回忆。
“好像是一个拿着一百块的小女孩换走了那张五十元人民币。”
“好像是?”
“嗯……嗯,抱歉,我也记不大清了,来买东西的人比往常多一些。”
店主模糊不清的记忆使我泣不成声,望着茫茫的街道和来往不息的人群,最终我妥协了。
没有了那张人民币,铁皮盒还原为铁皮盒,静静地躺在桌面上。白天我听不到它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它轻轻地叫一声,像是在向我哀求。这样想着,后来便总是失眠,像是要证明什么,我决定把铁皮盒锁起来了。
一放就是一个夏天,紧接着是秋天,最后冬天也过去了,铁皮盒再没有打开过。数数日子,爸爸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偶尔有人问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后,有没有觉得自己的人生轨迹受到了影响?
我很茫然,父亲走后,家人们都心照不宣地生活着,闭口不提与父亲有关的事情。直到有一天,和同学们聊起家人,我脫口而出“我爸爸也是这样”时,我才明白父亲原来真的不在了。
父亲啊,你种在池子旁的葡萄树已经结果了,你要是还在,该多好!
写给母亲
母亲不是传统的母亲,她的嗓门极大,总是连名带姓地喊我名字,做事雷厉风行,她有时候粗鄙、小气、没有见识、藏着农村母亲的缩影。但无论生活多么不如意,母亲一样热爱生活。
母亲算得上是一个美人,外婆总和我提起,“你妈年轻的时候啊头发乌黑又直,两只眼睛像一潭水,可多人追嘞。”在那个年代,每家每户的兄弟姐妹都很多,我母亲排行第一,底下有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母亲聪明能干学习好,可家境贫寒,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不满十岁的母亲就开始扛着锄头种菜卖菜,帮着外婆送弟弟妹妹上学。十六岁时,母亲一个人跑去广东打工,在她的坚持下,弟弟妹妹都完成了学业。母亲的好,舅舅和姨妈总记在心里,后来父亲生病,叔叔和姑姑从未问过,只有舅舅和姨妈们辞掉工作,一直陪伴母亲度过了那段日子。
爷爷出生在没落的地主家庭,遗留着“女孩读书无用”的观念,不肯送姑姑读书。母亲十八岁便嫁到我们家,爷爷拗不过性格刚烈且脾气又大的母亲,最终同意让姑姑读书。母亲每天骑一辆破烂的自行车走街串巷地卖豆腐,赚得的钱一边补贴家用,一边供姑姑读书。只是姑姑不是读书的料,考不上高中,初中毕业后便去广东打工了。奶奶一直不待见母亲,奶奶的偏见在于,她认为女人应该贤良恭顺,伺候公婆,料理家务。然而母亲偏离了这种期望,后来贤惠温和的小婶进门了,一对比后,奶奶的偏见愈演愈烈,直到大哥出生,婆媳的矛盾才逐渐缓解。
母亲是一个能干的女人,与父亲结婚后两人勤勤恳恳,白手起家,日子渐渐富裕起来。童年时代,母亲说一不二的性格使我产生了恐惧。我更愿意呆在婶婶家,看着婶婶温和地呼唤她的孩子,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讲故事时,我的脑海中便会浮现这样的想法:“要是我妈也和婶婶一样就好了,为什么我的妈妈不是婶婶。”母亲从来不曾这样温柔地待过我,可是长大后想起抱有那样想法的我,总是感到愧疚。因为无论我犯多大错,多么不优秀,她从不曾说过“我的孩子和某某某一样就好了”这样伤人的话。
我对黑夜充满恐惧,但母亲坚持让我一个人睡。看到月光照耀的树梢闪闪发亮,我总疑心它们会从窗口伸进来,把我夹走。我睁着眼迟迟不敢睡去,天越来越黑,月亮也不见了踪影,这样的情景使我发抖。母亲的房间在隔壁,我哭着喊她,却始终等不到母亲。哭到筋疲力尽,我才带着对母亲的愤恨入睡。我曾多次控诉她的无情,然而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夜里,母亲一直站在门外听我的动静,直到我睡着后才走开。如今再和她提起,母亲却觉得难为情,很快挂掉了我的电话。
和母亲通话的时间很少有超过五分钟,即便是我上了大学,每次主动给她打电话,总是聊不到几句便挂了电话。有一段时间我忙着社团的事情,很久没有和她联系。母亲竟破天荒地给我打电话:“最近很忙吗?你已经两个周末没有打过电话了……”
“最近事比较多,而且每次给你打电话总说不到五分钟你就挂了。”我小声地和母亲解释,得知我在忙的事情,而且常常熬夜,母亲很不解,说道:“你是在糟蹋自己的身体还是在糟蹋我?做这些有意义吗?”母亲的接连发问让我有些发怒,冲她喊:“你什么都不懂,我已经长大了,我在做什么我清楚。”
我的蛮横在母亲面前屡屡表现得淋漓尽致,母亲沉默了很久,母亲生气了,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缓和气氛。很久母亲才回我话:“随你自己吧,我的路已经走到这了,我没有什么文化,不懂你想走什么样的路,我只求你健健康康……”
我突然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话,直到母亲挂掉电话,我才意识到我说的话有多伤人。回想到这二十年来对母亲的愧疚,以及此刻说她“什么都不懂”的罪过,我恨不能就此站在她面前,向她请求宽恕。细细想来,就是这样一个年华渐逝、言语粗鄙的妇人,独自对抗着周围人的冷言嘲讽,将三个孩子送进大学。在人生旅途中,母亲赋予我的深度和广度,没有任何一本书能比她更周全。
我是一个怯懦的孩子,怕出头露面,搞砸事情,但母亲勇敢且强大的个性影响了我。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终年忙碌着,每晚夜里两点半,我们还在做着香甜的梦时,母亲已经起床了。到市里的路有十多公里,我无法体会一个女人在骇人的黑暗中是如何克服恐惧,日复一日地从市场带回货品,为我们换取生活费用的。母亲做事永远不敷衍,在忙碌之中,门前那株葡萄树依然被照顾得很好,隔年结着诱人的果肉,正如我们兄妹三人一样。母亲说,每次觉得自己撑不下去的时候,看到这株葡萄,便会想到父亲,想到三个可爱的孩子,便觉得内心一阵温暖,就想着还能再硬着头皮撑一段时间。于是,母亲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
母亲啊请你原谅,在旁人面前永远游刃有余的我,却笨拙地不知如何表达一个女儿对你的情感。这个世界并不完美,但我真的爱它。
写给阿才、阿福和胖小猫
我不知道狗和猫是带着什么使命来到人间的,在农村,它们能活到老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小时候我们家养有两条狗,它们出生后不久大母狗便死掉了,大伯父和叔叔们将它剥皮炖了肉,在他们眼里,狗的使命只有两个,一是看家护院,二是作为盘中肉。
我和哥哥喜欢狗,于是为活下来的两只小狗搭了一个窝,秉持着“贱名好养活”的原则,我们为小狗起了名字,大的叫阿才,小的叫阿福。它们越长越大,越来越高,身强力壮的狗狗掌握了一项技能――捉老鼠。每每捉到一只老鼠,便会额外得到一块骨头。这更激起了它俩逮老鼠的兴趣,心甘情愿地身兼多职,以表达对主人家的感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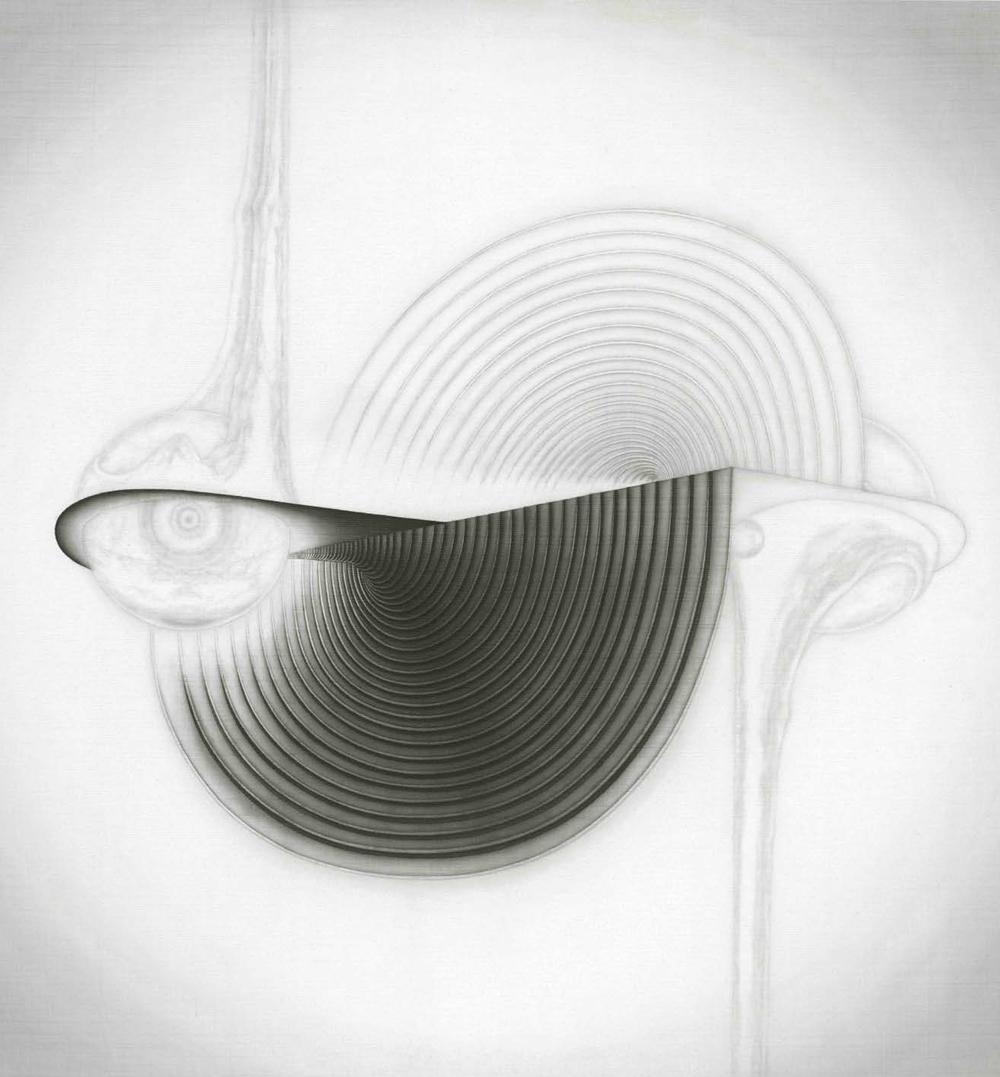
然而阿才阿福受到的待遇与付出是不对等的。突然有一天,阿福被路过的摩托车撞断了腿,嘴上的血不停地往下流。乡下没有给狗医治的地方,我只能心疼地给它绑上碎布。过了一个月,阿福死在了它的小窝里。失去了兄弟的阿才开始不愿意进食,它越来越不想回家,终日伏在门前的树下。我心疼地摸着它的脑袋,我和它说:“别难过,我会一直陪着你。”兴许是听懂了我的话,阿才的眸子又亮起了光,很乖巧地往我身上蹭。
一日放学回家,远远地便看见叔叔、伯父和爷爷们聚在门口,我走近一看,却发现阿才被绳子捆着吊在铁杆上,嘴上残留着血迹,早就断了气息。原来他们趁着狗没有饿瘦,打算早早把它打死吃掉。我气得发抖,只能崩溃地大哭。大人们被吓了一跳,却还是笑着说话:“你小孩子懂什么,狗没用了只能这样呗。”大人的语气平淡得好像只是不小心踩死了一只蚂蚁,我不知该如何控诉大人残忍的罪行,我曾信誓旦旦地向狗允诺,却没有践行。
日子过去将近十来年,我还是很喜欢狗,路上见到也会偶尔逗逗,但家里再没有养过狗。阿才死去后,奶奶开始养猫,猫比狗精明,更懂得讨主人的欢心。猫也会撒娇,当大人们坐在院子里晒太阳闲聊时,就会爬上主人的膝盖,蹭着手臂,千娇百媚。因为它的到来,家人们轻而易举地忘记了曾给家里带来快乐的阿才阿福。因此我格外憎恨那只猫,我愤恨地喊它“死小胖”,假装不小心踢翻它的食物,或者不经意地踢它一脚。但小胖似乎毫不介意我怎么评价它,我这些小把戏在它看来,估计太过可笑和幼稚。之后因为一次意外,它的腿被门重重夹了一下,走路就有些一瘸一拐。不久奶奶又养了一只猫,新来的猫白净、勤快、动作迅速,很快取代了小胖的地位。我竟表示愉快,隔三差五地在它面前揶揄它,它也不恼,我才想到,小胖听不懂人类的语言。
当我决定停止这无聊的玩笑后,小胖离家出走了,再没有回来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