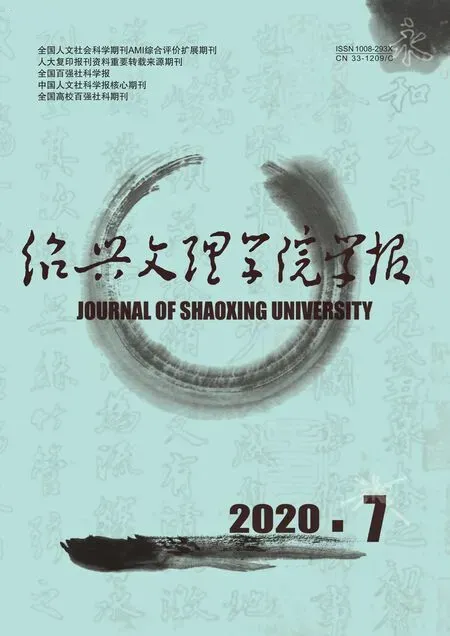生态文明与美好生活的创建
——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生态视角
2020-02-24任志芬
任志芬
(绍兴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直是社会文明发展的诉求。孔子的“大同社会”、陶渊明的“桃花源”到孙中山的“天下大同”,以及西方历史上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康普内拉的太阳城,再到19世纪初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揭示了对理想社会的渴求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基于历史的逻辑和深厚的现实根基,当前我国再次提出把实现美好生活作为新时代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这是时代的呼声,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美好生活的始基
何谓美好生活?美好生活是一种价值判断,对美好生活的界定往往存在各人各异。寇东亮从生活结果与生活过程相统一的角度评判生活的美好与否,认为只有当生活的目标和过程都是美好的,才能在结果意义上说生活既是幸福的,更是美好的[1]。袁祖社认为“美好生活”是社会发展的最大价值公约数,其本质是有内涵、有质量、可持续,稳定的有品质和境界的生活,是可欲的、可期待的生活[2]。武潇斐通过研析马克思的《44年手稿》后指出“美好生活”是建立在对象性关系基础上的人、自然界与社会相统一的生活[3]。尽管评判生活的美好与否具有主观性,但生活的内容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好生活的主体不同,内容也不一样,新时代下的美好生活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有的物质富裕、自由平等、可持续发展的生活。其中,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始基,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乐到人类进行的生产活动、社交活动等,都一刻也离不开生态环境。
可以说,生态环境维系着社会的文明演进和生活方式的动态变化。原始文明下人类主要以采集、狩猎为主,过着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生活,这种“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4]的生活当然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美好。农耕文明时代,人类逐渐脱离了自然的脐带,对生态环境影响日益增强。由于不懂得对自然资源的科学开发和利用,历史上曾经辉煌的文明逐渐衰落、消亡,如印度早期的哈拉巴文明、中国古楼兰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经过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人们渐渐地积累起一系列农耕生态思想,意识到生态环境对农业的产业结构、丰歉程度、生活需求的重要影响。相较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转变,创造了以往一切世代所无法比拟的巨大生产力,然而“这种巨大转变的悲剧性嘲弄在于消费者社会的历史性兴起对于损害环境有着重大影响,却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一种满意的生活。”[5]因为这种生产力受资本驱使,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工业文明剥离与自然的直接关系,强调人对自然的控制与利用,将人的欲望无限放大。对此,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在1968年《公地悲剧》中指出: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所有人们争先恐后追求的结果最终是崩溃[6]。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各种危机日益加深,促使人类进一步反思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发展问题,进而呼唤新的文明的到来。生态文明顺应了社会发展趋势,科学地扬弃工业文明的反生态性,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美好生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追求
生态文明不是现代人类中心论,认为一切都应该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罔顾因资本的逐利本性所带来的资源掠夺和环境危机。也不是生态中心论所主张确立自然价值、自然权利,崇尚对自然的崇拜,要求回归自然,否认人的主体地位。生态文明充分肯定自然价值,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系统,人只是自然界中一个物种,既不能超脱于自然界之外,更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生态文明建设追求的是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者高度统一的美好生活。
生态文明指引下的生产发展追求的是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统一,走的是绿色发展之路。自然界没有人类照样可以存在,而人离不开自然,没有自然界,没有自然提供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人类就无法生存。生态环境是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助于生产力的高效和持续的发展,多样和丰富的生态环境会促成多样和丰富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对传统发展模式,绿色发展是基于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有限的条件下,遵循绿色低碳循环原则,将人的生产劳动纳入生态系统中,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关系,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当前,绿色发展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本抓手,坚持生产生态化、生活低碳化,不断创新绿色技术,确保环境清洁和生态平衡。
生态文明实行的是低碳生活方式,创导生态消费,而不是追求消费主义。低碳生活倡导节俭生活,其目的是节制欲望,使消费符合生活目的,让消费回归本意。低碳生活的本质就是消费生态化,亦即生态消费。生态消费是一种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行为,具有适度性、持续性、全面性等特性。这种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同时保证了消费的代内和代际公正:一方面当代人之间能够机会均等地利用公共自然资源,享受良好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在满足当代人生活需要的同时不危及下一代人的生存与发展。生态文明主张的生态消费是对消费主义生活观的彻底否定,充分体现人在消费中的主体意识,不仅关注人的物质需求,更注重精神需求、生态需求,关注生活质量的提升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生态文明是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人道主义的统一。人类历史是一部自然界对人生成的历史,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活动史。生态文明是经人与自然反复较量之后的理性生成,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全新社会形态。人的活动和动物的生命活动的区别在于,动物是本能依存于自然界,人在自然界是“按美的规律来建造”,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人在实践活动中不断摒弃对自然界的“暴力”行径,消除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全面异化,踏上自觉规避危机和自我拯救的生态文明之路。生态文明下人类开始自觉地把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结合起来,遵循自然界内在运行规律,真正实践“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7]。
三、美好生活创建中不和谐的生态音符
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基本生活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实现美好生活就成为发展必然。然而现实发展中,依然存在有悖于美好生活创建的不和谐音符。
唯物史观指出,人类社会发展遵循着自身内在基本规律,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要义。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水平、生产力状况怎样不仅仅取决于人这单一因素,还包括自然因素,曾经辉煌的古代文明消失,现代文明下众多灾难的发生,自然界无不在向人类发出警告。
自然界是一个自组织的有机系统,人类在这个有机系统下既是能动的也是受动的,一切实践活动都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载能力。然而,受欲望的驱使和对资本利润的追逐,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依然是傲慢加偏见。
在国家层面,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问题上,国际谈判一直陷在“囚徒困境”中:各国在诉求建立公平公正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框架的同时,又害怕本国利益在国际制度议价中被牺牲。如《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的缔约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艰难谈判。每年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或无法达成协议,或签订的协议无法得到有效执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军事、科技实力实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强权政治肆意横行。2001年美国以美国经济受损为由退出《京都议定书》,2017年退出《巴黎协定》。当前,新一轮大国核武器竞赛存在进一步加剧之势:美国在《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提出要加大资金投入研发新型核武器,恢复和扩大核能力。俄罗斯不甘落后,曝光了一系列新研发的新型核武器。法国总统马克龙也称将在任内更新法军核威慑力。如此种种,造成全球对核武器之忧达到冷战以来最高程度。另外,地区性战争不断,恐怖活动在全球范围仍然嚣张等。世界的动荡与不安,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8]。
在社会层面,消费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消费促使社会再生产。无论社会文明如何进步,生产与消费这一关系范畴必须建立在自然的承载范围内,然而人类正在为社会发展努力生产,却无暇思考“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为谁生产”。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消费主义价值理念依然盛行于当下社会。人们消费追求的是商品的符号价值,而不是它的使用价值,通过消费什么来展示自己的社会身份、地位,消费即存在。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因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引发的,当前网上花样百出的财富消费就是一种炫耀性消费。这种没有节制的消费不仅是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损耗,而且产生的废弃物也严重污染了生存环境。对此,美国研究垃圾问题的专家威廉·拉斯吉曾批评指出“历史上任何文明社会,都没有丢弃过这么多、这么可观的物品”[9]。
一边是过度消费,一边又是极端贫困。意大利经济学家巴莱多曾经提出8020定律,指出全球20%的人拥有80%的财富,然而,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贫富差距却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数据显示,当前世界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全球82%的财富。贫富差距过大必然成为巨大隐患影响经济持续发展,使社会动荡不安。
在个人层面,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家、民族、地区乃至个人的一举一动往往就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追求物质经济增长的社会大环境下,造成了人人把获取物质利益作为人生奋斗目标,以财富论英雄,消费等同幸福。这种生产异化、消费异化,最终会导致人性异化。人与人之间不再是理性平和、亲善友爱,取而代之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人与人之间的危机必然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当我们完全以一种彻头彻尾的工具主义态度看待人工产品或自然资源时,我们也很难把意义赋予世界。”[10]
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创建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当前,生态环境质量和治理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围绕生态环境问题,我国在经济、政治、制度、文化等领域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和实践措施。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现美好生活,已经成为新时代的奋斗目标。
打造生命共同体,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在获得丰裕的物质满足的同时,也饱受自然环境的种种报复和威胁,已经由过去的“盼温饱”“求生存”转变为现在的“盼环保”“求生态”,生态环境直接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注重经济建设的同时,十分强调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然而实际建设中往往存在以牺牲环境获取经济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并详细阐述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强调人的生存与发展和各种自然资源、要素之间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有机体,一切实践行动都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尊重自然、维护自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资本本性必然会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为美好生活实现提供政治保障。生态环境问题作为基本国策和发展战略,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到科学发展观、构建“两型社会”再到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生态文明,无论是理念还是实践都充分表明,我国在维护和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上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从历史和全局的战略高度作了全面部署。2015年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不仅清晰了深化生态环保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也进一步凸显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高度,明确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党的重大使命的政治考量指标。
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新时代人们的生存需求已经发生质的改变,对生存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转变传统生产模式,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2015年我国正式提出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以需求侧为主调整为以供给侧为主。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产业结构,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建立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11]2000年以来,我国出台实施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有力打击了环境违法行为。2018年1月1日,《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实施,首次完成由环保费改税。随后又将生态文明写入国家根本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机构改革,整合各个部门,理顺相关职责,增强办事效率。加大制度考评,重塑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发展观,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职责明确、严格追责制度,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追求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离任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等。开展部署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对各地环境治理情况进行“回头看”,不但巩固了生态环境建设成效,也大大提升了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领世界生态环境治理。建设生态文明、构造美好生活离不开国际间交流与合作。中国在“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11]。1994年发布《中国21世纪议程》,积极履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1世纪议程》的承诺。1996年确立可持续国家基本发展战略,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从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到十八大之后,中国始终秉持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理念。提出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实施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率先发布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方案,向联合国交存《巴黎协定》气候变化文书等,以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为全世界提供了解决生态问题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美好生活的实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生态文明是对以往一切文明的扬弃,蕴含了美好生活的全部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正积极主动地担负着大国使命,以引领者、实践者的姿态迈向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创建以人民为主体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