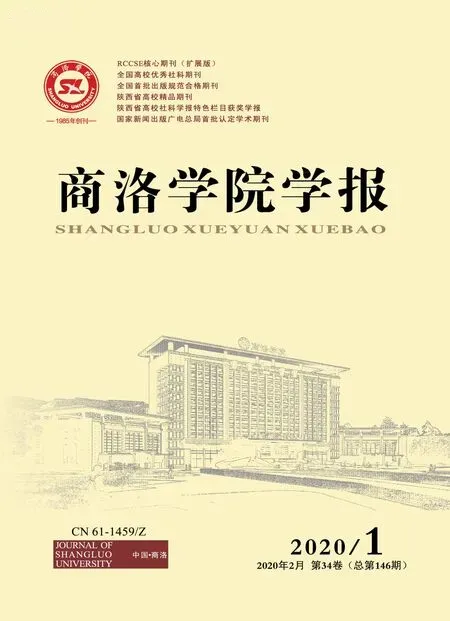乡土滋养下的生命体悟
——论白忠德散文《风过余家沟》
2020-02-24吴志新
吴志新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陕西汉中 723001)
白忠德出生于陕西佛坪县的余家沟,是陕西文学界一位厚积薄发的青年作家,故乡的人情山水陪他度过了漫长的青少年时光。因此,他的文学视线首先投注的就是那片极具自然之美的乡村故土。正如他所说的:“我对佛坪作为故乡有三重体认,即地理的故乡、情感的故乡和文学的故乡……这辈子,我是为故乡而生,我的笔也将为故乡所用。”[1]235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白忠德富含乡土特色的散文予以评论。张勇[2]运用文学地理学方法,对白忠德散文的创作个性展开研究,发现其散文创作的独特主题与审美个性;李继高[3]从生态主义出发,阐释了白忠德散文倡导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理念与祈愿,表现出人类对动物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田子爽[4]从白忠德的创作态度、故乡情结以及生态意识等方面叙述了作家对故乡佛坪的深切依恋和赤子情怀;宋宁刚[5]从散文的创作特质及文学的主体性出发,别开生面地论述了白忠德散文中存在的散文类型自我限制化及作品游离于文学边缘等弊病。当前的文献从白忠德故乡情怀出发挖掘隐藏在作家内心深处细腻的生命体验,并系统论述其以故土情结为基调而展现出来的人与物的交融以及神秘乡村文化的记忆与传承。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对白忠德的散文集《风过余家沟》 进行全新解读,挖掘其自然抒情创作状态下更深层次的“生命”本体写作境界。
一、淳朴人性的怀念与向往
“在哲思式的写作中,乡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明理念、一种价值依托。这个维度上的乡村,是立足于实际经验之上的抽象和升华,带有颇为强烈的主观性,受到写作者个人的知识趣味、价值立场的强烈介入和影响。因此,这类写作生成的‘乡土’显然存在着与现实对话的个人寄托,尤其是在城市化高歌凯进、乡村一再衰败的社会语境中,乡土的内涵凸显,形成一重镜像而折射出现实的匮乏,传达人们的乡土想象。但如果仅仅从观念形态来展示和肯定乡村的特定价值,难免会显得空泛,这时乡土经验的补充和支撑就显得极其重要。乡土经验,既是这类写作的重要构成,也是理解这类写作的重要基础和前提。”[6]白忠德的散文犹如泥土般质朴清新,浑厚深沉,处处洋溢着鲜活的生命气息和淳朴的风土人情。虽然他已离开故土多年,但凭着对故乡耳熟能详的优势和极致敏锐的观察力,他用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呈现出故乡最真实的人与物,特别是对淳朴人性的深情表达,令人迷醉向往。
白忠德在《风过余家沟》中书写了众多乡村人物,无论是与作者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还是淳朴善良的乡间百姓,又或是余家沟与众不同的“精人能人”,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显现出一种乡村生活者固有的淳朴气质——人性之美。白忠德从自己熟悉的家人开始写起,于是乐于帮人牵线搭桥的母亲形象跃然纸上。母亲是传统的乡村女性,她实诚善良,待人友好,招待客人总是竭尽所能地照顾周到,乃至对于过路的货郎都心生怜悯,赠给两个热气腾腾的馒头。命途多舛的大爹憨厚老实,听到曹家梁开荒地的火燃到山林的消息,放下背篼,拿起薅锄便奔赴山林救火,最终因此丧命。大爹虽没有任何荣誉,但他遇到危险毫不退缩的质朴精神值得我们为之一叹,他是余家沟实打实的救火英雄。余家沟人少,民风淳朴,人性善良,遇个外地人也是端茶倒水管饭的,更不用说邻里之间了。
《枣花飘香时》中,由于家庭变故,东东不得不辍学帮衬家里,他的小伙伴听说后便纷纷想办法帮助东东。大家轮流帮他放牛打猪草,并让自家大人帮他家种地,最终东东得以重返校园。这种来自乡村的深刻的慈和与仁爱,让作者看到了有别于城市的温暖与宁静,无论这温暖与宁静流淌在怎样的生活之谷,那生活都将是一片绚丽的斑斓。《邻居琐忆》中,作者用沉稳感激的笔调叙述了小时候与邻居家的一些琐事,无论是主动清扫牛屎、从未抱怨的张家,还是慷慨解囊、雪中送炭的屈家,又或是被大哥家狗咬导致发炎,自己悄悄花钱打针的“老表”,都显示出乡村人们的大度与宽容,善良与淳朴。他们活在作者永恒的记忆里,虽是隔着几十年岁月往回望,但故乡的人依旧如泥土般单纯厚重。而如今“那些充满泥土味的乡村淹没在我们匆忙追逐的脚步和荒凉的背影里。和许多中国村庄一样,余家沟也在经历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淘洗”[7]65。这里的住户已所剩无几,屋院荒凉成杂草和野兽的领地。曾经那些可敬的村民带着余家沟的质朴善良,死的死,老的老,走的走,空留一座荒芜。面对现代化进程的侵袭,作家白忠德极力用笔触去挽留,去定格,但他又深知自己的无奈与能力的有限,因此,他凄婉地感叹道:“我想挽留住什么?我又能挽留住什么?”[7]65
在叙述乡村美好人性的同时,白忠德还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和焦虑感,曾经生活的地方与他当下的生存状态形成巨大的反差,故乡越是单纯美好,这种失落感就越强烈,因为他不仅无力改变当下金钱至上的浮躁风气,更无法遏制它的侵蚀程度,所以他选择记忆故乡,寻找故乡,乃至回到故乡。而“人们对故乡的寻找,也就是在找寻一种自由自在、可以安放心灵的氛围和感觉。生活在当下这样一个‘速朽’的时代,一切似乎都显得虚无缥缈、难以把握,只有在对过去的回望中,才能建立起自身的连续性,这个意义上的怀旧不啻于一种自我拯救,是为了建立一个完整的、具有连续性的自我。”[8]这是白忠德对自我的不断审视与鞭挞。
二、民俗风情的记忆与传承
“民俗风情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世代承传、相沿成习、口耳教化的精神文化范式,且是某一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心理上所形成的共同思维习惯和生活模式。”[9]民俗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是需要被记忆和传承的,白忠德在《风过余家沟》中处处洋溢着对家乡民俗风情的热爱与怀念,那些关于乡村的记忆与信仰如涓涓细流涤荡他的心灵。因此,他用文字记录即将流失的乡村文化。
民俗文化是神秘且具有魅力的存在,它吸引着作家去着力发掘、怀念并表现它。在《风过余家沟》中,白忠德在表现乡村淳朴人性的同时,用深刻而朴实的笔触描绘了家乡的众多风俗及民间信仰,他用文学来审视农村社会文化,表现人与历史在文化中的存在与延续。在《回老家过年》中,白忠德用满是遗憾的笔触叙述了今非昔比的“年味”,他所渴望的记忆中的年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温情与热烈,物质生活丰富了,但人情却随之变得淡漠,乡邻之间缺乏走动。以前的农村都很穷,因此过年便显得正式而隆重,大家围在一起共享难得一尝的“美味”,围在核桃树下荡秋千,一起舞狮子、扭秧歌、扭旱船、唱花鼓……而如今村里人越来越少,连一台狮子旱船都凑不齐了,年味由浓咖啡稀成了白开水,“我的伤感与无奈像夏天野地里的茅草一样疯长”[7]68。在这里,白忠德对乡村文化的失落表现出深深的沮丧和怀念,如今的老家在城市化进程的“洗礼”下滋生出更多的寂寥与落寞,消解着故乡世代沿袭的传统风俗,而“我”面对这种缺憾却显得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便是记录与怀念。这对他来说也许是对故乡民俗文化最好的定格与传承了。
白忠德在《风过余家沟》中还记录了余家沟的众多民俗信仰,比如神秘的“撞鬼招魂”和充满传奇性质的“神话故事”等。“民俗信仰又称民间信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10]白忠德所记述的这些鬼神事件都是发生在自己及其亲人朋友身上的,这无疑增加了这些事件的“真实性”和神秘性,让他对故乡的民俗信仰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赵先生是母亲族中的长辈,除了医术高妙外,他还是一个懂法术的半仙式人物,他能通过念符咒来止血;遇到“水鬼”,能处变不惊地念咒击退“水鬼”;遇到“索命鬼魂”,他能有条不絮地用“法术”来保命。大爹是一位憨厚老实却命途多舛的人,他是被夜里出没的“鬼”勾了魂索了命的。因此“夜里谁叫你名字,一定要听清楚再回应,有前音没后声的,那是鬼,专门叫人名字勾魂的”[7]21。“‘叫魂’是一种民间疗法,说是人受到惊吓后魂就跑了,要不叫回来,轻则染病不愈,重则要丢性命。”[7]29白忠德用平实的话语记录了父亲和自己的“叫魂”经历。父亲黑夜赶路时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回来后婆婆便用特别制作的鸡蛋和专门的驱邪咒语帮父亲“叫魂”。“我”由于摔到沟里,耳朵上方的头发莫名脱落,母亲便让“我”专门从西安回来“叫魂”,神秘的是自从叫魂完毕后,那脱掉的地方又生出了发,人也格外精神了。“白忠德当然不是真相信有鬼魂存在,这些鬼魂的故事本质,是曾经的故乡人与当代故乡人、与作者自己穿越时空而进行的一次文化‘约会’。故乡的文化风物使他们互相牵挂着而精神相通!”[11]神文化在白忠德的笔下也表现出一定的传奇性,火神庙、观音庙、二郎庙等等都标志着民间信仰的崇高与完备。而民间信仰并不是一种无聊的存在,它是人们保持内心的一种希冀,他们深信世间有一种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力量,能够使自己或家人、亲人避灾趋利或满足其他生活心愿。
无论是乡间古老的民俗活动还是神秘的民间信仰,都是一种特定的文化标签,它们是一个地方重要的“物质客体”,是促成人们怀旧的重要生发点与落脚点。白忠德以自己的方式保留了对故乡民俗的记忆与传承,他对故乡文化的自豪感与失落感也随之装入细腻的笔端。
三、自然生命的崇尚与关切
“在乡土社会中,基于时间延续和空间延展所形成的‘熟悉’——既包括人与人的熟悉也包括人与物的熟悉,实际上塑造了乡土秩序和人们的熟悉感觉;经过长期的陶冶,这种感觉形成了浓厚的乡情的一部分,它不仅来自家人邻里,还来自所熟悉的花草树木等自然之物。”[12]白忠德在《风过余家沟》中不仅写了故乡的人与事,还用浓重的笔墨书写了故乡别具一格的自然生命景观,轻快而饱含柔情的笔调显示出其对故乡草木和动物的崇尚与热爱。
“自然事物与人性的古老力量相结合,塑造了人的生命体验,而这种体验往往在个体生命的早期便扎下深厚根基,其表现之一就是人的‘故土情结’,故乡的泥土和草木也会唤起人的记忆和感情。”[12]白忠德的生态散文中弥漫着对故乡自然生命的崇敬与关切,作者的目光不是居高临下的俯视,而是像看待伙伴一样看待这些生灵。在《故乡的竹园》中,作者叙述了故乡竹园的静谧与美好,展示了竹子低调沉稳、坚韧顽强的精神品格,同时流露出对喧嚣都市的担忧和焦虑。在《山里的春》中,作者深深沉浸在故乡春的意境中,描写了家乡的花草树木、鸟语花香。他带领我们走进山茱萸的淡雅与朴素;发现山桃花的谦虚与隐忍;找寻樱桃花的浓烈与欢快。在这里,鸟兽们欢呼雀跃,弹奏着美丽的交响曲,狗妈妈唤着狗儿来舔食;黄豆雀享受着恋爱的热烈;松鼠跳跃飞荡,释放一个冬天的沉闷;熊瞎子揉着肿胀的眼睛迎接春的到来……而“我”却“掐着臭老汉,挖着黄花苗,摘着阳雀花,躺在青草丛中数云朵”[7]143。这些文字表露出来的是白忠德对大自然的崇敬与热爱,他与自然万物和谐交融为一体,享受着大自然独特的馈赠与欢乐。
“动物是我的邻居和朋友,曾经与我朝夕相处,而今和我同居一城,是我生命中的一份子。然而, 我对这些朋友又了解多少呢?大约是在2003年‘非典’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将目光投向秦岭,瞩目佛坪,书写我眼里心里的动物朋友,以一颗平等真诚之心,与他们交流谈心,倾听记录他们的前世今生、喜怒哀乐。”[13]在《抱愧黄颌蛇》中,作者讲到:“以往我们那里蛇很多,自从南方时兴吃蛇,蛇就被人抓去卖了,蛇一少价钱便高,逮它的人就越多,蛇也就更少。没有了蛇,老鼠便成了灾。”[7]150如今的老家,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吃越来越讲究,吃法也越来越野蛮,“发明”出猴脑、活蝎、鲜牛、鲜羊等千奇百怪的吃法,各种珍稀动物都成了人类的盘中餐腹中食,人类变成野生动物的天敌。于是他感叹:“什么时候吃光了动物,人类就该吃自己了,那时才热闹呢!”[7]149上帝在创造人的同时也创造了形态万千的生命,这些生命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一方受到威胁的同时也给另一方带来不可回避的伤害,甚至是灭亡。而现实中人类的贪婪之欲正破坏着生态的平衡,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人类不能平等对待甚至无视自然界中的动植物生命,这最终会让人类自食恶果。
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物质财富的暴涨,在金钱利益的冲击下,人类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和自私狭隘的劣根性暴露无遗。正如作者在《黄鼠狼之殇》中所写的那样,黄鼠狼叼鸡只是偶尔的举动,但人们却只记住它是偷鸡的盗贼,全然把它“捕鼠高手”的职能抛在脑后。人类为了自己的一丝小利便漠视它的大功劳,这是何其悲哀。在《毛老鼠》中,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观赏欲望,把本应快乐生活于林中的毛老鼠囚禁在旅游景点的笼子里。他们本是林间的自由精灵,却因人类的私欲丧失了快乐家园,这对毛老鼠来说无疑是最为残忍的。自然万物都是充满灵性的,它们有着自己既定的生存轨迹和生活状态,它们拥有野性的力量和鲜活的生命,如果人类以自己的标准和愿望去驯化它们,“培养”它们,则会让它们失去原始的生命动力,变得呆滞而木讷,毫无生机。驯化动物或许能给人带来一时的利益和快感,但对动物本身的伤害是不可挽回的,它们将失去自己的野性与个性,失去动物最本真可贵的品质。
大自然所有的生命都应该是相互联系、不可缺少的,保护自然、与众生灵平等相处成为现代人急需建立的生态意识。白忠德用其饱含深情的笔触为我们书写了众多动植物的生命印记,他的每一次有感而发都带着深深的自我反省与体悟。在生态问题愈发严重的当下,他的生态散文便具有了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意义。
四、结语
白忠德的《风过余家沟》是在个体乡土经验的基础上写就的,在那里随处可见的是他对家乡的热爱与向往,他笔下尽情讴歌的是乡野民间的人性之美与和谐之美,流露出对人与物生存状态的关注,对弱者的深切关怀与同情,以及对乡村民俗风情和神话传说的怀念和眷恋。而这无一不体现着作家深刻的故土生命体验,他注重对乡村内部的细致观察和耐心体悟,以特殊的人文情怀和审美眼光、道德立场等情感体验,呈现出一个带有个人印记的“余家沟”。“那是一方美丽的土地,一方让人无法割舍的土地。我把生命的根留在那里,佛坪成为我的情感故乡。好比一只风筝,无论飘得多远,都被那根长长的线牵着。那根线,便是由我对故乡浓浓的爱凝结而成。我对故乡的爱,就像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对待圣地麦加。”[1]1
白忠德的作品朴素平白,娓娓道来的叙述显得更加醇厚动人,读来犹如雨后秋菊,芳香持久却略带忧愁。他用客观公正的笔触叙述故乡的一切人与事物,并找寻出隐藏在故乡背后深刻的人文生态危机。白忠德的散文意蕴丰富,语言质朴优美,他以最真实的生命状态、最朴素的生活情态给我们展示最真实的情感体悟,全然没有造作和雕饰。“愿他一直走在‘缓慢地、吃力地、倔强地推进……再从从容容地享受’的路上,保持努力、沉着、向上的状态,和内心尤其难得的自足、自在与自若。”[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