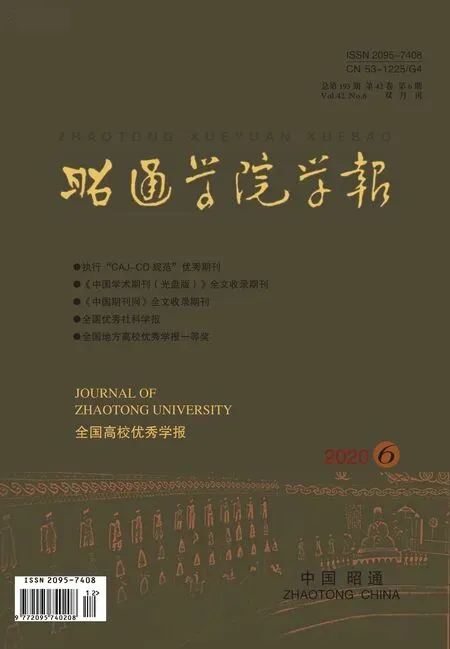废墟上的花朵
——陈力娇长篇小说《红灯笼》的死亡书写
2020-02-24黄大军
黄大军
(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黑龙江作家陈力娇的《红灯笼》(2019)是一部对历史与人性有着独特解悟与拷问的新历史主义小说。这部书被纳入复旦大学中文系“高山流水”文丛之一种出版,甫一问世就受到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该书堪称作家文学积累、生活阅历与创作颖悟的一次极尽升华,是其全部才情、心血、渴望与追求的高度结晶,因而在其创作序列中具有“扛鼎之作”的总结意味,同时它又是一部可以放在东北文学的群山之巅加以品评的力作。该小说讲述了建国后特殊意识形态背景下一群执迷于兵工与枪械的热血儿女为了坚持自己的梦想与信仰,在时代巨涛的拍击与裹挟下载沉载浮、血溅热土的悲情故事。作品具有地地道道的东北风味与历史氛围,从日常小人物的视角写出了一个时代的风云与凛冽,也写出了阴霾之下涌动的温暖与正义,尤其是从死亡感受与死亡意象展开的精神境域与空间隐喻,让我们不仅看到了大时代与小人物之间的复杂互动与权力运作,更让我们看到了大千世界为何一部分人注定要唱响自由的歌谣,而另一部分人却注定因逃避自由而毁灭。
一、作为否定的死亡
《红灯笼》写了特殊历史背景下日常生活世界的破坏与沦陷。它的典型症候就是人的非正常死亡。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走向了这个令人震悚的结局。死亡因而成为一个坚定的手势,一个表达作者是非爱憎的生命意象与核心意象。从故事人物的死亡结局来看,最早出局的战土改呈现的是一种无价值的生命终结形式,他是作者极端憎恶、蔑视的男性存在。他的人生悲剧既是时代铸就的,又是自我造成的。他的死与其说是个偶然,不如说是个必然。
从现实层面而言,战土改的死只是一个意外。在作品中,他是男主角之一,是乔米朵的丈夫,是战小易与战小莲的父亲。他在林业局工作,因欠单位二百元钱无力偿还,面临被开除的危机,他想去几百里地的枪厂工作,但怯于行动难以圆梦。于是,事业的不顺与理想的幻灭让他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沦为一个拿家庭与妻儿出气的施暴者,同时,他为了摆脱罪疚意识的纠缠,又渴望以受虐者的形象消解困窘。当受虐情结突然得到释放时,他顿时滑入苦闷厌世、颓废消沉的性格泥沼。不久,他即在沉默与抑郁下垮掉,成为疯癫世界的一员。当得知有人罗织罪名,连他这个疯人都不放过时,妻子乔米朵挺身而出将其藏匿,用安眠药拘禁其身心,但不料药性减弱被其逃脱,为了防止疯子泄密,为了保护密友李兰君不受侵害,乔米朵情急之下将疯丈夫推入了自家地窖,为了阻止他大喊大叫,又搬了一块大石头,“对着窖口砸了下去”[1]173。不想,石头太重,竟夺去了丈夫性命。从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来看,战土改不仅死于意外,而且死得异常窝囊。他原本可以不死。但他在作者笔下又焉能不死?
因为以这种死法结束他的故事来自作者对该人物的存在之思。可以说,战土改是作者在作品之中着重批判的两类“平庸之恶”的表现类型之一。这两种类型具体表现为:一类是以董大洪、副监狱长为代表的政治机器与统治工具,他们个人无思想,冷酷盲从,“平庸之恶往往隐匿于群体性之恶中”[2],作者直接将其塑造成扁平人物钉杀在耻辱柱上。另一类的极端代表就是战土改这类暴民,他同样无知与盲从,但寄寓着作者对群众运动更深层次的人性思考。作为陈力娇贡献给当代文坛的新形象,战土改呈现出圆型的人物特质,具有超越受害者与加害者双重身份的复杂性与象征性。他具有一些正面品质,比如酷爱兵工事业,一心想去枪厂工作,每次都拿出月工资的三分之一补贴他的母亲等,而且,他也是社会动乱的牺牲品,有令人同情的一面。但是,这些正面价值并不能为他的人性丑陋开脱与辩护。儿子战小易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男人有能力要在外面使,不能回家残害家人。”[1]110战土改人格闭锁、精神萎顿、心理阴暗而又充满破坏性。他不但不能肩负起家主之责,反而转嫁生存压力,以折磨、蹂躏妻儿为乐事。加缪说:“我反抗,故我存在”。当战土改自己折断双腿、匍匐在地时,他实际上就早已失去了主体、血性、尊严与存在。拉康曾言:“在遭受卑下的逆境时爆发的抑郁中产生的主要是固定在其形式中的致命的否定。”[3]104所以,陈力娇毫不掩饰地对这个人物表示了唾弃:“战土改是我最不喜欢的人物,不喜欢的程度达到了憎恨。”[1]275
二、作为仪式的死亡
《红灯笼》中有两位性格与命运都截然相反的孩子,这就是战小莲与战小易。他们一个保持了人性无尘无垢的本真状态,另一个则是被社会毒害、人性发生异变的孩子。战小莲既是作品中连接城市、自然与乡村三个世界的桥梁与纽带,又是整部作品中隐喻理想与光明的生命意象。作者发自内心地喜爱这个孩子,让其集美好、善良与聪慧于一身,让其在作品的悲剧氛围中闪动一抹光亮,当周围的故事主角相继沉入世界底部之际,战小莲则以失忆与失明为代价,实现了与社会之恶的根本诀别,从此踏上一条被爱与美环绕的上升之路,成为这个家庭中结局最好的一个成员,成为非常态社会中的终极救赎与最后希望。这是通过一种仪式化的死亡来实现的。
我们说战小莲的死亡是一种人生仪式,是从象征形式与象征意蕴角度着眼的。当战小易接受了成人世界的自私与暴力,并以此完成认同建构时,战小莲内在的善性与天性却仍在顽强的吐放生机。人性的生产与空间的属性是纠缠在一起的。陈力娇要拯救战小莲,就要重新组织她的空间关系。而在个人、家庭与社会的三元结构中,家庭无疑是最活跃的一个变项,它不仅内含着个体空间,而且也复制了社会空间。所以,要拯救战小莲就要首先拯救她的家庭关系。在作品中,与这种拯救相伴生的乃是作者对战小易异化人格的深度挖掘。在一个家暴成为常态的环境中长大的战小易,天性渐趋泯灭,主体成长过程中的原始侵凌性得到助长,成人的权力结构被恶意复制。为了让母亲能外出工作,生活不再那么贫困,他偏执地把根源归咎于小妹的拖累,并哄骗她来到荒郊野外,然后将其无情抛弃。孤独无助、弱小单薄的战小莲没能找到回城里的路,只能独自面对黑夜的降临和猛兽的威胁。途中,她用仅有的半块玉米饼和融化的雪水救助五只嗷嗷待哺的“小狗”,她将自己想象成它们的妈妈,但它们不是小狗而是被猎人捕获关在笼子里用作诱饵的狼崽。漫漫长夜迎来了它最恐怖的高潮。两只老狼悄无声息地绕过猎人的跟踪,机敏地救出了与战小莲一起熟睡的孩子们。它们没有吃掉这个可怜的人类孩子。但战小莲在暗夜里冻醒,因恐惧而长嚎,不幸被守候的猎人当作野狼猎杀。大难不死的她被好心的猎人救走,不仅从此失去了双眼,也因极度惊吓而丧失了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小莲的肉体固然没有死亡,但她从前的自我却不复存在了。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幅既齿冷又揪心的画面:战小易的恶让人震惊,战小莲的善又让人怜悯。“仪式是人类初年创造的一种精神性文化形态,它与神话有着密切的关联”[4],而死亡与复活则构成它的基本母题与信仰原型。战小莲的精神之死与重生也被作者纳入了神话与理想的框架。作者以童话的浪漫与神话的庄严构造了一个只属于战小莲的世外桃源,那里有因她的救助而对其不离不弃的小狼奶白,有勇敢护主的猎犬星星以及它的三个可爱的狗宝宝,这一切让她拥有了亲情之外更多的精神温暖。刘小波曾言:“在小说书写中引入幻想,产生的效果非同一般。”[5]的确,这个充满神性与生态魅力的世界是如此美好,奶白和星星超越兽类界线,呼朋引伴、相亲相爱,穿行于狼的世界与人的世界之间,并和人类的孩子战小莲构成了一个更大、更越界的生命共同体。作者用拟人的手法赋予这个世界以特有的轻盈与纯粹,让自然的世界成为批判人类世界的伊甸园。根据拉康的观点,健全的家庭和社会能够提供一个孩童成长所需要的“理想我”的镜像,帮助其顺利实现正向的成长认同,反之,人的精神创生就会遭遇障碍,不能有效完成从“自映的我”到“社会的我”[3]88的积极转变。战小莲的名字寄寓了出淤泥而不染之意,被猎人冯化一家收养后,改名冯捡花,她以这个新身份在另一个家庭、另一个社会中获得精神的滋养与成长的陪伴。新的父亲冯化具有男人的正直与善良,新的母亲文英具有女人的贤德与美好。冯家上下长幼和睦、幸福温馨。特别是误伤战小莲后,举家更是以赎罪、友善的姿态与自然、他人和社会平等共存、和谐相处。新母亲文英对孩子的照顾无微不至,带她背儿歌,尊重她和动物的友谊,想方设法送她去城里的盲人学校接受教育,将全部的母爱都倾注在这个命途多舛的女儿身上,让她真正成为一个全新的人,获得新生。
三、作为抵抗的死亡
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层次由低级到高级依次划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与自我实现的需要。前两者满足的是食、性、肉体等生物—生理层面的需求,属于低级需要,后三项建构了人格、意识以及智慧等人的主观体验与真实个性,属于高级需要。只有高级需要的满足才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与人性改进的方向。在个人目的与社会目的相龃龉的社会,高级需要的实现不仅没有外部条件,甚至可能引火烧身成为一种可怕的灾难,这虽是时代的可悲与历史的耻辱,却也无法摆脱无从回避。《红灯笼》中的李兰君、张刚、乔米朵与华晓绪就绞缠在这样一种现实与理想严重冲突、错位的矛盾之中。为了让自我实现的明星高悬于天穹,她们相互搀扶、彼此温暖、不畏牺牲,成为病态社会中挺立出污泥浊水的可贵的健全者。昆德拉说:“最重要的负担同时也是生命力最强烈的实现的标志。”[6]253李兰君们的大义与决绝让死水般的现实惊起了浪花、吼出了咆哮,较之那些在强权面前成片倒下的群氓而言,他们都用死亡捍卫了自己的挚爱、尊严与理想,从而见证了民族的骄傲,恢复着人生的伟大。
李兰君是作品中唯美与真理的化身,是与乔米朵素彩两映的另一位女主角。她有双重身份,一重是公共身份——泥城的京剧名角,另一重是匿名身份和私人行为——为国防研制新型无声手枪的“科研工作者”。作为艺术美的创造者,李兰君不仅外表芳姿绝丽,而且塑造“无论什么角色都能如雕塑一样刻痛人心”[1]117。她为泥城的人们带来了无限的艺术欢乐,同时也赢得了她们的信任、爱恋与保护。但在李兰君的少女心扉中,演戏还不能占据其全部,她还有一项高级需要就是制枪。由于大气候不好,后者不仅见不得阳光,甚至还可能招致杀身大祸。然而,出身枪械专家门楣的她,有着对这个行业的温馨记忆与特殊感情,那种挡不住的痴迷哪怕外压千钧也要破土而出。正如作者所评价的,“有着端慧的专业素质和孤绝的个性”的李兰君,她研发尖端、贡献非常,但生不逢时,她“没有左右世事的能力,同样也拒绝不了来自头脑深处灵感的实时投生”[1]273-,更拒绝不了时代对它的优秀儿女的无情毁灭,她的父亲已先落难,她也因自制枪支被污为特务、国民党间谍,这不啻是对那个人鬼不分的时代的莫大讽刺与尖锐控诉。马斯洛说:“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导致更伟大、更坚强以及更真实的个性。”[7]76李兰君就是这样。她清醒地知道个人与时代对抗的结果意味着什么,她理性、审慎地将研发的新成果托付于人,体面地走向了监狱。她在审讯室镇静、机智地应对副监狱长的暴力与摧残,在奄奄一息之际尚能奋起夺枪,以优美迅捷的姿势射杀仇敌。像演戏那样,以绝美与暴力的惊艳组合,为自我实现画上了生动的休止符。
李兰君是污泥浊世的那抹清妍,她执着地为理想而活,但她并不孤单,在她身畔还有华晓绪、张刚、乔米朵等挚爱亲朋为她而活。无论那付出的理由是真爱、是理解还是同性情谊,其无怨无悔的程度都不分轩轾。华晓绪虽贵为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却生就一副柔顺脆弱的性格,但他善良、忠诚,爱慕李兰君甚至达到了销骨蚀髓、不能自已的地步,意外得知其秘密后,他极度忐忑、失魂落魄,更深知自己软弱扛不住拷问,为了永守秘密,为了爱的意志,他泪眼模糊毅然决然地走向黑暗,用自杀、用血肉之躯永远地捍卫了这份珍贵。而这种伟大的牺牲与诀别,李兰君也只是在最后的生命关头,在同样不愿供出友人的时刻,才真正体会到,“她理解了华晓绪”[1]232,并第一次为他而流泪。加缪说:“所谓反抗,是指人与其自身的阴暗面进行永久的对抗。”[8]55从这个意义上说,可怜可叹的华晓绪也是反抗软弱的斗士、自我实现的英雄!张刚则反之。他军人出身,铁骨铮铮、侠肝义胆,酷爱枪支,志趣理想的一致,让他与李兰君成为心灵体己,他不顾个人安危,利用在机械厂工作的便利,协助其达成夙愿。他甘愿做“支撑李兰君的坚实的力量”,“把她当作了最近的人”,将她的事当成了他自己的事,并鼓励李兰君,“大气候我们把握不了,我们就把握小气候。”[1]190-191当他和李兰君一同沦为阶下囚时,为了严守秘密,他带进火药烧坏声带,成为哑巴,即便此时,他还想利用私人关系,帮助李兰君失音,也成为哑巴,希望他的朋友有一丝活下去的希望。此份真情,不能言传,深如地狱,高如天国,而它却无关乎男女,只关乎敬重!
四、作为正义的死亡
存在主义哲学家说:“谁自觉地走向死亡,谁就是自由。”[9]113在《红灯笼》中,真正自由而宁静地走向死亡的只有一位,那就是乔米朵。她的死不仅具有终结一个混乱时代的意味,更是一种为了女性情谊而选择的殉情。前者指的是她以带走自己儿子的方式象征性地斩断了恶由当下向未来的传播,后者指的是她要在另一个美丽而神圣的世界与李兰君再续同性之约。可以说,乔米朵以深沉的母爱与决绝的情爱证明着一个黑暗年代所闪烁的人性之光与道德之光。而她服食砒霜的自绝行为,更是在自己的宇宙与世界中开辟出一块晴朗,让至善至美的光芒从天而落,驱逐人间鬼蜮,普照山河大地,还人世以正义。
乔米朵不做命运与环境的奴隶而敢于赴死,这说明她已不属于那个年代中随风倒伏的芸芸众生,而是一个努力掌握自己命运的觉醒者。而生活在东北一个小城中的普通市民与家庭妇女在那样一个文化贫瘠、人人自危的社会中,又是如何获取这种人格转化与超越死亡的生命意志与道德力量的呢?从最具决定性的影响方面来说,这是通过乔米朵对李兰君的情恋认同来实现的,而李兰君在作品中则是作为真理与意志的正义化身而存在的,于是,乔米朵对李兰君的认同从本质上说就是对真理、美善与正义的认同。这样一条情感主线肇始于一个戏迷对名角的艺术认同,而终结于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灵魂认同。这种心心相印的美好情愫有几个转折与升华的节点。最初,乔米朵只是喜欢李兰君的戏以及她的美貌,对她所说的“就算是爱,也不能用命爱”的观点很不以为然,对“戏子无义”感到失望,而在心里坚持,“不用命爱那还叫爱吗?”[1]157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美是比任何语言都有力的推荐信”[10]38。乔米朵心中依旧放不下李兰君,还安排儿子保护这个“弱女子”。但李兰君的戏演的太好了,彻底征服了乔米朵,她心疼李兰君,敬她、爱她,她用白菜帮子和油条做馅给李兰君包饺子来表示心底最不能示人的那份隐秘情意,这种情意,“一生也许就生长一次,亲切,贵重,无价,百年不遇。”[1]167-168为了这份爱,为了能和在监狱“放风”时的李兰君见上最后一面,乔米朵将红火喜庆的大红灯笼挂上张天大院落中的高杆,自己则骑上屋脊放开歌喉,向着监狱方向的李兰君高唱《洪湖水浪打浪》,让李兰君能感受到自己的一番苦心,而在那个时刻,乔米朵也不再是乔米朵,她宛若李兰君,唱得完全是李兰君的水平,其音准和音高的相似度,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但是枪响了,红灯笼坠落了,正如有人所追问的,“不知它能否飘向我们的将来?”[11]
诗人里尔克坦言:“唯有从死才能透彻判断爱。”[12]251乔米朵对待密友李兰君深爱至此,她对待儿子战小易又何尝不是如此?虽然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爱——母爱。乔米朵与战小易之间从母子同心到母子离心的转变,牵动着整个故事的框架与结构。两者之间发生的破坏者与救助者的角色碰撞更是故事推进的根源与动力。而战小易从弑父到弑母的心理转移,则隐喻了一个少年在恶的社会中不断失落自身的质朴与纯真,最后被其吞没的人性异变过程。起初,战小易是站在母亲一边的,是她的好帮手,比如他帮助母亲反抗父亲的家暴,听从母亲的安排保护李兰君等等。但是这个孩子与其妹妹战小莲相比,因为年龄较大,受到的外界影响更深,自觉不自觉地就接受了外界的那套价值原则与行为方式。并且,在一个价值错乱、是非颠倒的社会,即便所行的是善事,所采取的形式也可能是有问题的。乔米朵就曾这样意味深长地告诫儿子,“人有时就是要装样子的,这样才能活得安稳。”[1]199这对于一个涉世未深、辨别力有限、家庭又是那样令人绝望的孩子而言,近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在家暴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战小易,创伤人格中结合了过多的不义、暴力、冷酷、自私、邪恶、非理性等负面东西。有人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每一种欲望都对应一种相反的欲望,是保持这种欲望,还是转向相反的欲望,往往就在一念之差。”[13]163而在一个“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不正常社会,战小易的亲身体验无处不告知他这一处事原则的颠扑不破。所以,他从葬送小妹到揭发李兰君,及至最后告发母亲。种种举动,看似匪夷所思,不符合孩子天性与人伦之常,实则正是极权主义扭曲人性、激发罪恶的必然逻辑,同时,这种对错误政治如何扼杀下一代的深入思考也代表着作者对此类题材的全新处理。
如上所述,《红灯笼》虽然写了各种形式的悲剧与死亡,让全篇呈现出某种尖锐、痛楚的叙事风格,但是只要环视一下作品中的死亡本身与死亡背景,我们就会发现,作品的死亡书写并不让人感到冰冷与绝望,而是充满恣肆的野性与蓬勃的活力,并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与文化理想主义情结。因为陈力娇笔下的死亡内含着伟大而崇高的精神质素,具有超越死亡的自然含义而向社会文化、政治伦理与人情人性多面拓展的丰富意蕴。在作品中,死亡首先是一种对恶的批判与清除,如战土改的死;死亡也是一种对善的温情呵护,如战小莲经历的仪式化死亡;死亡还是一种对不义社会的愤怒抵抗,如李兰君的死;死亡更是一种终结社会之恶的隐喻力量,如乔米朵母子的自杀。不仅如此,“在这一片人性的荒原中,人间最基本的怜悯和同情依然像草绿天涯一样顽强地生长,让乔米朵们也让读者不至于完全失去希望”[14],如热心救助乔米朵的齐补丁、盲人学校的刘文明主任、教乔米朵拆字的老学究、副监狱长李普利,尤其是抚养战小莲的文英一家,他们都以小人物特有的善意、真诚与勇气维系着传统人伦关系中最美好、最真挚的价值,让整个故事散射出温暖的火光。正是在如上方面,我们说《红灯笼》的死亡书写充满广阔深沉的人文关怀,带有坚定不移的历史理性,附着着美丽、宁静的神圣色彩!